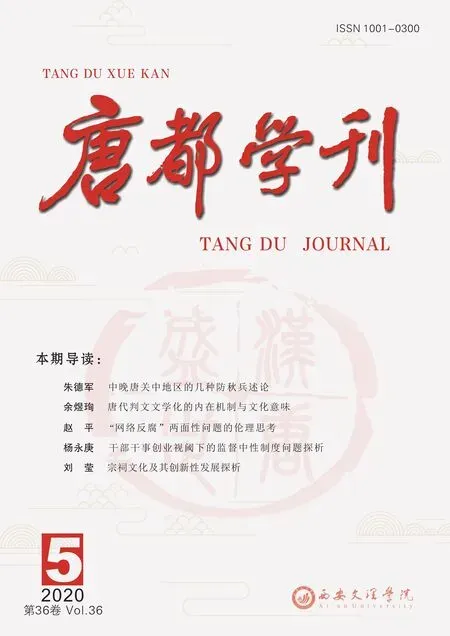审美“泛化”语境中当代审美价值观念的新动向
严红兰
(南昌师范学院 文学院,南昌 330032)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明显提高,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将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停留在实用层次,而是逐渐上升到“审美”层面,使日常生活披上一层审美光晕,变得美丽精致起来,出现了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开始逐渐增长,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之余,阅读小说、聆听音乐、观看画展等成为人们常见的休闲娱乐方式,使传统审美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等开始走向民间,走向大众,出现了一种“审美日常生活化”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审美与日常生活、生活与艺术之间开始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使审美走向“泛化”。正如有学者所描绘的那样:“美不在虚无缥缈间,美就在女士婀娜的线条中,诗意就在楼盘销售的广告间,美渗透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而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1]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的“泛化”
“日常生活审美化”本是西方学者韦尔施、费瑟斯通等提出的一个美学术语,用来形容西方后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一些审美泛化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也开始在中国出现。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
“日常生活审美化”,即“用审美因素来装扮现实,用审美眼光来给现实生活裹上一层糖衣”[2]40,使生活精致化、审美化。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实施,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不断提高,物质产品变得日渐丰富,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逐渐走出以往实用甚至简陋的层次,朝“审美化”、精致化的方向发展。首先,就“吃”的方面而言,俗语说:“民以食为天”,“吃”是人类首要的物质需求,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物质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加之人口众多,因此,国人的“吃”,尤其是普通大众,一般停留在实用层次,即能够填饱肚子、不至于使肌体处于饥饿状态即可,根本不敢指望能够达到“色、香、味”俱全的审美层次。可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副产品的丰富,人们对“吃”的要求开始提高,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不但饮食材料要美、饮食器皿要精致,而且饮食环境还要足够优美,甚至“诗意”化。这样一来,国人的饮食就开始超越温饱层次,走向审美。其次,从“住”的方面来说,以往国人对“住”多半停留在实用层面,对居住环境并没有太多的要求,一是因为物质的匮乏,二是因为审美观念的“懵懂”。但是,随着人们经济能力的增长以及审美意识的觉醒,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种花样翻新的新楼盘以及美化、亮化工程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形下,人们的居住环境变得“越来越美”了。此外,国人的其他物质生活需求,如服饰、交通工具、日用品也开始走出马克思所说的“粗陋的感性需要”层次而走向审美。“审美”的因子播撒到衣食住行、购物、休闲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出现了一股“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潮流。
(二)“审美日常生活化”
在经典美学观念中,审美关系指的是一种建立在人与现实之间非功利的、情感的关系,人们在美的欣赏与创造过程中无一不隐含着一种超越世俗功利需求的精神指向。其前提是要求人类从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功利状态超越出来,去发现自然、社会以及文学艺术等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美。正如德国美学家康德所指出的那样,审美判断不同于认知活动,也不同于道德活动,它是一种“不涉功利而愉快”的鉴赏判断,它发生的第一个契机就是审美主体必须摆脱主观欲念,以“纯然淡漠”的,即非功利的态度看待外界事物[3]。也就是说,在康德看来,日常生活是功利的,而审美活动是超功利,两者差异甚大。受其影响,经典美学理论往往十分强调审美活动的非功利性与超越性,以将其从日常生活分离开来,造成审美与日常生活、艺术与生活的分离。但是,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许多原先被视为高雅、脱俗的艺术作品开始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一些经典美术作品被大量复制,悬挂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的宣传面板上;经典音乐被当作背景音乐不时萦绕在人们的耳边;文学经典作品被改编成通俗影视剧,成为大众娱乐消遣的工具。审美和艺术活动不再局限于展览馆、艺术厅等场所,而是渗透到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街心花园、咖啡厅等日常生活场所。审美与日常生活、艺术与生活的疆界不再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出现了一股“审美日常生活化”潮流。正如陶东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艺术与商业、艺术与经济、审美和产业、精神和物质等之间的界限正在缩小乃至消失。”[4]
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当代审美活动已不再局限于经典美学、经典艺术的范围,逐渐走向“泛化”。
二、审美“泛化”语境中当代审美价值观念的“俗化”
“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审美日常生活化”等审美泛化现象的出现,不仅使人们对于审美、文学艺术的理解更加宽泛,而且还使当代文学审美价值观念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价值立场的大众化
在传统审美观念中,审美、艺术只是精英知识分子象牙塔中的一种“游戏”,普罗大众由于文化水平、生活条件有限,往往只能望洋兴叹。从中西艺术史来看,很多艺术,往往一开始源于民间,但随着文人知识分子的介入,他们从自己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出发,使之在形式上更成熟与完美,在内容上更深刻与厚重。这种从俗到雅的“雅化”过程,一方面使很多民间艺术、大众艺术变得更加高雅、神圣,被提升为精英文化,但同时又使艺术逐渐远离民众,最后成为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专利”。普罗大众的艺术、审美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审美日常生活化”之类的审美泛化现象出现以后,大众的艺术、审美权利开始得到重视。一些经典艺术开始借助现代传播艺术进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之中,这就带来了审美价值立场的大众化。正如金元浦先生所说,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审美日常生活化”现象的出现,“‘原先只为小众’进行的艺术创作,现在必须用现代的复制技术和市场手段传播开来,让社会能够更为广泛地最大限度地接受、了解和享用,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需要。”[1]王德胜也在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辩护时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意义在于它“在不断提升人的感性利益与满足过程中,进一步张扬了人的日常生存的感性权利”[5]。
由此可见,随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等审美泛化现象的出现,表明当代审美价值观念的价值立场开始从精英转向大众,变得更加“平易近人”。
(二)价值取向的世俗化
经典美学由于把审美视为一种超越世俗功利需要的审美体验,因此在价值取向上更侧重于审美对于个体的终极关怀作用,甚至把它视为对抗世俗功利社会、维护个体精神世界的纯洁性与超越性的武器。许多中国现代美学家都是如此。在朱光潜先生看来,现实世界是一个“密密无缝”的功利网,一般人无法挣脱这张网,总是被“功利”二字“系住”;而“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功利关系而独立。在创造或是欣赏艺术时,人都是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家到绝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因此,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6]。对此,当代美学家叶朗先生做了进一步阐释:“由于审美活动的核心是审美意象的生成,所以审美活动可以使人摆脱实用功利的和理性逻辑的束缚,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审美活动有可以使人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和有限意义,获得一种精神的解放。这种自由与解放使人得到一种欢乐,一种享受。”[7]也就是说,从经典美学的角度看,由于文学艺术营造了一个超功利的“意象世界”,可以帮助人类暂时脱离现实世界,忘却世俗生活的烦扰,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解放与自由。受其影响,许多当代美学家,包括童庆炳、王元骧等都比较强调审美的终极关怀作用。童庆炳曾多次指出,文学艺术等审美活动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超越时空的艺术世界,人置身于其中,往往会变得兴奋、忘我、全身心投入,对于对象物最为敏感,最具有感受力和想象力,最少功利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是人生的节日”[8]。王元骧先生也认为:“审美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它不带有个人占有的性质,一座雕像耸立于广场,一首乐曲传播于大厅,不仅人人都可以欣赏,而且在欣赏过程中,还可以使人们从各自原先的思想情绪中摆脱出来,超越了一己的喜怒哀乐,共同为这些美的东西所吸引、所陶醉、所欢娱……这种完全以美本身为追求对象所生的愉快乃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愉快,只有当人摆脱了一切由物质利害关系所生的粗野性的情欲的支配下才能产生。”[9]但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之类的审美泛化现象出现以后,这种审美价值取向开始被改变,有学者开始强调审美的世俗关怀价值。为维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合理性,被誉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三驾马车之一的王德胜先生,自2003年以来,发表了《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教授》等论文(1)参见《回归感性意义——日常生活美学论纲之一》,载于《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美学的改变——“感性”问题对中国美学的意义》,载于《文艺争鸣》2008年第9期;《“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为之“辩护”。这些文章虽然具体内容不同,但其观点基本相似,即从审美的感性维度出发来理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内涵及其意义。他指出,在当代日常生活中,正在出现这样一种美学事实,即“审美”开始冲破经典美学所强调的理性主义的藩篱,不再“仅仅与人的心灵存在、超越性的精神努力相联”,而是“极为突出地表现在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视觉性表达和享乐满足上”,这意味着一种以“视像的消费与生产”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正在崛起[10]。对于这种“新的美学原则”,王德胜先生认为,不应从经典美学,尤其是理性主义美学的角度加以批判,而应看到它在恢复美学的感性维度以及张扬人的感性生活权利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其理由主要如下:首先从美学本身来看,感性就是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后来,人类出于对感性警惕与鄙视,“希望通过理性权力的实现来驾驭感性的发展空间”,从而使美学一步一步滑入“理性”的轨道,并建立起强大的理性主义美学理想体系。在这种强调理性的美学体系中,人的感性受制于理性的压制,因此得不到合理的尊重与实现[5]。其次,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感性本来就是人性的维度之一,具有“内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而在中国过去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系统中,人的感性生活权利不是受到道德理性的压抑,就是被政治诉求所遮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常生活审美化”具有吁请人们关注当代生活的感性现实、还原感性在人的生存和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等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由此可见,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出现,当代文学审美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从终极关怀价值转向世俗关怀,出现一种“俗化”趋向。
三、关于当代审美价值观念“俗化”趋向的评析
对于当代审美价值观念的这种“俗化”趋向,我们不能简单地给予肯定或否定,而应联系其历史语境,对之进行辩证分析。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当代文学审美价值观念的这种“俗化”趋向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因为,虽然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确实还有些地区的人民群众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他们的日常生活可能还停留在实用阶段,并没有进入“审美”层次,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不可否认在一些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那里的一些市民已经开始追求“日常生活审美化”。他们对日常生活的追求不再满足于温饱、实用阶段,而是讲究生活的品位、格调,总是努力把自己的衣食住行等打造得更为精致、美丽。并且在闲暇时,他们还会进行一些艺术活动,比如听音乐、参观画展、看电影、阅读时尚杂志等,使艺术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前者可以视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后者则可以说是“审美日常生活化”。这些审美现象,无论是在价值立场还是在价值取向上,都迥异于经典美学所倡导的“超越性”与“非功利性”,它们主要表现为一种世俗关怀,即对人的世俗层面的抚慰与满足等。在这种情形下,当代文学审美价值观念必然走向世俗化。
其次,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趋向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我们的文化体系偏向于理性,对人的世俗欲望等感性一面的需求总是采取遮蔽甚至有意压制的策略。在封建时代,我们的主导文化是儒家文化。这种文化体系的特点强调“以道制欲”“以理节情”,其总体思路是以道德、礼教等理性武器来节制人的世俗感性欲望,以免它泛滥成灾,引来人性的失衡、社会的动荡。到宋明时期,儒家文化逐渐发展为一种具有唯理主义色彩的“理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口号,个体的感性生命欲求得不到起码的尊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状态,外有西方列强的入侵,内有军阀混战、党派纷争,身处这样的乱世,性命尚且得不到保障,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审美日常生活化”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观,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因此,人民的生活基本挣扎在“温饱线”上,人们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求尚且不能完全满足,更何况“审美”。因此,从这个角度看,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而出现的审美价值观念“俗化”趋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肯定人的感性生命欲求,使之从长期以来被压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恢复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它把美感混淆于快感,导致审美价值取向的浅俗化甚至庸俗化。诚如某些学者分析的那样,美学虽然最初被命名为“感性学”,但美学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感性,还包括理性;美感也不仅仅包括感官层面的愉悦,而是包括生理、心理、精神等多层次的愉悦。正如当代美学家李泽厚所说,审美应分为“悦耳悦目”(耳目愉快)、“悦心悦意”(内在心灵)、“悦神悦志”(超道德的人生感性境界)三个层次,“是生理性与社会性、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与积淀”(2)参见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91-499页。。因此,美学作为一门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学科,它所研究的“感性”恐怕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感官层面,而应该上升到精神层面,做到感官愉悦与精神愉悦、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的目标。由此可见,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中,那种把美学等同于“感性学”、审美价值理解为人的感官层面的愉悦的价值取向是片面的。这种价值取向虽然看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审美泛化现象在促进文学艺术等审美活动走向普罗大众、“张扬人的日常生存的感性权利”[10]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却忽略了审美在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愉快、精神的自由与超越方面的价值。这实际上将美感降为快感,结果可能导致审美的庸俗化与粗俗化,使人滑入一种一味追求感性享受的享乐主义的泥沼之中,带来人性的片面化。由此可见,那种大肆宣传“日常生活审美化”并陶醉其中的观点和做法是不够理性的。并且,就中国目前而言,随着社会物质产品的丰富,人们的感性享受意识不断增强,社会上已经出现了感性欲望的膨胀、理性精神的缺失等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大力提倡“日常生活审美化”,不但容易使审美变得浅俗化,恐怕还会进一步激起人们的感性欲望,使人性进一步朝着感性享乐的一面沉沦。正如赖大仁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将审美学意义上的感性解放悄然替换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感官欲望的放纵,人的精神美感下降为动物式的官能快感。当代审美观或审美精神的这种滑落,显然已影响到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审美价值取向。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必将使审美活动中的感性与理性重新失去平衡,这不仅会造成审美本身的异化,同时也将导致人性的异化。”[12]而且,这种审美观念往往是根据物品的外观形式的漂亮、美丽而做出的判断。从美学角度看,这种美只是浅表层次的美,它往往作用于人的眼睛、耳朵等感官层面,很少深入到人的精神、灵魂层次。因此,童庆炳先生把这种美学成为“眼睛的美学”[13]。因此,我们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只能说审美活动的浅表化,它所提供的更多是一种感官的愉悦,而不是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越。并且这种审美泛化现象还容易引起人们审美疲劳,导致人的审美兴趣和能力下降。正如当代美学家张世英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美有低层次和高层次之分:低层次的美,就是声色之美,好看好听。还有高层次的美,就是心灵之美,心灵之美就体现了美的神圣性。我们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就是在声色之美的背后缺乏心灵之美的支撑,也就是说,缺乏一种超越现实的高远的精神境界。”(3)转引自顾春芳《美感的神圣性——北京大学“美感的神圣性”研讨会综述》,载于《美育学刊》2015年第1期。
二是它忽略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背后所隐藏的消费主义与“伪民主”因素,在价值立场上也存在问题。如果从根源上分析,当今社会之所以出现“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审美泛化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商家无止尽的求利动机。一些商家为了使产品卖出更高的价格,用各种手段来包装商品,使商品变得更精致、漂亮;更有甚者把商品和人们摆脱实用需求、追求诗意生活的潜在需求联系起来,致力于营造一种“生活艺术化”的氛围,使自己的产品以“审美”或“艺术”的名义卖出更高的价钱,获得更丰厚的利润。德国美学家韦尔施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类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都服务于经济目的。一旦同美学联姻,甚至无人问津的商品也能销售出去,对于早已销得动的商品,销量则是两倍或三倍地增加。”[2]7由此可见,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实则是商家的一种用审美来装扮商品的经济策略,其背后潜藏着一定的功利目的,目的是使人们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之中。所谓“消费主义”指的是自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由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而出现的一种不断追求消费、消费至上的意识形态。消费本是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而实行的一种单纯的交换行为,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商家为了扩大再生产,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不断通过广告挑起人们的消费欲望,激起人的相对需要,结果使消费从一种单纯的物质行为变成一种操控人的精神意识的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和功能的复杂行为。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们陷入了对物质产品符号价值的无止尽追求当中。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有限的,而商品的符号价值,由于涉及身份、地位等,却是无限的。而事实上正是如此。一旦某种商品,无论是小到一块香皂、还是大到一处住房,只要披上审美、艺术的外衣,与使用者的身份、地位联系起来,其符号价值便陡然增长,价格成倍上涨。对于这种商品,普通老百姓往往由于经济实力不足而只能望洋兴叹了。正如童庆炳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对于一个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的国家来说,对于一个还有许许多多人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国家来说”,多数国人的消费水平还停留在实用层面,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恐怕只是少数富裕阶层生活中所出现的现象,并不具有广普性[13]。言下之意,这种“日常生活审美化”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深层次的不平等,并不是审美、艺术的真正民主化。并且,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如果过多地宣扬“日常生活审美化”,恐怕会更多地激起人们的消费欲望,为消费主义的盛行推波助澜,其价值立场是值得商榷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加辨析地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不但可能加剧大众的感性沉沦,还有可能无意地在为商家做广告。这就难怪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质疑:“当我们在这里谈论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时候,我们是否要一味地为那些少数的企业主和大商家作理论广告?我们是否要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中作一个选择?”[13]
由此可见,当代文学艺术审美价值观念的“俗化”趋向是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审美泛化现象而出现的必然结果,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这种趋向也可能带来审美价值的浅俗化、人性的片面化等问题,给当代文学艺术以及审美文化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我们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和方法,既要看到其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又要提防其负面效应。正如有学者强调的那样:“我们当前提倡生活艺术化,这很好。但是把生活艺术化降低为艺术功利化,单纯地炫耀一些声色货利之类的东西,而缺乏深沉的高远的精神境界,让人沉溺于低级欲求之中,把一切都变成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这种缺乏神圣性的所谓美和艺术,则是我们不应当提倡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