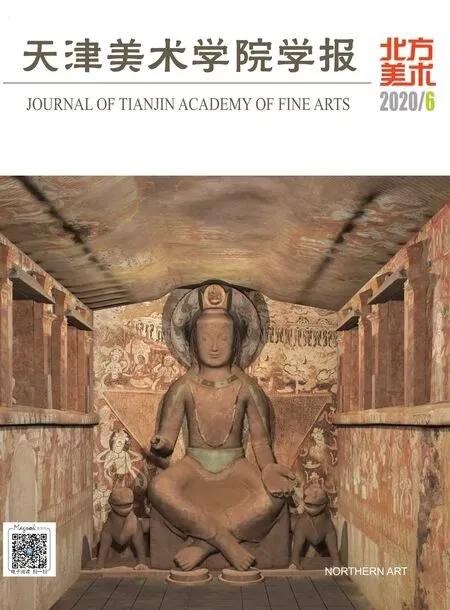神圣与解构:从内丘神码论原始文化艺术表达中的模糊性问题
鞠高雅/Ju Gaoya
纸马,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民间艺术,以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为人所知。从其进入主流学术视野以来,各地陆续发现的纸马有数种之多,其中,内丘神码(或称“内丘神马”)以其独特的造型和内涵,展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风俗魅力和活力。
2006年,内丘神码被列入首批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魏进军被列为内丘神码传承人。“与其他地区的纸马(神码)作品相比,内丘神码所饱含的质朴、原始的生命力,更具有穿透人心的特殊魅力。”[1]68从艺术类型看来,内丘神码是中国民间木刻版画的一种,属于民间艺术。它在内丘地区的流传历经数百年历史,其所绘人物的服饰衣帽特征可追溯至宋元时期,而魏氏神码的传承情况则在600年以上,自明洪武年间始有记载。它的缘起有许多成因,包括中国民间由来已久的儒、释、道精神和泛神论传统,宋元以来的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和隋唐时期以来的雕版印刷技术的完善等。目前,内丘神码作为一种“活”着的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依旧在内丘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销售也不局限于内丘本地,甚至可以远销到周边县市。但如今的内丘神码,机器印刷已经取代了绝大部分的手工印刷,连唯一的传承人也已经开始使用机器进行神码生产。[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载体和民间文化传承的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的重要作用。2017年,十九大报告将“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纳入坚定文化自信的一部分。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因此,除了从政策保护、行业开发、文化传播等角度对内丘神码展开切实工作之外,对其内涵、价值和发展动力的探讨也十分必要。如今,包括各地方政府、文化产业行业、美术及考古学、文艺界在内的众多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已经开始从各个角度对内丘神码进行解释研究。本文基于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对原始宗教信仰的社会学研究,从“模糊性”这一概念入手,着重分析内丘神码作为一种原始宗教信仰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其内在的矛盾和发展内生动力之间的关系。
一、内丘神码的文化独特性
内丘神码是原始民间信仰的一种图腾化、视觉化表现,其原始造型特征明显,古朴稚拙,大胆抽象。这种古朴率真源于其悠久的历史,当地先民对远古自然力量的敬畏,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朴素认知。与现代抽象不同,内丘神码的抽象化表达更类似于简化,并且带有明显的中华文明特征——讲究神似并且注重对称。此外,作为一种与信仰有关的文化风俗和现象,内丘神码也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性:艺术造型上的多变随意,选材技巧上的因地制宜,内容传承上的开放活力。
(一)造型形象的多变随意
内丘神码上的纹样往往作供奉和祭拜之用,因此大多刻绘的是原始神灵的形态、样貌。但有趣的是,即使都有揭神码、贴神码和供奉神码的习惯,同一文化圈内部的不同群体对神码的认知却可能不同,距离很近的两个村落,村民认可的神灵外貌、形象也会有所差别。这种随着地理空间分布而产生的差异显示出了内丘神码造型上的多变性。不仅如此,在时间上,随着村民生活状态的变化,内丘神码中的“神”还在不断增多,更新换代。村民会根据自身需求,敦促工匠创作新的神码,而新神码的创作方式也较为简单随意,完全靠工匠即时的临摹和创作。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拖拉机神码、摩托车神码,以及近二十年来出现的汽车神码等都是如此。这些不断演变、进化的新神码的出现,往往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推广有关,具备明显的时间属性,与空间属性一道,构成了内丘神码源源不绝的内生活力。
最开始只印几种老版,后来有的贩子拿样稿来要新样,我们就刻版,年年添年年刻,多年下来品种慢慢增加……八九十年代我新创一些品种,像拖拉机神、摩托车神、汽车神都是我自己添的……记得有一年贩子来要拖拉机神,我没有样稿,专门用照相机照了相,照相的时候拖拉机上的人戴着鸭舌帽,我原样给刻下来……[3]70-74
(二)选材技巧上的因地制宜
与其他非原始化的宗教信仰相比,内丘神码对于神灵的艺术化呈现方式要求不高,规则性不强,程序也并不繁复。所有流传下来的制版、印刷工序都是以制码本身为目的,不存在问卜、择日、沐浴净身、焚香祷告等程序要求,对工具、颜料、刻绘的顺序等也没有相应限定。从总体而言,其制作不拘小节,方式方法多变,选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用性极强。“内丘神码的制作者大多为木匠,没有经过专业的美术训练,他们大多采用单刀直入的手法,大处用凿,小处用刀,随意性较大,变化也较为丰富。”[4]
如果关键部位,就要重新刻,其他小地方坏一点不影响用。……过去的颜料是就地取材,自己制的,黄颜色是槐米制作的,绿色是琉璃湛,红色是石榴花做的……我做刀柄啥木头都用,就地取材,有槐木、枣木、泡桐木,枣木的最结实,所以我用得最多。[3]72-73
(三)内容传承上的开放活力
民间艺术源于生活却不脱离生活,因此很多民间手工艺人并不把自己的工作看作艺术,也不把自己制作的作品当作艺术品,艺术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内丘神码更是如此,它的传承方式简单、开放,以前多作为手艺人的谋生手段在家族内部传承,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乡土文化的弱化,这种家族传承的方式也逐渐开始松动。
刷码子是跟我义父魏桂堂学的,我们印码子不保密,谁都可以学,可从来没有外姓人来学过,都是家传……20岁结婚以后我媳妇算是我第一个徒弟……我想传给下一辈,他们学艺还可以,但都不愿意干……[3]70-75
因为缺乏作为艺术的自觉,所以内丘神码的传播、传承上带有明显的与时俱进的特征,一直以来,与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相适应,这也是民间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类型的本质原因所在。这种特性导致了至少正反两种后果。首先,自觉性的缺乏,使得内丘神码在内容、形式、技巧方面的规则性不强,内容流变极大,并且以口口相传为主,相关资料、记录保存困难,善本较少并且极易散轶。但从积极角度而言,作为一种始终与生活相通的“活”的艺术,内丘神码的自洽演变性很强。群众基础深厚,因此创造力和活力也远非其他艺术形式可比,很容易在短时间内通过日常生产生活、休闲娱乐等方式传播、流传开来,并且为人喜闻乐道。这种优势使得内丘神码具备与众不同的商业价值,当然,也可能带来时间、空间和创造力上的局限。“我们始终认为,离开了生存土壤的民间艺术已不能称为民间艺术。那些‘被限定的民间艺术’对于民间艺术本身是‘历史的终结’,内丘神码作为民间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其‘历史没有终结’。”[1]69
二、内丘神码演变的矛盾与动力
(一)粗犷与严谨:符号化的神
内丘神码在造型形象上的多变与随意,就现实层面而言,简化了它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和习俗的传承和传播过程,降低了它被不同地区、群体接受的困难程度。但就形象本身而言,多变和随意化恰恰否定了造型本身的意义,是对神的形象的高度概括,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达。
(出徒)得刻版刻不出什么毛病,线条要匀,粗点细点没关系,主要是匀。……刻版里面眼睛、鼻子和嘴巴最要注意,这几个刻好了,神就活了。……老版印刷的时候,如果眼睛磨平了没有线条了,就扔了不再用了。[3]70-73
对线条粗细的不看重、对除了面部之外的其他部分的容错度等,都说明神码中的“神”的形象往往是被整体图样中的某些特征所勾勒出来的,对于当地村民而言,这些重点部位的意义要远大于其他细节。这也解释了神码随时间、空间而出现的形象变化问题。可以说,神的形象在内丘神码漫长的制作、售卖和使用过程中,被匠人们解构并提炼出来,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在文化研究层面,符号化、解构化本身是一种否定化,它使得内丘神码尽管作为一种信仰,却不像其他宗教信仰中的“神”一样具有“神圣性”“超脱性”,这种以非神圣化工具敬神的现象令人费解,同时也是内丘神码的原始性和神秘性魅力所在。
(二)解构与神圣:原始宗教生活中的模糊性
与神码造型形象的“多变随意”“符号化解构”和“非神圣性”相反,内丘人民对于神码的虔诚敬畏,以及对与之相关的风俗习惯的坚守却百年如一。首先,那些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的神码(如土神等)的造型不能变,需要依循旧样;其次,画面必须整洁、清晰、匀称,否则不能售卖;最后,不同的神码有不同的张贴位置、讲究和供奉规矩,每位村民都熟知并按规行事。
(刻版)都要根据老样来,如果刻新的人家不认,认为你这神仙是假的。印样稿的时候刷墨要匀[……]印得不清晰算坏了,画面外留边不匀称也算坏了……[3]72
(没有神马的话)过年的时候就自己弄张红纸写几个字,路神就写“供奉路神之神位”,喜神就写“供奉喜神之神位”……一般家里头“天地”最主要,贴在院里的天地桌上,桌上摆放香炉和供品……灶王爷贴在灶房里[……]底下有一只鸡和一只狗,我们贴的时候都得叫那狗朝外边,鸡朝里。就是说狗朝外边为了驱邪,鸡就是吉,吉祥往家里边来……[3]70-71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矛盾现象?对于内丘先民和如今的当地村民而言,这种截然相反的逻辑背后隐藏着一以贯之的潜层意识吗?事实上,粗犷或者是严谨,解构或是神圣,这一悖论并非仅仅存在于内丘神码之中。大部分原始艺术及原始信仰都具备这样的矛盾特征,法国学者涂尔干在研究人类原始信仰的论述中曾将其概括为原始信仰的“模糊性”问题。
三、模糊的面目:神码背后的“模糊性”问题
最早提出宗教的模糊性概念的学者是英国学者威廉·罗伯逊·史密斯,而法国学者涂尔干则基于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丰富了对“模糊性”这一概念的解释。他提出:“事物之所以具有神圣性,是因为它就是集体情感的对象。”[5]566集体情感可以赋予事物以意义,其价值在于这种意义本身,而非它的承载物。涂尔干据此说明了原始宗教信仰中的圣物与祭祀、供奉与共享、模仿与纪念等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圣物既会因为“神圣”而被人敬仰远离,又会因为“神圣”而被用以屠宰和祭祀,贡品在被用来奉神的同时又可以被人分食……这些表面看来互相矛盾的行为背后,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转化逻辑,这就是神圣事物本身的“模糊性”逻辑。
其一,在同一种原始信仰中,具有相同构造和结构的单一仪式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如斋戒既可以用以表达赎罪和悔过,又可以被看作一种值得推崇的积极品格。这是因为仪式本身的意义是将人的心理和情感调动起来,因此,在原始宗教生活中,最初的目的和意义并不重要,使人的心理情感发生变化才是仪式的价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张贴神码之后,明明各人的境遇不同,喜怒哀乐依旧,但却无人追究,来年依旧会欢欢喜喜地揭神码“请神”回家。因为就本质而言,人们想要通过敬神而获得的东西,在敬神行为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得到了。当然,这类行为必然带有一定的共同行为的特性,因为对个人的情感调动往往缺乏感染力,只有当人们被集合起来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在进行着同样的仪式的时候,仪式本身才能体现更多的情感价值,成为民间风俗被保留下来。
其二,对人而言,所有的神圣事物都具有根源上的相通性。造型的形象或者抽象、美观或者恐怖、解构化或者精细化,只要与人的日常生活拉开距离,那么其造成的心理冲击力是一样的,而最终引发的行为后果也相同——那就是观者内心的敬畏交加感。敬或者畏,向往或者恐惧,这些意识都是“客观化了的集体状态,是社会本身的一个方面”[5]565,因此,对神的形象的解构化和神圣化、尊敬与不敬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它们的后果也是相似的。此外,也由于这种相通和转换性的存在,很多时候,不同的神码可以象征相同的寓意,例如仓官和粪神也都可以用来寄托人们对粮食丰收的企盼,日常生活中彼此互斥的要素也可以被一起供奉,如内丘人在祭拜火神的同时也祭拜井神和行雨龙王,人们对于神码的种类、形式、新旧等百无禁忌。正是因为它们带来的心理和情感价值的同根同源,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泛灵论在世界各地的原始信仰族群中普遍存在的原因。
总而言之,内丘神码作为一种带有明显原始色彩的宗教信仰产物,正是与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的密切关联,造就了它的原始性,保留了它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在当代社会的内在发展动力。但也正是这种生活化和原始性,为内丘神码的发展和现代化带来了困局,文化表达上的“模糊性”正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对内丘神码的“模糊性”问题的解读,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内丘神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为其将来的内涵挖掘提供了新的思路。当然,模糊性只是对这一现象的一方面的解读,还有更多其他的角度(如实用主义角度)等亟待研究者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