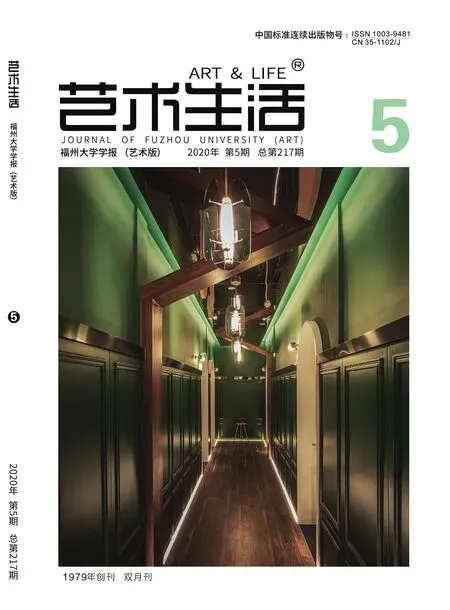新媒体传播视域下微纪录片叙事模式的公益价值探究
庄君 杨尚仙
(辽宁师范大学 影视艺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19 世纪末,世界电影诞生伊始,包括卢米埃尔兄弟的《工厂大门》《火车进站》在内,电影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领域中,几乎均以纪录片形态进入媒介范畴,同时也奠定和呈现了纪录片的早期雏形。如果说弗拉哈迪《北方的纳努克》的问世,正式打开了纪录片世界的大门,那么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纪录片拥抱以移动化、视频化、社交化为特征的新媒体而孕育的“微纪录”或许可以作为纪录片发展的新节点,微纪录时代正式到来。
在新媒体传播语境下,微纪录片也以其独特的叙事模式和传播手段迅速成为网络视频流量的主要入口之一。新媒体微纪录片对网络环境中受众心理与审美观念的影响,对社会文化、公益价值的传递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微文本叙事的人文内核
微纪录片是广义纪录片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它继承了传统纪录片真实美学的视听艺术规律,但在新媒体网络媒介环境下,又衍生出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特征,主要表现在微纪录片叙事形态上的“微叙事”。这种“微叙事”是在新媒体特性与网络时代受众审美认知心理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具体表现在微时长、微选题、微视角三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微纪录片最重要的艺术内核:以人为本的情感表达与现实关怀。这一点与传统纪录片的人文表达又有所不同,微纪录片主题更简练、集中、直接,这成为了微纪录片特有的名片。
本文所指微纪录片是指伴随着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基础的传播手段的发展,以互联网、手机移动网络为主要传播途径,以新媒体网络平台为主要生产者或专门为新媒体网络平台制作,并以其为主要传播途径的短时长纪录片,片长从几十秒到十几分钟不等的纪录影像。
微纪录片有限的时长使其必然不能按照长纪录片的叙事模式进行充分铺陈、全方位纪实;较之宏观的历史性、社会性、人文性选题,微纪录片更倾向于选择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件、小人物,通过微视角下的小人物、小事件来书写纪录历史和社会现实。微时长,导致了微选题,而微选题,则促成了微视角。微视角下的影像文本,通过镜头细微化的呈现,将选题放大,呈现在观众眼前。
这些人物、事件是受众熟悉、了解的,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微纪录片使得身边人、日常事通过影像纪录进入网络传播,与受众拉开一定距离,离开日常生活,进入审美视野,并再次被接受。这种接受过程使得受众觉得既亲切又陌生,产生影像观看、文本阅读的审美兴趣,颇具意味。而其中所渗透的人文意蕴,所包含的价值观、生活观等自然而然易于被受众—主要是网民—所接受。
《国旗下的演讲》里班金初身患眼疾,父母早亡,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却始终保有对知识的渴望。自立自强的奋斗生活、求知的诉求、求生的信念,这种朴素而坚韧的生命和生活观既被阅读,更被接受和传播,形成群体性的价值观认同。《不能结婚的妈妈》中,年过六旬的张雨霄为了照顾自己的25个孩子、9个孙子孙女,毅然投身到“SOS 儿童村”,选择终身不嫁来照顾他们。她放弃成为某一个孩子的母亲,而将自己的母爱放大,成为了许多孩子的母亲。微纪录片中那些普通而又平凡的纪实影像,通过平民化的视角呈现在观众面前,使得全社会的焦点聚集在有灵魂、有生命力量的人物身上,体现出一种广泛的人文性社会关怀。
二、预设的叙事主题
微纪录片人文性话语的表达是通过其显性的预设性叙事主题传达出来的,主要体现在叙述者内聚焦叙事的个性化表达、“花哨吸睛式”的标题形式这两个方面。传统纪录片在对影像主题的处理上,往往遵循较为深刻、含蓄的处理方式,创作者不会将主题赤裸裸地摆在观众面前,而是需要观众通过影像中客观纪实的镜头、中立又理性的解说使观众实现对主题的领悟。而微纪录因其时长短、选题小、视角集中,往往采取短、快、直接等并非常规纪录片审美的叙事手法来呈现尽可能明确、清晰的视听内容,表达出相对完整的叙事主题。
这种策略首先表现在叙述者的变化。在微纪录片的叙事中,影像画面往往会伴随着主人公作为叙述者的旁白,可被看作热奈特内聚焦叙事的一种颇为直接的形式。申丹在其《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一书中讲内聚焦徐思清晰地称之为第一人称内在式焦点叙述。这种叙事模式中,叙述者即人物,他不仅可以参与事件全过程,填充微纪录片有限的影像内容,又可以离开作品环境而向读者进行描述和评价,微记录的叙事视角直接用任务旁白以声音呈现。
叙述者这种直抒胸臆的主观情感表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主观性介入客观纪实,但也避免了据理论说和逻辑陈述所可能带来的乏味,是以一种或温和、或抒情、或调侃、或娱乐、或愤慨、或痛心、或惋惜的心灵沟通的方式,在情绪和情感上直接感染受众。这种以被摄主体第一人称的自我叙事方式,并没有破坏叙事的真实性、纪实的客观性,反而使得叙事产生另一种真实意味,由现实真实升华为情感真实,或者精神真实的双重真实。微纪录片创作来源于传统意义的纪录片,又对其有所创新,这种发展呼应了普通受众所共有的心灵呼声的愿望,呈现了多元化社会个体的生存状况,肯定了个体价值,体现了更普遍的人文性关爱。
微纪录片预设主题还体现在其命名策略上。长纪录片为符合其含蓄主题的叙事法则,追求客观性,片名通常以叙事内容或题材中的具体对象直接命名,有很多都是名词命名,如《高考》《幼儿园》《老头》《故宫》等。而微纪录片的叙事传播基于新媒体语境,面对信息庞杂的网络环境,一部微纪录片要想不被大量同类或相似信息瞬间淹没,就必须采取特定的传播策略—命名。
微纪录片命名以形容词居多,体现情感上的倾向性与感染性,以“花哨吸睛式”的标题来吸引受众眼球。如二更视频里的《大城小爱》《家能快乐》《粉红粉红的少女心》《暖心姜糖》等。以高刺激度信息在极短时间内吸引观者注意,勾起观者进一步了解详情的好奇心和兴趣。另一方面,这种显性的片名,相比较传统纪录片标题,更是一种简洁直观的,甚至“摇旗呐喊”式的对叙事主题的价值宣扬。片名中“大”“小”“暖”“粉红”等具有价值判断、情感倾向的用词本身即是微纪录片主题的概括,也是对每一个被记录的个体的价值评判和人文价值传递。
三、泛审美化的价值表达
(一)从日常生活到泛审美化叙事
周宪教授在《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文化视觉转向的一种解读》一文中指出,“一种新的‘视觉文化’已经崛起,其显著的特征乃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趋向于美化,视觉愉悦和快感体验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1]。这种“视觉文化”所指包含基于媒介影像下的“拟态现实”,媒介不仅提供人们信息的认知,塑造人们的意识形态,构建人们的价值观、是非观,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观,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受众的学习认知习惯和审美心理。这种习惯不再是口语式的、文字式的、广播式的,而是视觉的、图像的,是一种对受众视觉进行刺激从而形成的认知习惯和审美心理。如果说传统纪录片还有着泾渭分明的艺术审美范畴,那么微纪录片时代则打破了这条界线,呈现出泛审美化的价值表达。
英国社会学与传播学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在其《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最主要的特征是消解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变成艺术的同时,艺术也转换成了生活,从而达到了艺术无所不在的境地,呈现出审美泛化的趋势”[2]。微纪录片中大量出现的生活化纪实短视频题材,不仅涉及时尚达人、都市美食,还有底层边缘的务工者、小人物以及寻常的民风民俗、市民食客等。多样的生活形态、细枝末节的生活场景,在构成微纪录片审美化叙事主体内容的同时,也丰富和延伸了微纪录片的审美范畴,呈现出泛审美化特点。
艺术来源于生活,微纪录片的叙事主体便是现实生活,是泛生活化气息的日常生活。“二更”视频的口号是“发现身边不知道的美”①,将我们耳闻目睹的生活场景搬上微纪录片。代表性微纪录片《白毛煎饼》中北京老人30 年如一日做煎饼,《张桥再见》记录上海最大棚户区拆迁前的景象,《扫帚的艺术》姐妹俩传承手工扫帚制作工艺等。微纪录片的叙事焦点与审美主体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遗迹、有着独特艺术价值和艺术风格的艺术作品、有着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名人大家,亦或是具有深刻社会学研究意义的底层民众、弱势群体,而是充满人文性、风土性、社会性、草根性、时尚性等无所不包的日常生活的民众百态。煎饼里有着老人坚守与执着的馨香,张桥城中村有几代人的生活痕迹与社群风貌,扫帚是姐妹日常生活的持家手艺和生活初心。微纪录片似乎使得一切事物都具有了审美性和审美价值,如杜威所说“回到对普通或平常的东西的经验,发现这些经验中所拥有的审美性质”[3],微纪录片成为人们发现美的“眼睛”。微纪录片泛审美化的最大目的不在于审美性,而是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或许这便是微纪录片给这个时代最大的礼物。
(二)泛审美化叙事中的“审丑”
席勒《论悲剧艺术》中谈到:“我们的天性有个普遍现象,就是忧伤、可怕甚至恐怖的事物对我们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苦难和恐怖的场面,我们既排斥,又被其吸引。”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因创作主体的社会角色和其所属媒体(通常是电视台或电影厂)性质,出于社会责任下传播效果与社会影响的考虑,对纪实题材与纪录片主题进行取舍,选题严谨但所涉题材范围有一定限制。而微纪录片由于其相对宽松、自由的媒介平台和网络环境,相对而言具有更广泛多元的选题范围,在呈现出叙事上泛审美化倾向的同时,也对生活与现实中非主流的、不美好的、“另类”的人与事件进行了记录与呈现。罗森·克兰兹在其《丑的美学》中指出:“吸收丑是为了美而不是为了丑。”是否可以推而试论,上述另类的审丑也可能成为泛审美化的延伸。
在当下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审丑文化中,由于审丑对象的边缘化、另类性,审丑主体的大众化、草根性,使得审丑在某种意义上就具有了某些反崇高的美学意味。另一方面,审丑是对边缘化力量的重视,是对被压制和否认的事物的言说。微纪录片的审丑性叙事,使得人们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以一种新的视角对现实进行重新审视和辨识,从审丑中获得审美的满足。《男催乳师的困惑》记录了男性催乳师这一职业的尴尬处境;《盗亦有道》中专偷贪官的“女盗贼”又是否在行侠仗义;《女同性恋的自白》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性取向,追求所爱的同性伴侣。微纪录片打破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单一视角认识、判断和评价事物的习惯与心理,这些或特殊、或不为常规认知接受、或在现实生活中被看成“丑”的个体、或被诟病的对象、或被社会忽略的少数群体,进入微纪录片叙事视野。微纪录片对于“审丑”对象的叙事,通常采用双向多维,一方面简单直接地对叙事对象的“丑”予以呈现,另一方面对背后的不完整、深层次的原因予以揭示和说明,使得以往人们眼中纯粹的“丑”,进入有深度的审美视野,变得更具认知价值。比如,男催乳师尴尬的背后是人们对男性的僵化认知定式和刻板印象。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人的内心声音可能很难被听到、被理解,因为“丑”的自我表达往往无助而又无力,但微纪录片通过对“审丑”叙事的提炼与处理,使得“丑”不再仅仅是一个被人们表达和言说的对象,而是拥有着自我诉说和自我表演的权力。
四、理性狂欢与社会意识形态建构
(一)微纪录与狂欢化语境
巴赫金指出:“大众传播中的狂欢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由民众自发性组织的,具有反叛性和颠覆性的大众文化意义的狂欢。”[4]而在新媒体传播语境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手机移动终端的普及,打开了普通大众进入传播媒介的门槛,使得每一个受众都成为了新媒体时代的主角,每一个受众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自媒体”[5],每一个受众聚集在新媒体这个狂欢广场上,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参与社会话题,抒发个人观念,标榜人生态度。微纪录片诞生初期,是网民拍客将日常生活中有趣的人或事记录下来,并上传到网上供人娱乐欣赏的自发性活动,我们将其称之为UGC②,即用户内容生产。
在这个时期,微纪录片的传播主要由传播者个人兴趣和个人传播诉求驱动,目的只是基于新媒体时代狂欢化语境下,满足个体意识的树立与娱乐至上的自娱需求。这种狂欢化背景下的“微记录”是盲目的、具有随意性的、传播效果是有限的,甚至有些人刻意为了营造奇观化、吸引眼球的作品,而去拍摄或是编造一些耸人听闻、不真实甚至不健康的影像,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在经历了“微记录”短暂盲目的狂欢化阶段,以PGC③模式的微纪录片时代很快来临。在PGC 模式下,微纪录片的制作更加精良化,选题上往往基于受众诉求,更加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在生产制作和传播机制上呈现出多样性、类型化特征,聚拢了庞大的受众人群。在UGC 模式下,受众出于自身话语表达的渴望与需求,受限于缺乏寄托个人情感的优质内容平台,便采取主动但又盲目的狂欢化行为,利用新媒体所提供的“公共领域”,将生活以记录的形式置于狂欢广场之下,供众人娱乐。在这种媒介语境下,人们下意识寻求释放和满足网络“力比多”,并通过形形色色的狂欢化内容得以自我满足。而PGC 模式下生产的微纪录片因为其专业性、真实性、传播的规范性,某种意义上带有了民众意见领袖、审美引导的色彩。
巴赫金的“狂欢”堪称是乌托邦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状态的统一。受众基于现实生活,从PGC 生产的优质微纪录片中获得一种情感上的亲近性与心灵的慰藉。这种狂欢从主动到被动,从盲目到理性,从自我宣泄到自我认知,使“异己”的世界变成了自己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别人身上照见自己。微纪录片成为了一面镜子,打破了以往狂欢之后的虚无状态,让每一个人回归本真的生活现场,寻找到自由的精神归宿。
(二)微纪录与社会文化传播
20 世纪的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一章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出“媒介即讯息”[6],认为真正对社会和个人产生影响的并不是媒介所提供的信息,而是媒介本身,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会直接促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这放在21 世纪依然受用。微纪录片作为新媒体媒介技术下的产物,决不仅仅是传统形态长纪录片中所体现的文化形态,而是适应网络文化发展的一种新的微纪实文化现象。微纪录片有限的故事内容,使得微纪录片不得不专注聚焦于单一主题,无法像长纪录片那样传达出多义性的主题解读,但这种单一性却可以使得微纪录片的“微记录”以一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般的叙事方式将主题直接传达出来。
“微纪录”在影像表达上追求细腻、感性,同时略具有夸张的艺术特征。在镜头语言上,乐于运用特写、大特写、微距拍摄等特殊景别,将被摄对象的局部放大和突出强化,使观看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人或物的细节,拉近了观者与纪实影像的心理距离,实现了“微记录”“大主题”的表达。《最忆是杭州》中通过导演张艺谋的视角来观看为准备G20 杭州峰会水上音乐会表演所做出的准备与付出,为我们呈现杭州西湖美轮美奂的风景与新时代下中国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唤起我们的爱国心与民族自豪感;《网红时代:我要成名》男生整容十几次,为挣学费酒吧扮舞娘,只为支撑起父亲离去后的破碎家庭,网红外衣之下,有着寻常人同样的艰辛和不易;《致敬每一颗匠心》里幸福匠人KIKI 是一名普通的婚礼策划师,但用心、用情地为每一对新人送去祝福,专注做热爱的事、专心尽份内的责,也是对工匠态度最朴实的诠释。这种微纪录片通过镜头聚焦当代中国的多元社会与多样人生,记录大时代下形形色色的个体,从小处着手,致力于发现身边的美,传递能量,传播朴素、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理念,从多样的“微纪录”文化中,观照出一个富有时代感的“文化中国”。
微纪录片是适应网络媒介发展的新形态纪录片,它对网络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有机补充和丰富,一方面弥补了大众传播语境下传统纸媒和影视媒介对现实观照与表现的部分空白;另一方面也应警惕其存在对网络不良文化的迎合和附和,需要有所引导和规范。历史是当下的镜子,纪录是现实的影子,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微纪录片的艺术性、媒介价值、审美意蕴和思想价值应更好地加以挖掘;传播当代文化,传递民众声音,微纪录片应该能够以其以小见大之所长成为映照现实的人类生存之镜。
注释:
①“二更”是较为成功的原创段视频平台,成立于2014 年,2015 年注册为“杭州二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二更”原意是指每晚二更时分发布一条原创短视频,其口号是“发现身边不知道的美”。
② UGC 即User Generated Content,也就是用户生成内容,也就是内容由互联网用户原创。
③ PGC 即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专业生产内容,与UGC 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