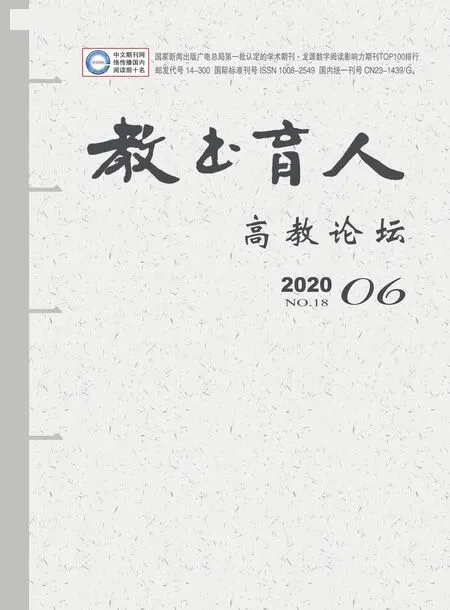教育品质与大学治理结构的科学重置
——基于体制规制错位与治理结构失措的视角
徐战平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育学院)
教育品质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打破学缘校缘派系团伙区块链,改善大学组织治理现状,需以“关键少数”的问题治理入手。教育组织治理结构问题,不仅涉及教育基质问题,也关系到教育领域政治生态问题。
基于拉动经济与改善大学入学率双重因素考虑,1999 年始,我国大学急速扩招,扩招产生的一个负面问题就是目前饱受社会各界舆论诟病的贴牌类大学带来的大学教育阈值熵增问题。
教育熵增的直接动因是学校招生规模扩张太快,更深层的因素则是教育治理的伦理困境问题。
一 治理结构失准与管理失措
“高校内部治理改革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1]。
自二十世纪初,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所产生的各类大学呈光谱状,贴牌大学办学模式也是国际高等教育主流国家通行的办学模式,但从产权关系角度来讲,所有权不清、治理结构规制错位的大学出现则罕见。
所有权是决定一所大学治理结构性质与状态的根本,出资主体没有实际出资,管理资源形成的商誉价值没有评估依据,是造成贴牌大学治理结构失控失准的体制原因。治理结构失准,体现在具体管理上,就会出现各种重大失误与失控问题,某贴牌大学,建校仅几年,在政府解决债务审计中,出现3000 多万账实不符问题;建校多年不建财务档案室,以抢工期为名,利用10 多亿银行债务完成的基建投入没有完整的基建基础账目;某过亿基建项目,完成多年后做结算,结算时,乙方要求与第三方评估出的工程总价竟相差近一倍;完全由学费与银行贷款支撑的财务模式,一年三公经费高达上千万元。
“破窗效应”进一步演进的动因是,制造各类管理重大失责失误的负责人,不仅没有被追责,而且带病升迁。当前管治这类贴牌大学的主要法规即《民办教育促进法》,但这类学校事实上又无民办性质,治理结构规制错位,“假民真公”,使这类贴牌大学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重“家规”轻国法的治理现状。
二 基本体制规制错位与治理结构的伦理困境
贴牌大学形成的建校模式,是利用异地政府划拨的土地做质押,由银行贷款建成,这种模式称为“市场举办”模式。由于没有财政资金投入,这类院校被规制为民办性质,事实上这类学校举办主体没有任何民办成分,用于银行贷款质押的土地,按我国相关法规,所有权、处置权在国家一级,所以银行贷款形成的建校资金实则是用国有资产质押权形成的暂时负债,就是说,这类院校既没有《公司法》意义上的实际出资人,也没有事业单位意义上的实际出资,在国家事业单位注册管理机构注册学校时,程序上必须要有的注册资本环节也是用暂借的资金过账完成的。虽然在注册章程中必须注明举办主体一是划拨土地的当地政府,二是被操办该校事宜的筹备组利用的名校本身,但从出资决定量化所有权比例产权清晰的角度认定,这类学校的所有权归属是无法具体量化的,这种名义上民办实则公办形成的“假民真公”学校,且又无法认定出资比例的教育机构,不仅在教育组织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一般成立的正式组织中也是见不到的,虽然以“创新”的名义诠释这类学校,但这种创新从组织体制归属角度具体合法合规的“新”在何处还有待探究。
由于产权不清、政策规制错位,这类贴牌大学在建校初期,在治理结构、运行模式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特性与规律,与传统方式形成的学校或产权清晰的学校有着本质的不同。比较国有公办(所谓体制内)大学,政府主管部门相应监管体系成熟,大学管理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处在相应法规与政府相关机构的管控之下,如对教育投入的各类专项资金,特别是涉及基建投入与大宗采购方面,发现问题,政府审计机构随时可以进行监察性质的专项审计。反观“假民真公”类的贴牌大学,几乎在各个管理的重大环节都处在仅依靠地盘码头性质的“自律”治理。
抛开产权关系不对称等结构问题,作为一所新建高校,治理复杂度远高出运行成熟的大学,没有一批具有高度公心且德才兼备、管理内行的干部,很难保证在学校建成初期设计的运行模式不走入“地盘码头”性质的模式,事实上,导致贴牌大学产生深层问题的另一主要原因,反映在管理干部派出的层次上。新建院校办学层次与原校差距较大,所以具有对称能力的优秀干部很难派出,干部力量的空缺,为迅速占据管理各个关键岗位的“团团伙伙”的滋生,产生了最大的发酵空间与间隙。
体制规制错位是造成治理结构失准的主要原因,没有成熟体制的监管,由自然人利用政策机遇发起的贴牌大学自然隐藏着私欲动机,加之被贴牌学校管控上的低能与责任心低下,一些贴牌大学出现严重的“圈子文化”现象,政治生态遭受“污染”,“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2]。
利用云计算、信息技术手段控制团伙组织区块链成为教育问题型组织羽化团伙力量的新特征。网络技术不仅影响了各类组织政治生态净化问题,信息技术突变,也改变了传统的组织行为学、领导科学众多理论的基本假设。团伙力量在控制组织形态与治人方面的高效性,使其在利用现代技术方面不择手段。事实上,一所大学,如果在组织各关键节点的岗位完全由团伙力量控制,辅之以网络技术、电子技术工具,的确对任何不在团伙之内的其他组织领导都可产生绝对的隐形伤害能力。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长期持续实施的“影子伤害”使具有高度责任心且“想干事能干事”的领导心理长期处在崩溃的临界状态,从而失去正常的工作意志与决断能力。顶层领导“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的心态为政,团伙势力对组织中层、基层、关键岗位、工作节点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渗透与分节控制,高层再出现权力真空或黑洞,在这类组织中,“形式主义”“圈子文化”“团团伙伙”成为大学“治理”的“主旋律”。
基本体制规制错位,使“假民真公”类的贴牌类大学的运行脱离了相关法规与制度框架约束,本质上是行驶在教育法规与制度的灰色地带。
三 私欲共识的团伙区块链与组织政治生态清明治理问题的解决
在一个教育组织内,如果建立在学缘校缘或地区缘等圈子团伙组织区块链形成,控制该组织的隐形力量羽化成型。团伙区块链的组织纽带是团伙私欲价值共识机制,形式上的连接纽带,主要是类似于反腐彻查出的“西山会帮”,即地域性连接纽带,个别地区偏好拉帮结派、搞关系的地域文化,成为支撑团伙组织区块链形成的重要的地域习性文化基础。
处在团伙内的成员,无论行为、品质如何,会受到团伙力量在各种荣誉称号与学术地位方面的培植、推送,出问题会得到及时的保护,处在团伙成员外的教师或职工,没有任何实质性组织权益而言。羽化成型的团伙区块链在组织构造与对外伤害能力方面的精密性与隐蔽性,一般教育组织的正面力量很难与之抗衡。在这类组织中,坚持原则不妥协的领导或教师,最终结果轻则遭受排挤,重则遭受“制度清洗”。
熵值迁移到组织行为学中,其定义为衡量一个组织治理结构的混乱与低级程度,一个组织的熵值越大,其团伙政治的色彩就越浓,两者互为因果。病灶组织区块链形成的最大“功效”,就是当影子组织缔造者与实际控制人利用人为设计出的组织管理的巨大漏洞,个人赚的“盆满钵满”并带着各种功臣符号志得意满的隐退后,组织自身教育功能却陷入一个外表光鲜亮丽实则沽名钓誉的漫长的高熵积状态。
熵积的过程,也就是团伙区块链深植教育组织治理根部的团伙势力侵害教育品质与正派教师职业安全与稳定性的组织生态恶化过程。这个持续恶化的过程具有高度的隐蔽性与周期的漫长性。即使发现问题,对这种广泛深植组织根部的机体“癌细胞”问题,也难以根除。
“关键少数”,指组织领导或组织事件起因的领导者。
治理结构失准的贴牌大学,组织生态拓普环境演化规律扭曲且复杂,病态组织生成机理根源归昝于“关键少数”责任心与管理动机上。
“‘关键少数’在净化政治生态中的角色、职责和净化政治生态在我国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净化政治生态必须抓好‘关键少数’,抓‘关键少数’,就抓住了净化政治生态的核心群体、关键群体和‘领头羊’。”[3]
没有执行与落实层面的保障,所有纸面上科学、合理、严谨的法规与制度都可以视为一纸空文,经常出现在贴牌大学高层管理会议与领导述职报告中反复强调的制度管理、依法治校,在我国大学组织行为语境里,到底能否解决当前问题还值得探究,因为实证检视的所有深层问题,都长期掩映在“科学”“合理”“制度”“法规”“创新”“特色”等高频词的语境之下,就是说,团团伙伙、圈子文化与精心打造“分赃式治理结构”的“关键少数”,恰恰是操弄形势主义最高调的人群。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
“教育传承过去、造就现在、开创未来,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4]大学现代治理结构的核心,首先要保证的是“关键少数”的清明廉政,要选择那些真正德才兼备、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干部,大学现代治理结构重置的核心,就是建设一支专业素养高、领导能力强、政治品质可靠、道德修养有底线的领导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