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互联网+公募”改变了谁?
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南方周末实习生 何玄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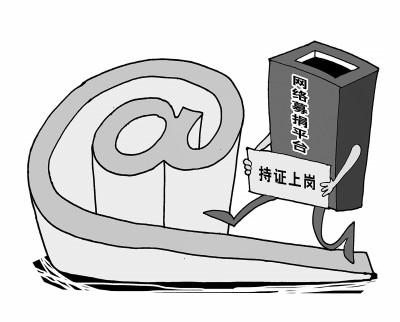
2018年,民政部依据慈善法指定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共为全国1400余家公募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2.3万条。 IC photo ❘图

民政部门指定这些平台,是希望帮公益组织破圈,找到更多潜在的捐赠人。“通过大家高频使用的软件,更容易让公益活动和大众建立连接。”
对于小型的公益机构而言,首次触网,有了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机会,五年来,互联网筹款成为他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每年的99公益日、95公益周,都是大大小小公益组织惦记的事情。
梁海光最近在琢磨一件事,作为一家公益机构负责人,他如何向楼下便利店、餐馆、商场推广一个互联网公益项目。简单来说,就是在合作的店里放上一张海报,“每笔成交都会捐赠1元给XX项目”,消费者自主决定选择哪个支付工具,如选了“消费捐”,每笔消费便能捐1元支持公益。
捐款额最低为1分钱,可以和店家商量。梁海光的小算盘是“只要一天捐十几笔1元就好。”这种捐款是一种新的互联网募捐玩法,由一家互联网企业推出,在线下为公益项目筹款。
细心观察,近年来,大众身边有不少此类“互联网+公益”项目,在日常生活,鼓励公众进行小额捐赠。
最近几年,梁海光所在的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满天星”)不断尝试互联网+公益的新“玩法”,从大型的腾讯“99公益日”,到淘宝公益覆盖上万商家的“公益宝贝”计划,这些“玩法”有效地支持了满天星的公益项目执行。
而这些“玩法”,发源于民政部于2016年、2018年分两批指定的20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互联网公募平台”)。从腾讯到淘宝,20家互联网公募平台做了不同的技术尝试,让公益与大众产生密切联系。这种联系难以估量,据民政部数据,2019年,20家互联网公募平台全年为全国公募慈善组织发布互联网募捐信息2.3万条,获得超过百亿人次的关注和参与,网络募捐总额超过54亿元,同比2018年增长70.4%。
为此,2020年11月3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遴选第三批互联网公募平台的通知,将稳步放宽互联网公募信息平台的指定范围,原来20家指定的互联网公募平台将增加新成员。
但同时,面对到处出现的公益劝募,也有人提出疑问,这样的互联网公募平台究竟怎么遴选?过去五年,互联网公募平台又如何改变公益慈善捐赠模式,同时产生了哪些问题?
慈善法的产物
在2016年慈善法公布前,“互联网+”概念已是很红火的概念。
联劝网创始人王志云记得,那时大大小小的公益筹款平台特别多,“有商业公司试水的,也有小部分慈善组织发起的”。
联劝网由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联劝”)发起,该基金会2009年成立,2014年正式更名为联劝,定位是“面向公众筹款”。
据王志云介绍,早在2011年,联劝前身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已与商业公司发起的公益基金会合作,试水互联网筹款。但那时,他们发现,商业公司对平台核心数据很敏感,不愿向公益组织开放捐赠数据。“大腿不好抱”,王志云决定自己搭建筹款网站,留存捐赠数据,以做筹款支持,因此在2015年5月联劝成立了联劝网。
彼时,在互联网风潮下,涌现出一批小型公益垂直领域的独立捐赠平台,如联劝网、公益宝、火堆、路人甲、善园网等。
2016年,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多家基金会发起成立公益筹款人联盟,据该联盟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截至2016年底,公益类第三方线上平台超过30个,但商业领域的公益捐赠平台依然为主流,其中腾讯公益、蚂蚁金服公益和淘宝公益三大平台的现金捐赠占比连续三年超过七成。
2016年3月,慈善法颁布,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为此,民政部成为互联网公募平台的监管单位,需要指定符合资格的信息平台发布募款信息。该信息平台基本要求是平台要有影响力,运营主体是社会组织,具有相应的互联网信息服务资格,从技术角度能够为募款服务。
据公益时报报道,2016年5月13日,距离慈善法正式实施还有三个多月,原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后更名社会组织管理局)组织了认定标准研讨会,邀请了新浪、百度、腾讯等十多家互联网服务商参与研讨。
当年7月20日,民政部发布通知,将以“遴选”的方式制定慈善组织公开募捐信息平台。遴选被认为是比制定标准然后开放申请、认定相比,更为快速的方法。
当时,王志云和同事意识到,如果不申请,联劝网将列入非法募捐平台。他们随后着手准备申请事宜。这一过程并不繁复,依照民政部设定的表格填写申请,经过两轮资料筛选后,入围的平台将面对专家组的评选。
据王志云回忆,她代表团队一个人参加专家评审会,在台上做了20多分钟的介绍,再接受专家质询。如今回忆评审场景,王志云感慨,当时“遴选的标准更接近摸索状态”,二十多位专家坐在台下,各有各自感兴趣的领域,实务型专家注重提问平台的运行管理和定位,她记得当时“实务方面问得比较多,因为实践两年,我们可以讲得更细”,但也存在一些申请的平台“还没有进入运营状态”。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作为当时专家组成员之一,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最初专家的想法。当时,他们重在考察平台是否拥有“做公益的能力”“做互联网平台的能力”。专家们对于遴选标准没有太多异议,其间他们很注意程序公正,专家们独立提问,独立打分,不交头接耳,政府官员则仅主持程序,不表达意见。
公益寻求破圈
最终,从首批申请的47家平台中遴选出13家,进行公示。这13家包括腾讯公益、淘宝公益、蚂蚁金服公益、新浪微公益、轻松公益等商业公司公益基金会发起的公益筹款平台,联劝网也成功入选。
2018年1月,民政部第二次遴选一批互联网公募平台,最终形成20家的格局。其中,11家为互联网企业发起,公益平台如联劝网、公益宝仅有5家。对于这些平台,民政部要求提交年中报告、年度报告,接受质询、评价、约谈,此外,平台每半年要接受全国慈善工作主管部门考核1次。
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负责人叶盈认为,民政部门和参与评审的专家在评选这些指定平台,是希望帮公益组织破圈,找到更多潜在的捐赠人。“通过大家高频使用的软件,更容易让公益活动和大众建立联结”。
而现实中的捐赠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以2018年民政部对互联网公募平台的年度考核情况为例,20家平台共为1400余家公募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2.1万条,募集善款总额超过31.7亿元。其中腾讯公益、蚂蚁金服公益、阿里巴巴公益三家平台总占比已达到89%,分别募款17.25亿元、6.7亿元、4.4亿元。
在此次考核中,联劝网被列入结合自身特色、成效显著的第一梯队。但在前几年的考评中,联劝网都遭遇专家追问,“怎么总在服务上海?”“为什么都是联劝基金会的项目?”
王志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被追问后他们倍感压力,随后两年向民政部提交的平台运营报告中,都提及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拓宽合作伙伴的数量和覆盖面。”
五年来,公益募款在“互联网+公益”的推动下有了巨大变化,各个互联网公募平台依据不同的特性,创造了与公众联结的差异化场景。
对公众来说,劝募的花样越来多见了,可以在社交软件上捐步、捐树,也可以在网购商品时,选择有公益项目的商品,包括梁海光所惦记的“消费捐”等线下募捐。叶盈认为,这些商业平台有巨大流量与资源,给公众带来了更多的启蒙和倡导,相比筹款本身,具有更大价值。
对于小型的公益机构而言,首次触网,有了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机会。互联网筹款成为他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每年的99公益日、95公益周,都是大大小小公益组织惦记的事情,参加或不参加,怎么参加,怎么筹款,都在深入地影响公益组织乃至行业的发展。
梁海光回忆,2015年首次参与“99公益日”时,“什么都不懂”。当时机构也小,专职人员仅有七个人,“分到传播筹款只有1.5人”。五年后,满天星公益的筹款传播人员已组成6人团队,正式筹款时线上线下都有相关的活动,增加与捐赠者接触的机会。
浙江省微笑明天公益基金会传播负责人申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互联网公募平台基于其技术优势,为小型公益机构提供各种筹款工具,还有各种财务批露、项目进展等实用模板。同时,他们在过去几年的互联网筹款动员中,联结到一批公益伙伴,这些伙伴在今年的抗击新冠疫情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筹款的异化
以商业公司公益基金会为主的互联网运营平台对公益行业来说,一方面看到强力推动,但另一方面是身不由己的“异化”,“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陶传进发现,这级年,各家平台都在或快或慢地推进规则建立,其中最为有趣的是借助于“99公益日”筹款平台而制定与改善,不断被磨合中的规则体系。而围绕着“99公益日”,这些年,公益行业内不断有种种争议和抱怨。
2016年起,叶盈注意到一些被她称为“筹款异化”的现象,包括公益机构以返利的形式,雇请“筹款志愿者”;配捐带来的套捐问题;个案筹款作假行为;资源大量倾向于筹款能力强的机构,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也看到了有人试图钻空子、平台则修改规则、加强技术监控的模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复磨合。
叶盈认为,腾讯公益平台目前依然是门槛最低、对中小型民间机构最为友好的的互联网公募平台,只要能挂靠,获得公募资质,都可以在上面筹款,恰恰是因为其短时间内卷入大量资源,客观上催化了公益慈善行业的种种问题。
2020年“99公益日”结束后,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会等七家机构联合举办“在数据更深处追问99公益日”线上专题讨论会,实务界代表、专家学者、媒体观察员共同参与讨论,腾讯公益的配捐规则是否会导致公众款项流向少数具备高度组织化、有大规模动员能力的机构。
此外,一些公益项目“比较小众”,难以短时间在网络平台获得大众关注。大理白族自治州云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心的“世界有猿份”项目,倡导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该中心执行主任阎璐发现,没有前期对项目的整体了解,这样的项目很难募款。更有公益组织负责人质问,如果我们仅仅以筹款为目的,是否失去了公益的“初心”。
“关键是过于追求筹款额和捐赠人次”,叶盈说,中国主流互联网公募平台基本依托于大型商业互联网平台,在运作逻辑上天然遵循商业的交易逻辑,也就是追求筹款额和捐赠人次,目前互联网平台推出的功能、设计的激励机制也多是围绕这两项商业标准。
叶盈认为,当公募基金会、公益组织、平台都以“筹款额”和“捐赠人次”作为筹款成功与否的标准,会弱化公益行业自身强调的价值。
而王志云所关心的捐赠人数据,过去几年依然锁在互联网公募平台。每次筹款后,公益组织能在后台看到捐赠流水信息,但没有具体的捐赠人名字及联系方式,他们只能在这些基于大型商业互联网平台的互联网公募平台上定期发布项目进展,无法与捐赠人建立联系和互动。
叶盈理解这种做法是商业互联网平台出于用户数据隐私权和安全的考虑,捐赠人数据平台是否有权开放给公益组织、公益组织获得数据后能否合理使用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但王志云和更多公益组织希望捐款本身能实现公益目的,成为公益倡导的第一步,与捐赠人产生更多的互动。
用脚投票
2020年7月,在2020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致辞指出,近3年来,中国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每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
鉴于网络筹款的增速,民政部于11月开启第三次遴选互联网公募平台,此次遴选不超过10家平台,申报截止日期为12月10日。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遴选新增了公众评价环节。据悉,民政部将通过开放网络评价的方式,鼓励社会公众参与评价,期望增加平台遴选的开放性和公开性。
公告发出后,公益慈善行业的从业人员纷纷猜测,短视频领域的商业平台将申请加入第三批的募捐平台,看完短视频能够随手捐赠公益项目将成为可能。
陶传进发现,在过去五年,民政部授予合法性的互联网筹款平台已经在多个方面发挥作用。面对新的遴选,陶传进建议应以支持的视角来帮助平台,看到互联网平台在自身范围内的创新举措、特有的运作技术与手法等等,借助专业化的视角挖掘、总结互联网平台特有的价值。
陶传进将互联网募捐平台的社会价值分为四个部分,筹款仅为其中一个部分,此外,公益资金在社会中发生的作用,通过规则建构规范社会公众以及公众倡导和公共动员,都是互联网募捐平台的价值。
他认为目前20家平台在这四部分各有优势,随着更多的平台被认定,平台服务的市场将被细化,受益人、公益组织、平台将能够彼此选择。
事实上,更多的公益机构在用脚投票。他们逐渐意识到不能依靠单一的互联网平台的单次筹款,有的机构开始创立自己的月捐制度,有的机构开始寻求更新的互联网手段,“擅长用短视频的公益组织可以关注短视频平台。”梁海光说。
满天星公益2017年开始加速建立机构的月捐制度,邀请捐赠人每月定期捐赠任意数额,而非一次性捐款。满天星每月向捐款人汇报项目进展、财务披露,也邀请捐赠者到项目地,和当地的孩子一起阅读等等,进一步加强公益项目与筹款人之间的连接,打破以筹款为目的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