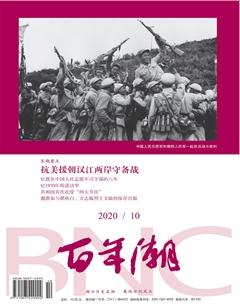忆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八年
阮家新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局部战争,是我军同世界上最强对手的一次较量,对中国、对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战争期间,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做参谋工作,从1950年10月21日进入朝鲜,到1958年10月25日撤出朝鲜,整整八年,我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而感到荣幸。今年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借此机会,谨就我记忆所及,对东北边防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组成、入朝、转战和凯旋等若干情况,作一些素描式回顾。
突然受命
讲志愿军要从东北边防军的组建讲起,而讲东北边防军,又要从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后改称第十三兵团)由广东北上讲起。
1949年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时,中央军委赋予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解放和经营中南六省,其中第四野战军所属第十五兵团的任务是解放和经营广东。1950年上半年,第十五兵团指挥第四十军、四十三军进行了渡海作战,一举解放海南岛,广东境内的大规模作战,画上了句号,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向经营方面转变。
所谓“经营”,就是军队除打仗外,还要帮助地方建設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剿灭土匪、维持治安、恢复经济等等,这也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海南岛战役之后,第十五兵团的番号也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兼广东军区”。那时,我在兵团司令部队列科文印组工作,司令部上报下发的各种机密文件,都由我们刻印发出。有时首长们开会,也叫我们去做记录。为做好经营广东的工作,兵团首长向各级干部作动员,作部署,开了很多会,下发了很多关于军分区、地方部队和民兵建设的文件,不少干部脱下军装,转业地方,直接参与地方建设工作。总之,全兵团官兵都准备在广东“安营扎寨”,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南大门了。
1950年6月25日以后,从广播中听说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美国已出兵干涉,并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控制台湾,我国政府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事态虽然严重,我们也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和我们驻在祖国最南端的部队有什么关系。
大约7月10日前后,兵团首长突然传达中央军委和四野首长的命令,要求我们兵团结束在广东的一切工作,迅速集结,准备北上,但究竟要到什么地方,执行什么任务,首长们并没有传达。大家对这一命令既感到突然,又感到兴奋,期待着迎接新的任务。
很快,又接到通知,我们调走后,由正在河南待命的第十三兵团来接替我们的防务。但这么重大的部队调动,很容易引起外界的关注和猜疑,特别是广东,靠近香港,更加敏感。为了保密,军委决定两个兵团的番号也同时互换,即我们第十五兵团改为第十三兵团,第十三兵团改为第十五兵团,这样,我们调走后,留在广州的,仍然是第十五兵团兼广东军区,使外界无从察觉部队的调动。
火速北上
我们兵团在执行广东作战任务时,指挥的部队有第四十、第四十三、第四十四三个军,这时,第四十三军已留在海南岛担任警备任务,第四十四军正在准备攻打万山群岛等沿海岛屿,第四十军刚从海南岛回来,还在补充休整。为重组和加强兵团力量,军委把在广西、云南作战后正在休整和执行剿匪任务的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连同第四十军都调归兵团指挥,并命令兵团机关和所有部队,立即北上。
新的序列确定后,兵团迅速与各军建立通讯联系,了解情况,协调动作,做好开动前的准备。我则参加兵团司令部临时组成的一个军运小组,跟随几位有经验的资深参谋,携带部队车运计划,到武汉向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部报告,并同武汉当地的轮渡、铁路等部门联系部队渡江、换乘、编组等事宜。那时长江上还没有桥梁,部队从江南乘火车到武昌后,只能在徐家棚车站下车,然后换乘渡轮,过江到汉口,再从汉口上岸,到大智门车站换乘火车继续北上,所以部队到达的顺序和两岸的换乘一定要组织衔接好,以免造成延误和拥堵。车运小组在武汉大约工作了半个月,7月底,待大部队顺利通过武汉,兵团司令部机关人员也到达武汉以后,我们便也登上火车,向北开去。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坐在闷罐车里,就像坐在烤箱里,燥热难耐,汗流不止,只有在夜间才稍微凉快一点。列车由京汉路到郑州后,转陇海路到徐州,再转津浦路、京榆路直开东北。我们在车上度过了八一建军节,8月5日前后,火车在安东(今丹东)停了下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真没想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从祖国最南端跑到了最北端,从珠江边来到了鸭绿江边。
直到这时,领导才向我们说明,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我国东北边境的安全受到威胁,成为国家紧急大事,而当时的东北只有很少部队,所以中央军委决定尽速组建东北边防军,把我们兵团调来,任务就是保卫东北边境的安全,并根据形势发展,于必要时入朝作战。我们顿时感到,中央领导的决策和部署,真是高瞻远瞩,果断厉行。
到东北以后,第四十二军、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和高炮团、工兵团等,也陆续编入第十三兵团序列,全兵团达到25万人以上,而且都是解放战争时在东北作战的部队,官兵中东北人很多,现在又回来保卫东北,思想上很好转弯,士气很高。
后来听说军委曾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但实际上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并没有成立,我们也没有使用过东北边防军的番号,所有边防部队仍由第十三兵团指挥(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由于是在东北军区的辖区内,所以兵团归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双重领导,后勤供给则全由东北军区负责。
部队在东北驻了两个多月,进行战备训练。这期间,侵朝美军的飞机经常飞到鸭绿江边我国境内侦察轰炸,安东更是美机多次“光顾”的地方,曾炸毁我方一些民房。看到这些,大家更加义愤填膺。有一天,司令部里突然出现几个穿朝鲜人民军军装的人,仔细一看,原来都是司令部作战、侦察等部门的领导人,他们正准备化装到朝鲜去,实地考察战场地形、道路、桥梁等情况,为部队进入朝鲜做准备。大家都预感到,我们离战争越来越近了。
秘密过江
9月中旬以后,美军在仁川港登陆,朝鲜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10月初,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向北发动猛烈进攻,眼看战火就要烧到鸭绿江边。
10月8日,中央下令将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立即准备,待命出动。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非常兴奋,按照规定,我们把“八一”帽徽、人民解放军胸章以及所有带有中文的书籍、笔记本等,都打成一个小包,写上名字,交给后方留守处的同志保存,换上没有任何标志的草绿色棉军衣,整装待发。
10月19日,美军占领了平壤。也就在这天晚上,志愿军各部队从安东、长甸河口、辑安等渡口开始渡江,进入朝鲜。所有部队一律夜行晓宿,不露痕迹,避开美军飞机的侦察。
彭总也是在19日夜里,只带了几个参谋、机要员、电台和警卫员,随先头部队过江与金日成会见,商讨双方联合作战的大事。
第十三兵团司令部是21日夜间从长甸河口渡江的。也正是在这一天,接毛主席来电,命令将第十三兵团司令部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并立即与彭总会合,以便指挥作战;随即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解方任参谋长。因此,从渡江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的番号就不再使用,兵团司令部开始履行中国人民志愿军统帅部的职责。
到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前,几十万大军秘密渡江(10月下旬,第五十军、第六十六军也编入了志愿军序列,随即入朝),并继续向前开进,到达各自的作战地域。这么大的行动,美军竟毫无察觉,从而保证了我军在战略上和战役上的突然性。这种大规模隐蔽行动本身,就是军事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
六处驻地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司”)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一共转移过五次,有六处驻地,其先后顺序为:大榆洞、玉泉站、君子里、甘凤里、空寺洞、桧仓。现将这六处驻地的大致情况和发生的重大事件略作说明。
第一次战役时,志司驻在大榆洞,离最近的前沿部队不过几十公里。指挥几十万大军的司令部,距离前沿这么近,是很少见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朝鲜北部当时已没有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这是彭总打仗时的一贯作风——靠前指挥,因为越是靠近前线,同部队的联系越紧密便捷,越有利于指挥员了解战场情况,实施切合实际的指挥,对部队也是一种激励。
大榆洞原是一个小镇,周边山上是一处矿场,矿洞外有几处独立家屋和工具棚。彭总、各位副司令和志司各部门分散住在几个矿洞里。这时敌人还未发现志愿军大规模入朝,但他们发现这里发射出的电波频繁而集中,判断这里一定有高级指挥机关,便多次派飞机到这里侦察轰炸。11月24日,敌机在这里上空盘旋了很长时间,没有俯冲,也没有投弹扫射,然后掉头南去,按照常规判断,这是敌人有计划轰炸前的侦察行动。为避免损失,第二天(11月25日)拂晓前,我们就分散到山里隐蔽起来了。上午9点左右,大批美军轰炸机、强击机突然飞来,密集的炸弹、燃烧弹倾泻而下,一波接着一波,轮番轰炸。毛岸英(在彭总身边任机要秘书)和作战处另一位参谋,拂晓前本来已分散隐蔽,天亮后见敌机还未来,便回到矿洞外的一间房子里,不料他们刚一回去,敌机也呼啸而至,他们还未跑出来,那间房子就被炸中,他们俩就这样牺牲了。这是志司在大榆洞发生的最悲惨而具有轰动性的事件。我们从1950年10月下旬到12月初,在大榆洞驻扎了一个多月,刚去时集镇上的大片房子还很完整,离开时已被夷为平地了。
朝鲜的地形是东部多高山峻岭,不利于美军行动,西部虽也多山,但較为平缓,所以美军的主攻方向在西线。经过志愿军第一次战役,麦克阿瑟挨了一棒,但并未清醒过来,仍然认为中国不过是象征性出兵,不可能阻止美军占领全朝鲜,所以美军暂停几天以后,便又大肆向北蠢动。彭总再次巧妙利用敌人的骄狂心理,在第一次战役之后,命令西线部队稍许后撤,故意“示弱”,让敌人放心北进,我军则隐蔽插入敌后,猛烈反击(东线以防御为主),发起第二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打响后不几天,我军不仅挡住了敌人的进攻,还很快转入进攻和追击,于是,彭总又决定司令部前移。12月上旬,第二次战役还在进行当中,志司就随着部队前移。途中经过朝鲜名胜妙香山,在一片树林里休息片刻,吃了干粮,但谁也顾不上欣赏那里的美景。因沿途都是双方刚刚激战过的战场,村庄几乎全部毁于战火,且这一带极易遭到美军侦察轰炸,于是我们就临时在一处较隐蔽的火车隧道里停了下来,这就是志司在朝鲜的第二处驻地——玉泉站。附近的火车站叫玉泉站,那时已无火车可通,司令部就设在这条隧道里,隧道口用一些填满沙石的草袋子加以掩蔽,彭总和司令部在这个只有几百米长的隧道里,工作了约十个日日夜夜,指挥了第二次战役的后期行动。
12月的朝鲜北部,冰天雪地,大风凛冽,气温降到摄氏零下30度,火车洞子的“灌堂风”更加厉害,吹得人瑟瑟发抖,又不能生火取暖,也不能做饭,只能吃压缩饼干、炒面和土豆干;同志们白天坐在背包上伏在文件箱上工作,晚上就挤在铺一点草或玉米秸秆的地面上和衣而睡,但没有人叫苦,那种兴奋的劲头,高昂的士气,团结的友情,至今想来还很留恋。我们在这里待了十天左右,才继续南移。这么高级的司令部设在火车隧道里,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可说是一大趣闻。美军也没有发现我们这个大目标,所以我们在玉泉站没有遭到轰炸。
12月下旬,“联合国军”因遭到痛击,损失惨重,有被志愿军切断后路的危险,所以拼命夺路而逃,一下子退到38度线附近,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后撤途中遭车祸身亡,可见其仓惶与狼狈。由于志愿军各部队大踏步向前追击,所以彭总和志司又前移到君子里(属成川郡),这便是志司的第三处驻地。这也是一处只有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才能找到的地名,是一个矿洞和分散的村落。这样,在第二次战役期间,志司就前移了两次。我们在这里过了1951年元旦和春节。在君子里最有意义的事情,一是指挥了第三次战役,二是召开了中朝双方高级干部会议。经过两次战役,在志愿军掩护下,人民军经过休整,可以重新投入战斗,所以就在君子里召开双方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联合作战问题。彭总、金日成、高岗(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志愿军后勤保障)、陈赓(奉军委之命正在朝鲜考察,准备率部入朝)和双方高级司令官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正式成立了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由彭总任联司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联司机构也以志司为主,朝方只派驻一位高级代表和一个很精干的联络机构,所以从这以后,志司同时担负起了联司的任务。
我们在君子里送走了1950年,迎来了1951年。1950年除夕之夜,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短短几天,西线部队就把“联合国军”驱赶到37度线附近。于是,志司也跟着前移。这次前移的距离最远,一下子前出到伊川郡一个叫甘凤里的小山村设营扎寨。这里距上甘岭很近,距38度线也不过100公里的样子,是志司的第四处驻地,也是志司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最靠前的位置。
第三次战役以后,由于连续作战,伤亡较大,部队疲劳,补给线延长等原因,我军转入休整,“联合国军”则乘机大肆反攻,我军被迫转入防御,这就是第四次战役。开始我军是坚守防御和反突击相结合,后来则转入机动防御,且战且退,“联合国军”又反攻到38度线附近。整个第四次战役打了两个多月,志司一直在甘凤里进行指挥。甘凤里地处朝鲜中部战线的战略制高点——五圣山脚下,距后来双方反复争夺的上甘岭战役主阵地很近。散落在山间的小山村中的房屋多已被毁,居民也多已逃亡,彭总、各位副司令和志司机关就分散驻在这些小山村里,指挥了第四次战役。这是志司入朝以来唯一没有住山洞的地方,但构筑了若干掩蔽部,作为防空之用。我们在这里住了约两个月,直到4月下旬,由于敌人的连续猛烈反攻,我方部队且战且退,又撤回到38度线附近时,志司才向后转移。
志司的第五处驻地是空寺洞,这里也是一处矿区。我们在这里驻了两三个月(1951年5—8月),这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一是指挥了第五次战役,作战双方在38度线附近形成拉锯;二是廖承志率领的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到达朝鲜前线,部分团员来到志司,在矿洞里作慰问演出,没有舞台,灯光昏暗,几十个观众挤在一起观看,演员和观众可说是零距离,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听侯宝林说相声;三是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举行,邓华副司令员和解方参谋长都是中朝方面谈判代表,去了开城。在空寺洞,我们曾遭遇到几次大的空袭,伤亡了几位同志。有一次,彭总刚从他在洞外的一间办公室转移出去,那间办公室就被扫射,他休息时用的一张行军床也被打了几个弹洞。
志司的第六处驻地是桧仓,记得我们是在1951年八九月间到达这里的。这也是一处矿洞,比我们以前住过的矿洞都大。这里的矿山有好几个洞口,洞内最宽大的地方被加固为可容纳上百人的“礼堂”,一些慰问演出,都是在这矿洞礼堂里举行的。敌机虽发现了这个大目标,多次进行轰炸,但随着志愿军空军和防空火力的增强,不再像战争初期那么肆无忌惮。此后两年,朝鲜战场的情况是边打边谈,打打谈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织,双方形成长期对峙和胶着状态,有时也打得非常激烈(如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但都没有大的进退,战线基本稳定在38度线附近,因此志司也没有再作迁移。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国际局部战争终于停止下来。
桧仓是志司在朝鲜的最后一处驻地,也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处驻地,共驻了七年之久(战时两年,战后五年)。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等都曾到此视察访问。
1952年4月,彭总奉调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未对外宣布),由陈赓代理其职务(但军委未正式任命陈赓为志愿军司令员)。两个月后,陈赓也奉调回国,其后的志愿军司令员依次是邓华(停战前为代理司令员,停战后才正式任命为司令员)、杨得志、杨勇,政治委员是李志民、王平。
關于停战以后的任务,杨勇司令员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他说:今后我们切记要抓好两件大事,一是搞好战备,不要让敌人把我们赶出去;二是搞好同朝方的关系,不要让朝鲜人民把我们赶出去。后来几年,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如此。
停战以后,志愿军在朝鲜修筑了多处烈士陵园,在桧仓也修筑了一处,毛岸英等烈士的遗体都集中到这里掩埋。陵园建在小山上,远远就可看见彩门上“浩气长存”几个大字,园内有100多座坟墓,每座坟墓都有一块墓碑,刻着烈士的姓名,他们都是志愿军总部牺牲的指战员,其中有我熟悉的战友。毛岸英的墓在第一排正中,墓碑正面刻着“毛岸英烈士之墓”,是郭沫若题写的,背面刻着他的简历。我曾多次来到这里凭吊,每次来,脑海中便浮现出已经逝去的岁月,崇敬肃穆之感,油然而生。
难忘印象
在志司八年,最值得回味的还是战争期间的两年零九个月,印象最深刻的有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是夜行军及战场所见。
战争期间,我们没有制空权,为了躲避敌机,部队行动大都是在夜间,夜行晓宿,每次战役发起进攻也都在夜间。上面说的志司的几次转移,都在夜间,因为要携带通讯装备、文件箱之类的东西,我们大都是乘卡车夜行。但即使是在夜间,敌机也经常光顾,我们的车队要拉开车距,不能开灯,只能借着雪光缓缓开进。志愿军部队中有一个公安师专门负责布设夜间防空哨,每一公里设置一个哨位,一听见敌机响,便对空鸣枪报警,在车上听见枪声由远及近,车子便停下来,赶紧隐蔽,待看见绿色信号弹解除警报,再继续前行。通过重要地点或枢纽路口时,经常会碰到敌机封锁,投照明弹,一次投几颗到十几颗,轮番地投,照得大地通明,敌机在头上盘旋,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只得停下来,有经验的司机能够利用地形地物,从容隐蔽,等照明弹熄灭后再走。一晚上就这样走走停停。即使这样,有时还免不了遭到袭击,在由玉泉站向君子里转移的一天夜里,敌机在暗夜中飞来,对着公路一阵扫射,紧挨着我们后面的一辆车不幸被打中,一位我认识的同志当场牺牲。也是在这次转移中,我们从清川江通过,大桥已毁,我们从冰冻的江面上行走,激战后的战场一片狼藉,满地是被击毁的车辆、枪炮,还有一些被大雪掩盖着的尸体,战争的破坏性与残酷性,于此可见!
还有另外一种战场所见——1952年夏秋某一天夜里,大批敌机来轰炸桧仓,这时已有一个高炮团保卫志司,我们的高射炮、高射机枪一齐开火,高射机枪一串串曳光弹射向高空,无数高射炮弹在夜空中爆炸闪光,探照灯巨大的光柱直上高空,交叉晃动着捕捉目标……我们在洞口观看,敌机盘旋了半个多小时,始终未敢低飞,胡乱投了几颗炸弹就飞走了。这种“战场夜景”,煞是好看,解气!所以也留下了难忘印象。
第二是彭总的一次“深夜查岗”。
在志司经常可以看见彭总早晨或傍晚在洞外散步,警卫员在后面跟着;有时在洞口吃饭,彭总还特意走过来看看我们吃些什么,问问大家能不能吃饱。我还意外地和彭总有过一次单独的“会见”。那是在君子里,一天夜里我正在值班,彭总突然走进我们办公的洞子,我马上起立向他敬礼,他走到我跟前,先问我的姓名、年龄、何时参军等,然后问部队伤亡情况。这时,我在志司队列处(后来叫军务处)工作,部队编制、实力统计、武器装备、共同条令、枪弹补充、兵员补充等具体业务,都由我们处负责办理。我把掌握的截至第三次战役结束的伤亡统计向他作了报告,彭总又特别问了一下东线部队因冻伤亡的情况。因为担负东线作战任务的第九兵团,原是华东的部队,是准备攻打台湾的主力兵团,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前急速北上,还没有来得及换上棉衣,就直接开进朝鲜,在东部海拔1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布防,在摄氏零下30度的条件下穿着单衣作战,被冻伤亡人数大大超过作战伤亡人数。我深恐自己的报告有什么不妥,心里直打鼓,彭总没说什么,点点头,示意我坐下,转身离去,我才舒了一口气。后来我想,这些数字,我们都及时汇总报给了参谋长,彭总肯定是了解的,无需再向我们询问,他深夜到来,可能是“查岗查哨”,检查一下参谋人员的值班情况和生活情况吧。那一夜,他走了多少洞穴,查看了多少部门,他自己能休息几个小时,我无从知晓,但这位日理万机、身负天下安危的司令员的忘我操劳,可想而知。
第三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司令部训练。
司令部好比部队的大脑,要把收集到的各种情报、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作为主官(司令员)决策的基础,又要通过缜密而迅速的手段,实现主官的决心,参谋长作为司令部“首脑”,其重大责任自不必说。
战争期间,志司参谋长是解方(中间有一段时间解方参加开城谈判,由张文舟代理),副参谋长是王政柱。他们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都是司令部工作的行家,非常重视司令部建设,强调要善于学习,发挥司令部作为首脑机关的作用。他们一再教导司令部参谋人员说:在朝鲜,我们是在打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战争,主要对手是不可一世的美军,又是在国外作战,是在狭窄的半岛的特殊地形上作战,条件和过去大不相同,对于这些我们还不熟悉的东西,更是要从头学起,不断提高参谋业务水平。
除了学习司令部工作条例、参谋工作手册,下部队进行调查研究以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53年初的一次司令部参谋工作总结。那时,志愿军正在全力准备抗击美军可能在西海岸的大规模登陆,解方参谋长为提高司令部工作效率,提出要进行一次工作总结。这次总结,不是由领导来作,讲给大家听;也不是算流水账,列举各种数字和成绩、教训,而是司令部参谋人人思考,人人动手,要求每个参谋按照自己的分工,把自己两年多来承办各种业务、处理各种问题的依据、程式、方法和效果,一件件一条条地梳理一下,挑选出自己认为比较成功和满意的事例,以及不太成功、不太满意的事例,当时是怎么办理的,应该怎么办理才好,经过深思熟虑,写成各自的工作細则。每人写一份,加起来就成了司令部各个岗位、各种业务的参谋工作细则。大家都感到,通过这次总结,把零星的经验升华为比较条理的工作细则,业务能力和工作效率确实得到了提升,是一次别开生面而切实有效的总结,是一次很好的司令部训练。我那时在军务处任参谋,负责承办实力统计、伤亡损失统计、兵员补充统计等具体业务,我也按照要求认真总结,写出了工作细则。没想到,我写的细则,还得到了解方参谋长的表扬,这对我是一次很大的鼓励,更重要的当然还是军事知识和工作经验的
积累,这就叫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凯 旋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所有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由朝鲜南北人民自主解决和平统一问题。
1958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与金日成会谈,并到桧仓视察志愿军总部。两国政府和志愿军总部先后发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年内全部撤出朝鲜的公报。
1958年4—9月,在组织指挥所属部队五个军撤回国内之后,志愿军总部也要撤回了。10月上中旬,志愿军总部派出10个代表团到朝鲜各道(相当于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告别,我随志司办公室主任李炎率领的代表团到黄海南道参加了隆重热烈的告别活动。10月下旬,志愿军总部组成一个100多人的代表团(另有文工团约450人),由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率领,准备参加在平壤的告别和回国后的汇报活动,我有幸也被遴选为这个代表团的成员。
10月23日,我们最后一次到烈士陵园凭吊,向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们告别。24日凌晨,环顾一下我们战斗生活了七年的驻地—桧仓,登上列车,很快就到了平壤,参观新落成的纪念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中朝友谊塔以及平壤的许多名胜。晚上,金日成首相举行盛大欢送国宴,宴会后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和志愿军文工团联合举行精彩的文艺表演,直到深夜。
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八周年纪念日,我们登上志愿军撤离的最后一趟列车,告别朝鲜,驶向祖国。在下榻宾馆到平壤火车站的一路上,30万平壤市民夹道欢送,鲜花挥舞,锣鼓喧天,歌声口号声连成一片,朝鲜小伙子频频把我们抬起来,抛向空中……金日成和朝鲜党政军最高领导人都到车站欢送。这天晚上,我们的专列到达安东(丹东),廖承志代表抗美援朝总会专程从北京前来迎接。
10月26日,志愿军总部发表公告,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已全部撤离朝鲜。
在由安东到北京的一路上,在沈阳、天津等大站,都举行了热烈欢迎志愿军凯旋归国的活动,但我都没有参加,因为我正在列车的一节公务车上,为杨勇司令员誊抄一篇到北京后要用的重要讲话稿,这篇讲话稿是在列车上刚刚敲定的。
10月28日下午,我们的专列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北京市市长彭真等到车站欢迎,安排我们在当时最好的宾馆——北京饭店下榻。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欢迎大会上,郭沫若、彭真把一面巨大的锦旗赠送给杨勇司令员、王平政委,上面绣着:“你们打败敌人,帮助了朋友,保卫了祖国,拯救了和平。你们的勋名万古存(陈毅元帅手迹)!”对志愿军作了全面的极高的评价。其实,这也是对抗美援朝这一伟大事件的历史作用的经典概括,这荣誉是属于全国人民的!
那天晚上,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欢迎晚宴,他特别兴奋,在致欢迎词后,鼓励大家说:“今天都是自家人,欢庆一堂,不必拘谨,可以开怀畅饮!”宴会厅里响起一片掌声。席间,大家纷纷向总理敬酒。回想起当时情景,我很理解他那时的欢快心情,作为总理,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当然比我们更加明了抗美援朝这件大事的历史分量,现在终于取得了预想的效果,真是来之不
易啊!
我清楚地记得,10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车辚辚,马萧萧,最可爱的人回来了!》这标题引用了唐朝大诗人杜甫《兵车行》开头的诗句,赋予了新意,很新鲜,很响亮,反映着那时人们对志愿军凯旋的欢畅和自豪!
在北京,我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彭总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第一任志愿军司令员,也接见了我们。杨勇司令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会和抗美援朝总会作了志愿军八年抗美援朝工作报告。首都人民举行了多种多样热烈的群众性欢迎活动。杨勇司令员、王平政委还带领我们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奠基劳动。
11月初,我们从北京回到大连,与先期到达这里的志司的战友们会合。在随后的约两个月里,大家都分配了新的工作,各自奔赴新的岗位。
至此,志愿军司令部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入朝那年我18岁,归来时26岁。我珍惜自己的这一段经历,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是我军旅生涯的奠基石。(责任编辑 杨琳)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
原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