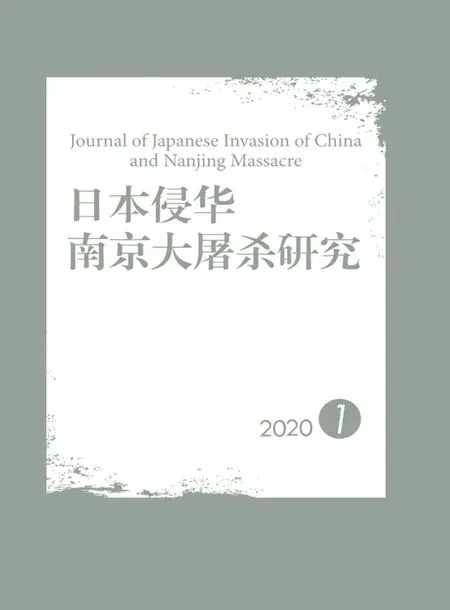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战时日本对华北通货政策*
王 萌
众所周知,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设立了诸多国策会社,为日本掠取沦陷区的各种资源服务。与华中沦陷区的情况相似,在日本军政当局的庇护下,华北沦陷区形成了一个资本雄厚、规模庞大的国策会社集团。1938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开办“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联银券”作为日本军政当局在华北沦陷区驱逐国民政府法币、抵抗中共边币、掠取民间财富与资源的经济武器,迄今中日学界对“联银券”发行与流通情况已有丰富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1)笔者曾系统考察过迄今中日学界关于战时中日货币战的主要研究成果,发现两国学界对于战时日本对华通货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本军政当局上层的动向与决策过程,而不太关注其施之于日本在华企业的影响。参见王萌《战中之战:中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中日货币战研究评述》,《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4期。然而,学界对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日本军政当局维持“联银券”价值之间的联系却鲜有专论。本文期待在此问题上有所推进,并揭示以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为首的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在战时日本对华北通货政策中扮演的角色。
一、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形成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决议在华北沦陷区设立一综合性国策会社,以之控制华北经济命脉。(2)《华北开发国策会社要纲案》(1937年9月30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华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6—159页。1937年11月16日,日本内阁制定《华北经济开发方针》,要求“为开发与统制华北经济,应设立一国策会社,使之充分体现举国一致的精神及全国产业总动员的旨趣”,并由该会社“负责对主要交通运输事业(含港口及道路)、通信事业、发电输电事业、矿产事业、盐业及盐加工业,以及棉花、羊毛等其他重要产业之经营或调整”。(3)「北支那経済開発方針」(1937年11月16日)、『内閣第三委員会関係一件』(第四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M-1-1-0-9_004。该方针于当年12月24日被日本内阁决议的《中国事变处理要纲》收入,但删去“以及其他棉花羊毛等”数字。1938年4月30日,日本国会通过《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法》,明确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成立之目的,乃“基于帝国政府决定之华北经济开发方针,紧密结合日、满、华北之经济,促进华北经济之开发,以期华北之繁荣,进而强化、扩充我国防经济之实力”。(4)「北支那開発株式会社設立要綱」(1938年3月15日)、多田井喜生編『続·現代史資料11 占領地通貨工作』、みすず書房、1983年、144頁。11月7日,日本军政当局正式成立华北开发会社,由贵族实业家大谷尊由出任总裁。
华北开发会社为日本特殊法人企业,初期投入资本额达3.5亿日圆,由日本政府与民间折半出资。日本军政当局一方面将日军所获得的战利品充作实物资本,成为该会社最大的股东,并通过派遣监理官等方式对该会社拥有绝对的经营支配权;另一方面,在承诺保证民间股东利润分红的情况下,又通过公开募股的方式谋求民众对其战时体制的支持。(5)关于华北开发会社的股份情况与日本军政当局背后之意图,参见柴田善雅『中国占領地日系企業の活動』、日本経済評論社,2008年、204—207頁。值得注意的是,华北开发会社的大股东都是军人组织和社会团体,以及日本国内的大企业经营者,如“军人后援会”控63212股、大日本制糖会社控46000股、关东配电会社控20800股等,(6)北支那開発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七回)、1943年度、三菱経済研究所蔵。充分体现出日本军政当局与军人组织、社会团体及财阀利益的一致性。为了保证华北开发会社民间股东的利益,日本军政当局在财政政策上给予该会社各种关照,甚至免除其自成立之日起十年的所得税、营业收益税与地方税。然而,自华北开发会社成立以来,因战乱与自然灾害导致的物资短缺、劳工招募困难等问题,以及日本军政当局所采取的军事优先的经营方针,其经营成本不断提高,这与日本军政当局保障性的利润分红形成了深刻的矛盾。
早在大正时期,日商即在华北各地开办各种企业。而华北开发会社成立后,在其下先后成立了一批子会社,由此在华北沦陷区形成一个资本雄厚、规模庞大的国策会社集团。关于日本军政当局如何利用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中日学界已有大量研究。(7)日本学界的代表性成果,可参见中村隆英『戦時日本の華北支配』、山川出版社、1983年;中国学界的代表性成果可参见居之芬《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需要指出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业务重点在于矿产开发、金属生产、化工产业等领域,这与华中国策会社将业务重点置于公共事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8)参见王萌《华中国策会社集团与战时日本对华中通货政策》,《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9年第1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将华北沦陷区视为其国防兵站基地,进一步加强对当地煤炭、盐、棉花等军需物资的掠取力度。若将从事矿产开发、商品生产的企业定义为生产型企业,那么1942年后,在华北开发会社的不断投资、融资下,华北沦陷区生产型企业不断成立,数量激增。至1944年3月,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成员共55家,其中从事各种资源开发的生产型企业达35家,占企业总数的64%。虽然生产型企业的实投资本总额因部分企业资料的缺失而无法精确统计,但可推算至少占全部企业实投资本总额的50%以上。(9)关于华北开发会社相关各国策会社的设立时间、实投资本额、业务情况等,参见槐樹会編『北支那開発株式会社之回顧』、槐樹会刊行会、1981年、23—29頁;另可参见《1944年8月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相关会社一览》(1944年8月末),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与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第170—186页。除生产型企业之外,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中也有少量的公共事业型企业与调控商品市场价格的市场调节型企业。公共事业型企业的代表是华北交通会社,该会社成立于1939年4月,是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中地位仅次于华北开发会社的重要成员。该会社成立之初实投资本额达3亿日圆,其中华北开发会社出资1.5亿日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资1.2亿日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出资0.3亿日圆。华北交通会社具有浓厚的“满铁”色彩,如同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中的“独立王国”,(10)槐樹会編『北支那開発株式会社之回顧』、85頁。日本铁道省、满铁职员担任该会社各部要职,其铁路运输部门处于日军的严密控制之下,经营活动深受日军军事行动的影响。市场调节型企业的代表是“粮谷开发组合”。“粮谷开发组合”成立于1943年8月,实投资本额0.2亿日圆,是日本军政当局为应对华北粮食产量不足及价格飙涨,而由日商统一采购和配给的特殊企业,其创办设想来自日本驻华大使馆,主要是为了满足华北各地日侨生活的需要。(11)槐樹会編『北支那開発株式会社之回顧』、122頁。无论从企业数量还是实投资本总额来看,战争中后期,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中以资源开发为核心的生产型企业都超过公共事业型企业及市场调节型企业,这意味着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在功能上更侧重于对资源的掠取。
二、“联银券”危机与日本军政当局的应对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将对华北的通货政策视为其对伪满通货政策的延伸。早在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军政当局就有所预谋,正如1936年11月朝鲜银行内部对此之认识:“此际乃日本乘满洲国之金圆化,确立对华北及中国方针、推进各项工作之最适宜时机”。(12)朝鮮銀行「北支通貨金融工作ニ関スル意見書」(1936年11月)、多田井喜生『続·現代史資料11 占領地通貨工作』、127頁。然而“朝鲜银行券”等日系货币在华北的广泛流通,其价值必然会受到华北物价体系的影响,从而使日系货币价值及日本国内经济体系受到冲击。因此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日本军政当局即筹谋在北平开办“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华北沦陷区发行“独立”的货币。(13)「華北連合銀行(仮称)設立要綱」(1937年11月26日)、多田井喜生編『続·現代史資料11 占領地通貨工作』、142頁。日本军政当局为将华北沦陷区如伪满洲国一样纳入日圆经济体系,实行将“联银券”与日圆等价联系之政策。“联银券”是日伪当局用来驱逐法币的经济武器,日伪当局先是要求民间将法币与“联银券”等价兑换,不久要求按九折、七折兑换,继而宣布自1939年3月11日起,禁止法币在华北沦陷区流通。(14)《华北临时政府禁用法币条文》(1939年1月18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华北经济掠夺》,第397页。“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后,日本军政当局规定,日本政府派驻华北的各类机构、日商会社、伪政权的各项开支与日军的薪俸均要以“联银券”支付。事实上,直至1942年1月1日日伪当局严禁一切小额货币在华北沦陷区流通之后,“联银券”才成为华北沦陷区的统一货币。(15)汪时璟:《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942年度营业报告》(1943年3月27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与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第965页。
自1939年末以来,华北沦陷区各地物价出现高涨之势,这与日伪将“联银券”和日圆等值联系的政策密切相关。这一联系对于日本将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至华北沦陷区并从当地进口各种生产原料极为有利。华北沦陷区从属于日圆经济体系的这层关系,如日本战犯古海忠之所言:“这一情况意味着强加给华北如此庞大的‘需求’,但却同生产与物资的扩大和增加毫无关联,而且同增加部分的相抵也不从日本运来,同其他国家的联系也被切断。这样一来,立即造成华北的物资匮乏”。(16)古海忠之:《以不兑换纸币进行掠夺》,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华北经济掠夺》,第397页。当时即有日本经济学者指出,华北物价高涨的真实原因在于“联银券”名义上与日圆等值而实质上贬值。(17)参见兵庫県興亜貿易協会『支那の経済事情』、兵庫県興亜貿易協会、1940年、11頁。为了满足当地日军的军费支出和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对资源“开发”的需求,“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不得不大量发行“联银券”,1938年末“联银券”的流通量为16196万元,1939年末达45804万元,1939年度通货膨胀之迅猛,几近1938年的3倍。(18)野田経済研究所『戦時下の国策会社』、577頁。“联银券”的流通量于1940年初突破5亿元,接近全面抗战前法币及其他旧币在华北的流通总量。1940年初“联银券”的流通区域远比全面抗战前法币的流通区域小,兼之水灾、战祸导致民间生产力低下,以及伪政权对日本的大量出口等,华北沦陷区的物资供给已近枯竭。1940年3月,以面粉、杂粮等粮食价格高涨为先声,棉布、绢布、棉花等各种商品出现齐涨态势。在资金换物浪潮下,华北市场呈现出的狂热商业状况引起了日本军政当局的高度关注。(19)「北支物価対策強行 銀行の貸付回収開始」、『東京朝日新聞』1940年3月1日。
在日本军政当局看来,若对“联银券”的增发不采取对策,则“不仅军费不得随意运用将导致军队无法作战,而且日满华经济圈也会因华北一角之崩溃而危及母国”,(20)「連銀券緊急対策ノ件」(1940年2月23日)、『聯銀券対策関係綴 住谷悌史資料』、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支那事変全般-499。由此进行“联银券”价值维持工作。这一工作的主要目的,即在确保“联银券”与日圆等值联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压缩“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对华北民间的资金投放,从而抑制华北物价的高涨。其中对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之具体要求体现于以下两点:
一、彻底实行开发技术上的重点主义及对中方资本的利用
1. 在经济开发上,缓和对单一品种的重点主义,而从地域重点主义角度限定于华北最有利的品种,若非如此,则应以指向国内、满洲为重点,完善设备资材,发挥其最佳效能。
2. 将重点置于华北当下农业及其他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开发与培育上,通过扩充该领域的物资生产来支持联银券。
3. 鼓励利用当地中国人的资金,打开实现这一利用之途径。
二、彻底回收游资
1. 奖励购买国策会社之社债等,极力压缩日本人的购买力。
2. 开发会社向第三国预订相关物资,除物资动员计划所认可者外,皆加以抑制。
3. 对于国策会社的政府资本一味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贷出之习惯,改为通过购买公债、社债来引导与利用中国方面的本土资本。
4. 使国策会社向临时政府开放持股,以吸收民间资本。(21)「連銀券緊急対策ニ関スル件」(1940年3月4日)、『聯銀券対策関係綴 住谷悌史資料』、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支那事変全般-499。
或许这些规定对于国策会社经营者而言过于抽象,不久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与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在《昭和十五年度华北金融货币对策》中,进一步明确国策会社对资金的运用方式,其出台的规定更为具体:
1. 各会社要制定精密的资金使用计划。
2. 对国内汇款、当地银行的借款,要尽可能加以抑制。
3. 在开发会社子会社新设之际,中国方面的现金出资不要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借入,而应通过政府的经常性收入或当地资本等来筹措。
4. 与以上相关的新会社的设立,未必急切。
5. 对于开发会社等资金不能强迫当地捐款(至少应调整之)。
6. 至少开发会社对第三国向华北方面预订相关物资,要采取审批许可的原则。(22)「昭和十五年度北支ニ於ケル金融通貨対策」(1940年3月12日)、『聯銀券対策関係綴 住谷悌史資料』、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支那事変全般-499。
虽然这些规定在国策会社对华北伪政权与第三国金融关系上更具弹性,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作为“联银券”价值维持工作策划者之一的日本经济学家高桥龟吉指出:“要极力扩大华北国策会社的利润,促进联银券的收缩,即使如此,也必须对物价的高涨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大陆开发事业要极力吸收中国的民族资本。但是,华北开发会社等开发事业由此就不得不预留能够吸收民族资本的利润,以此作为实行当下低物价政策的代价。开发事业将持续赤字状态,而要想改变这一状态,必须要有导致物价进一步高涨的心理准备”。(23)高橋亀吉「連銀券、軍票、蒙彊券対策私見」(1940年7月)、『連銀券、軍票関係文書綴』、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中央-軍事行政経理-317。正如高桥所指出的,为了实现日本军政当局制定的低物价政策,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开发”事业必将蒙受巨大损失,这当然是日本军政当局与会社经营者所不愿见到的结果。由此两者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即在尽量减少资金投入的前提下,国策会社的“开发”重点不得不集中于煤炭、铁、盐、棉花等军需物资上。为了满足日“满”华经济圈的综合需要,华北国策会社集团还必须实现日本军政当局所规定的军需物资增产计划,故而企业只能通过强化经营管理与节约经费等形式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24)陸軍省経理局「連銀券価値向上並に流通強化策」(1940年3月19日)、『聯銀券対策関係綴 住谷悌史資料』、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支那事変全般-499。
1940年4月,在北平举行的日本大藏、商工、农林、拓务、外务各省次官与军部官员的恳谈会上,专门讨论了维持“联银券”价值的对策问题,日本军政当局随后公开发表了“联银券”绝不贬值,且将极力抑制其增发与减少国策会社支出的声明。(25)兵庫県興亜貿易協会『支那の経済事情』、12頁。为了安定华北的“民心”,1940年5月,日本军政当局再次强调“联银券”与日圆维持等值联系。日本军政当局反复声明背后的危机感,正如当时日本舆论所指出的:“今日联银券价值下跌的情况并未发生改变,即使一次性将之贬值也不会达到稳定的效果,而每将之贬值,则唯恐将导致政道的紊乱,故而在方法上必须最为慎重。联银券与日圆等值挂钩所涉及之影响,不仅在于会对华北民众的生活造成痛苦,且对于物资不断流出的我国也是相当头痛的问题”。(26)「社説:連銀券の臨機措置」、『大阪毎日新聞』1940年5月16日。日本军政当局不断宣称“联银券”与日圆等值联系,不仅将其视为在经济上支持华北伪政权的具体表现,而且将其视为确保日圆经济体系稳定的重大问题。
然而,尽管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开发”重点集中于军需物资,物价高涨之风却并未得到抑制。当时日本经济学界从日本对华北“开发”事业及华北国策会社集团资本所受影响之角度,就是否坚持“联银券”与日圆等值联系进行过专门讨论,支持等值联系者认为:(1)从充分获取军费及华北“开发”费的角度看,需要利用“圆元等值”政策来发行大量纸币;(2)从“开发”华北的角度看,因不易获取来自日本的投资,故有必要将“联银券”作为日圆之“分身”;(3)若“圆元等值”政策发生变动,华北投资的资本及日本侨民的存款、债券等都会发生混乱;反对等值者则认为:若坚持“圆元等值”政策,将导致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在财政上出现“赤字化”,过多的支出将逐渐使其开发事业“窒息”,因此,为了可持续地“开发”华北,“不要束缚于目前不自然且不稳定的圆元等值联系,当下急务乃寻求合理且安定化之策略”。(27)高橋亀吉「連銀券、軍票、蒙彊券対策私見」(1940年7月)、『連銀券、軍票関係文書綴』、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中央-軍事行政経理-317。
然而,日本学界的讨论并未得到日本军政当局的响应。事实上,当时日本军政当局已决议通过对国策会社产品采取价格调控的手段来减少“联银券”的增发,即“国策会社产品之物价及费用,在成本范围内允许提高其价格,通过恢复原本之利润,以减少日本对开发资金的投入”;“将煤炭、盐等对华中输出物品的价格提高至适当程度,以之克服华北对华中的支付超出问题”。(28)1940年11月日本军政当局出台的《对华时局紧急对策》中,再次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加以干涉,即国策会社在当地的产业开发,严格限定于铁矿、煤炭、盐等基本国防资源,要确保对这些重要事业的资材及资金供给,具体措施为:(1)事业计划的根本性改订;(2)会社经营能效上的根本性措施;(3)非重点事业会社的综合性整理及移管;(3)过剩人员的整理及转业等。参见《日本内阁对华经济紧急对策》(1940年1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与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第31页。这些策略取得了一定效果,“联银券”的发行量自1940年7月以后逐步减少,8月即降至5.7亿元以下,此后略有膨胀,1940年末控制在7亿元左右。
“联银券”的价值危机是否真正得到解决?在1940年12月中国通货制度调查秘密委员会给大藏省的调查报告中提到,鉴于“联银券”的对内价值及对第三国通货汇兑之实际情况,与对日圆等值联系之政策并不相符,其寄希望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顶层的调控,“作为华北通货工作之基干……不仅使华北作为东亚经济圈之成员承担其使命,作为当前之要务,乃要使该行认真检讨关于华北开发或对内对外价值维持的调节策略”。(29)「支那通貨制度調査秘密委員会報告書」(1940年12月)、『支那通貨制度調査秘密委員会報告書 昭和15年12月』、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中央-軍事行政経理-323。1941年1月,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秘密报告中,专门述及此次“联银券”价值维持工作的效果与不足:
去年8月以来(华北物价)逐步稳定,特别是粮食价格打破往年之例,抑制了涨势,其原因在于通货紧缩政策的成功。然而8月实行的日满华进出口物资价格调整之政策,又导致华北经济不安,伴随着内地调整费的留保及留保费率的迟迟不决,华北再次出现物价高涨之气象。为了维持联银券的价值,不得不考虑采取其他措施……华北开发相关各会社及其他商社的金融极度梗塞,经营上出现障碍,例如华北交通会社、眼下处于解散中的兴中公司、华北电业株式会社等,都对大量负债感到困难,由此陷入经营困境。(30)「北支政務並経済の現況」(1941年1月13日)、『陸支受大日記(普)別冊 昭和16年1月—5月 (昭和16年1月27日 東京参謀長会議に際し 北支方面軍状況報告)』、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大日記-陸軍省-陸支普大日記-S16-28-217_2。
在日本军政当局看来,“联银券”价值维持工作虽然暂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谈不上成功。为了维持低物价政策,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已出现资金周转梗塞等问题,如东亚电力兴业会社等,“本年度的事业计划在最近物资及金融津贴困难的实情下,处于不得不顺延乃至中止的穷困之状”。(31)東亜電力興業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五回)、1939年10月1日—1940年3月31日、三菱経済研究所蔵。另一方面,一些国策会社如华北交通会社等,虽已负债累累,却仍对股东支付高额红利。(32)華北交通株式会社「営業報告書」(第二回)、1940年度、三菱経済研究所蔵。这都说明尽管国策会社的经营出现严重危机,但其背后的投资者并没有因“联银券”的通货膨胀而蒙受任何实质性的损失。
三、“联银券”的再次危机与日本军政当局的应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沦陷区出现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联银券”与日圆价值脱钩问题再次成为了日本经济界热议的话题。因军事开支过高导致“联银券”的增发,引起物价飙升,迫使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经营生产需要更多资金的投入,由此华北经济陷入“货币增发—物价膨胀—货币增发”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华北沦陷区的恶性通货膨胀,亦使日本资本输出华北的利润大幅减少,故而日本军政当局再度开始研究将“联银券”与日圆等值联系脱钩的可能性。1942年夏,日本大藏省理财局拟订《关于改订联银券对日圆币值办法之草案》,提出“联银券对日圆的改订比价预定为联银券100元兑日圆40圆”;“对华中货物出入交易以‘特别圆’本位为原则”;“对外国进出口交易实行‘特别圆’本位”。(33)该文件收录于昭和财政史编辑室:《昭和财政史》(第四卷),转引自浅田乔二等著,袁愈佺译:《1937—1945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所谓“特别圆”,是指1941年7月英美冻结日本资本后,日本炮制的虚拟贸易汇兑单位,这意味着此后日本对华北、华中沦陷区的贸易收支将转向以日圆或“特别圆”为本位的新经济体系。然而若切断“联银券”与日圆的等值联系,对于向华北不断输出资本的国策会社集团而言,必将在汇兑上蒙受巨大损失。按日本军政当局初步估计,华北开发会社及其子会社、准国策会社、一般企业的损失高达7.4亿日圆,相反因互存协议而拥有横滨正金银行及朝鲜银行日圆账户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却可从中获得13.8亿日圆的利益。(34)该文件收录于昭和财政史编辑室:《昭和财政史资料》,转引自浅田乔二等著,袁愈佺译:《1937—1945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第261—262页。
面对其中的损益,日本军政当局究竟如何考虑?从其所设想的“联银券”脱离日圆等值体系后对蒙受损失的国策会社的救济政策中,似可发现一些端倪。面对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在财务上出现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日本军政当局所考虑的救济办法为“致力于提高子会社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获取低利的融资,极力平衡收支”;为了尽可能减少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以“联银券”为本位而造成的损失,应“在当地发行开发债券,主要使之充当日圆债务来办理”。(35)「連銀券対日本円価値改訂ニ伴フ実施要領」(1942年4月19日)、『連銀券、軍票関係文書綴』、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中央-軍事行政経理-317。
显然,日本军政当局对于“联银券”价值跌落造成的后果,有过精密的考量。其预想的后果之一,即处于日圆经济圈内的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各会社的资产额、财务收支乃至投资者的利润都会相应“蒸发”,如当年中华航空会社将损失1410万日圆,而华北车辆会社将损失720万日圆等。在日本军政当局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主要依靠企业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获取低息融资来寻求收支上的平衡,即“联银券”贬值带给企业的损失,将由“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承担。但从历史的结果看,日本军政当局并没有选择切断“联银券”与日圆的等值联系,而是通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等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联银券”融资的方式,来满足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对“开发”资金的需求与收支平衡。这只能说明日本军政当局为避免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因“联银券”跌落蒙受过大的损失,最终还是选择维持“联银券”与日圆等值联系的政策。
1943年以后,日本对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投资已无法达到华北物价的高涨水平,企业必须依赖华北当地的资本以解决内部资金短缺的问题。1943年3月,“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宣称,“联银券”与日圆等价政策此后绝不更改,而日本军政当局也声明,参战之下华北对于通货之信念,绝对不会稍有动摇。(36)汪时璟:《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942年度营业报告》(1943年3月27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与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第965页。此前,“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已与日本银行签订2亿日圆的信用契约,将“联银券”彻底与日圆等值捆绑。“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与日本银行所谓的“互存借贷”关系,使日本军政当局对“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得以一味地索取,“即现在日本国内与大陆之间尽管物价水平明显拉开差距,因为依然坚持圆元等值或(中储券一百元兑换军票)十八圆汇率,故而在日中国际借贷关系中我方不得不增加账目支出。现今我国在大陆的军费支出及对军需物资的采购、资源开发等所需主要资金,乃利用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与中国政府银行之间的互存账户,通过现地通货的发行来供给,故而我方在账目上的大量支出,必然导致当地通货流通量的膨胀”。(37)中国経済文化研究会『北中支インフレーションとその対策』、中国経済文化研究会、1944年、13頁。因银行间这种“互存借贷”关系的存在,“联银券”的流通量在1943年12月末进一步膨胀,达40亿元,而至1944年4月更达48亿元。
1945年1月,在日本军政当局确立的“战时中国经济对策”中,为了竭力维持“联银券”等伪币的价值,防止日圆经济体系的崩溃,要求“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须大力调整货币的发行量,并实行货币的按期回收,以确保“日本帝国”的信用,国策会社则被要求“打破在华日人的经济与国策会社的现状,使之更好地为战争需要服务,同时实现善邻的经营方法”。(38)《日本政府确立中国战时经济的对策》(1945年1月11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与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第48页。由此可见,日本军政当局既要求在“联银券”与日圆等值联系的体系下减少货币对产业的投入,又要求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特别重视粮食、生活必需品、煤炭等的增产,发掘各种运输能力,加强物资流通,以敷战时日本物资动员计划的急迫需要。日本对华北沦陷区货币政策中的这一结构性矛盾延至日本战败,并无任何改观。
四、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当地银行的债务关系
目前中国学界关于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等国策会社的资本问题研究,成果十分有限,对于这些会社与当地傀儡银行间之债务关系,亦鲜有涉及。(39)张利民对华北开发会社的资本情况进行过较细致的分析,但未就该会社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之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参见张利民《日本华北开发会社资金透析》,《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战时日本经济学界即已发现,华北沦陷区所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在于日本军政当局为掠取煤、铁、盐、棉花等军需资源而由“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等华北当地傀儡银行放出巨额“开发”资金所致。(40)中国経済文化研究会『北中支インフレーションとその対策』、3頁。这些巨额资金许多是以国策会社社债的形式放出的。因此,有必要厘清华北开发会社与包括“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内的华北当地傀儡银行间错综复杂的债务关系,以揭示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战时日本对华北通货政策的另一种联系。
在法理上,日本军政当局对于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之社债发放,给予极优厚的待遇。按《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法》的规定,该会社可以发行五倍于投入资本的华北开发债券,而债券到期的本息则由日本政府保证偿还。(41)「北支那開発株式会社並関係会社の全貌」、『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関係会社関係』(第二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21_00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该会社第六次股东会议决议,该会社可发行十倍于投入资本的华北开发债券。至1945年1月,华北开发会社共投放47批“华北开发债券”,社债总额高达19.52亿日圆。(42)「上海北支那開発債券大口買取先調」(1945年1月31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三十八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38。然而,查阅“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行史及华北开发会社经营档案,该行历史上仅有一次购入过该债券,即1941年12月第19批“华北开发债券”,总额不过0.05亿日圆,且该笔债券年利息高达七分,以1948年12月20日为限全部偿清。“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购入该笔债券后,即向其伞下银行及伪邮政总局二次销售,从中获取了相当的利润。(43)中国連合準備銀行顧問室『中国連合準備銀行五年史』、 中国連合準備銀行、1944年、42頁。显然,“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对华北开发会社所发行债券之吸收,主要体现中日经济“提携”的象征意义,而非该行与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之间的常态债务关系。
1943年5月后,日本军政当局要求日本在华企业所需“开发”资金,应极力依靠当地金融机构解决。(44)按日本军政当局之要求,1943年度华北开发会社社债9.5亿日圆与华中振兴会社社债10.5亿日圆,须于当地解决。其具体处理方案为:“(一)社债(或长期借款等)尽量由当地一般金融机构消化。在一般金融机构消化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其他方法于当地以适当措施加以吸收;(二)社债以“联银券”或“中储券”表示;(三)社债的发行利率在与华北开发会社或华中振兴会社之子会社的融资利率间发生逆差的情况下,考虑对管理上仍有余力的子会社逐步提高融资利率。此外,对于华北开发会社或华中振兴会社的钢材采购资金及供应其子会社的短期运转资金(粮食资金、储煤储矿资金等),原则上不通过我国资金的调入,而由当地银行的账户透支来解决;小型熔炉相关资金则由我国调入。”参见「在支日系事業ノ企業資金現地調達ニ関スル件」(1943年5月31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二十七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27。至1945年初,华北日伪财政已严重失衡,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向日本国内与华北日资金融机构之贷款“均告绝望”,所需资金只能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借入。(45)《北支那开发会社概况》(1945年11月5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华北经济掠夺》,第397页。可以说,华北国策会社集团是在债务缠身中走向日本战败。通过日本军政当局对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指令关系文书可以发现,尽管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当地银行的债务关系极其复杂,但基本可归为以下三类。
第一,事业扩张型借款。(46)华北开发会社与当地银行的债务关系,并不能通过中文档案完全体现。虽然可以在“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档案中发现一些债务情况,然而这不过是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该行债务的一部分。如1943年8月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津岛寿一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签订借据,借入“联银券”1250万元,其中利息为四分五厘;1944年6月30日续借“联银券”3500万元,利息四分七厘;1945年3月续借“联银券”5.39亿元,利息四分五厘等。详见《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在华北的经济侵略活动》(1943年8月至1945年3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与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第140—142页。为了扩充华北交通会社、华北东亚烟草会社、开滦煤矿等企业的事业经费,1943年1月,华北开发会社从朝鲜银行北京分行、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扩大透支额度(即短期借款)至0.2亿日圆,年利息四分五厘,还款期限为1944年3月31日,华北开发会社方面无需任何担保。(47)「当座借越限度拡張ニ関スル認可申請ノ件」(1943年1月13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十九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19。这笔借款说明,早在日本军政当局对在华会社下达指令之前,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已开始通过当地银行筹措“开发”资金。
1943年5月,华北开发会社内部出现资金短缺问题,为此该会社从朝鲜银行北京分行、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扩张透支额度至0.8亿日圆,朝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年利息为四分五厘,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为五分,还款期限为1945年3月31日,其中粮食采购资金为0.2亿日圆,期限为1943年12月31日,会社方面无需任何担保。(48)「当座借越限度拡張ニ関スル認可申請ノ件」(1943年6月2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二十四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24。这笔借款以事业费名义贷出,粮食采购是其主要用途之一。
1943年10月下旬,华北开发会社及其子会社为扩充当年度事业资金,从天津银行、济南银行借款“联银券”0.2亿元,年利息五分,还款期限为10年,经双方协议该笔借款日后可转为社债。(49)「現地資金借入ニ関スル認可申請ノ件」(1943年9月27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二十六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26。
1943年11—12月间,华北开发会社及其子会社为扩充年度事业经费,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不动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安田储蓄银行天津分行、大阪储蓄银行青岛分行借款“联银券”0.25亿元,还款期限为10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年利息为六分,其他储蓄银行年利息为五分五厘,经双方协议,该笔借款日后可转为社债。(50)「現地資金借入ニ関スル認可申請ノ件」(1943年11月6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二十八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28。
1944年1月下旬,为扩充前一年度事业经费,华北开发会社向朝鲜银行北京分行、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各借款“联银券”0.15亿元,总计0.3亿元,年利息为四分五厘,还款期限为10年,经双方协议该笔借款日后可转为社债。(51)「現地資金借入方認可申請ノ件」(1944年1月11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二十九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29。
1944年2—3月间,因华北国策会社集团急需短期资金3.1亿日圆,而华北开发会社当时财政收入仅1亿日圆,故向朝鲜银行北京分行、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扩大透支额至“联银券”2亿元,年利息为四分五厘,还款期限为1945年3月31日,会社无需任何担保。(52)「当座借越限度拡張ニ関スル認可申請ノ件」(1944年2月25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三十一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31。这笔借款,开启了“联银券”大量流入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绪端。
1944年6月,华北开发会社及其子会社为扩充当年度事业经费,从朝鲜银行等八家银行借款“联银券”1.65亿元,期限为1年,朝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利息为四分七厘,天津银行、济南银行、青岛实业银行利息为五分五厘,不动储蓄银行、安田银行、大阪储蓄银行利息为六分,经双方协议该笔借款日后可转为社债。(53)「現地資金借入方認可申請ノ件」(1944年2月25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三十六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36。
1944年7—9月间,华北开发会社及其子会社为扩充当年度事业资金,从朝鲜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等10家银行及保险会社集团借款“联银券”2.2亿元,利息平均为五分四厘,还款期限为10年,前5年不必偿还,后5年可均额偿还,经双方协议该笔借款日后可转为社债。(54)「現地資金借入方認可申請ノ件(昭和十九年度第二四半期分220000千圓)」(1944年7月24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三十六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36。
第二,物资采购型借款。为了确保棉花、棉籽对日“满”的“特殊供应”,在日本军政当局授意之下,华北开发会社于1943年8月成立了华北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同时为确保交通、电业、煤炭开采业等部门劳动力所需的粮食,华北开发会社还成立了“华北煤矿粮食配给组合”“粮谷开发组合”。作为这三家企业的棉花、粮食采购资金,1943年10月,华北开发会社从朝鲜银行北京分行、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扩大透支额度至“联银券”7.5亿元,年利息为四分五厘,还款期限为1945年3月31日,无需任何担保。(55)「当座借越限度拡張認可申請ノ件」(1943年11月6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二十八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28。
1944年12月,作为华北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的棉花、棉籽采购资金,华北开发会社从朝鲜银行北京分行、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扩大透支额度至“联银券”14亿元,年利息四分七厘。(56)「当座借越契約締結方認可申請ノ件(昭和十九綿花年度第一期分1470000千圓口)」(1944年9月2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三十七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37。
第三,当地特别发行债券。1944年6月,第一批华北开发债券由华北开发会社发行,发行额为“联银券”0.2亿元,具体偿还方式与期限情况不详。(57)「北支開発債券(特第一回)政府保証印刷入方ノ件」(1944年4月15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三十一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31。
1944年7月,第二批特别华北开发债券由“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发行额为“联银券”0.4亿元,年利息七分,3年内不必偿还,此后7年间每半年在约定期限内偿还“联银券”60万元以上,发行后10年内偿清。(58)「北支開発債券(特第二回現地発行分)発行認可申請ノ件」(1944年5月8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三十二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32。
1944年12月,第三批特别华北开发债券由朝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天津银行、济南银行、不动储蓄银行、安田储蓄银行、大阪储蓄银行、青岛实业银行、日本劝业银行等发行,发行额为“联银券”0.3亿元,年利息五分五厘,3年内不必偿还,此后每年在约定期限内偿还“联银券”300万元以上,至1949年12月1日还清。(59)「北支開発債券(特第三回現地発行分)発行認可申請ノ件」(1944年11月2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三十五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35。
1945年3月,第四批特别华北开发债券由朝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天津银行、济南银行、不动储蓄银行、安田储蓄银行、大阪储蓄银行、青岛实业银行、日本劝业银行等发行,发行额为“联银券”0.4亿元,年利息五分五厘,3年内不必偿还,此后每年在约定期限内偿还“联银券”400万元以上,至1949年12月1日还清。(60)「北支開発債券(特第四回現地発行分)発行認可申請ノ件」(1945年2月8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北支開発及中支復興株式会社/会社ニ対スル認可指令関係』(第三十八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E-2-2-1-3_13_12_038。
以上四批特别华北开发债券都由日本政府担保本金、利息,到期如数偿还。
综合来看,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从当地银行的借款,维持着“予取予求”的关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性。在两者的债务关系中,1943年后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不断增加事业经费的投入,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该集团从当地银行的“联银券”借款,这也是“联银券”不断巨额增发,导致华北沦陷区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1943年下半年后,因战局恶化与“现地自活”的需要,日本军政当局加紧了对棉花、粮食等生产生活物资的掠取。以笔者仅见的两笔华北开发会社的物资采购型借款来看,其金额即高达“联银券”7.5亿元与14亿元之巨,而1943年12月(借款则在10月)与1944年12月“联银券”的发行总量也不过37.6亿元与158.4亿元,(61)大蔵省『昭和財政史·資料』(第17巻)、東洋経済新聞社、1981年、265頁。前者约占后者的19.9%与8.8%,说明战争后期“联银券”的另一货币功能——对物资的“征发”性愈加凸显。1944年6月后,华北国策会社集团除在日本国内发行日圆债券之外,另在华北沦陷区发行四批“联银券”特别债券,这些债券的发行额不大,但条件相当优惠,尤以第二批年利息高达七分,体现了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对“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某种“关照”,这或许是出于展现日伪在经济上“相互提携”与“共赴时艰”的用意。
五、结语
设立国策会社与发行日系货币、伪币,是全面抗战期间日本控制中国沦陷区经济的两大策略,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战时环境下以华北开发会社为首的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形成,其主要任务即在于掠取华北沦陷区的资源。“联银券”作为日圆的“分身”,逐步成为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内部投资、融资的“血液”。在两次“联银券”危机中,华北国策会社集团都成为日本军政当局的统制对象,其经营方针集中于对军需资源的开发与对中国民间资本的利用。伴随华北国策会社集团的扩张,日伪当局不断增发“联银券”,导致华北沦陷区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可谓战时华北沦陷区经济不断恶化的主要推手。
“联银券”作为日圆集团的一员,日本军政当局始终坚持“联银券”与日圆等值联系,这既是为了确保日圆经济体系的稳定,也是为了维护国策会社股东的利益。华北沦陷区的物价高涨与华中沦陷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导致华北物价恶性飞涨的根本原因,在于粮食等一般物资的普遍不足,解决的渠道在于促进生产、扩大进口,这在“联银券”与日圆等值联系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做到。而华北沦陷区物价的高涨,带动对日出口物资价格的上升,日本军政当局又不得不进一步增发“联银券”,这必然导致华北经济陷入“货币增发—物价膨胀—货币增发”的恶性循环之中。
考察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当地银行的债务关系可以发现,华北国策会社集团是日本军政当局利用“联银券”大量“征发”民间物资的实际操作者。1943年后,日本军政当局因战局恶化与“现地自活”的需要,加紧对棉花、粮食等军需物资与生活必需品的掠取,“联银券”在货币功能上的“征发”性质愈加凸显,这充分体现在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从当地银行的巨额“联银券”借款中。在对民间物资的“征发”上,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联银券”的紧密结合,“联银券”对于华北国策会社集团而言,则不仅是“开发”资源的“血液”,也是其掠取资源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