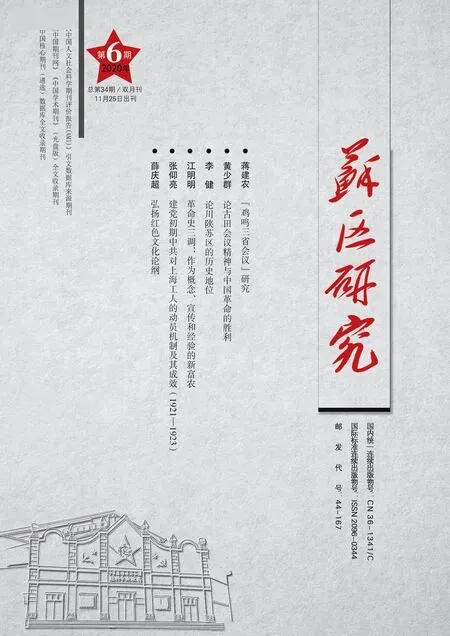《毛泽东选集》中“陕北肃反”注释修订的历史变迁
魏德平
提要:《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肃反”注释的确立和修订,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指向。新中国成立后,1953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关于“陕北肃反”注释,基本以西北高干会颁布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为权威依据,强调了“左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朱理治、郭洪涛在肃反中的责任,肯定了刘志丹、高岗作为中共西北党史“正确路线代表”的政治地位。“高饶事件”后,高岗作为西北高干会树立起来的“正确路线代表”政治地位彻底坍塌。随后,高岗名字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之中被隐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对党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并依据此精神形成了中共中央重新处理“陕北肃反”争议问题的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关于“陕北肃反”注释根据上述政治要求和认识,进而隐去了原注释朱理治、郭洪涛的名字。《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人名“显”与“隐”之间的变化,反映出中共中央在不同时期对党内重大争议历史问题处理认识的发展,也揭示了学术研究和政治定性之间的微妙关系。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亲自主持对《毛泽东选集》进行统一编辑和注释工作,甚至亲自撰写相关注释。(1)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1989年7月),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参与编辑工作的胡乔木回忆:“建国以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主席提议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2)《党的历史决议》,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所以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与其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胡乔木回忆:“历史决议草稿交给中央全会之前,已在相当大的范围进行了讨论。交给全会之后,讨论的范围更大了。讨论是频繁、认真、深入的。每一句话经过斟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段落,讨论得很仔细。那时中央领导层的讨论也很认真。这种讨论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每次修改都是以这些讨论为基础。这样地讨论历史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文件。”(3)《关于历史问题决议和七大》(1991年11月7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3页。“它倾注了毛主席的心血,也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了。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4)《党的历史决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8页。毛泽东和当时中共中央核心层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重视和关切,奠定了其在中共党内的权威政治地位。这也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亲自提议将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重要原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介绍“陕北肃反”时写到中共中央抵达西北根据地,“挽救了‘左’倾路线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5)《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71页。。新中国建立后重新整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还对这段涉及“陕北肃反”的正文作了详细注释:“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路线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6)《毛泽东选集》第3卷“高饶事件”前印次,“高饶事件”后印次原注释中高岗名字被删除。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十一月,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7)《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高饶事件”前印次,第1000页。此后,这条注释成为新中国“陕北肃反”官方解释的核心版本,也是其他各种相关出版物关于该事件表述的理论和历史依据。新中国建立至今,《毛泽东选集》共发行两版,对“陕北肃反”注释也作了两次修订。“陕北肃反”注释的确立和两次修订,有很强的政治指向,这既是中共现实政治斗争对党史的反作用,也折射出中共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党史问题认识发展的复杂历程,值得对此问题做深入研究和拓展。
当前《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肃反”注释确立和修订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和考证的问题。首先,官方权威出版物对《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肃反”的介绍还需要进一步考订。如对第二版《毛泽东选集》注释演变进行专门介绍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因“使用的底本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出版说明第1—2页。,故未能反映该注释确立和此前修订变化的基本情况。《〈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对“陕北肃反”注释的解释也存在史实性错误,如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35年“十一月三日将刘志丹等释放”(后文将对此问题进行专门介绍)(9)《〈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第394页。。其次,学术研究对《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肃反”注释的说明和使用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朱理治传》对“陕北肃反”问题有较为深入研究,但在介绍《毛泽东选集》对“陕北肃反”注释确立时,所用版本为“高饶事件”后经过修订的版次,未能反映出该注释的本来面貌。(10)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28页。第三,官方出版物关于“陕北肃反”注释变化的内在原因,目前也有待系统全面梳理。如第二版《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肃反”注释修订原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认为是“根据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印发的有关文件精神,对原注的表述作了改动”(11)《〈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第394页。。但是,如认为“陕北肃反”注释仅以此为修订主要依据,似也难完全自圆其说,因为该文件主要是再次解决“陕北肃反”争论史实认识分歧(12)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61—362页。,所以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13)《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原则与该注释修订之间的关系。因此,《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肃反”注释确立和修订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笔者有幸收集到1942年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问题作出处理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4)再次征引该文件,一律简称《决定》。和1983年中共中央出台的《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即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附件)等文件文本,因此拟在已经掌握的史料基础上,参照目前公开出版的相关回忆录、专著和研究文章等,对该问题作进一步梳理和研究。
一、《决定》是《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确立的权威依据
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北高干会上颁布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处理的《决定》,强调肃反“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批判和追究了朱理治、郭洪涛等人在肃反中的责任,肯定了刘志丹、高岗等肃反受迫害者的历史地位。《决定》的主要结论被凝练载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在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被进一步肯定和维护。因此,《决定》是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肃反”注释的权威依据。
中共中央在西北高干会上对“陕北肃反”问题作了重新处理。西北高干会是西北党史乃至中共党史上都非常重要且影响深远的一次会议。西北高干会自1942年10月19日开幕,至1943年1月14日结束,历时88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属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干部266人出席会议。中共中央高级学习组成员和中央党校209名领导干部到会旁听。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期望甚高,在开幕会议上发言强调:“高干会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5页。“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毛泽东不但出席开幕和闭幕式。而且在会议期间作了两个重要报告。”(16)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一个区域性的会议,规格之高和时间之长,在中共的历史上是空前的。”(17)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398页。在西北高干会上,中共中央对西北党史上长期存在激烈争论的“陕北肃反”问题作了集中处理,否定了1935年11月26日由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颁布的《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并于1942年12月12日通过《决定》。关于“陕北肃反”的性质,《决定》指出:“1935年9、10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从陕北历史问题检讨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错误肃反开始之前,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与红军,另一方面是以朱理治、郭洪涛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18)《中共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42年12月12日),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因此,“中央认为在一九三五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与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中共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42年12月12日),《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04页。。《决定》确立了刘志丹、高岗在西北党史上“正确路线”代表的政治地位,也明确了朱理治、郭洪涛作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主要责任人的政治定性。
《决定》也对西北高干会确定的应对“陕北肃反”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作了组织处理。关于“陕北肃反”主要当事人的责任问题,《决定》认为:“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以及他们打击刘高抬高自己预定的企图,就把党内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的性质。他们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压倒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满足自己篡夺整个陕北党政军领导地位的目的,这样就造成了当时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决定还对上述责任认定做了分析说明:“朱理治同志是当时陕北党的最高负责者(代表团书记和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在一九三五年夏来陕北前,即抱着陕甘党内存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成见。来到陕北后便以钦差大臣的架子,不与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作任何谈话,不作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只是片面听信郭洪涛同志关于苏区红军党和群众工作及干部等方面的情况报告(郭是一九三三年底到达陕北,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打击过陕北特委重要负责同志马明方等,一九三四年七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打击过刘志丹、高岗,企图夺取二十六军及陕甘党的领导地位,但这种企图受到抵抗而未能成功)。而郭洪涛同志所供给的报告材料,基本上又是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性质。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对陕甘边及二十六军的主要干部是右倾取消主义者和右派反革命的包庇者(其实刘、高曾对右派作过斗争的)的共同认识。”“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作了‘肃反’的准备。”因此,“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应该负最重要的责任”。(20)《中共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42年12月12日),《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02—303页。在对“陕北肃反”性质和责任等重新分析和定性的基础上,《决定》最后对肃反主要责任人作出了处理结论:“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本应开除党籍。估计他们曾为党作过一些工作,本着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予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撤销朱理治同志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之职务,撤销郭洪涛同志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并限定朱郭二同志在三年以内不能担负重要的党的工作。由中央组织部与西北局继续搜集材料,如果发现他们还继续对党欺骗,而不诚意改正他们的错误,党就必须重新讨论他们的党籍问题。”(21)《中共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42年12月12日),《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304页。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的处理,以“路线斗争”方式总结了西北地区中共早期的革命斗争,树立起了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强调朱理治、郭洪涛执行的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造成了“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的严峻局面。上述结论代表了参加会议的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参加会议的原西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尤其是“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当时的基本共识。(22)魏德平:《西北高干会解决西北党史争论问题结论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3期,第17—23页。
西北高干会后,中共中央对《决定》作了进一步的维护和升格。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的定性和处理并未能完全平息当事人的分歧和争论。郭洪涛回忆:他在接到《决定》等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的有关文件后,即找相关领导反映自己对“陕北历史问题和对我个人结论的保留意见”,随后又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负责领导西北局工作的任弼时提出了四条保留意见,其中关涉“陕北肃反”问题的有三条:“第一,高岗说陕北特委和我在实际工作中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不符合事实的;陕北党和谢子长同志领导创造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第二,高岗说陕北和陕甘边是一个苏区,并说成是他们(指高岗等人)创造的,是不符合事实的;陕北苏区是陕北特委和谢子长同志领导创造的。第三,高岗说我主持肃反,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不是肃反主持人,我是反对逮捕刘、高、张等红26军领导干部的。”(23)《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朱理治也因为《决定》对自己的定性和处理而内心倍感煎熬和委屈:“从受人尊敬的党的高级干部,跌落成为与李立三、张国焘并列的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被指为‘有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的人。他内心非常痛苦,常常彻夜难眠。”(24)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17页。郭洪涛等对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定性和处理的不满和异议在一定范围内扩散后,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后果。张秀山回忆:“有人对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有不同意见,对西北党的历史有另一套说法,否定《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即《决定》——引者注)。这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七大代表和一些西北的干部中引起争论,造成了一些同志的思想混乱。”(25)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58页。上述言论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西北高干会处理“陕北肃反”问题《决议》的权威性。
针对西北高干会解决“陕北肃反”诱发的争论,中共中央重申和维护了《决议》的权威性。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问题处理引发的争论逐渐引起中共中央的关注和重视。中共“七大”前,中共中央获悉“陕北肃反”当事人对西北高干会关于肃反重新处理存有异议和争论后,曾征求部分“陕北肃反”当事人的意见并准备召开会议加以解决。(26)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58页。中共“七大”后,中共中央委托朱德、任弼时、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主持召开了西北历史座谈会,专门解决“陕北肃反”争论。西北历史座谈会于1945年6月26日召开,至8月2日结束,历时38天。(27)关于西北历史座谈会召开的具体时间,说法有些差异。有些著作明确指出是本文所用时间,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9页;《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89页;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58页。《朱理治传》等认为是“七月”,且结束时间均未明确指出。高岗、朱理治、郭洪涛、张秀山、习仲勋等“陕北肃反”当事人都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会议期间,“西北很多同志在会上发言,再次对陕北的‘左’倾错误进行批评”(28)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58页。。会上,朱理治、郭洪涛对自己在“陕北肃反”中的错误也作了进一步的自我批评。7月10日,朱理治在会上发言,详细介绍了自己到西北根据地工作的经过和“陕北肃反”始末,承认错误,说清事实。(29)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28页。郭洪涛也在西北高干会上作了“自我检讨”。(30)《郭洪涛回忆录》,前言第6页。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的定性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得到进一步肯定和加强。参加会议的张秀山回忆:“西北很多同志在会上发言,再次对陕北的‘左’倾错误进行批评。座谈会经过认真讨论,再次澄清了西北党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是非,维护了《党中央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即《决定》——引者注)。”(31)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58页。因此,“西北党史座谈会,也可以说是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继续,或者说是延安整风的深入”(32)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62页。。西北历史座谈会为西北高干会《决定》的权威化提供了保障。随后,中共中央将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的定性结论升格成为中共的权威公开结论。中共“七大”后,中共中央最终将《决定》的主要结论凝练地载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会议上原则通过。此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稿又历经中共中央多次修订,直到8月9日中共中央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才一致通过。中共七届一中全会最终确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介绍“陕北肃反”时写道:中共中央经过长征抵达西北根据地,“挽救了‘左’倾路线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3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1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陕北肃反”时,因是概要回顾中共党史,所以对肃反着墨不多,仅用上述数语介绍,但是对肃反性质和造成危害的定性则是非常明确的。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当时对“陕北肃反”的权威裁定。
《决议》最终成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陕北肃反”注释的理论和历史依据。西北历史座谈会强化了西北高干会处理“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权威性。西北历史座谈会通过讨论,将西北高干会解决“陕北肃反”问题遗留的争论问题作了再次处理。座谈会按照西北高干会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精神和决议,进一步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重申了高干会关于肃反问题的相关结论,并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而载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选集》正式统一修订出版时收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对“陕北肃反”作了详细注释。胡乔木回忆:“建国以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主席提议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1950年8月19日,毛主席致中央政治局的信说:‘此件拟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续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陈秦二同志名字,请加审阅,提出意见。’”“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最后编入第三卷于1953年4月出版。”(34)《党的历史决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8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收录进《毛泽东选集》时,在其注释部分对“陕北肃反”作了如前文所引的详细注释。(35)《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高饶事件”前印次,第1000页。这个注释不仅是对《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内容的补充和说明,也是对“肃反”结论的进一步权威化。《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肃反”注释主要源于西北高干会《决定》相关结论(36)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523页。,而这场会议又与高岗密切相关,高岗在会议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树立为“正确路线代表”。因此,当“高饶事件”发生高岗受政治批判和历史清算后,《决定》某些内容和结论受到质疑,《毛泽东选集》中“陕北肃反”注释相应作出修订也就有其必然性。
二、“高饶事件”是《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修订的重要动力
“高饶事件”是动摇高岗作为中共党史上“正确路线代表”地位的关键性事件。“正当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需要全党团结一致地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共产党内出现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严重事件。”(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高饶事件”的发生是高岗人生轨迹发生决定性逆转的关键点,终结了高岗的政治生命,并最终导致其自杀身亡。在处理“高饶事件”期间,中共中央对高岗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和历史清算。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对西北高干会出台的《决定》也提出了质疑。高岗作为西北高干会树立起来的“正确路线代表”的历史和政治地位彻底坍塌。随后,高岗的名字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陕北肃反”注释之中被隐去。
“高饶事件”是动摇高岗作为中共党史上“正确路线代表”地位的关键性事件。“高饶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高岗问题的处理逐渐升级。毛泽东发现高岗“搞阴谋”后,“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一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指名地批评高岗。”12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多次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等谈话,商讨解决高岗问题。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在内的29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不点名但是又非常明确地在中共高层中强调了高岗问题的严重性。(38)《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280—281页。随后,中共中央对高岗进行了彻底的政治批判和历史清算。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1954年2月25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周恩来“综合四十三人的发言和他们揭发的材料”,归纳出了高岗十方面的主要问题。最后,周恩来对高岗问题作了定性说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0页。3月26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全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周恩来批判了高岗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强调: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经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40)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页。1955年3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岗定性为“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开除出党。(41)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2卷,第492页。至此,中共中央对高岗的批判和清算已经完全公开化。此时高岗在中共党内的形象与西北高干会期间相比已然判若天渊。此时将高岗作为中共党史上“正确路线代表”继续保留在中共权威著作《毛泽东选集》之中,已经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很不适宜。因此,《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肃反”注释的修订,尤其是去掉高岗作为“正确路线代表”评价的内容,已成为当时政治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为中共党内重评高岗历史功过提供了政治条件。
“高饶事件”后,西北高干会《决定》中关于高岗的内容逐渐受到质疑。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会后,曾担任过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北省委书记的马明方受中共中央委托,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从4月4日开始至4月13日结束,期间共举行了8次会议。“出席全国代表会议的西北代表和在京的有关同志共30多人在会上发了言,着重揭露批判了高岗在西北的反党罪行。”(4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马明方》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高饶事件”后,一些在西北高干会上受到批判的西北历史亲历者获得了对西北早期党史、军事的发言权。阎红彦是“高饶事件”后重新获得对西北党史、军事发言权最为典型的例子。阎红彦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是西北早期党史、军事的重要亲历者,较为熟悉高岗在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过程中的功过。阎红彦在对西北党史、军事,尤其是高岗在早期西北革命中的作用与高岗本人说法及西北高干会结论存在严重分歧。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阎红彦当着高岗的面指出:“你不要将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时你是五支队的一个大队长,临真战斗当了逃兵。你根本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43)贺晋年:《阎红彦同志二三事》,中共云南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编:《光明磊落耿直刚强——阎红彦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由于对西北党史、军史与高岗等的不同看法,阎红彦在西北高干会和西北历史座谈会上受到批判,并被指责存在“造他高岗的谣”“闹独立性”“有野心”“搞宗派”等问题。(44)雷恩均:《坚毅忠贞刚正廉洁——敬悼阎红彦同志》,《光明磊落耿直刚强——阎红彦纪念文集》,第213页。阎红彦不认同这些批判和指责,并且积极向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反映高岗的问题。“‘七大’以后,阎红彦同志就高岗问题,向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反映了‘几条意见’,并说:‘高岗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不可信赖,迟早要出问题,望中央注意。’并且要求中央把他的‘意见’记录存档。”(45)薄一波、陈锡联、贺晋年:《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纪念阎红彦同志逝世二十周年》(1987年1月8日),本书编写组编著:《怀念阎红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但是,阎红彦反映的高岗的问题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他自己也因“反高岗”受到批评。(46)毕兴、周天德、贺安华、何盛明:《阎红彦》,《怀念阎红彦》,第195页。“高饶事件”后,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得到了中共中央高层的认可和肯定。“1954年,高岗反党篡权野心败露,党中央查阅了阎红彦当年要求记录存档的档案,证明阎红彦是真诚的,实事求是的,光明磊落的。阎红彦、贺晋年都被通知参加了中央解决高岗问题的会议。会上,刘少奇说:‘在延安,阎红彦同志就对我打过招呼,并向中央反映,高岗这个人品质不好,你们要上他的当,迟早要出乱子,望中央注意。’周恩来也说:‘最近中央查阅了当年阎红彦对高岗的几条意见,历史证明,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是正确的。’”“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专门把阎红彦叫到身边,公开向他道歉。不无感慨地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47)李原:《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3页。阎红彦等西北早期革命参与者重新获得对西北党史、军史的发言权,以及参与对高岗在西北革命历史上“错误”“污点”的揭露和批判,严重动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陕北肃反”注释关于高岗“正确路线代表”评价的史实基础。
“高饶事件”后,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对西北高干会处理“陕北肃反”结论《决定》的态度和认识也发生了改变。1954年2月底至3月上旬,在中共中央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找林枫、张秀山、张明远就如何召开东北高干会议,深入揭批高岗问题谈过一次话。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延安审干,高岗也很‘左’;整风时西北高干会也过火了。”(48)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页。朱理治之子朱佳木回忆:“高岗反党阴谋败露后,邓小平同志托人转告,要父亲对高岗歪曲事实伪造历史提出申诉。”(49)《在〈纪念朱理治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选录)》(1992年10月5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52页。中共中央领导层对高岗个人历史的系统批判和重新认识,动摇了西北高干会和西北历史座谈会确定和重申的“陕北肃反”《决定》结论之中高岗的地位。朱理治、郭洪涛对“陕北肃反”问题的申诉取得的成果也影响到官方出版物对“陕北肃反”的表述。郭洪涛回忆:“在《毛泽东选集》附录《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者注)的一条关于陕北错误肃反的解释中涉及到我。对这个问题,党中央在1960年重新作了结论,我曾请求中央在毛选再版时,对这条解释做适当修改,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同志)已经同意修改。”(50)《郭洪涛回忆录》,第275页。1964年10月4日,朱理治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有一次谈话。谈话内容涉及《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学习和时局》附录中《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十条关于“陕北肃反”的解释。刘少奇向朱理治表示:任何一个决议或者一项政策,不管是中央的或者是谁的,错了都要改,不改就是非马克思主义。……至于历史决议错了,也可以改么。田家英正在修改毛选注,你去找他,就说我说的,毛选注中有错要改,高干会决议错了,可以废除么,就说高干会的决议有很多地方不对,基本上是错误的,应废除。(51)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523页。刘少奇的表态进一步动摇了《毛泽东选集》原“陕北肃反”注释的政治权威性。
“高饶事件”导致高岗从《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中西北根据地“正确路线代表”位置被隐去。高岗在政治斗争中的浮沉直接影响了他在中共党史上的历史定位。“高饶事件”后,中共中央通过各种形式肃清高岗的影响,清查高岗在各个时期的历史,西北高干会树立起来的以高岗为实际核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正确路线代表”的结论受到冲击。这种批判清算必然涉及对高岗历史上参与过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再评价,通过对高岗个人历史的否定,强化对高岗现实政治否定的说服力和权威性。因此,“高饶事件”的发生,高岗政治生命的结束,就成为改写《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高饶事件”改变了高岗的人生轨迹,也推动了《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的改写。因此,“高饶事件”后,当《毛泽东选集》再次刊印时,高岗的名字即从“陕北肃反”注释中被隐去(52)《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高饶事件”后印次,第1000页。,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西北高干会是在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没有毛泽东的首肯,“陕北肃反”注释诸如史实认定、事件定性等其他内容的修订显然时机尚未成熟。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转折。胡乔木回忆:“这个‘历史决议’后来的命运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其中有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的贡献这样的内容,整个决议被从《毛泽东选集》中删除。”(53)《党的历史决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30页。因此,“那条根据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决议写的注也随之不见了”。(54)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523页。但是,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全面拨乱反正的展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恢复到《毛泽东选集》之中。中共中央对党史问题新认识和结论,又在《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修订中得到了体现。
三、“宜粗不宜细”标准是《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再次修订的主要依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开始对中共党史进行重新总结。邓小平多次强调对党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这一原则在中共中央1981年出台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落实和体现。这也成为其后中共中央总结党史问题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1983年,中共中央委托五人小组处理“陕北肃反”争论,根据“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指导精神,出台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1991年第二版《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即是在这样的政治要求和认识条件下进行进一步修订,进而隐去了原注释“左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朱理治、郭洪涛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高层开始对党史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强调对待党史问题要坚持“宜粗不宜细”原则。邓小平复出后,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对待党史问题要坚持“宜粗不宜细”原则。1977年12月20日,邓小平听取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汇报时指出:“要注意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和一切犯过错误而改正了的同志团结起来,问题就容易解决。纠缠历史问题,算历史旧账,会改变政治方向,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5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1978年11月25日,邓小平听取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汇报时讲话强调:“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5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35页。1978年12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指出:“历史问题只能粗搞,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5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45页。1979年3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情况报告会上作报告时强调:“有好多问题应该从大局着眼,不能搞得太细。现在的关键是安定团结。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集中力量向前看。”(5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3页。邓小平关于党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观点,在随后起草和修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得到了体现和落实。1980年3月19日上午,邓小平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强调:“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5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10页。邓小平关于党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观点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得到了落实。1980年5月16日,胡乔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时指出:“小平同志说得很对,宜粗不宜细。还是要按小平同志的要求来做。”(60)《〈历史决议〉要有一种理论的力量》(1980年5月16日),《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1981年5月19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决议稿并未隐瞒或掩饰任何重大错误,只是有些问题没有说得完备,有些次要的问题没有提罢了。这也就是‘宜粗不宜细’。”(61)《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1981年5月19日),《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149页。邓小平关于处理党史争议问题的上述观点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出台,为中共中央重新处理党史遗留问题确立了“宜粗不宜细”的政治准则。此后,中共中央即在坚持“宜粗不宜细”原则下,对中共党史有争议的重大问题进行重新梳理和仲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陕北肃反”争论再次迅速激化。郭洪涛对西北党史尤其是对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结论的新“解读”,是引起争论的主要诱因。1981年下半年,郭洪涛连续在全国政协《革命史资料》第5期发表《陕北烽火》,在《陕西文史资料》第12辑发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两篇文章,对西北地区,主要是对陕北地区早期党史作了介绍和评析,其中包括“陕北肃反”问题。在涉及“陕北肃反”问题时,郭洪涛提出了一些与西北高干会处理肃反问题结论不一致的观点。郭洪涛指出:“从一九三三年陕北特委创建游击队和根据地开始,到一九三五年陕甘边、陕北两个特委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两支红军的合并统一,陕北特委在实际工作中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特委内部也是团结的,对于这一点,陕北特委同志的认识是一致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脱离实际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是执行不通的,陕北特委的同志处身于群众的实际斗争之中,基本上是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的,这可以从很多事实中得到证明。”(62)郭洪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1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6页。关于自己在“陕北肃反”中的责任问题,郭洪涛认为:“一九三五年七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推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执行了错误的肃反政策。当时担任西北保卫局局长的戴季英采取逼供信的办法,在党内进行了错误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一批红二十六军的老干部,前方还错杀了一批干部,造成了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铸成这一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于错误肃反中我应负的责任问题,中央已于一九六〇年重新作了审查结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央组织部又就此事摘要发了通知,这里就不再多说了。”(63)郭洪涛:《陕北烽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郭洪涛还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就完全证明这是由于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如果特委执行的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实际却又取得这样大的发展,那就将无法得到解释。对于这一点,特委几个同志的认识也是一致的。”(64)郭洪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陕西文史资料》第12辑,第26页。郭洪涛上述观点与1942年中共中央在西北高干会上通过的《决定》结论有重要区别。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1981年,郭洪涛连续公开发表文章,虽然承认当时的‘肃反’是错误的,但谈到自己时,回避1942年的《决定》,只提1959年中央监委和1978年中组部先后修订的结论,以证明自己不应承担‘肃反’的领导责任和‘路线错误’。”(65)王晓中:《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第23页。
“陕北肃反”问题日趋激烈的争论,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和重视。郭洪涛上述文章的发表及其影响的逐渐扩大,引起拥护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结论老干部的强烈不满。“从1981年开始的争论日渐激烈,一些老同志不仅仅对郭洪涛的态度和‘肃反’结论的反复表示不满,又把二三十年代的旧事翻腾出来,越翻腾越生气,开始影响到广大西北出身的干部之间的关系,并引申出如何评价西北革命历史的问题。”(66)王晓中:《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第23—24页。张秀山对这段历史有详细回忆:“1959年11月23日,中监委的同志根据郭洪涛的要求,提出《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审查意见》根据郭洪涛本人的说法,否定了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78年,中央组织部应郭洪涛的要求,以‘组通字36号通知’,将1959年《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政治部。这个通知还传到了某些基层单位。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把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注释说明抹掉了。”“1979年和1980年,我和刘景范等同志出来工作后,得知以上情况,我们认为郭洪涛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关同志的处理是不妥当的。我们分别给中央组织部和党中央写报告,要求认真处理这一问题。”“1983年2月,我和刘景范、张策、张邦英联名给耀邦、小平、陈云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建议党中央召开有关同志参加的西北党史座谈会,解决这个问题。”(67)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359页。中共中央对当时日趋激烈的“陕北肃反”争论较为重视,随即委托相关人员进行处理。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宋任穷回忆:“1983年初,一部分老同志对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历史问题,即三十年代前期以错误肃反为中心的一段历史问题,发生了相当广泛和激烈的争论。一些老同志致信中央,要求中央过问此事。中央研究后认为,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有利于增进党内团结,而且还关系到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全局出发,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和处理好我党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问题。因此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处理这件事,并指定由我代表中央负责联系。经我与李维汉同志商议,并经中央批准,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同志组成5人小组,会同原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有代表性的负责干部,共同研究解决这个问题。”(68)《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76页。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争论的重视和介入,为该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创造了政治和组织条件。
随后,五人小组积极贯彻“宜粗不宜细”标准,对“陕北肃反”争论进行了新处理。五人小组在确定解决“陕北肃反”问题原则时强调:“解决争论问题的方针是分清是非,团结同志,不再追究个人责任,不纠缠枝节问题,最终结束争论。分清是非,主要是分清路线是非,大是大非;团结同志,就是团结一切同志包括犯了错误和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在内。”(69)《宋任穷回忆录(续集)》,第176页。经过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五人小组与陕甘边和陕北参会代表对“陕北肃反”主要争论问题达成了共识:关于“陕北肃反”的性质,“大家也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大家认为,1935年错误肃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产物,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关于“陕北肃反”相关责任人责任问题,“对于党史中有争论的问题,要从全局上、根本上来看,除了路线是非必须分清外,对其他具体问题的分歧,不要再纠缠不放。”(70)《宋任穷回忆录(续集)》,第177页。五人小组最终制定出《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71)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34页。,报中共中央审定批准。1983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并肯定五人小组“对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所提的方针是正确的,采取的方法是稳妥的”。关于错误肃反问题,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我们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指出其错误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产生这种错误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根源,看到事情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犯错误的同志也接受了教训,几十年来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不应再着重个人责任。”(72)《宋任穷回忆录(续集)》,第178页。随后,中共中央即将《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以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下发有关单位和个人。(73)《郭洪涛回忆录》,第88页。
综上,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再次处理“陕北肃反”争论正是在中共中央对党史问题坚持“宜粗不宜细”背景和基础上展开的。一方面,中共中央对诸如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定性等原则性争议问题明确予以定性,肯定西北高干会对肃反处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在对“陕北肃反”责任认定等敏感而颇具争议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则积极倡导“宜粗不宜细”,强调不要“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处理,不仅基本上平息了关于肃反的原则性争论,而且对后来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修订提供了理论和史实依据。
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在坚持“宜粗不宜细”原则和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具体结论基础上进行了再次修订。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全文如下:“一九三五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同年十月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74)《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0—1001页。这条新注释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处理党史争论问题“宜粗不宜细”基本原则和解决“陕北肃反”问题具体结论。首先,该注释在原则问题上观点鲜明,定性明确。如该注释在对“陕北肃反”性质定性方面坚持了西北高干会《决定》和《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相关文件的论断,再次强调“陕北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其次,该注释对某些具体问题采取了淡化和回避的行文表述。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根据也根据“宜粗不宜细”原则和1983年28号文件“不应再着重个人责任”精神,对原注释表述作了修订。新版《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将原注释作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代表朱理治、郭洪涛的名字隐去。(75)《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0—1001页。最后,该注释纠正了原注释史实表述上的存在的问题。新注释订正了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具体时间上的错误,将中共中央抵达陕北的时间从原认定的1935年11月,改正为同年10月。(76)参见魏德平:《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3期,第16页。
结语
《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修订的历史变迁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首先,《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人名“显”与“隐”之间的转变,是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晴雨表”。《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在官方权威文献中的确立和变化,正是中共不同时期党内现实斗争的一种重要折射和反映。中共权威文献上历史当事人评价的改变,名字的“显”与“隐”,以及对历史问题总结模式的变化,大都与现实政治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的修订既可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又可以避免删改文献造成的混乱。其次,《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修订的历史变迁,也反映出中共中央在不同时期对党内重大争议历史问题处理认识的发展。《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确立的主要依据是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文件《决定》。《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重新审查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政治定性和组织处理而颁布的文件。因此,《决定》具有弄清史实、重新政治定性和继续追究责任的要求。“高饶事件”后《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的修订则与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对西北党史新认识相关联。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新修订,更与当时中共中央强调对党史争议问题处理“宜粗不宜细”直接联系在一起。最后,《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肃反”注释的确立和修订揭示了学术研究和政治定性之间的微妙差别。文献是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结论只有建构在真实客观的史料基础上,才能具有学术意义和生命力。如果学术研究没有对这类材料进行严格而深入的考证,则有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尤其是研究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历史问题,研究者不但要善于透过纷繁芜杂的表象,深入研判深层实质性问题,而且还要在基础史料甄别上多下功夫,不断夯实学术研究的立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