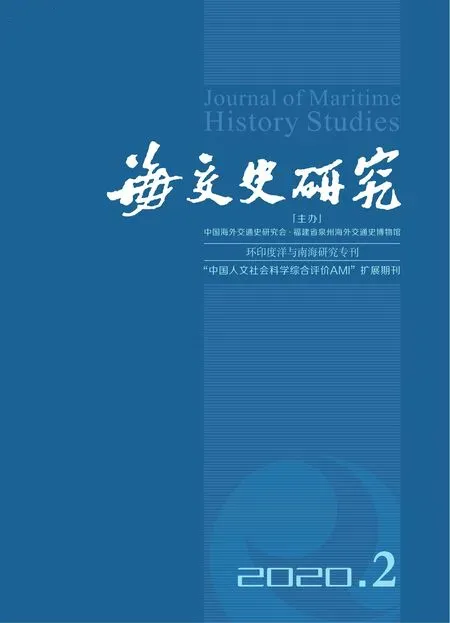辛塔·克拉埃:《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国瓷》(Cinta Krahe: Chinese Porcelain in Habsburg Spain, Madrid: CEEH, 2016, 600 pp.)
于施洋
如同欧美许多研究中国外销瓷的书籍一样,这本600页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国瓷》,封面也截取了油画中一个青花瓷碗的细部,只是这幅画的作者西班牙黄金世纪巴洛克画家胡安·德苏巴朗(Juan de Zurbarán,1620—1649),并不太为国人所知,该画家的《柳条筐里的柠檬》静物画,直至2015年才从私人收藏中被发现,2017年刚刚被伦敦国家美术馆购藏。挑选这个局部做为封面,似乎暗暗传达着该书的题旨:陌生但实存。亦即,虽然国内外学术界、鉴赏界了解不多,但在西班牙1517—1700年间的哈布斯堡王朝,中国瓷确实大量流传到王室、贵族和教会手中,切实地传递着“中国”形象和想象。这个过程最初假葡萄牙人之手,后来是通过直接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比起荷兰人构造“克拉克瓷”概念要早上百年。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国瓷》的作者辛塔·克拉埃(Cinta Krahe,1965生),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艺术史学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硕士,2014年获得莱顿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荷兰著名东西方交流史、克拉克瓷专家克里斯蒂安·约格(Christiaan Jörg)。上世纪90年代起,克拉埃在西班牙马德里海事博物馆、王室收藏委员会担任顾问,从事教学、编目、策展、讲座等多项工作,并逐渐确定了这样一个选题:以现代西班牙成形和巩固的哈布斯堡王朝为界,对应中国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前期,同时也是“马尼拉大帆船”最繁盛的阶段,以中国瓷为对象,用收藏的完整瓷器、出土出水瓷片、同时期绘画作品,辅以各大档案馆原始文献,还原其在西班牙近两百年间的流传、接受和影响。
由此,她的博士论文及随后出版的专著主要分四个部分。首先廓清路径,回顾“两个帝国的相遇”,即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之后,西班牙王室对美洲宣示占有,并且很快越过美洲,与亚洲的菲律宾乃至中国建立起直接关联。这里的跨大西洋殖民部分,对国内历史、拉美研究界来说不算陌生,大致为1530年代巩固新西班牙(今墨西哥及其南北延伸地区)、秘鲁总督辖区核心地带,之后逐渐向美洲边缘地区延伸的过程。但是,同时期跨太平洋的活动却较少为人所知——麦哲伦、埃尔加诺一行1521年抵达某群岛并以王子“菲利普”命名“菲律宾”;埃尔加诺完成环球航行,带回新的知识和经验;1529年,西葡在1494年《托尔德西亚斯条约》所定“教皇子午线”的基础上再次签订《萨拉戈萨条约》,划分两国在“东方”的保教范围;经过不断的探索,西班牙人于1565年发现从菲律宾返回新西班牙的稳定航路,1571年占领据点并建立马尼拉城;很快,从中国闽粤地区贩货到马尼拉,再横跨太平洋到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开始运行,最终持续时间达二百五十年,把宽阔的大洋变成一汪“西班牙湖”。
虽然作者在此主要只是铺陈史实,但对非专业读者不断提请注意并梳理脉络也很有价值。实际上,正是伴随这样的进程,“中国”才成为16、17世纪西班牙政治、商业和文学想象的目标,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和西班牙两国并不因为各居欧亚大陆一端而隔膜,也没有停留于从罗马时代到穆斯林政权的陆路交通,而是跨越两大洋在物质和人文方面进行着诸多交换,尤其在货币、商品、物种、人种和语言等问题上形成交错共生的状态,影响延续至今。
其次,克拉埃把话题收缩到“中国瓷”,配合许多古地图和示意图,勾画其进入哈布斯堡王朝的路线:从当时已经高度产业化的景德镇窑场出发,翻山、沿江送到广州再到澳门,或者混合一些漳州窑产品从月港出发,一齐汇集到马尼拉批发转口;在海上漂流六个月后,瓷器随同其它货物抵达阿卡普尔科港口(12月中旬),经为期近一个月(2月)的拍卖,一部分北上到墨西哥城,直至今天的美国南部地区,一部分转运到美洲其它地区如秘鲁,还有一部分由驼畜自西向东运到维拉克鲁兹港口,如果能再次躲过风浪和“加勒比海盗”,将最终进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港口。总体来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所见的中国瓷,除少量正德、嘉靖年制,主要都是万历(1573—1620)年间景德镇窑制品,特别是克拉克瓷数量最多,器型包括深汤盘、玉壶春瓶、葫芦瓶、军持等,器身常饰单线或双线开光装饰,内绘山水、人物、鹿、暗八仙等纹样。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五彩瓷器以及康熙年间才出现的粉彩瓷器,还有过渡时期的日本金襕手风格器物,以及景德镇仿烧日本伊万里风格器物。
这个过程中,有几点值得着重关注。第一,早期大帆船贸易的货物中,陶瓷器并不是大宗,数量更多的是纺织品、香料,另外还有家具、蜂蜡和麝香;第二,在登记造册的时候,陶瓷器往往被放在“礼物”一栏,这一点与葡萄牙人相仿,也就是说,在接收之初,这一物件的美学欣赏价值大于实用;第三,陶瓷器虽然经过长途运输和多次转手,抵达西班牙时价格攀升,但并没有达到传统认为(或欧洲其它地区传扬)价值连城的程度,其购买和收藏主要出于个人喜好,没有过多沾染阶级色彩;第四,由于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在欧洲拥有众多领地,其女儿曾经携带300件瓷器前往低地国家(被弗莱芒画家忠实记录),而塞维利亚聚集的进货商中也有一个很大的来自该地区的群体,从某种程度上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受到西班牙“大帆船贸易”的影响,该地区与中国瓷的接触要比1603 年抢掠葡萄牙船回国拍卖要更早。
接下来是近100页的论文主体部分,盘点中国瓷如何被哈布斯堡王朝的精英社会阶层所看待、使用和展示。与这一部分相配合的,是230页的附录,为作者走访六年,从希曼卡斯档案总馆、塞维利亚西印度档案总馆等处整理出的王室财产清单、贵族财产清单、贸易记录(中国瓷并不为社会中上层所专有,但他们留下的文字资料相对更充分),既清楚地呈现出整体情况,也实录了许多供进一步细读和推敲的文书,如档案记录最早可以上溯到1503年5月10日(哈布斯堡王朝开启之前),记为“白色瓷器一件。蓝嘴、中间画一朵蓝花的白色瓷器一件。绘满蓝色花枝的白色瓷器一件。绘满蓝色花枝的小型白色瓷器两件。小型白色瓷器一件。”这是著名的天主教女王、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尔一世,从丈夫费尔南多自巴塞罗那运来的“某种玻璃器”(çierto vidrio)中挑选给女官的赏赐品。
如前所述,中国瓷抵达西班牙后虽然出现溢价,但并不属于奢侈品,比如1585年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记道,在中国,4“王币”雷阿尔(real,约3.35克银)能买50件瓷器。而1596年,伊莎贝尔·克拉拉·欧亨尼亚公主买6组碗盘,每组4.5雷阿尔,同时她还花2雷阿尔买了竹筐、1.5雷阿尔买一磅布进行包装,并为骡夫一天的运输付2雷阿尔。另有资料表明,17世纪初,一件中国青花瓷的平均价格是3个雷阿尔,而一公斤面包0.28雷阿尔,一公斤羊肉2.35雷阿尔。在巴洛克风气弥漫的17世纪西班牙,中国瓷与金银等贵金属相比,仍然是“情感价值”高于“有用性”,不是彰显财富和地位的主要象征。
由此,西班牙王室要到18世纪法系的波旁王朝入主后,才开始在餐桌上广泛使用瓷器,而哈布斯堡王朝主要仍然使用金银器,只以中国瓷存储橄榄油、葡萄酒醋、香水(包括喷洒的浓香水和洗手、洗澡的香露),或者盛装细面条汤、甜点、果脯和水果。不过,一个突出的特例跟消费巧克力有关:原产墨西哥、中美洲地区的巧克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磨制、加香料包括辣椒等烧煮后饮用,用葫芦、椰壳(jícara)盛装,后被传教士带回西班牙,1620年代由西班牙公主、奥地利的安妮引入路易十三的宫廷并传遍欧洲。中国瓷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三大妙用:第一作为“巧克力豆罐”(chocolatero),主要由将军罐充当,尤其罐盖遗失破损后加扣对开的铜片、上锁,可以很好地防潮防盗;第二替代“巧克力杯”(jícara,用一种景德镇产仰钟形不带把瓷杯摆桌,在胡安·德苏巴朗、安东尼奥·德佩雷达的画作中常有展现,装饰为过渡期风格;第三催生“曼塞里纳杯托”(mancerina),一种中部带圈形围托的小碟,传说由患帕金森症的秘鲁总督曼塞拉侯爵“发明”,实为景德镇加工制作。
陈列上,一方面,西班牙本土从15世纪便出现储物加展示的橱柜(aparador),另一方面,欧洲贵族中间开始流行“奇物柜”(Kunstkammer)以表现自己的趣味和积累。从文档、信件、诗歌和油画中,可以看到摆放中国瓷的描述越来越多。
最后,作者用实物对档案文件进行了支持:传世的四件珍品、遗址挖掘、沉船出水、静物和其它画作中出现的中国瓷器。哈布斯堡王朝中,收藏中国瓷数量最多、品味最精的是菲利普二世及其子女(传说他们能够分辨瓷器的产地是中国还是日本),但随着使用损毁,尤其是用做仓储的塔楼遭遇火灾,已经无法得见原貌。幸好仍有四件散落的藏品流传下来:(1)萨拉戈萨一教堂所藏的镶镀金银底座青花瓷碗(配金箔皮套);(2)托雷多嘉布遣会修道院所藏的一个青花瓷绣墩;(3)巴伦西亚一方济各会修道院井底发现的青花碗;(4)瓜达尔基维尔河一岛上方济各会修道院留下的青花碗。另外,随着近年来西班牙各地考古工作的开展,除巴斯克、阿斯图里亚斯、坎塔布连地区之外都发现了中国瓷的瓷片,其中马德里和塞维利亚作为政治和商贸中心所获最多,而加利西亚因与葡萄牙接壤也有大量的遗存。
随后,作者把1576—1641年期间沉没的包括“圣斐理伯”号、“圣奥古斯丁”号在内的10艘沉船的出水瓷器进行比对。由于作者曾经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菲律宾海域打捞的“圣迭戈”号沉船编制出水瓷器目录,因此,得以运用大约1 200件完整器物和大量残片,这些很好地成为同时期文字材料的还原和旁证。
在此基础上,作者出于艺术史的专业素养,引用了16、17世纪的7位画家及其他几位无名氏,展示其宗教、静物、肖像画里出现的中国瓷器,进一步说明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流传和观赏情况。
结论部分,作者重新梳理了全书的逻辑和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强调尽管采取了一种比较“死板老套”的艺术史研究方法,但全书的主要目的是梳理并呈现中国瓷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输入、消费、使用模式,以较为原始的档案和数据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依托,进一步凸显西班牙在东西方艺术和物质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
结合皮尔森(Stacey Pierson)“从器物到观念”的观点,可以看到克拉埃的资料整理工作经历了很多困难,其中之一便是当下的“瓷器”(porcelana)一词并不是西班牙语中对这类物品天然、稳定的指称,而是经历了诸如带有价值低、不实用、异国风情、女性爱好、旅行纪念品等意味的bujería, barro, loça, jarrón chino等词。由此,浏览和甄别工作强度大增,但也真实还原了西班牙社会对中国瓷的认识过程。可以说,中国瓷在西班牙并没有受到如同在葡萄牙、英格兰、荷兰等地的追捧,一定程度上源于其社会在“光复运动”、驱逐阿拉伯政权之后的保守和封闭性,尤其南方地区,美学上仍然深受意大利、摩尔人的影响。
作者在英国、荷兰的求学经历,使之直接感受到了传播和话语的力量。因此,她将找到的所有档案都翻译成了英语、后附西语原文,论文和专著也以英语写作。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遗憾,比如某个词汇实在无法在英西两种语言中找到对等,或者前述“天主教女王赐中国瓷与女官”在英译文中颠倒了对象。无论如何,以英语呈现这批资料并阐述这一课题,对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中国外销瓷研究,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瓷外销西班牙”这一历史事实的关注度,都是一件极有价值的事情。
究竟有多少中国瓷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进入哈布斯堡西班牙,或者留在了西属美洲,仍是一个未知而必然庞大的数目,目前只采用了一些官方的资料,沉船、走私尚不包括在内。中国瓷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的商品/艺术品值得展开平行研究,如克拉埃的博士同门甘淑美(Teresa Canepa),关注的对象就在中国的基础上纳入了日本,在瓷器的基础上加入了丝绸、漆器。作为16、17世纪东西方之间最重要的殖民和贸易力量之一,西班牙(连同西属美洲)与中国之间发生的物质和文化交流还有待更加充分的挖掘和构建。
(本文得到金国平、刘淼老师审读,在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