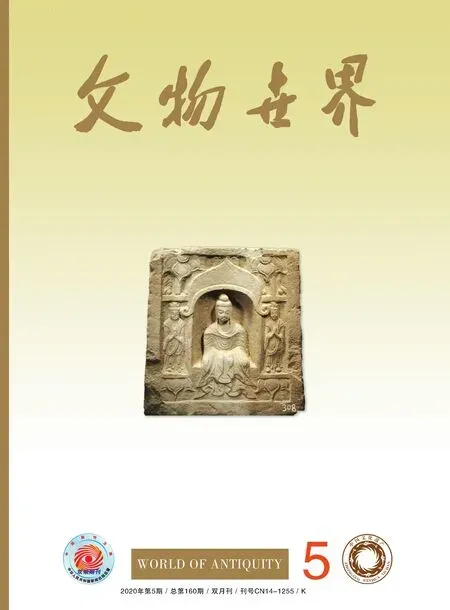关于早期拓跋鲜卑“毁镜”葬的文化思考
□马颖
拓跋鲜卑是鲜卑族中著名的一支,创造了从森林到草原,直至入主中原的历史性大迁徙。随着鲜卑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对其历史文化的研究成为学者们竞相追逐的热点。复原其历史文化的过程,亦是复原古代北方民族从森林,经草原,进入中原腹地生产、生活模板的过程。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鲜卑葬俗的研究对于判断其文化属性、族源以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内容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
毁器葬是中国古代形式各异的丧葬制度中的一种,抛盏、碎物等名称与之齐名,具有流行时间长、地域广之特点。历史、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的许多墓葬中,就已经发现有“毁器”习俗的现象[2]。“在随葬品里面的尖底瓶和长颈壶一类器物,很多是把口打破后再埋入的……[3]”。鄂温克族的丧葬习俗至今仍保持着若干原始的形态,“不论死者是男是女,其随葬品一律都要砸坏一块,因为传说不砸坏随葬品,就将对活着的人不利”[4]。可见,毁器葬至少在新石器时期便已经在我国出现,直至今日一些少数民族仍在沿用,前后有近七千年的历史。地域上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世界性的,如蒙古、外贝加尔等地亦有发现。所毁器物种类繁多,有玉石器、骨器、陶器、铁器、铜器、金器等等。既有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又有装饰品、兵器等。
在现已发掘的四百余座拓跋鲜卑墓葬中毁器习俗亦是早期拓跋鲜卑墓中所常见的,只是所毁器物的种类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各异。铜镜是众多的毁器对象之一,纵观我国古代历史,早在齐家文化时期铜镜已经作为随葬品出现[5]。目前出土的毁镜材料虽然不多,但分布范围广,陕西、河南、广东、安徽、江西、内蒙古等地皆有出土;时间跨度大,秦、两汉、唐、宋、清均有发现。本文仅以早期拓跋鲜卑墓葬中的“毁镜”葬为视角,结合前人对“毁器”葬的研究成果,再次对“毁镜”葬进行探索性的分析、研究。
首先早期拓跋鲜卑的“毁镜”葬来源于匈奴族。拓跋鲜卑与匈奴族在族源、人种、物质文化特征以及某些习俗上有着诸多的相似、相同之处。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墓葬已发掘近千座,其时代主要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相当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前期,断代的依据是来自于中原的随葬品,如铜镜、钱币、丝织品、漆器、铁器等。其中铜镜的出土比较多见,不仅限于贵族墓,普通平民墓也多有出土,而无论贫富贵贱,随葬铜镜几乎全部都是残片[6]。在蒙古的诺音乌拉、高勒毛都、莫林·托勒盖等匈奴墓地,俄罗斯的伊利莫瓦谷地、切列姆霍夫、德列斯图依等匈奴墓地都发现了铜镜残片。中国境内新疆哈密市西汉时期的东庙尔沟、和静县东汉时期的吾乎沟口三号匈奴墓地,以及东汉晚期内蒙古东胜市补洞沟墓地、准格尔旗大饭铺、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等匈奴墓地也都出土了铜镜残片。前苏联伊沃尔加城址内出土了8片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的铜镜残片,其中1片战国晚期至秦代中原流行的凸弦纹镜是迄今所知匈奴境内出土最早的铜镜,其年代可推至公元前3世纪末[7]。所以,可以断定匈奴族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毁镜”习俗。期间经历了南北匈奴的分裂,西迁的北匈奴到达新疆仍然沿袭这一习俗,南匈奴归汉以后这一习俗随着与汉文化的融合而逐渐松动,公元2世纪之后“毁镜”习俗开始在南匈奴中衰落,直至完全被摒弃。
鲜卑族在其原住地——大兴安岭北段,深山密林之中,狩猎是其主要的生存来源,与外界接触甚少,甚至是没有,一切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皆源于民族自身的原始本性。鲜卑族一旦走出原居住地,随着与外界的不断接触、融合,与其他民族进一步的交流、碰撞,其原始的生产生活习性必然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
鲜卑族,特别是拓跋鲜卑与匈奴族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史料记载,拓跋鲜卑民族成分部分源于匈奴。西晋时期,鲜卑族分裂为东、西、北三个部分。东部鲜卑有段部、慕容部及宇文部等;北部鲜卑以著名的拓跋鲜卑为代表;西部鲜卑有乞伏部、秃发部等。关于“拓跋”二字,从目前发现的史料看,两晋之前尚未有该词的记载。《宋书·索虏传》载:“索头虏姓讬跋氏”;《南齐书·魏虏传》载:“魏虏……姓托跋氏”。在目前所见史籍中,成书于5世纪末期的《宋书》,是我们所见有关“拓跋”姓氏的最早记载[8]。据《北周李贤墓志铭》“公讳贤……本姓李,汉将陵之后也。十世祖俟地归……知魏圣帝齐圣广渊,奄有天下,乃率诸国定扶戴之议。凿石开路,南越阴山。竭手爪之功,成股肱之任。建国拓跋,因以为氏”[9];《魏书·序记》:“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北史》《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亦都延续了此种说法;《魏书》还载,力微是诘汾迁徙途中与“天女”所生。由《北周李贤墓志铭》可知,北部鲜卑是在“魏圣帝”即圣武帝诘汾时“建国拓跋,因以为氏”的;而《魏书》的记载中“除去神话成分,实际上反映的是拓跋鲜卑自诘汾时起,开始与外族通婚,与外族有血缘关系这一事实。由此可以推测,以拓跋为氏是诘汾时的事”[10]。“从拓跋鲜卑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来看,此族由大兴安岭北段迁到呼伦贝尔大泽之时,我们只能称之为鲜卑,不能称之为拓跋。只有从大泽西迁之后,鲜卑部落已经与匈奴(或高车等)部落相混合,我们才可以称之为拓跋部或拓跋鲜卑”[11]。据以上的记述,我们可以认定,起源于鲜卑山并一路迁徙至匈奴故地的一支鲜卑,在迁徙过程中,与蒙古高原的其他民族,如匈奴、高车等族接触、融合,在圣武帝诘汾时形成一个新的部落,自称“拓跋”,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拓跋鲜卑。
拓跋鲜卑出土铜镜的墓葬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3世纪末之间,相当于西汉末年至东汉中晚期。处于拓跋鲜卑南迁“大泽”的途中或“大泽”周围居住时期,经南迁“匈奴故地”途中,至“匈奴故地”时期,贯穿了早期拓跋鲜卑南迁西进的全过程。
东汉初年,拓跋鲜卑初见史载,依附于匈奴,受其辖制。鲜卑族每岁必向匈奴交纳牛、马、羊皮张和“皮布税”以获得保护,若过时不交则使其妻子成为奴隶,还要随匈奴出兵入塞抄掠汉的边境。随着匈奴政权势力渐弱,南北匈奴分裂、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南下,拓跋鲜卑趁机占据匈奴故地,并吞并匈奴余众十余万,遂成为草原上新一代霸主。在“大泽”到匈奴故地迁徙途中,及至初居匈奴故地时期,拓跋鲜卑“毁镜”习俗盛行,其原因一方面是与匈奴的交流融合进一步加深,匈奴风俗对其影响亦随之深入;另一方面,与中原的接近,与中原互市的开通,经济往来不断,使中原物资大量涌入拓跋鲜卑内部,铜镜亦在其列。铜镜拥有数量的增加,是随葬铜镜数量骤增的客观原因。从拓跋鲜卑“毁镜”葬流行的地域上看,匈奴曾经活跃,后被拓跋鲜卑占据的“匈奴故地”是“毁镜”葬的主要流行地区;从时间上看,拓跋鲜卑出现“毁镜”葬是在与匈奴存在依附关系以后,流行于匈奴败北,大量匈奴人融入拓跋鲜卑之时、之后。可见,拓跋鲜卑与匈奴族的“毁镜”习俗存在着并行、承接的关系。故早期拓跋鲜卑“毁镜”习俗是受到匈奴族的影响而产生,并延续的一种丧葬制度。
其次关于拓跋鲜卑“毁镜”葬的文化思考。拓跋鲜卑为何选择铜镜作为随葬品?又为何要将其打烂后随葬,究竟要表达一种怎样的思想?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毁镜”葬是否与性别有关。张明东先生认为毁兵是周人的葬俗,并且注意到这种葬俗主要用于男性墓葬中[12]。根据秦文化与周文化都源于关中西部,有许多学者认为秦文化受到周文化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秦文化就是直接接受周文化的产物。秦墓中出土了大量铜镜,同时毁镜葬也是秦墓中的一种常见葬俗。马利清先生将秦毁镜葬与拓跋鲜卑的毁镜葬相互联系、类推,提出毁镜是否与毁兵一样,是否存在性别的原因[13]。拓跋鲜卑存在“毁镜”葬且已经进行人骨分析可以确定墓主人性别的墓葬共有11座,其中只有扎赉诺尔M11为男性,其余10座皆为有女性的墓葬,7座为女性墓,3座为男女合葬墓。可见,在拓跋鲜卑进行性别鉴定的墓葬中“毁镜”葬极大部分出现在有女性的墓葬中。那么,拓跋鲜卑的“毁镜”葬与墓主人的性别有关这一观点是有可能成立的。
2.是否与“破镜重圆”寓意有关。铜镜在我国古代日常生活中除了最基本的照容作用之外,还有消灾避邪、礼物赠送、进贡赏赐、感情信物等用途[14]。山东一些汉墓中发现打碎的两半铜镜叠压放置。可以与之相印证的有洛阳烧沟汉墓M38夫妇合葬墓,随葬铜镜在两个棺中各半,合起来恰为一个完整的镜子。中原地区这种一件铜镜一分为二随葬于两座墓中的现象并非个例。在安徽省怀宁县两座唐墓、江西省星子北宋夫妇合葬墓等都存在一件铜镜分两半,夫妇各一半的现象。所以有学者认为“毁镜”葬是夫妻各执半面铜镜,在阴间再度“重圆”之见证,以永续爱情[15],即所谓的“破镜重圆”之意。如果毁镜葬是破镜重圆之意,随葬铜镜的墓葬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铜镜出自夫妻合葬墓或两座墓葬墓主人分别为男性和女性;(2)墓葬中随葬铜镜数量至多不能超过一面;(3)随葬铜镜残片合在一起为一面铜镜,即便无法完整拼接,至少残片也应出自同一面镜子。扎赉诺尔M11为男性墓,与之同时期的墓葬只有另一件完整铜镜出土,且不论出土另一件铜镜的墓主人是否为女性,仅就铜镜的出土状态即可断定,这两件铜镜的出土与“破镜重圆”寓意无关。其余可以判定墓主人性别的墓葬皆为女性墓或男女合葬墓。在三道湾M11和东大井SDM7男女合葬墓中皆有发现被毁坏的铜镜,但遗憾的是仅见铜镜残片一件,非夫妻各执一半。三道湾M2一墓同时出土两件铜镜残片,一件为B型“位至三公”铜镜残片,另一件为规矩纹镜残片。故“破镜重圆”之说对于拓跋鲜卑“毁镜”葬是不适合的。
3.是否与宗教、法器有关。萨满教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普遍信仰的一种宗教,以万物有灵观念为基础,对自然、图腾、祖先的崇拜。太阳在信奉萨满教的古代北方民族心目中的地位是极高的,是自然崇拜的主要对象。萨满民族因铜镜的形状、反光性能及与人的密切关系和被珍视的程度,而将其象征太阳并应用于萨满教中,或作为萨满身份的认证,或作为萨满法器的必备之物。西伯利亚诸民族如雅库特、埃文基、那乃等族萨满皆佩戴铜镜。中国境内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萨满亦是如此。作为萨满教的信奉民族——鲜卑族,对太阳的崇拜亦是有史可查的。如《后汉书·乌桓传》载鲜卑“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拓跋鲜卑并不制造铜镜,随葬铜镜皆为中原的汉镜,故铜镜对于拓跋鲜卑远未达到普及和日用之物,正因为它的珍贵才可能被人们赋予特定的宗教内涵。在三道湾M104中尸骨基本保存完好,不见头骨,在头骨部位放一件连弧纹铜镜残片[16]。这种葬俗在众多的拓跋鲜卑墓葬中仅此一例。这种特殊的出土位置及葬俗是否具有宗教含义,抑或仅仅是一种偶然情况,至今尚无法确定。但从古至今,铜镜应用于萨满教皆是以完整形态出现,而在拓跋鲜卑的墓葬中出现的铜镜大部分皆为残件,且残损铜镜皆是下葬前故意人为毁坏而造成的。截至目前,拓跋鲜卑墓葬中出土铜镜30件,其中残损铜镜22件,占总量的73.3%。因此,拓跋鲜卑“毁镜”葬是否与其信仰的宗教、法器有关还有待商榷。
4.是否与古人的生死观念有关。《西安半坡》报告在解释墓葬中的毁器现象时说:“原始社会的人们相信无生命的东西也都有一个灵魂,如果要随葬物的灵魂受死者灵魂的驱使,就需要把器物打破,否则,死者不能享用”。这种过于笼统的解释对于有选择性的毁器葬无法自圆其说。为什么有的东西毁而有的不毁,即使是同一类器物也并不是都毁?[17]
[1]孙危《鲜卑“毁器”葬俗研究》,《边疆考古研究》2009年第4期,北京,科学出版社,第139页。
[2]张英《从考古学看我国东北古代民族“毁器”习俗》,《北方文物》1990年第3期,第25页。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
[4]王晓明、王咏曦《鄂温克人的婚丧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年第3期。
[5]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2页。
[6]马利清《匈奴墓葬出土铜镜及毁镜习俗源流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76页。
[7]同 [6]。
[8]梁云《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31页。
[9]韩兆民《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11期,第19页。
[10]郭峰《关于秃发南凉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兰州学刊》1986年第4期,第83页。
[11]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45页。
[12]张明东《略论商周墓葬的毁兵葬俗》,《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3期。
[13]马利清《出土秦镜与秦人毁镜习俗蠡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1期,第151页。
[14]索德浩《破镜考》,《四川文物》2005年第4期,第69页。
[15]同 [14],第 69 页。
[16]乌兰察布博物馆《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17]同[11],第 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