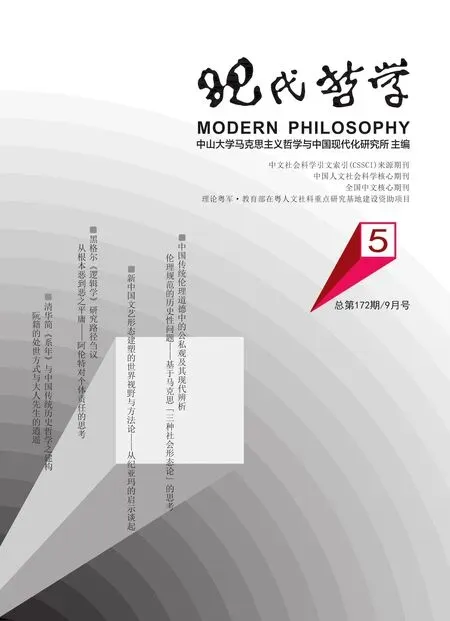感受性在列维纳斯思想中的转变及与他人或超越性的关系
钱 捷 张荔君
一、自我建立中的感受性
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聚焦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感受性概念对于其伦理思想的展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自我的建立,还是自我向他人的敞开,感受性都是关键的环节。我们首先看自我建立中的感受性。
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列维纳斯分别在两个不同的阶段描述过自我的建立:一是《从实存到实存者》(1947)对从匿名的有(il y a)中的出离和凝聚;二是《总体与无限》(1961)对安置、享受和家政等活动如何建立起具体的生存的描述。
在《从实存到实存者》阶段,列维纳斯以有来描述无人称的匿名领域,它是存在者诞生之前的状态。关于有的经验更多地是一种消极的经验,类似于关于“黑夜”(nuit)的经验。黑夜意味着在其中没有丝毫的可见光,而光代表理解、认识,代表人格、人称的升起,没有光就意味着还没有意识、人格,也就是还没有主体出现。温伯格(Gerhard Weinberger)认为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感性的质的经验,(黑夜)不是任何特殊含义的经验,而是与思想不再相关/不再系缚于思想,是一种直接在场的不确定的经验”(1)G.Weinberger, La sensibilité dans la pensée d’Emmanuel Levinas et de Maurice Merleau-Ponty, Paris: Atelier National de Reproduction des Thèse, 2009, p.75.。换言之,这样的经验是一种“个体化的主体被构造之前的一种匿名的存在方式”(2)[英]柯林·戴维斯:《列维纳斯》,李瑞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页。。主体的建立或存在者的诞生对于这种无人称的有来说是第二位的,因此自我的建立首先就需要从有中突破而出,打破其匿名性。“安置”(position)表示安位于“此”(ici)的自身凝聚,“此”表示“以其自身为出发点”的起源,即“主体的诞生”,列维纳斯称之为“实显”(hypostase)。“安置”的功能仅仅在于自身凝聚,主体紧紧抓住自身并笼合于自身,这意味着主体从诞生之初即被封闭在自身的生存之中,一切都围绕着其生存之有限性而展开。在这个时期,列维纳斯将存在者规定为:既介入存在,又具有人称性。介入存在对峙于有不具有任何具体在场的特点,具有人称性对峙于有的匿名性。但一个主体或自我从匿名的有中的诞生仅仅是一种准备性的说明,是“我与自身的第一性关系的样式”(3)[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19页,黑体为笔者所加,以下简称《总体与无限》。。
到了《总体与无限》阶段,自我如何具体地建立起自身以及自我的存在方式才得到充分阐释。在这一阶段列维纳斯认为,自我是通过享受才具体地建立其自身,并维持和巩固了在匿名的有中的自身凝聚,“在享受中,我们总是把自己维持在第二阶段上”(4)同上,第92页,黑体为笔者所加。。享受是与世界中他者的直接相关联,是内在于其享受的世界。享受并不像表象那样构造一个世界,而是“构造实存的满足状态本身”,“作为满足状态的有限就是感受性”(5)同上,第116页,黑体为笔者所加。。感受性即享受的方式。在享受中,事物回到元素的纯粹质性,享受“体验”着这些感受性的质,而并不将它们作为认识的对象,享受因此具有一种“根本的和不可还原的自足”(6)同上,第119页,黑体为笔者所加。。感受性元素“类似于”他者但还不是他者,“类似于”意味着元素通过享受保持主体的自足,但元素的“他异性”却在享受中被转化为同一,因此并不具有绝对的他异性。
元素的这种特点使得它具有不稳靠性(insécurité),“感受性不能严格地将它自己与元素隔离开来,它已经被元素所渗透,并且总是从内部搅乱和激发感受性”(7)Stacy Bautista, “The Development of Levinas’ Philosophy of Sensibility”, Philosophy Today, 2013, Vol. 57, Issue 3, p.259.。由于元素将自身呈交给享受的同时又抽身而退,它像他者那样搅扰着享受的自足,因此在享受中带来不安。贝蒂娜·贝戈(Bettina Bergo)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比喻:“温暖我们的阳光同样会焚烧起来;泡澡的水也可能将我们淹死。世界是家园的同时也是威胁,存在是元素性的,因此它也代表了威胁。”(8)Bettina Bergo, “Ontology, Transcendence,and Immanence in Emmanuel Levinas’ Philosophy”,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2005, 35(1), p.163.贝戈为此补充了犹太教思想的背景:存在代表着威胁,“这是因为在存在中缺乏了一些可以打断它的流动以及过剩的东西。在犹太教思想中,能够打断这种流动性的应该是‘非自然’的律法,阿尔芒·阿贝卡西斯在谈到以赛亚时说道:‘以赛亚认为,指导犹大人行为的律法,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不应该从自然中汲取,而应该从别处汲取。尽管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高于自然。’在这个意义上,人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人不应该屈从于自然,相反应该通过伦理的法则来组织和发掘自然。”贝戈指出,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接受了阿贝卡西斯关于人对于自然来说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以及通过伦理的法则来打断自然的这种看法,因此,列维纳斯才找到“面容”和与他人的相遇这种伦理的方式来为人的超越性进行说明。为了克服元素的不稳靠性,为了使享受的自足能够持续,就有必要展开劳动和居住。劳动和居住是家政的底层结构,家政活动使对元素的占有持续和稳固。通过占有一个地方,居住建立起与元素不同的另一种内在性,“借由家,我们与作为距离的广延的空间关系,就代替了单纯的‘沐浴在元素中’”。(9)[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112页。这就使主体的内在生活成为可能,使得一个存在者封闭在自身之内。自我通过享受而建立起它的具体生存,这就进一步完成了在元素的匿名性中作为开端可能性的自我之诞生。
列维纳斯将这种存在方式表述为一种“存在之努力”(conatus essendi)的结构,这是存在论的根本运行方式,它以同一化为特点。感受性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自我中心的、“持守于自身”的自我的生存方式,这样的自我的特点表现为内在性和封闭性。这样的主体似乎独自在世界之中,而享受触及的世界是一个“既没有秘密也没有真正陌生性的世界”(10)同上,第147页。,这也就是以感受性的享受为特征的主体是内在和封闭的原因。而这就导致它无法真正面对他人,因为面对他人的唯一方式是将他人转化为相对他者,最终将他者之他异性吸收进同一之中。尽管在家政中已经“预设了他人的最初启示”(11)同上,第133页。,预设了向他人的敞开和对他人的欢迎,但在没有现实地遭遇他人之前,对他人的欢迎仅仅停留在“预设”之中,感受性的享受中也没有向他人敞开的机制。
然而,列维纳斯强调:享受建立起的“内在性必须同时既封闭又敞开”(12)[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131页。。在《总体与无限》中,向他人敞开的缺口由面容所打开。面容代表了无限和外在性,它的临显(épiphanie)(13)épiphanie表示以一种“启示”的方式给出自身,启示是溢出人的把握的自行显示。它在宗教语境中指“主显节”,即耶稣或上帝向人们的显现,这种显现是一种启示。列维纳斯借此来表示面容的显示是溢出任何统握和显现方式,面容只能凭其外在性而自身显示,它显示自身的同时又逃离其显示,这样面容的临显才能够抵制我的把握和我的权能。同时是命令和恳请,它的出现使自我的内在性遭受质疑,使主体不得不为自己的享受和权能进行申辩,迫使自我放弃其整个内在性而向他人敞开。朝向他人意味着一种“形而上学的欲望”:欲望高于人的存在和享受的幸福,它代表了超越。在列维纳斯看来,形而上学即超越,并且“只能在分离的、享受着的和自我主义的存在者中产生的形而上学欲望,并不是从享受中引出来的”(14)[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130页,译文略有改动。。享受的运动与超越的运动处于不同层面,前者是向心运动,后者是由他异性所激发的离心运动。可以看到,在一个自足的自我中并没有向他人敞开的缺口,形而上学的欲望只能由他人所激起,并不能从享受的感受性中引发。
二、朝向他人的感受性
《总体与无限》出版后的第三年,德里达发表一篇题为《暴力与形而上学》(15)[法]德里达:《暴力与形而上学》,《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28—276页。的长文。他指出,与他者的相遇使他异性激起超越,这意味着“单纯的内在意识如果没有那种彻底的他者的突然侵入,恐怕不可能给自己提供那种每一时刻之时间及其绝对他异性,同样地,我如果不与他者相遇,也就不可能从自身产生出他异性”(16)同上,第159页。,也就是说,在自我之中“不可能有内在性的差异以及根本性的、原地生成的他异性”(17)同上,第189页。。这切中列维纳斯这个阶段思想的要害之一,由于过于强调他异性的绝对外在性以及自我与其绝对的分离,自我成为封闭的,在其封闭性中并没有能力产生差异性(这里的“产生”仅仅在内部拥有差异这个意思上理解,根本来说他异性并不由我产生)。差异绝对地外在于自我,因此自我之内并没有容纳他异性的空间。这就会带来严重的质疑:如果他人引发的超越始终是外在的,超越又始终从自我出发,那超越在主体之内将如何进行?若如列维纳斯所言,超越以“放弃自身的内在性”为条件,那从主体一侧又如何说明这种放弃的必然性?如果自我的内部并没有进行超越的能力,这样的主体又如何能够是一个奠基在无限观念中的主体,形而上学的欲望又当如何解释?
感受性概念在列维纳斯思想中的扩展正好回答这些问题。到了《别于存在或去在之外》(1974)阶段,(18)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La Haye : Nijhoff, 1974. 该书中译本为《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伍晓明译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本文相关术语翻译与该中译本略有差异,将“être”译为“存在”,将“essence”译为“去在”,因此本文主张该书名译为《别于存在或去在之外》,理由将在别处给出。下文涉及到该书文献时将给出法文版页码,并随附中译本页码。该中译本以下简称《另外于是》。感受性不再仅仅被用于描述自我的建立,而是更多被用于描述自我向他者的敞开;它也不再仅仅是享受的方式,而是主体的“被动性”、“易受伤害性”、“母性”,它以“同中有异”、“他者在同一之中”、“切近”等在封闭的主体中打开了一道缝隙。感受性因此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以享受建立主体;二是以易受伤害性应承他者。列维纳斯确立了感受性的直接性和其基础地位:(1)感受性作为享受的自足,就是主体的“自我性”,主体的实体性,享受构成自我的快乐;(2)感受性暴露给伤害,伤害来自他人,主体同时是脆弱的、易受伤的。感受性首先作为享受,它才能够以易受伤害性暴露于他者,因为享受包含向他者暴露的条件,是给予的条件。向他人敞开即“为了他者”,这就意味着自我被拔除于其享受,剥夺其同一性。享受的快乐变成了痛苦,一个能感受痛苦的主体就不再是一个为了自身生存而不断向外攫取的大写的自我(le Moi),而是成为了承担他人给我带来的创伤的小写的我(le moi),成为“为了他者的同者”(le même-pour-l’autre)。主体在创伤中使其“自身被撕离于自身”(19)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p.95.中译参见《另外于是》,第185页。。被撕开的自我在痛苦中将原来自我中心的享受完全拆卸,以应承的方式向他人敞开。概言之,感受性的扩展使得主体的敞开“由于他者”(par l’autre)并且“为了他者”(pour l’autre),由于其内部的易受伤害性,主体的自我性和封闭性被“除去内核”(dénucléation)。
对此,菲利克斯·佩雷(Félix Perez)评述道:“与感受性第一刻的封闭(享受的感受性)相比,它在第二刻(感受性的易受伤害性)所打开的缺口显示出如下事实:此后,正是他者、扰乱和创伤成为表示主体性作为感受性的方式。”(20)Félix Perez, D’une sensibilité à l’autre dans la pensée d’Emmanuel Lévinas: ce n’est pas moi, c’est l’autre, Paris: L’Harmattan, 2001, pp.100-101. 括弧内容为笔者所补充。他在另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列维纳斯用一种新的感受性来描述主体与他人的关系,“感受性不再从一个自我开始,而是被描述为‘为了他者的一者’(l’un pour l’autre)的事件”(21)Félix Perez, “L’empathie et le visage”, Corps & Psychisme, 2017(2)(N° 72), p.90.。感受性的敞开唤起了人类主体与他人关系的来源即自我牺牲(abnégation)(22)Ibid., p.90.,即主体作为“人质”去替代他人。感受性在根本上从享受的满足和快乐转变为被他人折磨的痛苦,在主体中打开一道向他人敞开的缝隙,因而成为主体痛苦的源头。如佩雷所言,享受不再是感受性的唯一本质性的内涵,“一者为了他者”这一含义使得《总体与无限》中所要求的对面容的欢迎真正地实现,而不再仅仅是一种预设。他人的他异性从一开始就指出以我去“替代”他者,并以彻底地放弃在享受中获得的同一性为代价进行“替代”,而享受中建立起的分离的自我则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条件。享受因此成为感受性的一个阶段,感受性扩展为主体的被动性和易受伤害性(vulnérabilité)(23)vulnérabilité一词表示“受伤的可能性”。它的拉丁词源是vulnus,表示伤口或会造成伤口的物体(如武器、箭头等)。易受伤害性从主体出发,表明主体受到影响的被动状态。易受伤害性“并不是失败的代名词,它只是提醒着我们,我们并不是不会受伤的。因此,处于易受伤害性之中,这指的是我们暴露给伤害,无论在身体上、心理上、智力上还是在社会性上,我们都容易遭到伤害。伤口记录了我们可能遭受的任何变化。处于易受伤害之中指的是我们会受到影响,会被我们暴露于其中的事物改变和塑造。易受伤害性有一种根本性的悖论,它表示人的一种能力:一种受某些事物或受某人影响的能力。易受伤害性与脆弱性(fragilité)不同,脆弱性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而易受伤害性却由外在性所定义,它指示着主体与自身之他者之间的关系”。See Agata Zielinski, Reconnaissance de la vulnérabilité: vers une éthique de la sollicitude, L’éthique de la dépendance face au corps vulnérable, 2019, pp.253-254.,这在主体内部打开了朝向他人的通道。列维纳斯强调“内在性必须既封闭又敞开”,拥有无限观念是主体能够敞开的根本原因。感受性扩展为易受伤害性,正好回答了“内在性如何敞开”这一问题,也回应了主体是有限的却“拥有无限观念”这一问题。
然而,这却导致在主体中存在着无法弥合的间隙,也使主体无法完全获得同一性。这样的特点在列维纳斯看来恰恰表明了主体的善性和向他人敞开的可能性,“善对一者的支配先于起源,它比任何的现在、任何的开始都更加古老”(24)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p.73.中译参见《另外于是》,第146页,译文略有改动。,主体性、人性即在善性的支配下向他者的敞开。列维纳斯最终寻求超出去在(essence)、别于存在之处,通过主体无私/破出存在(désintéressement)(25)伍晓明在《另外于是》中将intéressement一词译为“关心”。inter表示两者之间,表示利益、关切;esse与essence表示存在的活动;列维纳斯有时也会拆解使用intér-esse-ment一词,表示存在这一活动之“本质”在于对存在esse有所关心,与存在有利益牵扯、利益关系,因此intér-esse-ment所表示的是存在牵连在自身的存在活动。《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的中译者将intéressement译为“耽于存在”,笔者认为这个译法传神地表达了intér-esse-ment的韵味,既照顾了“有所关心”“利益相关”之义,又与“存在之努力”(conatus essendi)、“存在坚持自身而存在”所表达的含义相得益彰,因此笔者倾向于将intéressement译为“耽于存在”。与之相关的désintéressement一词表示“无私”“解除与存在的利益关系”,译为“破出存在”。的善性来表达此敞开性。正是由于感受性的扩展,他异性成为了主体性的“构成部分”(26)Levinas, Dieu, la mort et le temps,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93, p.268.参见[法]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90页。。主体性因此原初地就是伦理的,我对他人的责任并不是主体的一种属性或者特征,而是主体性之本质,因此对他人的责任才成为不可避免的。有学者指出,从伦理的角度来说,列维纳斯讨论的是不可还原的伦理的感受性,而他的论证却始终是形而上学的,以他者为中心的“形而上学”是以“他异性的绝对超越而重新定义的形而上学”(27)Agata Zielinski, Levinas, La responsabilité est sans pourquoi, PUF, 2004, p.92.。
三、感受性概念扩展的内在机制
外在性或他异性尽管保证了超越的绝对性,但它本身并不“产生”超越的关系。在列维纳斯看来,正是因为“为了他者的责任”本身就是“超越性”,这才使得超越能够在伦理关系中发生。如果要在主体内部建立起与他人的关联,就要求主体的内部有一种进行超越的动力,尽管超越始终以外在性为前提,但它不再单纯由外在性所激发,而是通过主体彻底的被动性而实现。贝戈指出,“通向他人的感受性是自我内部的‘反向通道’(reverse conatus),这种表述留下了概念所无法把捉和表达的谜团”(28)Bettina Bergo, “What is Levinas Doing? Phenomen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an Ethical Un-Conscious”, Philosophy & Rhetoric, Vol. 38, No. 2, 2005, p.139.,“reverse conatus”实际上是对“存在之努力”(conatus essendi)的翻转,即对存在之“破出”。感受性撕开主体的意义就是此“破出存在”的可能性,与享受的感受性所不同,主体被一种新的感受性所规定,这种感受性从根本上酝酿着超越,并通向无限。列维纳斯指出哲学真正的呼吸应该是“打破自我之幽闭的超越”,并且它“只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在邻人之切近中才被完全地揭示出来”。(29)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p.228.参见《另外于是》,第415页,译文略有改动,黑体为笔者所加。经过扩展为易受伤害性的感受性,自我与他人伦理关系被刻画为“在同一之中的他者”(l’Autre dans le Même),“同中有异者”的关系。因此,超越成为主体“内在性中的超越”(transcendance dans l’immanence),成为主体“奇特的心灵结构”或“灵魂中的灵魂”,主体在它“最内在的同一性”中被“无限地引向他者”(30)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aris: J. Vrin, 2004, pp.47-48. 参见[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王恒、王士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4—45页,译文有改动。。
感受性含义的变化将论题从自我建立的存在论领域引向主体与他人关系的伦理领域,而伦理关系的背后是关于超越的问题。主体向他人超越的方式从通过某种外部的“突然降临”转变为从主体的内部“破出”,换句话说,超越“内在化”于主体之中(31)列维纳斯所指的超越借取自让·华尔(Jean Wahl),表示“与他者的相遇”,以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绝对分离为前提,即“形而上学的超越”。它是向他人、向绝对外在性、向无限所进行的超越。本文基于列维纳斯将超越作为“形而上学的欲望”、作为与外在性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基本前提来理解超越。列维纳斯的研究者中,卡林(Rodolphe Calin)和贝戈(Bettina Bergo)以 “内在性中的超越”(transcendance dans l’immanence;transcendence-in-immanence)来表述这个阶段超越的特点。这也是列维纳斯在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使用的术语,参见《论来到观念的上帝》。。超越不再以被激起的欲望来强调,而是以主体的无私/破出存在(désintéressement)来强调。在《别于存在》中,感受性的易受伤害性和被动性在主体内部撬开一道裂缝,以无限“经过自身/发生”(sepasse)、主体对无限的见证这两重关系来说明无限性怎样引起主体的内爆。这就解释了“外在性”之“外”的真正意味。此“外”并不是与一个实体的自我同样的实体性的外在性,而是主体中之“外”“同中之异”以及“无限之在我之中”,是“在我之中”的“外”。无限性的外在性并不离开自我,也不是来自于自我。无限性作为外在性激发主体的超越,而此超越却“在(我)之中”发生,它发生的同时使我的内在性和同一性得以解开。通过这种“内在化”的转换,封闭主体的内部被撬开一个空间,在自身内部打开了进行超越的通道并使得超越能够彻底在主体内实现。超越在主体内部的实现即意味着主体“朝向他人”的实现,这反过来实现了主体的主体性。因此,所谓将超越“内在化”于主体,实际上是使主体彻底地实现超越,也即彻底实现其主体性。这也就是对于列维纳斯来说,伦理高于并超越于存在的原因。伦理关系之所以独特,伦理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哲学,乃是因为伦理指向超越性,它“破出存在”并指向“别于存在”之处。对主体存在方式以及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的追问,使得存在问题、他人问题、超越性问题交织在一起,而它们的交织最终指向无限,却表现为伦理关系。列维纳斯对伦理的关注与他同时代的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布伯(Martin Buber)等犹太哲学家惊人的相似,他们思想中的“犹太因素”表现为将伦理放在首要地位,并放在对他人的具体责任中,而伦理最终与绝对超越的上帝相关。超越性、无限、外在性及神圣性始终伴随并驱动着列维纳斯的思考。正如《论来到观念的上帝》德译本导言所指出,在以科学为准绳的时代,“言说超越的困难已经变得几乎无法克服”,而列维纳斯正是极少数真正指出通过思来谈论此“不可言说”之问题的人之一(32)参见[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德译本导言,中译本附录第283页。。
列维纳斯在一次与德里达的谈话中说道,“人们为了描述我的工作常常说到伦理学,但真正让我着迷的却不是伦理学,或不仅仅是伦理学,而是神圣,神圣的神圣性(la sainteté du saint)”(33)Jacques Derrida, Adieu à Emmanuel Lévinas, Galilée, 1997, p.15.中译参见[法]德里达:《永别了,莱维纳》,胡继华译,《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第85页。。《别于存在》中,列维纳斯指出人的独一无二性在于“作为无人可替代者而被召唤”(34)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p.75.参见《另外于是》,第150页。,主体是这样一种自由:“自由是一种可能性,是在我的位置去做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做的事的可能性。”(35)Levinas, Dieu, la mort et le temps, p.210.参见《上帝·死亡和时间》,第222页,译文有改动。因此,自由意味着责任的独一性(unicité),意味着作为责任主体的我的独一无二性。这样的自由定义了人的神圣性,而“这一神圣性正是目前这一研究所欲指出者”(36)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p.76.参见《另外于是》,第151页,黑体为笔者所加。。列维纳斯在《上帝与哲学》一文中指出,伦理“别于存在,它是超出存在的可能性本身”,他在这段话末还附加一个注释来表明其“所寻求的是超出的示意、超越的示意,而不是伦理。但超越的示意需要在伦理中寻找”(37)[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第115页及注释2,译文略有改动。。可见,列维纳斯多处澄清他所寻求的不仅仅是伦理,而是超越或神圣性。他总以伦理的方式推进自己的工作并以主体与他人的关系来阐释主体与无限的关系,这是因为超越或神圣性表现在伦理关系中。也就是说,在主体与他人的关系中,神圣性才得以显现。
在列维纳斯那里,“他人”几乎可以与“无限”一词的使用语境相互置换,他人就像无限的影子般的存在。如戴维斯所言,在列维纳斯的语境里,无限者就是他者,而他者的他异性即超越性和外在性;“无限观念之在我”与“我和上帝的关系”可以被看作是同义的(38)参见[英]柯林·戴维斯:《列维纳斯》,第43、106页。。“无限观念之在我,或曰我和上帝的关系,是在我和他人的关系这一具体的情境中来临于我的……也就是在我对邻人的责任中来临于我的……这一责任并非通过契约或许诺,他人的面容通过他异性来向我言说不知来自何处的诫命……这‘不知来自何处’的真正意味是:他人的面容一上来就‘要求于我’、命令我。”(39)[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前言第8—9页,译文略有改动。无限观念的“超越是一种由伦理开始的超越”,它“整个地以伦理性的术语言说自身”(40)同上,第148、30页。,代表着超越和无限的“形而上学在伦理关系中上演”(41)[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55页。。伦理的两端是主体与他人,主体是有限的自我,他人代表了无限;在无限的关系中,无限落入主体之中,主体见证无限。因此,伦理学应该是一个“由以下悖论所描绘出的领域:无限与有限的联系不是一种相关性”,而是“描绘了与有限相关的无限性之悖论的领域”(42)Levinas, Dieu, la mort et le temps, pp.229, 231.参见《上帝·死亡和时间》,第246、248页,译文有改动。。在列维纳斯那里,如何通达无限,以什么样的方式言说无限,如何“思向上帝”的问题是他思想深处的动力,也是感受性概念扩展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