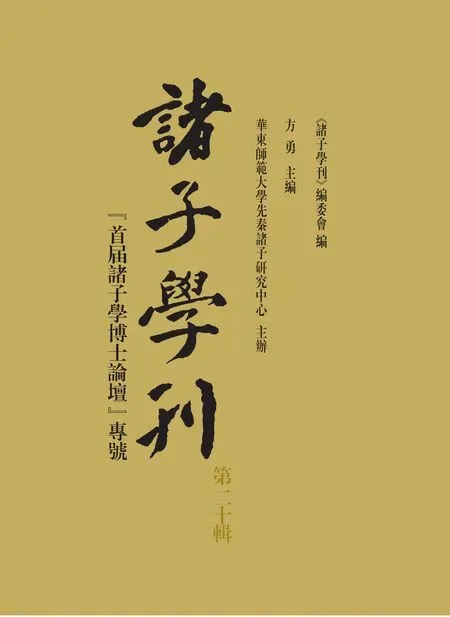《吕氏春秋》“君道無爲論”淵源新論
——以互見文獻爲研究對象
(香港) 陳玉衡
内容提要 學界對《吕氏春秋》之思想性質多有研究,論争不絶,素無定見。本文從《吕氏春秋》之“君道無爲論”爲切入點,嘗試析論《吕氏春秋》之論説來源,並就《吕氏春秋》撰著者如何總合諸家論説提供新證。本文先劃分“君道無爲論”之相關篇章,並概述“君道無爲論”之論説。再者,以《吕氏春秋》與諸書之互見現象爲論據,先後析論“君道無爲論”與《老子》《韓非子》《慎子》之關係,並從《莊子》《荀子》《吕氏春秋》三者之學派承傳梳理“君道無爲論”之思想淵源,望能對整理先秦諸子學術思想流變有所裨益。
關鍵詞 《吕氏春秋》 無爲 雜家 新子學
一、 《吕氏春秋》“君道無爲論”相關篇章及概論
(一) “君道無爲論”相關篇章
“君道無爲論”乃《吕氏春秋》君主治國理論系統中極爲重要之部分,其治國理論牽涉“君”“臣”“民”三者之關係,而“君道無爲論”則集中討論“君”“臣”關係,並詳細闡述兩者之名實問題,以明兩者之職能。考《吕氏春秋》全書,幾乎全以治國之道爲論説之本,其“君道無爲論”既言治國,亦及治身。“君道無爲論”從君主無爲,臣下有爲立論,並與君主治身理論結合,故有“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1)吕不韋《吕氏春秋》,明萬曆雲間宋邦乂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版,第445頁。之語。此理論實爲吕氏門客取諸各家學説糅合而成,亦爲其獨創之理論。
“君道無爲論”相關篇章主要集中於《審分覽》《似順論》,本文認爲《審分覽》八篇(2)即《審分》《君守》《任數》《勿躬》《知度》《慎勢》《不二》《執一》八篇。、《似順論》之《有度》《分職》《處方》三篇、《慎大覽·貴因》《先識覽·正名》均屬於“君道無爲論”之核心篇章。再者,本文亦會旁及與“君道無爲論”相關之段落,因此論乃治國治身之結合,故與部分“貴生論”篇章亦可對應,如《圜道》篇:“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3)吕不韋《吕氏春秋》,第89頁。此言以天、地喻“君”“臣”之道,言“君”“臣”各有分職,不可相踰越,亦與“君道無爲論”相關。
考之《審分覽》,其旨爲集中討論君主具體治國之方略,本覽意在論人君無爲,循名責實,如《知度》篇言:“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詔。”(4)同上,第470頁。牟鍾鑒總結《吕氏春秋》討論“君”“臣”關係,並云:“君應當因而不爲,責而不詔,正名審分,任賢使能;臣應當賢而不愚,公而不私,直而不阿。”(5)牟鍾鑒《〈吕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頁。承此論言之,《審分覽》主要從君主治術申論,並從不同角度分析“君道無爲”之理。吴福相總結《審分覽》之篇章編排,並言:
綜觀《審分覽》八篇論文,並申論人君之治術。《審分》《君守》《任數》三篇並明人君無爲而治之要。《勿躬》《知度》《慎勢》三篇與前三篇所論之實質内涵相近,唯《勿躬》篇重修己德化,以任賢使能;《知度》篇重去智去巧,以督名審實;《慎勢》篇重因勢令行,以正名審分。《不二》《執一》二篇主張人君執一不二,守一不變以治國。蓋無知無爲所以得執一不二之道,而執一不二亦正足以無知無爲以治國也,其篇次脉絡,深得微言之旨。(6)吴福相《吕氏春秋八覽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第55~56頁。
吴説甚是。龐慧之説亦近,又以《尹文子·大道上》與本覽互爲印證(7)龐慧云:“《審分覽》從不可角度闡明君王南面之術。《審分》,明察君臣職分,辨正名實。《君守》,君主應清静無爲。《任數》,君主駕馭臣下之術。《勿躬》,君主不應躬親事務,亦君臣分職之意。《知度》,君主應懂得用術之道。《慎勢》,君主應重視和利用威勢。《不二》似爲殘篇,今存者主要闡説法令一統的必要性。《執一》即執守根本之意。……其次第與《尹文子·大道上》所云頗近:‘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治。’”參見龐慧《〈吕氏春秋〉對社會秩序的理解與構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頁。。《審分覽》爲《八覽》中主題最集中,八篇均與其“君道無爲”之主題相關,而其循名責實之主題亦與部分先秦子部典籍相合,可由此深論“君道無爲論”之思想淵源。
《似順論》凡六篇,牟鍾鑒以爲《别類》《有度》論辨異類、辨真僞,《分職》《處方》《慎小》三篇論賢主治國之術(8)牟鍾鑒《〈吕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第22頁。。牟氏之説可商,如《有度》篇云:“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9)吕不韋《吕氏春秋》,第712頁。此篇仍從治國之術立論,與《似順論》之論題有别。龐慧則以《有度》以下四篇均與治術相關。本文則認爲《慎小》篇言“君”“臣”關係與“君道無爲”並不相關(10)張雙棣云:“本篇旨在告誡君主要慎於小事,防微杜漸。慎於小事,就會取信於民,取賢名於天下。”(張雙棣、殷國光等《吕氏春秋譯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64頁。)又如陳奇猷云:“法家術派最重視審於小事以爲治。”(陳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0頁。),故僅以《有度》《分職》《處方》三篇爲申述“君道無爲論”之篇章。
《慎大覽·貴因》篇言“因則無敵”之理(11)吕不韋《吕氏春秋》,第394頁。,龐慧以本篇言“順應客觀情勢”,而龐説甚爲簡略(12)龐慧《〈吕氏春秋〉對社會秩序的理解與構建》,第63頁。。熊鐵基析述較爲詳審,“因”爲順應多方面之事物,並且爲治國之術(13)熊氏云:“第一,因甚麽?是包括著因時、因勢、因人之力等多方面的……這裏除了因天、因時、因機遇等之外,還有因習俗、因人際關係,其他地方又有‘因人之心’、‘因人之力’、‘因便’,乃至‘因水之力’、‘因其械’等等説法。‘貴因’思想頗爲豐富。”見熊鐵基《秦漢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253頁。。《貴因》篇實與“君道無爲論”關係密切,如《審分》篇言:“因形而任之”(14)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50頁。此則言“君道無爲”之要在於君主因應臣下之能力而治國,從而强調唯有君主無爲,臣下有爲。
《先識覽·正名》篇爲《先識覽》末篇,下啓《審分覽》,前人學者多以《審分覽》承《正名》篇而闡述其理,如吴福相云:“《正名》篇論述正名之要,其關係甚而足以影響國家之興亡與個人之成敗。”又言:“《審分》篇承《正名》篇而來,補述正名之意義,認定正名審分爲君主治政之術。”(15)吴福相《吕氏春秋八覽研究》,第52~53頁。熊鐵基則從《八覽》之結構立論,熊氏認爲《正名》篇旨爲循名責實,於《先識覽》提出問題,爲《審分覽》之論述打下基礎(16)熊鐵基《秦漢新道家》,第254頁。。《正名》篇云:“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所爲善、而從邪辟,所謂可、從悖逆也,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17)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41頁。《正名》篇作者認爲,國家昏亂在於人君不明正名之理,自以爲“用賢”“聽善”“爲可”,實則行相反之事。可見《正名》篇通過闡述名、實相合之必要,申論君主治國之道,而《正名》篇並未詳述具體循名責實之道理,只可歸類爲“君道無爲論”之理論基調。
總上言之,本文以《慎大覽·貴因》《先識覽·正名》《審分覽》八篇、《似順論》三篇,共十三篇爲“君道無爲論”之相關篇章。
(二) “君道無爲論”概論
《吕氏春秋》撰者衆多,其理論系統龐雜而間有牴牾,但全書核心仍然圍繞治身、治國兩方面立論。《吕氏春秋》之理想君主應深明“貴生”之理,不宜過分縱欲,損傷一己之生命,於此層面而言,治國亦不宜事事躬親,故謂“君曰勿身”(18)吕不韋《吕氏春秋》,第77頁。。另一方面,君主亦需明“時機”難得,必須勤以待時,修養己身,亦需明任賢之道,兩重遇合,則有功成之時。以“治國”言之,則吕氏門客重君主無爲,君主只需明人臣之能力,以分其職位。人主執守治國之要,則可“全國完身”(19)同上,第484頁。。故此,可以説《吕氏春秋》之治國理論核心在於“無爲”,吕氏門客認爲“治身”“治國”兩者相通,君主在上位修養生命、盡其天年,對下則選賢任能,方可身治國治。
“君道無爲論”先從人主必先明“君”“臣”職分相異,人主不宜自恃其能,據一己之意願妄行臣下之職。若上位者不知辨正名實之理,則招至亡國身死。如《審分》篇言:“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20)同上,第446~447頁。此則言人主不察審名實之理,則使百官職能淆亂、社會失序。然而,吕氏門客强調正名實乃君主之責,其言曰:“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21)同上,第447~448頁。人主若能辨正名實、君臣有序,則治國可免於壅塞。
既知審名實之重要,吕氏門客即據此爲基礎,申論爲君者應明“無爲”之道。《君守》《任數》《勿躬》等篇則從君主無事、無知、無能等角度立論,此等用語乃“無爲”之發揮。《君守》篇先言“無知”,其言曰:“得道者必静。静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22)同上,第452頁。“無知”者,陳奇猷以爲“無知”即下文言“無識”,乃“不須以耳目知巧以求知”之意,其説甚是(23)陳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釋》,第1062頁。。又《任數》篇言:“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静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24)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61頁。其所謂“無言無思”,亦申論無知無識之意。據此而言,撰寫“君道無爲論”之吕氏門客認爲人君在上位應以“無爲”爲目的,而“無爲”可表現爲“無知”“無識”“無思”等方面。
上言爲君主應“無爲”,此“無爲”非一事不爲,君主應如《分職》篇所言“用非其有”(25)同上,第713頁。。所謂“用非其有”,即君主能借用非其所能掌握之客觀情勢。“用非其有”亦作“使非有者”,兩者義同(26)語出《圜道》篇,曰:“主也者,使非有者也,舜、禹、湯、武皆然。”(吕不韋《吕氏春秋》,第88頁。)陳奇猷以爲兩者相異,以爲:“‘用非其有’與‘使非其有者也’,文法完全不同,其義大相逕庭也。”(陳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釋》,第185頁。)龐慧已駁其非,曰:“句式雖然有異,但意義並無差别,這兩個斷語中的關鍵字,‘用’、‘使’都是‘使用’的意思,而導致句式發生變化的‘其’字、‘者’字,在句中不過是襯字,不影響整句意思的表達。而就《分職》對‘用非其有’、《圜道》對‘使非有者也’的解説來看,二説所指的具體内容也並無差别。”龐慧《〈吕氏春秋〉對社會秩序的理解與構建》,第163頁。。“用非其有”亦可表述爲“用衆”或“用民”,即君主善於使群臣盡其力、使百姓收爲己用。龐慧以“用非其有”有兩義: 一爲君主善用臣下之能;二爲君主能用人之民(27)龐慧《〈吕氏春秋〉對社會秩序的理解與構建》,第165頁。。何志華則以吕氏門客“因而不爲”論有“用衆”“刑名”與“用民”三義,前兩者言人主借助衆力,使臣下各當其分,第三者爲君主善於因民之欲,使其爲己所用(28)何志華《吕氏春秋管窺》,第159~168頁。。由此言之,“用衆”“刑名”“用民”爲“用非其有”之表現方式。《分職》篇言:“夫君也者,處虚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29)吕不韋《吕氏春秋》,第713頁。王念孫以“素服”爲“服素”,其説是。(許維遹《吕氏春秋集釋》,第666頁。)此句言君主“無智”“無能”“無爲”,故可用衆人之力,此即“用衆”。
“君道無爲論”倡君主不擅爲、不逞能,但人君仍需有其執守,此爲《不二》《執一》兩篇所申論之旨。吕氏門客多稱道“執一”之道,言人君可執一應萬,故可執一無爲而天下治。《知度》篇云:“明君者,非遍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30)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67~468頁。此段言人主不能盡知盡見萬物,即吕氏門客承認人主有所不知、有所不明。因此,人君治國需有其執守,以補其不足,而人君需“執一”。《執一》篇言:“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一則治,兩則亂。”(31)同上,第481頁。此段析論“君道無爲論”所言之“執一”,吕氏門客以治軍喻治國,則君之於國猶將之於軍,若君主執守一道,即可使國治。
二、 “君道無爲論”所言“無爲”淵源發微
上文所言“君道無爲論”相關篇章既以“無爲”爲主旨,其所言“無爲”所據爲何書,其所言義理與他書關係爲何,亦可深思。考“君道無爲論”相關篇章多論及“無爲”一語,其例五見,今列如下:
1. 《任數》: 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静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32)同上,第461頁。
2. 《執一》: 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33)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81~482頁。
3. 《有度》: 正則静,静則清明,清明則虚,虚則無爲而無不爲也。(34)同上,第713頁。
4. 《分職》: 夫君也者,處虚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35)同上,第713~714頁。
例1、例3、例4,所言相近,稱許“無爲”之論。例1言君主無知無爲,重“因”之道,以“有爲”者應爲“臣道”。例3與《莊子·庚桑楚》之文互見,其文作:“正則静,静則明,明則虚,虚則無爲而無不爲也。”(36)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810頁。其文相近,此例言君主應明“執一”之道,方可“正則静”,後而至“無爲而無不爲”,即吕氏門客此處以“無爲”爲君主應遵從之治國原則。例2所言與他例稍異,此記楚王問治國於詹何,詹何則以治身先於治國,吕氏門客强調國非無爲,而應以治身爲治國之本,故身治則國治。由此可知,吕氏門客所言“無爲”非言君主放任不爲,應修養己身,執守君道,如熊鐵基言:“‘無爲而無不爲’的思想在它們(《吕氏春秋》與《淮南子》)那裏發展了,它們所主張的‘無爲’有了新的内容。……這種無爲是大有作爲的。”(37)熊鐵基《秦漢新道家》,第117頁。其説可參。吕氏門客所言之“無爲”則近於一種具體之治術,而非空泛之道論。
除“無爲”以外,吕氏門客亦言“不爲”,其意相近,《審分》篇云:“問而不詔,知而不爲,和而不矜,成而不處。”(38)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49~450頁。此言君主爲君之道,應知臣下所爲之事,而不親爲之。陳奇猷言“此文謂君雖知之而不自爲之”(39)陳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釋》,第1053頁。,亦是“無爲”之術。又如《君守》篇云:“不爲者,所以爲之也。”高注云:“不爲而有所成,與爲無異,故曰所以爲之。”(40)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53頁。與上文所言“無爲而無不爲”亦相近。
據上例言之,“君道無爲論”所言之“無爲”“不爲”用例,其所論述之理甚爲統一,而且貫穿其理論體系,可見其重要。下文將分析“無爲”與他書所相合之義理,而考論吕氏門客如何構建其“君道無爲論”。
(一) “無爲”與《老子》重合考論
“無爲”一詞,多見於《老子》(41)“無爲”一詞凡十一見,見於二章、三章、三十七章、三十八章、四十三章、四十八章、五十七章、六十三章、六十四章。,其中亦有用例討論“無爲”與治國之關係,如三十七章:“道常无爲而无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42)朱謙之《老子校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46頁。又如四十八章:“无爲而无不爲。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43)同上,第193~194頁。其言“无爲而无不爲”亦見於上引《有度》篇之用例。
前人亦有析述《老子》與“君道無爲論”相關篇章之淵源。傅武光以《君守》《任數》《知度》等篇所言之“無爲”乃本之於《老子》,其言曰:“《吕氏春秋》論政,最重君道;而於老莊之無爲,尤三致意焉。”(44)傅武光《吕氏春秋與諸子之關係》,臺北私立東吴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93年版,第253頁。劉元彦則言:“‘無爲而無不爲’的觀點,虚、静的要求,在《吕氏春秋》都占有重要的地位。”(45)劉元彦《雜家帝王學〈吕氏春秋〉》,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196頁。王範之則以《不二》《執一》爲“老聃學”,其言曰:“《不二》主齊一,齊一耳心衆力,一則安,異則危。都是老聃執一守一的道理。”又以《執一》所言與《不二》相同(46)王範之《吕氏春秋研究》,内蒙古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頁。。王氏又以《君守》《勿躬》《分職》《任數》《知度》五篇爲“老聃後學”,王氏以爲此五篇既本於《老子》亦有異於《老子》之處,或通於《莊子》,故名爲“後學”(47)同上,第119~122頁。。由此言之,《老子》與“君道無爲論”之關係實有可深研之處,今將據“君道無爲論”相關篇章與《老子》相合之條目分析兩者之關係。
1. 《審分》篇“成而不處”
《審分》篇云:“問而不詔,知而不爲,和而不矜,成而不處。”(48)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49~450頁。“成而不處”句,高注云:“處,居也。《老子》曰:‘功成而弗居’此之謂也。”(49)同上。高誘所引《老子》見於今本第二章,其言曰:“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成功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50)朱謙之《老子校釋》,第11頁。其“成功不居”,據朱謙之《老子校釋》及劉笑敢《老子古今》所引諸本,河上公本作“功成而弗居”,王弼本作“功成而弗居”,帛書本作“成功而弗居”,郭店簡本《老子甲》作“成而弗居”(51)劉笑敢《老子古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2頁。。據本章句例,簡本“成而弗居”較合於文意,陳鼓應亦言:“簡文四字成句,上下文對稱,優於各本。”(52)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香港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00頁。按此第二章作“成而弗居”較佳,而《老子》“成而弗居”與《審分》篇“成而不處”相合。《審分》篇此言君主應多問臣下之事而不擅行、知臣下之事而不爲、和諧萬物而不競争、事成而不居功。其文句論説模式與《老子》“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成而弗居”正合。又《老子》七十七章云:“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斯不見賢。”(53)朱謙之《老子校釋》,第300頁。“功成不處”,河上公本、王弼本並作“功成而不處”,傅奕本作“功成而不居”,帛書乙本作“成功而弗居”(54)劉笑敢《老子古今》,第721~722頁。,可知《老子》各本已有“居”“處”二字互用之例證。由此而言,《審分》作“成而不處”即化用《老子》之文以論證“無爲”之主題。
2. 《君守》篇“可以爲天下正”
《君守》篇云:“天之大静,既静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高注云:“正,主。”(55)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52頁。此句言君主若明清静之理,使其天性寧静,則可以爲天下之主。《執一》篇亦言:“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高注:“正者主。”(56)同上,第481頁。兩者句例正同。考之《老子》三十九章云:“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57)朱謙之《老子校釋》,第155頁。王弼本、傅奕本作“天下貞”,帛書甲、乙本並作“正”(58)劉笑敢《老子古今》,第406~407頁。。王念孫《讀書雜志》考《老子》此章亦引《君守》篇此句爲證,並論“正”爲“君長”之義(59)王念孫《讀書雜志》,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0~1011頁。。四十五章亦言:“清静以爲天下正。”(60)朱謙之《老子校釋》,第184頁。河上公本、王弼本無“以”字,帛書甲本作“清静可以爲天下正”(61)劉笑敢《老子古今》,第459頁。。王範之言此句顯然是《君守》對《老子》此章之稱引(62)王範之《吕氏春秋研究》,第120頁。。張雙棣亦以《君守》爲《老子》思想之宣揚,其言曰:“文章批判了‘博聞’、‘强識’之士,‘堅白’、‘無厚’之説,宣揚了老子的思想。”(63)張雙棣、殷國光等《吕氏春秋譯注》,第470頁。又如《執一》篇云:“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64)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81頁。“爲萬物正”,即謂人君爲萬物之主,其意與《君守》篇此句亦近。此章《老子》言得“清静”而可以爲天下之主,與《君守》篇言君道清静之意相合,乃吕氏門客據《老子》立説之明證。
3. 《君守》篇“不出於户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
《君守》篇云:“故曰: 不出於户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65)同上,第452~453頁。此句見於《老子》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牗,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66)朱謙之《老子校釋》,第189~191頁。“窺牗”,河上公本作“窺牖”,王弼本作“闚牖”。“見天道”,傅奕本作“知天道”(67)劉笑敢《老子古今》,第471頁。。各本以帛書本與《君守》篇所引爲近,帛書甲乙本作“不出於户以知天下,不規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68)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第29頁。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第127~128頁。與《君守》篇句式相近。《君守》篇此言“故曰”,可知行文當有所據,此處所引當爲《老子》無疑。《韓非子·喻老》亦解此句《老子》,其言曰:“空竅者,神明之户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户,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69)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78頁。《韓非》此言其耳目精神不受外物損耗,故以不出於户、不闚於牖而可知天下之事,其所論之重點與《君守》稍異。《君守》篇論爲君者以“無爲”爲尚,不傷其天性,此則吕氏門客亦重《老子》無知無識之説。
下文云:“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70)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53頁。此爲反復闡述此不出户、不妄爲之理。高注此句云:“不出户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故曰所以出之。不爲而有所成,與爲無異,故曰所以爲之。”(71)同上。高注所言“不出户庭而知天下”,蓋亦據《老子》四十七章立説。此句所言“不爲者,所以爲之也”,則合於《老子》三十八章“上德無爲而無以爲”(72)朱謙之《老子校釋》,第150頁。。陳鼓應譯作“上德的人順任自然而無心作爲”(73)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第251頁。,亦得其要旨。《君守》此句化用《老子》之語,以君子無爲,故能成事,即吕氏門客强調君道必静、無知無爲,轉而善用臣下之能。
4. 《任數》篇“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
《任數》篇云:“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静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74)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61頁。《老子》三十八章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75)朱謙之《老子校釋》,第150頁。其“上德不德”,陳鼓應譯爲“不自恃有德”(76)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第247頁。,劉笑敢解爲“最高的德不自以爲有德,不炫耀自己的德性”(77)劉笑敢《老子古今》,第397頁。,從《任數》篇言之,則吕氏門客以爲治國之道無二,强調君道無爲,心暇無知,不强調自身之“智”“仁”“德”,則可國治功成。張雙棣譯爲“最高的道德是不要道德”(78)張雙棣、殷國光等《吕氏春秋譯注》,第481頁。,廖名春所譯亦近(79)廖名春《吕氏春秋全譯》解此句云:“最有德行的是不講德行。”《吕氏春秋全譯》,第218頁。。由《老子》之文言之,則張、廖兩者之譯文失之直白,不得《任數》篇之篇旨。“君道無爲論”爲君主之治術,並言修身,上文已言治身治國乃“一理之術”,吕氏門客斷不會以君主“無德”爲尚,可知張、廖兩者所解實可再商。
總此四例言之,吕氏門客撰寫“君道無爲論”,其核心概念之“無爲”乃效法於《老子》,然而,其説實有糅合各家之説,則其“無爲”又異於《老子》。
(二) “無爲”與《韓非子》重合考論
《韓非子》亦重君主無爲之論,二書成書年代接近,兩者理論之相合亦有可深研之處。傅武光分析《吕氏春秋》與法家之關係,以“用術”爲綱,並以“無爲”“因任授官”“循名責實”爲具體之君主治國之術(80)傅武光《吕氏春秋與諸子之關係》,第324~334頁。。傅氏言:“唯在‘無爲’與‘無不爲’之間,尚須有一具體之架構,以資操作執行,然後方可有‘無不爲’之績效呈現。此一具體架構爲何?即下文所欲論之‘因任授官、循名責實’是也。”(81)同上,第331頁。何志華則指出“刑名”之學,多見於《韓非》,並云:“《吕氏春秋》於韓非‘刑名’之論,顯然有所承襲,因而倡言‘有道之主’,亦當‘因而不爲’,而‘督名審實’。”(82)何志華《吕氏春秋管窺》,第165頁。據本文所考,《韓非子》與“君道無爲論”相關之篇章爲《主道》《有度》《揚權》等篇章,今將細析如下。
1. 《審分》篇“按其實而審其名”
《審分》篇云:“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83)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47頁。此段爲“君道無爲論”之核心,其言“正名審分”,蓋有兩義: 第一,據官員之能力而安排職位,即“因任授官”;第二,檢驗官員之實績是否與其官職相符,即“循名責實”。此説亦見於《韓非子》,《揚權》篇云:“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84)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50頁。此節言君主聽言之道,應據臣下所出之言,以驗證其所爲,故需要審名定位。注云:“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85)同上。其説甚明。《審分》篇此段“按其實而審其名”與《揚權》“審名以定位”相合,其文意亦近。其“聽其言而察其類”則與《揚權》“明分以辯類”相合,均從聽言之道立説,何志華引《韓非子·二柄》所謂“同合刑名”,並言:“韓非以爲此與臣子表現成績好壞無關,而全在乎臣子之‘言’與‘事’,即‘刑’與‘名’之不相符,即當受罰。”(86)何志華《吕氏春秋管窺》,第165頁。《二柄》篇此論“刑名”,亦可與《揚權》此段相發揮。
2. 《君守》篇“中欲不出謂之扃”
《君守》篇云:“得道者必静。静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 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 天之用密,有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静,既静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87)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52頁。此段言君道尚清静,以無知故能知。故有言内欲不出、外欲不入,尚能爲此,則可得天性之密。後能得天性之静,則可以爲天下之主。此謂天性去欲、尚清静無爲,頗有道家意味,但“中欲不出謂之扃”一語,亦見於《韓非子》。《揚權》篇云:
故去喜去惡,虚心以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内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88)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51~52頁。
此段言爲君者應去一己之私好私惡,使道能居於己心。若君主不與臣下共事,明其職分,則能立君主之威嚴。注謂:“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89)同上,第51頁。似與《韓非子》之意不合,《韓非子》此段言君主之治術,先言君主去一己之喜惡,使臣下難測其心思,後不淆亂名分,使君主受人民尊重。所謂“上固閉内扃”,注云:“‘閉内扃’,謂閉心以察臣也。由内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繆矣。”(90)同上。此段詳析《揚權》所謂“上固閉内扃”,言君主去一己之智巧,只按臣下之名實以行賞罰。陳奇猷謂“扃”“閉”爲法家家法(91)陳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釋》,第1062頁。,其説亦有所本。唯考之《君守》此段,與《揚權》所言頗有不同,其相異者有二: 第一,《君守》篇重君主之修養,非以“扃”“閉”爲君主陰謀神秘之治術;第二,《君守》篇重賢臣,尚衆力,而《揚權》篇此段僅以臣下爲一工具,亦非以臣下之賢不肖爲重,《揚權》所强調僅爲臣下之名實是否相符。
3. 《任數》篇“上下不分别”
《任數》篇云:“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不分别,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92)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58~459頁。此言亡國之主其耳目心智存而不可用,皆因其不明君臣之名分,上下不分,故使國家滅亡。“馳騁而因”,高注以馳騁爲田獵,前人已駁其誤(93)李經彝云:“此上疑有闕文不可强通,注以田獵釋馳騁恐亦似是而非。”見李寶洤《吕氏春秋高注補正》,臺北廣文書局1975年版,第37頁。。陳奇猷以“馳騁而因”之“因”爲貴因之君術,其言曰:“必馳騁其因之術而無所拘束即可矣,然愚者則不能達此也。”(94)陳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釋》,第1081頁。張雙棣譯作“要達到隨心所欲無所不至的境界,就得有所憑借啊。”(95)張雙棣、殷國光等《吕氏春秋譯注》,第480頁。蓋亦據陳氏之説爲解。《韓非子·有度》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别矣。”(96)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41頁。《有度》此段强調“刑”“法”之重,以“刑”“法”爲維繫國家秩序之利器,使君臣上下各當其分,反之,若人主捨法而用私,則上下不分,使國家趨於滅亡。《任數》與《有度》篇此段皆從維繫國家君臣上下之秩序立説,前者强調人主任無爲之術,而可正君臣名實,後者則强調“刑”“法”以保持君王之威嚴與地位,可知兩者之側重實有不同。
4. 《任數》“脩其數、行其理爲可”
《任數》篇云:“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唯脩其數、行其理爲可。……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説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宫而心不能知。”(97)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59~460頁。此段言耳目心智均有其限制,不可自恃耳目心智之用。吕氏門客以爲一己之耳目心智所能聞見甚少,不足以治天下,故需“脩其數、行其理”。何謂吕氏門客之“數”“理”?下文云:“凡應之理,清净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静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由此言之,吕氏門客所認爲治國之“數”在於君道無爲而因臣下之力。
吕氏門客所言“脩其數、行其理”,亦見於《韓非子》。《韓非子》多言人主耳目心智之不足恃,《有度》篇云:“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98)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39頁。“飾觀”“飾聲”“繁辭”,注解爲“目視不得其真”,“耳聽不知其僞也”,“慮惑於説也”(99)同上。。此言人君之“目”“耳”“慮”不足爲用,故君主應因“法數”,而且並用賞罰,方可使國家大治。又如《姦劫弒臣》篇云:
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100)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107~108頁。
此段强調人君若自恃“耳”“目”之用,則其聞見必寡,人主需“任其數”“因其勢”,方可使臣下不能蔽、不能欺。其“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與《任數》篇所言“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宫而心不能知”頗爲近似,《任數》篇乃從反面立論,言人主不任數、不行理之負面結果。由此言之,則《吕氏春秋》“君道無爲論”及《韓非子》均强調人主不可自恃耳目心智之巧,而雖循治國之“數”“理”。
然而,兩者所重亦稍有不同,“君道無爲論”不言“法”,只言“數”“理”,而其“數”“理”乃君道清静、無知無爲之意。《韓非子·解老》篇言:
聰明睿智天也,動静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托於天智以思慮。……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静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101)同上,第147~148頁。
此段爲韓非子解《老子》五十九章(102)五十九章云:“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朱謙之《老子校釋》,第239~242頁。。《老子》倡不宜過分耗費精神,以養人之天性之論説,韓非子從此理論進路而下,發展其人君不宜自恃耳目智識,需任法重勢之君術。《吕氏春秋》則吸收《老子》論“嗇”之思想,其影響可見於兩處: 第一,“貴生論”吸收《老子》言“嗇”,强調人君應“論早定則知早嗇”“嗇其大寶”,以修養一己之生命;第二,以人君不應損其耳目心智,勸導人君不恃耳目心智之用,而轉以無知無爲。此爲《吕氏春秋》《韓非子》二書在吸收《老子》時而所出現之歧見。
5. 《知度》篇“因而不爲”
《知度》篇云:“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103)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70頁。此段爲“君道無爲論”之要語,言人君無爲,使臣下安其分、行其職。《韓非子》亦多言“無爲”,《主道》篇云:
明君無爲於上,群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104)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29頁。
此段言人主無爲,而使群臣惶恐驚懼於下,故不得不爲君盡力。若人君能使群臣盡其力,則人君之“無”“能”“名”均不窮。君主因群臣之辛勞而功成,乃賢主之道。此處言“無爲”則從人主盡用臣下之力立説,並使群臣驚懼於下,乃典型法家論説,非《吕氏春秋》所有。
又如《揚權》篇所言:“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105)同上,第47~48頁。此段言萬物均有其才能,而明君應令其各有所施、各安其職,此則令上下無擅爲。若應使臣下盡其能力,則“上乃無事”,“上乃無事”即《韓非子》之“無爲”。反之,若爲君主矜其才能,則使君臣易處,國家大亂。《揚權》此段所言則稍近於《知度》篇所言“因而不爲”之理。
然而,“君道無爲論”基於“無爲”闡發“任賢”(106)《吕氏春秋》極重“任賢”,上文所言“時機論”言君主修身待時,亦勸導君主用賢任賢之理。又如《下賢》《察賢》《期賢》等篇,以“賢”爲篇名。《下賢》篇首即云:“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吕不韋《吕氏春秋》,第374頁。之思想,即君主無爲,故需任賢人以治國,使君主身佚而國治,如《勿躬》篇舉二十賢人輔國君治國之例,以證賢人能補國君之不足(107)《勿躬》篇言:“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厤,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63~464頁。,同篇篇末又言:“凡君也者,處平静、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實相保,之謂知道。”(108)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67頁。此亦申論君主無爲以任賢人之理。反之,《韓非子》則以任賢爲人主之患,《二柄》篇曰:
人主有二患: 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妄舉,則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群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 去好去惡,群臣見素。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109)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44~46頁。
此段以賢人爲治國之障礙,若人主好賢,則群臣僞飾爲賢德以合君欲,故人君難辨真僞。《韓非子》以人君“去好去惡”爲尚,若人君無私好私惡,則可使群臣不僞飾己身。其言“去好去惡,群臣見素”,蓋爲《韓非子》所重之説,《主道》篇亦有“去好去惡,臣乃見素”(110)同上,第29頁。,皆强調人君去好惡,使臣下不可揣測其喜好,君主因此不被蒙蔽。
總上言之,“君道無爲論”實有與《韓非子》相合之處,吴汝綸云:“《吕覽》窮極事情,其文往往類《韓子》,亦風氣使然。”(111)原文載吴汝綸《吕氏春秋點勘》,轉引自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2034頁。吴氏所説實爲洞見,《吕氏春秋》“君道無爲論”與《韓非子》論“無爲”其淵源均自《老子》,而兩者用字、表述亦頗爲相近。然而,兩者“無爲”理論之闡述亦有差異。簡而言之,《吕氏春秋》據《老子》之“無爲”而成“治身治國一理之術”;《韓非子》則以“無爲”爲君術,而使臣下惶恐盡力爲國。《吕氏春秋》與《韓非子》之“無爲”實爲同源異流之理論體現。
三、 “君道無爲論”與《慎子》關係考論
今本《慎子》凡七篇,其文多有殘缺,但其與《吕氏春秋》亦有相合之處。前人多以《慎勢》篇爲慎子學派之作品,王範之云:“《吕覽·慎勢》,文意多近慎到。”(112)王範之《吕氏春秋研究》,第164頁。王氏又引《慎勢》篇四例與慎子學派之關係(113)同上,第164~165頁。,唯王氏並未引今本《慎子》之文爲證。陳奇猷云:“此篇亦法家言也。……此篇言勢,勢派以慎到爲代表。”(114)陳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釋》,第1121頁。唯前人所從慎子學派言之,未嘗舉證《慎子》一書與“君道無爲論”相關篇章相合之處。本文認爲“君道無爲論”與《慎子》相合者有二: 第一,《貴因》篇與《慎子·因循》所論義理相合;第二,《慎勢》篇與《慎子·德立》篇兩篇部分段落互見。
(一) 《貴因》篇與《慎子·因循》義理相合
《貴因》篇論因循之理,言聖王善於利用客觀條件以成就功業。張雙棣云:“‘貴因’是重視憑借、利用外物,順應客觀情勢的意思。”(115)張雙棣、殷國光等《吕氏春秋譯注》,第409頁。前人多以“貴因”説爲道家學説,如王叔岷引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所謂“其術以因循爲用”,以證“因循”爲道家所重之論説。王氏繼而舉《慎子·因循》篇爲例,以《慎子》之説近於道家而非法家(116)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講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77~178頁。。
《慎子·因循》云:“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見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與入難。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117)許富宏《慎子集校集注》,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4~25頁。此篇言因循之重要,並言人皆自私,若强使人爲他人做事,則不可爲用。故在上者應利用人之自私,若君主能厚禄臣下,則臣下皆得爲君主所用。由此言之,《慎子》此處之“因人之情”,乃利用人之自私自利。
考之《吕氏春秋》,《貴因》篇整篇皆言“因循”之理,而所論亦有與《慎子·因循》相近之處。《貴因》篇云:“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118)吕不韋《吕氏春秋》,第394~395頁。此段言先聖王之功成在於利用客觀事物與形勢,即其所謂“因水之力”“因人之心”“因民之欲”。《貴因》篇所言“因人之心”“因民之欲”則近於《慎子》所言“因人之情”,而《貴因》又不限於用百姓之自私,而是强調堯、舜、湯、武之成功在於因應百姓之好惡。
再者,《貴因》篇亦有段落與《慎子》互見。《貴因》篇云:“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119)同上,第395頁。《慎子·佚文》:“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秦、越遠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120)許富宏《慎子集校集注》,第60頁。據許富宏《慎子集校集注》所輯,此佚文引自《太平御覽》《白孔六帖》,而可與《貴因》互參(121)同上。。兩者句式相近,《貴因》篇以“如秦者”在前,《慎子》以“行海者”在前。《貴因》末句作“因其械也”而與《慎子》“械也”相異,蓋撰者欲統一其句式,與《貴因》上言“因水之力”“因人之心”“因民之欲”文正一律。
然而,《吕氏春秋》之“貴因”論説較《慎子》完足,吕氏門客亦有論《慎子》所言因民之爲己,何志華引《用民》《爲欲》兩篇,言君主治國需善用百姓之欲,其欲多則其用多,此與《慎子·因循》所言相合(122)何志華云:“《吕氏春秋》以爲人君善於利用人民‘爲己’的心態,使之有欲,則萬民皆可爲可。民之 爲己,志在得欲去害,而民之所欲者爲‘榮利’,所惡者爲‘辱害’。所謂‘榮利’,其實則爲‘賞實’;所謂‘辱害’,其實則爲‘刑罰’。人君善於運用賞罰,則民無不用矣。”見何志華《吕氏春秋管窺》,第166~167頁。。然而,《吕氏春秋》論“貴因”亦有超出《慎子》之處,如《君守》篇云:“故曰作者憂,因者平。”(123)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57頁。又如《任數》篇:“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静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124)同上,第461頁。由此可知“君道無爲論”所倡之“因”,乃言因天時、因人力之重要。
(二) 《慎勢》篇與《慎子》互見段落考
上言王範之引《慎勢》篇四例爲證,論《慎勢》與慎子學派相合。包括:“因其勢也者令行”“不知恃可恃而恃不可恃也”“湯其無郼,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有知小之愈於大,小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四例(125)王範之《吕氏春秋研究》,第164~165頁。,唯王氏所考尚有可補足之處。
《慎勢》篇有明引“慎子曰”之語,其言曰:“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126)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77~478頁。輯佚者多以其爲《慎子》佚文。據許富宏之輯佚,此段文字見於《慎勢》篇、《後漢書·袁紹傳》注、《意林》及《太平御覽》,文字稍有異同。譚樸森之輯佚並引《商君書·定分》《尹文子·大道上》《後漢書·袁紹傳》《金樓子·立言》諸書記述,並以《慎勢》篇所記爲準。見許富宏《慎子集校集注》,第79~80頁。此段以兔爲喻,論定分之重要。一兔走於地,百人追逐,並非因爲一兔子足够爲百人所分,而是因爲兔子之歸屬未定。反之,若兔子均在市集中販賣,則無人願意競逐,乃因其歸屬已定,由此而喻治國亦以定職分爲首要。此文不見於今本《慎子》,但其明言“慎子曰”,當知其思想與是時慎子學派關係密切。此段記述亦見於《商君書·定分》,其言曰:“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騖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貪盜不取。”(127)蔣禮鴻《商君書錐指》,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45頁。其所論亦近,大抵此比喻爲法家論定名分之熟語,唯《慎勢》篇引作“慎子曰”,故今仍以其與《慎子》相合之例。
另外,《慎勢》篇“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段與《慎子·德立》相合,今排列如下:
《慎勢》: 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
《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
《慎勢》: 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
《德立》: 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
《慎勢》: 疑生争,争生亂。(128)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77頁。
《德立》: 疑則動,兩則争,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129)許富宏《慎子集校集注》,第47~48頁。
兩段文句相近,《德立》篇多“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一句,但不妨礙整體之文意。《慎勢》篇此段言“位尊”“威立”之重要,若人君能得其“勢”,則可無敵於天下。後文“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數句,“疑”應從陶鴻慶、王利器解作“比”(130)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2070~2071頁。,即言在上者不可使在下者能與己比擬,以亂名位。
據許富宏《慎子集校集汪》所舉證,《管子·君臣下》與《韓非子》亦有類近之表述,《管子·君臣下》篇云:“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内有疑妻之妾,此宫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131)黎翔鳳《管子校注》,第593頁。《韓非子·説疑》云:“故曰: 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 内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132)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446頁。唯句式不同,難以證成《慎勢》篇取法《管子》及《韓非子》,而《慎勢》篇顯然與《慎子》句例最爲相近。
本文嘗試就《慎勢》篇此段與《慎子》關係提出新證,《慎勢》篇首云:“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133)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73頁。此言兩者之“權”“勢”“治亂”不可相等,若相等則兩者不能相治。由此言之,《慎勢》篇强調人君應得治國之“勢”,以維持君主之地位。《慎勢》篇描述治國之法在於使君臣、嫡庶、夫妻不淆亂其地位,因此治國之重點在於“定分”。考《慎勢》篇此句,前人曾究其源,王利器以此句與《意林》引《慎子》之佚文相合,其文作:“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134)許富宏《慎子集校集注》,第88頁。陳奇猷則舉《遇合》篇“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一段及《韓非子·亡徵》:“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兩句以證《慎勢》之文意(135)陳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釋》,第1122頁。。陳氏所舉兩例,義理雖近,而句式不合,非爲明證。王氏以《慎子》佚文爲證,誠有卓識。然而,《荀子·王制》實有相近之文句,其言曰:“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136)王天海《荀子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46頁。此言君主治國需有禮義制度,以明上下貴賤之分,其所謂“兩貴之不能相事”與《慎勢》“權鈞則不能相使”意亦近。《荀子·王制》此句之句式、義理與《慎勢》篇亦近,王天海謂此句乃“古之常語”(137)同上,第349頁。,蓋爲《王制》《慎勢》兩篇作者所取之熟語。
再者,《慎勢》篇謂“疑生争,争生亂”,與《德立》“疑則動,兩則争,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近而不同。考之《荀子·王制》有言“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争,争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138)王天海《荀子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81頁。,同篇又言“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争;争則必亂,亂則窮矣”(139)同上,第346頁。。“分則争,争則亂”及“物不能澹則必争;争則必亂”之句式,與《慎勢》篇“疑生争,争生亂”之句式相近。《慎勢》篇此句固然取之於《慎子》,但吕氏門客於撰著之時因其立論之需要,亦就《慎子》之説稍作修訂。就“權鈞不能相使”及“疑生争,争生亂”兩句以言,本文認爲撰寫《慎勢》篇之吕氏門客或曾參考《荀子·王制》或其相關之文獻,此可證《慎勢》篇與《荀子·王制》關係密切。
由此言之,《慎勢》篇除與《慎子》關係密切,亦參考《荀子·王制》爲文。劉文典云:“《吕氏春秋》作者,多荀卿弟子,故用字多與荀卿同。”(140)劉文典《三餘札記》,黄山書社1990年版,第91頁。《荀》《吕》二書關係密切,今由《慎勢》篇取法《慎子》與《荀子·王制》可以印證。
四、 “君道無爲論”之《莊》《荀》並見用例舉隅
本節嘗試從“君道無爲論”相關篇章博取衆書以立説之角度出發,探論其所采用之字詞、義理乃並見於《莊子》《荀子》二書,以梳理“君道無爲論”與二書之關係。上文雖已言《吕氏春秋》用語多類《荀子》,然而,諸如《吕氏春秋》亦多有取法於《莊子》(141)王叔岷曾有《吕氏春秋引用莊子舉正》,舉《吕》書引《莊子》凡51條,其中以《讓王》《山木》篇相合者多。王叔岷《吕氏春秋引用莊子舉正》,《道家文化研究》第10輯,第250~266頁。。王範之首倡《吕氏春秋》最重《莊子》,王氏從文意、詞句兩方面舉證撰寫《吕氏春秋》之門客以莊子門徒爲多(142)王範之《吕氏春秋研究》,第12頁。。
何以《吕氏春秋》用語既多類《荀子》,又多取法《莊子》?何志華提出《荀子》之論説實多取自《莊子》,何氏於《再論荀卿學説源出莊周》一文(143)何志華論《莊》《荀》學派有《荀卿論説源出莊周證》(《諸子學刊》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282頁)、《〈莊〉〈荀〉禮説淵源考辨》(《諸子學刊》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170頁)、《再論荀卿學説源出莊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2016年主辦“先秦諸子的哲學與交鋒”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第1~23頁)三文,以證成《荀子》與《莊子》二書關係密切。前人以爲《荀子》除《天論》篇曾評莊子外,餘篇皆無所及,然而據何氏所論,則《荀子》實有取法《莊子》之處。後伍亭因亦有《荀卿論説源出莊周補證》(《諸子學刊》第1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203頁)一文,並從“《荀子》沿襲《莊子》用詞”“荀卿部分論説源出莊周及辯莊證”“荀卿論評諸家學説多據莊周證”三方面補足何氏之説,誠有洞見。,歸納己説,從文辭用語、義理、旨在辯莊、駁詰莊周各方面證成《荀子》一書實多有采《莊子》之處(144)何志華《荀卿論説源出莊周證》,第4~23頁。林麗玲《〈荀子〉與先秦典籍關係重探》一文以《荀子》一書爲切入,嘗試以詞彙分析《荀子》與各文獻之關係。其中論及《荀子》用《莊子》之詞彙共二十條,而《吕氏春秋》用《荀子》之詞例則共二十一條。見林麗玲《〈荀子〉與先秦典籍關係重探》,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中文學部哲學碩士論文,2011年,第82~98頁、161~177頁。。既知《莊》《荀》二書關係密切,則其與《吕氏春秋》之關係實有可深研之處。本節嘗試提出“君道無爲論”相關篇章之論説有同時采自二書之理論,並因其理論需要以修訂二書之材料。本節所論牽涉《莊》《荀》二書之部分篇章,其成書年代問題甚爲複雜,或有學者認爲其成書後於《吕氏春秋》,難以證明乃《吕氏春秋》采二書以成己説,本文不能否認此一可能性,故只取其中爲《吕氏春秋》或采於他書之例子。再者,何氏《再論荀卿學説源出莊周》一文以《莊子》流行於《荀子》編撰以前爲前提,本節亦循此前設進行討論,以探討三書之關係(145)何志華據王葆玹《老莊學新探》之觀點,謂:“本文探究《莊》《荀》二書用詞片語重合互見時,即據王氏‘《莊子》流行於《荀子》編撰以前’之説,從而推論《莊子》之成書年代,亦在《荀子》編撰成書以前。至於學者質疑《莊子》外雜篇個别篇章成書年代較遲,容或晚於荀況生年,自亦不無道理。”見何志華《再論荀卿學説源出莊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辦2016年“先秦諸子的哲學與交鋒”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第8~9頁。。
1. 《有度》篇“通意之悖”段
《有度》篇末申論聖王執一之理,並以人君執一之障礙爲外物之干擾,後文“故曰”以下一段與《莊子·庚桑楚》幾近全同,今排列如下:
《有度》: 故曰: 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
《庚桑楚》: 徹志之勃,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達道之塞。
《有度》: 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
《庚桑楚》: 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也。
《有度》: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
《庚桑楚》: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
《有度》: 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
《庚桑楚》: 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
《有度》: 正則静,静則清明,清明則虚,虚則無爲而無不爲也。(146)吕不韋《吕氏春秋》,第712~713頁。
《庚桑楚》: 正則静,静則明,明則虚,虚則無爲而無不爲也。(147)郭慶藩《莊子集釋》,第810頁。
兩段所載文字稍異處僅有數處,第一,《有度》作“通志之悖”,而《庚桑楚》作“徹志之勃”,《莊子集釋》引《釋文》以“勃”又作“悖”,則知二字本通(148)郭慶藩《莊子集釋》,第810頁。。“通”“徹”二字,或爲避漢諱所改(149)王利器云:“‘徹’作‘通’,此高氏作注時避漢諱改。”此或爲漢代傳鈔避武帝諱所改,非必高注時避諱改。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2979頁。。第二,《有度》“通道之塞”,而《庚桑楚》作“達通之塞”,“通”“達”二字本多互用,如《莊子·讓王》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吕氏春秋·慎人》篇“通”字即作“達”(150)吕不韋《吕氏春秋》,第347頁。。第三,《有度》作“智能去就取舍”,而《庚桑楚》作“去就取與知能”,“智”“知”互通,王先謙亦言“知音智”(151)王先謙《莊子集解》,第205頁。。《有度》作“舍”,《庚桑楚》作“與”,取義微别而大意不改。
《有度》篇末句“正則静,静則清明,清明則虚,虚則無爲而無不爲也。”《庚桑楚》“清明”作“明”。考“清明”一詞,多見於《禮記》,其意與目視清明相關,如《郊特牲》篇云:“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152)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01頁。孔穎達言“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潔净也。”(153)同上,第702頁。此由目視清明,引伸至清明潔净之意。又如《玉藻》篇云:“視容清明”,鄭玄謂“察於事也”(154)同上,第835頁。,亦從目視清明之意引伸之,王夢鷗解此句爲“判别事物要十分明察”(155)王夢鷗《禮記今註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1969年版,第418頁。。《孔子閒居》云:“清明在躬,氣志如神。”(156)孫希旦《禮記集解》,第1278頁。王夢鷗解曰:“王者身有清明的德行,如神的意志。”(157)王夢鷗《禮記今註今譯》,第671頁。孫希旦云:“聖人無私,故其德之在躬者極其清明,合於神明,而能上格乎天焉。”(158)孫希旦《禮記集解》,第1279頁。此“清明”即從德行立説,稍近於《有度》篇之言。《管子》亦言“清明”,《宙合》篇云:“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159)黎翔鳳《管子校注》,第219頁。房注云:“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籍,所以俟亂世清明,候風雲以舉翼也。”(160)同上。“清明”即世道清明。考《禮記》與《管子》所言之“清明”,並不全然合於《有度》篇之“静則清明”。
考《有度》所言“清明”實本於荀卿,《荀子》多言“清明”,《解蔽》篇“清明”一詞四見。其“清明”一詞多言心性修養,今列其文例如下:
(1) 人何以知道?曰: 心。心何以知?曰: 虚壹而静。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虚;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壹;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虚;不以已所臧害所將受謂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静;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虚壹而静。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虚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静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虚壹而静,謂之大清明。(161)王天海《荀子校釋》,第846~847頁。
(2) 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162)同上,第855頁。
(3) 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清明内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163)同上,第856頁。
例(2)言人心如水,若處於静止,則濁物下沉,而水面清明,足以明見人面之鬚眉與肌膚之文理。若微風吹拂,則清濁淆亂,連容貌亦不可明視,更遑論鬚眉肌理。此段以水與風比喻心性與外物,人若不得“清明”之理,則心性昏亂,不足以決是非嫌疑。此言“清明”乃應對外物紛亂之手段。
例(3)言“至人”之境界在於明白“微”之理。“濁明外景”,王天海云:“濁明,指火、日之明。外景,照事物形影於外。”(164)同上,第866頁。“清明内景”,王天海云:“清明,金、水之明。内景,照事物形影於内。”(165)同上。王氏之説亦迂晦難解,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解之最爲詳審,其言曰:
按景乃日光;蓋心的認識能力,有如日光之照射,故荀子比擬之爲景。外景,指心光之向外照射。水含他物即濁;濁明者,心光向外照射,必攝取外物之對象;此外物含於心光之中,有如水含他物,故曰濁。心光對所含之外物,能知能論,故曰“濁明”。清明者,心光内涵時,無一物之蔽,故曰“清明”。(166)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版,第245頁。
即“清明”乃描述聖人之心性修養,心性清明,故不以外物爲蔽。“縱其欲”,王先謙(167)王先謙云:“‘縱’,當爲‘從’。聖人無縱欲之事。從其欲,猶言從心所欲。”王先謙《荀子集解》,第404頁。、王天海(168)王天海《荀子校釋》,第866頁。並解作“從”,言從心所欲之意。“兼其情”,王先謙解爲“盡其情”。兩句言聖人可從心所欲,盡其天性,皆因其以理節制情欲。總例(2)與(3)言之,“清明”乃聖人面對外物干擾心性以節制其情欲之修養方法。
例(1)提出“虚壹而静”之綱領,其論述層層遞進,先提出人以“心”知“道”,而“心”需“虚壹而静”。何謂“虚壹而静”?《解蔽》篇亦知人受成見與外物之影響,“心”往往處於“臧”“兩”“動”之狀態,“臧”即“藏”(169)楊倞注:“臧,讀爲‘藏’,古字通,下同。言心未嘗不苞藏,然有所謂虚也。”王天海《荀子校釋》,第846~ 847頁。,三者分别對應“虚”“壹”“静”。心雖有求道之障礙(“臧”“兩”“動”),但《解蔽》認爲此亦可解決。“臧”,本篇言“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虚;不以己所臧害所將受謂之虚。”“己所臧”當作“所已臧”(170)王念孫云:“‘不以己所臧(古藏字)害所將受謂之虚’,盧云:‘“己所臧”,元刻作“所己臧”。’念孫案:‘所己臧’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楊注‘積習’二字正釋‘所己臧’三字,宋錢本世德堂本並作‘所己臧’。”見王念孫《讀書雜誌》,第719頁。,此言人生而有識,識即人之是非成見,若人能不以一己之是非成見妨害未知未識之事,則可稱爲“虚”。“兩”,本篇言“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此言人認知事物有不同角度,同時兼知則爲“兩”。若一能不以“彼一”害“此一”則可謂“壹”,於“虚壹而静”之角度言之,“一”與“壹”實有别,不可混同(171)《説文解字》謂“壹”字云:“壹,專壹也。”“一”字則云:“唯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可知二字本義有别。見許慎《説文解字》,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214頁。,“一”乃認知事物之一隅,並非真正之專一,故下文以諸前賢爲例,如“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172)王天海《荀子校釋》,第855頁。其所謂“壹”即今言“專一”。“動”,本篇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甞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静;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静。”此言人入卧則有夢、苟且則放縱、使役則多謀,即人之生活環境干擾甚多,心知難静。本篇則言不以心知紛擾以亂己心,可以謂之“静”。下文言若爲“虚壹而静”,求道之人(“須道”“事道”“思道”)可知道而察之、知道而行之,繼而仍爲體道之人。若明“虚壹而静”之道,則可以稱之爲“大清明”。
“大清明”一詞,先秦兩漢文獻僅見於《荀子》一書。楊注謂“無有壅蔽者”(173)同上,第852頁。,王天海云:“大,極也。清明,神清志明也。《禮記·禮運》:‘清明在躬,志氣如神。’”(174)同上,第852~853頁。按此實爲《孔子閒居》篇文。《解蔽》不言“清明”,而以“大清明”指稱心神清明之狀態,此乃《解蔽》篇撰者强調“虚壹而静”於心性修養之正面影響。徐復觀嘗總結例(1)所論之體道過程: 求道>心虚壹而静>心知道>微,其言曰:“心求道,是心求得一個標準(衡);心有了標準,然後能虚壹而静。心能虚壹而静,才能知道。心能知道,則心與道是一,而可以達到微的境界,亦即至人的境界。”(175)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246頁。“虚壹而静”謂之“大清明”,即心需清明,才能知道。
若並言《莊子庚桑楚》《荀子·解蔽》與《吕氏春秋·有度》三篇之關係(176)前人已指出《解蔽》所言“虚壹而静”乃受《莊子》之影響,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曾詳析之,其言曰:“虚壹而静的觀念,從《老》《莊》來。……但所謂受影響,乃是學術上廣泛吸收,各自消化的影響。道家講虚,講静,是要把心知的活動消納下去,使其不致影響、擾亂作爲人的生命根源的自然。《荀子》則在於用虚静來保障心知的活動,發揮心知的活動。”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第237頁。,《有度》篇末段先言“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177)吕不韋《吕氏春秋》,第712頁。此段先總結《有度》篇君主不能盡知萬物之意,並以“執一”爲治國之方,又言不能“執一”乃外物之干擾心性所所致。其“故曰”後之文句即與《庚桑楚》相合之段落,既言“故曰”可知《有度》篇之作者實有所本而引“通意之悖”段。其與《庚桑楚》篇之關係應相當密切,《有度》篇蓋本《庚桑楚》篇而引述此段材料。
《有度》篇又作“静則清明,清明則虚”而異於《庚桑楚》之文句,本文認爲此當爲吕氏門客據《解蔽》篇之言“虚壹而静,謂之大清明”。首先,《解蔽》所言“大清明”與《莊子》義理相合,何志華已詳考之,其言曰:“荀子所謂‘大清明’,意謂‘心’可以全面正確地認知外界事物,其義則又與莊所謂‘莫若以明’相近。”(178)何志華《荀卿論説源出莊周證》,第278~279頁。以《有度》此段言之,則吕氏門客又據《解蔽》修訂所引之材料,因“清明”一詞更能彰顯段旨,故改易《庚桑楚》之“明”以爲“清明”,使義理更見明晰。上已言“虚壹而静”乃强調人之心性修養,以避免外物干擾心性,正與“正則静,静則清明,清明則虚”之理相合,若人君能清明其心性,免於“意悸”“心繆”“德累”“道塞”,才可“無爲而無不爲”。
2. 《正名》篇“可不可而然不然”
《正名》篇云:“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説也。説淫則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179)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40頁。此段言正名之重要,並以失實之説辭爲名喪之理由,若説辭失實,則“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高注云:“不可者而可之也,不然者而然之也,不是者而是之也,不非者而非之也,故曰淫説也。”(180)同上。其説甚明,即言是非顛倒,混亂名實之意。
“可不可而然不然”,亦多見於《莊子》。《天地》篇云:“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宇。”若是,則可謂聖人乎?’”(181)郭慶藩《莊子集釋》,第427頁。成疏云:“布行政化,使人效放,以己制物,物失其性,故己之可者,物或不可,己之然者,物或不然,物之可然,於己亦爾也。”(182)郭慶藩《莊子集釋》,第427頁。成疏所言即言治人者以不可爲可、以不然爲然之意,與高注相合。又如《秋水》篇云:“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雜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183)同上,第597頁。此段乃公孫龍之自白,成疏云:“故能合異爲同,離同爲異;可爲不可,然爲不然,難百氏之書皆困,窮衆口之辯咸屈。”(184)同上,第597~598頁。公孫龍善辯,故能以不可爲可、以不然爲然,與《正名》篇所言之“淫説”正合。
《齊物論》亦論“可”“然”之理,其言曰:“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185)此段又見於《寓言》篇:“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郭慶藩《莊子集釋》,第69頁、950頁。“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郭象注云:“可乎己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186)郭慶藩《莊子集釋》,第70頁。“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王先謙云:“何以謂之然?有然者,即從而皆然之。何以謂之不然?有不然者,即從而皆不然之。隨人爲是非也。”(187)同上,第15頁。此段言物之名實問題,《齊物論》認爲物本無名,凡人謂之而然,因此,物之名實隨人爲是、隨人爲非,由此言之,則物之“可”“然”難定,皆因人有成見,各執一端之故。故下文謂“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188)同上,第70頁。。此即言聖人和通是非,而息於“自然均平之地”(189)同上,第17頁。。此論“可”“然”之理與他篇相異,蓋《天地》《秋水》篇僅取“可不可”“然不然”論名實是非之意而已。
《荀子》亦言“然不然”。《儒效》篇云:“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樽,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190)王天海《荀子校釋》,第274頁。“卹”,王先謙云:“‘卹’‘恤’通用。《秦策》‘不恤楚交’,韋注:‘恤,顧也。’”(191)王先謙《荀子集解》,第123頁。“薦樽”,義爲驕倨他人之意(192)楊注云:“薦,藉也。謂相蹈藉、撙抑,皆謂相陵駕也。怍,慙也。”劉師培云:“薦撙,當作‘踐蹲’。薦,踐義同。蹲字,《説文》訓爲踞。踐蹲者,即驕倨以臨人之義也。楊注訓‘薦’爲蹈藉,其訓甚當,唯不知‘薦’即‘踐’字之異文。若以撙爲抑,即屬不詞。”王天海則引朱起鳳之言,並以朱説“撙”爲“踏”之訛過迂。王氏以“撙”原爲“蹬”,“踐蹬”王氏解作“又踩又蹬”,則王説又流於迂曲,其以“撙”爲“蹬”又過於臆斷。今以劉説爲是。王天海《荀子校釋》,第277~278頁。。此句乃謂若言論不顧是非對錯、互相驕倨、羞辱,君子亦不如惠施、鄧析之徒。又《性惡》篇云:“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193)王天海《荀子校釋》,第960頁。“恬禍”,楊注爲“安禍”之意(194)同上,第962頁。。“廣解苟免”,王天海解爲“自我慰解能僥倖避禍”(195)同上。。此段言三勇,下勇即輕一己之生命而重財貨,禍患將至則自我寬解能僥倖避禍,而且不顧是非對錯,並以欲勝他人爲志。其所謂“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即指稱“惠施、鄧析”及“下勇”之人,“是非然不然”亦近《正名》篇“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之意。
由此言之,《正名》篇所論“淫説”淆亂是非之立場,並見於《莊子》(辯者、公孫龍)、《荀子》(惠施、鄧析、下勇之人)二書。《正名》所稱“淫説”,蓋爲擷取總結《莊》《荀》二書所言辯者不分是非、以説辭爲尚之風氣。
3. 《君守》篇“一能應萬”
《君守》篇云:“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196)吕不韋《吕氏春秋》,第454頁。此言執守一道能應萬變之理,唯有道者能爲之。其中“一能應萬”,亦見於《莊子》。《天地》篇云:“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197)郭慶藩《莊子集釋》,第403頁。又言:“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198)同上,第404頁。其所謂“萬物雖多,其治一也”與“通於一而萬事畢”,言天地萬物雖衆,而治理之法只一而已。成疏云:“一,道也。夫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末,故知一,萬事畢。”(199)同上,第406頁。以一應萬之理,《天地》篇之句式雖異於《君守》篇,但其言以探論持一應萬以治國之理仍近。又如《天道》篇云:“故曰:‘其動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200)同上,第462~463頁。“一心定”,成疏謂之“境智冥合,謂之爲一。物不能撓,謂之爲定。”(201)同上,第464頁。《天道》篇此處言定一心之重要,若能定於一心之理,即可服萬物、王天下,亦歸於以一應萬之理。
考之《荀子·非相》篇云:“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202)王天海《荀子校釋》,第175頁。王天海云:“此即執簡馭繁,以要統類之術。”(203)王天海亦引梁啓雄之説,其言曰:“以近,指‘審今日’;知遠,指‘觀千歲’;就時間上説。以一,指‘一二’;知萬,指‘知億萬’;就空間上説。以微,指‘審其人’;知明,指‘知上世’‘知周道’;兼時間空間説。《王制》‘以類行雜’,就是指用這種統類來審察古今繁雜的事物。”王天海《荀子校釋》,第180頁。可知“以一知萬”亦是言執守一道以馭萬物之道,而《非相》篇則非專就治國言之而已。《儒效》篇論“大儒”,亦云:“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204)王天海《荀子校釋》,第315頁。“以古持今”即參照先王之法以治今之世道。“以淺持博”“以一持萬”皆言以簡馭繁、以少馭多之理(205)王天海云:“淺,少也;博,多也。持,猶治也,馭也。以淺持博,即以少馭多之意。”王天海《荀子校釋》,第321頁。,唯“以一持萬”兼承上文“統禮義”之意,其“一”即“禮義”(206)王天海云:“以一持萬,即以禮義統馭萬物。”王天海《荀子校釋》,第321頁。。由此言之,《荀子》所言“以一知萬”“以一持萬”與《莊子》“通於一而萬事畢”之理相近,而《君守》篇“一能應萬”大抵亦承二書之説而闡述之。唯《君守》所言之“一”乃“因而不爲”之君道,非如《荀子》所言之“禮義”,其論説模式雖一,而義理則相去甚遠。此又一吕氏門客博采他書,並據己説修訂前人論説之證。
總 結
吕氏門客撰寫“君道無爲論”之時顯然嘗試融匯各家論説,本文分析吕氏門客具體如何整合諸説,傅武光曾總論“無爲”論説,並云:“《吕氏春秋》以解決政治問題爲其立説之重點。對於‘無爲而治’之説,自不能不在意。……唯儒道法三家俱主無爲,而各異其趣,則吕書之言無爲,究屬之誰家乎?吕書言君主無爲之要,常在乎‘處虚服素’‘神合太一’‘虚無爲本’,是皆道家之言也。其言無爲之具體作法,要在‘分職’‘審分’,而君主執轡以御之,復引慎到、申不客之言以爲證;此則法家之言也。”(207)傅武光《吕氏春秋與諸子之關係》,第175~176頁。傅氏從傳統之學派歸屬爲分類法,並指《吕氏春秋》“無爲”論説之宗趣在儒家,此實其論説之偏見。然而,傅氏詳考儒道法三家於《吕氏春秋》“君道無爲論”之角色,可謂切中肯綮(208)傅武光云:“總之,《吕氏春秋》之言無爲,實以儒家之仁義爲根本,而出以道家之形態,復以法家之架構表現之也。蓋道家只言形態而不具顔色;法家之架構,亦僅具工具性能而無價值意味,故皆可視爲‘共法’而運用之也。”見傅武光《吕氏春秋與諸子之關係》,第180頁。。
本文承其思路,從《吕氏春秋》所用之文獻材料剖析“君道無爲論”如何整合諸子論説。《吕氏春秋》“君道無爲論”用語頗近於《老子》,亦見其引用《老子》一書之痕迹。其“無爲”之理論框架亦多類《韓非子》,主要吸收其君主無爲、臣下有爲之理論,但《吕氏春秋》之“無爲”異於《韓非子》之處亦顯然而見。再者,本文亦就《慎勢》篇與《荀子·王制》《慎子》二書之關係提出新證,即《慎勢》篇之撰者或許同時參照上言二書或其相關材料以成篇。最後,本文就“君道無爲論”與《莊》《荀》二書並見之用例,深化《吕氏春秋》如何融匯諸家論説之討論。總上言之,《吕氏春秋》“君道無爲論”吸收諸子論説之現象甚爲豐富,或據一書改易另一書、或同詞異義、或另立新説,方法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