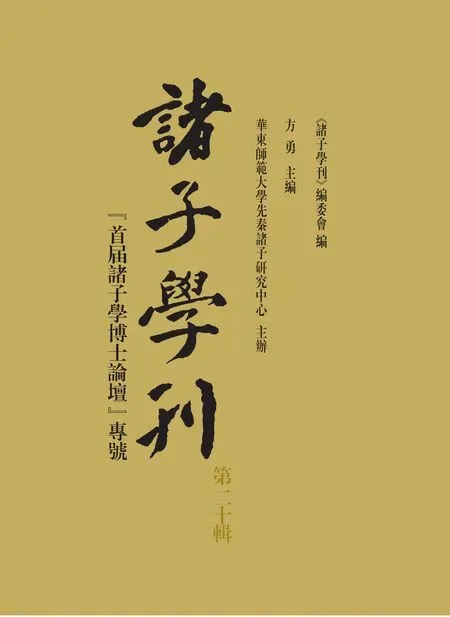禽獸與秩序
——先秦諸子文本中“禽獸”的意義
楊基煒
内容提要 在不少論述中,禽獸扮演着道德勸説或文明比較中低劣者的角色,但禽獸的特性以及生活狀態,都非常接近於人。它們能生存、能形成群體生活。在原始時代,人類甚至不如禽獸。諸子常以禽獸爲例,以期説明人類生活的特殊意義。而理解後者的前提,首先在於把握禽獸之特殊性。其特殊性在於,它們恰好缺乏構成人類生活的最關鍵因素: 義。在諸子的論述中,禽獸無不被用以闡述“義”的問題,即人爲秩序如何産生,以及爲什麽秩序是必要的。
關鍵詞 禽獸 秩序 倫理 自然狀態 義
禽獸是先秦諸子用以彰顯人的特殊性的事物。諸子的論證思路大要有三: 第一,將禽獸視爲低於人類的次級生物,以期揭示獨特的人性;第二,用禽獸生活來描繪一種自然狀態,以期闡發文明生活的特徵與意義;第三,以禽獸爲譬,以期昭顯聖人的用意,激起國君反思。
上述視角會引出儒家脉絡中經久不衰的話題——人禽之辨。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若任由本心放逐,人與禽獸便没有區别。本心、良知良能等似乎都是人所獨有的特質,諸子會藉由這些概念去推演或建構人類秩序。在經學中,禽獸也用於譬喻夷狄,人禽之辨由此轉化爲夷夏之辨。夷夏之辨揭示了兩種既存生活方式的差異,進而彰顯了華夏文明的優越性。然而這卻帶來一個問題: 夷狄可變爲華夏,禽獸又如何變爲人呢?
换一種角度來看人禽之辨,其所隱含的意義又能如是展開: 人類有其群體生活,禽獸亦然。禽獸生活至少有兩種,第一是虎狼廝殺,這是不安定的;第二是牛羊犬豕的生活,它們過着較爲安定的群體生活。前者近似於自然狀態,而後者與人類生活的根本區别是什麽?考慮到“牧民”“畜妻子”等詞彙,不妨推定,禽獸一詞不全是負面意義的。因此,若要進一步揭示“禽獸”的意義,其首要方式在於考察禽獸本身的特殊性及其隱喻,並以此考察先秦諸子所要論述的問題。
一、 由恐懼到厭惡: 文明視角的産生
恐懼是人類對禽獸的最初態度。有巢氏的傳説描繪了上古人類懼怕禽獸的情形: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韓非子·五蠹》)
“且吾聞之: 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莊子·盜跖》)
諸子引述有巢氏的傳説,意在説明人類由自然動物轉變爲社會動物的過程,如同魯迅在《自文字至文章》中指出的:“至於上古實狀,則荒漠不可考,君長之名,且難審知,世以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者,列三才開始之序,繼以有巢燧人伏羲神農者,明人群進化之程,殆皆後人所命,非真號矣。”(1)魯迅《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頁。
韓非子與莊子的叙述大致相仿,可見有巢氏傳説在戰國時期已經很流行了。在上古時期,人類稀少,禽獸衆多。人類不敵禽獸,此時有聖人出現,發明木屋,民衆能居於房子之中而躲避禽獸的傷害。莊子則認爲,民衆自行巢居於樹上,躲避禽獸傷害。
就其細節而言,也存在幾點疑惑,比如《韓非子》中“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兩句的關係是什麽?人類不勝禽獸蟲蛇,是因爲數量原因,還是禽獸有爪牙之利,抑或禽獸的生活方式破壞了人類生活呢?而《莊子》認爲人類白天拾取樹果,晚上在樹上休息,由此可猜測,人類懼怕在夜晚遭受禽獸傷害。在樹上棲息,夜晚能安心休息。
木屋的出現,意味着人類與禽獸能够分隔開,而人類也能躲避禽獸的傷害。韓非子認爲,聖人能讓人類躲避傷害,贏得了民衆的歸附。有巢氏以降的傳説,大多也是由此引申出統治者的統治正當性,即統治者做了某件開端性的大事情,或發明了某類事物,使得民衆不受傷害,民衆因此而歸附於他。
在有巢氏時代,禽獸對人的影響,主要在於它們會傷害人類,與倫理、文明等並無瓜葛。而人類也並不優於禽獸,他們只能選擇躲避禽獸,在莊子叙述中,地面是人獸相争的領域,人類不敵禽獸,才逃到樹上築巢而生。另一方面,禽獸在一些方面强於人類,數量多暗示着它們可能是群體,而人類群體不勝禽獸群體。此外,禽獸的體力、爪牙、毒液等,都强於或異於人類,如《淮南子·説林訓》云“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
與莊子相反,孟子叙述了大禹時代,禽獸占據地面而爲人所驅: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没,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宫室以爲污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説暴行又作,園囿、污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悦。”(《孟子·滕文公下》)
在這個叙述中,“水逆行”象徵着人類與禽獸的顛倒。由於大水覆蓋了陸地,因此蛇龍得以居住在陸地上。如前所述,人類對於禽獸來説,力量薄弱,一旦蛇龍居於陸地的水中,那麽人便無法安定地生活。人類只能躲避禽獸。大禹治水,疏通河道,引水入海,驅趕蛇龍進入沼澤。由此,人類又占據了土地而得以安居。
所謂“一治一亂”,堯舜以後,人類社會又陷入了混亂狀態。倘若堯舜時期的大洪水源於天譴,那麽堯舜以降的混亂則源於暴君造作。由於暴君破壞了民衆安居的房子以及耕種的田地,而修建了湖沼和園囿,這又吸引了禽獸前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的叙述暗示着人類生活與禽獸天然對立。只要人類賴以生活的房子和田地遭到破壞,那麽禽獸就會占領人類的生活領域。换而言之,擁有房子和田地是人類與禽獸的區别之一。
逮至周公輔佐武王討伐商紂,他們將飛廉驅逐到海邊並誅殺他。倘若陸地是孟子語境下人類的生活領域,那麽海隅就是人類生活的邊界。周公的做法,既將惡人驅逐出了人類的生活環境,同時也在邊界施行殺戮,保全了人類生活的健康。此外,虎豹犀象等禽獸,也被一同驅逐出去。
在孟子的論述綫索中,禽獸暗示着危害人類倫理生活的事物,譬如邪説暴行等。禽獸占領人類的領域,正如邪説占領人心本應占有的地方,它們使得人無法保持正常的倫理生活,譬如孝父忠君等。而大禹、周公、孔子、孟子所要做的,就是驅逐禽獸,平息邪説,拒斥暴行,來讓人回歸到本有的位置。
由此來看,禽獸便被視爲人類的對立面。倘若人類不能保存他們獨有的事物,禽獸便會占據主導。這種觀念,不止出現在《孟子》之中:
“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荀子·勸學》)
“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禮記·曲禮》)
“無别無義,禽獸之道也。”(《禮記·郊特牲》)
“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别,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管子·立政九敗解》)
《荀子》的“義”,《禮記》的“禮”,《管子》的“禮義廉恥”,均是人應當保持或堅守的事物。“禮”“義”等大體都是與倫理、道德相關的事物。上述論述可簡單還原爲: 倘若人放棄道德、不行倫理,那麽他與禽獸幾無區别。
這樣的還原並不準確,因爲這個邏輯同樣適用於一切勸説的例子,譬如人應當不貪婪: 禽獸貪婪,倘若人貪婪了,那麽人與禽獸無區别;人應當多讀書: 禽獸没有高效而複雜的認知系統,倘若人不進行複雜的認知,那麽人與禽獸無區别。這樣的邏輯繼續演化下去,則成了: 烏鴉反哺,羊羔跪乳,禽獸尚且懂得孝,人若不孝,那他便連禽獸都不如。這種萬能的勸説邏輯,便掩蓋了先秦諸子的思考。
所謂“禽獸”,大抵不是禽獸對自身的理解。人們將正面或負面的價值意義賦予它們,才有所謂人禽之辨的“禽獸”。這種賦予,往往藴含着人們對於這些意義的理解。它們對於形成人這一群體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如前所述,倘若人類群體不具有某些特徵或學會某些東西,那麽在自然環境下,人類必然不勝禽獸。因此,考察“禽獸”,應當思考禽獸生活本身的優勢或缺陷,以及其優勢對於人類生活而言的意義、造成其缺陷的原因等等。
二、 禽獸的内涵: 無秩序的原始狀態
禽與獸,意義模糊。《爾雅·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禽”指鳥,“獸”指走獸。如前引孟子文:“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禽獸即鳥獸。“禽”也可指稱“獸”。《説文解字》云:“禽,走獸總名……禽、離、兕頭相似”;“離,山神,獸也,從禽頭”,“兕”是野生青牛或者犀牛,也屬於獸,如孔子云“虎兕出於柙”,兕與虎屬於同樣兇猛的野獸,許慎認爲禽、離、兕的頭相似,可見禽指稱猛獸一類。段玉裁補充道:“然則倉頡造字之本意謂四足而走者明矣。以名毛屬者名羽屬,此乃稱謂之轉移假借。及其久也,遂爲羽屬之定名矣。《爾雅》自其轉移者言之,許指造字之本言之。”(2)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746頁。最初“禽”指的是野獸,但後來被用來指稱鳥類,時間長了,“禽”便專指鳥類了。簡言之,在一般用法中,“禽”大多用來指稱鳥類,“獸”指稱四足行走的動物。
“禽獸”一詞,其意義也模糊。籠統來看,“禽獸”包含家養與野生動物。比如齊宣王不忍牛的觳觫之聲而以羊易牛,孟子稱“今恩足以及禽獸”(《孟子·梁惠王上》),可見“禽獸”包含牛羊一類的家養動物。更普遍的用法中,“禽獸”特指野生動物。比如《周禮》云“六禽”“六獸”,鄭司農注云:“雁、鶉、鷃、雉、鳩、鴿也”;“麋、鹿、熊、麕、野豕、兔也”(3)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周禮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頁。,這些動物均非用於家庭日常食用與使用的事物。又如《荀子·致士》云“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清明的政治是民衆所歸屬的,山林是禽獸的歸屬地,可見禽獸不屬於家庭豢養的動物。《禮記·月令》載“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禽獸生活的地方是山林藪澤,它們在山林之中自己尋覓食物,生存與否全賴自身,與家養動物的“牧養”“畜養”全然不同。人類對待它們的態度是狩獵,這亦可見禽獸指稱野生動物。
禽獸,固然可以泛指一切野生動物。但進一步辨析的話,虎狼豺等動物又不屬於禽獸,這在《荀子》最爲多見:
“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修身》)
“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正論》)
“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臣道》)
第一則材料説明,禽獸與虎狼有區别,虎狼更側重於心靈上的特質,而禽獸傾向於行爲上的表現。但古人有互文的習慣,第二條材料則説明上述區别是存在的,而且虎狼在心靈上的特質體現爲貪。這種用法並不特殊,《史記·魏世家》載: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
秦人和戎翟生活在相似的風俗之中,他們都有虎狼之心。所謂的虎狼之心,指稱的就是“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這與荀子稱“虎狼貪”相一致。《史記·項羽本紀》也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虎狼的特徵在於心貪。它們一方面可以無休無止地追逐某些利益,另一方面爲達成目標而不擇手段。因此,荀子稱“狎虎則危”,親近小人,如同親近老虎一般,隨時有生命危險。
“虎狼”涉及的是生存,“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人們出於生存的考慮,擔憂爲小人所害,才敬不肖者。禽獸涉及的是倫理或禮義,“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們理應敬賢者,倘若在理應尊敬的時候,不生尊敬之心,那麽建構在上下尊卑次序之上的社會秩序便有混亂的可能。“禽獸”涉及的是秩序。生存是最低限度的,即使處於混亂狀態下,人們也能生存。
“禽獸”出現的場合,多半與混亂相關。除上述材料外,孟子叙述大禹治水、周公伐紂等一系列的事件時,也以“亂”刻畫當時的社會狀態——“一治一亂”,“天下又大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荀子云“桀紂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正論》)。禽獸,破壞人類的生活;禽獸行,破壞人倫。
其次,虎狼和禽獸,象徵着義的兩方面。第一,在分配上,義是人們取其所應取。《孟子·盡心上》載“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即使人之將死,需要食物,倘若不是自己所應得的,“行道之人弗受”。虎狼,貪於利。對於虎狼而言,没有什麽東西是應得或不應得的,它們只想要更多的利益,譬如國君如虎狼,便追求更多的土地而對外擴張;臣子如虎狼,便追求更高的地位而弑君。
第二,從規範性看,義是人們各有其位,各安其分。《荀子·仲尼》載“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年少者事奉年長者,身份卑微者事奉身份顯貴者,能力或品德不足者事奉賢達之人,是義最基本也最普遍的内涵。義,便建立在這種分别與差序的基礎上。原則上,義建立在人類的不平等之上,無論是自然性,還是社會性。掌握更多資源或能更有效地運用資源的人,自然能養活更多人,也因此擁有高於一般人的地位。義的第一層含義,規範了這些賢達或顯達之人,《荀子·强國》載:“夫義者,内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内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要求人應當有所節制,符合禮的規範,根據自身的身份來取其所應取、與其所應與。禽獸的問題,不出在第一層含義的義上,而源於它們没有因“其位”“其分”而産生這種規範性,譬喻到人身上,便是見到賢者而不待之以尊敬。這種叙述,暗示着禽獸能够認識到他者是否爲自己的父母,是否爲賢者等,問題只出在與之相應的規範性是否産生。由此來理解《荀子·王制》“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禽獸與人的區别,就在於是否有“義”,是否能産生和諧而穩定的秩序。
禽獸的另一個特徵體現在對父親和雌雄的態度上。《荀子·非相》概括爲:“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别。”禽獸有父子關係,也存在雌雄關係,但這些關係並不構成對它們行爲的規範。父子關係,亦見於《儀禮·喪服》:“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在古人眼裏,禽獸只會認識並親近母親,或許是因爲雌性動物會自然地生産並哺育幼崽。另一方面,這也與雌雄之别相關。普遍來看,雌性動物可以和任一雄性動物交配,倘若雄性動物没有在幼崽出生後進行哺育和保護行爲,那麽幼崽自然不知道誰與它有親情,遑論孝父敬父了。
如此叙述,不僅指禽獸,還被用於描述人類的原始狀態或作爲假想的自然狀態: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别,愛私則險。民衆,而以别、險爲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争,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説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商君書·開塞》)
天地剛剛形成,人類便産生了,這時候,人們只知道生育自己的母親,而不知道也不曾想過自己的父親是誰,他們天然地親近那些親愛自己的人,天然地吝惜自己及其擁有的事物。隨着人類數量的增多,分别和愛私便引起了紛争和混亂。紛争源於雙方存在訴求而無人能公正地裁決。此時,出現了賢能之人,他開闢了無私的領域,人們依循中正之法來實現自身的訴求,獲得公正的判決。
這種叙述正對應前文提及的邏輯。“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是一種禽獸的狀態。之所以荀子認爲禽獸見賢而不敬,是因爲賢者在禽獸的生活是無意義的。其中的關鍵,就是禽獸的世界不存在訴訟,更没有中正。强淩弱,衆暴寡,是叢林法則的表現,禽獸爲了生存而廝殺或逃竄。不存在通用語言,自然就不存在跨種族的交流。不存在交流,自然就没有訴訟。具有强力的動物,便成了這支群體的領袖。《吕氏春秋·恃君覽》載:
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
民衆如禽獸一般,以力量爲標準來衡量人事物。青年人使唤年長者,年長者敬畏壯年人。有力量的人被尊爲賢者,殘暴的人被尊奉。這帶來的結果,便是人與人互相殘害,没有半點時刻可以安心休息。禽獸的生活,註定是朝不保夕、終日不安的狀態。結束這一混亂的狀態,商鞅學派認爲應當引入公的領域,使得人們在其中能解決訴訟;《吕氏春秋》則認爲應當設立專門思慮的統治者,“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恃君覽》),他們能根據長遠的利益來統率民衆,建立原初秩序。公權力由此産生。
此外,還有另一類模式,即由分别男女,過渡到明晰父子關係,乃至於通過父子關係來爲整個禮義系統奠基。在這種叙述中,禽獸的狀態要和諧得多了。《莊子·盜跖》載: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於於,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在莊子的描繪中,人們依然是知母而不知父,和麋鹿生活在一起,但他們非常淳樸,没有傷害他者的想法。這種圖景,固然與莊子思想有關。但知母而不知父,會導向另一條綫索: 没有分别。《禮記·曲禮》云:“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由於禽獸没有禮法的規範,所以鹿的父子會和同一只母鹿發生交配行爲。這不僅發生在禽獸世界中,人類群體也曾如此。《史記·商君列傳》載: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别,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
商鞅認爲,秦人奉行戎翟之教,父子無别,同室而居。這恐怕並非説父子住在同一間房子裏,而是説父子共同處在一個私人空間,乃至於和鹿一樣没有分别。因此,商鞅入手之處,是分别男女,將男女關係納入一定的規範之中。通過教化來禁止淫亂,父子關係才可能被確立起來。又《禮記·郊特牲》載:
男女有别,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别無義,禽獸之道也。
母子相親,是天然的,爲何母子相親就不生義呢?同篇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割刀因其鋒利而能切肉,這是自然而然的;而附有鈴鐺的鸞刀,其刀刃並不鋒利,但在祭祀的環境下,用鸞刀和着音樂來切肉,目的不在切肉,而在於中節。符合節拍和禮儀,是人們對之賦予的意義。
義,是禮的内核。它不完全是自然的,一方面它要銜接由人製作的秩序體系;另一方面,它也源於一些自然的特質,譬如鸞刀是在切割的過程中發出鈴聲的。因此,分别男女之後,才能明確父子關係。在明確父子關係後,父子相親,才可能産生最原初的義。這是因爲父子相親暗示着人們受到文明或人爲秩序的影響,進而産生一種自然之外的情感。譬如掌握家庭資源與權力的父親,使得家庭成員對之産生尊敬或敬畏的感受;承擔撫養任務的父親,使得孩子對之産生親愛或感激的感受等等。自然狀態下,幾乎不存在“應當”的情況,它們縱欲所爲,荀子云“縱情性,安恣孳,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非十二子》),可見禽獸没有“義”;當出現超越於自然情性或情欲的善時,義才有可能被引出。不然,人們只需要放縱情性,即可讓生活環境處在秩序狀態中。
要之,倘若把禽獸作爲一個參照物,那麽先秦諸子討論禽獸問題,不是去論證人固有的親親之情,而是論證人倫生活中的義。義的多重含義,在禽獸問題中也被凸顯出來。
三、 人禽之辨: 群體秩序的形成
人與禽獸都有群體生活,荀子云“禽獸群焉”(《勸學》)。群居動物形成群體是自然而然的,不存在這個群體内部崩塌而回歸到個體狀態的情況。而在諸子語境下,人類社會總是會面臨兩個問題: 亂與危。亂,形容社會狀態;危,關涉着統治者的政權。一個小國,可以危而不亂,因爲國君對内治理妥當,社會秩序井井有條,但大國虎視眈眈,隨時都會吞併它。但亂而不危的國家,則少之又少。亂和危的問題,説明人類社會並非自然構成的,一旦有所不當,便會從秩序回到混亂狀態。如前所述,禽獸問題論證的不是自然生活如何形成,而是文明秩序如何産生的問題。
禽獸有着强大的生存武器,它們能讓人恐懼到躲在穴窟裏、爬到樹上生活。人與禽獸的差别,便在於人能形成創造效益的群體: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群,而人備可完矣。(《吕氏春秋·恃君覽》)
除了智力外,人在各方面都次於禽獸,但人卻能裁制萬物,制服禽獸狡蟲,面臨惡劣的生活環境也能抵抗得住。所以如此,是因爲人能够形成共同體。之所以能形成共同體,是因爲人們能相互合作,産生效益。之所以在群體中能産生新的效益,是因爲存在良好的統治者,他能考慮長利,協調人們的關係。在《吕氏春秋》看來,人類的合作(相與)和領導者的領導才能(君道)是使得人類强於禽獸的地方。
在《墨子·非樂》中,墨子給出了更具體的叙述:
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絝屨,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蓺,多聚叔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此其分事也。今唯毋在乎王公大人説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
在墨子看來,禽獸可以自足,而人類卻不能。在温飽層面上,人類社會需要有人耕作和紡織,禽獸的皮毛能爲自身提供温暖和禦寒功能,它們飲水食草,也能滿足温飽需求。在維繫秩序以及使人類群體産出效益的層面上,需要有人專門裁決訴訟,有人專門指導人們生活,也需要有人竭盡思慮,形成良好的經濟狀態,儲存足够的資源等。各類人各司其職,各安其分,完成原初的社會分工。
這樣的叙述,也見於《荀子》: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 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 分。分何以能行?曰: 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强,强則勝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
人與禽獸的差别,就在於人有義。義的表現之一,是人們能够理解並做自己所應當做的事情,而這些事情源於聖人根據秩序而作出的合理規劃:“分義”。人們能認識到義,便能認識到各自的職分和位分,各司其職,各安其位,這個群體才能和諧摶一,如《荀子·榮辱》云:“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人能摶一,才能聚攏並形成强大的力量。力量强大,才可能改變自然事物,譬如伐木造宫室來居住。如前所述,造宫室象徵着人與禽獸徹底分别開: 由最初人居於房子内躲避禽獸的傷害,到居宫室之中人們才有男女之别、父子之親,再到建造宫室象徵着分工和一的共同體産生。由此可見,群體秩序産生的兩個條件,一是分工,二是資源配置。
禮義的作用不止如此。禽獸的另一特徵是縱情性,虎狼則貪欲無窮。餓了吃,渴了喝,累了歇,時節到了交配。它們被自己的情性所主宰。倘若人類如禽獸一樣,没有節制,那麽在人多而資源少的時代,人們必然會爲了滿足自己的欲望而相互争鬥殺害;即使在人少而資源多的時代,人們也可能會聚攏財富而統治其他人,以滿足自身的權力欲。《列子·楊朱》中子産云:“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欲,則性命危矣。”這種叙述與荀子相似,人所以爲人,在於人能思慮。通過思慮,人能判斷事物的優劣利弊、善惡真假,也因此人才有戰勝自身情欲的可能。倘若判斷的準則是禮義,那麽人自然能别於禽獸,克制私欲,完成禮義的要求。
荀子所述的義,是由聖人根據秩序要求而裁定製作的,即使自然之勢要求一個人做出某種倫理行爲,倘若這種行爲不符合整體秩序,那麽不做該行爲反而是良善的:“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荀子·子道》)與先秦諸子不同,清代章學誠所論述的分工,則是源於群體本身: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啓閉其門户,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尊之别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衆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4)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19頁。
三人,或指三口,或泛指多人。他們要共同生活,必然要采集資源。爲了解決饑渴問題,就必然要去汲水砍樵。只要不是一個人居住,那麽三個人必然有分工或换班,來均分各自的勞動和責任。又存在各自相争的情況,那麽自然要選擇一名年長者來解決紛争,保證公平。由於年長者的特殊職分,長幼尊尊的秩序便産生了。人口增多,地域增廣,又需要有傑出的人來理順繁雜的人口與事務。形勢紛亂,又需要有德之人來施行教化,使民衆自然模仿,逐漸順從。
在章學誠看來,某種意義上,群體秩序内在於人。只要將人置於群體之中,人們便會根據群體的需要,自然而然地參與到秩序的構建之中。但這個群體秩序的基本要素,也不出先秦諸子的設想。譬如分配職分,起到裁決争訟作用的賢者或長者,治理社會的君主,以及克制情欲的教化等等。
小 結
上述基本要素,無不源於先秦諸子對於禽獸問題的思考。現實中的禽獸生活,或者如莊子所述,一派祥和;或者如叢林法則所描述的一般,禽獸間互相殺害,朝不保夕。假想中的禽獸生活,則被賦予重重意義。禽獸雖然能群居,但卻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也不能形成使群體成員安寧生活的秩序。二者的缺失,是因爲禽獸生活不存在“義”。它們有認知能力,能認識它們所需求的食物,能認識群體中的領袖,也能認識哺育自己的母親。人之所以爲人,是因爲他們能認識到超出自然情性範圍内的人事物,並且能産生相應的倫理情感,譬如民對君的尊敬,子對父的親愛等等。以此爲端緒,引申出一整套的由人賦予其意義的秩序體系。這種體系,包含着分工、資源配置、節制情性等因素,這些因素使得人類群體更爲强大有力,摶一力量來改變事物,産生更多的資源,在合理的分配下,滿足群體成員的需求;同時也形成了倫理秩序,使得分别男女、父子得以可能,也使得對君臣關係、人我關係的論述得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