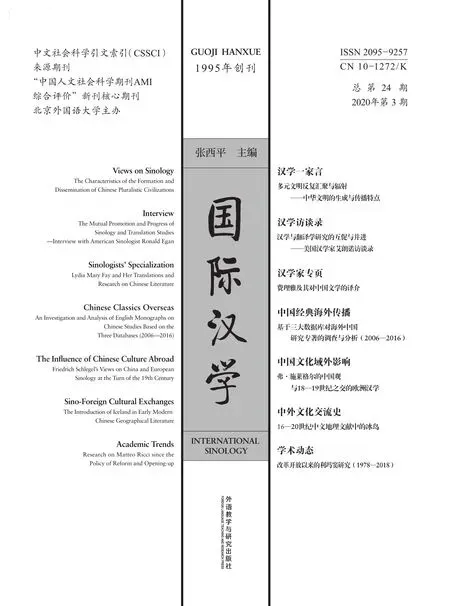弗·施莱格尔的中国观与18—19 世纪之交的欧洲汉学 *
□ 陈 敏
弗·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著名代表和奠基人之一,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文化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和古典语文学家”①Friedrich Schlegel, https://de.wikipedia.org/wiki/Friedrich_Schlegel,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8 月12 日。,亦是欧洲杰出的东方学者。他曾深入研究印度、中国文化近30 年,被视为开拓性的印度学家。学界对施莱格尔东方学的研究多聚焦其印度学,而忽视他的中国研究。实际上,从施莱格尔研究中国文化的持续时间、广度和深度来看,至少证明他对中印两国文化同等重视。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正是欧洲面对中国文明从18 世纪的“热”转为19 世纪“冷”的开始阶段。②张西平:《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159 页。施莱格尔的中国观与欧洲汉学的转折期紧密相关。作为当时著名的东方学者和耶拿浪漫派(Yana Romantics)的灵魂人物,其中国观对当时海外汉学接受史研究有着重要价值。目前,国内外从文学、哲学层面针对施莱格尔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从海外汉学层面的研究尚不多见。
当前,针对施莱格尔中国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基督教与他者:弗·施莱格尔与谢林对中国的阐释》(“Christianity and the Other: Friedrich Schlegel’s and F. W. J. Schelling’s Interpretation of China”)③Lucie Bernier, “Christianity and the Other: Friedrich Schlegel’s and F. W. J. Schelling’s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 2, 2005, pp. 265—273.,《德国唯心主义中的寻找东方》(“The Search for the Orient in German Idealism”)④Vittorio Hösle, “The Search for the Orient in German Idealism,”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 163, No. 2, 2013, pp. 431—454.,《德国东方主义中的自我—他者:以弗·施莱格尔为例》(“Self-Othering in German Orientalism: The Case of Friedrich Schlegel”)⑤Nicholas A. Germana, “Self-Othering in German Orientalism: The Case of Friedrich Schlegel,” The Comparatist, Vol. 34, 2010, pp. 80—94.。本文以施莱格尔关于中国文化的著述为论据,结合时代背景探究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欧洲汉学对其影响,并阐述其中国观特点,以期为海外汉学接受史研究提供理论尝试。
一、弗·施莱格尔的东方情结
18 世纪启蒙运动兴起,崇尚理性推动着欧洲世俗化进程。理性取代神性成为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大趋势。早期浪漫派们对此痛心疾首①以赛亚·柏林著,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年,第40 页。,他们认为神性式微而理性尚未完善,过度强调理性导致人的精神价值缺席,掀起反思启蒙运动的思潮。施莱格尔于1802 年撰写的游记《法兰西之旅》(Reise nach Frankreich)中,称欧洲人的共性是“左右一切和最终决定一切的主导原则,乃是盈利与暴利”②弗·施莱格尔著,李伯杰译:《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年,第230 页。, 哀叹失去中世纪基督教光芒沐浴的德国仅仅“从德国人过去更美好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里遗留下来……无以计数的残渣碎片,我们所有的只是这些残留下来的碎片”③同上,第231 页。。此时的欧洲“由于内在的必然而分裂”④同上,第233 页。,极端分裂的精神力量彻底丧失了宗教能力,衰败且无自我上升之力。因此,施莱格尔认为重建欧洲精神只能借助外来的影响进行一场革命。⑤同上,第232—235 页。
施莱格尔认为这场革命应该来自亚洲,东方是“一个原始的、永不枯竭的热忱之源”⑥同上,第238 页。,代表着未曾分裂的整体力量,“真正的革命只能从凝聚起来的力量的中心里出来”⑦同上。。施莱格尔的东方情结既源于对现实欧洲的失望与否定,也源于东方对欧洲精神根基——希腊思想和《圣经·旧约》的巨大影响。施莱格尔视希腊精神为欧洲精神典范,然而“欧洲人片面的,仅仅游戏性地研究希腊人,致使过去几个世纪里,欧洲精神过多远离古老的严肃,甚或远离所有更高级的真理源泉。”⑧Siehe Friedrich Schlegel, 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 Heidelberg: Mohr und Zimmer, 1808, S. 219.《旧约》时而“晦涩难懂”,有悖“神启的单纯”⑨Ibid., S. 198.。溯其缘由,概因东方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在西方接受过程中被误读、扭曲、篡改。因此,想要识清欧洲最古老的古代必须研究东方,“……还需完全确定东方思维方式与欧洲思维方式的关系,说清楚前者对后者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应当产生怎样的影响”⑩Ibid., S. 196.。在他看来,越是重新深入了解和观察东方古代,欧洲人越是能领悟更多属神的东西和精神之力。
二、施莱格尔的中国观概貌
施莱格尔“不仅研究文学和哲学, 一再关注道德伦理学。在他看来,道德伦理学包括风俗习惯、法律法规。此外,宗教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神话学均是其东方学兴趣所在。”⑪Friedrich Schlegel, Vorlesungen und Fragmente zur Literatur—Teil 1. Orientalia, Bd.15, in 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be, hrsg. v. Uraula Struc-Oppenberg. Paderborn: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2002, S. XI.1802 年至1828年,他以历史学家严谨、执着的精神持续关注和研究中国,不仅关注中国的“人口数量、地理范围等外在力量……更在于内在精神或者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在于其较高的教育程度及已达到的精神发展阶段”⑫Friedrich Schl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Achtzehn 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28, Bd. 9, in 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be, hrsg. v. Jean-Jacques Anstett. Paderborn: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1971. S. 61.。据35 卷本《弗·施莱格尔批评文集》(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be),从未踏足亚洲的施莱格尔,广泛搜集、记录了当时所能获得的汉学成果并予以阐释。1802 年他在《诗歌与文学断片》(Fragmente zur Poesie und Literatur)中最早谈到中国,之后相关记录和研究散见于断片、讲座、专著中。
19 世纪初期,欧洲汉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汉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和欧洲同时展开。中国本土的汉学研究主要是在华传教士汉学,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明清来华传教士为中国文化走向欧洲做出了巨大贡献,促成16—18 世纪的“东学西渐”,“实予17 世纪、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创造了思想革命的有利条件”①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前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欧洲以德国东方学者研究为主,与法国、英国等国学者先后展开,学界合称为“欧洲早期汉学”②张西平:《展开西方早期汉学的丰富画卷》,载龙伯格著,王丽虹译《汉学先驱巴耶尔》,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 年,第2 页。;1814 年11 月29 日,“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讲座,标志着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学术体系中正式确立”③李真:《从历史中国走向未来中国——二百年法国汉学研究的新起点》,《国外社会科学》2014 年第6 期,第154 页。,欧洲诞生了专业汉学。因此,在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参与汉学研究的人物庞杂,很难进行学科分类。从施莱格尔接受的汉学文献来看,除了早期传教士的汉学译著和著述之外,法兰西学院首任汉学教授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欧 洲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伏尔泰等人的著述以及英国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访华使团纪要等均为其文献来源。
施莱格尔热衷使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在此层面上,雷慕沙对施莱格尔尤为重要,为其提供了更加丰富切实的文献资料及突破性的研究方法,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的中国观。施莱格尔的评判可兹证明:“雷慕沙对中国的评述很可能最具权威性”④Schl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achtzehn 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28, S. 73.,“这位著名的法国学者雷慕沙,他为我们这个时代赋予整个中国研究以新的生命,比既有研究更加鲜明清楚。他认为那本首部中国文化基本概论论述的中国思想范围极其有限且歪曲失真,遂颇有见地给予评注,其论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⑤Ibid., S. 70.。
施莱格尔将中国的哲学宗教、历史政治、语言文字等与欧亚非等国进行平行比较。他对中国的认识也随着研究逐渐改观。在1802 年和1803年,在东方学研究之初,他比较了中国、埃及和印度,认为“中国人或许纯粹是埃及人的影子”⑥Frichtrich Schlegel, Fragmente zur Poesie und Literatur Teil 1, Bd.16, in 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be, S. 375.,亦或中国部族源自印度,他们从印度人“那儿接受了很多”⑦Schlegel, Fragmente zur Poesie und Literatur Teil 1, S. 375.。两三年之后,他眼中的中国形象彻底改变,“尽管在他们那儿未发现与印度同样多的古代神迹,但是无疑(中国)是最具教养的民族”⑧Friedrich Schlegel, Vorlesungen über Universalgeschichte (1805—1806), Bd.14, in 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be, S. 252.,中国人是“亚洲最具教养的人”⑨Friedrich Schlegel, Fragmente zu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I, Bd.20, in 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be, S. 71.。
施莱格尔认为,“人类的四要素是诗学、哲学、道德伦理和宗教”,⑩Schlegel, Vorlesungen und Fragmente zur Literatur—Teil 1. Orientalia, S. XI.因此他对中国的研究虽涉猎广泛,但始终围绕这四个方面寻其文化精神特征。以下就从这四个方面概述施莱格尔的中国观并梳理他对欧洲汉学的继受。
施莱格尔认为中国文学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特点。1828 年,他在维也纳举办的历史哲学讲座中综述了中国文学特点。他认为,中国流传的古代文学“不像亚洲的大多数民族那样,富含诗歌甚或变形为诗歌。譬如印度或者欧洲早期异教国家的文学均属此类”⑪Schl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achtzehn 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28, S. 76.,并指出中国古代文学单纯从历史层面上进行构思设计。“因此,即使是中国人的诗歌,也不像那些民族具有神话性,而长于抒情性或现实性。前者见于孔子编辑的《诗经》,后者见于当前多部知名的小说译本。它们聚焦现实生活,描写社会关系。”⑫Ibid.
施莱格尔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以雷慕沙的中国典籍及世俗文学翻译为基础。雷慕沙的《玉娇梨》(Lü-kiau-Li, ou Les deux cousines)、《中国短篇小说译本》(Sur quelgues mouveiles traduites du chinois)(三卷本)等为他提供了欧洲汉学界不曾有过的俗文学资料。施莱格尔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等为中国文学的代表,在这些译本的助益下,他进一步认识了孔子学派。他从雷慕沙译本中了解到中国风俗,并曾在讲座中引述雷慕沙小说译本①《中国短篇小说译本》(Sur quelques nouvelles traduites du chinois)选自《亚洲杂纂》(Mélanges asiatiques),巴黎,1826年,II 卷,第335 页。Schl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achtzehn 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28, S. 64.中描述的民俗风情,如贵族绅士、学者们留着鸟爪似的长指甲,女性的三寸金莲,以此证明中国小说映照了社会现状。
在哲学、宗教方面,他重点阐释《易经》及儒道典籍。“如同这位浪漫派的几乎所有作品一样,施莱格尔的东方学研究取决于其哲学思考”②Schlegel, Vorlesungen und Fragmente zur Literatur—Teil 1. Orientalia, S. XI.。中国哲学是施莱格尔的研究之重,他将宗教与哲学合并。施莱格尔通过传教士汉学得知中国哲学以《易经》为基础和源头③Schlegel, Vorlesungen und Fragmente zur Literatur—Teil 1. Orientalia, S. 61。此处施莱格尔提到在巴黎图书馆发现一位传教士完整翻译的《易经》。,“老子和孔子两个教派发端于同一源头,却相背而行”④Schlegel, Vorlesungen und Fragmente zur Literatur—Teil 1. Orientalia, S. 18.。
施莱格尔最初受到法国东方学者和汉学家老德金(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的影响。老德金于1756 年、1757 年和1758 年在巴黎出版四卷本著作《匈奴和土耳其、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公元前直至当代》(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gols, et des a utres Tartares occtdentaux, & c. ayant et depuis Jesus—Christ iusqu’à présent,以下简称《通史》),并编辑出版多部法国来华传教士译作,如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的《书经》(Shujing,1771)法译本⑤Joseph de Guignes, https://de.wikipedia.org/wiki/Joseph_de_Guignes,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5 月17 日。。施莱格尔通过老德金了解到中国上古传说、阴阳八卦、易经和中国语言文字等。⑥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c. avant et depuis Jesus—Christ jusqu’à présent. Siehe Schlegel, Vorlesungen und Fragmente zur Literatur—Teil 1. Orientalia, S. 57ff, S. 195; Schlegel, 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 S. 59.
施莱格尔在《东方》(Orientalia)中依据老德金著述阐释了八卦、阴阳五行及其图像以及《易经》与汉字起源。“德金认为太清是原初空气,产生五种元素”⑦Schlegel, Vorlesungen und Fragmente zur Literatur—Teil 1. Orientalia, S. 59.。太清产生阴、阳,因而古老的阴、阳意指太清、道,即理性。“根据老子理论,道(理性)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⑧Ibid., S. 57.。 于是,施莱格尔认为阴阳是中国哲学的两个最基本概念,方生成八卦图像。
中国三大宗教“儒、释、道”中,施莱格尔起初对道、道家概念非常模糊。他最初谈到老子和道家时,引用伏尔泰观点:
关于中国人最古老宗教的报道总是谈到炼金,这看来属于一种弥撒形式的拜神仪式。中国人有三种宗教:那个最古老的、佛陀教和最后一个,现行的统治宗教——孔教。它看来只是一种伦理学,可能也是中国源生的。⑨此处施莱格尔在文献处标注:“Siehe V[o]lt[ai]re, tom[e] 23, p. 33 u[nd] 35,” Schlegel, Vorlesungen über Universalgeschichte (1805—1806), S. 42, Note 2.
此时看来施莱格尔还未接触到道家及道教名称,只知其为中国最古老的宗教。
后来,施莱格尔认为老子和道教是具有神话特征的宗教⑩Schlegel, Vorlesungen und Fragmente zur Literatur—Teil 1. Orientalia, S. 18.,与神秘主义和炼金术相关,道教“似乎完全以魔法为基础,可能是基于唯心主义哲学”⑪Schlegel, Vorlesungen über Universalgeschichte (1805—1806), S. 42.。 老子学说与西亚宗教存在近亲关系,“或许也与波斯古经最为一致。(与印度有非常多的近似性,因此印度教是其无可争辩的起源)——因此耶稣会士将之与旧约相类比”⑫Schlegel, Vorlesungen und Fragmente zur Literatur—Teil 1. Orientalia, S. 19.。显然,这些认识主要源自传教士汉学。明清耶稣会士们认为儒学能够与天主教相容,因此轻视道家研究。他们一方面将道家学说混同于巫术和迷信,另一方面“竭力在《道德经》等道教经籍中寻找与基督教教义相吻合的蛛丝马迹”①张粲:《法国经院汉学鼻祖雷慕沙的道教研究》,《宗教学研究》2017 年第1 期,第106 页。。
雷慕沙于1823 年在《亚洲丛刊》(Mélanges Asiatiques)上发表《论老子生平及其观点》(“Mémoire sur la vie et les opinions de Lao-tseu”),1825年发表《关于老子的生平及其学说》(“Sur la vie et les opinions de Lao-tseu”)。在继承耶稣会前辈观点的基础上,他认为《道德经》中“道”只能译成三种涵义:最高的存在(即上帝)、理性及体现,并举证老子思想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学派有某种相似之处,假设《老子》第14 章中的“夷” “希” “微”与基督教的耶和华等同起来,最终证明老子思想源于西方,并推断其“受过希伯来宗教影响”②姚达兑、陈晓君:《雷慕沙、鲍狄埃和儒莲〈道德经〉法语译本及其译文特色比较》,《国际汉学》2018 年第2 期,第9 页。。
在雷慕沙的影响下,施莱格尔放弃了《易经》和老子学说具有神话学和神秘主义的说法,转变为“《易经》是所有中国科学知识的基础”③Schl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achtzehn 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28, S. 71—72.。他借用古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阐释阴阳八卦,用希腊的“Thohu”与“Bohu”(混沌)概念与阴阳相比较,以说明八卦符号的本真意义和自然象征。《易经》与“柏拉图作品中的基本原理一样,经常谈到一和多,统一性和二元性作为本原的自然要素或者所有存在的首要原理”④Ibid., S. 73.。因此,《易经》基本理论以矛盾对立性为第一性,从中衍生出更多的矛盾对立性,对立之间存在和谐统一化。这是一种片面的动态思想的否定性绝对理性体系,本质具有泛神论特点,“不具普遍适用性。只以动态的生命法则和存在运动为基础,未全面考虑其他方面和通向内在体验、精神生活、心灵直观和神启的更高精神源泉”⑤Ibid., S. 74.,源自《易经》的中国哲学和宗教具有辩证和自然宗教特点。
施莱格尔眼中的老子学说最终被其后代门徒演变为泛神论,道家是“单纯思辨的理性体系”(reinen spekulativen Vernunftsystem)⑥Ibid., S. 75.。他甚至认为中国宗教最终走向泛神论皆因道家这一理性教派,“中华帝国广泛传播这种绝对理性科学的泛神论,以致中国的一个时代几乎为它所统治”⑦Ibid.。可见,雷慕沙对中国哲学的解读促成施莱格尔从理性和思辨的角度阐释《易经》、老子教派及中国宗教特征。
施莱格尔认为孔学对中国文化精神意义重大,是中国道德风俗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作为注重实践性的道德伦理学主导着中国伦理思想并与国家政权彼此融合,决定着中国古代的国家制度、历史传记。他对儒学基本持赞扬态度,从儒家礼制中深受启发。根据儒教“在一个学校式的国家中,私人生活被最大限度标准化,单一模式化管理,以便每个行为举止皆是规范的”⑧Schlegel, Fragmente zu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1820—1828), S. 17.,他提出了“真正荣誉”的政治理念,“荣誉”应是孔教式的标准规则,用来规范德国人的一切言行举止。“在德国的宪法和生活制度中,荣誉也必须决定一切,成为一切,就像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一样”⑨Ibid., S. 340.。
在他看来,佛教是“所有仿效真理的异教中最低级、最末端的”⑩Schl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achtzehn 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28, S. 76.,“无疑是所有伪宗教中最应受到谴责的宗教”⑪Ibid., S. 78.,传入中国损害了中国文化。施莱格尔的态度源自传教士们的理论。当时佛教被视为中国传布基督教的最大障碍,受到传教士们不遗余力地攻击。⑫参见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年,第142 页。
总体来看,施莱格尔“尊孔、轻道、蔑佛”的姿态,大多受到早期耶稣会士在中国的适应政策——“合儒补儒”“排佛排道”之影响。
身为著名的语文学家,施莱格尔认为:“古代世界中那些实际上只有内部历史的国家①施莱格尔认为中国属于这类国家。参见Schlegel, Fragmente Zu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1820—1828), S. 399.,语言(心灵原则)、知识(精神原则)和艺术(对应第三心理原则),即至高无上的意识和神启,构成其民族特征的三重原则”②Ibid.,因而他深入研究了中国语言和文字。
施莱格尔根据老德金《通史》③Schlegel, Vorlesungen und Fragmente zur Literatur—Teil 1, Orientalia, S. 198 ff.,认为汉字最早起源于伏羲、仓颉造字。夏、商、周时期随意发明毫无规则的大量文字,④Ibid., S. 61.《易经》及八卦的“那些象征符号必然影响中国文字”。⑤Ibid., S. 60.1806 年,施莱格尔在一则断片⑥Ibid., S. 61—62.中记录了汉字发展史,从大小篆、隶、楷、草等字体演变,到佛教引入26 430新汉字。他采用了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将汉字与印度、埃及、波斯、希腊等国语言进行对比,指出埃及和中文中名词占统治地位,而腓尼基民族以及印度语和波斯语中动词具统治地位。⑦Ibid., S. 377.他基于这些研究并结合雷慕沙等主要欧洲汉语语言学家的观点⑧Schl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achtzehn 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28, S. 64—65.,他最后总结道,这门语言只有300 多个,最多不超过400 个(在有些研究中只有272个)基本音节字符,全无语法,“汉语通过四声变化,完全以字表意。同音不同意,且毫无关联。这种字符现有80 000 个,埃及象形文字不过800个左右”⑨Ibid., S. 64—65.。这种语言更多以字符为基础,而不是活跃的语音,“因为通常160 个不同字符竟然发音相同”。⑩Ibid., S. 65.
施莱格尔认为:“语言之美由以下因素决定:1)词的丰富度——词干音节的数量及其构成多音节词汇的变化度; 2)统一性或意象程度”⑪Schlegel, Vorlesungen und Fragmente zur Literatur—Teil 1. Orientalia, S. 18.。他据此审查汉字体系,认为单音节汉字数量少,字音对照性不统一,字符数巨大。施莱格尔的胞兄奥古斯特·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将语言分类为曲折变形语、粘合语和孤立语。弗·施莱格尔在《印度的语言与智慧》(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 1808)中将中文归类为孤立语,视为最低级语言,认为它不具备语言美。粘合语较之代表更高的发展水平,曲折语则最为复杂高级,⑫Schlegel, 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 S. 49ff.像梵语这样的曲折语是有机的、有生命力的,而粘合语和孤立语是机械的。⑬Ibid., S. 41.“希腊语是腓尼基文字,包含诸多德语或波斯语, 二者是野生的印度语,中文相反是过度人造化”⑭Schlegel, Fragmente zur Poesie und Literatur Teil 1, S. 396.。这些同属印欧语系的字母文字⑮施莱格尔指出:“梵语、拉丁语、希腊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之间的完全相似性不是相互影响的结果,而是指向了共同的起源。”(Friedrich Schlegel, 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 S. 3)当时,印度语和波斯语已经被认为与大多数欧洲语言有关。“印欧语”一词是托马斯·杨(Thomas Young)于1813 年创造,弗朗茨·博普(Franz Bopp)于1816年通过对它们的文法比较研究,证明了印欧语言的共同起源。参见Hölse, “The Search for the Orient in German Idealism,” p. 434.对施莱格尔来说更易于理解和把握。他用字母文字原则审判表意文字的汉字系统,汉字体系显得随意任性,是毫无语法可言的奇怪文字。
施莱格尔主要依赖英国外交官乔治·马戛尔尼的出使,了解同时代的中国。该使团游览了当时中国最富庶、最代表中华文化的地域,其考察具有更全面的优势。①叶向阳:《西方中国形象成因的复杂性初探——以17、18 世纪英国旅华游记为例》,《国际汉学》2012 年第23 辑,郑州:大象出版社,第382 页。后经艾尼阿斯·安德森(Aeneas Anderson)编辑出版《马戛尔尼勋爵出使中国详录》(An Accurate Accout of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1795)和《1792、1793 和1794年出使中国之英国大使述》(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1795),报道了中国的人口现状、农业种植以及运河等基础建设工程。施莱格尔从这两本书中发现中国“是一部‘奇怪’的史诗(Epopöe)”②Schlegel, Fragmente zur Poesie und Literatur Teil 1, S. 331.,最早引发其对中国的兴趣。直至1828 年,他在讲座中依然引用这两本书内容。根据马戛尔尼的出使报道,施莱格尔勾勒出一幅人口众多、富饶美丽的帝国形象:“从人口方面来看,中华帝国可能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帝国”③Schl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achtzehn 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28, S. 59.,各地“遍布通航河流和运河,耸立着人口密集的城市。在这个与印度同样或者更加富饶的天空下农耕畜牧。”④Ibid., S. 60.世界上再无国家能建造、通行这种“长达120 英里的巨大帝国运河……这条运河高效航运,船帆穿行显得波澜壮阔”⑤Ibid., S. 66.。
除此之外,施莱格尔还关注德国学者K. J. H.温德施曼(Karl Joseph Hieronymus Windischmann,1775—1839)、克里斯多夫·迈内斯(Christoph Meiners,1747—1810)、语言学家朱利叶斯·海因里希·克拉普罗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1783—1835)等人⑥Klaproth, mit dem A.W. S. in Paris 1820—1821 verkehrte, in Schl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achtzehn 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28, S. 64, Note 2.的中国研究。
三、施莱格尔中国观之特点
施莱格尔在研究中国时,并未简单接受汉学家的思想,而是侧重于独立总结、研究和思考,因此其研究内容和方法颇具自身特点,借此形成的中国观与他所属的文学流派及当时德国现实密不可分。
施莱格尔认为以《易经》为基础的中国哲学使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缺乏神话性,无论是孔学还是道家理论都导致中国充满形而上的理性和机械性。尽管他对孔学有所赞扬,但认为处于中国思想统治地位的孔学导致国家封闭与实践机械化,⑦Schlegel, Fragmente zu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I, S. 137.欧洲学者过去对孔学过度赞赏、钦佩,导致认识片面性,阻碍“后人全面正确地认识孔学”⑧Schl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achtzehn 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28, S. 75.。具有理性与泛神论特点的老子学说则导致中国宗教步向泛神论。
施莱格尔的汉语研究未能跨越当时欧洲汉语主流研究的樊篱——汉语是最低级文字,“整个世界最为人造化的体系”⑨Ibid., S. 64—65.,缺乏语言美。他试图避免将语言与文化发展简单关联,在批评汉字的同时依然称赞“中国为优雅精致的民族”⑩Schlegel, 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 S. 49.,高级别的曲折语也有不足之处——失去形态结构的艺术性和优美性。⑪Ibid., S. 55—56.但施莱格尔最终评判仍然是“中国人的各种思想教育原理上,语言或文字中充斥着人造性。它超越所有规范和概念。这也恰恰从另一面证明了中国人本质上巨大的内在贫乏或精神空虚。”⑫Schl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achtzehn 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28, S. 64.由此看来,他为中国精神所谓的机械性、孤立性找出了心灵根源。
19 世纪初期,雷慕沙已经论证了汉字的优越性和精妙,赞赏中国文字和文化。①《欧洲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慕沙》,第43 页。他在1825 年发表的《论汉语的单音节语言特性》(“Considérations sur la nature monosyllabique attibuée communnément à la langue chinoise”)一文中,指出当时欧洲语言学界将汉语归为单音节语言,欠缺语法规则是对汉语粗浅的认识和偏见,并反对汉语是语言发展的低级阶段。②同上。但作为欧洲语文学家,施莱格尔更相信以字母文字为研究基础的结论,并未接受雷慕沙的观点。
总体来看,施莱格尔认为作为亚洲最有文化的文明国度,中国文化精神仅在自我领域中孤立、封闭的机械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显得被动而消极,因此缺乏世界影响力。③Schl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achtzehn 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28, S. 62.他指出中国文化及其高贵典雅的礼仪风俗“几乎更似欧洲”④Ibid., S. 63.,而非穆罕默德的东方道德,从而提出欧洲人应该重新认识亚洲的道德。他以中国长城、运河等伟大工程及四大发明为据,多次提出欧洲应该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定位中国的世界地位。“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为何不应据此要求更高的地位呢?”⑤Ibid.由此可知,施莱格尔针对当时欧洲“贬华论”提出了异议和批评。
众所周知,来华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竭力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基督教痕迹”⑥《法国经院汉学鼻祖雷慕沙的道教研究》,第105 页。。《圣经·创世记》使他们相信所有民族均同根同源——由上帝创造。施莱格尔同样深信存在这样一个流向世界各地,形成各族文化的源泉。⑦Schl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Achtzehn 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28, S. 58.他借鉴索隐法“在异质文化中也存在基督教的启示信息”⑧《法国经院汉学鼻祖雷慕沙的道教研究》,第105 页。,在中国文献中追踪上帝的神迹,论证中国文化起源西方。他指出“中国许多古老传说令人或多或少联想到摩西契约中的某些神启传说,或者想起西亚其他民族的神圣传说,尤其是来自波斯人的传说”⑨Schl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Achtzehn 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28, S. 76.。中国是“大洪水之后重建的四个不完善的君主制样本”⑩Schlegel, Fragmente zu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1820—1828), S. 257。 其余三个是印度、埃及以及巴比伦—亚述—波斯帝国。之一,从而认为中国的基本思想与“君士坦丁堡历史”有关⑪Schlegel, Fragmente zur Poesie und Literatur Teil 1, S. 332.,由此猜想中国文明根源西方。
施莱格尔研究东方文化的目的在于寻找真实的东方精神原始光辉,帮助欧洲读懂《圣经》,真正理解基督教的伟大精神。在经由哲学、语言与宗教研究中国文化精神时,他始终以天主教和欧洲传统为基础,“笼统而言,最古老的哲学亦即东方思维方式的历史就是圣经的最美妙且最富教益的外部注释”⑫Schlegel, 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 S. 198.,否定那些与其宗教和文化根源相悖的东西。他在《印度语言与智慧》中指出:“研究东方的价值和实用性在于加强圣经的权威性,因为基督教义更加接近天命之意”⑬Ibid., S. 201—203.,可见其研究最终以展现和论证基督教精神为目的。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施莱格尔兄弟为当时东方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德国唯心主义不仅受到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其普遍历史哲学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当时大量涌进欧洲的各种东方文化知识⑭Hölse, “The Search for the Orient in German Idealism,” S. 432.。施莱格尔兄弟与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关系密切,因此其东方文化研究对当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与施莱格尔同时代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亦属此列。黑格尔的论述涵盖了东方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艺术宗教及其中的哲学。但他是那个时代著名的东方批判者,不喜施莱格尔对印度哲学浪漫化的形象塑造。①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 Bd.18, in Werke in 20 Bänden, hrsg. v. Eva Moldenhauer and Karl Markus Mich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1, S. 149.
黑格尔认为以中国字符为代表的古代文字形态异常复杂,是古代思想繁琐本质的标志,因此不如字母书写系统②Hölse, “The Search for the Orient in German Idealism,” S. 441.。与康德不同,黑格尔认可中国有哲学和宗教。他主要也是参考雷慕沙的相关译作③秦家懿:《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年,第175 页。。黑格尔从辩证法的角度理解佛、老的一些概念,认为中国的道德、哲学和宗教均受制于政治,缺乏自由意识的空间。“黑格尔遵循孟德斯鸠的观点,认为专制是东方的天然属性。此观念在当时非常普遍”④Hölse, “The Search for the Orient in German Idealism,” S. 440.。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东方的专制制度与现代自由制度形成鲜明对比。⑤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Bd.14, in Gesammelte Werke, hrsg. v. Klaus Grotsch und Elisa bath Weisser-Lohmann. 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 2009, S. 172—173, S. 212—223.黑格尔借比提出世界历史四域说,东方域、希腊域、罗马域和日耳曼域。古老的东方文化构成第一个世界历史领域,是人类精神自我发展的早期,低于其他三个域,欧洲民族大迁徙之后的所有欧洲文化均包含在后者。⑥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S. 278—279.中国儒教思想统治下的家长专制制度导致人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因此被放在人类历史的第一级。⑦Ibid., S. 279, S. 212—223.东方文化是静止的、复制式的,缺乏内在发展。他在《历史哲学讲座》中写道:“即使这段历史本身,压倒性的依然是非历史性的,因为它只是重复着每一轮雄伟的衰落”⑧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Bd.12, in Werke in 20 Bänden, hrsg. v. Eva Moldenhauer und Karl Markus Mich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69–1971, S. 137.。因此他未分析中国与印度历史,便确定了世界地理和历史进程⑨Hölse, “The Search for the Orient in German Idealism,” S. 441.。作为那个时代享誉欧洲的大思想家,黑格尔的批评更加黑化了当时的中国形象。
黑格尔与施莱格尔均生长于启蒙运动精神之下,历经1789 年法国大革命,但是二人对当时欧洲现实的态度不尽相同。1648—1815 年,比起日益强大的英法等西欧国家,政治狭隘,经济落后的德国还处于“专制主义时代”,独特的德国启蒙运动对世俗领主是支持和臣服的,⑩玛丽·福布鲁克著,高旖嬉译:《剑桥德国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 年,第70 页。部分知识分子希冀国家实行“开明君主制”。尽管法国大革命激起德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但是大部分人认为国家进步应该通过改良,而不是暴力革命。在此社会背景下,施莱格尔、诺瓦利斯(Georg Philipp Friedrich Freiherr von Hardenberg,1772—1801)等早期浪漫派在政治上不反对开明君主制,在宗教方面颂扬天主教信仰,注重提升个体精神的教育力,追寻人类和谐美好的普世精神。因此他并不反感中国的专制制度和文化,接受莱布尼茨与伏尔泰的思想,严谨地研究大量汉学文献资料,探索中国文化精神。
黑格尔崇尚法国大革命所引领的自由精神,誉之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西方社会中引入真正的自由”⑪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https://de.wikipedia.org/wiki/Georg_Wilhelm_Friedrich_Hegel,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8 月12 日。。他反对专制和民族分裂,渴望德国统一,卢梭思想对其影响甚重。他认为革命中的暴力高潮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经验,基于对此经验的反思与学习,革命理想的立宪政府才能出现。他轻视东方的古老历史和专制制度,延续了康德对中国的批判态度,甚至更加激烈。黑格尔将哲学与世界历史、国际政治紧密相连,指出“世界精神”(Weltgeist)将进入新时代。⑫同上。
可以说,施莱格尔与黑格尔的观点在当时代表着两种方向:基本肯定与全面否定。17 世纪明朝灭亡带给欧洲巨大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受到欧洲学者的质疑和探究。18 世纪末19 世纪初,西欧科技快速发展,在世界范围进行海洋贸易和殖民扩张,欧洲进入全方位上升轨道。反之,清朝闭关锁国,国力走向衰落。欧人眼中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受到西欧商人,尤其马戛尔尼使团的负面宣传。18 世纪末,欧洲愈加广泛地尖锐批评中国各个方面。从黑格尔的历史四域说可以看出,欧洲眼中的新时代是争夺世界话语权的时代,建立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无论向内还是向外,都需要否定中国。
结 语
综上所述,施莱格尔的中国研究依靠当时欧洲早期汉学以及专业汉学的研究成果,从不同领域的学者手中了解他们所描述的中国,借助自身熟悉的欧亚文化,运用比较方法阐释中国文化精神,并形成总体积极且肯定的中国观,但认为中国文化精神机械孤立,缺乏世界影响力,与基督教世界有着历史上的关联。在当时的欧洲环境下,可以说属于少数“挺华派”。
施莱格尔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追本溯源,厘清东方文化的本源面貌,真正理解基督教的伟大,从东方精神中汲取力量以实现整个欧洲精神世界的复兴。这是德国耶拿浪漫派的重要精神特征之一。另外,施莱格尔等人以及汉学家们对于东方文化的传播与研究,为当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