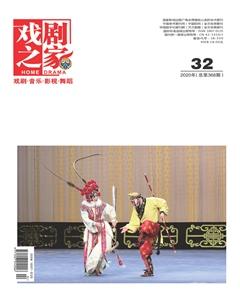浅谈歌剧《党的女儿》中田玉梅唱段的演唱技术问题
周芳
【摘 要】歌剧《党的女儿》诞生于1991年,是由剧作家阎肃、贺东久等编剧,王祖皆、张卓娅等作曲,田立为等进行舞美设计,苏陀、张海伦、汪俊导演的六幕大型民族歌剧。歌剧《党的女儿》主要描述了地下党组织革命者同国民党及叛徒之间英勇不屈、复杂激烈的斗争。该剧以田玉梅为主线,以区委书记马家辉叛变为导火索,成功塑造了一位临危不惧、坚贞不屈、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可歌可泣的女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讴歌了以田玉梅为代表的革命英雄为反抗国民党血腥统治,完成人民解放事业的不朽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品质。
【关键词】声乐形象;风格;演唱技术
中图分类号:J617.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32-0058-02
歌剧《党的女儿》中,田玉梅声乐形象集中体现在田玉梅的主要唱段中,分布在全剧的六场之中。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声乐技术处理难度与复杂性,不是探讨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声与情、意、理的结合,以及声与字、韵、律的结合的技术处理难度与复杂性。在这个范畴中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风格的基本功。作为中国歌剧演员,必须具有双重功底,即中国戏曲声乐功底和西洋歌剧声乐功底。演员进行歌剧《党的女儿》田玉梅的声乐形象的二度创作,要具备一定的梆子腔声乐和京剧声乐基本功和技巧,掌握主要的风格、特色。同时要具备一定的西洋歌剧演唱的基本功和技巧,掌握相关的常识。这是应对声乐技术处理难度与复杂性的必备基础条件。
第二,重视语言演唱在解决声乐技术问题上的地位和重要性。要树立语言与发声同是声乐载体的观念。语言演唱,不只是唱清语音词汇,还要唱出良好的语感(也是乐感的重要体现)的韵味,唱出美好的音质音色,唱出语言与声腔的完美融合。语言演唱是歌剧乃至整个声乐艺术的主要基础之一。语言演唱与声乐关系的处理,关乎歌剧的产生、歌剧的发展。在歌剧与整个声乐艺术的二度创作中,关于语言演唱技术的训练、探讨、实践是长存的,而且是常用常新的。我们要从以往的有关论著中接受启示,深化认识,以提高处理语言演唱的能力和创造性。卡奇尼·G作为十七世纪初意大利最早歌剧创作小组的重要成员,他引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前427-前347)的话:“音乐中语言第一,节奏次之,声乐居末”,并以此为理论根据,创造了单声部、数字低音伴奏以及注重歌词的“用音乐说话”的声乐作品和演唱方法。尽管在柏拉图和卡奇尼·G等人的观点中,难免有些偏颇之意,但却对他们认为的“复调音乐歪曲、遮蔽了歌词”的矫枉过正起到了作用,为歌剧的产生作了语言演唱与声乐结合的重要准备[1]。在上个世纪,苏联音乐美学家克列姆辽夫论述到“音乐与语言还有更为内在的联系”:“人声音调在形成作为表情艺术音乐的音调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决定性意义既适用于声乐,也适用于器乐(虽然程度不完全相同)。在一个民族的音乐中,自然要反映出这个民族的语言的全部音调节奏构造。而且这不仅包括旋律、和声、复调音乐,也包括乐器音色的性质。”[2]“音乐音调主要是导源于人类言语的音调,但它反过来也给后者以影响。用形象的说法是,言语使音乐成为说话的音乐,而音乐则使言语成为歌唱的言语,使它具有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音乐特质。”[3]在克列姆辽夫出版《音乐美学问题概论》一书的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剧团排演歌剧《两个女红军》,非常巧合地也提出并体现了“言语使音乐成为说话的音乐,而音乐则使言语成为歌唱的言语”这样的观念。扮演《两个女红军》主角的张越男在《学习歌剧演唱、表演札记》一文中回忆到:“1956年,我在《两个女红军》中扮演女主角顾梅英。演出后同志们反映:歌听起来不够亲切,有点洋,认为掌握和熟悉的民族音乐语汇太少;通过歌唱来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做得不够,语言缺乏形象。针对以上问题,我先从口语化入手,按照导演要求,‘说像唱,唱像说这样做的效果很好。”[4]这里所说的“说像唱,唱像说”,既是对歌剧声乐形象塑造的表现方法的基本规律深入浅出的概括,也是对歌剧声乐形象塑造的表现方法的特色表述。
第三,在解决了上述问题后,有些演唱倾向值得我们注意。1.我在觀察社会上一些歌手演唱歌剧《党的女儿》中田玉梅的唱段《万里春色满家园》时,发现有不少人过于强调了戏曲风格,歌剧风格相对弱一些。我分析缘由,主要是因为以“字”包“腔”的唱法处理问题。以“字”包“腔”也并非是戏曲声乐的基本特性,这种技术处理只可以作为一种特殊形式表现,如在说唱性的技巧中去加以运用,而不可以在自然形态下因“咬字”而“吃腔”,也不可以把“咬字吃腔”作为一种基本的声乐演唱方法。传统戏曲声乐中的“以字带声”,并不是“以字代声”,这个问题要在观念和实践上予以关注。2.社会上个别的歌手也有在演唱《万里春色满家园》时缺少风格性、缺少语感与乐感结合的韵味的情况。这种情况则主要是由于以“腔”包“字”的唱法处理问题。这种情况的产生也有观念上的问题,因为缺少西洋美声唱法的一般常识,对外国语言生疏,以为西洋美声是一种只重视发声美的声乐艺术,而不知道其是产生于“用音乐说话”的歌唱中,不知道西洋美声的美感是在欧洲各国语言美感的结合中体现出来的。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声乐、民族声乐功底不足的原因所致。以“腔”包“字”的演唱处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即便是无词歌的演唱,也是有语言母音的,更何况声乐的语音词义、语感韵味、音质音色都是语言因素所致。
第四,田玉梅唱段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经常是旋律大幅度的高翔低徊,有的地方回转幅度超过8度达到13度至17度。田玉梅唱段的技术处理难度,不只是在于高音的演唱,更是在于高音区与低音区瞬间的巧妙衔接与结合。这些问题,似乎在两百多年前徐大椿(活动年代在清朝乾隆甲子年1744年前后)所著的《乐府传声》中早有预见性的论断。如果说田玉梅声乐形象的基础塑造集中体现在第一场的唱段《血里火里又还魂》中,那么第六场的唱段《万里春色满家园》便是以对小娟子这个人物形象的嘱咐为发展行动线的咏叹,在情感上层层推进,虽然唱段长达八分零九秒,但由于有具体人物的交流指向,感情上一气呵成,不让人感到冗长,直攀人物感情的顶峰。《万里春色满家园》中,在各个段落结尾处出现了七次“主题乐句”,这些“主题乐句”与第一场《血里火里又还魂》中出现的“主题乐句”情况相仿。这种对应性出现“主题乐句”的做法,最后完成了对田玉梅声乐形象的概括。应该娴熟自如地演唱好这些“主题乐句”,把“主题乐句”与田玉梅的艺术形象完全融为一体,在观众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象。如最后结束句高音降B延续的演唱,是在表现田玉梅对未来生活的渴望、憧憬和祝福。不可以用一般美声唱高音的方法演唱,这样唱会“炸”。也不可以用戏曲声乐“嘎腔”式的方法演唱,这样唱会“噪”。而《乐府传声》中《高腔轻过》一节中对“高腔轻过”有所论述,这恰恰是《万里春色满家园》最后结束句的高音的情意深切、难以言尽之意和技术处理上对气息、声音的特殊控制、延伸所需要的。《高腔轻过》记载:“腔之高低,不系声之响与不响也。盖所谓高者,音高,非声高也。音与声大不同。用力呼字,使人远闻,谓之声高;揭起字声,使之向上,谓之音高……凡高音之响,必狭、必细、必锐、必深;低音之响,必阔、必粗、必钝、必浅。如此字要高唱,不必用力尽呼,惟将此字做狭、做细、做锐、做深,则音自高矣。”[5]在《血里火里又还魂》中,“呼天喊地唤亲人”乐句的拖腔和“哭英灵啊”乐句的拖腔;在《万里春色满家园》中,“告别了那远在天边的罗明哥”乐句的拖腔,“风风雨雨闹翻身,红米南瓜苦也甜”乐句的拖腔等,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出现了低徊于低音区的A音;二是出现了高翔于高音区的G音,高音区与低音区的衔接非常连贯。
其一,关于低音的演唱,《乐府传声》中的《低腔重煞》一节中又有精辟论述:“凡情深气盛之曲,低腔反最多,能写沉郁不舒之情,故低腔宜重、宜缓、宜沉、宜顿,与轻腔绝不相同。”[6]
其二,关于“高翔”之音与“低徊”之音两者的衔接。在歌剧《党的女儿》中不是大跳,是没有断腔的连续、婉转、曲线式的衔接。这是“坐南朝北”的音乐特色的体现。从高音十几度上的音,连续婉转地衔接到低音区的拖腔,中间没有大跳和断腔,而有曲线式的小跳回转,又有气息偷断而意不断的律动和“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情感寓于其中。这种处理方法又如《乐府传声》中的《断腔》所论及的:“南曲之唱,以连为主。北曲之唱,以断为主”,“南曲之断,与北曲迥别……盖南曲之断,乃连中之断,不以断为重,北曲未尝不连,乃断中之连,愈断则愈连,一应神情皆在断中顿出。”[7]其中,“南连”与“北断”,“南断于连之中”,“北连于断之中”等观点,都是我们可以依照作品演唱处理的需要而加以利用的。
以上举例,是对歌剧《党的女儿》中田玉梅唱段的技术处理问题的一些提示性的探讨,以引起演员对声乐基本功以及语言演唱的重视。对中国传统声乐理论进行探讨,并将美声歌唱、戏曲声乐融为一体,有利于提升对中国歌剧中的声乐形象进行二度创作的能力,以更好地、更积极能动地释放出艺术能量。
参考文献:
[1]张洪岛.欧洲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41.
[2]克列姆辽夫.音乐美学问题概论[M].音乐出版社,1959.205.
[3]克列姆辽夫.音乐美学问题概论[M].音乐出版社,1959.206.
[4]张越男.学习歌剧演唱、表演札记[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642.
[5]徐大椿.乐府传声[M].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研究班编辑出版,1962.436.
[6]徐大椿.乐府传声[M].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研究班编辑出版,1962.437.
[7]徐大椿.乐府传声[M].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研究班编辑出版,1962.433-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