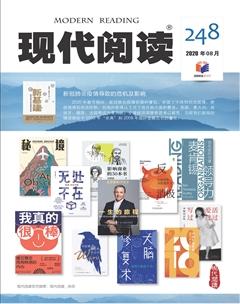从《水浒》的翻译看翻译策略中的法律问题
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是其结果……话语传递并产生权力,它加强权力但又削弱并揭露权力,使其虚弱并能够使其挫败。
《水浒》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一旦成为名著,就意味着通常要翻译成外文,让非母语的读者可以阅读。当然,翻译有时是“主动的推销”,有时是“积极的接纳”。前者说的是,母语的主体自己翻译,目的在于“推出”,用一种话讲就是“开拓进取世界”。后者说的是,非母语的主体也即“他者”翻译,目的在于“接入引入”,时常通称“引进吸收打开眼界”。现代性的展开,其方式之一,就是翻译。
翻译中有学问,而且是大學问,故现在对翻译颇多研究,遂促成一门显学成立,造就了新的学术分工,并引发了“翻译极为可能是一种话语策略”的警惕。人们开始思索,翻译是否隐含着话语权力的运作。《水浒》的翻译,历经数次,其本身的故事,翻新不断,其中似乎就有“策略”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国际友人,叫沙博理。此人居住中国多年,十分精通汉语,又特别喜好《水浒》。当时篡政的“四人帮”力邀沙博理用英文翻译《水浒》,以便“推销”,送及海外。沙博理勉强答应下来。翻译完成之际,沙博理将译稿交给“四人帮”,算是交差。可“四人帮”初读英文译本书名,立即表示了不满。英文书名是Heroes of the Marsh。“四人帮”说,宋江被帝王招安了,他是叛徒,而且跟随他的相当一部分梁山泊人物,没有“阶级觉悟”,同样是叛徒。既然是一群叛徒, 怎么能用heroes(英雄)这个词?所以,这里的翻译之误是根本性的,有关立场。“四人帮”有想法,他们觉得,既然是“开拓世界”式的“推出”,就要有意识地通过翻译策略引导非母语的读者,让他们看出历史中人物的真正问题,特别是历史中人物和当代人物之间的隐喻关系,以明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某些人物的“深层一面”。“四人帮”说,应该用与中文里的“歹徒”一词相对应的英文词,而且要求沙博理一定要准确找到这个英文词。“四人帮”指出,梁山泊人物,开始时是“造反”,可后来是叛徒,两相连贯,就有了比叛徒还要恶劣的情节,于是非用“歹徒”一词就不能揭发其实质。沙博理这时发现,“四人帮”对翻译有点在行,接着答应找词。最后,英文书名成为Outlaws of the Marsh。outlaws的确有中文“歹徒”的意思,而且,主要是这个意思。“四人帮”读后,觉得“爽”,遂宣布翻译“大功告成”。然而,沙博理暗自偷笑,而且在“四人帮”垮台之后,还不无得意地说,outlaws还有中文“好汉”的意思,通过全书的翻译,英文读者一定相信,书名在指“好汉”!沙博理似乎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用outlaws的双重隐意来暗中进行话语抵抗运动。他同情那些“四人帮”不喜欢的人物。
在《水浒》翻译过程中的这个“版本”故事,非常鲜明地表现了翻译的意识形态策略的斗争。
现在转入法律问题。在梁山泊的特定语境中,不论heroes,还是outlaws,都针对的是法律制度。不同意思的语词使用,表现了对特定人物或者特定法律制度的不同立场。尽管,英文里outlaws也有“好汉”的意思——和“英雄”的意思有了点滴相通的地方。但颇为重要的是,“英雄”所对应的“反抗”,表达的是对一类制度的否定;而“歹徒”所对应的“违反”则相反,表达了对一类制度的肯定。
在法学里,一个问题始终暗中作祟:为什么在某些语境中,人们总是中性地看待法律?比如,在前面的语词使用中,无论“英雄”还是“歹徒”,无论“反抗”还是“违反”,都没有否定法律本身的资格;而在某些语境中,人们却仅仅正面地、怀有偏激道德立场地看待法律,比如,我们的语言表达习惯中总有“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法,平之如水”……
当然可以认为,这是法学里常说的实证主义话语和自然法学话语的“争论”现象。实证主义从来都说“法律的存在是一码事,法律的好坏则是另一码事”,因而,在《水浒》的翻译中,“英雄”“反抗”也好,“歹徒”“违反”也好,同时都是对法律资格的认定,但却可以表现出对法律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自然法学,尤其是极端的自然法学理论,则是相反,认为“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好坏从来都是一码事”,所以,在“英雄”和“反抗”的语词使用过程中,法律表面上看是存在的,实际上则并不存在。否则,英雄就可以反抗“正义的” “智慧的”“平之如水”的法律了,这会违反了一些重要的语言游戏规则。
但是,传统的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的“笔墨官司”已经过时。因为语言的使用从来都是应景式的,更为打紧的是,语言的使用者,从来都是从自我理解的角度去看自己的语言使用,并不喜欢跳出“自己的立场”,尤其针对法律这样的社会建制问题。进而,语言游戏规则也变得是多重的、复杂的,构成了多维曲扭演化的空间。而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话语,都在从“他者的立场”来讨论问题。这种立场相信,法学知识的寻觅也是知识中立追求的一种。两种话语的这种“他者”潜意识,决定了其不可逃避的“过时”。不论实证主义认为自己怎样有道理,认为自己对法律制度的建设怎样大有裨益,不论自然法学认为自己多么“讲正气”,对法律制度的建设多么立意高远,生活在现实中的个体,还会采取自己的语言行动策略,标明观点,进行“斗争”,自我伸张,从事征服,进而构筑“法律想象”的一个方面。这就是“过时”的意思。
因此,暗中作祟的法学问题,不是“他者”可以争论清楚、论证清楚的问题。这个“暗中作祟”,是持续的、生长的,是和作为个体的我们每个人眼睛中的鲜活法律场景持续相互作用的,并在相互作用之中,凸显个体的利益、嗜好和立场。如果将法律游戏看作语言游戏的一种,那么,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断言是不能忽略的:语言游戏是生活,生活是语言游戏,而语言游戏是有规则的,尽管规则在变化。
可是,个体化的法律话语实践,因其是从自我立场出发的,或者说是从“内在实践立场”出发的,所以,法律游戏规则的变化,是由自我个体的争斗加以催发的。“自我”确定着立场,谋划着策略,设计着方式,运用着权力,从而在一种法律游戏规则中不断注入新鲜元素,也即导致演化可能出现的新诱因;“自我”总是将自己的意志及热情,诉诸战场。而一种法律游戏规则和自我介入的相互关系,是无法确定的,是无法知识化的,尽管可以小作描述。于是,法学知识的努力总是面对了无法知识化的部分对象。
这就是在一个《水浒》翻译的故事版本中可以发现的问题。
在“四人帮”“想象”着梁山泊时代的法律的同时,沙博理也在“想象”着,尽管他们都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也会“想象”。只要在生活中有着争斗,比如,像“四人帮”那样有着力图含沙射影的攻击意图,像沙博理那样有着春秋笔法方式的迂回抵制思虑,人们就会不断地“想象”法律,“砌筑”法律,不论这个法律是什么时代的,并且,为其击鼓,为其呐喊,为其披挂,为其上阵。人们不仅要争论究竟是用“英雄”“歹徒”“好汉”还是“反抗”“抵制”等语词去阐述《水浒》的故事,以及其中的翻译,而且要争论究竟是否用其他语词去阐述去翻译,从而准备设置不同的法律气氛,制造不同版本的法律故事,包括不同版本的翻译故事,使法律游戏规则变得“既在此时又不在此时”,十分辩证。
当然,我们可以自我约束地做个“旅行者”,克己复“法”,走马观花,不卷入上面所说的一切,去客观地描述法律现象,生产普适的法律知识,指出“四人帮”和沙博理都是不客观的。但是,就是我们自己,恐怕都没有办法可以不生活在特定的法律制度中。毕竟,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无法自拔头发从而脱离地面的“法律地球村庄”中。
如果无法成为法律知识的“旅行者”,那么,就必定是法律知识的“角斗士”——而且是在使用文字的每一刻,包括笔者写下上述文字的这一刻。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法律的隐喻(增订版)》 作者: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