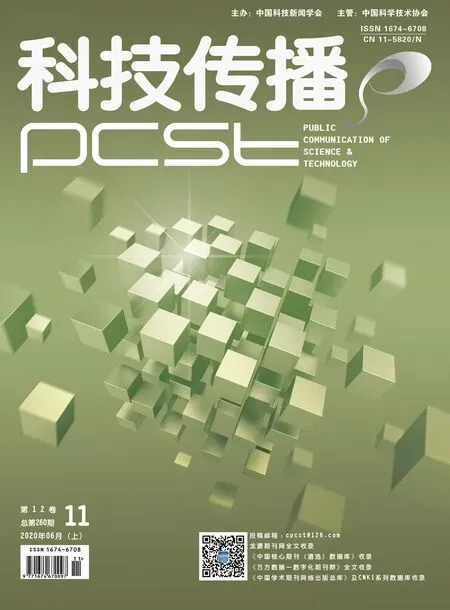社交媒体数字劳动的特点与动因分析
智 慧
社交媒体的崛起与不断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现象与新改变,传统物质劳工的形式变化便是其中之一。社交媒体场域“数字劳动”的现象比比皆是,产消表现出合一的趋势。与传统物质劳动相比,数字劳动呈现出非物质性,隐蔽性,有偿与无偿共存等诸多特点。同时劳动者的劳动动机兼具自愿性与非自愿性,这些特征更是给数字劳动及其背后的数字资本主义剥削披上了暧昧模糊的面纱。本文将结合政治经济学派中的受众劳动论,从受众心理分析的角度来分析互联网数字劳动的驱动因素。
1 受众研究中的数字劳动
有关数字劳工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免费数字劳动与价值产出的关系①。从受众研究的角度有助于解释价值产出的相关问题,而受众心理驱动因素的研究还需要借助受众研究相关的理论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将“积极受众”的生产性放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受众主体地位提高,更加具有发言权与发表权,是意义的真实制造者②。所以文章首先对政治经济学派中的“受众劳动论”的正当性进行简单的梳理。
斯麦兹曾提出受众商品论,认为商业媒介生产的新闻娱乐节目,从深层意义上来看是为了换取观众的注意力,再把这些注意力出售给广告主。因此受众的视听成了真正被出售的商品,而全部的商业媒介就建立在这种对受众剩余价值的剥削上。大众传媒时代传统定义上的受众,以及Web2.0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用户都需要在媒介环境中找到容身之处,因而运用主观能动性与数字生产能力来创造内容、价值与意义。“受众劳动论”最根本的关注点是受众地位的问题,“受众劳动是否参与价值生产”是评判“受众劳动论”合理性的重要因素②。
2 数字劳动的特征
2.1 隐蔽性
数字劳动的形式较为隐蔽:没有特定的工作场所,没有监工,没有鲜明的劳动表现:受众只要打开手机和电脑,浏览、点赞、评论、发文……注意力和创造性劳作被投入其中,而数字劳动以及价值的产生,其实是在资本的劳动组织之外的,我们很难见到某种显在的工厂或是监工进行明确的组织。除了劳动本身的隐蔽性,数字劳动的剥削也具有隐蔽性,互联网大场域的构建,入场本身就需要用户让渡一部分的权利,获得“通行证”,用户进入虚拟社交的世界,交换价值把受众诱入其中,而数字化生活中又需要遵循着资本和技术的逻辑,社交平台营造的媒介环境成为人们日常社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③。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的,人们迈入“数字化生存”的时代,虚拟数字世界里生存的需要也让背后资本隐蔽的剥削蒙上面纱。
2.2 劳动时间与空间模糊化
新媒体和社交场所的出现,使得时间呈现碎片化的趋势,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方式。卡斯特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流动的空间”:“在更深的层次上,社会、空间与时间的物质基础正在转化,并环绕着流动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而组织起 来。”④时间变成了“无时间的时间”,人们对于互联网空间中的时空感受能力降低,数字劳工的工作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无需打卡计时付薪,工作与娱乐、休闲与创造的界限模糊。正如意大利自治学者提出的社会工厂:原先固定的实体场所变得社会化,尤其在互联网的场景下无所不在,这种社会工厂成了虚拟的网络,越来越多的“新作坊”开张了,图片、音乐、视频、游戏、新闻甚至是观念都成了劳动的新形式。
2.3 自愿与非自愿并行
在社交媒体上存在必然性劳动和或然性劳动,比如对于自媒体生产者们,做视频出内容是必然,这种必然性劳动由于限制了较为固定的产出时间和周期,如周更或日更,因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非自愿性;而对于广泛的互联网受众来说,做的更多的是类似偶然点赞转发评论,间接性产出内容等的或然性劳动,这类或然性劳动很多时候是带着受众一定的意愿和无意识的自发性,甚至于“乐在其中”,受众出于一时的兴趣和需要,借助社交媒体平台自愿进行发声和交流。
2.4 有偿与无偿共存
社交媒体场域中的部分数字劳动是有偿的,比如付费内容的生产,有些类似B站的MCN平台也会提供一定的创作激励,但是这类报酬几乎微乎其微。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场域中,人类传统的劳动形式受数字劳动影响而趋于崩解,这与马克思论述的异化劳动一样,数字劳动本质上也是一种异化的无偿劳动,暗含剥削、不平等和不正义⑤。由于劳动的娱乐性质,受众往往难以察觉自己被剥削的本质,也更难想到自己的劳动应该获得一定的报酬。
3 社交媒体数字劳工的驱动因素
3.1 “新情景”中的使用与满足
卡茨在《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一书中提出,受众个体对于媒介本身及其内容抱有某些期望,因此会基于目的性来选择不同的媒体及内容以满足其需求,这一理论被称为使用与满足理论。互联网的出现使得该理论得到加强,受众从接触媒介过渡至学会使用甚至是控制媒介,更清楚如何进行“产消”。同时社交媒体的互动性使得受众从产生需求到需求被满足间经历的线性的媒介接触过程升级为从信息到传播者,再到传播媒介,再到受众,到媒体最终回归至传播者的链环式过程。用户看似拥有选择的自主权权,实际上在“社交孤立”的胁迫下,不得不通过使用特定的媒介来满足融入群体、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的需求⑥。
社交媒体平台的聚合能力以及圈层分众的特性演化出无数新情境,根据梅罗维茨媒介情境论的观点,媒介形式的转变会创造出新的信息系统,新的情境也就相应而生。人们对于每一种情境的适应都离不开相对明确的界限。所以不同情境的区分界限一旦混淆,就会产生新的情境。新的情境要求人们采取新的行为。此外,互联网正在促成许多旧情境的变化和整合,同时造就出众多新情境,受众踏入不同的情境,也相应追寻不同满足需要;获取信息、交流交友、展现自我、获取尊重和认同、娱乐消遣等等,不同情境的转换促使受众变换媒介的使用方式以满足自身的需求。
3.2 数字生存中连接的需要
尼葛洛庞帝认为对于互联网来说,“永远在线”极为重要⑦。无线通信技术模糊了公私领域的界限,数字社会中沟通的核心不再单单是以算法为代表的信息,而更多是象征人情的智能。所以数字化生存中人们不再满足于获取信息,而是更渴望在网络中获取“连接”。连接是其他所有东西的前提条件。在相互连接的世界里,物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与历史上相比越来越微弱,“原子思维”正在被抛弃。
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具有渴望连接的本能,社交媒体的存在就吸引着人们置身其中。只有进入社交平台的虚拟世界并且获取连接,数字化时代虚拟生活的基本条件才能被满足。因此受众需服从社交媒体场域的潜规则,才能获得社交网络生存的准入资格。如知乎或者豆瓣上很多优质的帖子,字数多,排版精美,图文并茂,制作者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为了获取某种实在的报酬,而是在贴在发出之后,能够收获大量网友的点评、赞赏、讨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更为深层持久的驱动因素。
3.3 “阴影原型”的释放
社交媒体场域中,快节奏和强压力的生活环境下,焦虑型、鸡汤或是反鸡汤类内容很容易汇集受众。反观数字劳动中的内容类型,很大一部分内容和价值产出离不开焦虑话题,包括工作收入、阶级、两性关系上的焦虑、攀比,越和人性深处偏“暗面”的部分相关的,也正是这类话题刺激着数字劳工们乐此不疲地进行产出,随之而来的交流活动也格外激烈。
借助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派理论中“阴影原型”的理论框架可以发现,这些创造力的源泉,从个体自身来说,就是阴影原型的释放。荣格认为,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源泉是“攻击力”,这种偏负面的特质是我们潜意识中最隐蔽和奥秘的存在,人类也因此形成不道德感、攻击性和易冲动的趋向⑧。只有在自我与阴影两者间协调和谐时,也就是阴影释放后,人性才会重新充满生命的活力。而充满创造力的人往往是充满“动物性”的,这种动物性阴影的顽强和韧性,会推动人寻找,并且进入到更令人满意、更富创造力的活动中去。社交媒体的出现正式迎合了这种心理上的隐蔽渴望,人性中隐藏的嫉妒、渴望、攀比、怨恨、愤怒在互联网海洋中找到了宣泄的场所,受众一方面借助社交媒体发泄阴影,一方面以一种具有创造力和价值力的形式释放阴影背后的生命力,这是互联网数字劳动驱动因素中更为隐秘的一种。
通过对社交媒体场域中数字劳动特点对分析,我们能够更好了解资本背后隐密对一种劳动形式,在受众主体地位提升的社交媒体时代,了解受众发起数字劳动的驱动因素,能够更全方位理解数字劳动的形成与运作。
注释
①Wittel A .Digital labor: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J].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ociety,2014,17(7):144-145.
②蔡润芳.“积极受众”的价值生产——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观”与Web2.0“受众劳动论”之争[J].国际新闻界,2018,40(3):114-131.
③李璟,从“数字劳工”分析Facebook受众策略与效果.青年记者,2018(36):97-98.
④(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40.
⑤张雯,数字资本主义的数据劳动及其正义重构.学术论坛,2019,42(3):106-111.
⑥徐晶洁,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媒介用户的数字劳动解读——以知乎网为例.视听,2019(10):13-14.
⑦(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著;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1.
⑧(瑞士)荣格著.心理类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3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