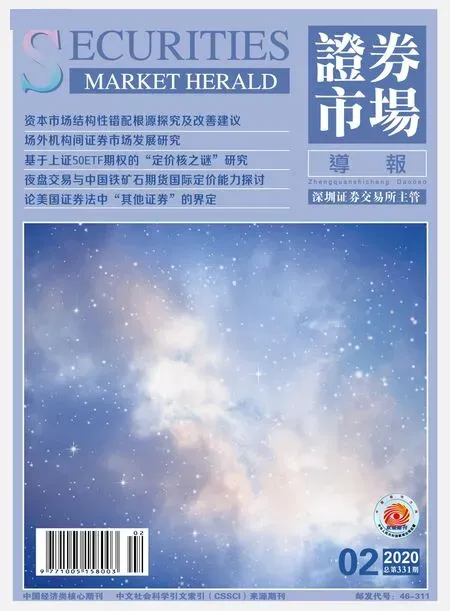论美国证券法中“其他证券”的界定
——规则演变及相互关系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一、逻辑起点:为后续研究提供智识基础
在我国,“证券”是一个逐渐为立法所扩张的概念。1998年《证券法》只规定了股票、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三类证券,同时将“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作为兜底性规定;2005年《证券法》将“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和“证券衍生品种”纳入其中,这是我国《证券法》在实质意义上对证券概念的首次扩容;2014年《证券法》沿用了2005年《证券法》对证券概念的界定;2019年《证券法》将“存托凭证”纳入证券的范围,这是我国《证券法》在实质意义上对证券概念的再次扩容。从立法技术上说,我国《证券法》对证券概念的界定采用的是“一般列举”加“兜底认定”的方式,“兜底认定”的主要功能在于弥补“一般列举”的不周延,增强证券概念的张力,以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只不过,在我国证券法发展史上,“兜底认定”方式一直没有发挥作用,因为时至今日,国务院并没有认定过其他证券。所以,增强证券概念张力的重任就落在“一般列举”方式的身上了。
与此同时,金融学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大概有三种,即银行导向型的结构、市场导向型的结构和金融证券化的结构。三种类型在促进金融创新方面的作用是依次增强的。我国的金融结构正处于由银行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的结构转变过程中,未来我国金融结构还会进一步向金融证券化的结构演进。1与我国金融结构逐步变迁相适应的是,我国证券的范围也会逐渐扩大。这意味着,我国证券法对证券概念的界定应该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我国金融创新的需要和金融结构变迁的趋势。但是,“一般列举”的有限性、程序性与证券范围扩张的无限性、灵活性之间具有天然矛盾,仅通过“一般列举”方式扩张证券的概念可能扭曲金融市场结构的需求与直接融资制度供给之间的关系。一旦直接融资制度供给跟不上,很多证券类的直接融资活动将会被排挤到现行的间接融资活动的规制体系中。2这也是我国非法集资犯罪“口袋化”现象严重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3, 这样的制度设计反过来又会与金融创新和金融结构变迁形成抵牾。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学者建议我国应该借鉴“美国证券法上定义证券的方式”,使用证券监管的方式来规制直接融资类的集资活动。4
所谓美国证券法上定义证券的方式,实际上也是“一般列举”加“兜底认定”。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部分第2(a)(1)节详尽规定了“证券”的种类。5在该定义中,金融票证(note)和投资合同(investment contract)的认定承担了“兜底认定”功能,除此之外的证券都属于“一般列举”的范畴。美国证券法中的金融票证和投资合同,在功能意义上相当于是我国《证券法》规定的“其他证券”。所以,学习“美国证券法上定义证券的方式”,关键在于借鉴美国证券法上证券概念的“兜底认定”方式,即认定金融票证和投资合同所确立的判例法规则,以充实我国《证券法》中“其他证券”的认定规则,使“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之规定落到实处,进而激活我国《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涵盖力和解释力。
对于是否应该应学习和借鉴美国证券“兜底认定”的判例法规则,我国学者持不同观点。赞成观点的立论出发点在于促进金融创新,即“中国《证券法》的证券概念主要以股票、债券为原型,其适用范围显然不足以应对金融创新的新发展。”6对于扩大证券概念的具体路径,又大致形成了两种思路:一种是“借鉴韩日两国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的经验”,用“以金钱出资形成集合性资产”“由资产管理人开展事业”和“将所获收益向参与人进行分配”这三个要件来定义“集合投资计划”,“最大限度地把几乎所有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和投资服务纳入(证券法的)适用对象(范围)”。7另一种是借鉴美国判例法所确定的Howey规则,将“投资合同”作为证券的一种新类型,即“证券是指具有投资性、风险性及可转让性的标准化权利凭证或投资合同”。8不过,“集合投资计划”明显是受美国Howey规则的影响而发展出来的概念,9所以扩大证券概念的具体路径实际上就是将美国证券法中的“投资合同”移植到我国。
反对观点的立论出发点在于Howey规则所确立的“投资合同”概念不具有可移植性。具体来说,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模式、习惯和法治水平来看,我国证券定义的规范依据比较模糊,在没有理清规范依据之前,盲目地在《证券法》中扩大证券的概念,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规范、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性问题;从我国证券的扩张历史来看,其呈现出条块分割和条条分割的零散化、偶发性特征,这种复杂的扩张路径、方式与概念,很难被一个“投资合同”的概念给统合起来;从我国证券定义的功能来看,“定义证券的作用首先在于为企业提供明确、合法的融资途径和手段,以免企业落入非法集资罪等刑事罪名中,而不是从兜底性全面监管的立场出发加以界定”。10有鉴于此,我国目前不能盲目地将美国的“投资合同”概念纳入到我国的证券定义之中。
毫无疑问,赞成和反对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不过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是赞成或反对我国在《证券法》中引入“投资合同”的概念,而在于对投资合同的概念、判例法规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金融票证”的概念、判例法规则等进行系统梳理,以摸清美国证券法中投资合同、金融票证的概念和认定在事实上的原貌,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证券概念的界定或者充实我国国务院依法认定其他证券的规则内涵等议题提供智识基础。
二、“投资合同”的认定规则:Howey规则之简析
(一)Howey规则的由来
判定投资合同是否属于证券的主要方法是194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Howey案中确立的Howey规则(Howey test)。11本案的争议是担保地契(warranty deed)是否构成了证券法项下的投资合同。弗兰克·墨菲(Frank Murphy)大法官认为,被告所提供的绝非是绝对的地产权利益(fee simple interests),它所提供的是给那些身处远方且没有种植、收割、销售工具和专业技能的人一个投资大型水果企业的投资创业和利润分享的机会。12进而,墨菲大法官提出了著名的Howey规则:确定所争议的担保地契是否属于证券的方法是看“在所争议的计划中,投资者投资于共同利益体(common enterprise)的金钱所带来的利润是否是完全(solely)来自筹资人或第三人的努力”。13根据学界通说,Howey规则有四个构成要件:(1)包含金钱投资的计划;(2)共同利益体;(3)获利期望;(4)利润完全来自他人的努力。14
(二) Howey规则的主要争议点
学界、实务界在对这四个构成要件进行解释时,争议主要出现在第四个构成要件的内部。具体包括如下内容:
1.对“完全地”的解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Howey案中,没有对要件四中的“完全地”该作何理解做出明确说明。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对Howey规则第四个要件中的“完全地”的理解产生了分歧。该分歧的本质是对“完全地”的理解是应该坚持文义解释还是目的解释。按照文义解释,投资者所获利润必须完全地、绝对地来自他人的努力,只要投资者在获利中付出了一点点努力,那么投资者所获利润就不是完全地来自他人的努力。在Turner案中,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如果严格坚持文义解释,那么极有可能引发筹资人规避证券法监管的情况。因为投资者一丁点的参与行为,都可能规避Howey规则的适用,进而也就将筹资人的行为排除在证券法的监管范围之外。15为实现证券法对投资者的保护,避免筹资人规避监管,法院发展出了目的解释。在Koscot Interplanetary一案中,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认为,按照目的解释,要件四并不绝对禁止投资者在经营共同利益体中所付出的努力,只要筹资人对与获利有关的重要管理行为有着“密切控制”(immediate control),投资者的那些在功能上不决定是否产生收益、产生多少收益等事项的努力就可以被忽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所获利润仍然是完全地来自他人的努力。16从规则效力方面来说,由于美国联邦第五巡回法院所做的判决,只对第五巡回法院自身和由其所辖的联邦地区法院具有约束力,所以对“完全地”的理解到底是采用文义解释的方法还是采用目的解释的方法,仍然存在多种解释的空间。
2.对“筹资人或第三人”援引的改变
很多案例在援引Howey规则的过程中,将“来自筹资人或第三人的努力”改为“来自他人的努力”。17“筹资人或第三人”的内涵与外延是否与“他人”相同,值得进一步探讨。从美国证券法的立法目的来看,应该将“筹资人或第三人”与“他人”相等同,二者的共同本质就是这种努力是来自于投资者以外的其他主体。不过在“来自筹资人或第三人的努力”的表述中,法院似乎更加强调这种努力是来自“筹资人”的,“第三人的努力”应当是一个兜底性或补充性的主体,其主要功能在于弥补“筹资人”外延的不足。“来自他人的努力”则将“筹资人”和“第三人”等同起来,不区分主次。这在语义上意味着,“第三人”的地位被提升至与“筹资人”等同的地位了。但是,从规则的明确性角度来说,宜采用Howey规则的提法,因为“筹资人或第三人”与“他人”的表述更为明确具体。如果采用“他人”这一称谓,法院在进行司法裁判时,仍然要将“他人”进一步细分为“筹资人”和“第三人”这两部分。与其这样麻烦,还不如直接采用“筹资人或第三人”的称谓。
3.对“筹资人”与“第三人”关系的解释
“筹资人”和“第三人”之间是否需要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在实践中也曾引发过争论。在Continental Marketing Corp.(CMC) v.SEC一案中,CMC认为根据Howey规则,向投资者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主体都是筹资人,而它充其量是个与筹资者没有直接控制关系的第三人,所以它的行为不构成被证券法所监管的行为。CMC主张,它在本案中是以海狸养殖业代理人的身份出现,与投资者签订海狸买卖合同,其主要工作内容是向投资者销售、运送海狸,它不是海狸的实际养殖人,它与海狸养殖人属于不同主体,也不存在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所以,这一买卖合同不属于证券法项下的投资合同,进而该海狸买卖活动不受证券法规制。但是美国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认为,筹资人与其他主体(比如筹资人的代理人)之间的控制关系不是关键,关键是看这些主体在作为整体的海狸行业中所起的作用,很显然CMC公司在促成整个海狸交易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该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签订的海狸买卖合同属于证券法所规定的投资合同,CMC就是证券的发行人,应当履行证券法所规定的义务。18本案的另一层含义是说,Howey规则中的“来自他人的努力”既可以是“筹资人的努力”,也可以是“第三人的努力”,而且筹资人和第三人之间有没有控制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三人本身在整个筹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法院的这种解释,大大扩展了Howey规则的适用范围,这有利于保护投资者,不过这也意味着加重了筹资者或者其他参与人的合规负担。
(三)小结
Howey规则的一大特点是,只有四要件同时被满足之后,才能将所争议的投资设计认定为投资合同。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件,都将使所争议的投资工具或设计被排除在证券概念之外。正如前文所述,是否将某一争议的投资工具或设计认定为证券将对相关义务人和投资者的权益产生巨大影响,所以相关义务人和投资者将围绕着Howey规则四要件的解释展开激烈博弈。至于司法机关和监管部门如何解释这四个要件,需要根据具体情形进行分析。
Howey规则的一个重大意义是极大地避免了经济领域中的集资活动轻易地滑入刑事犯罪领域,在客观上抑制了集资类刑事法律适用范围的扩张,为创新型集资活动争取了空间。在美国,集资类活动主要受两大类法律制度规制:一是以Howey规则为中心的证券法体系;二是诈骗等侵犯财产的刑事法体系。所有的集资活动先经过Howey规则这第一道网过滤一遍以后,被滤出来的严重侵犯财产的集资行为将受刑事法规制。绝大部分的集资活动,基本上都可以被纳入到证券法这道网中进行规制,进入刑事法规则范畴的集资行为相对较少。19而证券法规制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督促集资主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相关信息。其基本逻辑是,只要集资主体按要求披露信息了,如果其中有诈骗,那么投资者肯定能够识别骗局,进而也就没有人进行投资,集资活动最终也就会消亡;如果投资者开始没有发现其中有诈骗,那么投资者就可以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b)部分的规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的10b-5规则提起集体诉讼,进行事后追责。20这是一种对集资活动进行市场化规制的思路,它不仅会逼迫集资行为人放弃诈骗,尽可能探索可行的商业模式,而且还限制了刑事法律适用的扩张可能性,真正地做到了为创新留空间。
三、“金融票证”的认定规则:Reves规则之简析
(一) Reves规则的由来
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1976年在Touche Rose一案中最早对金融票证的认定做了尝试。在Touche Rose案中,法院对《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证券”定义条款中的“根据具体情况所作的他种规定(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进行文义解释时,认为这里所说的“他种规定”属于证券概念的例外规定,即只要当事人能够证明所争议的投资工具属于“他种规定”,那么所争议的投资工具就不属于证券;进而,当事人也就不受证券法律规制,不用承担证券法项下的责任。但是,法院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判定“他种规定”的标准,而是列出了六种属于“他种规定”的金融票证。这六种金融票证是:(1)在消费融资中交付的票证;(2)由房屋按揭担保的票证;(3)被小额公司留置权或其资产担保的短期票证;(4)为银行消费者提供信用贷款证明的票证;(5)被应收账款转让所担保的短期票证;(6)仅仅因在正常业务范围内产生的公开账户债务而形成的票证。法院将这六种金融票证看成是一个家族(笔者称之为“家族票证”),首次提出了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概念。211984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Arthur Andersen一案中进一步完善了家族相似性规则,并将“为服务于经常性营业的商业银行贷款提供证明的票证”新列入到家族票证中去。22199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Reves案中采用了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1976年提出的家族相似性概念,并沿用了该法院在1976年和1984年所归纳出的七种家族票证。在前述司法裁判经验的基础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美国证券法史上另一个里程碑式规则——Reves规则。23
(二) Reves规则的真义
辨明Reves规则真义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厘清Reves规则和家族相似性规则的逻辑关系。关于此点,具体分析如下:
1.Reves规则的内涵
(1)假设所有票证都是证券,但这一假设可以被推翻;
(2)如果要推翻前述假设,当事人就要证明所争议的票证与家族票证有着强相似性,此时所争议的票证就属于家族票证,进而也就不是证券;反之,要么被认定为证券,要么进行下一步判定;
(3)如果所争议的票证与家族票证没有足够的相似性时,法院就判定所争议的票证是否应该被新列入家族票证;如果被新列入家族票证,那所争议票证就不是证券;反之,则为证券;
(4)判定前述(2)中所争议的票证与家族票证是否有相似性和判定前述(3)中所争议的票证是否应被新列入家族票证的方法相同,即下文所说的家族相似性规则。
2.家族相似性规则的内涵
家族相似性规则主要包含四方面的考量因素:
(1)买卖双方的动机。如果卖方的动机是为企业经营筹集资金或者为大笔投资融资,并且买方的主要动机是营利,那么此时的票证很可能是证券。换句话说,如果卖方的动机是为营业而融资,买方的动机是为盈利而投资,那么承载前述目的的票证很可能就是证券;如果票证的作用是促进小额资产、消费性商品的购买与销售,解决出卖人的现金流问题,或者实现其他商业性或消费性目的,那么此时的票证很可能不是证券。
(2)分配计划。这一点主要是看否存在一个针对票证的共同交易(common trading),不管这个交易是为了投资还是为了投机。24所谓的共同交易是指发生在公共交易场所的交易或者向广大社会成员发出要约、销售投资工具的交易。25
(3)投资者的合理预期。如果投资者的合理期待是认为票证属于证券,那票证就属于证券。
(4)是否存在其他风险防范或救济措施。若存在其他大幅减轻票证风险的监管措施,那就没有必要将票证认定为证券;如果不存在风险防控措施,则需要考虑将票证定性为证券。26
(三)小结
在实践中,有观点说判定金融票证是否属于证券时应该采用Reves规则,也有观点则说应采用家族相似性规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混乱,使外界搞不清楚Reves规则与家族相似性规则之间的关系。通过前述分析可知,Reves规则和家族相似规则的关系如下:Reves规则共包含四个要件,家族相似性规则是Reves规则中第(2)和第(3)两个要件的适用方法,所以家族相似性规则是Reves规则的一部分。为避免引起混乱,我们在实践中宜采用“Reves规则是解决金融票证是否属于证券”的说法。
此外,Reves规则所列的家族票证范围是开放的。在Reves案之后,1992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Banco案中又将“短期贷款参与计划”和“为商业银行自身的客户之经常性营业而提供的商业银行贷款出具证明的票证”纳入到家族票证中。27至此,家族票证的家族囊括了至少九个成员:(1)在消费融资中交付的票证;(2)由房屋按揭担保的票证;(3)被小额公司留置权或其资产担保的短期票证;(4)为银行消费者提供信用贷款证明的票证;(5)被应收账款转让所担保的短期票证;(6)仅仅因在正常业务范围内产生的公开账户债务而形成的票证;(7)为服务于经常性营业的商业银行贷款提供证明的票证;(8)短期贷款参与计划;(9)为商业银行自身的客户之经常性营业而提供的商业银行贷款出具证明的票证。从理论上说,在金融创新大潮中,家族票证的成员仍然会不断增多。这种开放性的范围也更加说明了美国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开放性,进而更能够满足多变的现实需要。
四、Howey规则与Reves规则的关系
(一)理论解剖
在Reves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利用Howey规则来判定一个票证是否属于证券的方法不可取,因为与投资合同项下的投资工具相比,金融票证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投资工具,自然应该采用不同的认定方法。如果直接用Howey规则来判定票证是否属于证券,那立法者就没有必要将投资合同与金融票证并列写在《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了。28基于这一判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Howey规则和Reves规则是两个独立的、并行的证券认定规则。
然而,学术界却提出了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家族相似性规则是Reves规则的核心,而家族相似性规则又与Howey规则没有本质区别,进而Reves规则和Howey规则没有本质区别。家族相似性规则与Howey规则的核心内容都可以被总结为以下四点:(1)在交易中必须存在投资动机或投机动机;(2)此种投资工具必须被大规模营销或者大范围交易;(3)在符合情理的情况下,投资大众认为此种投资工具是证券,并对投资收益有合理期待;(4)是否存在大幅降低投资损失风险的替代性监管框架(学者认为,这一要求是暗含在Howey规则中的29)。至于Howey规则中“完全来自他人的努力”的要件则又暗含在所有的票证交易中,这也就是说Howey规则与家族相似性规则在构成要件上是完全重合的,家族相似性规则只不过是对Howey规则的简单重复。30进而,家族相似性规则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家族相似性规则是Reves规则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Reves规则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实践中也存在利用Howey规则将票证判定为证券的先例31,这说明Howey标准能够满足实践的需要。
客观地说,Reves规则的确与Howey规则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Howey规则和Reves规则能够同时被运用于相同的案件中去。但是笔者认为,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Reves规则的独立价值。因为Howey规则和Reves规则也存在着很多不同:
(1)Howey规则和Reves规则都注重对投资者获利动机的强调,但Howey规则并不强调筹资人的主观状态,而Reves规则则强调筹资人的主观状态必须是为了筹资。从这个角度说,Reves规则的启动门槛要高于Howey规则,即可能存在的一种情况是:不被Reves规则认定为“证券”的交易设计很可能会被Howey规则认定为“证券”。
(2)因为家族票证的存在,Reves规则变得更加具体,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也更强。Howey规则相对抽象,而且围绕着各个要件的争议很多,到底应该对所争议的要件内容做何种理解存在不确定性,进而使得裁判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3)从功能意义上看,Howey规则是从正面规定什么是证券,而Reves规则则是从反面规定什么不是证券。两者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美国证券法中“其他证券”判定方法的逻辑闭环,使得证券法调整的对象变得更加精确,进而也就减小了法律适用错误的可能性。
(4)Howey规则具有固定的构成要件,它的启动需要这些要件同时成就,缺一不可。相反,学术界虽然将家族相似性规则也解构成不同要素,但是家族相似性规则的启动并不需要不同要素同时满足。在家族相似性的考量要素中,每个要素的背后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原理,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具有妥当性的原理都应当尽可能地得到满足;然而由于它们彼此间相互掣肘(不同要件背后的原理具有相对独立性,所以它们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所以不得不做出权衡。”32这就存在一种可能,当某一要素背后的价值诉求被特别强调的时候,即便其他要素没有被满足,那么Reves规则仍然会被启动。
正是因为存在上述区别,所以笔者并不认为Reves规则是对Howey规则的简单重复,二者都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上述区别也是我们在选用证券认定规则时应该把握的。
此外,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我国学术界在对美国“其他证券”之界定进行引介时,主要将笔墨放在了对投资合同的引介上,忽略了对金融票证认定规则的研究。笔者认为形成此种局面的可能原因大致有三:第一,从适用范围上看,投资合同判定规则的应用范围极其广泛,基本上能够解决绝大多数证券的认定难题,而金融票证判定规则的应用范围相对较窄,其主要被用于票证类证券的认定中。宽广的适用范围极大地增强了投资合同判定规则的解释力,进而也增大了其在我国的影响力和接受度。第二,从规则需求的迫切性角度看,我国经济现实更加需要投资合同的判定规则。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各类融资活动势必活跃,伴随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非法集资。自1993年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集中信贷资金保证当前经济发展重点需要意见的通知》以来,非法集资的规制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缺乏对非法集资活动的具体分析,导致混淆了不同性质的集资行为,从而粗暴禁止了所有未经批准的集资活动……建议将更多非法集资活动划入直接融资领域监管。”33因此,我们应该学习美国,主要用投资合同判定规则对集资行为进行先行筛选,将绝大多数集资行为纳入直接融资领域进行监管;经过投资合同判定规则筛选之后的严重非法集资行为再由刑事法律进行规制。第三,金融票证判定规则的适用逻辑与我国金融结构现状不契合。金融票证判定规则的逻辑起点在于假定所有票证都是证券,然后再由当事人证明所争议的投资设计不是金融票证。这种具有推定意味的证券判定规则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所争议的投资设计都纳入证券监管的范畴,这与美国金融证券化的金融结构是相契合的,而我国现在的金融结构正处于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结构转变之中,推定性的证券判定规则对我国来说可能有点步调过大。相反,利用投资合同判定规则对证券进行正面界定,就比较容易控制证券范围扩张的节奏,不致引发新的风险。
(二)实例分析
2008年11月23日,SEC根据《1933年证券法》第8A节向Prosper发布停止令时,同时采用了Howey规则和Reves规则。这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有观点认为SEC根据Howey规则对Prosper的note进行认定是不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Prosper的note更像债券而非投资合同,Prosper的交易在本质上是个体借款人借款的证券化;另一方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拒绝将Howey规则适用于对票证性质的判定上。34不管争议如何,我们将Reves规则运用到P2P网贷note性质的判定中,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1.交易双方的动机
在美国式P2P网贷中,交易双方是P2P网贷公司和投资者。P2P网贷note是P2P网贷公司销售的金融产品。P2P网贷公司销售P2P网贷note的行为和普通的经营者销售一般货物一样,都是为了获得营业收入。所以,P2P网贷公司的目的不是“为企业经营筹集资金或者为大笔投资融资”。这就意味着从卖方动机的角度来说,P2P网贷公司不满足家族相似性规则的第一个考量要素中对卖方动机的要求。这有可能使P2P网贷note不被认为是金融票证。相反,P2P网贷note购买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投资获益,这满足了家族相似性的第一个考量要素中对买方动机的要求。这又有可能使P2P网贷note被认为是金融票证。
2.分配计划
P2P网贷note是在P2P网贷公司网站上公开向社会大众发售的,它相当于是向广大社会成员发出要约并销售投资工具的活动。这意味着,P2P网贷note的交易活动满足了家族相似性的第二个考量要素的要求。
3.投资者的合理预期
因为P2P网贷note是以25美元的等额面值发售给投资者的,而且在借款人违约的情况下投资者不享有任何的事后追索权,这就使P2P网贷note很像证券(转手证券)。35这意味着,在一个理性的投资者眼中,P2P网贷note属于证券。这说明,P2P网贷note的交易活动满足了家族相似性的第三个考量要素的要求。
4.是否存在其他风险防范或救济措施
从P2P网贷实践来看,并不存在其他大幅减轻P2P网贷note风险的监管措施。
如上面的分析所示,在家族相似性规则的检验下,仅P2P网贷公司的主观状态不满足家族相似性规则第一个要素的规定。不过,如前所述,在Reves规则下,并不要求所有的家族相似性规则要件同时被满足,即便某一个或多个要素的要求没有被满足,所争议的交易设计仍然有可能被认定为金融票证。换句话说,家族相似性规则的考量要素被满足只是增加了所争议的交易设计被认定为金融票证的可能性。在美国式P2P网贷交易中,仅P2P网贷公司的主观状态没有满足家族相似性规则的第一个考量要素的要求,这意味着P2P网贷note仍有可能被认定为是金融票证。
笔者认为,将P2P网贷note认定为金融票证是合适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P2P网贷公司进行金融创新的需要。后一原因更为重要,因为Reves规则所列的家族票证范围是开放性的,有利于保持法律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它可以充分激发当事人的创造力——如果票证被认定为证券,那么证券法所设定的各项义务都要适用于票证,相关当事人的法律义务也会随之加重。当事人为了规避证券法律责任,就会极尽所能来挖掘票证与既有证券的不同之处,这就会促使当事人不断地进行创新,发展出越来越多的融资工具,争取将P2P网贷note加入到新的家族票证家族中去。总之,Reves规则将给Prosper等P2P网贷公司留下“自证清白”的创新机会,有利于充分激发P2P网贷公司的创新潜能。在金融科技大发展的背景下,Reves规则所具有的促进创新的意义应该被监管者们重视。
五、Howey规则和Reves规则的替代性规则
(一)州法院的探索:整个交易计划是否满足“风险资本规则”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对Howey规则很多构成要件进行多种解释。自1946年该规则诞生以来,司法实践围绕着如何准确地理解这些构成要件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争论。对每个构成要件的含义,我们几乎都可以找到相反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有法院就想避开Howey规则而寻找替代性规则。在此要说明的是,Howey规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规则,但它只对所有的联邦法院有约束力,对州法院通常仅有说服力。原因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有自己独立的证券法,联邦证券法和州证券法相对独立地对本适用范围内的证券活动进行监管,相对独立地适用自己的证券法。州法院根据州证券法进行裁判时,并不需要遵守联邦证券法和依据联邦证券法而制作的判例。所以,州法院可以不遵守Howey规则。36此处所说的司法实践寻找替代Howey规则的方法恰恰是州法院的实践。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1971年夏威夷州最高法院在State by Commissioner of Securities v.Hawaii Market Center Inc.(HMC)一案中确立的风险资本规则(risk capital test)。
在HMC案中,上诉人HMC主张夏威夷最高法院利用Howey规则来判定HMC的计划是否属于投资合同。因为在HMC的计划中,发起人的主要目的是招募新成员,并向这些成员发售购买授权卡(purchase authorization cards)以赚取利润。本案中,发起人招募成员之目的与Howey规则中完全地从他人的努力中获取利润的目的相悖,这就说明HMC的计划不是投资合同,进而HMC的计划就不是证券。夏威夷州最高法院认为Howey规则太机械而不能给投资大众以充分保护。因为Howey规则会使案件当事人和法院过多地纠缠于对“完全地”“投资者参与”等字词的解释。与其这样玩文字游戏,还不如避开这些文字游戏而关注证券交易的经济实质(economic realities)——将投资者的资金置于一项事业的风险之下,而投资者在这项事项中没有管控权(managerial control)。37基于这样的经济实质,证券法的基本目标就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保护。本案中,夏威夷州最高法院提出了风险资本规则,具体内容如下38:
(1)被要约人(投资者)将初始价值(initial value)提供给要约人。
(2)初始价值受制于某一实体的风险。
(3)要约人对被要约人的价值回报承诺。在这一要件中,投资者初始投资所面临的风险是建立在要约人的固定回报承诺上,还是建立在与要约人的利润共享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考察被要约人的期待,而非要约人的资产负债表。而且,被要约人的回报直接来自于要约人的给付或者间接来自其所接受资产的增值,都属于被要约人所获得的利润。这样就扩大了“利润”的含义,避免了因为文义限制而将本该受证券法保护的被要约人排除在证券法保护之外。
(4)被要约人对实体的管理决策不享有实际(practical and actual)的控制权。为避开证券法的规管,要约人要证明被要约人对实体的管理决策享有实际的控制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被要约人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投资。
夏威夷州最高法院认为,风险资本规则不仅能够在常规性的融资形式中为公众提供保护,而且能够在新型的融资形式中为公众提供保护。39按照这一论断,晚于风险资本规则而产生的Reves规则也能够被风险资本规则替代,也即风险资本规则是Howey规则和Reves规则的替代性规则。笔者认为,Howey规则与Reves规则的区别也是风险资本规则与Reves规则的区别,对于不断创新的金融市场来说,采用Reves规则更有利于激发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活力和创造性。而且,风险资本规则也并没有完全解决Howey规则纠缠于字义解释的问题。比如,“初始价值”的内涵与外延、“价值回报承诺”的内容、“实际的控制权”的认定等都存在不确定性,这也可能引发当事人所谓的文字游戏。
夏威夷州最高法院的“风险资本规则”在未来可能会有两种命运:一种是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调卷令的方式,将HMC案提审,明确否定“风险资本规则”;另一种是联邦最高法院不对前述案件进行提审,任由“风险资本规则”在夏威夷州范围内作为先例性规则而被适用。
(二)联邦法院的探索:投资人的出资是否为“风险资本”
在联邦层面,也曾有法院利用风险资本规则对票证的性质进行认定。在Underhill案中,被告人Royal在向加利福尼亚按揭交易公司(California Mortgage Exchange, CME)购买贷款协议的基础上,于1976年开展了一项所谓的“贷款协议”项目,向投资者销售承诺函(promissory notes)。这一销售计划通过NME和NMESC两家公司进行。根据合作协议,NMESC可以利用NME的名称,并经营NME才能经营的抵押贷款经纪业务。根据贷款协议规定,NMESC以“担保贷款协议/承诺函(promissory note)”的形式从贷款人处借得资金。这种票证的期限为1~3年,期限届满后贷款人将根据特定票证获得本金和利息。NMESC利用所获的资金从第三方处购买受信托契约担保的折后承诺函,NMESC在第三方承诺函中的利益被用来担保贷款人从NMESC处购买的票证的权益。贷款人有权转让自己手中的票证。1981年,NMESC的现金流出现问题并提出破产。同年9月,Underhill向法院提起诉讼称,NMESC和Royal的行为属于违法发行证券,应负证券法项下的责任。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支持了Underhill的主张。Royal不服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向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的核心争议是,被告Royal所发行的票证是否属于证券法项下的金融票证。为了判定本案票证的性质,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采用了风险资本标准。法院以非穷尽的方式列举了风险资本标准所具有的六个要素:(1)票证的赎回时间;(2)担保;(3)义务形式;(4)发行的条件;(5)借款人借款的数量与借款人营业规模之间的关系;以及(6)资金的预期用途。这些标准的核心是要认定,贷款人或投资者的出资是否属于“风险资本”。40Royal认为,本案中票证在时间上是可以随时赎回的,票证有担保,票证协议的内容是可协商的且每个贷款人的出资额度仅占NMESC业务规模很小一部分,所以本案的票证实质上是一般的商业借贷,而不是证券交易。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并没有采纳Royal的辩驳,认为本案的票证属于证券法所规定的票证,进而Royal的行为属于非法发行证券行为,应负证券法项下的责任。比较奇怪的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并没有对前述六个要素在本案中的适用做详细解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Underhill案中所创设的风险资本规则是和Howey规则一样的规则,它不过是Howey规则的另一种表述;而Underhill案件的争议是判定所销售的票证是否属于证券法规定的票证,故而承担此项判定任务的不应该是Howey规则。41因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拒绝将Howey规则适用于判定票证是否属于证券的案件的态度,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风险资本”规则在其被提出来以后不久就夭折了。
六、结语
美国Howey规则和Reves规则都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前者通过对四个构成要件的关键因素进行张弛有度的解释,来保证规则本身与现实生活的适应性;后者并没有一个封闭式的构成要件,而是列明了存在争议的投资设计可能被认定为证券的影响因素,同时赋予相关主体“自证清白”的机会,这也很好地消解了规则有限性与现实无限性之间的张力。从促进金融创新的角度来说,这两个判例规则确实给实践留下了较大的试错空间,这一点也正是被我国学者所青睐的。但当前主张引进美国判例法规则以扩大证券概念的观点,主要将目光集中于对Howey规则所定义的投资合同的探讨,较少对Reves规则所定义的金融票证进行探讨,最终的结论大多是要在我国证券法中引入投资合同的概念。从理论上说,如果我国会出现类投资合同的证券,那么一定也会出现类金融票证的证券。尤其是在我国强调“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政策背景下,移植美国Howey规则和Reves规则的呼声必定还会出现,对这两个规则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准确把握,则是一个必定绕不开的前提。本文通过对两个规则的梳理和研究,填补我国当前对Reves规则研究不足的现状,并对我国证券概念的界定发挥助益。
注释
1.参见巴曙松, 吴博, 刘睿.金融结构、风险结构与我国金融监管改革[J].新金融, 2013, (5): 12-13.
2.参见彭冰.非法集资活动规制研究[J].中国法学, 2008, (4): 49-50.
3.参见高振翔.互联网金融语境中的非法集资风险及其刑法规制[J].交大法学, 2016, (2): 50-51.
4.同注2。
5.根据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部分第2(a)(1)节的规定,证券包括任何金融票证、股票、库存股票、证券期货、有担保的互换、长期债券、短期债券、债务凭证、利润分享协议中的息票或参与证书、担保信托证书、预组建证书或认购书、可转让股票、投资合同、委托表权决证书、存股证书、石油煤气或其他矿产小额利息滚存权,基于存款证书、证券组合或指数享有的看跌期权、看涨期权、跨界期权、期权、特权,与国外货币、任何利益或通常被认为是证券的投资工具有关而进入全国性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看跌期权、看涨期权、跨界期权、期权、特权,上述任一种证券的权益或参与证书、暂时或临时证书、收据、担保证书、或认股证书或订购权或购买权。
6.参见姚海放.论证券概念的扩大及对金融监管的意义[J].政治与法律, 2012, (8): 22.
7.参见杨东.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亟需扩大证券概念[N].法制日报, 2014-04-09.
8.参见万国华, 王才伟.论我国股权众筹的证券法属性[J].理论月刊, 2016, (1): 84.
9.同注6。
10.参见吕成龙.我国“证券法”需要什么样的证券定义[J].政治与法律, 2017, (2): 138-141.
11.SEC v.W.J.Howey Co., 328 U.S.293, 294-302 (1946).关于本案案情和Howey规则构成要件的介绍,可参见董华春.美国证券法“投资合同”的法律辨析[J].证券市场导报, 2003, (4): 71;董华春.从“Howey检验”看“投资合同”——美国证券法“证券”定义的法律辨析(一)[J].金融法苑, 2003, (2): 40-41.
12.SEC v.W.J.Howey Co., 328 U.S.293, 299 (1946).
13.判决原文为“Transaction or scheme whereby a person invests his money in a common enterprise and is led to expect profits solely from the efforts of the promoter or a third party.” 参见SEC v.W.J.Howey Co., 328 U.S.293, 299 (1946).
14.See Taibl S M.Federal Securities Law/Note Transactions[J].Ill.B.J.,1985, 74:141; Welle E A.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interests as securities:an analysis of federal and state actions agains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under the securities laws[J].Denv.U.L.Rev., 1996, 73(2): 441-454.
15.SEC v.Glenn W.Turner Enterprises Inc., 474 F.2d 476, 482 (1973).
16.SEC v.Koscot Interplanetary Inc., 497 F.2d 473, 485 (1974).
17.Steinhardt Group Inc.v.Citicorp, 126 F.3d 144, 151 (1997);Goldenberg v.Indel Inc., 741 F.Supp.2d 618, 643 (2010); SEC v.Arcturus Corporation, 171 F.Supp.3d 512, 522 (2016).
18.Continental Marketing Corp.v.SEC, 387 F.2d 466, 467-471 (1967).
19.参见王荣芳.合法私募与非法集资的界定标准[J].政法论坛,2014, (6): 106.
20.参见朱锦清.证券法(第三版)[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9.
21.Exchange Nat.Bank of Chicago v.Touche Ross & Co., 544 F.2d 1126, 1138 (1976).
22.Chemical Bank v.Arthur Andersen & Co., 726 F.2d 930, 939 (1984).
23.Reves v.Ernst & Young, 110 S.Ct.945, 945-960 (1990).关于Reves案的案情, 可参见刘新民.中国证券法精要: 原理与案例[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31-33.
24.SEC v.C.M.Joiner Leasing Corp., 320 U.S.344, 351 (1943).
25.Roer v.Oxbridge Inc., 198 F.Supp.2d 212, 224 (2001).不过也有观点认为, 共同交易不仅要求存在一级市场(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易),还是要求存在二级市场(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易),只有这两个市场同时存在时才满足共同交易的要求。参见Gordon J D III.Interplanetary intelligence about promissory notes as securities [J].Tex.L.Rev., 1990, 69: 392.
26.Reves v.Ernst & Young, 110 S.Ct.945, 951-52 (1990).
27.BancoEspanol de Credito v.Security Pacific Nat.Bank, 973 F.2d 51, 54-60 (1992).
28.同注26。
29.See Gordon J D III.Interplanetary intelligence about promissory notes as securities [J].Tex.L.Rev., 1990, 69: 395.
30.同注29。
31.SEC v.Diversified Industries Inc., 465 F.Supp.104,106-112(1979); Baurer v.Planning Group Inc., 669 F.2d 770, 775-779 (1981).
32.参见解亘,班天可.被误解和被高估的动态体系论[J].法学研究, 2017, (2): 48.
33.同注2。
34.See Magee J R.Peer-to-Peer len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surviving after Dodd-Frank [J].N.C.Banking Inst., 2011, 15(1): 155-156.
35.LendingClub.Prospectus dated August 22, 2014, LendingClub (Aug.22, 2014)[EB/OL].(2014-08-22)[2020-02-19].https://www.lendingclub.com/fileDownload.action?file=Clean_As_Filed_20140822.pdf&type=docs.
36.不过,这并不意味州法院完全不受联邦最高法院的影响。在特定情况下,即便州法院所审理的案件完全属于州内事务,联邦最高法院仍然可以通过调卷令(writ of certiorari)直接对州法院的判决进行提审。需要注意的是,联邦最高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联邦地区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必须遵守Rooker-Feldman规则,在没有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此类法院不能直接作为州法院的上诉审法院。参见Rooker v.Fidelity Trust Co., 263 U.S.413 (1923); District of Columbia Court of Appeals v.Feldman, 460 U.S.462 (1983).
37.State by Commissioner of Securities v.Hawaii Market Center Inc., 52 Haw.642, 647-648 (1971).
38.同注37。
39.同注37。
40.通过比较发现,HMC案的风险资本规则的核心是将整个交易计划看成一个整体,从总体上来判断一个交易计划是否属于证券;而Underhill案的核心是判断投资人的出资是否属于风险资本。二者虽然都采用了“风险资本”这一称谓,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裁判规则。参见Underhill v.Royal, 769 F.2d 1426, 1428-1432 (1985).
41.同注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