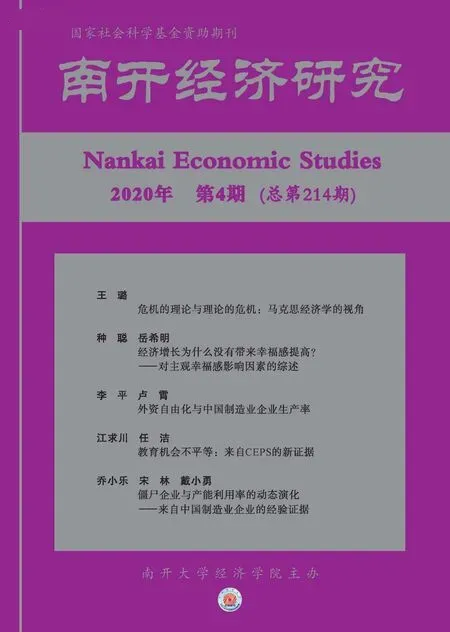经济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 幸福感提高?
——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综述
种 聪 岳希明
一、引 言
幸福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使本国居民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美国早在1776 年的《独立宣言》中写道:“所有人都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之一就是追求幸福”。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居民幸福感的提高,重视改善人们的福利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十九大报告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李克强总理在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幸福感可以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高居民健康水平(Diener 和Chan,2011)和降低离婚率(Clark,2018);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劳动投入量和劳动力生产效率(Oswald 等,2015);有利于政治稳定、降低犯罪率(Liberini 等,2017);有利于增进人们之间的信任与社会和谐(Clark,2018)。所以,研究幸福感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高居民幸福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直以来,收入被认为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然而,经济学领域的很多学者通过各国数据发现,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或收入提高而增加,Easterlin(1974)将这一现象称为“伊斯特林悖论”——短期内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正向相关,在长时间序列中这种正向相关关系消失,这一悖论得到很多学者支持(Easterlin 和Sawangfa,2010;Deaton 和Stone,2016)。还有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会持续提升幸福感(Stevenson 和Wolfers,2008;Diener 等,2012),但总的来说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呈下降趋势。已有研究显示,性别、年龄、民族、教育、健康等个体特征以及经济、社会、政治等社会特征均会影响幸福感。社会特征中,有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与幸福感的研究(Clark 和Oswald,1994;Di Tella 等,2001);有收入差距和不平等与幸福感的研究(Knight,2017);有社会关系、社会地位、公共安全(信任感和犯罪率情况)与幸福感的研究(Helliwell 等,2018);有政治制度、公共服务、官员腐败和寻租行为与幸福感的研究(Frey 和Stutzer,2000);也有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与幸福感的研究(Van Praag 和Barsma,2005)。从上述研究来看,收入是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本文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寻找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为提升我国居民幸福感提供政策建议,使人们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和获得感。
文章的主要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幸福感测算方法及评价;第三部分是关于“伊斯特林悖论”的讨论;第四部分是个体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社会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展望。
二、幸福感测算方法及评价
人们一直在追求幸福,那么何为幸福?英语中用Well-being 来表示美好的生活,也有用Happiness 来表示快乐,在希腊语中用Eudaimonia 表示美满。托马斯·霍布斯提出“欲望-满足”理论,即人的幸福是由于欲望得到不断满足。尼采认为:“快乐就是权力意志得以伸张,而痛苦就是权力意志受到挫折。”即当你能行使自己的权力满足自身的欲望时,就会感到快乐和幸福,反之就会感到痛苦。19 世纪后,以边沁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主张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幸福观,将效用等同于幸福并对幸福进行量化,认为不同个体的幸福也是可以比较和加总的,更加关注如何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进而增加人们的福祉。20 世纪初,马歇尔、拉姆齐和冯·诺伊曼等经济学家引入偏好概念解释什么是幸福,将效用与幸福等同看待,认为经济发展可以使人们得到物质欲望的满足,进而提高效用水平和增加幸福感。20 世纪中期,心理学家从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角度对人们幸福感进行定义和量化。20 世纪末至今,伊斯特林、安格斯·迪顿、卡尼曼等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家将幸福与经济学结合起来形成幸福经济学。
作为幸福经济学的核心变量,幸福感在量化分析中一般有三种表述,分别是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和生活阶梯(Ladder-of-life)①主观幸福感是被调查者自我报告的幸福状况(Deaton 和Stone,2016);生活满意度是指一个人对他(她)评估的自身整体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Veenhoven,1996);生活阶梯是指坎特里尔阶梯法中被调查者回答的幸福感等级(Cantril,1965)。,这几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都可以作为幸福感的代理变量,在之后的幸福感表述中本文也并未区分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幸福感测算代表性的方法主要有:坎特里尔阶梯法(Cantril Ladder)、生活满意度评价法和享乐幸福测算法。
美国心理学家Cantril 在1965 年对世界上14 个国家的希望、恐惧和幸福感研究中提出坎特里尔阶梯法,用来评价被访者现在、过去和将来的幸福感,将“自我定位奋斗量表”(Self-Anchoring Striving Scale)作为幸福感的测算标准,在量表中使用一个非语言阶梯的方式显示数字0~10,代表生活满意度从下到上的阶梯,0 代表最坏的生活,10 代表最好的生活,而被访者会被问道“您认为自己当前处于哪个阶梯”。被访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给出了9 个参考指标,分别是经济、健康、家庭、个人价值、现在状态、工作情况、国际形势、社会价值和政治。其中经济、健康和家庭关系是人们自我评价得分的重要指标。坎特里尔阶梯法是幸福感测算的基础,通过被访者自我评价的阶梯位置,可以得到被访者的幸福程度。有学者对坎特里尔阶梯法存在一些“合理”的疑虑,即人们并不清楚当被调查者回答幸福时,其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也并不知道被调查者是否理解关于幸福的问题,不同的环境下被调查者的回答可能不同。这种自我报告的幸福感的价值和实用性被Easterlin(1974)、Kahneman 和Krueger(2006)等通过数据分析及实验的方法所证实。随着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充分合作,幸福感测算方法也在不断改进(Kahneman 和Deaton,2010;Steptoe 等,2015)。从目前研究来看,幸福感测算不仅要考虑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还要考虑人们对情感满意度的评价。因此,幸福感一般从生活质量评价(Life Evaluation)、享乐幸福(Hedonic Wellbeing)等角度进行测算(Deaton,2010;Miret 等,2014)。
(一)生活质量评价法
Deaton 提出主观幸福感是一个认知过程,与个体对生活的总体评价相关,或是对个体一段时间的生活状况的整体回忆。通过制定生活满意量表对生活满意度的大小进行测算。这种测算方法以坎特里尔阶梯法为基础,将生活满意度划分为10 个等级,从低到高代表不同生活质量的满意水平。Deaton 和Stone(2016)在坎特里尔阶梯法的基础上,研究生活质量评价法中的情境效应(Context Effect)。所谓情境效应就是之前事件或者经验对随后发生事件的反应。将政治问题作为一种情境,随机抽取1000 名被调查者的每日调查样本,处理组为500 名被调查者被问到政治问题,对照组为500 名被调查者没有被问到政治问题。结果发现,当没有被问到政治问题时,生活满意度得分(阶梯值)很高,为6.45,政治问题的提出导致了阶梯分数平均下降0.67。这种政治问题的情境效应改变不同群体分组的幸福感排名,如性别、种族、就业状况、教育、健康等,特殊情境下,某一种因素会显著影响幸福感,这种因素对不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不相同。
(二)“享乐幸福”测算法
Deaton 提出的享乐幸福或者体验幸福主要用来评价个体最近周或者月中每天的情绪变化,一般使用快乐、生气、压力等情感因素来衡量人们幸福感。传统测算享乐幸福的方法是对一段时间情绪状况的评价,这造成评估内容很可能是个体对生活质量的评估而不是个体的情绪状态。Steptoe 等(2015)提出了生态瞬时评估法(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EMA),即在很短时间内随机抽取个体进行汇报,以得到被调查者最直接的情感状态,如快乐、担忧、抑郁、痛苦等。EMA 法被证明可以得到与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关于幸福感使用的昨日情感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RM)相同效果。关于EMA 法的科学性研究,直接测量对幸福感的瞬时感觉比测量记忆中的幸福情感在指导决策方面更可靠,通过随机记录被调查者当前的活动和感受,并将每一段经历的感受联系起来进行评价,可以准确测算人们心理幸福程度。
(三)生活评估和“享乐幸福”测算方法的总结与评价
Kahneman 和Deaton(2010)发现生活评估(“自我定位奋斗量表”测算)和享乐幸福(昨日重现法测算)有很大区别,前者是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后者主要体现最近的情绪。本文认为两者的主要区别如下:(1)不同变量对应幸福感测算的方法不同,同一变量在不同测算方法中得到的结果也存在差异。(2)Kahneman 等人发现与他们最初的假设相反的是,情感评估与生活评估相比更容易受到享乐适应性的影响,与每天的情感质量相关,而与长期生活环境的联系较少。(3)这两种衡量指标虽然结果存在差异,但又不矛盾,幸福感有多个维度,测算幸福感时不能使用单一静态维度,还应该考虑到其多维动态变化(Steptoe 等,2015)。基于以上测算方法,国外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WVS)、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GWP)以及国内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等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测算,得到了幸福感一手数据,为后续大量的实证研究提供数据支持①由于很多研究均使用以上四个数据库对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为了简便,后文使用每个数据库的英文缩写代表该数据库。。
三、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关系的探讨
伊斯特林在1974 年《经济能否改善人类的命运?一些经验证据》中对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截面数据研究中,某国的人均GDP 水平越高,居民幸福感越高,这种关系在时间序列研究中却不存在,即某国居民幸福感并未随该国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个别时期甚至出现下降,显然与人们的预想不符,这种“矛盾现象”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自悖论提出后,关于幸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争论就一直存在。有支持伊斯特林悖论的(Veenhoven,1991;Frey 和Stutzer,2002;Deaton,2008;Easterlin,2013),也有对伊斯特林悖论提出质疑的(Stevenson 和Wolfers,2008;Diener 等,2012;Helliwell 等,2012)。争论的内容除了“收入的增加是否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还包括“截面数据中幸福感与收入的正向关系为什么会在时间序列中消失?” “幸福感与经济增长的截面证据能否预测时间趋势?”等等,这些问题一起构成了幸福感与收入悖论的核心问题。
(一)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横截面关系
在截面数据研究中,个体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正相关,个人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如果将一个国家居民根据收入分组,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会低于高收入阶层,但收入对高收入者幸福感增加的效用低于低收入者,显示出边际递减的趋势。Easterlin(1974)使用美国公众意见学会(AIPO)的投票数据,对美国1970 年不同收入阶层的幸福感进行比较,发现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低于高收入阶层,这一结论在其他国家和使用其他调查方法下仍然成立。进一步发现在截面数据中,个体收入比平均收入水平越高会获得越强的幸福感,个体收入比平均水平越低,幸福感就会越弱,即幸福感与绝对收入水平正相关。之后,Easterlin 等人在2010 年、2013 年的文献中也验证了个体收入与幸福感的正相关关系非常稳健。
表现在国家层面就是某国越富裕,幸福感越高,而且增加相同的收入对富裕国家幸福感的增加程度低于贫穷国家(Frey 和Stutzer,2002;Deaton,2008;Deaton,2018)。Deaton(2008)对人均GDP 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被Easterlin 认为是最全面的,在某一时点上,人均实际GDP 与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正相关。在对世界民意调查(World Poll)中的123 个国家数据分析发现,富裕国家居民的平均生活满意度更高,在7.5~8.5 之间,贫穷国家居民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在3.1~4.5 之间,而且这是一条先快速上升然后趋于平稳的曲线,左侧贫穷国家生活满意度曲线比较陡峭,说明收入对幸福感或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大,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富有国家生活满意度曲线比较平缓,其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小。同时使用WVS 数据验证两者正向关系具有稳健性。
Deaton 等人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经济增长率通常用人均GDP 变动的百分比表示①Veenhoven(1991)将对数尺度的使用称为“经典的缩放技巧”。,将人均GDP 取对数后,人均GDP 对数每翻一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会持续地增加。基于幸福感和人均GDP 对数的回归发现,回归系数为0.838,标准误差为0.051,进一步验证了幸福感与人均GDP 对数的线性关系。综上所述,截面数据中收入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幸福感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
(二)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时间序列关系
在时间序列中,收入和幸福感也是正相关关系吗?在国家时间序列研究中,时间序列的长短对一个国家幸福和收入的关系影响较大。一般认为短期内的生活满意度和人均GDP 是正相关的。为了验证这种正相关关系普遍适用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Di Tella 等(2001)发现发达国家在短期内的经济衰退(失业)带来幸福感的降低,幸福感的变动趋势与收入水平变动趋势相同。在经济转型国家的经验上,Easterlin 和Sawangfa (2010)发现民主德国、爱沙尼亚和俄罗斯等欧洲转型国家在转型前和转型后生活满意度呈“U 型”变化(即下降后逐渐上升),幸福感的变动趋势与实际GDP 的变动一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只考虑转型中经济收缩或经济扩张的某一时段,幸福感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能确定。17 个拉丁美洲国家数据的短时间序列研究也发现财政满意度和GDP 的回归结果显著正相关。这种短期时间序列的正相关关系也被中国的研究者证明。
在长时间序列研究中,截面和短时间序列中的国家间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正相关关系消失,有些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幸福感也不一定较高。Madison(1991)研究发现,在1972—1991 年间,美国人均GDP 增加了一倍多,但美国人的幸福感没有提升。日本的人均GDP 在1958—1987 年间以平均5 倍的速度增长,使其生活水平提高到美国的66%,而日本的平均主观幸福感也没有改善。也有研究发现中国也存在收入与幸福悖论,Easterlin 和Sawangfa(2010)发现中国居民幸福感从1995 年的3.05 下降为2007 年的2.94,证明中国也存在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2012)将幸福感数据延长到2010 年后,幸福感仍在下降。比较时间跨度为21 年~34 年的17 个发达国家、时间跨度为15 年~33 年的9 个发展中国家和时间跨度为12 年~22 年的11 个转型国家,发现生活满意度的增长率与实际人均GDP 的增长率也没有明显的关系。最后将37 个国家去除异常值的情况下,两者的关系仍不明显。人均GDP 增长率和幸福感变动在短期时间序列内正相关,而在长期内不相关,若将短期和长期序列混合后,短期的正相关关系占主导地位。由于WVS 中发展中国家数量较少,加入了拉丁美洲国家数据后,发现居民幸福感并没有增加,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回归结果中也未发现相关关系。还有学者认为时间序列结果中主观幸福感和人均GDP 为负相关。Deaton 和Stone(2013)指出经济增长率对生活满意度有负面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高于当前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长期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影响依然为负,进一步证明了经济增长快的国家幸福感一定高的假设不一定成立,这一结论在其2008 年的研究中已经给出。很多实证证实,在时间序列中一个国家的收入与平均生活满意度之间很少或者没有直接关系,收入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因素(就业、婚姻状况)的影响更小(Di Tella 等,2001;Blanchflower 和Oswald,2004)。
(三)幸福悖论的一些理论解释
以上文献给出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关系在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中的不同结果。那么,在截面数据中的正相关关系为什么会在时间序列中消失了呢?截面数据国家间幸福感与人均GDP 的正相关关系能否用来预测时间序列趋势?很多学者尝试使用相对剥夺理论和适应性理论对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这种关系进行分析(Easterlin,1974、2010;Knight 和Gunatilaka,2011;Amendola 等,2015)。
1. 从相对剥夺的角度解释与证明悖论
社会学家认为当人们评估自己的地位时,习惯比较他们自己和其他个体或群体的相对位置(Merton 和Kitt,1950),也可以理解为相互之间的攀比效应。经济学家借鉴相对剥夺理论对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分析。Easterlin(1974)提出,幸福是一个相对概念,任何个体绝对收入的增加都会提高其幸福感,而当所有人的绝对收入都增加时幸福感不再发生变化。Amendola 等(2015)发现,当预测自己的收入增加时,人们会认为周围所有的群体收入都有所增加,这种绝对收入增加带来的幸福感变化被周围人收入同比例的变动所抵消,幸福感不会发生变化。国家间也是如此,一个相对富有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幸福的国家,这取决于相对收入的变化。与其他方面的剥夺相比,较低的绝对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小。Luttmer(2005)认为人们总是将个人收入水平和周围人的收入水平进行比较。假设一个国家居民收入是对数正态分布的,不平等实际测量的是收入分布的方差,当不平等增加时,平均数位于中位数的右侧(偏富裕的一侧),这会让中等收入水平的居民因为相对收入水平下降感到更痛苦,尽管绝对收入水平没有变化。Knight 和Gunatilaka(2011)使用相对剥夺理论对中国的幸福悖论进行解释:虽然农村人口相对贫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但在有限的信息集和狭窄的参考群体条件下,居民并不知道自己的收入在整个群体中的位置,因而相对剥夺感较低;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居民收入相对较高,而且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也高,但由于参照群体的过高期望,导致城市居民相对的剥夺感更高,幸福感更低。整体来看,与平均收入水平相比,当居民收入高于平均收入水平时,幸福感和收入正相关,低于平均收入水平时,幸福感和收入负相关,而且高收入阶层回归系数比低收入阶层高1.05,说明高收入阶层的幸福感高于低收入阶层。分农村、城市和流动人口来看,相对收入水平对幸福感有负向影响。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提高,但平均幸福指数低于农村居民,主要原因是流动人口在城镇生活中获得高收入的同时,与周围城市人相比收入并未提高,导致工作满意度、家庭关系等与幸福感负相关。
2. 从享乐适应性理论解释与证明悖论
享乐适应性理论是指个体在评价自己幸福感的时候,往往会以实际状态作为参考标准或基准,并与过去和现在进行比较。随着时间和空间变化,个体基于自己社会经验的参考基准也在变化,收入和幸福感的相关性也会减弱。Easterlin 和Angelescu(2009)提出人的欲望会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当收入水平低于心理预期水平时,个体会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导致幸福感下降。Clark(2018)对享乐适应性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给出幸福感和收入在短期和长期的变化趋势。当收入在第二年突然增加时,幸福感在第二年有一个明显增加,当收入水平在第二年后不发生变化时,幸福感开始逐渐下降,到第五年时,幸福感基本回到第一年的水平(也就是收入增加前的水平)。这证明了由于享乐适应性的存在,收入的增加不一定会使幸福感显著增加。假设每个个体都有自己幸福感得分的设定值,当遇到失业或遭受严重伤害或疾病时,会使他的幸福感得分发生向上或向下偏离,从而低于或高于设定值,但享乐适应性会使个体快速地回到初始水平。长期来看,人的物质和品味随着收入提高会有所提高,由于实际收入的增长,每代人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产生更高层次的消费标准。即使在一代人的不同生命周期里,由于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的规模和习惯也会发生变化,但这些物质欲望和品位的上升会抵消收入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
享乐适应性理论也被用来解释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悖论,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有可能高于城市居民。罗楚亮(2006)发现收入水平或者物质福利的增长,不一定表明居民个人福利的改善。农村比城市的主观幸福感高,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居民对收入有较低的预期或欲望,并且对未来收入变动有良好预期。低收入的农村居民欲望比较低,对未来收入预期乐观,幸福感较高,而高收入的城镇居民欲望比较高,对未来收入预期下降,幸福感下降。Knight 和Gunatilaka(2011)实证发现,人们会将自己现在的生活与之前的生活进行比较,目前生活水平比5 年前好的农村居民幸福感回归系数为正,比5 年前差的城镇居民幸福感回归系数为负。幸福感还与人们预期收入有关,预期自己收入好(乐观)的农村居民,幸福感回归系数为正,预期自己收入下降的城镇居民,幸福感回归系数为负。因此,虽然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居民,但农村居民有较低的欲望和较乐观的收入预期,其幸福感可能会高于城镇居民。
(四)对悖论的一些质疑
自从Easterlin 提出幸福-收入悖论后,有一些学者对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提出质疑,Sachs 等(2012)就认为长时间序列中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仍然存在正相关关系。Stevenson 和Wolfers(2008)使用WVS 数据重新评估了伊斯特林悖论,发现各国主观幸福感的平均水平与人均GDP 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均GDP 超过某一定点后各国的主观幸福感就不会增加,进而对幸福悖论加以否定。Helliwell 在2012 年《世界幸福感报告》中引用以上两篇论文的结果,认为长时间序列中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是正相关关系,否定了伊斯特林悖论(S-S-W)。针对以上质疑,Easterlin 在2015 年的研究中进行反驳,认为以上反对者使用的数据时间跨度较短是悖论不存在的主要原因,然后使用WVS 数据中俄罗斯、斯洛文尼亚等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证明幸福感和收入并不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即幸福悖论是存在的。Edsel 和Beja (2013)也提出收入和幸福感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或许可以成为反驳的证据,然而他们认为估计结果得出的两者相关性太小,并不足以推翻幸福-收入悖论,也不能说经济的增长对提高长期幸福感有实质性的效果。
已有文献表明,幸福感和收入悖论是存在的,现在最重要的挑战是解释其合理性,并调整实证中发现的这一悖论(Clark 等,2008;Easterlin 和Sawangfa,2010)。不可否认,短期中幸福感会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但随着收入的增加,幸福感呈边际递减趋势,如短期收入的增加对贫穷国家的影响大于富裕国家,以及收入增加对低收入者幸福感影响高于高收入者。长期中,幸福感和收入的关系基本消失。学者们使用相对剥夺理论和享乐适应性理论对上述结果进行分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上理论和实证只是讨论收入变化是如何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然而收入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接下来第四和第五部分将对幸福感的其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四、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个体特征
研究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多,Alesina 等(2004)根据不同的属性将幸福感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年龄、性别、民族、教育、健康、婚姻等个体特征,二是失业率、收入不平等、政治身份、民主制度等社会特征。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都会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也可以为政府提高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政策设计提供更为直接的建议。
(一)性别、年龄与主观幸福感
在性别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中,由于在社会和家庭中普遍存在性别歧视,传统观点认为男性的幸福感得分比女性高,Blanchflower 和Oswald(2004)证实美国男性幸福感与日俱增,尽管存在针对性别歧视的立法,女性的幸福感仍然呈下降趋势。可能是因为男性在社会中的职业和家庭中的地位都处于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男性的优越感,不过这种差异在逐渐缩小。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女性汇报的幸福感也可以高于男性,这与女性收入的提高、社会和家庭地位上升、心理上更容易发泄不满的情绪等因素有关(Deaton 和Stone,2016)。总结原因有以下几点:女性的收入水平较以前有了明显的提升,而收入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地位上,对女性工作、能力的歧视正在减少,社会的认可对提升幸福感有积极影响;在情绪管理上,女性也比男性更好地控制情绪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U 型”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加幸福感会先下降后增加,该结论已经被大量文献证实(Blanchflower 和Oswald,2004;Deaton,2015、2016;Clark,2018)。Deaton 将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U 型”关系总结为年龄-收入悖论:“收入水平本身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而对生活水平感到满意的人的比例反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以及“经济危机使所有群体的生活水平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种影响的严重程度会随着年龄的上升而降低”。Deaton 和Stone(2016)使用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对悖论进行了解释: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情感智慧不断累积,人们选择保留更多让自己情绪满意的事件和友情等,加上积极情绪体验的适度增长,或许可以抵消身体疼痛的增加。因此,尽管老年人面临收入减少、社会地位降低和死亡率提升等,但幸福感不一定会下降。Blanchflower 和Oswald (2004)认为这种“U 型”变化反映了一个对环境的适应过程,人们中年时期幸福感较低的原因是其对未来不能达到预期的失望,即欲望得不到满足带来的痛苦。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平均年龄与幸福感的“U 型”关系并不稳定,Steptoe 等(2015)利用GWP针对160 个国家的持续调查显示,富有国家的幸福感得分与年龄存在“U 型”关系,居民在45 岁~55 岁时的幸福感最低,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这种模式在其他类型国家没有出现,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居民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非洲地区没有发现年龄与幸福感的关系。
(二)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
健康是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健康与幸福感是正相关关系,自身评价更健康的个体幸福感越高(MacKerron,2011),幸福感对身体的健康也有正向影响。健康状况与幸福的关系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大部分研究通过问卷中的主观报告来衡量健康状况,而生活满意度也是主观的,两者可能受到共同情绪的影响。所以,使用尽量客观的健康状况指标是非常必要的,如去医院的次数、住院天数等。Deaton(2008)使用GWP 数据研究发现,是否对健康照料与医疗体系有信心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085。但这种健康指标的回答比较主观,不能确定实际的健康医疗体系对幸福感的影响。Deaton 和Stone(2015)认为,健康状况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身体健康是心理幸福感的决定因素,患有冠心病、关节炎和慢性肺病等疾病的老年人表现出抑郁情绪增加,享乐情绪下降,幸福感受损;心理幸福感对健康也有保护作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一些心理疾病,更加长寿。其在控制人口统计因素(收入、教育、婚姻状况和教育状况)、健康指标(对长期疾病的限制,如癌症、冠心病、糖尿病等)、抑郁症历史和抑郁程度、健康行为(吸烟、饮酒、运动)等变量后,发现幸福感和人们的寿命相关,在平均为8.5 年的受访期内,幸福感位于最低四分之一水平居民死亡率为29.3%,而幸福感位于最高四分之一水平居民死亡率为9.3%,两者相差20%。Case 和Deaton(2015)认为伴随着压力的增加,中年美国人因吸毒和酗酒等行为导致患病率比较高,其身体的疼痛导致自杀率提高,幸福感水平降低。除了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对主观幸福感也有影响。心理健康的评价指标中,既包含快乐、满意、幸福等积极情绪,也包括压力、抑郁、悲伤等消极情绪。积极健康的情绪对幸福感有正向影响,消极悲伤的情绪对幸福感有负向影响。Case 和Deaton(2015)利用GWP 数据探索了中年人自杀和不幸福的关系,根据年龄和幸福感的“U 型”关系,中年人的幸福感最低,自杀率最高。同样结果也出现在Daly 等(2013)的研究中。因此,由身体疼痛和情绪问题导致的自杀与幸福感相关。
(三)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拥有越高的幸福感,同时幸福的人也会选择接受更高的教育(Easterlin 和Angelescu,2009)。在劳动经济学中,首先,教育可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已经被证实,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人们收入增加,而收入和主观幸福感正相关,在特定时间点(与没受过教育的同龄人相比),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其次,教育会增加人们对生活和工作的期望,主要表现在实际产出相对于预期结果的增加;然后,教育水平越高,可以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幸福感也会越高;最后,教育会给人一种自信,受过教育的人会获得更多的尊重,生活满意度也会提高(Oreopoulos 和Salvanes,2011)。MacKerron(2011)认为,教育水平与幸福感有正向相关关系,对于个人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幸福感越高。对于国家来说,平均教育水平越高的国家,幸福感也越高。在某个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具有初等教育水平的同龄人有更高的幸福感,但随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受教育水平在初等阶段对幸福感的增加的程度比高等阶段对幸福感的增加的程度要高。
(四)家庭关系与主观幸福感
家庭和睦的成员主观幸福感越高。主要从家庭关系中的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这两方面入手。从夫妻双方婚姻关系来看,已婚者报告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比离婚、分居者更高,而且家庭中夫妻婚姻状况不仅提高配偶的幸福感,也有利于增加子女的幸福感,父母在婚的子女幸福感明显高于父母离异的子女。Stutzer 和Frey(2006)研究了婚姻是否使人快乐,利用德国时间跨度为17 年的社会经济面板(SOEP)数据发现,一方面,婚姻可以增加人们幸福感,但配偶之间从婚姻中获得的收益存在差异,潜在的和实际的劳动分工有利于提高女性和年轻家庭夫妇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单身时快乐的人更有可能在未来结婚,幸福可以增加人们对婚姻的信心。Zimmermann 和Easterlin(2006)比较德国结婚、同居、离婚、分居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发现存在夫妻关系会显著提高家庭的生活满意度,离婚或分居对生活满意度有消极影响。时间序列上,生活满意度在结婚当年和第二年提高最快,随着结婚时间的延长,生活满意度的增速在逐渐下降,但仍然高于结婚之前的满意度。
子女数量和性别均会对父母主观幸福有影响。子女数量与幸福感的关系是:有子女父母主观幸福感比较高,尤其使母亲幸福感显著提高,但有二胎之后,母亲主观幸福感不会增加,而父亲主观幸福感会上升。因为年轻女性需要照顾家庭,面临更严重的工作与家庭冲突,闲暇时间减少,也更容易产生压力,因而汇报的生活满意度会下降(Stutzer 和Frey,2006;Cetre,2016)。Cetre(2016)认为子女数量与父母幸福感的关系还要考虑家庭的收入水平,对来自GWP 数据的研究发现,子女和父母幸福之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人群中存在巨大差异,收入水平对子女和父母幸福感的相关性有决定性影响:当收入低于20000 美元时,有子女会降低父母的幸福感,当收入高于20000 美元时,有子女会增加父母的幸福感。子女的性别对父母幸福感也有显著影响,陆方文等(2017)利用CGSS2008 数据,定量研究子女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发现随着中国市场化和经济快速发展,女性经济地位提高,女儿给父母带来比儿子更多的幸福感。回归结果均支持养儿子带给父母幸福感显著低于女儿。儿子带来幸福感降低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否定了“养儿防老”假说,随着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的完善,儿子作为养老产品的需求减少,是否为儿子也不影响父母与子女居住。二是随着房价上涨,儿子结婚买房会增加父母压力,减少父母幸福感。该研究充分揭示了子女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有利于改变重男轻女的观念,对调整性别不平衡现状有积极意义。 个体特征对幸福感影响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性别上,男性汇报的幸福感要高于女性,但这一结论正在发生改变;在年龄上,幸福感呈“U 型”变化趋势,中年人的幸福感水平最低;健康状况、教育、家庭关系等个体变量与幸福感正相关。
五、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社会特征
除了以上个体特征外,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生态因素等社会特征也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经济因素主要是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Clark 和Oswald,1994;Di Tella 等,2001)、收入差距和不平等(Knight,2017);政治因素主要是基本公共服务、官员腐败和寻租行为(Alvarez-Diaz 等,2010;Deaton,2018);社会因素主要是社会关系、社会荣誉和地位、社会信任感和犯罪率情况(Dustmann 和Fasani,2014;Helliwell 等,2018);生态环境主要是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储德银等,2017)。同时以Deaton 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和心理学家Kahneman、Stone 等人合作,研究心理因素对幸福感的重要性(Deaton,2012、2018;Frey 和Stutzer,2002;Layard,2006;Clark 等,2008)。
(一)经济因素与主观幸福感
1. 失业可以通过直接增加劳动者的心理痛苦程度影响幸福感,也可以通过失业后收入下降影响劳动者的幸福感(罗楚亮,2006)。Clark 和Oswald(1994)认为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有三个方面:(1)失业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就业者低,如果将不幸福用平均心理痛苦程度表示,那么失业者的痛苦程度为2.95,有工作的痛苦程度为1.45,失业者的不幸福感是就业者的2 倍,而自愿性失业工人的平均心理痛苦程度低于非自愿性失业;(2)受教育程度越高,失业带来的痛苦程度越高,这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失业的机会成本可能更高;(3)失业者的年龄和平均痛苦程度呈“倒U 型”关系,而且失业者中年轻人和老年人比中年人表现出更少的痛苦,这种关系说明失业是影响年龄与幸福感变动趋势的重要原因。在失业率的研究中,Di Tella 等(2001)将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引入到主观幸福感模型中,研究通货膨胀和失业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与生活满意度负相关。在比较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对幸福感影响大小时发现,失业率变动1%和通货膨胀率变动1.7%对幸福感的影响是相同的,失业率对幸福感下降的影响高于通货膨胀率。我国的幸福感研究也发现失业与幸福感的负相关关系,Easterlin 等(2012)将20 世纪90 年代初中国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部分归因于高就业率和高福利水平。将21 世纪初幸福感下降解释为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的下降。伊斯特林等(2013)测算出1990—2010 年中国近二十年的幸福感“U型”变化,整体趋势是先下降再上升,与转型国家的幸福感变动趋势接近。这进一步验证了失业是劳动者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原因。
学者们也关注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Aghion 等(2016)运用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Schumpeterian Creative Destruction)建立了一个关于创造性破坏与幸福感的理论模型。创造性破坏会引发企业和职位的增加或消失,通过研究不同劳动力市场环境下创造性破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建立起就业增长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该模型中,人员流动率对生活满意度有两种影响,直接影响为高流动率可能会增加找到工作的机会进而提高生活满意度,间接影响为高流动率有正的增长外部性,提高未来收入的现值水平,进而提高生活满意度,而且人员流动率越高幸福感越高,创造就业机会能够提高幸福感。这种理论扩展了人员流动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如何受到个人特点、劳动力市场及政策的影响。
2. 收入不平等通过影响人们组间和组内收入差距、公平与不公平的差距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其中由于阶层固化、户籍制度、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负向影响显著。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发现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存在负向影响,基尼系数每上升0.1 单位,居民主观幸福感下降0.057 单位。
(1) 对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区分组间不平等和组内不平等,组内不平等是横向比较同一收入阶层收入差距,组间不平等是纵向比较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组内收入差距是降低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取决于个体位于某一收入群体的位置或者是某一收入群体与平均收入水平的关系。Amendola 等(2015)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只有相同收入群体的不平等才会影响幸福感,使用欧洲生活质量调查(EQLS)数据,将收入分配分为同组内和不同组间两部分,发现不同群体间的不平等对幸福感影响较小,而组内的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负向影响较大。从组间的收入差距来看,Easterlin(1974)比较不同年份的美国各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变化,发现1963—1966 年整体幸福感略微上升,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上升抵消了低收入阶层下降的幸福感。Dynan 和Ravina(2007)研究是否不同收入群体的相对位置的改变会造成幸福感的变化,发现当一个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位于该地区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之上时,幸福感提高。第一轮回归结果发现,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是正的。第二轮结果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对幸福感的反应不同,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居民不会受到其收入水平与平均收入差距的影响,而高收入水平的居民会受到其高于平均收入多少的影响。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发现,收入不平等对不同的收入阶层幸福感影响存在差异,显著损害了低、中低和高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对中上收入阶层的影响并不显著。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降低也验证了负向隧道效应和相对剥夺理论。
(2) 对不平等的研究区分公平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不平等。公平的不平等一般是因为能力因素导致的,对幸福感影响较小甚至会有积极影响(Knight 和Gunatilaka,2011)。不公平的不平等是因为机会不均等导致的,如身份差距、腐败问题、社会阶层固化等,这些不公平感会给幸福感带来负面影响(Alesina 等,2004;Knight,2017)。分别来看,一方面,公平的不平等对幸福感可能有正向影响,Knight 和Gunatilaka(2011)等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对幸福感有正向影响,即不平等程度越高幸福感越高。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因为更有能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的收入水平增加较快,这种类型的收入差距扩大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是积极的,也可以用收入的“示范效应”来解释①所谓“示范效应”即当其他人收入提高时,居民会预期自己的收入水平也会提高(Senik,2004)。。这与心理学中的隧道效应相似,在一个隧道中有两条拥堵的车道,当一条车道的车移动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所有车道都会移动的乐观期望。以上实证表明,收入差距也可能对幸福感有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人们受到传统思想“不患寡,患不均,更患不公”的影响,往往对不公平更加敏感(阳义南和章上峰,2016)。龚峰(2017)认为处于不利环境的个体面临的机会不平等程度较高时,可以通过努力缩小机会不平等。但当努力不平等也出现时,机会不平等就会产生,所以他强调要弱化外部环境,提高努力的回报率,完善收入公平分配机制,为弱势群体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命运提供机会。这种机会不平等主要体现在阶层流动性、城乡分割和行业垄断等。
从阶层流动性与幸福感关系来看,Alesina 等(2004)认为不平等对幸福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内部流动性,如果社会流动性较高,平等可能就不重要了,因为收入公平性主要是由社会公认的努力程度和能力差异造成的。其基于“收入平等的偏好”和“未来收入不平等的预期”理论,将美国各州的“幸福”与欧洲国家的“幸福”与不平等、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和个体特征联系起来,发现不平等对幸福的影响在欧洲和美国都是巨大的、负面的和显著的,但欧洲的负向效应大于美国。这一论点表明,生活在流动性更强的社会(如美国)的个人受到不平等的负面影响较小。鲁元平(2012)研究阶层固化导致的机会不均等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结果发现阶层向下流动给幸福感带来的负向影响远远大于阶层向上流动带来的正向影响,阶层的固化降低了向上流动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也导致了不同阶层的机会不均等和机会缺失,进而对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户籍制度下的身份差异引起的城乡收入不平等降低居民幸福感,城市的外来移民幸福感受到与身份相关的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构建机会不平等感知指数(OIPI)作为解释变量,发现城乡分割与政治身份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Ordered Probit 回归结果显示,OIPI回归系数为-0.6334,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机会不均等对幸福有负向影响,这一结果在OLS 回归中依然成立。陆铭等(2014)认为减少身份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超过收入增加。实证发现身份收入差距下降1 单位所带来的快乐提升相当于家庭人均收入提高53.2%和人均住房面积增加29.9 平方米。在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中,主要是出生在农村的“新城市人”对身份收入差距表示不满。这种与身份有关的不平等具有不公平的性质。在户籍制度下,农村居民从出生开始就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在基础教育和医疗、劳动力市场回报等方面,农村居民相对于城市居民受到不平等对待,而且这种户籍身份导致的差异不是城市化能消除的,从而形成城市中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的“新二元结构”。
行业机会不均等导致幸福感下降。岳希明等(2010)使用Oaxaca-Blinder 分解方法,假定垄断行业实际收入是统计收入的1.2 倍,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部分达到60%,假定垄断行业实际收入是统计收入的1.5 倍,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部分达到70%。聂海峰和岳希明(2016)发现,行业垄断是收入不平等的第二大影响因素,这种不公正会导致消费者的福利减少,也会导致公众不满的情绪增加。
(二)政治因素与主观幸福感
从政府质量角度看,政府规模、政府效率、公共服务、官员是否腐败等因素显著影响了居民幸福感,这对幸福感的促进效应高于经济增长。
1.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养老、教育、医疗等)可能不会改变市场行为,但可以体现在居民幸福感报告中,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胡洪曙和鲁元平,2012;阳义南和章上峰,2016)。许海平和付国华(2018)通过实证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年龄来看,社保支出对老年人的幸福感影响最大;分地区来看,社保支出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影响要高于东部地区。Deaton(2018)探讨了不同的公共政策措施和不同的价值判断对幸福感的影响。考虑收入再分配时,收入优先主义者将收入分配给收入水平较低的年轻人和老年人,这样可以增加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收入水平,而功利主义者认为生活满意度低的中年群体应获得较高的权重,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增加收入获得较高的边际效用。殷金朋等(2019)使用双变量有序Probit 模型研究了公共教育支出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我国公共教育总投入和分项投入均对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但公共教育投入也产生了一定的负向隧道效应,对幸福感和社会阶层流动有负向作用。
2. 官员腐败行为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是直接的,通过影响人们对社会保障满意度、政府信任和收入分配不公平感等途径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容易造成居民幸福感的断崖式下降(Knight 和Gunatilaka,2011;鲁元平和王韬,2011;陈刚和李树,2013)。陈刚和李树(2013)发现腐败导致的不公平对居民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样本城市的腐败水平上升一个标准差,居民幸福感将会下降4.05%,这需要GDP 增长率上升6 个百分点才能弥补。
(三)社会因素与主观幸福感
幸福感与良好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和谐的社会关系会增加人们幸福感。有关实证显示,社会地位、社会关系(Knight 和Gunatilaka,2011)、社会信任程度、安全感和社交活动(Helliwell 等,2018)以及地区犯罪率(Dustmann 和Fasani,2014)等因素会对幸福感有重要影响。
从社会关系角度,Knight 和Gunatilaka(2011)认为家庭和朋友关系和睦与幸福感正相关;居住的城镇越和谐,幸福感越高。整体来看,农村居民的幸福感高于城市居民和移民,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带来了新的城市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这种社会关系对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负面影响。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受到城市高收入居民的影响,幸福感也在降低。从农村和城市的对比来看,农村居民更加注重和周围居民的和谐关系,这也是农村幸福感比城市居民更高的原因之一。地区犯罪率对幸福感有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情绪上的压力、焦虑等,影响人们的心理幸福感。Dustmann 和Fasani(2014)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犯罪率增加会影响当地居民的心理健康。犯罪率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地区犯罪通过增加人们成为受害者的恐惧心理来降低幸福感,因为犯罪率的提高,该地区的居民会处于一个压抑、恐惧的情绪中,降低生活满意度。鲁元平和王韬(2011)认为,我国的不平等有提高犯罪率的风险,而社会犯罪间接导致幸福感的下降。
(四)生态环境与主观幸福感
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污染会降低人们生活满意度,影响居民的健康和情绪,导致幸福感下降,其中主要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等(Van Praag 和Barsma,2005)。人们对主观可以感受到的污染敏感度高,这些污染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有些污染虽然实际存在,但不容易感受到,对幸福感的影响就会比较小。杨继东和章逸然(2014)利用2010 年CGSS 数据,将空气污染分为主观和客观污染,这样做的优点是区分人们主观感受到的空气污染和客观存在的空气污染,主观感受的污染大小和实际的污染会存在偏离,结果发现主观感受的污染对幸福感影响更大,人们愿意为降低13µg/m 的空气污染支付1114 元。储德银等(2017)使用2010—2012 年CGSS 数据和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主观空气污染对幸福感影响,发现环保模范城市的主观空气污染的改善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非模范城市内部较低等级的空气质量导致的主观污染会降低居民幸福感,因为污染严重的项目会安排在低收入地区,人们对污染的敏感度更高。另外主观空气污染对不同群组的研究表明,主观空气污染的改善和恶化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空气污染的改善对男性、高收入、城市幸福感作用大。因此,政府不仅要提高地区的空气质量,还要提高各类居民对空气质量的主观感受。Van Praag和Barsma(2005)研究了新西兰飞机场噪音污染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活在飞机场周围的居民幸福感要低于远离飞机场的居民。这些环境变量都是公共政策的潜在目标,随着公共干预对环境污染和绿地进行治理,该地区居民的幸福感会有一定的提高。
从社会特征对幸福感的影响看,收入是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主观幸福感受到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生态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在某些对幸福感有负向影响的因素在社会中占有较大比重时,收入增加不一定会提高居民幸福感,所以伊斯特林悖论有可能存在。在经济因素中,失业和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有负向影响。分组间和组内不平等来看,组内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分公平与不公平的不平等来看,不公平的不平等肯定会降低居民幸福感,公平的不平等可能会增加居民幸福感。政治因素中,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尤其社保支出增加,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官员腐败会降低居民幸福感。社会因素中,社会关系和睦、犯罪率低的地区居民幸福感较高。环境因素中,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总的来看,这些影响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
六、结 论
(一)主要结论
1. 伊斯特林悖论在很多国家得到验证,即某一时点上,幸福感和收入正相关,然而这种正相关关系在长时间序列中消失。在分析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可以发现,收入并不是幸福感的唯一因素,幸福感的这种变化受到很多因素共同作用。国内外学者从个体特征和社会特征等多个维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个体特征包括收入、年龄、性别、健康、教育等因素,社会特征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生态环境等。同时,需要注意很多因素不仅对幸福感有直接影响,还会有间接影响,如收入与健康有关,收入与幸福感有关,健康与幸福感也有关,在实证中需要考虑到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2. 除了以上因素对幸福感起到重要作用,还有一些因素并未在以往文献中被过多提及。经济因素中,消费作为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并没有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较多,缺少劳动者的就业环境、劳动力流动率等宏观因素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税收因素中,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也较少,我国实行的个税改革和减税政策也会间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社区邻里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较少,在社区关系中存在相对剥夺证据,居民更加关注自己在社区的位置,会将自身情况与社区的其他居民进行比较。借鉴社区邻里效应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
3. 在中国的实践中,对收入分配中公平或不公平的认识比收入分配本身更重要,人们对不公平的不平等更敏感,关注更多的是社会中权力关系不平等及其不公平的问题。因此,减少城镇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城乡居民不公平问题是我国政府目前需要做的。政府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制结构,减少垄断、腐败等不公平的行为,适当增加公平的不平等的激励机制,并促进政府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公共服务支出中,增加老弱病残群体的社会保障支出,可以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二)研究展望
1. 幸福感不再是某一个学科就可以研究清楚的,幸福感影响因素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因此,幸福感研究需要将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不断的结合和发展。首先,测算幸福感的方法需要进一步创新,目前在幸福感测算中存在两个难点:个人是否有专门的目的,或一个人是否相信某件事有价值,即每个人获得幸福的需求不确定;影响幸福的因素比较复杂,很难说清楚哪种因素对幸福是最重要的,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其次,幸福感的学科交叉研究很有必要,已有学者从心理学、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的神经、基因对幸福感的影响。这些新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幸福感的来源,为找到影响幸福感的决定因素提供帮助。
2. 实证分析方面,可以使用面板数据研究幸福感的因果关系,显著的贡献是可以控制个体的固定效应,区别出个体不随时间变化且可能与幸福感相关的因素,还可以考虑过去发生的事件对现在幸福感的作用,如过去失业的疤痕效应(Scar Effect)。另外,幸福感实证文献中的数据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内学者使用最多的数据是CHIP、CGSS 和WVS 数据库,其中CHIP 和CGSS 仅有国内的数据,无法进行国际比较,而WVS 拥有一百多个国家的数据,但对中国的数据搜集不如CHIP 和CGSS 详细,需要考虑数据的国际比较问题。
3. 为什么要提高居民幸福感以及幸福感提高可以带来什么益处的研究文献较少。在仅有的一些文献中,Diener和Chan(2011)研究幸福感增加对身体健康状况的正向影响,快乐的人有更强的免疫力、更少的炎症和心血管疾病。Clark 等(2008)研究幸福感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认为低水平的生活满意度会增加夫妻离婚和分居的可能性。幸福感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Oswald 等(2015)发现幸福感与生产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幸福感提高使实验中参与者的生产效率提高12%。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带来收入的提高,也可以增加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收益。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幸福感对政治参与、政治支持、减少犯罪的影响(Liberini 等,2017)。因此,研究幸福感影响因素,进一步提高居民幸福感,既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也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身体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