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之二)
黄 荭
南京大学
母亲和堤坝的故事
1950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掀开了杜拉斯自传叙事的冰川一角,堤坝的故事浮出水面,但所有的地名还是模糊的,母亲和儿子约瑟夫、母亲和女儿苏珊娜,尤其是苏珊娜和若先生(Monsieur Jo)的关系也没有明朗。需要迂回地进入:“其他的进展本来可以出现,其他的运行,在处于我们这个位置的其他人之间,有着其他的名字,其他的时限本可以生成,更长一些或更短一些,其他的充满遗忘、向遗忘垂直下坠、猝然进入其他记忆的故事,其他的有着无尽的爱的长夜……”[1]1954年的小说《成天上树的日子》和1965年的同名戏剧照亮了母子关系,但作为地点的东方已然不在,除了书名中的“树”让人联想到暹罗茂密繁盛的森林。
自身经历的故事就是一个结束不了的故事,“拔不出的泥潭”:
不过,在这讲述共同的关于毁灭和死亡的故事里,不论在爱或是恨的情况下,都是一样的,总之,就是关于这一家人的故事,其中也有恨,这恨可怕极了,对这恨,我不懂,至今我也不能理解,这恨就隐藏在我的血肉深处,就像刚刚出世只有一天的婴儿那样盲目。恨之所在,就是沉默据以开始的门槛。只有沉默可以从中通过。对我这一生来说,这是绵绵久远的苦役。我至今依然如故,面对这么多受苦受难的孩子,我始终保持着同样的神秘距离。我自以为我在写作,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曾写过,我以为在爱,但我从来也不曾爱过,我什么也没有做,不过是站在那紧闭的门前等待罢了。[2]

杜拉斯的母亲
杜拉斯一直在等待,无望地等待,等待母亲如春风的手抚摸她的秀发,但母亲的目光越过她的头顶,只有大哥,永远的大哥。从杜拉斯的第一部小说《无耻之徒》(1943年)开始,她的作品就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始终萦绕作者的三角关系“女儿-儿子-母亲”也在此形成。我们在《平静的生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成天上树的日子》《伊甸园影院》《情人》和《中国北方的情人》中都不难找到极度偏爱长子的母亲、放荡无耻的大哥皮埃尔的影子。小哥哥保尔或许是杜拉斯童年唯一的慰藉,他让杜拉斯体会到了贫穷却自由的童年。在那里,母亲不管他们,兄妹俩四处乱跑,爬树、抓鸟、猎猴子,像当地人一样生活,讲越南话,和越南孩子一起玩耍。自然的美景、殖民地的阳光、各种气味和颜色深深地印在了玛格丽特的记忆里。但这份美好是脆弱的、短暂的,被大哥的霸道和母亲的不幸淹没、窒息了。
母亲一直是杜拉斯挥之不去的主题。照片上年轻的她面容姣好,目光中有一抹散不去的愁绪和一定要战胜命运的坚定,看上去更像一个母亲,而不是一个女人,痛苦已然写在她的脸上。1904年11月24日,师范毕业刚当上老师的玛丽·勒格朗(Marie Legrand)和一个从印度支那回法国休假的小学教师费尔曼·奥布斯居尔(Firmin Obscur)相遇并结婚,婚后不久夫妻双双去了印度支那任教。1905年3月10日,玛丽成为西贡市立女子学校的一名临时教师,费尔曼仍在嘉定师范学校教三年级。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费尔曼就染病被遣返回国治疗,并于1907年2月5日去世。丈夫的离世对玛丽打击很大,她也病倒了,担心回印度支那会跟很多在殖民地的白种人一样,受到各种来势汹汹的地方病和传染病的侵扰:疟疾、麻风病、肝炎、痢疾、鼠疫、霍乱……但她还是在1909年12月1日回到了西贡,第二天就去了女子学校上课。是出于对殖民地教育事业的无私热爱?责任感?她无法忍受一个孩子因为太贫穷、因为买不起书本和文具而不能上学。因为她坚信只有教育才能改变命运。抑或是跟她丈夫的姓氏一样,有什么其他“晦暗不明(Obscur)”的原因?比如爱情?
人们只知道,1909年10月20日,亨利·多纳迪厄(Henri Donnadieu),三等教师,嘉定师范学校年轻英俊的校长,娶了同事奥布斯居尔的遗孀玛丽·勒格朗为妻。当时,他的前任妻子阿丽丝去世才5 个月,给他留下了两个儿子:让和雅克。两颗孤独的灵魂撞出了火花,希望开始“新生活”,重组新家庭?还是两人早已有了私情?从保存在亨利·多纳迪厄档案里的一封匿名信中,可以读到某种居心阴险的告密:“这个男人让妻子不明不白地死在西贡,他有家丑,情妇怀孕了,妻子必须消失,情妇变成了多纳迪厄夫人,事情自然也就不会败露了。”玛丽和亨利的第一个孩子皮埃尔是他们结婚一年后出生的,那么匿名信中未婚先孕的指控便不攻自破。但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晦暗不明(Obscur)”。
1911年12月23日,圣诞节前夕,亨利和玛丽迎来了第二个儿子保尔。1914年4月4日,玛格丽特的出生让父亲很高兴,但这一年也是多事之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亨利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急性阑尾炎、双侧性肺炎、痢疾和慢性疟疾,唯一的好处或许是疾病让他躲过了上前线当炮灰的厄运。再度回到印度支那,亨利被委派到东京地区,负责有“热带巴黎”之称的河内的小学教育,之后又被派往金边。1920年12月31日,他们搬进了一栋豪华的巴洛克风格的公务员官邸,玛丽也顺利地找到了公职,很快被任命为诺罗敦学校的校长。但亨利越来越感觉体力不支,1921年3月,病重卧床,4月被遣送回国急救,12月4日离开了人世。玛丽又一次成了寡妇,这次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分别是11 岁、10 岁和7 岁。处理完家事和遗产问题,1924年6月5日,带着三个孩子,玛丽回到了西贡。她在途中还不知道将去何处任职,她希望是西贡,最好是河内,而等待她的任命却是金边,她给印度支那总督写了一封充满绝望的信:
如果我是孤身一人,我当然很乐意到柬埔寨就职,因为我曾在1921-1922年间任诺罗敦学校的校长,我非常喜欢我的职业。但是我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儿子分别是14 岁和13 岁。他们已经结束了六年级的课程,柬埔寨根本无法让他们继续受到教育。
……
我二十几岁起在殖民地工作,我对于交付给我的工作,我在儿童教育方面一直是恪尽职守的,而现在,正是我自己的孩子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他们的前途不应该受到影响。[3]
总督收到信后,让殖民行政当局进行调查。柬埔寨小学的校长发了封电报给西贡,说多纳迪厄夫人“不论在诺罗敦学校还是在考试委员会,都声名狼藉”,只要有她在,就有“混乱和不团结”。第一次,玛丽感觉遭到了“自己人”的背叛,她被陷害了,她想和同事评评理,但所有人都躲着她。一个人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城市生活,没有面对面的对抗,有的是暗箭难防,告密、诽谤和指指点点。她的疯狂和偏执或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母亲害怕为国家做事的人,公务员、财政部官员、海关官员,所有以法律名义做事的人……她总觉得在他们面前,自己是错的。”[4]最后是总督帮了她的忙,她被调往永隆,任女子学校的校长。但母亲也没有真正融入永隆的白人圈子,她是寡妇,个性太强,嗓门太大,又爱抱怨,还爱提要求,喜欢指手画脚教训人。玛丽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做枯燥乏味的公务员,按资历一点点晋级。她开始幻想发财,她穷怕了,她一辈子都认为只有金钱才能带来尊重和幸福。在不停地写信要求之后,她终于得到了那笔期待已久的寡妇抚恤金,她卖掉了河内的那栋房子,加上微薄的积蓄,头脑发热地开始筹备一项宏图伟业:她要买地,她要成为太平洋稻米女王。
玛丽一心想买的“特许经营地”其实是法国行政当局从当地农民手中抢来的,然后转手卖给做“地主梦”的白人。1927年3月28日,印度支那总督颁布了一份通报,允许教师参与国有土地的竞标项目,这对玛丽·多纳迪厄来说绝对是利好消息,她又给相关部门写信,一遍遍强调自己的情况,她要一块地,一块很大的地,她可以等。
玛丽终于等来了她的地,柬埔寨一块850 公顷的地和一片位于象山与大海之间的森林。因为玛丽没有贿赂土地管理局的官员,他们给了她一块太平洋岸边备受海潮侵蚀的盐碱地。太平洋的海潮一来,地里的收成旦夕之间就荡然无存,只有竹楼孤零零地杵在这片巨大的沼泽中央,玛丽带着孩子,撑着船,巡视着她的这片荒芜领土:“一年当中有6个月,这块地都泡在海水里。而她为了这样一块地,付出了20年的积蓄。”[5]但玛丽不认命,她要再次向命运抗争。她抵押房屋、购买木料(红树的树干)、雇当地农民修筑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她自己也干。“我们招来了100 多个工人,堤坝在我母亲的监督下造起来了,正好是在旱季。不幸的是,堤坝给涨潮时躲在泥沙里的螃蟹啃噬一空。”[6]堤坝被毁,稻田被毁,玛丽也被毁了。周围是令人绝望的平原,单调而呆板,吊脚楼孤零零地立在海滩中,没钱翻新的屋顶有白蚂蚁不断落在床单上、饭桌上。饭是有得吃,只有米饭和涉禽肉,千篇一律令人作呕。平原上不断有光屁股的小孩玩泥巴,因吃青芒果害了霍乱一茬茬死去,再一茬茬出生。死掉的孩子被父亲埋在泥土里用脚踩平。多纳迪厄一家一无所有,债台高筑。玛丽并非唯一受殖民地地方行政官员欺骗的人,“胡志明市的殖民档案有这方面的记录。一共有几十个人,都买了这种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在坚持不懈地与绝望作斗争,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他们用泥沙和粗木修筑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在放弃以前他们都反抗过。他们甚至试着申诉,不过一直毫无结果”[7]。

玛格丽特和母亲,摄于20世纪30年代初
堤坝于是成了不公正的现实给杜拉斯打下的最初也是最深的烙印。杜拉斯的毁灭感就源于母亲的被毁,她的家园、她的亲情,她生存的世界已被毁灭。在母亲买下的那座每年都会遭到季风和潮汐侵袭的小楼的平台上,她常常梦想“财富与奢华”,而“傍晚出奇的安静,太阳西下,消失在山的后面……”[8]一起消失的还有少女玛格丽特对生活的热望与信心。
所以她一开始就不相信爱情,甚至不承认它。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苏珊对若先生有的只是羞耻感,她成了交易的对象,而情人则成了金钱的化身。“由于各种原因,我的一生充满了耻辱。”[9]这种羞耻感是家族和社会灌输给她的,出于白种人的倨傲,母亲、大哥还有苏珊自己都排斥中国人(属于白人看不起的黄种人),但由于生活窘迫,他们无法拒绝他的金钱和钻戒的诱惑。母亲紧紧抓住中国人送给她女儿的钻戒时,双眼迸射出希望的凶光:只要有钱,生活就可以重新开始。可是生活并不能重新开始,母亲的青春与健康已经耗尽。在《伊甸园影院》这部戏剧中,母亲默默地坐在舞台的一隅,儿女们讲述着她的过去,生活已磨平了她的锋芒,她麻木了,熄灭了。曾经如此相信殖民主义的美梦,结果却遭到了无情的背叛和嘲弄,这种痛苦从此一直深深地锩刻在多纳迪厄一家的身上,也渗透到杜拉斯的全部作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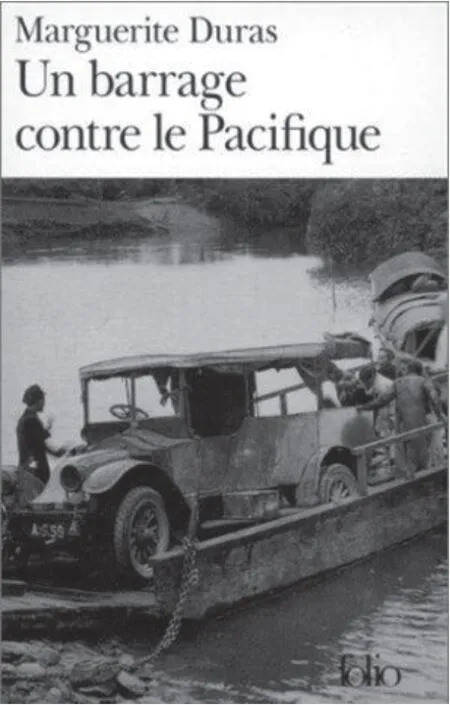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无耻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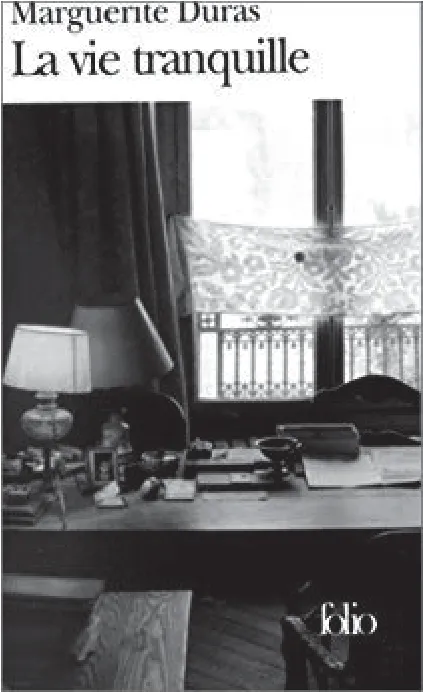
《平静的生活》
和母亲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死死纠缠着杜拉斯的生活和作品的另一个人物是“大哥”皮埃尔,她恨他、嫉妒他,因为他,她有一种被母亲抛弃的感觉。杜拉斯最初的两本小说《无耻之徒》中的雅克和《平静的生活》中的热罗姆身上都分明有“大哥”的影子。杜拉斯在《无耻之徒》中借女主人公“慕”之口说:“如果没有雅克,她母亲也许会留下她。无论如何,母亲不会这么快就抛弃她,仿佛在无意识中卸下包袱。母亲不自觉地在大儿子周围继续制造真空,直到她在完成对其他儿女的责任以后,只剩下这个儿子去全身心地爱。”[10]作为不受宠的孩子,“一想到哥哥,她就感到奇异的痛苦,疼倒不是太疼,但无法忍受,像脓包一样在她体内抽搐”[11]。大哥不仅独享了母亲特殊的爱护,还是个“败家子”。在《平静的生活》中,“热罗姆挥霍了我们的所有家产。因为他,尼古拉一直都上不了学,我也是一样,我们永远也没有钱走出布格,这也是为什么我还没有出嫁的原因”[12]。
大哥是压抑玛格丽特和小哥哥生存的阴影,“母亲的殴打和大哥的殴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大哥的殴打更疼,更让我无法接受。每一次,我都觉得他简直要把我杀了,我不再是愤怒,而是害怕,害怕我的头会掉下来,在地上乱滚,或者头还在,但是疯了”[13]。他对她进行不仅是肉体上的暴力,还对她的心灵造成了不可愈合的创伤。他也殴打小哥哥,不让其和妹妹亲近。他一边挥霍妹妹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金钱,一边嘲笑中国人的愚蠢和笨拙,让妹妹觉得自己堕落、肮脏、罪孽深重。玛格丽特要反抗,“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我想要制服他,哪怕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目的是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她所爱的对象搞掉,把她的儿子搞掉,为了惩罚她对他的爱;这种爱是那么强烈,又那么邪恶,尤其是为了拯救我的小哥哥,……大哥的生命把他的生命死死地压在下面,他的那条命非搞掉不可,非把这遮住光明的黑幕布搞掉不可,非把那个由他、由一个人代表、规定的法权搞掉不可……”[14]有大哥在,杜拉斯就只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受到压抑和摧残。只有“杀死”大哥,用刀或用文字,杜拉斯才能摆脱恐惧,走出童年的阴霾。
在《情人》这部自传色彩更浓的作品中,“大哥”的形象更加暴露无遗:“他就是那么一个人,贼眉鼠眼,嗅觉灵敏,翻橱撬柜,什么也不放过,一叠叠被单放在那里,他也能找到,藏东西的小角落,也发现被翻过。他还偷亲戚的东西,偷得很多,珠宝首饰、食物,都偷。他偷阿杜,偷仆役,偷我的小哥哥。偷我,偷得多了。”[15]母亲也不得不面对这个让她伤心欲绝的现实:她最看重的长子不学无术,成天游手好闲在外惹祸,不是赌博欠债就是在烟馆吸食鸦片,甚至肆无忌惮地偷窃,仗着母亲对他的溺爱和毫无底线的迁就,蛮横霸道,一副殖民地害群之马厚颜无耻的嘴脸。母亲知道儿子已经误入歧途,在殖民地任何教育都不可能让他走回正道,1929年,母亲痛下决心把长子送回巴黎,希望他重新上学,有朝一日可以考取机电学校,但这一切都是徒然。他混世魔王一样消磨着日子,拉过皮条,二战期间曾经出卖过很多犹太人;后来母亲死了,他伪造遗嘱继承了母亲所有的家产,无所事事,继续赌博,很快败光了一切,包括那栋误传属于路易十四的古堡。一直到年过半百,他总算在海运保险公司谋得了一份信差的差事,有生以来第一次靠薪水过活,干了有15年。最后,他孤零零地死去,和母亲葬在一起,墓穴里没有其他人的位置。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