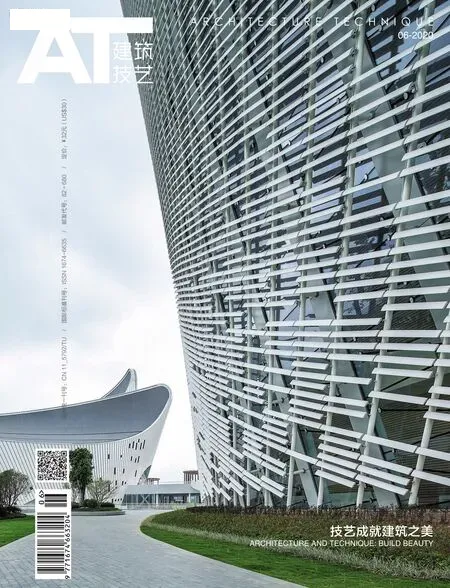细节中体现整体
黑川雅之提到过日本的“一期一会”阐述了巴舍拉的理念,认为时间是点状的,是由每一个瞬间串成的。Presence是一种“在场”,或者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的内心一动。这种微妙的瞬间带着某种神性,有着过去的记忆、未来的梦想,这一瞬也包含了整个时间轴。
回想起我在台湾农禅寺水月道场前的水池边坐着,光线正好,眼睛一闭一睁,一片落叶顺着水飘到我面前,我把它拿了起来……那么,水月道场的大部分并没有打动我,是它没有通过设计打动我吗?这是表象,底层的缘由仔细想来,还是它的设计打动了我。因为如果这不是一个和禅意有关的道场(道场周围有很多僧人,道场很静,水波纹都非常小),如果没有设计那个水池(哪怕水池不是为了那片落叶设计的),就不会有那片落叶,我也不会被那一瞬所震撼。这是一个可以“轻轻抓住”的整个世界。
记得我们院大楼准备拆除原址重建的时候,我在敲得七零八乱的现场,有种说不出的难过,似乎那不是一片废墟,而是许多人的青春。以前我最多的是待在这栋楼的七层,因为那里有一个安静的图书室,每当躲到这里,在大大的台面上摊开白色的拷贝纸时,图书室的朋友就会笑眯眯地问,又开始做方案了吧?这个迈耶风格的白色建筑有着动人的简洁的力量,以至于我后来固执地想我一定要在新的建筑里放一张最大的台子,然后郑重地摊开白色的拷贝纸,画一张温暖的记忆中的老建筑。就像是麦克阿瑟将军说的那样——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那一瞬间觉得,建筑不死,他只会悄然而去。
作为建筑师,只不过是去提供一个场所媒介给每一个人罢了。一念起、一念落,构成了因缘巧合,在不经意处最是动心。没有什么是可以留住的,时间可能并不存在,小到叶子,大到建筑都会转瞬即逝。
疫情期间,纽约有一幅不完整的李医生的画像(脸部被挖空),放在空旷的广场上,人们可以透过空荡的脸,看到远处的天空。当我们看向这个作品时,为什么会那么悲伤,因为看到天空这个“空”的东西时,那空白是被我们的思念和悲伤填满的。设计师要做的也许不是完全实体的设计,而是一个诚实、真诚的向导。
物质的存在客观而无所指,Presence是精神的存在即主观且有所指,随着一念的变动而变得飘渺。建筑可以“诱导”某种先验的认知,但只在一人之内和一瞬之间,所以强符号意义的纪念碑注定被祛魅,而轻轻抓住歧义性的建筑才有长久的Pres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