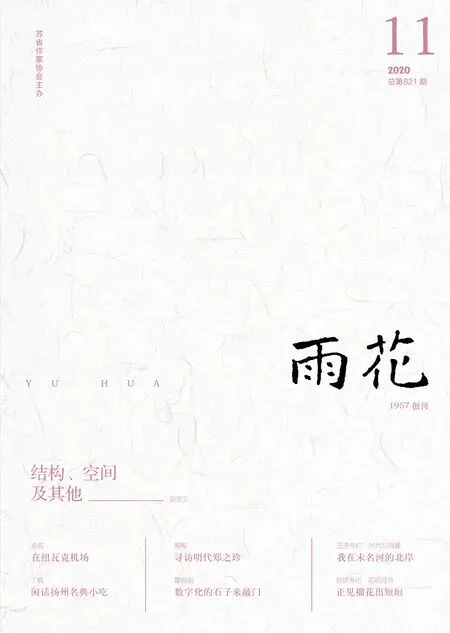摘酒师
山下静读
仿佛奔跑,需要仰望一下
即将到来的星空。
南太行止步,天空弯下它的身子。
仿佛大果榉张开了喉咙,
静默就如它委身的岩石,在夜晚
才出来散了几步。
松针从诗歌的词缝里落下,似乎在星空这个瓷盘子里
跳了一下,又回到泥土里。
一次穿针引线的缝补,已然结束。
仿佛温暖,已摊开在果农的手中。
“大果榉是做车轮的,僵子栎是上好的碳材,
现在,我侍弄这些苹果。“
仿佛,辽阔与空寂
找到了自己的根。
摘酒师
秋天深了,你的目光眯成了一条缝。
它们就要卸妆,大地摇曳,抖出
无限的可能。就连叶子,也逼出了最后的
骨血。孤单的领春木,早早地在舞台上
伸出了修长的手臂。
引领春天的人,用预言肯定着
一粒米、一粒麦子,风越来越厚,河床下切。
你需要跃下悬崖,在经久的深渊中,寻找
一朵花。
不是空气凤梨,也不是白酒草。一束黄金的光
穿过水晶峡谷——
仿佛阿炳的情欲被音乐
咬了一口。
你摘到了风的皱褶、断碑中
一个湮没的痛。就在九徽的位置,一个散音,
激起了一阵颤栗……胸中
渗出了溪流,山河,和灵魂的决绝
与青苔。
我想起汉代的一条河竟然叫冥水,如今
早已抹去了。日月向西,还是说说人间吧,摆渡人,
我们有相同的喉咙,还有
难得的神。
注:摘酒师,酿酒师的古称,断花摘酒,对酒分级的技艺。
当蓬草遇到另一个被吹响的自己
他从夜色的水面上走过来,他从
水上的栈桥走过来,内心透亮。他可能
刚刚被擦着水面的风拍打过,星星落在水里,词语
轻微游动。他和岸边有了一丝默契,他甚至
伸出手摸了摸岸边。
灯掉到水里,沉默的影子一直还亮着。一张无根的
面孔,在水波中,灌满了风。
早安,云端
一定有早起的鸟鸣,
打扫过庭院。一定有耕牛,犁过
云朵的自留地。一定是卧在房顶的猫,
眼睛里空旷的图书馆。
一定有一座接引的拱桥,桥下有水,水上
有双翼的蜻蜓悬停了一会儿。摆渡车也可以
逗留一下,过了桥头发就白了,好像来到了
另一个人间。
抱着云睡觉的人,偶尔闪过
无数人仰望过的苍穹。
一个冬日的下午
你确定要睡在树荫下,身子就会
和树干的影子一样长。
阳光透过玻璃窗,暖暖地
照着一排排的书脊,它们
是安静的。
风,从现在开始,都带着出生的记号。
可以玻璃一样地刮着。
我的老花镜依然是真诚的,词语依然
带着荒芜,浇铸的时间到了……
一首诡诗。
不确定的一声问候之后,他们又回到一枚
黑瘦而又皱纹满面的核桃中。
只有这一天是清明的
我摸到了门把手,扭动
这是向内打开的门,这是墓地。
风来以前,父亲坐了起来,接过
我递过去的纸烟,他的胡子
像麦地里的杂草一样长。
只有它们,还在守护一个
苍老的词,黑白的词。生者追逐着死者——
只有这一天,我们会
回到出生地,和地下的人握手、哭泣,
在自己体内,再钉下一枚钉子。
像是苏醒过来的那个人,
和我调换了一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