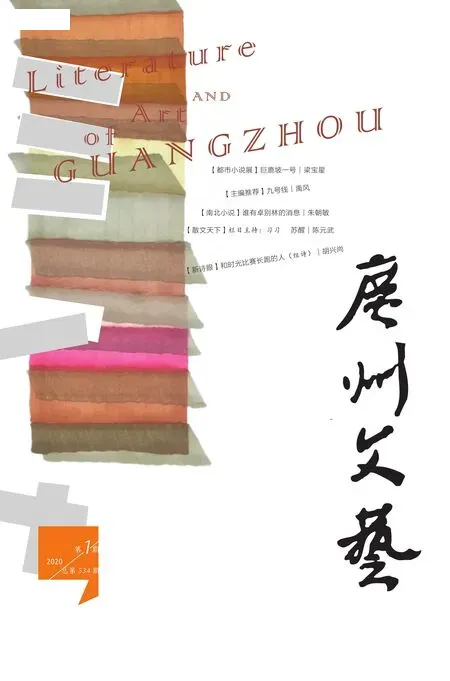巨鹿坡一号
梁宝星
1
从北京到东京要坐四个多小时的飞机。出发时是北京时间十一点三十五分,飞到东京上空的时候我把手表调为东京时间,那时是十四点五十五分。
父亲来机场接我,一年不见,他又沧桑了许多。他把我的行李提到后车厢,载着我前往他和母亲在东京市区租住的公寓。他问我为何突然来东京,我坐在副驾驶座看着街上的广告屏幕没说话。东京下雨,广场屏幕上的画面被雨打散了,在光洁的地面上胡乱流淌。我熟悉东京,十七岁之前,一年当中我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生活在这里。十七岁那年,我去北海道疗养所治病,在那里度过了四年时间,随后便直接回国读书了。我在国内和外婆住在一起,其间再也没有来过东京。这次来日本,不是为了看望我的父母,我要去的是北海道,那是一趟势在必行的旅程。
我把车窗摇下来,雨小了一些。东京比北京要暖和,街道拥挤的缘故,海水削弱了西北风的缘故。父亲不时侧过脸来观察我,他十分谨慎地开着车,跟我说了许多这些年发生在东京的事情,对于他正在经营的海鲜市场只字不提。
我的父母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四周的风景我依旧感到熟悉。母亲撑着雨伞走来,问我一个人来东京,外婆在家里谁来照顾。我说表妹在北京上大学,我出来的这几天,她住我们家。母亲看我闷闷不乐的样子,明白我这次来日本的目的不简单。她盯着我把饭吃完,然后领我到楼上的房间。
房间保持着我离开时的模样,连尘埃都没有积下。母亲说她经常到房间里来翻我的东西,特别是跟父亲吵完架十分想念我的时候。她比父亲老得快,经常发愁的缘故,发愁的时候她就打电话到北京找我说话,好几次她都说在东京太孤单了。他们想找机会放下海鲜市场的生意回国,然而又一年过去了,他们还没放下。他们喜欢小孩,特别是女孩,那样的生活会热闹一些,但是他们不敢再给我生一个妹妹,害怕生出一个像我这样的怪物。
看着房间里的一件件东西,过去的画面不断在我脑海中翻滚,这几天我都生活在回忆与现实不断切换的模糊状态下。十二月十五日,我在北京的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淑子告诉我玉子去世了,去世之前她一直在呼唤我的名字。
“你该去送送她。”淑子说。
站在窗边能够看见繁华的东京市区,车辆像神经点在立交桥上穿梭。雨还在下,不知要下到什么时候,这个时节,北海道已经大雪纷飞了。
我第一次去北海道,同样是在下着大雪的寒冬。我和父母从东京出发,坐了好久的电车抵达青森县。那时我精神状态不好,整个人昏昏沉沉,不停地睡去又一次次醒来,以至于东京到北海道的距离在我印象中变得无比漫长。
从电车里出来,坐船渡过津轻海峡,再坐电车前往札幌,穿过札幌市还要往北走二十多里路。父亲开着租来的汽车在林间水泥路上疾驰,后来他说那是他开过最快的一趟车,走过最长的一段路。他当时以为我要死了,顾不上安危,忘记了饥饿与疲惫将我带到巨鹿坡一号。我被北方的寒风吹醒了,摇下车窗看见父亲在跟保安说话。他急匆匆交代我的病情,恳求保安尽快放我们进去,保安依旧有条不紊地登记着我们的信息。我看到了被大雪覆盖的北海道,漫山遍野都是白色,只有后面的水泥公路留下黑色的车辙。
进入疗养所时我已经清醒了许多。医生拿着手电筒观察我的五官,护士测量我的血液。母亲在旁边跟医生讲述我发病时的症状,在她口中,我发病时浑身发抖,眼睛泛白,口吐白沫,怎么叫都没有反应。这些症状是否真正在我身上发生过,我无从知晓,我只记得我沉睡过去了,醒来时已经身处医院,医生正在向父亲介绍坐落于札幌北部的巨鹿坡一号辐射病疗养所。
那是一所占地面积很大的疗养所,有三座六层高的大楼,分别属于癌症科、变异科和调理科。医生让母亲安静下来,他观察了半天我那只有四根手指的左手,然后让护士带我到变异科去等候进一步治疗。辐射病康复治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父母很不情愿地把我留在那里,等待医生将我体内被损害的机能重新激活。
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疗养所接受治疗,开始的时候父母十分频繁地来看我,我身体渐渐恢复以后他们便很少到北海道来了。在巨鹿坡,那个四周布满密林的山地里,安静带走了所有的痛苦和烦恼。那年我十七岁,身体已经不再生长,身高定在172厘米,左手依旧是四个手指,除了无法完成必须要五个手指才能做的事情,我尚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我的病情较为稳定,只要每天注射维生素和抗体,食用抗辐射食品,身体均能维持在健康状态,因此,护士对我的看管不严。白天我会和调理科的人到山林里去散步,面对漫山遍野的雪我并不觉得单调乏味,我喜欢在山坡上晒太阳。护士不允许我们在太阳底下晒太久,因为太阳光带有辐射。但是北海道太冷,再者,长时间生活在被树林覆盖的地方,太阳光实在诱人。遇见淑子的那天,她和我一样穿着厚厚的衣服,头戴一顶针织帽站在山坡上贪婪地吸收阳光。护士在不远处使劲招手叫我们回病房休息,我们假装没看见,淑子拉着我的手逃出护士的视线跑到山的另一边去了。
“你怕不怕山上有熊?”淑子问我。她比我大三岁,但是她身体瘦小,丝毫看不出她已经二十岁了,她看上去像个十五岁的小女孩,“在富良野和知床的森林里,随时都可能碰到棕熊。”
我说这里不是富良野,也不是知床,这里是札幌,再说熊不会吃不健康的人的。她问我得了什么病,我挣脱她的手,摘下手套,露出左手。她有些吃惊地盯着我的左手,确认那根消失的手指并不是因为意外而被截断的,而是实实在在忘了长出来。“你是变异科的?”我点点头。“你不是日本人?”我又点点头,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你日语说得很好嘛。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日本,但是在这家疗养所我认识了几个外国人,一个是白俄罗斯人,一个是韩国人,你是第三个,中国人。”
淑子所说的白俄罗斯人是阿拉多夫,一个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中被灼伤的农夫,而韩国人就是刚去世的玉子。
2
清晨,我醒来的时候父母已经到海鲜市场去上班了,早餐放在一楼餐桌上。我给淑子打电话,告诉她我已经顺利抵达日本,正准备北上,会在天黑之前抵达新千岁机场。吃完早餐,到外面去散步,这个地方好些人曾经认得我,现在如果不去看我的左手,大概不会想起我就是当年那个中国男孩。
海鲜市场就在附近,跟公寓相隔两条街。母亲在跟员工讨论什么问题,看见我走过去,她被吓了一跳。她不希望我到海鲜市场来,因为我以前对海鲜的腥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我曾告诉母亲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在巨鹿坡的时候我体内已经培养出了抗体。母亲还是担心我旧病复发,她和父亲永远无法忘记一九九五年夏天,四岁的我哭着从幼儿园回来问他们为何我只有九个手指头的那个情景。父亲当时说他们是在海上生下的我,我的一根手指变成白鲸游到大海里去了。当我自豪地把这个故事告诉幼儿园那些说我是怪物的小朋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而仰慕我,反而嘲笑我是“鲸鱼男孩”。事实上,我的病情是母亲怀着我在海上作业的时候,被海上的辐射渗入体内造成的。那时候太平洋有核弹引爆试验,海洋污染严重,而我的父母对那片寂静的海域毫无警惕。
我告诉母亲我要去一趟北海道,已经订了下午的机票。这些话原本只要在电话里交代清楚或者留纸条告知他们即可,我的路程太匆忙,还没跟父母好好说会儿话就要离开,为此我决定到海鲜市场亲自跟他们说明白。虽然我已经二十五岁,在他们眼中我依旧是个需要被人关照的男孩。父亲说他可以送我到机场,我拒绝了。我想坐地铁去机场,我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准备面对玉子的死。
其实玉子不是韩国人,她是个地道的日本女人,只是嫁到韩国后入了韩国国籍。最初认识玉子,是通过淑子的介绍。由于不能使用电子通讯,图书馆成了巨鹿坡最受人欢迎的地方。在那个狭小的图书馆里,图书被翻过好多遍,皱巴巴的。在漫长而枯燥的日子里,这些书都是大伙儿消遣时间的道具。跟玉子见面那天,她坐在灯下,正在看太宰治的小说。这个四年前还是三十四岁的女人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大,我从淑子口中得知她是癌症科的,在医院放射科工作的时候由于机器出现故障导致辐射外泄,她患了子宫癌。玉子见到我们十分高兴,她把书合上,跟我们到图书馆外面去喝茶。她喜欢向我们打听山林里的景致,说她来这个地方一年多了,还没有到山林里去过,每天只能通过房间的窗口往那边眺望。
“你在这里一年多了?”我问。
“实际上,我可能要在这个地方过完这一生呢。”玉子望着不远处被雪覆盖的山林说,“我的一生并不长久。”
“我们不能老这样子,”淑子说,“这里所有人都死气沉沉的,我们不要跟他们一样,我们要过得开心才是。”原本是灾难的受害者,在这个地方却成了幸运儿。淑子的心境比其他病人开朗,她牵着玉子的手走进图书馆,告诉玉子不要老看太宰治的书,应该多读读海明威的小说,毕竟,人是不能被打败的。
玉子对我这个刚来到巨鹿坡的男孩给予了足够多的关怀,她告诉我在医院要遵守规则,告诉我怎样才能讨得护士的欢心,“跟护士关系好的话,她们打针的时候会温柔一些,在限制出行方面也不那么死板。”她还给我介绍她家乡长野县的景色和美食,跟我说韩国女人多么温柔。
抵达机场,飞机误点,我在候机厅里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那些飞走又飞回来的庞大机器,有些心慌,再过两三个小时我就要回到那个熟悉的北方了,回到那个充满死亡与病痛的山林里。上飞机之前,淑子给我发来短信问我到哪里了,说她从福岛出发已经抵达北海道。淑子比我更早离开巨鹿坡,她是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受害者,所幸她没有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害,她在调理科只待了两年时间就离开了。我在巨鹿坡的最后两年,淑子来看过我两次。两次都是在酷冷的冬天,她说她喜欢北海道的冬天,四处白茫茫一片让人觉得干净舒适。虽然只在巨鹿坡住了两年,这两年时间在她的一生中足以造成深远的影响。那片看似寂静的山林里,病人每天面对的都是死亡。早上六点,往往是天还没亮,疗养所西门的水泥公路上就会有一辆白色卡车开进来,那些在夜里死去的人被抬到白色卡车里送到两公里外的殡仪馆,病床留给后来者。许多人像我一样,每天早早醒来,等候那辆白色卡车开进来,又看着它离开,有时候卡车会带走两三个死者。午后我们就会留意谁没有出来散步,那些没有出现的人很可能就是在夜里死去的人。玉子每天早上都坐在癌症科大楼前的花坛边看一会儿书,好让楼上的我们知道她尚未被白色卡车运走。我们都害怕死亡,玉子也一样,她在那张病床上抗争了将近十年,最终还是被白色卡车带走了,而我正在前往巨鹿坡参加她的葬礼。
3
飞机经过漫长的奔跑升上了天空,建筑物变得越来越小,整个东京城都在慢慢变小,仿佛只是一片堆满石头的平地。穿过云层,飞机往北驶去。这是我两天里第二次飞上天空,第二次进入云层,仿佛置身于皑皑白雪当中,不见人影。
我还记得阿拉多夫偷来保安的雪地车带我和淑子、玉子到冰湖去玩耍的那个早晨。那是我在巨鹿坡度过的第二个寒冬,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雪,宛如大地被盖了一层一米厚的棉被。我们帮清洁员打扫院子里的雪,淑子说她知道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湖泊,那里的景色非常美,阿拉多夫便建议我们到那里去看看。阿拉多夫是个开朗的东欧人,那时他的双腿已经不是特别灵活,他每天早上绕着癌症科大楼跑步,以此来跟肌肉萎缩作斗争。他用生硬的日语跟保安说了半天也没借到停放在医院门口的雪地车,便趁保安去喝水的时候悄悄把车开走了。他得意地呼唤我们上车,“伙计们,是时候离开这个鬼地方去见识一下大自然的魅力了。”凌乱的胡子遮住了他的嘴巴,白气透过胡子从他嘴里冒出来。
公路被铲雪车清理过后又铺了一层雪,淑子和玉子为能够开车出去走走而感到兴奋,因为暴风雪,我们在医院里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困在病房的时间里玉子的精神状况很差,护士说她已经出现幻觉了,总对着镜子说话。玉子曾怀过一个小孩,只是那时年少,才十七岁,因为恐惧,她的男友带她去做了引流,没想到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怀孕。她不是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她是在和她尚未来得及降临这个世界便死去的孩子说话。她曾跟我说过,假如当初把小孩生下来,小孩的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因此,她做梦的时候时常会梦见我,梦见我敲开她的房门叫她妈妈。她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有点难为情,她希望我理解她。我当然理解她,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是孤独的。
湖面结了厚厚一层冰,冰上又堆了厚厚一层雪,几个当地人在雪上面行走,拖着沉重的双腿慢吞吞地从这边去往那边。我们把车停在湖边,然后跑到湖面上去玩耍,扒开湖面上的雪观看冰下静止的水。玉子很开心,忘记了身上的病痛,忘记了伤心事,沉浸在白色的冰冷的世界里。我们到树林里去找野兔,下了这么大的雪,兔子在雪地里跑不动,捉到手丝毫不费力气。阿拉多夫十分轻松就把一只灰兔捉住了,提着兔子的耳朵放在玉子怀里。回医院的路上,阿拉多夫不停地讲述过去他在白俄罗斯的生活,他感慨说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切尔诺贝利附近变成了无人区,只有那些变异的动植物在那里艰苦地生存着。玉子把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仿佛所有的力气都在雪地上花完了一般,她疲惫不堪。刚来巨鹿坡的时候,医生跟她说她最多只能再活两年,然而她不但挺过了医生诊断的时间,还多活了七年。
天空已经昏暗,大地银装素裹,新千岁机场上的灯光星星点点,机场像一块巨大的墨石。飞机平稳落地,空姐十分友好地帮我提行李送我下飞机。刚走到机场出口我就看见了淑子,她穿着一件黑色大衣,戴着粉色针织帽。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四年前,我从巨鹿坡一号出来的那天,她从福岛来给我送行。我们在机场喝了一杯咖啡便告别了,我回中国去,她继续留在日本。相比四年前,她成熟了许多,不再是那个活蹦乱跳的女孩了。她把我搂进怀里,然后捧着我的脸说我长大了,像个男人了。“这一天还是来了呢,”她哽咽着说,“听说她这两年过得很不好,癌细胞不断扩散,她原本不打算接受化疗的,担心死得太难看,后来可能是不想死,她还是接受了化疗,她没能挺过去。”
从机场到巨鹿坡的大巴一天只有三趟,我们错过了前面两趟,只好等下午六点四十五分那趟。机场外面的停车场上有几辆正在离开的公交车,其余熄火的车辆上已经铺了一层雪。我和淑子捧着热咖啡站在候车厅门口,望着久违了的景象说着各自的生活。淑子说她已经结婚了,生了个女儿,丈夫是一名环保组织人员,他们在福岛环保局认识,结婚以后她也加入了丈夫的组织,帮助那些在核事故中受到伤害的人。
“生活还过得去,每天都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女儿还算健康?”
“健康,没有受到我的影响,不过她不跟我们住,她跟爷爷奶奶住在乡下。”
“还是会担心?”
“当然会担心,主要是我现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有时候意外是不可避免的。”
大巴进站以后,我们相互依偎着往前走,这么晚还到巨鹿坡去的只有我们两个。上车以后淑子突然想起忘记买花了,“只顾着说话,把这件事都给忘记了呢。”她问司机能否等几分钟,她去买一束花就回来。司机看一眼空空的车厢,点点头说我们要在一根烟的时间内回到车上,不然他就要送一车空气到山里去了。
淑子牵着我的手往外面跑去,天又开始下雪,我们身上挂着绒毛似的雪花,天黑得深沉,灯泡已经尽力了,灯光依旧无法照得更远。我们在一个老人的摊档里买了一束兰花,这种花在北方较为难得,特别是在这样寒冷的冬天里。
“以前在巨鹿坡图书馆里,玉子偷偷养了一棵君子兰,那时候还不懂得把植物放在温室里,在这么冷的地方君子兰是不会开花的。”淑子挽住我的手臂,脸蛋贴着我的肩膀,“她非常细心地照顾那棵君子兰,时常坐在窗下盼着它开花,样子十分可怜。”
图书馆里的君子兰在最里面那排书架后面的窗台上,因为阳光不足,长得特别瘦弱。它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并没有死去,我离开巨鹿坡的那天它还在图书馆那个逼仄的角落里努力往太阳光的方向伸展。
4
大巴走了四十分钟的山间道路,终于来到了巨鹿坡。阿拉多夫在疗养所门口等候我们,他两条腿已经不能行走,只好坐在轮椅上。为了不让雪花落在身上,他蜷缩在保安亭的屋檐下,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头。他远远就张开了双手,呼唤我和淑子的名字。这个四十几岁的白俄罗斯人,在这个地方待了近十年。前往招待所的路上,我提着行李,淑子推着阿拉多夫,轮子碾压地上的雪发出清脆的声响。阿拉多夫说他要回白俄罗斯了,他非常想念他的家乡。在这个地方待这么久,完全是为了玉子,如今玉子已经死了,他也没有理由在这个地方继续待下去。我问他的病情如何,他说不是很乐观,我和淑子不好再问下去,三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过头来问我在中国过得怎样。
“我修完了大学的课程,正准备找工作。”
阿拉多夫对此表示满意,他说,“玉子去世前还叨念着你,你好久没有写信来了,我们困在这个地方也不清楚你过得怎样。”
四周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招待所还是四年前那个样子。我和淑子住一个房间,把行李放下以后,趁医院饭堂尚未关门,阿拉多夫带我们到饭堂去吃饭。阿拉多夫最大的变化是他不再有说不完的话了,他甚至变得沉默寡言。淑子为了不让气氛过于冷清,不停地问阿拉多夫这几年的生活状况。在阿拉多夫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得知在我离开以后,他和玉子过着孤独又乏味的日子。玉子依旧每天早上到癌症科大楼前的花坛边坐半个小时,以此证明自己并没有被白色卡车带走;阿拉多夫坚持绕着癌症科大楼跑步,直至跑不动。随着两人病情的加深,他们在治疗室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玉子接受化疗以后脸色日渐苍白,头发掉光了,轻易不会走出病房,阿拉多夫就摇着轮椅从三楼爬到五楼去看她。
“医生说一般人不能忍受化疗的过程,她的毅力胜于常人,遗憾的是,化疗并没能控制癌细胞扩散。”
吃过晚饭,我和淑子送阿拉多夫回病房休息,阿拉多夫在病床上躺下没多久便睡去了。我和淑子在大楼后面的院子里踱步,离开四年后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走进图书馆,光线不是特别充足,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很难要求它再明亮一些。玉子精神病发作的那个晚上,我们同样是吃过晚饭到图书馆去看书,看了将近二十分钟的书。玉子突然哭了起来,把脸藏在书本里,身体剧烈的颤抖着。淑子靠过去安慰她,被她一把推开了。她踉踉跄跄站起来,走到图书馆外面,门外大雪纷飞,她张开双手不知在寻找什么,她头发散乱,涕泪横流,样子十分狼狈。她说她儿子来找她了,他就在这个院子里头。之前我们都不知道玉子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她结过婚,生病后丈夫到巨鹿坡来过一次,她的丈夫是来跟她商量离婚的事情的,这件事狠狠打击了她。
图书馆里有一面照片墙,上面的人多数已经去世,我们四人的合照还在墙上。那是淑子离开巨鹿坡的前几天,我们约摄影师拍的。照片中的玉子端庄优雅,她挽着我的手臂,右手抱着那株瘦黄的君子兰,那时她已经把我当作她的儿子。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离开会给她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我走到图书馆后面,看见那棵君子兰在月光下如雕像一般悄无声息。我决定把这棵君子兰带走,带回东京,带回中国,让它在暖和的地方开枝散叶。
招待所有些简陋,房间里冷冰冰的,我和淑子都喝了一点酒才钻进各自的被窝。淑子说她曾想过回来这里做公益服务。她问我有没有打算到日本来生活。我摇摇头,说我不能在日本待太久,虽然日本是个宜居的国家,但总有一种不安的气息在这个国度弥漫,我从飞机里走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到这种气息了。
“其实,我选择到环保组织去工作正是因为这个,我们见识过真正的死亡,才懂得活着的意义。”淑子希望我到福岛去一趟,去看看她们为救助当地辐射病患者做的努力,“在福岛,环保组织人员是特别辛苦的,我们抵抗电子产品,抵抗核电,推销抗辐射食品,组织大伙接受治疗。虽然我们不是医院,向我们寻找帮助的人还真不少,大多是没钱去医院看病的低收入人群。好些人身上的病十分恶劣,要在这里,他们就应该被关进癌症科大楼。他们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希望,按时来取药片,跟我们反映自己的身体情况,汇报自己生活上的困难。”淑子爬到我的床上,钻进我的被子里,脸庞贴着我的胸膛,“有时候人真的很脆弱,但是只要有一股力量推着我们向前去,我们就会特别强大。就好像如果我们静止不动躺在地上,一群蚂蚁就能把我们吃掉,但是如果我们在高速行驶的飞机上,我们就是一颗子弹,我们能穿破任何东西。”
淑子在我的臂弯里睡去了,而我依旧没有睡意。那棵君子兰在桌子上静静地吸收着月光,就好像玉子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我和玉子的故事绝非偶然,在前往巨鹿坡之前我曾做过一个梦,梦到我并非我的父母所生,我是白鲸的孩子。来到巨鹿坡以后,我发现玉子就是梦中的那头白鲸。玉子对我关切之至,给我送吃的,给我织围巾,托她的护士从札幌给我带三文鱼寿司。别人认为玉子对我好是她的精神病导致的,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在和我相处的时间里,她一直都是那个真实的她,甚至真实得过于理智,以至于我要离开巨鹿坡的时候她没有因为舍不得我而不让我走。
成为一枚子弹,是否能够穿透时间和死亡呢?我爬起床,找来纸笔,坐在窗前写了满满一页字才回到床上。
天亮了,我始终没能闭上眼睛睡一会儿,窗外的景色一幕幕被阳光照亮。我看到了二世古雪山,它高高挺立,在十分遥远的地方,天气晴朗,它得以在窗外露出庄严的面貌。玉子曾说她最想去的地方是二世古雪山,想去那里滑雪,她没有滑过雪,只是觉得在雪上飘着会很自由。我想她肯定从后山、病房窗口或者图书馆天台上看见过二世古雪山,看到它如此美丽的影姿才想要到那里去。
淑子翻身醒来看我满眼血丝,为打扰到我睡觉而道歉,“晚上一个人冷冰冰的,所以我才爬到你这里来,害你整晚睡不好。”她走到窗边,戴上乳罩,又从行李箱里拿出一套黑色西服,她的身材已经变样,穿上西服也不显瘦。
“穿这么少,不会冷?”
“外面还要披一件大衣。”
我没有西服,找了一件黑色大衣穿上就出门了,和淑子去癌症科大楼接阿拉多夫,三人一起到楼下去吃了点东西才去告别玉子的遗体。淑子推着阿拉多夫,阿拉多夫捧着昨晚我和淑子在机场买的兰花,我捧着从图书馆带出来的那盆君子兰,我们走在通往殡仪馆的路上。阿拉多夫跟我们说,玉子的家属并不知道她已经过世。她去世之前嘱咐医院说不要通知家人,这样她会走得安心些。玉子的后事是阿拉多夫帮忙打理的,墓地选在殡仪馆后面的墓园。我在殡仪馆门前看到了那辆曾令我毛骨悚然的白色卡车,车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我们绕过白色卡车走进殡仪馆大厅,玉子的主治医生以及照顾了她好些年的护士也来了,我跟他们简单问候几句就去找玉子的棺木。大厅里停放着四个黑色的棺木,玉子的棺木在最里面。我把君子兰放在棺木旁边,端详起玉子冰冷的面容。她很瘦,皮肤是紫色的,圆碌碌的脑袋上只有几根黄色的头发,眼圈是黑色的,看起来像一只受伤的鸟。
淑子靠在我肩膀上哭了,受到她的影响,大厅里另外几个死者的家属也跟着哭了起来。医院和殡仪馆的代表陆续走进来,巨鹿坡有一个传统,为每一个死者举办追悼会,鼓励死者家属、朋友以及照顾了死者好些年的医生护士把死者生前的故事说出来。玉子是巨鹿坡第二百三十二个死者,轮到我上去念追悼词的时候,我把那盆君子兰捧在胸前,将视线投放到门外,白色卡车开走以后,二世古雪山竟出现在眼前。我回忆着玉子的过往,摊开昨晚写好的悼念稿读了起来:
现在,一个不健康的人正在悼念一个刚死去的人。她是无辜的,她被一道从机器里逃出来的锋利的光所伤害,使她失去了作为女人的完整的躯体。玉子生命中的最后几年精神不好,她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承受着失去丈夫、家庭和生育能力的痛苦。她在病痛面前挣扎了九年,一次次赶走死神,她知道人只活一次。
我还记得玉子在图书馆跟我说过的话,她说她之所以喜欢待在图书馆,是因为读书的时候时间走得比较慢,她希望活着的时候能够更真实地去感受时间。没有人比玉子更渴望活下去,而那些轻生者,那些虚度者都不能把活着的机会留给她,给巨鹿坡其他已经死去和即将死去的人。我知道,这里还有许许多多命运多舛的人,这些人都有各自的故事。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科学正带领我们走向未来,玉子没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巨鹿坡大部分人都没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但是在这个一年里有将近四个月时间被大雪冰封的地方,我们不应该把悲痛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珍惜活着的机会。活着的时候很多事情不尽人意,但死亡面前一切平等,希望玉子在天上能够获得永恒的健康。死者已矣,生者节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