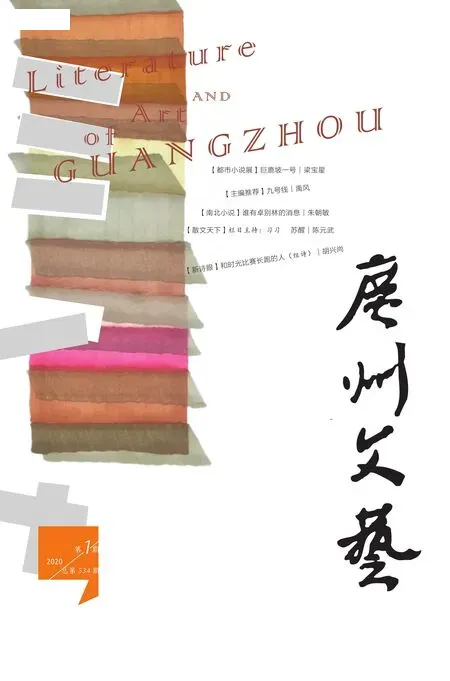清明·谷雨
刘伟林
清 明
在春分至清明的日子,天气日日晴好,即便偶尔落雨,也轻薄如烟。乡下人忌讳多,对这时节的扫墓颇多讲究,既不能过早,也不能太迟,尤其是清明节前两天,更有讲究。前一天是寒食日,更前一天是四绝日,都不能祭祀。清明时节的雨总是不期而至,匆忙而来,又匆忙而去,仿佛要为节气缝上哀白的花边。那些逝者,那些闭口的亲人,他们的骨头已腐烂,灵魂却苏醒了过来,被花朵与焰火包裹。
雨来得及时,我与父亲去河边祭祀,墓地已平,唯一小土包,每年的雨水推动着,把泥土一层层地推开,又一层层地湮没。父亲肩扛铁锹,我拿纸钱,捎上祭祀之物(米饭、春酒、荤菜)。鞭炮在雨中炸开,泥浆溅动,父亲刈草添土。我灼纸钱洒春酒,又叩拜作揖,迷惘间像听到了灵魂的叹息,幽幽地从地底传出。我是否可以借助风,把心灵的柔情增强。蹚过时间的河流,拉近事物中远逝的图象,用以省察肉眼无法看到的部分。借助雨水,种子在地底萌动,花朵举起芬芳。而借助季节,我得到了心的居所,就像这些安寝的灵魂。借助天空,我看到飞鸟的翅膀,给时间画上刻痕。借助大地,我的泪水有了盛接的器皿。而借助清明,我们无疑找到了对死者最好的祭祀方式。
《帝京岁记胜》载:“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明朗,谓之清明。”天气暖了,偶尔的寒流只不过是这个节气的点缀。草木茂郁一片,天气清澈明朗,万物欣荣。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演变为民间节日的节气。此前的寒食日,村里家家户户吃冷食,吃上两日。那两日,村子的上空没有炊烟升起。夜间,我观星象,坚持生冷的素食,关心明日天气是否晴好,露水是否浓如雨水,道路是否能载动那些哀痛。夜空的底下有一只鸟在叫着,暗合了夜晚寂寞的长途。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个尘世,在斜线抛下的坡面上,我只是大地上的一只蚂蚁,沿着坡度缓慢地爬动,但请允许我张开喉咙,把晚风喊高一些。
对寒食日,我做过认真的考究,虽然书上有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但毕竟不可考证,疑为后人牵强的传说。这样的节日,当然有它的来历与意义,它们肯定存在于某个地方,正如历史只存在于历史中,任何的道听途说与推测都不是历史。时间是流沙,不动声色地从我们的面前流过,重要的往往没留下,留下的又往往不重要。那些被覆盖的、被湮没的永远是事物真实的面目,而保存的、呈现的并不是事物的内核。
在乡下,寒食日熄火两日后,家中的灶膛才能新燃,称之为“改火”。母亲言,正如腊月三十那天不能扫地一样,是扫帚的生日,火在一年中也有生日,要停熄两日,新燃的火才会烧得旺。这样的禁忌与传说显然是乡俗的延续,真实而生动——扫帚忙了一年要歇息,火烧了一年也要歇息。万物都有灵,一朵花,一片云,一根草,一滴露……它们游走在尘世,浪荡在天地间,汲地气为灵,纳阳光为魄,多年修炼成魂。也许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能望见那些死者的灵魂。
第二日,我与村人一道去西山祭祀。一大群人,浩浩荡荡,沿着西山一带的河溯流而上,经镇街,经大道,经村舍,沿途都是祭祀之人。人们的脸上洋溢着欢乐,好像悲痛与他们无关,把这个节日看成了盛典,一点也不庄严、不虔诚。来到故园的墓地,那块碑石却被他人挪到了另一侧,我们重新抬回,挖坑深埋。青山高处水自流,山上的杜鹃花开满坡,粉红一片,湿湿地绽在枝头。我忽然黯然,眼睛湿润。在这个初生的故园,这个终老的家乡,死者为什么要选择离开,跑得远远的。一个人的根呢?他成了孤魂野鬼,他的灵魂是否真正得到了安寝?村里人正一个个地往外搬,要到城里居住,正在把家园摒弃。另一种生活成了大家心中涂改的部分,而在那弯起的部分,它扯出了内心的痉挛。我满目忧伤,低头不语,万物清洁明净,仪式一点也不重要,正演变成荣耀的纸灰,不再是对死者的吊唁与怀念,而成了庇佑心灵的体现。面对坟墓,他们滔滔不绝,祈求着物质的到来,而不是平安与健康。我竟觉陌生,仿佛不是生于斯,长于斯,有了平生的羞愧,但岁月的修为,终会让我遣怀。
我说:“那些死者安息吧,明星灿烂,天地宁,永寂山眠,万赖无声。他们的离去,使得时光漫长、寂寥。长风鼓荡,年复一年,终有一日,我生命的图象也将暗了下来,就像布帛被缓慢地裂开,一点一点地归于尘土。”
时光清洁,我黯然的思绪被触目的青山绿水化解。
清明、日光、广袤的大地、母亲的话语,岁月是这样地静好。对此,我没理由不珍惜,不潜藏,不怀揣,不记录。在乡下,我只想以清洁的文字记录生活,睡觉、起床、阅读、写作、行走,给友人写简短的信,偶尔去后山的寺院静听经文。夜间,我打开电脑,坐在灯下,枯坐的时候多,独自言语的时候亦多,好像文字的鲜活不必落于纸张。天亮时,我头昏脑涨,电脑的屏已暗,桌上的一本书掉到了地面,新添折痕几处。兴之所至,情之所落,少了“揉熟其纸”的铭记,人生大抵如此,不必多费心机。“知数固死,不知亦死,与其昏昏,何如昭昭”,我的内心就少了悲戚,少了心惊,多了安定与淡然。就着晨光,站在窗前,看晨色如何一层一层地升起。底下,母亲正打开屋门,去菜园中就着露水摘菜,父亲扛着铁锹去田畈地头。
对于清明,我从不认为那是祭祀的仪式,而是对生者的追问,用以表明时间的易逝。前两天,母亲蹲在院地上杀鸡,身影闪来闪去。按我们这一带的风俗,清明节那天要带上酒肉到亲人的坟前祭祀,所以鸡必须在寒食前宰杀。我并没观察母亲是如何杀死鸡的,而是看院角排成队的蚂蚁。黑蚁正从墙角的穴居中爬出,连成一条黑线伸向另一侧,它们匆忙爬过阶下的苔痕,爬过枯落的花瓣,爬过一处洼地。蚂蚁出穴,必降大雨。我观天象,察自然,居住在植物、河流与星光中,怀想着这些古老的事物与礼仪,并对此深感精深,比如,世说中的德行、方正、雅量、品藻、容止、栖逸、惑溺、捷悟;又比如,饰巾、洗浴、诗章、禁忌、神明、内经、车辕、本草、训诫、饮酒,诸如此类的词语,念念不忘,它们与清明如出一辙,浩荡在文字的深处。
我喜欢这个节气,它安静、博大,透出另类的迷香。我喜欢灵魂归于大地的一掬尘,此时,天空清朗,行人穿行于亡灵的道路,鞭炮的响声扰碎了这个季节的雍容。我伫立着,有了瞬间的惶恐,顿时对尘世怀抱热爱。山青青,水长长,“到得再相逢,恰经年离别”。夜风吹过,我的面容沉静,与村庄同眠,就像花朵回到了寂静的花房。
谷 雨
古历三月二十三日,为谷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载:“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即“雨生自谷”,故此得名。春季的花正逐渐凋零,有些枝头还留有一抹残红,依然闹嚷嚷的模样。这时节结实的都已结实,春日花性急,亦开得早,架子端得紧,然几日明媚,转眼在枝头暴出了核。这样率然的场景,不拘束,不做作,令我心底无端生出感慨。
谷雨已至,它是这季节中一次华丽的转身,裙裾曳地,香气冲天。夜未央,风雨忽来,我坐在这季节的怀抱,愿聚散依依,愿所有的事物都没终点与起点,愿风随雨动,雨随心至。我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只愿在季节的深处徘徊、低吟,我更愿意这些事物回到各自的终点,比如雨回到谷里,它黄金一样的容颜熠熠生辉;一朵花回到枝条的裂缝中,它的味道被风吹得远远地(我是否能从一朵花中看到它骨骼一样的光芒);风回到寺院的那头,它不知道该向左还是向右;黑暗回到光明的顶部,它收拢翅膀,如倦怠的鸟立着……夜里,就着那盏灯火,父亲在院中修理犁耙。谷雨水响,犁耙下田。父亲要就着晴好的天气,把水田翻耕一遍。对于土地,父亲珍惜,总说要把一块土地种熟,不是一两年的事情,得数年,千万不能撂荒。乡下,人都往城里涌,那些荒芜的土地太多,父亲每每又顾不上,只好摇头叹气。万物周转的秩序正被打破,但天道的节气不会变,不以人的意志发生移位,或者跌落到时间的背面。
天气暖得实在,雨却明显地多了,也大了起来,从屋顶湍急地走过,在屋檐形成瀑布样的水帘。天色昏暗,除了雨声,就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斜眼望去,雨水疾驰而至,从对面的山上往下推,如一首自天庭而降的玄妙乐曲,地面溅起的雨点是跳跃的音符。
记得清明节后,我与母亲去茶园中采摘茶叶。早晨的露水已干,茶树碧绿一片,晃得眼前幽绿丛丛。若我能抹几页工笔,定让风光落在薄宣上,把自己也定在薄宣的某处,让旧梦之人聚神寻找。他要找的又不一定是我,而是谷雨汩汩的流水声。谷雨路遥遥,春色媸已尽,我慢慢地收拾着,把它揽在怀中。是否就此春色年年不同,是否我还是那个镜里的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园沐在谷雨中。每年的谷雨节,母亲都要去茶园摘茶,做“谷雨尖”。茶叶摘回,放在锅里炒焙,锅只要烧热就行,万不可烧过了,母亲用手慢慢揉搓,就形成了谷粒大小的尖叶,曰“谷雨尖”。置热水浸泡,茶叶舒展,纤毫毕现,柔如银针,根根直立杯中,若是玻璃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对于茶道,我不懂,亦不善饮,惹得母亲每每说我“牛饮”,茶不是这样喝的,要细细地尝,你就没尝到别的味道?母亲擅于此道,但也不至于讲究到有泡茶的工夫,只是说热茶慢喝,不能冷却,可治咳嗽、伤风、感冒。每年,趁着谷雨刚到,即便是下雨,母亲也要去园中摘茶,说是再过了几天,就不是春茶了,该称为夏茶。逢年过节,母亲就拿出这些茶叶招待客人,礼仪隆重。谷雨这个词,就从母亲嘴中吐出,像是节气的痕迹还刻在时间的深处。母亲一遍遍地念着,这是谷雨尖,是谷雨茶。
风和日丽,春光踏遍,母亲手指如蝶,翻飞于茶树上,数声杜鹃从茶园的上空响起。连空气中也弥散着茶的清香,软软地流着。这些茶树历冬经夏,沐霜浴雪,把四季的阳光、土地的肥沃一点点地汲取,它的每一茎脉里,就藏有一个季节的秘密。这样美好的事物让我为之流泪,为之“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每年,母亲总是雷打不动在那几日去采茶,时日既不会早,也不会迟,一定要在那几日把茶叶采回。问母亲,看不出要如此费心,像是茶就成了另一种味道。这些物事透出隔世的美,清晰而迷蒙,就像年年美好的曾经,而生命的河流总是匆忙就旋入岁月的深处。
谷雨已起身,节气不饶人。春天最后的一个节气居然是谷雨,是谁在用这样的词语,标明天道的更迭。我坐在阳台上,在这个午后,这个寂静的时分,手中握着茶杯,杯里泡着“谷雨尖”,探嘴品咂一下,似乎这是春天最后的味道,似乎这是我抵达梦境的一个暗示。
晚上,我还是静坐在阳台上,独拥天籁。不远的田野上传来阵阵蛙鸣,蛙鸣成了这个节气的和声,扰乱了这个节气的动与静。这样的夜晚,父亲肯定要失眠,规划着明天的农事。农事堆积在那里,把父亲拽向节气的深处。蛙鸣半夜时分停止了,夜空浩瀚无边,村庄安详而朴素。谷雨的金黄正在广袤的天底呈现,再过三个月,谷子该成熟了。虽然它们还没移植到水田中,但它们的青苗正在垄间茁壮。然后,它们发蔸、抽穗、扬花、结实,被阳光烤熟,接着收割、晾晒、净秕、入仓,滋养着我们的肠胃。
谚语言:“谷雨阴沉沉,立夏雨淋淋。”看着这样的天色,父亲说今年又会有好年成。谷雨阴天,立夏就会落雨,立夏落了雨,小满也会落雨。父亲的意思是说,节气都是融会贯通的,它们互相联结得紧,若是立夏不落雨,小满就不会下雨。年景就是旱年,那些置在高坡处的田就用不着去种植,即便种了,也会旱死。父亲的话,就像谷雨的光芒照亮我的眼眸,照亮这个节气中最精粹的部分,既吻合了我的想象,又超出了我的想象。它们神秘、玄妙,但透过日常生活,荡漾在时间的平面,似乎是为了证实生活的美好,辟出一条道路,让人们去寻找它的佳趣。节气同样是声色并行的,需要用眼睛与心灵去感应,去发现,去瞻望。虽然生活始终尖锐、拖沓、脆弱、尘垢满布,但节气却带着我的身体投奔远方,用以省察我内心的敏锐,并构筑了我内心的慈善与仁厚。节气随河水流动,像这个季节的花朵亮出了它骨骼中的光芒,向天空与大地标出了时间的履历。它越过山峦,越过原野,越过我心灵柔软的部位,也越过我的猜测与臆想,抵达每一重季节之门……
第二日,天空真的在落雨。母亲一早打着雨伞去园中摘菜,黄瓜已上架。父亲在屋檐下,锯着一段木头,修理犁柄。雨水很好,不徐不疾地下着,亮着白翅的鸟,从我眼前飞过。院角杂草丛生,里面长出一种细碎的黄花,暗香微散,须夜间才可闻见。我不明白,这花为何夜间才可闻香,白昼不能?听母亲说,是一种草药,可以清脑醒目,茎、叶、花、根都有用处:茎可治脚疾;叶可泡水,只是味道很苦;根晒干熬水,夏日涂在蚊虫叮咬处,可消肿止痛。母亲每年都要挖出一部分根,留于一部分来年新长。我每年见着,竟懒得去查一查书,看看到底是什么药草。
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为银杏,一棵为杨梅。银杏的叶子呈绿茶色,雨的光斑滑过,绿色更浓;而杨梅树已挂果,只是还没熟透,得过些时日。
我嗅着谷雨的芬芳,静立在那里,就让这些清草丽花永存于记忆,目光所及处,“独吟池塘自碧,细咽枣锢飞燕”,于谷雨的光影中,我保持住——对这个季节最后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