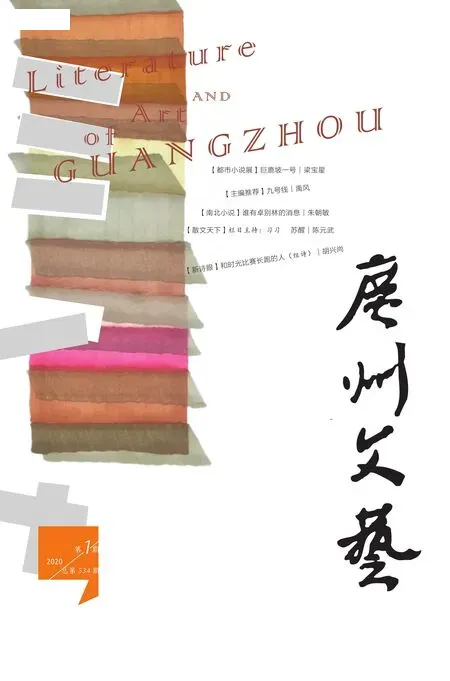修改练习
牛利利
“对不起,我是警察。”模仿了一小时梁朝伟的沉默后,我开口说话。客人很少,调酒师坐我对面,百无聊赖,用白手帕不停擦拭高脚杯。他抬眼说:“是吗?这行很辛苦的。警察天天来酒吧,查酒驾?”他没看过《无间道》,不知道这句台词,我很失望。女歌手唱了首《倩女幽魂》,是老烟嗓,歌声苍凉粗粝,像极了北方的冬夜。“多谢!”女歌手用粤语说道,抱着吉他从台上下来,没有掌声。调酒师说:“我挺喜欢这歌。”他哼唱起来。我没搭理他。“瞧那女孩,”调酒师挂起高脚杯,俯下身,低声给我说,“她在你左后方,看了你好一会儿了。”我转过头,左后方果然有个女孩。她一个人坐着,桌上摆着一杯橙汁。她并没看我,而是低头玩手机。“我觉得今晚你能带走她。真的,我这方面有经验,别信她的外表,看着是挺纯的,但肯定不是那么回事。你得请她喝一杯。”调酒师的声音很小,字吐得飞快,仿佛嘴里的话是夜的拉链,他在快速地拉开它。他轻轻一拍调酒台,说:“差点忘了,你是警察,对吗?”我喝了一口酒。他指指眼角,问:“执行任务时留下的?”我说:“是。”他端详了会儿,说:“生活不易。”说完,他取下刚挂上的那只高脚杯,用白手帕擦拭起来。
我不是警察,这不过是和调酒师开的玩笑。不知为什么,我只要喝点酒,就喜欢和陌生人开玩笑。酒精作用下,我觉得玩笑是我和世界发生联系的唯一方式。我并不擅长玩笑,喜欢归喜欢,擅长归擅长,这是两码事。在另一条街道,另一个酒吧,另一个夜里,我喝醉了,坐在吧台前,和旁边的人开了另一个玩笑。什么玩笑,我不记得了。几个混混站起来,昏光里女歌手同样怀抱吉他。他们把我架出酒吧,在巷子揍了我一顿。眼角的伤疤就是那次留下的。他们说我“嘴欠”。我像虾米一样蜷着身子,他们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我渐渐舒展身体,望着夜空犯困。我忽然想,自己不能睡着,冻死了怎么办?醉酒后,除了爱开玩笑,我还爱自己的命。我爬起来回了家,继续写那篇叫作《修改练习》的小说。我忍着恶心和疼痛写。写作是唯一可以使败坏的生活变废为宝的技艺,电视上有个老头这么说过。这话吸引着我。让我觉得只要我不断地写啊写啊,生活就不会发出“嘣”的一声响。我写得很糟。海明威曾教导:“第一稿永远是堆臭狗屎。”我写了好几稿,都很糟。臭狗屎是臭狗屎,海明威是海明威。
时间还早,我埋了单。调酒师说:“我最近在练一款新的鸡尾酒,下次你可以试试。”“好的。”我裹紧夹克出了门。我没喝多。在喧闹的人群里,我保持摇晃的姿态。我经过一家酒馆,酒馆正挂红灯笼。一个女孩抬头望着灯笼。她穿着朱红中式裙褂,梳着丫鬟头,眼神清澈纯净,与世无争,美好、庄严、温顺,夜里的画眉鸟。有人注视着女孩,有人蹲在地上拍照。我知道庄严和温顺都来自被注视,只有美好属于她自己。碎雪在光里飞,灯笼在夜空的背景下显得虚幻。这些都很美好,但和我无关。我摇晃到钢厂附近,点上一支烟,看了会高炉。钢厂倒闭了,高炉不会再吐白烟了,我替它吐了会儿。
两边路灯都黑着,阅报栏的玻璃碎了,过期报纸在风里翻飞。我向前走去,高炉甩在了我身后。这时,我发现有人跟踪我。当我走快时,身后的脚步声也密集起来;当我停下时,身后的人也停了下来。我一下子清醒了不少。有人注视着我。当我想到这点时,我不再摇晃,尽量挺直身板,步履匆匆,像有要事等我处理。我想让自己变得庄严起来,就像那个仰头看灯的汉服女孩。被人注视时,我没有美好,但或许还有庄严。当夜风吹过,我清醒到一定程度时,我才想到危险。我和世界要发生关联了,但可能是以一种危险的方式。这附近治安不好。几天前的深夜,一个女人拐角处横死。墙上写着“拆”字,地上白色的现场尸体痕迹固定线已经不见了。匆匆走过斑马线后,我抑制不住好奇,猛然转身。我看到了一个女孩,二十岁出头的样子。她穿着红色大衣,梳着马尾,眼神茫然而紧张,进退为难。她最终走了过来,一言不发,向远处主干道方向走去,面向隐约的光亮。我在脑海中搜索她的形象,搜索无果。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我本来就有点脸盲。我也向主干道走去,夜风忽然大了起来,碎雪扑面,槐树枝叶摩擦,沙沙作响,纸屑和塑料袋加速起飞。女孩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风中大喊着:“我知道的!你应该送我回家。我知道的!”
我问:“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就让你在风中疾呼?她的刘海被风吹乱,神情说不上是坚定还是愤怒。但我清楚只要风再吹,沉默继续,她的坚定会消散。果然,她再度张口时声音变得怯懦:“我在酒吧里听到了。我知道你没有喝醉,你应该送我回家。你会的,对吗?”我知道了。我有想哭的冲动,酒还没有醒。我向陌生人说玩笑话,有人听到了,而且当了真。我想起来了,在酒吧里,她坐我的左后方,桌上摆一杯橙汁。我说:“好的,我送你回家。”她说:“谢谢。”我严肃地说:“职责所在,不必言谢。”路上,女孩告诉我,她叫赵小枝,刚失业,第一次去酒吧,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因此没法打车。“鲜榨南美柳橙汁,定价:38.00RMB。”酒水单上这么写着。如果她没有撒谎,她所说的“身上所有的钱”也就区区三十八元了。她忽然故作成熟:“干这行几年了?”我说:“刚干不久,快从良了。”她瞪圆眼睛瞧我。我想着把玩笑开下去:“我是一名卧底,快归队了。”她努了努嘴,说:“哦,放心吧,我会保密的。”
我和赵小枝走了一个多小时。其间,我几次提出打车,她都拒绝了。夜风时大时小,风大时,我俩竖起衣领,相互远离,风小时,我们并肩聊天。路过广场时,她忽然问我:“当卧底什么感觉?”我想了想,说:“像被时间开除了一样。”她又问:“你平时有什么爱好?逛街吗?还是喜欢看电影、玩游戏?男生都爱玩游戏。”我说:“都不喜欢。我有时会写点东西,干我们这行,得有点爱好。《盗梦空间》看过吧,莱昂纳多主演的,他能在梦境穿行,他擅长这个,但副作用是他把现实和梦搞混了。所以他有个陀螺。他掏出陀螺,转一下,过会儿陀螺倒了,他就知道是在现实中。干我们这一行也得有个陀螺,它告诉我们,这是假的。你被时间开除了,但你得回去,迟早的事,别忘了。”说完这么一番话,我有些被自己打动了。赵小枝说:“那你写什么呢?玄幻、言情,还是穿越?有个叫什么土豆西红柿的,写得挺好。”我对她的失望超过对调酒师的失望。我想说,都不是,不是那样的小说,我想写的小说是关于时间的,它很慢很慢……风又变大了,她竖起领子,神情阴冷,匆匆走在了前面。我什么都没说。
城市是起伏着的。我送赵小枝到小区门口,那里是一个巨大的褶皱,拥挤脏乱,没有风。街道被各式摊贩挤占。这里有二十元一件的衣服,五毛一串的烧烤,还有五块钱半米的“金”项链。树下摆几桌台球,一元一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满地是垃圾。街边站着个中年女人,穿着艳丽的服装,化着廉价浓妆,如一株有毒的植物,在向我笑。赵小枝轻轻扽住我的袖子,低声说:“别看,她是干那个的。”进了小区,她站住了,双手背在身后,问:“讲讲你的小说吧。”我看得出来,她不关心小说,不过是想再聊会儿天,消磨时间。我说:“还在修改,下次吧。”
我步行回家,冷风吹得脑壳疼,酒渐渐醒了。再次经过高炉时,我看了眼手腕上的天王表,时针指向十二点。手表是钢厂厂庆时发的,男职工一人一块天王表,女职工则是一整套安利洗漱品。但钢厂倒闭了,在两个月前。钢厂倒闭的那个夜里,我和几个同事举着酒瓶,仰望高炉。夜里有雾,或是霾。黑夜如熔化的玻璃,高炉漂浮其上。当我意识到厂子的倒闭时,高炉不再漂浮。在一瞬间,它矗立在黑暗中,像巨大的时针,永远停在了午夜零时。我们喝一口酒,骂一句娘。我们围着火堆,大声说话,砸碎每个空酒瓶,怕寂静包围。有个同事哭了,他说,谁都没听到那“嘣”的一声响,生活怎么就塌了呢?他哭得那么伤心,我以为他会夜夜烂醉下去。失业后,我开始害怕白天,窗外小山上是残雪和萧索的树影,看上去寂寞极了。我看不到高炉,但我知道它就在身后。失业的头几天,我们几个同事每晚都聚一起。没过一个礼拜,他们都去找工作了,满怀对新生活的向往,期待时间重启。夜夜烂醉的是我。
看到高炉,我便会觉得伤感,但我还是决定往好的方面想,比如今晚是特别的。虽然我是被时间开除的人,但今晚我开了个玩笑,有人听到了,并且当真了。我渐渐兴奋起来。我回到房间,关了灯,躺在床上,听夜风呼啸,一阵紧似一阵,把我心中的兴奋全部吹尽了。我又一次厌烦。失业是寻常事,以前的同事们开始向新生活努力,他们的时间重新开始了。而我为什么表现得过分颓废?我不是被时间开除了,我是不愿意回去。
到了后半夜,我起床,打开电脑,又开始写起那篇叫作《修改练习》的小说。只要我不断地写啊写啊,生活就不会发出“嘣”的一声响。我在想,我究竟爱不爱小说这么技艺呢?答案是:算不上爱。我不知道自己爱什么。我哪怕在这上面耗费再多的时间,也都算不得爱,只不过是在玩罢了。就像是贪官们为情妇身败名裂,但他们未必爱那些女人,不过是在玩,在耗费时间。《修改练习》从未真正的开始。换句话说,这篇小说没有动过。它只是在描摹一个个静止的画面,没有冲突、没有主题、人和人之间没有交集,象征物和象征物之间也没有联系。毫无疑问,注定失败的写法。但我迷恋于此,不断修改它,但每次不过是给主人公换个新的身份:教师、科学家、官员、巫师、杀手、赌徒……主人公不会因为职业变化而变化,他永远茫茫然地闲逛,在夜里看到一个个无关联的象征物。这次我又开始修改,把主人公的职业换成了卧底。
写着写着,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我们几个小孩在夜里爬山,在荒野上燃起高高的火堆。火让黑夜更高,我们仰着头,看着星星。时间无始无终,我们并不孤独。我看到祖父在火光中。我流下了眼泪。我在键盘上敲着字,期待黎明不再有风。
第二天醒来,我破天荒在房间里锻炼起来,做俯卧撑、深蹲和仰卧起坐。锻炼完,我开始看书,喝茶。夜晚到来,我不再出去喝酒,风像是一列长长的列车,准时从窗前呼啸而过。如此规律的生活持续了半个月,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奇迹。我心想,这是因为酒吧里的玩笑,有了这句玩笑,我才送赵小枝回家,如此像是和世界又有了联系。但我还是没有去找工作。我为自己辩解:时间重新开始是庄严的,它需要一个事件的启动。有天,我读到一句诗:“他走在时间的裂缝里/被自己的伤口照亮。”我想到自己现在就是在时间的裂缝里,但我没有伤口。我在晚上写作,写那篇《修改练习》,依旧写得糟糕。我只是不断写啊写啊。
有个夜晚,小马约我出去喝酒,地点在他的出租屋里。我冒风雪前去。我们五人围着圆桌落座。我们都在钢厂上过班,且在一个部门,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该算是朋友。桌上摆两铝盆卤菜,全是些海带结、土豆片、豆干之类,一盆里还有三四个鸭头。桌下码着三箱本地啤酒,还有一瓶一斤半的杜康酒。白炽灯在我们头顶“嘶嘶”作响。
小马新找了工作,地点在临省省会,很快就离开。我们祝贺小马。大家又问起我。我说,还没找工作,在家闲待。小马说:“毕业后我们天天奔命,哪有过这么长的假期,应该享受。况且你有才,不像我们这些俗人,可怜巴巴地求人赏饭,怕赶晚了,没口热的。”我听他的话,心里不痛快,很快就醉了,话也多起来。
大家问我,待家无聊不?我说,不无聊。小马说,他就跟聊斋里的书生一样,一到晚上就假装读书,其实是在等什么。我凑过去问,我能等什么呢?他说,你等个鬼!大家拍桌子笑,泪都笑出来了。又有人提起我向厂报投稿的事。那是刚入职的事,稿子没过审,我提着酒瓶去厂报编辑部去闹。我脸拉了下来。他们说,要是厂报发表,我们还能读一读,现在厂子倒闭了,还没读过大作,不如今晚讲讲吧。我喝醉了,心里憋火,知道他们大多找了新工作,有些张狂,瞧不起我。我应该站起来走人,嘴上却说“好”。小马问:“题目叫啥啊?”我顺着他的话,说:“《修改练习》。”他问:“都啥内容啊?”我说:“内容一直在修改。”他又问:“那你想要表达什么主题呢,总有主题吧。”我说:“我想表达时间,但我搞不清楚。我一直在修改。”他们又大笑起来。这次我不生气,反而羞愧,觉得自己犯了错。小马说:“你讲讲嘛。”我喝了口酒,忘了拍案而去这件事。在一瞬间,我想起前段时间在酒吧,我喝得烂醉,跟陌生人开个玩笑,他们把我架到小巷子里,一个混混扇我耳光。红灯笼在风雪中摇摆,朱红裙褂的女孩望着它,她有被人注视的庄严和优雅。荒野上一道道光柱交错,祖父涌失在黑夜里,时间静止。或者,祖父消失在了时间里,黑夜静止。小马递给我香烟。我伸手接烟,打翻了纸杯,啤酒洒在裤子上。我想找抹布,环顾一圈,看到大家醉后的眼神。他们冷冷望着我。我想到,如果是玻璃杯多好,掉在地上会发出清脆的响声,它不会被无视。
我开始讲一个新的故事:我是个卧底。我记不清干这行多久了,只记得一个夜里,一间小会议室,空气中有霉味,白炽灯嘶嘶响,像是盘在我们头顶上的一条蛇。老领导抽着红万,眼神缥缈。他说,他们罪大恶极。我点头。他又说,但没人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恶。我说,是的,他们作恶,但不够具体。老领导说,去吧,去当卧底,年轻人不要担心,他们从不贩卖毒品和枪支,也不走私,不组织卖淫,不收保护费,没有暴力倾向。你是安全的,但你得找到他们做的恶。这是你的任务。我离开了公安局,夜里有风,无雪,漆黑一片。我回望公安局,它仿佛荒野里一座年久失修的庙宇。我穿过树林,夜鸟飞过我的头顶。第二天,我进入了犯罪团伙。他们组织了两轮面试,还查看了我的学位证、毕业证、英语六级证以及计算机二级证。我进入了一家钢厂,成为一名技术员,先在天车车间,后来又去了连铸车间。车间的空气里满是粉尘,噪音惊人。我口袋里装着静音耳塞,却陷入两难。如果不戴耳塞,我的耳膜就会受损,以至失聪。如果戴上耳塞,我就无法听到天车过来,有一定概率被重物砸中。或许是因为噪音的缘故,我对于白天的生活一片茫然,我只记得夜里。我在夜里仰望高炉,常常陷入到一种茫然的情绪里……
“Stop!”小马喊着,比划出停止的手势。他脸色通红,眼里满是血丝。有人趴桌上睡着了。我听见窗外起了风。我讨厌这个地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总在夜里刮风。有人说:“小马你干吗呢!让老黄接着讲嘛!”小马说:“武侠不是武侠,玄幻不是玄幻!有什么意思!听来听去,这不又是钢厂的破事嘛!我讨厌钢厂,不想别人提钢厂!静音耳塞谁不知道啊,我口袋里还有四五对呢!我还有两双劳保鞋,你要不要?虚构,我们得听点虚构的!”那人说:“你着什么急嘛?老黄你别生气,你是卧底嘛,要有城府!”
我冷笑。我该发火,但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忘这茬。我又喝了几杯。醒着的人都红着眼,沉默着。窗外漆黑一片。我听到脚步声,仔细辨认,才知是风拖着枯叶。我正听着枯叶的沙沙声,陌生感击中了我,就在一瞬间。就像是钢厂倒闭那夜,一瞬间我看到高炉静止,不再浮动。我看着酒桌上沉默的几个人,悚然心惊: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是在庆祝吗?庆祝什么呢?
窗外又刮起烈风,我害怕这种寂静,再次讲了起来:不管过去多久,我总记得老领导的指示。我要找出恶的证据。时间始于罪恶,正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后,一个大陆的时间才真正开启。钢厂产能开始下降,一切变得寂静。高炉很久没有再吐过白烟了,它的脚下长满野草,野草越长越高。我在月夜蹲在野草里,希望发现罪恶。月下,我怀念祖父。他消失在夜里,他在酒后来到钢厂。有人看到他摇晃着走过连铸车间,有人看到他走过转炉,但没人再见到他。我想起祖父,并非因为我对他感情多深厚。他消失时,我只有六岁。我只记得慌乱的人群,荒野上手电筒里射出的道道光柱。我只记得因为寻找他,好多个夜晚,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对寂静。窗帘没有拉上,我看到死亡的各种象征物:凶鸟立窗台上,爪子拨弄枯枝败叶;雪纷纷落下,情侣在接吻,拿着黑色的玫瑰;远处是黑暗的小树林……我在脑海里修改着他的结局,就像修改一篇小说。但是只是修改,没法撕了重写。祖父无声的消失让我惊惧,如坠深渊。我时常想,要是能见证他的死亡该多好。这样一切都确切无疑,如在白昼,没有隐喻。哪怕是惨烈的死,也是在时间的强力中,一切不会模糊,死亡会作为纪年。只要找到罪恶,我就可以重新回去。秋草渐渐枯黄,天上是阴沉的云,碎雪飘洒着,接着是鹅毛雪。钢厂倒闭了。我们几个同事相约在夜里为钢厂祭奠。我早到了两个小时,夜里有雾,或是霾。我一个人喝着酒,把酒瓶摔碎。我仍觉得不过瘾,我从荒草里捡起一把红色防火锹。我希望有一轮月亮,照着我。我愤怒地挖掘。我蹲守了这么久,我什么罪恶没有见识到。如果现在远处有人看到荒野上的我,他一定以为自己正见证一项恶行。我听到“当当”的声响。我从微醉中清醒了过来。我蹲下身,扔出了坑里的石头。我继续向下挖,铁锹又遇到阻碍,我扔出了一块锈蚀的铁块。然后,我看到了白骨。我静静望着它。我哭泣着,将白骨掩埋。我希望夜里没有雾,或者霾,而是一轮惨白的月,我们白骨相认。让白骨告诉我,它是我的祖父,一切都有确切的时间。朋友们带着酒过来了。我们举着酒瓶,仰望高炉。高炉漂浮在夜色上。我们喝一口酒,骂一句娘。我们醉了,有人唱歌,有人点火。我们围着火堆,大声说话,砸碎酒瓶,生怕寂静包围。当他们醉倒时,我走向远方。我走出城区,走过黑暗森林,夜鸟飞过头顶。但我没有找到公安局。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有过那么一位老领导,在一个深夜里坐在小会议室里,抽着红万,头顶白炽灯嘶嘶响着,如一条蛇盘在我们头顶……
我讲完时,他们都趴在了桌上,没人听我讲。当然,我不在乎。我站起来,椅子发出声响。小马抬起头,嘴巴含着核桃一样:“讲完了?”我说:“完了。”他趴在了桌子上。窗外寒风吹彻,寂寥极了。我站在窗前,抽完了一根烟,离开了。
小马的出租屋在郊区,出门不见车影,稀疏的灯火远处亮着。我扶着槐树吐了几回。我穿过一片树林,几只黑鸟尖叫,风雪中起飞,仿佛盘旋的落叶,仿佛灰烬。风掠过林梢,鸣镝般射向远方。我回味刚才的故事,得出了结论:很糟糕。但我很快忘了这个结论,又一次回味故事,再次得出“很糟”的结论。风雪越来越大,我怀疑自己永远回不去了。穿过了树林,透过风雪,我看到一处院落。不是农家院落,是一家单位,门口有电动道闸,门柱上挂着一长木牌,白底黑字,保卫室的灯亮着。我想起我的《修改练习》,决定把小院落当作公安局。对,我是卧底,在故事中,在玩笑中。我站直身子,向那盏灯火敬了军礼,手掌外翻,指抵眉尖,标准的英式敬礼,我在模仿《无间道》里的梁朝伟。
一进市区,风雪就小了,我也清醒了些,能觉出浑身肌肉的酸痛。街上几乎没人。我想看看时间,手表和手机不知什么时候丢了。红色的人影出现在前面。我要忠于卧底的角色,忠实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我没有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作品,我只看过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因此知道这个名字,还知道他是体验派。我是卧底,要去发现罪恶,重启时间。因此,我要跟踪前面的人。
女孩脚步越来越紧,但节奏仍在,可见还未完全慌乱,雪落在逼仄的巷道里。我心想,她应该是庄严的,因为有人在注视她。我望着女孩的背影,想起了高中时读过的一篇散文,题目叫《脚印》,还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那会儿的我可算过目不忘,但记忆力仿佛就好了那么一个夏天。我在巷子里跟踪一个女孩,寒风吹着我,我决定默背《脚印》。除了玩笑,跟随一个背影,拾捡一个人的脚印,这也是和世界发生联系的一种方式。胃里又开始翻腾,我压抑着恶心,眼里憋出了泪。女孩掏出了手机,她要报警吗?警察来了,我该说什么呢?阿Sir,误会,自己人。
女孩走出了巷口,主干道上一片光亮,潮湿的路面反映着霓虹,更显凄清。她站在街边,急切地挥舞双手,仿佛挣扎的溺水者,积雪团团落下,没一点声响。你应该庄严,你在被人注视!我想大声对她喊道。她的几缕头发风中飘扬,发梢有雪化后的水珠。几辆出租车开过,但都亮着“有客”的牌子。我肩膀撞在电线杆上,疼得叫出声来。女孩猛地转身,惊惧的眼神在夜里迅速化开,她说:“怎么是你?”我没认出她,我有点脸盲,何况是在酒后。但我听出了她的声音。我说:“我看到了你的背影,但不敢确定,就跟着走了一段路,实在冒昧。”赵小枝说:“我以为是变态呢,之前吓坏了。是不是你想起我上次跟着你,所以报复我。”我说:“哪有的事,我送你回家吧。”她笑了。我心里涌出了一种幻梦的感觉,心跳有些加速。她出现在了黑夜里,她被我注视。“看着我,就是治疗我。”我忽然想起这句古突厥的民歌来,人人都需要被注视。我提出打车,她拒绝了。她说,想再走走。她问,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我去执行任务了。她说,你喝酒了。我说,是的,特殊任务。我得早点回去,回到时间里去,不是吗?
我尽量想让自己庄严一些,但步伐仍摇晃,胳膊和肩膀不时碰到她,别有用心一般。我问她,这么晚了,怎么一个人走?她说,心里闷,散散心。我又问,找到工作了吗?她没有理我。我想起上次遇到她时,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现在却冷着脸,沉默着。过了好一会,她忽然问:“你家住哪儿?”我说:“城北,钢厂那边。”话一出口,我就后悔,卧底不该住那儿。她挽起我的胳膊,说:“不回家了,去钢厂吧。”我想起调酒师对她的评价,开始有绮丽的幻想,嘴角展露微笑。她说:“别想歪,我只是去看高炉。”我俩走进一家小商铺,拉开推拉门,机器音在昏暗中响起:“欢迎光临!欢迎光临!”门口一张小床上爬起来一个人来,打开了所有的灯。赵小枝打量着货架。老板望着我俩,指指后边一排避孕套:“要哪种?”赵小枝问:“白酒有吗?就要那种便宜的,度数高的。”
我俩到钢厂时,雪停了,雪地上没有一个脚印。赵小枝注视着高炉,伸手从我口袋里掏出二锅头。她一拧瓶盖,然后用大拇指一挑,瓶盖划出一道抛物线,如一枚枪膛中弹跳出的空弹壳。她喝了一大口。我看了她一眼,她生气地说:“你不能喝!”我说:“我没想喝,我喝得够多了。你得慢点喝,稍微压一下。不然冷风吹进胃,特别容易吐。”她说:“我没事。”她又喝了两口,转身,步态已踉跄。她不是想喝酒,她是想醉。她说:“我记得,你说你家不远。”我转身,指指后边一排红砖楼,说:“就那儿。”她用力拉着我的胳膊,说:“带我去。”到了房间,我打开灯,弯腰去给她找拖鞋。她皱着鼻子,说:“臭的,像狗窝!”说完,她瘫倒在沙发上,眼里满是怒气。我喊了声:“赵小枝!”她说:“喊我干吗?”我开始怀疑,这个赵小枝和上次的我见的是否同一个人。她又喝了一口酒,这次是抿了口。我极其疲惫,对她有些失望。但我知道我永远都是失望的,上次见她就觉得失望,这次却又失望她和上次不一样。
她大着舌头,说:“这是钢厂家属院,你才不是什么卧底。在你们这些人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个年轻的傻帽儿?”我没说话。她哈哈笑了几声,然后皱着眉,压抑着恶心,缓了一会儿,她接着说:“上次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卧底。钢厂倒闭了。那会儿大街上的醉汉,十个里面有九个是你们钢厂的,个顶个爱吹牛。我见过醉汉挺个大肚子,衣襟上全是自己的呕吐物,他说自己是战狼,去过非洲,救过一千多人,还上过新闻联播。还有个酒鬼穿着你们钢厂的工装,对着一面墙,说自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专门来咱们这儿学牛肉拉面、美容美发,还有汽车维修!哈哈!”我伸手拿酒瓶,她狠狠拍了下我手背:“我的酒,你他妈别动!你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假装当你是警察吗?因为我希望遇到个警察,真的!那晚我有点装,装纯,你知道吗?”我说:“你为什么希望碰到到警察?”她说:“我不想说。不过,那晚你表现挺好,尤其是什么陀螺啊时间啊,说得我一愣一愣的。”她伸手指了指桌上的电脑,说:“你那篇小说,叫什么来着?”我说:“《修改练习》。”她说:“能看看不?”我说:“你喝醉了。”她忽然笑了起来,说:“其实我不叫赵小枝。”我有点吃惊,问:“那你叫什么?”她把玩着酒瓶,说:“不重要,你就叫我赵小枝吧。”她不再说话。我渐渐觉得酒醒了,一种破败的孤独感弥漫,我开始烦躁。她说:“这里能看到高炉吗?”我说:“房间里看不到,得去楼道,有个小窗户可以看到。”她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是陀螺。她得意地看着我:“上次你说的挺好,陀螺什么的,我还专门买了个。这样吧,如果你真是卧底,我就给你讲个真事。你要不是卧底,我就给你讲个故事。”我说:“那你讲个故事吧。”
我看到窗外的黑暗在退去,夜晚快要结束了。她又喝了一口酒,一斤装的酒她已经喝下去一半了。她说:“讲故事还挺难的。比如主人公叫什么呢?王晓莉,李爱花?”我说:“还叫赵小枝吧,反正都是假的。我把你讲的故事写在《修改练习》里,小说里人名不该出现太多,因为篇幅不会太长。”她说:“好吧,可我讲不好。”我说:“没关系,还可以修改。”她说:“那主题是什么呢?”我说:“时间吧。”她说:“不会,太高端。”我说:“那你就瞎讲吧。”
她想了会儿,又喝了口酒,说:“两句话能说清的事,怎么讲。而且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觉得挺有趣的,当你要给别人讲时,你发现其实它挺无聊。故事可以无聊吗?”我说:“可以。但不能用无聊来讲无聊。要不,你先简单点讲。”她说:“赵小枝和一个有妇之夫搞在了一起,后来她怀孕了,再然后打胎了。就这么简单。但你说的时间主题在哪儿呢?加不进去嘛。”我苦笑,说:“打胎是为了让时间重新开始。赵小枝觉得这样能在时间中回头是岸。”她用力磕了下酒瓶,泡桐木茶几被磕掉了一块漆,像是夜里睁开了一只眼。她说:“扯淡!孩子生下来,时间才能重新开始!”我说:“也有道理,你可以加入些细节,还有象征。再详细一点。”她摇摇头:“我不喜欢这样。故事不会详细起来的,讲的时候自己反而会变得详细,不是吗?搞清楚,你我是陌生人,我可不想变得详细,被你评价,被你分析。你上次说,你写东西,但还在修改。那你究竟想要隐藏什么?”我点上一支烟,没有搭话。她继续说:“但是,我给这个故事想了个结局,我觉得还行。”我说:“说说看。”她说:“赵小枝打了胎,但她很快后悔。她觉得,嗯,用你的话说,她觉得时间没法重新开始了。于是,她想弄死那个渣男。最后在一个黑夜,杀了男人。”我说:“这没什么特别的。”她有些生气:“你别那么高高在上!你觉得你可以指导我吗?我觉得震撼,这就够了!”她掏出陀螺,在茶几上用力转了下,陀螺急速转动。我注视着陀螺。陀螺“嗡嗡”响着,一切寂静。窗外夜色淡了,能看到远处的山影,高悬的白炽灯变得虚弱。赵小枝红着眼,鼻翼一张一合,满是酒气。
等陀螺停下,她又说:“赵小枝杀了男人,把他草草埋葬,埋在高炉下面的荒地里,至今算来也有一年了。”我掐掉了烟,觉得嘴巴特别干,心脏咚咚咚敲着胸膛,像铁锤砸着墙壁:“赵小枝为什么把男人埋在高炉下?”她笑了,说:“就是讲故事嘛,想到哪儿算哪儿。当然赵小枝也可以埋到别的地方去,这不重要。”我问:“埋得深不深?”“特别浅。赵小枝毕竟没力气。她不敢打车,深夜来到了这里。钢厂以前三班倒,后来不行了,长年也不开工,开工反而亏得更多。但风险是家属院离高炉太近。但她没办法,想不周全,也做不周全,毕竟这种事没有经验可循,她想着全看运气了。因此埋得浅。她为这事挺后悔的,怕大雨什么把骨头冲出来,但是这座城市年均降水量不到四百,不会有冲出白骨的大雨的,怎么样?故事合理吗?对了,你这儿看不到高炉吗?”我取过酒瓶,猛地灌了自己几口。她开始喊:“这是我的酒,你不能喝!”我又一次感到眩晕,一瞬间我感到了陌生。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和一个自称“赵小枝”的女孩讲故事?我站起来,从电脑上拔下U盘,走到洗手间,把U盘扔进马桶,然后撒了泡尿。滚蛋吧,《修改练习》。等我出来,看到她从茶几下摸出一盒烟,红盒万宝路。我不常抽万宝路,有时候看港片,发现港片里不论警匪,都抽这烟。我买了几盒,专供看港片时模仿主人公。我把打火机扔给她。她说:“我倒觉得,你最好还是卧底。你是卧底,该给你什么样的任务呢?让你潜伏在这家钢厂,去发现赵小枝的罪行?”她抽着红万,眼神缥缈,白炽灯在她头顶嘶嘶作响,仿佛一条蛇盘在我们头顶。
我打开门,走到楼道里,推开小窗户,半截高炉入眼。夜色渐淡。我忽然看到高炉动了起来,在一瞬间。时间启动了。我转过身,想喊赵小枝过来。赵小枝坐在沙发上,玩着陀螺。陀螺从桌子上掉了下来,在白色瓷砖地板上继续旋转,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看到楼下有人,是个捡垃圾的老头,夜色越来越清浅。四面高墙围着钢厂和家属院,仿佛一个巨大的泳池,盛着越来越浅的夜色。老人在这泳池里奋力向前,游向高炉。太阳快出来了,白昼没有隐喻,夜里的一切不必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