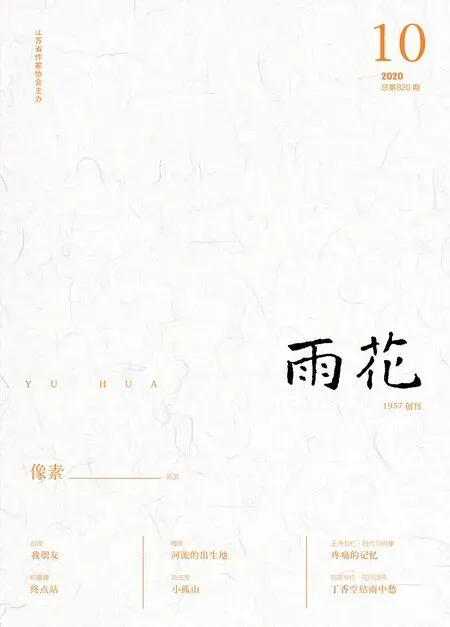疼痛的记忆
许多年前,我背着一个木箱,过了村前的大桥,去十里外的公路等候开往县城的汽车,再从县城搭乘长途车去苏州。在公路上上车的时候,我还没有离乡的感觉,即便在县城车站,我也没有伤感。车行百里,在江边上渡船时,我才意识到,那个乡村在我身后了。我很少用“乡愁”这个词,写作“时代与肖像”也不是抒发乡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在写这篇后记时,我想起一个细节——大学的一个寒假,我夜间从安丰镇踏雪回到村口,在桥南我就听到桥北的父亲和母亲说:王尧回来了。
故乡没有故事。我负笈江南时带去的那只木箱里也没有收藏故事。如果有,那是因为我把我的乡亲们当作故事叙述了。他们都活在散乱的细节中,或者说,那些散乱的细节是他们的呼吸,是春夏秋冬之后落定的尘埃。又过了许多年,这些细节也在尘埃中湮没了。
写作《时代与肖像》时,我一直无法回答自己:在叙述中,我是靠近了他们,还是远离了他们。在以我青少年时期的伙伴为主的微信群中,这些伙伴们议论着我说到的那些人、那些事。不知道他们是否熟悉我说的那些,而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我是熟悉还是不熟悉,我不忍心告诉他们,我可能有意无意修改了我的记忆。有意思的是,我们都在寻找共同记忆并在记忆的修复中共鸣。当我和他们在一些人和事上能够聚焦时,我的感觉像是我们在久别重逢后说“干杯”。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失去了共同记忆,写作和阅读是拼贴已经碎片化的记忆,也是恢复已经无影无踪的记忆。在我们离开故乡时,我们的目的地并不一样,行囊里也塞着不同的细节和体验。记忆是在时空错落后产生的,不断膨胀和变幻的现实在此后一直压抑这些细节和体验,有一天,当你觉得你可以把现实这个庞然大物挪开时,记忆就在庞然大物的缝隙里生长出来。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们都是渺小的,我们都是在共同记忆中寻找曾经的自己。这让我多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写作者一旦写到父母亲在与不在的故乡都会让人感动,因为这个记忆是疼痛的。疼痛的记忆才能转换成感人的文字。
那些共同的记忆,生长在我们赤脚奔跑的土地上。有一天,突然有块硬物触痛了我们的脚掌,甚至刺破了脚趾,划破了脚后跟,这个时候,你看到了自己的鲜血。我在田里割蚕豆时,镰刀划破了我左手的食指,这个刀疤至今还留着。我记得我在慌乱中,先用蚕豆叶子拭去了鲜血,再将割破的皮抚平。我用右手捏紧割破的食指,鲜血仍然不停地从右手的指尖流出。站在我旁边的同伴,在慌张中撕下他裤管上的一块补丁,给我包扎起来。然后我们继续劳动,直到傍晚我去卫生室用纱布替换那块补丁时,我才意识到十指连心是什么意思。当年的疼痛感在几十年后已经无法再去体会了。
想来,那时如果什么部位破皮了,通常都是用破布包扎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破布,抽屉里、柜子里到处都是。抹布不是用毛巾做的,是各种破布缝起来的。破布的作用太大了,可以补鞋子、补衣服、补帽子、补蚊帐、补被子、补书包、补袜子。我印象中,那时候的衣物几乎很少没有补丁。补丁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最朴素的花朵,就像田埂上长出的青草,天空中的云朵,水上的浮萍,树上的叶子,碗里的山芋。这些破布历史悠久,它可能是从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的衣服上拆下来的,那上面有他们的汗水、气息,有他们子女的屎尿,有他们从泥水中穿过的月光、打谷场上的尘土和风雨中流淌的泥浆。我们都是穿着有这样的补丁的衣服在地上奔跑的。
给我包扎手指的同伴姓胡。他长我几岁,小学毕业后就劳动了。或许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他在各种场合始终微笑着,在离开这个村子时也是微笑着。我印象中他的堂哥在安徽,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堂哥,在我还没有出生时去了安徽,在那里成家了。我不知道这位堂哥的名字,这里就称他“老胡”吧。我曾见过这位老胡一次,他理着平顶头,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回到村上,那脸上的笑容似乎表明他在安徽的生活至少是稳定的。那时我还不知道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人物都是从安徽走出来的,而到我们村上讨饭的人多数是安徽过来的,衣衫褴褛,我就觉得“安徽”比我们村还要贫困。当你觉得还有更贫困的生活时,你的心理会稍微发生变化,会在自己的贫困中体会出些微的美好。在跟着大人去看这位老胡时,我第一次看到竹笋。在山区生活的老胡好像没有因成分受到什么冲击,相对封闭的生活也许就是保护层。我的同伴小胡,此时有没有萌生去安徽的念头,我们都不知道。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小胡说他也要去安徽了,老胡在那里给他介绍了对象。生计与老婆,是所有男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但在贫困的乡村,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男人比其他男人更为困窘。瘦弱的小胡已经在农田里扛了十多年的扁担,他毫不犹豫地用这根扁担一头担着木箱一头担着被褥什么的上路了。木箱重些,为了平衡肩膀上的扁担,木箱几乎靠着他的后背。每个人都是带着疼痛离开村庄的,但疼痛并不是村庄对你的伤害。如果疼痛中流着鲜血,那么疼痛中总是散发着暖意。
我看到手指上的鲜血在阳光下暗淡、凝结,甚至变黑。就在这样的时刻,我的另一个少年伙伴已经决定不想读完初中了,暑假后他就由学生变成人民公社的社员了。我在医务室换好纱布要出门时,这位余同学进门了。几天之前,他从船上挑着担子上岸,在跳板上摔了下去,跌伤了右胳膊。他手臂绑着绷带,额头上贴着纱布,纱布里隐隐约约有血痕。他说他是来看我的。本来我们约好这几天晚餐后到河里下钩捕鱼,现在我们都受伤了。自从他决定不读书后,他的嘴里堂而皇之地叼起了香烟。以前他只是偷偷摸摸地吸几口。在卫生室门口出现时,他从嘴巴里吐出一口烟。他当时的样子,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反动士兵。这位单纯善良的同学,在学生时代几乎被他吊儿郎当的样子毁了。只要班级出现异常情况,老师首先怀疑是他作祟。而他又很少辩解,他一说话就满口吐沫,还有点结巴,既然说不清楚,他干脆就不说了。余同学大我两岁,力气特别大,劳动课上的脏活重活都是他承担。
余同学最让我惊讶的是,他会去想那些不需要他想的问题。我少年时快乐的时光,都是和余同学一起度过的。夏天的雨后,我们一起在水沟里捉青蛙。晚上撑船在河里撒网,在河边放鱼钩。其实,我们很少有大的收获,但这个过程带给我们的快乐无可替代。冬天,我们一起在生产队的场头抓麻雀。大风起来后,麻雀都钻进草堆里,余同学特别能辨别麻雀在草堆里的位置。我现在无法想象当时的残忍,我们把抓到的麻雀放在开水里去毛去内脏,然后在火中烤熟。有一天我们俩不知怎么突然厌恶了这件事。我们靠在草堆的旁边,看着麻雀在网兜里挣扎、哀鸣,我们都不说话了。我心里想着放掉这些麻雀时,余同学已经在解网兜,他站着把网兜口朝下,麻雀在纷乱中飞出。在我们俩的吼声中,麻雀向西面八方飞去。那天余同学跟我说:读了高中还是回来种田,我不想读书了,我有力气干活。我没有劝他,我知道他这也是放飞自己。我读高中时,余同学已经是种庄稼的好手,是生产队挣工分最多的社员之一。
因为地震,我回到村上几个月,邻村的同学都在我们村上上课。说是上课,其实是以自学为主,大部分时间在田里干活。我因此有了更多时间和余同学一起劳动,那半年我一直跟着余同学,那是我工分挣得最多的一年。暑假里,我和余同学在河里捞水草,突然广播里响起了哀乐。听到毛主席辞世的消息,我手中的竹篙掉到了河里。余同学也呆呆地坐在船帮上,他掏出香烟,但火柴沾水后已经擦不出火花。我想起几年前我们坐在篮球架下他问我的话,那时是紧张,现在是慌乱。我们把船靠到岸边,余同学说:“我没有前途的问题了,我明年秋天造房子,然后找个对象结婚。你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谁能知道呢?卑微如我,如余同学,也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命运连在了一起。余同学说他每天回家都累得不行,晚上喝两碗粥,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如果哪一天干活不累,反而睡不着。我问他,你怎么打发自己呢?余同学说,干活不累,我回家后就来几杯酒,喝了以后,兴奋劲过了,就开始发困,躺到床上就呼噜噜了。当时我已经知道鲁迅笔下的闰土,但我觉得我眼前的余同学不是闰土。
他是谁呢?许多年以后,我们在村口重逢时,余同学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女儿中专毕业后工作了。他说如果去苏州,就找我喝酒。当他发现我也抽烟时,惊讶地说:你这个老同学怎么也学坏了?我没有回答他,只是笑了一声,他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余同学好像听说我去台湾教了半年书,问我:你真的去了台湾?以前村上的人向别人借钱时会说一句话:我会还钱的,不会跑到台湾。那时大家认为一个人跑到台湾,你就找不到他了。他问我台湾人抽什么香烟,我告诉他很多人抽一种叫“长寿”的香烟。余同学又笑起来:抽烟会长寿。
我再也没有见过小胡。通常的情形是,如果背井离乡后再返回,一定是膝下有儿女之后。小胡肯定带着他的儿子或女儿回来过,但我也是游子了,我和小胡连在村上失之交臂的可能性都没有。他一定是穿着有补丁的裤子离开的,返乡时一定跟他堂哥一样,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出现在乡亲面前。一个人无论对故乡的感情如何,总会尽可能把他最好的形象留在故乡。小胡,你还好吧?如果有一天我写作虚构文本,无疑会出现“安徽”,那里有你的堂哥老胡,还有现在已经是“老胡”的你。如果我虚构一个去了“安徽山区”的姑娘,实现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势必是你的责任。
好像就在我虚构这样一个去“安徽”的初一同学时,我的电话响了。听口音,我就知道不是初中同学就是高中同学。同学在电话中说:“我女儿也在苏州工作,她最近要搬家,有些东西能不能存放在你们家车库?”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