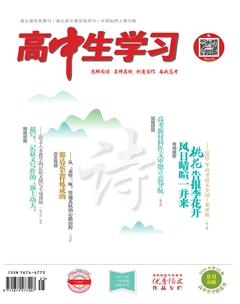感悟书院文化
黄树生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有别于官学的教育系统,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教育模式,也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学、研究学问的场所。它对古代和近现代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菁课程旨归:开放办学
创办于清光绪八年(1882)的南菁书院,之所以称为“中国名学”,成为清代学术和传统书院文化的一个优秀代表,缘于其开放的办学理念和专业的课程旨归。后人一般认为校名源自朱熹的“南方之学,得其菁华”,其实未必完全符合创办人的初衷。依笔者揣摩,南菁以培育如“菁菁者莪”的菁英为办学目标,此语取自《诗经》,体现了企望君子长育人才的喜悦心情,英才之盛犹如一幅萝蒿满地、青绿繁盛的春天胜景。
清代“清流”黄体芳(1832—1899)是南菁书院的创办人,其教育思想隐约于其为藏书楼撰写的名联之中。此联气势豪迈,胸襟博大,可知瑞安先生并非偏狭之人,汉宋相融,其学识胸怀和教育视野是何等的开放:
东西汉,南北宋,儒林文苑,集大成于二先生,宣圣室中人,吾党未容分两派;
十三经,廿四史,诸子百家,萃总目之万余种,文宗江上阁,斯楼应许附千秋。
黄以周不仅是南菁書院的创始人之一,还主持书院长达15年之久,更是南菁学术的“灵魂”。对于书院教育资源和课生知识结构,他如此阐释:
夫学必先之以博文,犹木有枝叶也。学必继之以约礼,犹木有菁华也。今之言学者,空谈玄妙,直以《诗》《书》为糟粕,是欲求菁华而先翦其枝叶,菁华终不可得也。或又孜孜于辞章故训,不复进窥乎大道,是误以枝叶当菁华,又不知枝叶之未可持也。
显然,多元课程的融合与“先博后约”的课程策略,是南菁书院的核心教育理念。要以枝叶培养菁华,先后培育出曾国藩和左宗棠这样经世致用的菁英。由此,南菁的学术取向和课程旨归清晰地呈现出来。
在南菁书院,立东汉经学大师郑玄(127—200)、宋儒学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两位先生的木主而祭祀,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实事求是”治学精髓,同时也佐证了南菁书院这种超越南北和“博文约礼”的治学理念。“西学东渐”浪潮中的南菁,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八(1902年1月17日)上呈朝廷学堂课程框架,充分体现了这种办学思想。以树喻之,“礼”是树的精华,而“文”则是树的枝叶。基础教育是普及的,但也服务于优秀人才的培养。民族振兴需要培育菁华,但也决不可剪去枝叶,因为菁华就蕴含在枝叶之中。这无疑就是南菁书院文化中某些能体现的当代教育价值部分。要关注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成长,为满足特殊需要规划、设计和开发个性化课程,理直气壮地切实追求适合时代要求的教育,努力让每个学生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南菁育人师范:结识名师
道德文章,为人师表。南菁书院的创办主体为江苏学政,是两江总督管辖的学府,一时名师云集,书院山长和教习都以文化育人为己任,实施个性化的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书院逐步形成了“忠、恕、勤、俭”的院训。清光绪十一年(1885)底,王先谦接任黄体芳为江苏学政。上任伊始,亲自撰写了《劝学琐言》,告诫学子:“为学所以明心,所以养心。人之放心,最难收束,惟读书可以制之。”倡导做人重于学问的道理,他说“经济非可空谈,人苟心术不端,意气不化,虽才美如周公,只足以作恶偾事。能由正学生正识,以实心行实事,即绝大经济也。”,还建议学子“当熟览史书,以古为鉴,至当代掌故,尤贵讨究精通,奉为准的,则道学、经济、文章一以贯之矣。”山长和讲习身先垂范,付诸实践。
身体力行,诲人不倦。黄以周为南菁学子留下了“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训示,“令学者各取其所长,互补其所短”。吴稚晖认为,这是先生“最精警的话,古人从没有这样说过”,他告诉好友“一辈子忘不了这八个字”。黄以周还经常教育诸生做学问不要囿于一种学说,应博采众长,他以为“郑注之义理,时有长于朱子;朱子之训诂,亦有胜于郑君”。南菁名师的德行和学问对于南菁诸生的影响是终生难忘的,造就了近现代一批卓有成就的“国学名师”。翘楚如唐文治,在无锡创办“国学专修学校”时,“惟追先生之训,恒自警惕”,以此时时策勉自己。
南菁学风遗韵:了解诸生
晚清至民国,南菁是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块圣地,氤氲着自由研习的好学风。胡适曾多次提到南菁书院。1923年12月10日,他在南京东南大学作《书院制史略》的演讲时说,南菁书院“其自修和研究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治学严谨,勤学成风。南菁诸生平时博览群书,勤于自学,做笔记,写心得。据清代钱崇威回忆,课卷(即大作文)每月一次,由山长命题,三天内交卷。书院还规定课生须写日记,备札记,并需按时交院长检查。其中,札记主要叙说课生的研习感悟,必须上交山长或讲习评阅;而日记则是给自己一个人看的,但也必须定期检查是否完成。即便书院后来改成学堂,仍循此规。吴稚晖当年曾因故漏写数日,院方征收日记时,他不得不补写完整后才上缴。
南菁诸生做读书笔记各有不同的方法。每人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笔记。有的只是摘录观点及其出处,有的则评述成文。更用心好学者甚至分“看”“读”“杂看”“杂检”和“略看”数种体裁及内容。
凡看书,首尾读迄曰“看”;复读曰“读”;一书随手揭看,不能详举其目,曰“杂看”某书;并未用心看者,曰“杂检”某书;看一二篇者,曰“略看”某书。
自主研习,优学为师。南菁“院中有十万卷藏书”,学习环境宽松自由,教学以课生自学为主,山长、讲习指导和解惑为辅。教导诸生为学之法,贵在“静”和“专”,举一反三,活学活用,还必须有“恒”。山长黄以周及其课生吴稚晖如是言之:
学问必由积累,初无顿悟之方,而积累全在“静”“专”,亦无袭取之道。人有终日读书而掩卷辄忘者,病在不静;有终身读书而白首不名一艺者,病在不专。静则记性强,专则学术成。
夫学问之道,藏修游息,只需行之有恒,不贵进锐之功。
上述三字要诀被南菁诸生奉为治学圭臬。他们研究学问刻苦异常,有时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大家终日相聚在一起,共同学习,潜心探讨,互质疑义,增进学问。“每当春诵夏弦,读书露坐,讨论经史疑义,滔滔辩论,得一新知,相与欢笑以为乐,不炫异而矜奇,惟实事以求是。”因仰慕对方的学行,南菁诸生相互拜师学艺,蔚然成风。如泰兴于璠、松江雷瑨执弟子礼,问学于太仓的唐文治;而唐本人则钦佩于璠讲解经学大旨,“心已器之”,“心折余言”,回执弟子礼。南菁诸生多才多艺,研习经史辞章之余,也常抒发传统文人的雅兴,喜欢以琴棋书画作为消遣。 南菁及其书院志的历史文本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自晚清至今,南菁由书院而学堂,进而发展为高级中学和实验学校,文脉绵延,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