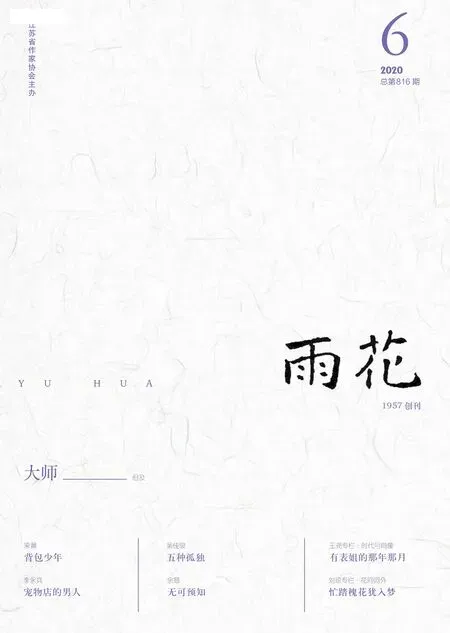大师
但 及
1
难道他真做成了?阿舍满是疑惑。
天成站在对面,滔滔不绝,神采飞扬。这是近几年来,他最得意的时刻。阿舍好久没去他的工场了,现在他宣布,他成功了,他做成了一对高级玫瑰椅。他还拿出手机,翻出照片,递给阿舍。放大,看细部,看榫卯,看光滑的扶手。
“看看这工艺,浑然天成。就像我的名字一样。”口气里充满了自豪。
天成是他的师兄,都是木工,师承同一个师傅。阿舍既高兴,又惆怅。
“你过来看,近距离地看,我准备好烟和茶。”两人在路上,都骑电瓶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警察在吹哨子了,于是,他们分开了。
“下午就来。”阿舍说。
下午,阿舍果真去了。作坊在芦席汇,一间老屋里。门前有一棵老梅花树。两侧是厢房,一边是睡,一边是吃。中间成了作坊,东西堆得像山头,天成在后面搭了个石棉屋,开了天窗,锯床、手工台和打磨机都放在那。他说,这里简陋,但光线好,乱七八糟的,像叫花子的房。阿舍想,怪不得他老婆要离开。
玫瑰椅放在大作坊里,一进门,就看到了。两把椅子,齐整地放着。椅子是大红酸枝,没油漆,打了层蜡,亮锃锃的。比照片漂亮,也更有质感。两张椅子,就仿佛两个美人。因长相动人,阿舍甚至产生了手足无措感。天成给阿舍递烟,但阿舍没接,手在摸椅子,舍不得缩回来。手触到红木,坚硬,光滑,还带一丝凉意。手就在椅背上来回地蹭,线条柔美,手感好极了。
“好椅,你做了两把好椅。”每一个榫卯,每一处都严丝合缝。他们研究明式家具已有段时间,但真动手就困难重重,现在天成终于凭他的聪慧做成了一对。阿舍心里空荡荡的,也酸溜溜的。
“怎么能弄得这样完美?我甚至怀疑这不是你做的。”阿舍这回接了烟。
“我就对着古斯塔夫的书琢磨,我要破解这个谜,非破解不可。我反复地琢磨,直到想通为止。” 古斯塔夫之谜,这个叫法是天成首先提出来的。他说书里面充满了谜,他要一一破解。
“废了多少木头?”
“不知其数。我就这样,做了废,废了做。一直在循环。”
说完,天成哈哈笑。两人在玫瑰椅上坐下来,一人一把。天成很自得,手抚椅沿,跷着二郎腿。阿舍开始吐气。“你就照古斯塔夫说的做吗?”他问。
“古斯塔夫吗?我翻烂了,就好像看了菜谱去烧菜,实际是烧不出的。他只有尺寸,只有尺寸你什么也做不成的。”天成去了石棉屋,过了一会儿,找来了古斯塔夫·艾克著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书到了阿舍手上。他们都是明式家具的崇拜者,这可不是一般的崇拜,是极度崇拜。
书已变形,封面也起皱了。“再看也没用,再看也做不出。”天成说。
他忽然明白了天成的意思,那意思就是你阿舍再努力也做不出,这让阿舍心里不舒服。“你了不起的,天成。”阿舍故作镇定地说。
“我就是钻研,钻研,再钻研。我就不信,解不开这个谜,这真的是个谜,连古斯塔夫也解不开。我不信我做不好,我不信邪,我本身就是邪。你现在看看,这不是做出来了吗?我就是能做的,我说到做到。”他趾高气扬。
“你这水平,在市里是一流的。”阿舍说。
“岂止市里,笑话,在省内,在全国,也是一流的,这不是自夸。谁能做到这样?谁能?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能超过我的人,一个也没有。”这吹牛是要有资本的,现在天成有资本了。他把附近的木匠都打趴下了。望望天成,他天庭饱满,红光满面,自得而又骄傲。
“他娘的,神气什么呢?”阿舍想。
阿舍在作坊里转了半天,照理天成做出来,他应该高兴,但他高兴不起来。临走前,他向天成借古斯塔夫的书,天成有些犹豫,想了想说:“借可以,但必须还回来。这是个孤本,我好不容易弄来的。”
2
阿舍把玫瑰椅的照片放在微信,引来一片叫好。好多人竖起了大拇指。
许威来了电话。
许威是个商人,有自己的服装厂,还做外贸出口,喜欢古董和文物。许威的店,他去过,在市中心,布置得古色古香,风雅里有种淡定。他的边上围了一帮人,有艺术家,有刻字人,也有一些“刨地皮”的文物贩子。有一回拳术比赛,阿舍在湖滨公园表演,许威看完后,一个劲地鼓掌,说打得好。那天,阿舍得了个第二名,打的是一套长拳,虎虎生威。许威是赞助商,赛后给了名片,他们就这样认识了。这回许威主动来电话,这多少让阿舍吃惊。
“我想见见这个人。”许威说。
“噢,他是我师兄。”
“我想买那两把玫瑰椅。”
“不知行不行,他没说过要卖。”
“认识一下,去看看那两把椅子。做个朋友也行啊。”
阿舍陪他去的那天,正好下雪。车由司机开,许威和他坐在后排。雪卷在空中,忽高忽低,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暖色的灯光打在冷色的雪地上,轮胎碾过发出吱吱声。天成用一个铁锅烧木炭在取暖,屋里没空调,不过充满了木香。天成说,许老板是贵客,在这么个天气赶来,让这个屋子温暖了。
三个人嘻嘻哈哈说笑着。天成打开一瓶烧酒,给每人都倒了点。大家围着火堆,烤着,再抿几口白酒。
“看到照片,我就赶来了,你这个了不得。你说个价吧,我想买。”许威指着不远处的玫瑰椅说。
天成摇了摇头,说不卖。
“开个价吧。”许威又说。
天成的头发都白了,看上去更显老,其实也只有六十。他脸上都是皱纹,嘴唇也被烟熏黄了。他站起来加酒,许威的杯子里又添了好些。
“这是做着玩的,不是卖的。如果要卖的话,成本就大了。做这个是不计成本的,前前后后,不知费了许多时间,阿舍知道。所以,这个是不卖的,我做出来让朋友欣赏。比如你今天来,一起欣赏,就很好。”
“这个我明白,手艺就是这样做出来的。谈钱就俗了,是不是啊?”许威开玩笑说。
“钱当然是好。再说,钱谁不喜欢呢?但这个是算不来的。我的心血值多少钱?我死掉的脑细胞值多少钱?我花下去的时间值多少钱?有些东西是算不来的,比如友谊,你能论斤两吗?”天成说。
“也是,也是。我明白你的意思。”许威点头。
阿舍明白,许威是不喝这种土白干的,在家里肯定喝洋酒,但这会儿他照样把白干喝得很香。“没关系,你再想想,或许有一天你想卖了呢?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排在第一啦。”说完,他把杯子递过去,与天成碰了下,许威把酒都干了。
回去时,雪变大了,漫天飞雪在空中舞动。
“这人特别,是个人才。”许威道。
“他是不一样,为了手艺,离婚了,跟儿子也闹别扭。他向来一根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看得出来,他很真诚,这个时代真诚的人不多了。”
阿舍不完全认同:“他没多少收入,做起事来不要命。钻研东西的话,会沉在里面。他有点疯癫。”
“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精品。这是宿命啊。在我心里,他倒是崇高的。”
“崇高?可有时候不值的,他妻离子散啊。”
“像他这样的人,世面上基本没有了。说真的,我今天看了还有些感动。阿舍,谢谢你带我过来。”许威这样说,阿舍便不吱声了。
雪横过来了,一团团地砸向车子。雨刮器不时摆动,整辆车就露出两个窟窿眼。
3
“我听到木头的声音了,真的听到了,很清晰。”有时,半夜,天成会给阿舍打电话。
“是木头开裂的声音吧?”
“不是,是木头的说话声,真的是,很轻柔地在说。我也说了,我们就这样对话了。”
阿舍的妻子说天成病了,要么是神经系统出问题,要么是脑子搭错,总之是不正常了。阿舍不这样看,天成能读出木头的声音,是有可能的。他没有到天成这个层次,但他能理解一些。他喜欢听天成说话。听天成说这说那时,总会有收获,仿佛从中偷到什么宝货似的。
天成六十,比阿舍大十五岁。天成出道早,很早就做木工,桌子、凳子和柜子都做。他说,最早是在下放的时候,在乡下弄了间房,在里面捣鼓。实际上,这一代人学工学农,粗鄙得不得了,都是自学或旁门左道学来的。后来,他们一块儿拜的师,天成肯钻研,有悟性,以古人为师。有时,他跟师傅也要争论,师傅吃不消,说他张狂,背后总说收错了一个徒弟。
一天,天成来了,骑着那辆快散架的电瓶车。车在墙边一靠,就叼着烟,面色阴沉,进了阿舍的作坊。“情况有些糟,师弟,能借我些钱吗?”
阿舍愣了一下,不吭声。
“我跟你说话呢,能借点钱吗?我会还的,一定会还的。”
“我买了房。房子涨得离谱,老婆催得像债主,只好咬咬牙买了。现在欠了银行一屁股债。”
阿舍说的是实情。他的确在三个月前买了秀湖边的中梁一号。
天成踩了烟屁股,坐在那里闷闷不乐。天成儿子考上了大学,是个三本。天成说:“每年要供学校三万,怎么那么贵呢?”
后来,他又站起来,看阿舍做的东西,东看一件,西看一件。阿舍在刨机上冲板。有个工地开工了,需要做吊顶,要冲许多木材。他与天成不同,除了木工活,还接装修。装修容易赚钱,但天成不同,天成看不起装修,说那不是技术活,好像用纸糊一下,中看不中用,唬人的。
“你儿子跟你不亲。”阿舍说。
“不亲,也是儿子啊。他要钱,总要给的。我已经欠他了,再不补就来不及了。”对于儿子,天成说过多次,他结婚晚,好不容易有了个儿子,但儿子对他很凶,说话很冲。这些天成都忍了。在外人看来他对儿子没任何办法。他自己可以苦,但不能苦了儿子,尽管他认为儿子做什么事都不像样。
机器停了的时候,他突然一把拖住阿舍的手臂:“就三万块,周转一下,你肯定有办法。怎么样?就三万。”
三万元,阿舍是掏得出来的,但他想,万一借了还不出怎么办?天成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你给他三万,基本是扔到了水里,阿舍就是这样想的。
“我每个月都在还贷呢。”阿舍还是不想借。
“唉,我理解。你是我师弟,不会骗我的。”他默默地说。过了一会儿,突然,他喉咙响了:“狗屁!阿舍啊阿舍,你怎么像我一样无能呢?照理你过得比我好,你还弄装修,装修是很赚钱的。但你也没赚到什么钱!你啊你,还弄什么木匠呢?这木匠是没有前途的,你不要再这样了,去弄点挣钱多的活。你不要像我,我不是你的榜样。”
说了一堆话后,一个转身,他竟走了。过了五分钟,天成又回来。站在门口,一副腼腆的样子。
阿舍想,是不是又碰上其他的事了呢?
“刚才的话不算数,当作放屁好了。你不要往心里想。一起做木匠吧,我们能做出好东西来。阿舍,你行的,你好学,而且年轻,一定要好好做。”
看到天成如此,他又改变主意了。“好的,师兄,我借你。”话都已经在嘴边,却一直没说出来。
“记得啊,前面说的都不算。”说完,天成笑了笑,骑着破电瓶车走了。
4
天成把玫瑰椅“垫”了出去。
他“垫”给了许威,他说这不是卖,是暂时“垫”一下,等有钱了,再把玫瑰椅赎回来。“这相当于去当铺,把玫瑰椅当了。”天成说。事后,阿舍了解到,许威出了三万块钱。
阿舍想,自己过分了。他应该借钱给天成的,但现在已经晚了。
遇到天成的时候,天成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事:“暂时寄存下,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们签了协议?”
“签了。本来想当一把的,但许老板不肯,他一定要两把。”
“就同意了?”他不解。
“一把两把是一样的。以后,等有钱了,再赎回来。这事就这么简单。”
许威把两把玫瑰椅放到了市中心的门店里,放在一个醒目的地方,供人参观、品鉴和欣赏。看到的人都啧啧称奇,说是珍品。他叫了摄影师布光拍摄,照片登到了《时尚家居》杂志上。为了介绍这两把玫瑰椅,还请作家撰稿,用生动、准确又形象的文字,对这两件艺术品进行推介,并把天成称为大师。许威又订了一千份杂志,来店里的人都会看到杂志。后来,本地的报纸也进行了报道,登载照片,还附上了更多的文字。一时间,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两把稀有的玫瑰椅。
阿舍手捧杂志,忍不住给天成打电话。一接通,就调侃道:“大师,都称你‘大师’了。”
“不对,我觉得不对,这是个阴谋。”
“阴谋?叫‘大师’也是阴谋?”
“我觉得这个事不妙。我有预感。有时我的直觉挺灵的。”天成说。
“怎么说呢?”
“他在炒作那两把椅子。实不相瞒,我担心要不回来。”
阿舍想了想,没那么悲观。尽管许威是个商人,但他出手阔气,有义气,且爱文化。他觉得,如果他去说的话,或许许威愿意送三万给天成,他是有这个把握的。天成把人看庸俗了。
“大师,是社会对你的承认,是一种荣誉。”
“哪敢称大师啊,你看看古人,那才是大师。我算个屁,雕虫小技而已。”此时的天成又变得谦虚无比。
阿舍看不惯天成的做作,那是假的,装的,他内心狂着呢。师傅在世的时候就说,天成太骄傲,他要吃亏的。他一直看不起周围的人,包括阿舍,甚至还包括他们的师傅,他有时话中有话地讥讽几下师傅,因此,每次天成装腔作势的时候,他最反感。天成时而高傲得像公鸡,时而又低微得像蚂蚁,他就在这两个角色间转换。前一句话还是谦虚,后一句话就变成了自负。他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像正负两极弄错了,接到了一起。
临近春节时,天公不作美了,一直下雨。那日,雨正大,门“哗”的被推开了,天成穿着雨披来了。脱下雨披,拍了拍身上的雨珠,人好像瘦了许多。他两颊紧缩,情绪低靡,一进来就坐下,直喘粗气。阿舍给他点烟的时候,看到他的手指和手掌都裂开了,涂了一层什么油。“完了,完了,真有那种感觉了。”阿舍忙问发生了什么。
“什么也没发生,就是糟。最近做的那几件都不成样子,糟透了。”
“你被‘大师’叫晕了。”阿舍逗着说。
“别开我玩笑,我没感觉了。做玫瑰椅的时候感觉挺好,好得不得了,一下子就进去了。现在就是不行,一点也进不去,还走神。我是不是完了?阿舍,不做东西,比死还难受,我好像身上长满了疮,有好多的虫子在爬,在吃我。”
“你只是鼻子塞了,像感冒的时候,塞一下,不久就会通的。”
“这些日子我一直难受。”
“是不是病了?去看一下医生吧。”阿舍感觉到天成的瘦,腿在裤子里像麻秆儿了。
“我为什么越活越难了呢?阿舍,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你有时候还像个孩子,怄起气来,恨不得把自己的肠子扯断。你要学会对自己宽容,我觉得你把你自己当成了敌人。”两个人坐在门口抽烟,看一阵阵的雨飘进走廊。
天成把烟屁股扔进雨水里:“师弟,你这话漂亮,我就是这样,把自己当敌人了。我就是自己的敌人,这太深刻了。你好像是学哲学的。”
天成低垂着头,阿舍有些得意。
“师弟啊师弟,你还是懂我的,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你最懂我了。你说得对,我逼自己逼得太紧了,把自己当成了敌人。怪不得,我会这么不舒服,我是自己对着自己开枪啊。”天成拍着那双开裂的手说。
“可能病了,去看看医生吧。”
“不看,没心思看,再说也没时间。”天成的顽固又表现出来了。
“你这是在寻找理由,但这不是理由。说到底,你是怕生活。像你这样的人,内心善良,但在生活里却是个弱者。”阿舍想好心劝劝他。
没想到此话一出,天成脸色大变:“什么?你说我弱智?”
“不是弱智,你听错了。”
“我听得清清楚楚。”
“不是,我没有这样说你。”
“你说我弱智。你是存心看不起我。你一天到晚叫我大师,也是假的。你巴不得我做不好,我做不好你就开心。我早看出来了,你在敷衍我。你是有钱的,但你就是不肯借我,你以为我不明白吗?我明白着呢!”天成像是找到了突破口,怒气涌了上来。
“你误会了。”阿舍想解释。
“误会?我们之间会有误会?你一直假惺惺地对待我,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太假了,师弟,你做人太假了。”
他越说越火,最后竟站了起来。走时,在门槛处还绊了一下,摇晃一阵,差点跌倒。他没拿雨披,直接骑着电瓶车冲进了雨里。阿舍连叫几声,也没唤回他。
阿舍拿了雨披去追,那个雨里晃动的背影根本不理他。
5
天成住院是春节以后的事。
天成得了重病,是绝症。这消息来得突然,令阿舍震惊,因为上次那件事,两人有了不快,想不到现在竟有那么大的变化。无论如何,他要去探一下,也把那件事说清楚。阿舍心急火燎地赶往医院。
天成在病床上躺着,胸口都是线头,像是背着心脏监测仪。眼前这一幕,令阿舍不适。天成闭着眼,阿舍进去也没反应。于是,他推了推。半天,天成才睁开眼,一行眼泪淌了下来。阿舍的鼻子酸了。
眼前这人瘦得不成样,两颊陷凹,如果在大街上,阿舍肯定认不出来。天成把那些线头都拆了,扔到一边。“去他妈的。”他说。
“这不行啊。”阿舍说。
“死就死吧,这样活着没意思。成天在医院发傻,活着比死还难受。”天成眼眶发黑,像涂了黑炭。手还在颤,被子也是一抖一抖的。
“很想闻闻木头的香味。这里臭死了,没有木头的香味。”他努力地撑起身子,被阿舍按了回去。
“等你好了,就能做了。不要急,越急事情越办不成。”阿舍懂得天成的想法。
“怕是回不去了。师弟,上次对不起,我胡说八道。你也知道,我有时候会这样,你知道就会理解的。我回去以后后悔死了,我一直在后悔。你明白吗?你来之前,我还躺在床上后悔。”
“是我不对,我乱说让你生气。”阿舍也认错。
“哎哟,你道什么歉呢?是我道歉才对。你知道吗?我那天回去就发烧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后悔过。连你我也要得罪,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天成握着他的手。阿舍觉得天成很陌生,这个病床上的男人与在工作室里的男人不是一个人。
“我还想做,做出更好的。我已经在准备了,可想想那两把椅子的命运,真是伤心。”
说着说着,天成居然哭了。他的声音嗡嗡的,拿起被单擦眼泪。
“是许威拿去的那两把吗?”
“他不肯还。我去过了,他不肯了,还说替我做了许多,替我包装宣传。说来说去,好像还是我欠了他。”天成眼圈红了,像个无辜的儿童,用一种期望的目光望着阿舍。
护士进来了,一进来就训斥。最后,护士又把线头重新装好了,并命令天成躺下。天成噘着嘴,不耐烦地重新缩进被窝。他躺在那,像是受了罚似的。护士走后,他的手在枕头下摸索,摸来摸去,掏出一个皮夹。他手上的皲裂很严重,有些地方还用橡皮胶胶着。掏了一阵,弄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来。
“当条:今有两把玫瑰椅当给许威先生,共三万元。以后待钱凑齐后,即归还玫瑰椅。”
后面有两个签名,一个是天成,另一个便是许威。
“无赖!”天成喃喃地说。
天成的目光投过来,像在等待他的判决。“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是流氓。”阿舍说。
“岂止是流氓,流氓还讲道理呢。”天成无力地说。
“你还他钱,他不给?”阿舍问。
“我现在没钱,可我试探过,他就是不肯。他说已经买下了,成交了。如果真要卖的话,这两把椅子十万也不够。”说完,天成闭上了眼睛。病房内有股不好闻的味道忽隐忽现,像是尿臊味,这令阿舍难受。他摇了摇天成,想把那张纸条还他,但天成没拿。
“帮我去要。这椅子要般配他的人,这个人不配。”
阿舍手握纸条,一片尴尬。他想,这事难办啊,但他又不好意思拒绝。
“求你了,帮个忙。”天成那眼神更可怜了。
从医院回来,阿舍没有去办这事,一直拖着。许威与天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清楚,再说,他听到的也只是天成的一面之词。那纸条他一直放在自己的包里。好几次起兴,他都想到许威的店里去坐坐,但一旦真要去,退堂鼓又叮当响了。
阿舍喜欢古斯塔夫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古斯塔夫把明式家具一一作了解剖,长短高矮,里里外外,都作了丈量,但那只是一堆图片和尺寸,没有具体的施工说明。阿舍能看出其中的好,真要上手又畏惧重重。他明白自己做不出来。明式家具里包含了内在与力量,在极简之中渗透出复杂与无限来。即使一个弧度,也蕴藏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美。他无法把这种复杂悟出来。说白了,就像变魔术,他知道奥秘,就是变不出来。这就是他痛苦的地方。
他不断地翻看那本起皱的书,想象着天成曾经在里面探索、摸爬和求证。阿舍也动手,可一上手,所有的毛病和缺点便暴露无遗。
过了几天,更大的不幸传来:天成死了。
6
葬礼办得潦草。送别那天,阿舍买了大花圏,送了两千元钱。
前妻没出现,只有零星的几个亲戚,也是不冷不热。阿舍打听到,这是天成欠他们钱的缘故。这些钱变成水了,再也要不回来了。天成的儿子从学校回来,高个子,表情冷漠,对外面来的人都不理不睬。报社的人倒是来了,用录音机采访人,许多人都不愿谈。只有一个亲戚站出来,他说,天成不该做木匠,他随便做什么都比现在强,做木匠真是害了他。在他们看来,他既没有挣到钱,又把自己贴了进去,弄得人不像人,那人说完便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面对这葬礼,阿舍充满了失望。他不能容忍大伙对师兄这样一个态度,芸芸众生真是太实际了。不知怎的,天成一死,他真觉得天成是大师了,特别是自己研究古斯塔夫一事无成以后。他觉得天成是有特别功力的。
葬礼后,他几次把那条纸片取出来,一遍遍地看,最后决定去找一次许威。这事总该有个了结。
他没有去许威的门店,而是直接去了他住的香堡别墅。按了门铃后,许威来开门。看到阿舍,许威有些惊诧。的确,不请自来,换了任何人都会惊讶。“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许威话里带点不欢迎,但阿舍还是跨了进去。别墅很大,放满了古董,有青瓷、宝剑、木雕,还有许多中外摆件。这里简直成了博物馆。
玫瑰椅放在醒目的正中位置,许威也不避,把阿舍引过去。一人一把,在玫瑰椅上坐了下来。
许威倒了杯洋酒,是马蒂尼XO,递给了他。许威说:“正要找你,天成死了,那些古董的修复只有你能胜任了。”许威收古董,有些破东西不成样子,需要整修,偷梁换柱,再换大钱。他要跟阿舍谈这个。
阿舍没有喝杯中的酒,他把口袋里的纸条拿了出来。“你对这个不陌生吧?”他问。许威愣了愣。
“你拿这个什么意思?”许威道。
“天成说,让我把那两把椅子要回去。他委托了我。”
“兄弟,别闹了,我们喝酒。这事情已经了结。”
“是天成死之前说的,让我要回去。他就是这么说的,也可以说是他的遗嘱。”
商人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好像要从中找出某个破绽来。“他这人有时候情商低得离谱,我说了,这事情已经了结。”
“那纸条怎么会在我手里?”他舞了舞那纸条。
“跟你说了,这事情早解决了。”许威递过酒杯,碰了碰他的酒杯,以示友好。阿舍还是没喝。气氛在变化,静默的状态里有些难堪。
这时,阿舍突发奇想,想扛走椅子。有协议在,他怕什么呢?“这样,我把椅子搬回去,三万块钱事后会付。”
“不要搞错,这是我家。”许威吼了起来,但阿舍仿佛没听见。
当阿舍伸手搬椅子时,两个人扭到了一起。
“我是替我师兄行道,你这样霸占毫无道理。”
“放下,你命令你放下。”许威的喉咙响了,见他不放,干脆一拳过来了。
阿舍练过武功,耍过大刀、三节棍和红缨枪,于是轻轻一掌就出去了。他完全是无意识,但这一掌还是见到了分量,只见许威摇晃一阵,撞到了墙上。许威不服,再起来。这一回,阿舍又来了一掌,许威摔得更远,连地上的花瓶也碰到了。哗啦一声,人倒地,花瓶也碎了。
“不要怪我下三滥,逼急了,我什么也做得出来。”这是他练武以来,第一次这样无耻地恐吓别人。
许威坐在地上,一脸无辜。
室内灯光柔和地落在玫瑰椅上,椅子显得静谧而安详。
“天成,安息吧,我替你拿!”阿舍用手抚摸那椅子,感受着每一个细节,椅子带给他惊人的活力。“一对好椅啊。”他心中这样赞叹道。
“要不这样?这椅子可以传世,你拥有一把,我也拥有一把。”许威起身,边拍打着衣服边这样说。
阿舍眼前一亮,一时还反应不过来。
“兄弟,如何?”对方又问。
阿舍有些尴尬,也有些出乎意料,心想商人到底是商人,头脑发达,反应快。
心中对那人的反感在迅速消退,阿舍甚至觉察到某种真实和可爱。他把眼皮垂了下来,有些不好意思,他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正在靠近的身影。
“我们谈谈吧。”商人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