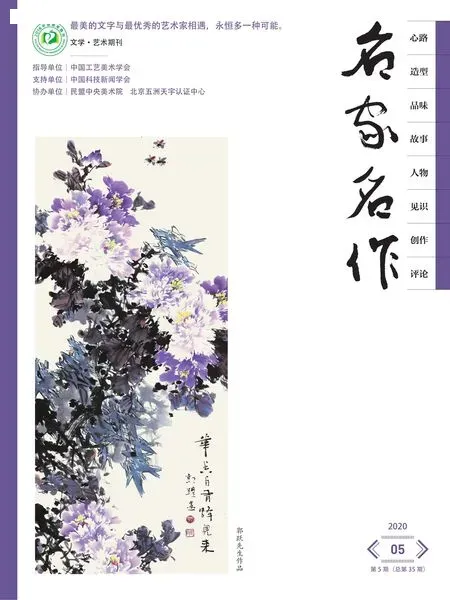“二十四节气”主题书法展的策划思路与实践步骤初探
宋江悦 张文豪 彭敏敏 徐淑坤
一、“二十四节气”主题书法展的切入点:二者都赋有人文情感
随着社会发展,二十四节气不再仅仅是气象学或记时刻度上有意义的日期,也不再仅仅是农业生产的指南针,它更广泛深刻地植入了民俗和文化。它影响了中国人的饮食、文学,乃至情感等方面。花知时而开,人顺势而立,与天地唱和,与万物相谐,二十四节气逐渐演变出了天、地、人相合一的共生观念。农谚说“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清明节前后气温升高,是一年中耕种的大好时节,在这天,人们思先祖、放纸鸢、吃青团,节气逐渐与节日结合起来,给它赋予了情感和人文内涵。小满时节,万物繁茂,生长最为旺盛,北方地区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已开始饱满。二十四节气里,有小雪,便有大雪;有小暑,便有大暑;唯独有个小满,却没有大满。小满一词,巧妙地表达了古人“欹器以满覆,扑满以空全”的思想。虽为节气,但用于比喻人生,亦为巧妙,恰好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理念。
对中国人来说,二十四节气是一个共同的认知体系,体现的是一种集体认同的情感纽带,体现的是我们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创造力,它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古人通过节气诗或抒发感慨、寄托心志,或吊古伤今、怀乡念友,或寄寓人生悲愁、忧国忧民等情感。
从古到今,好的书法作品,情感注入亦必不可少。如孙过庭在评论王羲之书法时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说明了王羲之的不同作品表达了不同的情感。又如颜真卿怀着悲痛的心情给牺牲的侄儿写的祭文,其中由行到草的书写节奏、力透纸背的线条点画,乱头粗服的章法等,无不说明了没有那种特定的悲痛情感,就写不出“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那样的作品。因此说,书法创作是书家精神状态的表达,是情感的表现。古人也讲“字如其人”,就是说一个人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认知,通过笔墨语言展现出来。
二、“二十四节气”主题书法展的实践步骤
1.书体风格与节气有机结合
书法有五体,风格多样,可以将艺术形象与节气的内涵有机结合。其核心就是以书表意,以不同的书体、不同的风格演绎二十四节气的不同内涵。我们将节气以四季为分界线,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块,便于宏观阐述。
在书法中,甲骨文和金文因其产生时间早,处于书法的萌芽阶段,与春季万物复苏的特点不谋而合。并且二者具有较高象形性,对于节气的表达也会更加生动。因此在展览中,我们可以选择甲骨文和金文来表现春季的节气。
夏季气候多富变化,其节气可用行草书风格为主来表现。行草书富于变化,“心电图式”的线条旋律与夏季节气的气候具有共通之处。同时行草书也是最能体现书法“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功能性。
历来收获的喜悦和悲秋的惆怅共存于秋季,秋高气爽与悲苦凄凉齐驱。因此,各书体中或厚重饱满、气势磅礴;或冲淡洗练、悠然从容的书风都可用于秋季节气的书法作品。
冬季幽静寒冷,纯洁寂静。古代书家一般以正体写碑,用正体或古体书额,以显庄重。曹魏时期,正书字仍然是隶书体,古体字是篆书体,用这两种字体写碑,才称得上“作字得体”“体用得法”,“得体”又“得法”,才是“方正循纪”。在书写冬季作品时,我们可以利用篆书和隶书的庄重感和冬天的安静肃穆达到契合。
此外,如“春分秋分,昼夜平分”这样的气候特征,以小篆平衡对称、整齐均匀或隶书字体宽扁、左右舒展的字形来创作亦恰到好处。
2.书法形制与节气的结合
此展览中既可利用各种传统书法表现形式,如条幅、楹联、条屏、扇面、册页、手卷等,又可大胆尝试各种纸、布、绢、竹、木甚至砖、瓦、土、石等载体,使得每一件书法作品都能够将每个节气情景化、立体化。
立春不仅是二十四节气之首,亦是中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立春习俗主要有吃春卷、鞭春牛、探春游玩、贴宜春字画等等。在立春时节,人们在门楣、门壁上张贴的字称“宜春字”,所张贴的画称“宜春画”,如“迎春”“春色宜人”“春暖花开”“蜡梅图”“一门欢笑春风暖,四季祥和淑景新”等,院内、屋内墙上也贴“春”或“福”字等。展览中可利用“宜春字”的风俗,以红色宣纸为载体,配以金色或黑色墨汁进行书法创作,在展览中营造出春意盎然的氛围。
雨水节气前后气温回升,降水开始增多,展览中可运用纸伞作为书写载体,书写效果可用淡墨表现,以契合烟雨蒙蒙、雨滋水养之感。在古建筑中用于排除雨水、保护椽头与墙面的瓦、瓦当、滴水等建筑部件,近几年艺术家利用这些载体进行书法创作已屡见不鲜,展览中可加以利用,在青瓦上施以朱砂文字,古意横生又极富观赏性。
“春雷响,万物长”,惊蛰前后春雷震响,在泥土里冬眠的动物逐渐苏醒。在书法中,鸟虫篆作为一种独特的字体被篆刻家们用在了篆刻艺术创作当中,它将常见的小篆线条加以盘桓弯曲化处理,并加以细长的鸟、虫、龙纹装饰,极富有活泼性。在对应的惊蛰节气的书法作品中,可大胆地将鸟虫篆运用到书法作品中,以表现惊蛰时节万物萌动的特点。
古人云“阳春三月试新茶”,清明节前,是茶叶生长最好的时节。茶叶经过冬天的潜伏,饱蕴天地精华,因此有“明前茶,贵如金”的说法。清明节气的书法作品可以书刻于瓷器与紫砂壶等茶具之上。
芒种是一个丰收与耕种并存的节气。展览中可以长卷蝇头小楷形式,以字寓种,以纸比田,呈现一片播种气象。在书法艺术中,金石题跋是古代文人们对钟鼎等器物拓片进行考证、鉴赏、记事、表情的书法形式。芒种节气对应的书法作品可以利用铜斛、方升等古代与农业相关的器物的拓片进行题跋,以示农业丰收。
在书法碑刻中,因时间久远,碑刻石面风化剥裂,导致一些文字残泐,在拓本中残泐的地方呈现出与大雪纷飞相通的意象。汉代《李孟初神祠碑》正是因石面剥落,碑面残损,其拓本便有了“明月照积雪”之誉。大雪节气的作品可用胶矾作墨书于白宣之上,书毕再以国画中弹矾画雪的技法,反面涂墨,从而制作出石刻泐损、大雪纷飞的意境。也可用黑色宣纸配以白色、银色颜料进行创作,也能营造出银装素裹的氛围。
同时书法作品在装裱上也有多种形式,或框或轴,或各色镶料,在视觉上给人的感觉各不相同,在春分、清明等节气的书法作品上,装裱中可施以绿色镶料;在夏至、大暑等节气书法作品上,装裱中施以红色镶料等。也可运用惊燕、锦眉、局条、签条等装饰加工,创造出既贴切节气特征又符合美学特征的装裱形式。
3.历代节气书法作品的临摹与演绎
古代书法帖中有不少与节气相关的书法作品,也许书家本无意于节气与书法的结合,但却真实反映了节气与情感相关的内容,也融入了当时书写。例如“快雪时晴,佳想安善。”出自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此帖表现出雪后天空初霁的愉快心情并问候亲朋之意。“大雪,十一月节,至此而雪盛也。”此帖便与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相对应。“寒切,体中比何似,甚耿耿。仆疾遂不差,眠食少,忧深,遣书不次。”出自王珉《此年帖》。此帖则是书家喟叹年关之交、深冬腊月的忧戚,当是描述大寒节气。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授时通考·天时》引《三礼义宗》有云:“寒气之逆极,故谓大寒”。“雨三日未解,海岱只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不能昼眠,又人少往还,惘惘!足下比何所乐?”出自米芾《焚香帖》。细雨霏霏,三日不歇,每日只得焚香而已。描述的是江南梅雨季节中芒种节气,“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时节雨三日不解,米芾无奈之下发出“足下比何所乐”的感慨。王羲之霜降之前寄给友人橘子三百枚,并附简短书信“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因而有了名垂书法史的《奉橘帖》。此外立春节气有文徵明《进贺帖》,雨水有米芾的《值雨帖》,大暑有蔡襄的《暑热帖》,立秋有杨凝式的《韭花帖》,白露有苏轼的《颍州西湖听琴》等等,可说明节气对书家思维和行为的影响,这次主题展便可以参考、临摹甚至演绎此类法帖,赋予形式和内容更多的意义。
4.展览的主题与布局
主题书法展必然要主题先行,二十四节气的意象如何明确而又不死板地呈现是个难题,不能生搬硬套、表面结合,而要挖掘内涵、深度结合,充分调动书法与节气的可契合部分,从风格到名称,从材料到内容,从形式到载体,浑然一体,不露刻痕又能充分表达,不仅仅是书写水平的检验,还是思想层次的检验。展览的主题与布局休戚相关,从展览的顺序上,以节气为序,立春为首,以大寒为尾,调整作品平面位置与纵向高度整体成螺旋式排布,实现首尾相连、循环往复的效果。渗入多层次的分主题,例如四季划分的营造,通过不同色调的渐变,突出四季的主体色彩,将二十四节气分列其中。节气的展示,既面面俱到,又有主有次,每一个节气都有比较丰富的内容,一个节气也可以作为主体,但对于此次展览,显然要割舍很多,要有详略主次,通过立体的布置展示具有代表性的节气场景。通过作品尺幅的大小、多寡来呈现,榜书、小楷等字体大小、色彩基调的轻重、画面感的分量都可以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