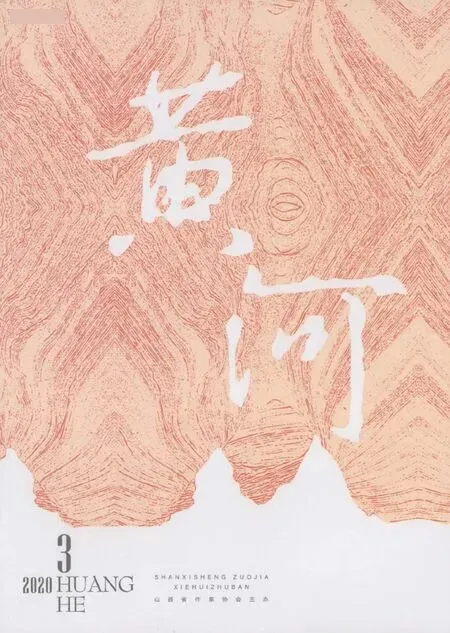古拙而有风致
——赵园文集品藻漫笔
朱航满
赵园在文章《我读傅山》中,论及傅山文字:“‘拙’而富有谐趣。 ‘拙’正属他所好。但拙非即枯淡;傅山所好的,是古拙而有风致(亦即‘韵’)的一类。他本人的文字就一派朴茂,因古拙以至生涩示人以‘人性力度’,那‘拙’于此是文境又是人性境界。其朴其拙,都经了打磨烧炼,类木石之精,精气内蕴,只待由文字间稍泄而已。 ”赵园对于明清之际的傅山多有偏爱,所作的《我读傅山》,附录于她的学术专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且可以作为她的“遗民”研究的典型个案。而她对于傅山文章的评价,用来形容她笔下的文章追求,也是恰当的。在她的治学杂谈《思想·材料·文体》中,亦有论及傅山:“某些题目写作的缘起,就因了被文字所吸引。写傅山,就出于对傅氏那种特别的文字组织的兴趣。 ”与她在《我读傅山》一文中论述相呼应的,在这篇治学杂谈中,有一段很相似的论述:“中国古代文论、画论每每说到避熟、滑,其中有得之于经验的智慧。 为文亦然,治学也一样,写得太熟,太无阻力,太易见好,就需要警戒。 ”
赵园的学术论著或文章,正如她前所论述一样,似乎初读并未见才华,但愈是深入阅读,愈是感到一种“朴茂”之气。显然,她是在有意追求一种特殊的写作风格,乃是慎用“才华”,避免“横溢”。而这种好处,初读者是难以领会的。赵园举例说,陈老莲再三临摹周昉的画,别人说所临摹的画,已经超过了周昉,但陈却坦言这正是自己不及周之处。为此,她继而论述道:“自己的画易见好,因此‘能事未尽’;周则本至能而若无能,也就难能。 ”赵园的代表作《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是其从现代文学研究转入明清思想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其最为盛名的作品,而她极力追求的文风,即“古拙以至生涩”。此书中,除了附录的《我读傅山》一文外,全书的第一小节《说“戾气”》,颇具提纲挈领意味,乃也是可以独立于全书的精彩篇章。这篇论述,择“戾气”二字,很好地概括了明清之际士人的生存状态,并给予了全面解读。文章写得惊心动魄,但却极力克制,不渲染铺陈,不作情感代入,而是以冷静的态度进行反思和审视,可谓难得。
与这篇《说“戾气”》有着相似阅读感受的,则是学术论著《想象与叙述》的开篇《那一个历史瞬间》。这两部学术著作的两个章节,都有着区别全书的文体感受,可谓巧运匠心,亦均可作独立的文章来看。《那一个历史瞬间》,以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明朝京城陷落这一历史瞬间为切入,通过时间、空间、社会、家庭、家族等诸多方面来进行讨论,细腻而深入还原当时情景下的士大夫的内心世界,由此写出了这个特殊“历史瞬间”中的激烈反应。就赵园此文的写作方式来说,乃是择其一点来进行微观解剖,从而深入历史的肌理之中。读此文,不难想到陈平原的文章《五月四日那一天》,也是同样就一个特殊时间点来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作为同门的钱理群,写过一册著作《1948:天地玄黄》,将研究的视角关注于革故鼎新的前夕,也是此类著述的一个典范。从明清之际士大夫“刻骨铭心”的灾难性的记忆,到“五四”所带来的思想变革和启蒙,再到1948 年旧文人的“天地玄黄”,很难说作为同门之间的学术影响,但互相之间启发和磨砺,应是难免的。
倒是值得关注的是,赵园的《那一个历史瞬间》中的部分章节,诸如《南·北》《山,湖,与海》《兵、贼、盗、虏、义军》等部分,在论述上似乎又与她的导师王瑶的《中古文学论集》中部分篇章的研究范式有异曲同工之处,或者再往上追溯,乃是鲁迅关于魏晋的名文《魏晋风度及文字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种找出一个特殊的时间切入点,又在这个时间点上寻找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事物来研究,从而能够抵达少有关注的幽微之处,才可展示出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和斑斓。这种研究方式,既显示了论者极强的写作能力,又展示了对于研究内容很深入的把握,从完成度来说,均可以看作一篇极精彩的文章。赵园此书之后的数篇章节,不能不说精彩,但比起此篇,则都显得逊色很多。 《想象与叙述》一书出版后被授以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但此书实际上是一册关于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论著,归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则多少显得牵强。反倒是此书中的这篇《那一个历史瞬间》,如若授予该奖项的散文随笔奖,则更可展示散文题材的丰富与厚重。
当然,赵园的诸多学术著作,虽然有着特别的文体追求,却乃是无意于归于文苑之列的。她的早期著作《论小说十家》《艰难的选择》《北京:城与人》等,作为文学论著,可以见出写作者的激情与才华,其论述的耐心和品鉴的敏感,都是令人称许的。但整体读来,似乎多少有些不够克制的“横溢”,反而不如后来研究明清之际文人的那种特别的“隔”,值得反复品味。此中,值得特别关注的,还有一册专著《易堂寻踪》,这是一册关于明清之际遗民群落研究的著作,却是以实地寻访和史料钩沉、品读来展开的。相比之前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和《想象与叙述》等专著,此书在整体上来说,颇有一气呵成的精致与从容。对此,赵园也是甚感满意的,故而可以作为一部特别的文学作品来看待,她也曾这样写道:“用散文的方式组织学术,也让我更有可能体验写作中的快感。那本书所写的一组人物,在他们的时代并非都声名显赫,却多少令人想到了鲁迅的论刘半农,清浅得可喜。这本小书的写作中,时有感动,有沉醉。那在我是一段美好的写作经历。 ”
学术著作之外,赵园亦有数册随笔著作,诸如《独语》《红之羽》《窗下》《世事苍茫》等。相比于她的学术著作,这些随笔文章是研究之余的小憩,但在赵园的笔下,亦是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古拙”。这种“古拙”的追求,乃是正如她所论述的,“是文境又是人性境界”,“都经了打磨烧炼,类木石之精,精气内蕴。 ”《王瑶先生杂忆》一篇,处处与读者的期待和想象作对,开篇写她随师母护送王瑶先生的骨灰回京,是极具萧瑟之气的。接着劈头写道:“先生于我,并非始终慈蔼。 ”乃是故意展示自己与导师之间的“不快”,这些完全区别于诸多同窗对于导师的温情追忆。再接下来,她更是写及自己“对于先生的冒犯”,以及她对“文革”中王瑶极狼狈生存境遇的片段记忆,这些都是很多弟子在追忆中极力回避的。此文中的一个特别的记述,乃是对于北大1988 年校庆的追记,其中写及校庆那一夜“最兴致勃勃”的王瑶。当王瑶与弟子们在未名湖走了数圈后,仍是“意犹未尽”,提议去办公楼看录像,但到了那里,放映却已结束,“楼窗黑洞洞的”。她至此议论道:“像是藏有极尽繁华后的荒凉似的。 ”
赵园的这篇悼念恩师的文字,乃是将王瑶放置于特殊历史背景下来审视的。她已完全超越了对于师辈的寻常记述,而是将一个经历过诸多政治磨难的知识分子个案来进行解读的,故而她也是在躲避一种“熟”与“滑”的纪念模式。由此,她笔下的文字,会令初读者感到一些冷酷,甚至是不解人情。如果这样理解,则是完全误解了赵园。显然,这是一种“古拙”的写作追求,是建立在对于人生的“打磨烧炼”之后的深切感悟。经过长达数十年政治运动消耗后的王瑶,对于所带学生期待和寄寓厚望甚深,苛求也自然难免,这也便能特别理解王瑶的那种“并非慈蔼”的原因了。而王瑶在“文革”中狼狈境遇,以及特别写及校庆之日遭遇的那种“荒凉”,似乎也在暗示一种知识分子并未根本改变的生存处境。对于王瑶的人生与学术际遇的深入审视,或许使赵园的学术选择,更多了一种清醒。 1989年,王瑶去世。此后不久,赵园便由现代文学研究,转入到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研究,这与王瑶的学术路径恰恰相反。在更深处,这也是一种特别的纪念。
在赵园的随笔散文中,似乎常常有意寻找人性或者时代的痛点来着笔,但恰恰是这种有意为之,使得她笔下的文字显得更为个性和尖锐。诸如《闲话北大》中,她特意写及自己到北大求学后,一度感到的“格格不入”,这种与北大气象不协调的,则是自己“十足乡下人”的记忆。由此,她反思那种看似特别的“仪态”背后,“也许竟是一无所有的”,这种论述,对于母校来说,则是显得有些刺耳了。不仅如此,她继而谈及所谓的“大”气象,就显得有些违和了:“其积极效果,是有可能使你逃脱委琐。纵然落到了极为不堪的境地,骨子里的那点傲气,也够你撑持一阵子尊严,所谓‘倒驴不倒架’。消极处却也在此:你或许要为你的不肯趋附付一点代价。这令人约略想到贵族的命运,虽然明知有点拟于不伦。我的确发现我的校友在北大北京之外,比起别个更难于生存。当然这或许只是由于我观察的粗疏。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个民族留给狂狷者的生存余地从来狭窄。至于校园文化,与社会向有疏离,纯粹的校园动物,很可能永远地失去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
诸如此类随笔文章,尚有《关于“老年”的笔记之一》《关于“老年”的笔记之二》《关于“老年”的笔记之三》,也是不避人性的痛点来着意描述的。 《养鸟者语》则又是一篇颇堪玩味之作了。虽然是写养鸟闲事,但却令人想到了人之生存境遇,文末附录一段幼鸟之亡的补记,则更有一种冷酷。再有《读人》系列文章,则是以读书随笔的形式来予以表达的精彩之作。由这些篇章,可以见出赵园内心之敏锐、细腻,并非孤僻与尖刻,而恰恰是一种不予回避的勇敢和倔强。这种写作之难得,乃是不投所好,更是有一种与流于俗滑的思维模式的坚决对抗。故而,虽然赵园并不看重她的这些随笔短章,但却一样值得我们郑重对待。偶尔亦有温暖之作,乃是她对友情与亲情的描述,诸如《从前,有个老头和他的老太婆》《中岛先生》两篇,均是深沉而婉转的。尤其前者,乃是借普希金的一则寓言故事,对自我的一种尖锐的审视,对丈夫的包容甚至是纵容的谢意,并以此作为自己对于丈夫六十岁生日的“礼物”。这种表达,寄寓深情,亦别有风致。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