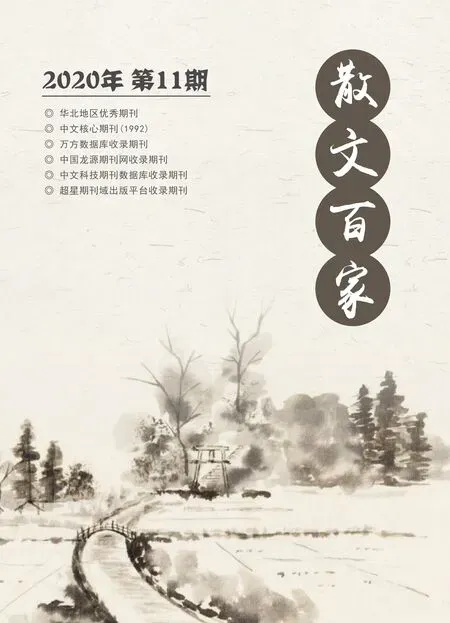大家小巷
黄丽淳
华南师范大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爸爸就怀揣勇气和向往来到那刚刚打开“门”的深圳。他曾回忆,罗湖火车站是他落脚的第一站,无数的大巴小车在那里停留,又离开。他辗转多处,兢兢业业,终是从一名走街串巷的鱼贩变成了一个小巷口杂货店的小老板。
店铺所在的小巷是一条不太长的老旧巷子,那里坐落着二十一间小店:店里两侧挂着衣服,门口跟着潮流摆人形模特的是卖服装的;半高的纸盒成沓地堆在门前,门内小板凳前必有一面斜放的镜子,这是间小鞋铺;总是飘着似有若无的大悲咒经乐的是出售佛具佛香的小店……
很巧合,一条巷子,二十一间小铺,或者说是二十一个家庭,每家都是潮汕人家。在我们潮汕地区,有着八月十五拜月亮的习俗。在每个中秋节的晚上,潮汕人家的家中妇女将桌子朝向月亮所在的方位,将贡品精心摆放到桌上,点燃两只粗红蜡烛置于各贡品前,蜡烛底部还安有一个小部件能够循环播放《十五的月亮》。待到蜡烛燃尽,小部件还余有电量,仍发出清脆响亮的音乐声,直到耗尽电量,声音戛然而止。巷子里的大家大多都是以店为家。每至农历八月十五,在月亮刚探出头,发出朦朦月光时,大家就已经半拉上了店铺的卷闸门,抬出桌子,摆上提前准备好的瓜果、芋头、月饼以及用金纸折成的宝塔或是用果冻垒成的果冻塔。桌上或许还放着隔壁给的炸酥饺或是巷尾哪位厨艺了得的阿姨亲手做的粿。在那月圆的夜晚,大家总是很默契地关上了电灯,任由随风跃动的烛光和或皎洁或朦胧的月光照亮这本该漆黑一片的小巷。
在等待蜡烛燃尽的时候,大家也不闲下来。从店里搬张小板凳,就坐在门前,向左边扭头说说话,或是向右边偏下身子也插两句话。妇女们聚在一块儿,在这有特别寓意的夜晚,聊着普通的日常。男人们或手执香烟,或呷一口功夫茶,低低地讲着话。年纪尚小的孩子窝在母亲怀里,懵懵懂懂地抬头看看月亮,又忍不住把目光投向跳跃的烛火,想探手去抓握,却又被母亲拉到怀里坐好。稍大一些的孩子就提着灯笼互相追着嬉笑打闹,从巷头到巷尾,又从巷尾到巷头。明明灭灭的烛光微微映着大家满含笑容的脸庞,一时之间飘进耳朵的,是宛转悠扬的音乐声,是各式各调的潮州话和孩子们清脆的欢声笑语。这样的场景值得被定格,被记录。大家都以为每一个来年的八月十五都还会有再聚一起的时候,也不曾想过2013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会是大家在一起拜月亮的最后一个中秋节。
2012年9月我离开巷旁的小学成为了一名初中生。当时的班主任是一名语文老师,她给我们布置了每周随笔,而我每周随笔的内容都离不开小巷里的人和事。有好几次老师还将我的随笔评为“优秀随笔”,这让我感到小小的骄傲:小巷,和小巷里的大家都只有我才有。七年级的日子如流水般地过,时而平缓,时而也叮咚作响。就在店附近的居民楼被盖上“拆”字的那一天起,“我们小巷好像也要被拆了。”这句话就时常在我耳边响起。
“怎么会呢!我们不才刚刚又交了一次费用嘛!没理由拆的!”
大家如此一边安慰自己,一边又偏信“即将被拆”的说法,时不时地聚在巷头商讨着小孩子不懂的事情。事与愿违,即将被拆的消息终究是以一纸通知准确告知每一户。大家再聚时不再互相给出自己都不太相信的安慰话语,而是就如何争取更好利益齐齐出谋划策。大家尝试过“负隅顽抗”的法子,也走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道路。但只换来拆迁方的断水断电、恐吓甚至雇人泼粪。大家无奈之下联系记者,最后却也不了了之。
最终还是会拆的,大家心里都清楚明白。到了最后,也不再做任何抵抗、反抗,只强撑着做最后几天的生意。或许是不想让人耽于过去,时间总喜欢将回忆压成薄薄的纸片,我已想不起二十一家人是何时开始搬离小巷,小巷里每家的卷闸门是何时都紧紧拉下,巷间只剩偶尔的行人走动。我家——巷头的杂货铺是小巷的最后“撤离”的一家店。等我后来路过小巷时,我看到已经有小批的工人和机器在作业。第二次路过时,曾经一间又一间的店铺已然成了遍地的碎瓦。我们姐妹几人对着空气指认曾经的二十一家店,我们的说法存在分歧,但也再找不到标准答案。直到店门前原先的一棵老树被砍去,我才真正再也找不到小巷了。
后来上了高中,我阅读到王开岭先生的《每个故乡都在消逝》一文,他在文中对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提出批判,认为“每个故乡都在沦陷,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在偌大的、日新月异的城市里,热闹温暖的小巷就是我的故乡。深圳这座城市无疑需要持续的建设发展,我也为她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感到骄傲自豪。小巷所在片区经过改造建设后,焕然一新了,它确实在奔向充满光明的前途。那篇文章还引用了于坚先生的一句话:“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一种谎言。”我不禁联想到自己:不复存在的小巷,再也聚不齐的大家,是不是也让我笔下的随笔都成了谎言?现实中已经没有我描述的内容的对应物,已经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能够作为小巷的视觉凭证。于坚先生曾经感叹道,“回忆也是靠不住的,回忆只是对昔日的改写,一次绘声绘色的扯谎,回忆是没有证据的,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并没有一个现实来对它的可靠性加以验证。”或许,我脑海中的小巷形象也是经过了回忆不自觉的整改和塑造。或许,真实的大家和小巷其实并非我如我笔下那般热闹温暖。没有照片,没有视频,没有“遗址”,我找不到小巷,找不到大家。有时候猛然再想起小巷和小巷里的人和事,就只能是想想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