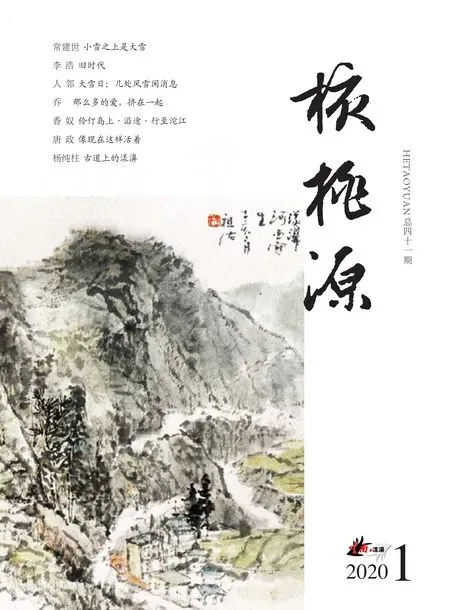古道上的漾濞
杨纯柱
一、漾濞沿革略述
漾濞古称“样备”,初为部落名,后为巡检司名,今为自治县专名。西汉时漾濞主体所在的邪龙县属元封二年(前109)设的益州郡管辖。东汉永平十二年(69)设永昌郡时,邪龙县划归永昌郡管辖。三国、两晋时,邪龙县归属南中七郡之一的云南郡。南北朝时期,漾濞分属云南郡和永昌郡。唐初属姚州都护府的阳瓜州,六诏称雄时为蒙雋诏。南诏时期,漾濞属蒙秦赕。两宋大理国前期属蒙舍赕,大理国后期属蒙舍镇。元朝分属蒙化州、永平县。明、清时期均分属蒙化府和永昌府永平县。
明朝洪武十七年(1384),明王朝在今漾濞境内设“样备巡检司”和“打牛坪巡检司”。前者一直延续到清末,后者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裁撤。在行政区划上,“样备巡检司”属蒙化府,“打牛坪巡检司”属永昌府永平县。“样备巡检司”驻地漾濞和“打牛坪巡检司”驻地打牛坪(今太平乡周家湾)均为博南古道的咽喉要道,是来往商贾和旅客的必经地和歇宿之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漾濞凭借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发展成马帮运输物资的重要集散地和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1912年,漾濞从蒙化、永平、洱源、云龙分出,建立漾濞县,建国后,曾一度同大理市合并。1985年,又设为漾濞彝族自治县。设县不过一百多年历史的漾濞古城,凭藉古驿道带来的一方商贸往来的繁荣和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成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名城。
二、漾濞古驿道概况
近些年来,我所接触的不少到过漾濞的人,大都对漾濞印象深刻,以至流连忘返。他们告诉我漾濞的独特的灵气和魅力,不只来自秀美的山川,旖旎的风光,清澈的溪流,纵横交错的江河,还来自其以漾濞古街古巷弥漫着的厚重的人文积淀。追根溯源,漾濞古街古巷这种厚重的人文积淀,就是得益于历史上曾经四通八达的古驿道。
众所周知,路对人类的重要性,是怎样估量都不会过份的。人类的历史,总是与路密切相关。路紧密联系着人生四大基本要素“衣、食、住、行”之一的“行”。人类的经济史,文明史,无不靠路来延伸、拓展、沟通、交流、融合、发展以及互相学习促进。对漾濞而言,路的地位同样是无法代替的。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著名的交通要道和滇西北交通枢纽,前人曾自豪地说,漾濞虽然“地连别属,境处一隅”,但“自汉永昌设郡,驿道先通,开化不后邻邑”。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是在遥远的历史岁月,还是可触可摸的当下,路对漾濞的意义和影响都是显而易见,无处不在,甚至是深入血脉和骨髓的,路打开了漾濞封闭的门,架通了漾濞与外界联系的桥梁;路给漾濞带来了热闹和繁荣,让漾濞这个山高水远,谷深壑险的弹丸之地,长期驿站店铺林立,商旅络绎不绝;路让漾濞受到了八面来风的洗礼和熏陶,使漾濞变得开放、包容、多元和自信。甚至可以这么说,是路改变了漾濞,造就了漾濞。路是漾濞的生命和灵魂,漾濞的历史文化总是与路息息相关,漾濞现在和将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要靠路来承载、推动和繁荣……
漾濞作为古代滇西北交通枢纽和古驿道重镇,境内的古道历来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其中影响比较大的驿道就有三条:博南古道、茶马古道(漾剑驿道)、盐米古道(漾云驿道)。
1.博南古道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便有道路从西南地区通向缅甸、印度等国,这就是古代所称的“蜀身毒道”。此道是从四川成都起点,经云南昆明、楚雄到达大理、保山等地,再转向缅甸到印度的一条古代国际通道,历史上被誉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马背上的国际通道”,其中从大理往西,过漾濞境内,进入永平博南山一段,又称为“博南古道”。
博南古道漾濞段,历史上虽然因特大山洪暴发导致的大面积山体滑坡等自然因素,曾经多次改道,特别是县城过云龙桥到太平打牛坪一段,可谓三十年走柏木铺、大觉寺、秀岭铺、虾蚂塘、清水哨、太平铺一线,四十年走大红梁子、小水塘、小浪坝、黄李子树、长岭岗,“猪嘴崖”、新街子、洗脸山、大陡坡一线。但基本的大方向没有变化。从东向西贯穿漾濞县境的博南古道,走向与1938年修筑滇缅公路大体一致,许多地段基本重合。只不过古驿道多顺半山坡蜿蜒,公路则大都沿着河谷沿岸延伸。
博南古道在漾濞境内分两段:从下关到漾濞县城的一段,被称“关漾驿道”,开始是顺着点苍山西麓的原始森林中行走,后来是一片片田园里穿越。漾濞境内的“关漾驿道”,全长约30来公里。此段古驿道至今仍残留着不少古道遗址,而平坡大合江,金牛街心、县城里的上街下街,以及河西的柏木铺等地段,老店铺还依稀犹存。而1990年7月被洪水所毁的平坡卷桥河两边古驿道上的大石面上,至今还有一串串深深的马蹄印,深的达15公分,一般都在10公分左右。从漾濞县城至永平一段,被称之为“漾永驿道”,是沿着崇山峻岭间的陡峭幽深箐壑穿行的。“漾永驿道”在漾境内长约40多公里。
2.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互易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就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商贸通道,也是中国西部民族经济和宗教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
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其中滇藏道起自滇西洱海一带,经丽江、迪庆、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西藏出境至缅甸、印度。其实,这只是滇藏茶马古道的主干道。滇藏茶马古道还有许多分支。漾濞茶马古道就是滇藏茶马古道的一条重要分支。历史上唐王朝、吐蕃、南诏之间冲突不断,虽然滇藏茶马古道主干线一直比较畅通,但商旅为避免民族冲突带来损失,于是开通了苍山西面的漾剑驿道。到大理国时期,这条古道依然畅通,元朝军队就是沿漾濞茶马古道,也就“漾剑驿道”进入漾濞境内,再从今天的石门关翻越点苍山攻取大理国的,后来的明朝军队也是选择此条路线对大理段氏政权进行出其不意袭击的。漾剑驿道已经成为从下关通往西藏的一条重要路线。
漾剑驿道下关至漾濞一段与博南古道是重合的。在漾濞古城与博南古道分道后,漾剑古道顺漾濞江东岸北上剑川,走向同今天“平甸公路”(平坡-甸南)的走向基本一致,许多地段上还有重合:云龙桥-罗屯-沙波登村-木瓜坞-狗白羊-小西果-桑不老-毛沙坪-甘屯-脉地,一路溯漾濞江而上到达剑川沙溪镇,然后辗转进入藏区。此段古道作为从剑川、丽江进藏的著名“茶马古道”的其中一段,现今仍存数段遗道。
3.漾云驿道
自漾濞县城过云龙桥北行,经杨茂村河、罗屯村、沙波登村、木瓜坞、狗白羊、张武哨、施家村,再转西北的石竹坡、苍蒲塘、白荞地、白露村、知达拉、罗里密,进入云龙境内的关坪。
除上述三条古道外,漾濞境内的重要古驿道还有:
1.自漾濞县城南行,经河西、木瓜箐、下村、洒密之达、小山神牌、新村、小村、毛鼠狼,过顺濞河链子桥、密古、龙潭、鸡街,从鸡街又分道,一条通往巍山地区,另一条则通往永平龙街、保山昌宁地区。
2.漾濞县城东行,经平坡、四十里桥、跨西洱河、茅草哨至巍山大仓。
3.翻越点苍山的古道。
滇缅公路通车前,上街至脉地一线的商旅为节省路程,多由捷径翻越苍山至大理。主要捷径有4条,4条路间有小路连贯。平时供商旅往来,在战争年代则为险要关卡,常为兵家必争之道。(1)经金星、密场上钟山,经黄龙潭向北转紧风口翻越苍山顶,向北行可达大理银桥。此路崎岖险要,一般人不敢通行。(2)经淮安、马军田、大寺村上苍山,由薄刀岭翻越苍山顶直下,向东至大理银桥。此路骡马可以通行。(3) 脉地至喜洲径。自脉地到登头,由大脉地直上翻越罗平山,可直达大理喜洲、洱源邓川。此路为旧时大道,在洱源至炼铁未通车前,是脉地至凤羽商旅来往必经之地,至今尚有人通行。(4)由脉地、金盏、苍山西坡大花园上去,翻越紧风口、顺上阳溪到达弯桥。此路历史悠久,至今有人通行。此外,还有一条由石门关上去,经漾濞当地人称为三尖峰、苍山电视转播台抵达下关路径。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元军和明军攻克大理国及大理段氏政权所走的山径。
物换星移,随着时间的流逝,漾濞的古道被公路代替后大多已经消失。马、马帮、马锅头,这些历史上曾长期活跃在古道上的主人和灵魂已退隐成很久远的故事和传说。但沿着昔日的马帮路线漫游,仍然不难寻觅到古道上保留的古代马帮往来的痕迹,你时不时会看见青石板上一道道马蹄踏出或深或浅的蹄印,还经常能够与一个个含有铺、驿、塘、哨的古驿道地名不期而遇。
据有关资料记载,博南古道历史上上有“九关十八铺”,十八个铺就是18个驿站,漾濞境内比较重要的驿站有四十里桥铺、合江铺(小合江、大合江)、平坡铺、鸡邑铺、驿前铺、漾濞铺、柏木铺、秀岭铺、太平铺、打牛坪铺等,此外,还有为沿线行路安全提供保护的白马哨、清水哨、后山哨等哨所。这些历史上曾经热闹一时的马帮和商旅的歇脚地,如今早已冷落沉寂。抚今追昔,让人怀想不已……
漾濞古驿道,承载着本土漫长的历史记忆,从遥远的岁月深处,款款向我们走来。随着公路运输的飞速发展,马帮运输方式早已经被时代淘汰。在时空的转换下,黯然失色,不再拥有昔日辉煌的一条条古驿道,不是隐没在丛林、河滩深处,就是被茂盛的蒿莱灌木淹埋于山野之间,更多的古驿道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无痕迹。如今残留的为数不多的几段古驿道也是行人稀少、空寂荒凉,安静得如梦境一样。正如诗人们感叹的刻着旧日时光痕迹的古驿道,仍然停留在另一个时代里。
这些古驿道是特别让人怀旧的地方,在奔流不息的时间长河中,它所流露和保存的更多的是一种往日的岁月,代表的是另一种辉煌的记忆,尽管这种辉煌的记忆,已经无可奈何地被现代文明飞速抛弃,却承载着向现在,也向未来不断诉说人类发展的历史沧桑和文明兴衰更替故事的重任。
还有作为博南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漾濞古驿道还可以说是一个“文明”与“蛮荒”的重要分野。明代谢肇淛(1567~1624)《过漾备渡谣》诗云:“过了漾备渡,阎王请上薄;到得龙尾关,才是到人间”,说明在历史上,被称为“小夷方”的漾濞渡,曾经既是西南丝绸之路上必经的一个重要渡口,同时也是滇西北一带文明与蛮荒的分界线。从下关西行进入漾濞,特别是从漾濞古城渡过漾濞江,沿着秀岭铺继续西行,就踏上了原始森林遮天蔽日,豺狼出没、人烟稀少的“漾永驿道”。
实际上,一直到建国初期,跨过漾濞江往西行,还被当地人视为无异于踏上了“走夷方”的充满凶险的路途。事实上,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等,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才被学术界叫响的。在过去,当地人称跨过漾濞江,沿着我们今天所称的博南古道往永平方向西行,再经今天的保山、腾冲辗转到缅甸之路为“走夷方”。建国前,漾濞“走夷方”的人不少,特别是善于赶马做生意的上下街回族男青年,不少都走过夷方,有的还侨居国外多年,甚至直接在那里安家落户。因此,漾濞上下街回族当中,至今都还有数量可观的侨属。
不过,总体上讲,当年的走夷方是迫不得以的冒险行为,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走夷方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去无回,有的长期流落异国他乡,有的很快成了“望乡鬼”。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我母亲胡先廉的爷爷胡元科,就是为了改变家庭经济窘境,铤而走险,同人结伴走夷方——到当时云南人称的“英国老银厂”淘金,实际上就是去当时英属殖民地的缅甸老银场做苦力,不料一去不复返。多少年后,家里人才打听到消息说,胡元科到夷方的当天,在街上买了一笼猪肠子回驻地煮吃后,当晚就命丧黄泉了。所以那时有一句话:“穷走夷方急走场”,这里所说“夷方”就是指缅甸,“场”,就是指英国殖民者在缅甸开办的矿山银场。
三、典籍里的漾濞古驿道
最早记录漾濞古驿道的,是明代杨慎,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状元公杨升庵。这位明嘉靖三年(1524)因“大礼议”谪戍于云南永昌卫(今保山)的四川明代大才子,在他的《滇程记》里,除记录漾濞境内的驿道亭站外,还以其优美的文笔生动记录了沿途的山川风物。
比如他描绘“横岭”(今河西秀岭)道:“其高侵云,缘箐以升,树多松,花多杜鹃(土人名映山红),鸟多鹦鹉,群飞蔽林,若朔方鸦然。”也就是说,沿着高耸入云的秀岭崖箐往上攀登,周围的树多半是郁郁葱葱的松树,所开的花大都是杜鹃花,也就是当地人称的映山红,鸟儿多半是鹦鹉。这些鹦鹉,被行人惊起群飞,数量之多,将下面山林都遮盖了,像极了北方一群群飞起来铺天盖地的乌鸦一样。
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幽美而壮观的景致,更透着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古朴苍莽的原生态韵味。至于杨升庵在此文中关于“又西为云龙桥”的记述,则是至今有文字可证的关于漾濞云龙桥这一省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的最早记载。也是该桥为明代中前期建造的有力佐证。
历史上记录漾濞古驿道最详实的两部书,一部是明末大旅行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另一部是辛亥革命前夕,腾冲人李根源主持编修的《滇西兵要界务图注钞》。
明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二十一日,徐霞客偕同仆人顾行和大理三塔寺一位随行僧人三个人,由今天大理市的四十里桥进入漾濞地面,至二十四日,过今太平乡境内顺濞河上游出漾濞县境进入永平,共在漾濞境内游历了4天。《徐霞客游记》中的《滇游日记》之八,对此4天的行程和游踪作了非常翔实的记录,留下了4600多字的日记,即平均每天记述1100余字。不过,他主要是在漾濞石门关流连。时隔380年后的今天,我们翻开《徐霞客游记》,通过徐霞客记录的自己在漾濞亲历亲见的准确、生动、写实的笔触,当年漾濞的古驿道行程、状况,沿途秀丽多姿的山水风光,仿佛一幅幅立体的画卷,徐徐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徐霞客游记》可以作为漾濞古驿道的导游手册。尤其难得的是,徐霞客在沿着漾濞古驿道边行走边记述漾濞的山川地理和自然生态的同时,还注重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和挖掘其历史人文资源,更增添和彰显了漾濞这方山水风物的人文光辉和魅力。他在苍山漾水之间的旅游日记,已成为漾濞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文积淀。
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务图注钞》则详细记录了漾濞古驿道上驿站之间的距离、村落分布、人文物产等状况。比如它记载:“漾濞街:永平、蒙化分管,旧设永昌协标千总已裁。蒙化巡检驻此,分上下街,共七百余户,尚殷富。巡署在下街。寺庙十二,客栈七家、马栈九家。能容一混成协宿营,给养饮水补充俱便,产木棉,核桃极丰。平坡至此四十五里,道路半石质,宽可容步兵二路纵队行进。途中住户多贫寒者。漾濞江水如碧玉,其声终夜如雷鸣,行客宿此多不成眠。”
随后,李根源还介绍说:“余族人李希贤家迁此已三代。街东北有团山、东旁村、打鱼村、光庄、密厂、梅花村、十九古街、纸村、黄庄、董庄、黄央屯(淮安屯)、茂盛江、大铺子、柳树坡、下坝等,均在点苍西麓,漾濞江东岸。十九古街每年二月十九日,四方商人云集于此贸易,有数万人之多。”
最后,李根源还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说:“是地距蒙化、永平、云龙均远在百里以外,似应专设一县治理之。西行渡铁索桥,上漾濞坡,往太平铺,通永平县”。1912年,漾濞从邻近的巍山、永平、洱源、云龙分出单独设县,也是得力于李根源一手促成的。
此外,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王昶著的《滇行日录》和晚清黄懋材撰的《西輶日记》等典籍,以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人亨利·奥尔良所著的《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苏格兰裔澳大利亚人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撰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美国著名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籍,还有撰写《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又译《西行漫记》)而闻名于世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写的《马帮旅行》等外国人撰写的旅游考察书籍,对漾濞驿古道的里程、山川名胜、城镇馆驿、地理人文也多有记录。
老实说,我阅读外国人记录在中国驿道沿途见闻的书籍的时候,感受可以说是五味杂陈的。在这些西方人的笔下,当时的中国,包括漾濞古驿道在内的中国土地,自然生态是非常良好的,风光也异常秀丽优美,地方却难以想象的贫穷落后。当地的人是那么的麻木不仁,不讲文明卫生,甚至是贪婪丑陋,野蛮堕落的。虽然这些对昨日中国的灰色记述,倾向上看不无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渗透在里面,但更多的仍是一种“实录”性质的东西,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现象的客观、真实的描摹。
令人欣慰的是,历史早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近代史上那积贫积弱、任人欺凌、污辱和宰割的不堪回首的一幕幕往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四、漾濞古驿道的人文积淀
如前所述,美丽神奇的漾濞,由于地处汉唐以来的“蜀身毒道”与“茶马古道”的要冲和交叉口,自古就店铺驿站林立、往来商旅和马帮络绎不绝。历代许多名人因云游或途经,都与这片山川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数千年的漫漫岁月里,漾濞驿古道上马帮络绎不绝,而镶嵌在这条古驿道上的包括合江铺、漾濞古城、柏木铺、太平铺、打牛坪等的一个个驿站,为东来西往,匆匆忙忙奔波在这条古驿道上的数不胜数的马帮、商客、旅人、官宦以及兵马提供了歇宿。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有史籍可稽或民间口碑资料可寻的,与漾濞这方山川水土有过深浅不一情缘的帝王将相和名贤鸿儒,除诸葛亮、唐九征、徐霞客之外,还可以列数出一长串熠熠生辉的名字,如吐蕃赞普弃都松、南诏王异牟寻、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明末大西政权著名将领李定国、清朝晚期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云南辛亥革命“三杰”之一的马骧、抗日民族英雄戴安澜、现代绘画大师徐悲鸿等等。
根据有关典籍记载和民间传说以及口碑资料,最早与漾濞这方山水发生联系,并对漾濞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著名历史人物是大名鼎鼎的诸葛亮。
从有关民间传说中,我们知道,“关漾驿道”上的漾濞江河谷和西洱河谷,就是诸葛亮第七次擒获孟获的地方。此次被擒,孟获终于向诸葛亮表示:“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因此后来将此条路称之为天威径。漾濞中学的校歌中就有“诸葛亮的战地,徐霞客的游记”之语,来彰显漾濞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之脉。
如果说“诸葛亮战地”只是一种“层垒”起来的民间传说,并不足为凭的话,那么“唐标铁柱”则是尘埃落定的信史了。唐景龙元年(707),唐王朝命“姚嶲道讨击使唐九征”挥师追击并一举大破吐蕃军队“斩俘三千余人”。唐九征凯旋班师回朝时,在漾濞江畔立集“纪功”和“标界”为一体的“铁柱”的举措,使漾濞第一次彪炳史册,沾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光,除了使“漾濞”二字先后载入了《大唐新语》《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重要历史典籍外还为漾濞贡献了一项世界之最:这就是被《大唐新语》卷十一所记载的“时吐蕃以铁索跨漾水濞水为桥,以通洱河”的“铁索桥”,被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的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所著的《中国科技史》考证为全世界关于“铁桥”见诸于文字的最早记录。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历史上过往漾濞的文人学士,所留下的吟咏漾濞的诗文。当这些背井离乡、长年漂泊四方的行旅之人奔走在深山野谷、崖高箐险、虎啸猿啼的驿道上,艰难辗转行走在人烟稀少、景象迥然不同于内地的“蛮烟瘴雨”之地时,难免触景生情,多感多怀。特别是在这里驻足歇宿或流连漫步,观风赏景的历代诗人学者们,往往会雅兴迭起,有的饮酒赋诗,遣兴抒怀,有的作文记游,留下他们对这方风土人文的观感。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唐代内地著名诗人吟咏漾濞的诗共有三首。第一首是晚唐时期因“蜀中战乱”被攻克成都的南诏军队所掳,流落云南的成都诗人雍陶所写的《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入蛮界不许有悲泣之声》,其诗云:
云南路出洱河西,毒草长青瘴色低。
渐近蛮城谁敢哭?一时收泪羡猿啼。
从诗人一行所走的“路出洱河西”的路线和方向上推断,诗中所吟咏的“蛮城”,就是今天的漾濞古城。也就是说,诗人离开大理洱海往西经过下关天生桥,沿着西洱河往滇西边走了一程又一程,远远地望见一座城池——即坐落于漾濞江边的漾濞古城,也就是诗人谓之的“蛮城”,更加胆战心惊起来,只得忍泪含悲,不敢啼哭号泣,只能羡慕漾濞江两岸高岩峭崖间,自由自在的声声鸣啼的猿猴。其大背景是由于当年唐王朝和南诏之间连年征战攻伐,双边的百姓都深受祸害,难免造成了内地与边疆深刻的地区隔绝所造成的民族隔膜。尤其是雍陶这位被战争掳入南诏的饱经忧患的诗人,自然早已系惊弓之鸟,因而见到前边出现的漾濞城池,反而担惊受怕,忧心忡忡起来,也是不难理解的。
第二首是唐咸通五年(864)七月,被唐懿宗任命为安南都护、经略招讨使以抵御南诏对安南地区的侵略的高骈,在征战南诏路过漾濞时所写的《过天威径》诗,其诗曰:
豺狼坑尽却朝天,战马休嘶瘴岭烟。
归路崄巇今坦荡,一条千里直如弦。
诗所咏的“天威径”,前边已经提到,就是后来的“关漾驿道”和“关永驿道”,也就是大理市下关天生桥至永平之间的博南古道。高骈率军靖边,辗转于相传曾经是第七次擒获孟获的天威径,也就是漾濞平坡到下关天生桥之间的险峻山谷,不禁缅怀起汉丞相诸葛孔明前辈“豺狼坑尽却朝天”的“以夷治夷”的高明安边谋略,即“豺狼坑尽”后,没有留下一兵一卒戍边,“却”班师回朝了。因为孟获大王已被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心战”降服,率豺狼之兵归顺蜀汉政权。从此,不用再派兵马征战于蛮烟瘴雨的西南云岭了。这位节度使踏上当年汉军曾战斗过的险峻归途时,遂感叹如今千里如弦的古驿道,已经坦荡无阻了。第三首就是跟随高骈征战南中的池州(今属安徽)诗人顾云留下的《天威径行》一诗。其诗曰:“蛮岭高,蛮海阔,去舸回艘投此歇。一夜舟人得梦间,草草相呼一时发。飓风忽起云颠狂,波涛摆掣鱼龙僵。海神怕急上岸走,山燕股粟入石藏。金蛇飞状霍闪过,白日倒挂银绳长。轰轰砢砢雷车转,霹雳一声天地战。风定云开始望看,万里青山分两片。车遥遥,马阗阗,平如砥,直如弦。云南八国万部落,皆知此路来朝天。耿恭拜出井底水,广利刺开山上泉。若论终古济物意,二将之功皆小焉。”诗中所写的“蛮岭高,蛮海阔”中的“蛮岭”和“蛮海”,分别就是指“天威径”东侧的苍山和“天威径”起点背后的洱海。
历史上在漾濞留下著名诗歌词赋的文人,应首推杨升庵。漾濞地处博南古道要冲,是杨升庵前往流放地永昌卫的必经之地。不难想见,在流寓云南的长达三十五年的岁月里,杨升庵曾无数次往返于这条逶迤于漾濞崇山峻岭间的悠长苍茫古驿道,并停歇住宿于漾濞境内的驿站客栈里,以及流连忘返于漾濞的明山秀水间。作为一位出口成章的旷世才子和著述等身的文章大家,杨升庵肯定会对漾濞这方美丽神奇、秀色可餐的佳山丽水,多有吟咏和记录。可惜时过境迁,大都荡然无存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杨状元在漾濞留下的人文遗产有两首诗和一首词。其中一首题为《题石牛诗》曰:
怪石生来恰似牛,不知经历几千秋。
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洒周身似汗流。
细草平铺难下口,金鞭任打弗回头。
牧童吹笛枉入耳,天地为栏夜不收。
诗中吟咏的石牛,即位于距漾濞县城东10公里的“天开石门”前——漾濞江边金牛村的“有首无身,头大如斗”的石牛。杨升庵在此,无疑是借诗言志,以“天地为栏夜不收”的“金牛”自比,表达自己安于偏远江湖,不受朝廷约束,自由自在的旷达高迈的生活。
杨升庵在漾濞江畔所留下的《临江仙》词云:“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后来这首词被人冠在中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正文前面,广为流传。
当地父老为纪念杨状元,就在传说杨状元与漾濞当地两个老倌相逢揖坐,开怀畅饮,并乘兴挥毫填词的地方——今漾濞古城周家巷隔漾濞江的对岸、望江亭下面的古道上立了一座石牌坊,并在上面镌刻上杨状元此首著名的《临江仙》词。可惜,这座相传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当地颇有价值的人文景观,已经毁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如今连蛛丝马迹都已荡然无存,而当地人们到现在仍管此地叫石牌坊。据当地老人讲,过去赶马人常在石牌坊前的草坪上开稍歇脚,生火做炊。历史上被官府斩杀的匪首或要犯的人头也常被挂在石牌坊上示众。
当然,杨升庵写《临江仙》地点,历来颇多争议。我认为,从此首词的风格和境界上,当属杨升庵晚年的作品,而并非是其春风得意,意气风发的早年创作。因为只有在历经磨难,饱经沧桑后,诗人的思想认识和人生境界,才能升华到这种同在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的“白发渔樵”,“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豁然开朗、达观洒脱的精神境界。而众所周知,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戍所,享年七十二岁的杨升庵,除晚年曾返回泸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抚派四名指挥将其押解回永昌外,一直都在云南流放地煎熬苦度余生。
漾濞是杨升庵往返昆明与永昌的必经之地,而汹涌澎湃,一泻千里的漾濞江,更是横亘在昆明至永昌古驿道上,被《康熙蒙化府志》形容为“奔湍雪浪,触石吞岸,舟楫难施,诚为天险万仞”的最重要的大江大河。所以,我们说杨升庵途径漾濞江时,触景生情,思接千古,有感于“浪花淘尽英雄”,进而发出“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深沉感慨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最符合逻辑的。
以“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豪言壮语,为世人熟悉的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中国古代大文学家、史学家赵翼,也在漾濞古驿道上留下了数首诗。
赵翼在漾濞博南古道上吟咏的诗作,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这首《至合江铺已就宿矣忽京兵来乃移避于山后》。其诗云:
数间寓舍让京营,移就山家破草棚。
人共马牛眠一屋,月随风雨涌三更。
也知入世应安堵,自笑从军转避兵。
信是健儿骁可畏,先今瞻落到书生。
此诗是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五月、清王朝反对缅甸木梳王朝对中国边疆侵袭战争的第三年,赵翼奉诏从军入滇,途经漾濞合江铺奔赴永昌(今保山)前线,参加筹划与缅甸的战事时所写的。
从诗中我们读到赵翼这位正风尘仆仆赶赴永昌拟参与筹划对缅作战大计的诗人,途中夜宿于合江铺客栈时,忽然从京城来了一营京兵,数间不多的寓舍迫不得已让给京兵住了。他只好回避到山后破草棚里就寝,与马牛牲畜同睡在一屋之下。在乌云吞月、风雨骤至的半夜三更,这位难以入眠的诗人,自然知道世间本该安居无扰,面对当夜忽然发生的“鹊巢鸠占”之惊,他不禁苦笑自嘲自己千里迢迢来从军参战,却反而要躲避这些蛮不讲理的京兵。原以为自己也可以跻身于骁勇可畏的健儿壮士,今夜却一下子又变成个文弱书生了。
此外,赵翼路过秀岭大觉寺时,也留下《题大觉寺》的诗云:
漾濞南来箐盆深,万松黑到最高岭。
马行危蹬蹄包铁,佛守荒庵面落金。
怪石偻如奇鬼搏,古枫幻作老人吟。
问途空说天威迳,何处遗踪访七擒。
较之前一首,此首的风格沉郁,韵味苍凉。诗人渡过漾濞江向山高谷深的秀岭山上进发,举目青绿色的松林遮黑了前面的山峰,蹄上钉着铁掌的马,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崎岖危险的山道上,路过道旁的大觉寺,只见面上容金粉斑驳脱落的古佛,守着一座荒芜的庵庙,满目怪石如伛偻的奇鬼互相搏击。而一路走来的天威迳上,却难寻觅传说中千年之前,诸葛亮率军南征,七擒蛮王孟获显示天威,使边疆归顺内地王朝的历史遗迹。从这些意象上和感叹中,我们不难品味出诗人胸中的块垒、郁闷和茫然。
为什么诗人会有这样低落荒凉的情绪呢?这可能与诗人此行的心情和所要完成任务的艰巨性不无关系。我们知道,此前担任广西镇安府知府的赵翼,由于为前任守道辩护触怒了两广总督李侍尧,曾被李侍尧上本“参劾”罢官。所以,被重新起用的诗人昼夜兼程,餐风宿露,辗转滇西千山万水间的诗人,不免有一种失落沮丧的心情。况且他也不知道自己前往参加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何日能够结束。诗人回望关山历历,抛家别口于万里之外,前眺山险水恶,兵荒马乱,前程未卜,因而难免忧思重重,感慨深沉。
还有前文提到的那位清朝乾隆皇帝后期随云贵总督阿桂入滇,数年奔波于腾越永昌前线,参加维护祖国边疆稳定的军事活动且屡立战功,之后人生顺风顺水,一路青云直上,官至刑部右侍郎的江苏青浦(今上海市青浦区)人王昶,曾多次往返于博南古道上。作为一代著名学者,王昶在云南不只著有《滇行日录》,还留下了大量诗词。其中,王昶在漾濞太平写的《过太平铺坡》诗云:
霜华薄薄上疏襟,鸟语猿啼并好音。
木栈萦回连石栈,松林迢递接杉林。
请缨差遂平生志,负米偏愁岁暮心。
喜见太平真有象,蔬畦稻廪遍高岭。
诗中所展现的这方山川风物,可谓一片太平祥和景象,满眼迷人的田园风光,连那深山野箐的古猿老猴的啼叫,也十分悦耳动听。这自然与诗人“请缨差遂平生志”的功成名就的良好自我感觉,以及展望前程似锦的轻松愉悦心情有关。清代封疆大吏、著名的汉学家阮元,也在漾濞古驿道上写有《漾濞合江上看月》一首诗云:“点苍山背乱峰堆,漾濞双流转百回。云水万重山万里,一轮明月总追来。”
最后,还应当注意一下民国时期,剑川著名的白族学者赵藩在《永平途中杂诗》里写的一首内容涉及打牛坪的诗。诗是这样写的:
丞相天威定永昌,南中处处有祠堂。
打牛叫狗殊荒忽,附会都缘服武乡。
作为娴熟祖国历史,尤其是深谙地方典籍掌故的一代宿儒,赵藩的诗一语道破了“南中”之所以到处都有武候祠,就是在学术界公认的诸葛亮本人并没有亲自到过的滇西一带,也有关于他活动的大量灼灼古迹和许多有板有眼传说,原因就在于当地各族人民由衷地崇敬其南征时所采取的“攻心为上”,贵在“心服”的“和抚”政策及策略,以及深深感戴他曾在这些被当时人目为“蛮烟瘴雨”的“不毛”之地,不遗余力地传播内地汉族地区先进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朽历史功绩。
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的是,三国两晋以来,云南各地对“汉丞相诸葛孔明”与日俱增的崇拜敬仰,甚至是盲目的攀附追捧,实际上反映出的是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对祖国内地汉文化文明的羡慕、向往和归依心理,或者说是折射出的是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一家亲”思想和“中国大一统”意识的深入骨髓,融入血脉的认同与接纳。
除上述著名的诗人骚客外,其他如明代抗倭将军邓子龙等在漾濞古驿道上也多有吟咏,在此不一一列举。经过时间的不断冲刷和岁月的漫长过滤,这些古驿道上著名的“匆匆过客”,在漾濞古驿道题咏抒怀和描写所见所感的诗文,大部分都失佚了,有幸存留下来的也寥寥无几。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主要分散保存在漾濞、永平、巍山、保山、腾冲等地方文献资料中。今天重温这些诗文,我们在倍感亲切温馨,别有趣味的同时,还会产生许多抚今追昔的感触,甚至不禁浮想联翩……更重要的是这些诗词,可以说丰厚了漾濞的人文积淀,给本土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星罗棋布的人文景观,增了色添了彩,并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历史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五、“蜀身毒道”的发现问题及其作用
长期以来,主流学术观点认为,“蜀身毒道”的开辟,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意外收获”。我认为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从逻辑上讲,对这条被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古道,张骞之功劳,其实只是偶然发现而已。早在张骞发现之前,这条古驿道就不知存在了多少年,多少代,甚至多少个世纪,只是不为包括中央王朝在内的内地人民知悉而已。所以,我认为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张骞是“蜀身毒道”的意外发现者,西汉和东汉王朝只是在其中扮演了全面打通中原地区与“蜀身毒道”联结关系的关键角色,而并非是所谓“蜀身毒道”的“开辟”者。当然,我这里否定张骞和中原王朝的“开辟”权,并不意味着要贬低张骞发现“蜀身毒道”的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而是为了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公元前138年,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以联络西域各国挟击匈奴,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时,在大夏(今阿富汗)“见蜀布邛竹杖”,由此推断在西南地区有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从而发现了“蜀身毒道”的存在,进而导致汉王朝千方百计地寻找。两汉王朝经过长达207年的努力,终于在东汉永平十二年(69),将这条始于四川,分“朱提道”和“灵光道”两路进入云南,在楚雄汇合后并入“博南古道”,跨过澜沧江,再经“永昌道”“腾冲道”出缅甸、印度等国的国际性通道完全打开,其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因为张骞发现之前,这条古交通要道只是作为一条西南地区对外交往和货物流通的民间来往和商贸运输的通道,其价值和作用是区域性、民间性的。张骞发现上报给朝廷后,引起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从而促使其由民间通道上升为“官马大道”,其军事和政治价值、作用和影响才一下凸显出来,并日益发挥壮大起来。
从国家版图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上看,张骞对“蜀身毒道”的发现,极大地增强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重要战略地位的兴趣和重视,为了寻找和打通这个具有军事、政治、商业、文化以及宗教多重功能和意义的国际大通道,并保障其尽可能地畅通无阻,中央王朝加大了经略西南边疆的力度,从而有力促进了祖国内地与西南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来往,空前地增强和扩大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和影响,进一步密切了西南边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特别是进一步增强了西南边疆人民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臣属关系以及主流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有利于中国大一统思想和意识的形成,进而为中华民族共同民族心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张骞发现“蜀身毒道”的功劳,可以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如果没有张骞这次及时发现,印度宗教文化还不知将继续单独影响西南地区多少年多少代。但也不会是多少世纪,因为张骞这次不发现,绝对还有人会发现,而且时间不会推迟得很长。发现是绝对的,只是时间早一点迟一点的问题,发现者是张三李四还是王麻子的问题,但早一点发现总比迟一点发现好,这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还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蜀身毒道”重要组成部分的博南古道,不仅对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产生了非常深刻深远的影响,而且伴随而来的祖国内地以儒家思想代表的汉文化,对沿途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的长期日浸月润,其产生的积极影响,除有力推动了沿途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融合外,还给这些地区打上了深深的汉文化烙印,不断强化了边疆民族地区对中华大一统的认同感和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
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古道沿线的地区而言,博南古驿道留下来的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已成为我们地方重要的人文资源积累。充分挖掘整理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可以充分彰显我们地方源远流长的文脉和丰富多采的文化资源,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而且还能够进一步增添我们地方的历史文化韵味和人文魅力。
——谨以献给漾濞5.21地震救援的消防指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