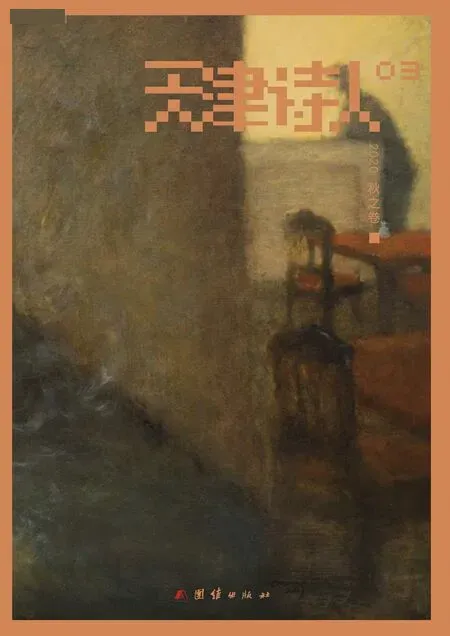怀着孤岛的心,与一场大雾对峙
——评祝立根的诗及其宗祠诗学观的确认
张福超
无疑,在云南诗歌高原上,祝立根是当下最活跃的青年诗人之一。但从历时和空间的坐标去考察和阅读祝立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线性诗歌史角度看,一个诗人成就高低往往取决于他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时代的书写,汇入了诗歌潮流的合唱,或者影响了后来诗歌的走向。新世纪以来的诗坛呈现出碎片化、多元化,口号纷纭的集体化诗歌浪潮已成往事,且祝立根也无意参与大时代大事件的书写,他的诗像是长了“反骨”,是对时代束缚的逃逸,往往出自个人的忧愁、悲苦与焦虑,是个体“小时代”里涌溢出来的涓涓细流。另外在空间地域上看,诗人的地域写作价值则在于其对地理图景和地域文化症候的想象与建构,进而成为地域精神的代言人。祝立根出生腾冲,寓居昆明,通常被视为云南地域写作的代表,但是纵深到诗歌内部纹理,却不难发现他与云南、故乡保持了一种疏离感紧张感,对于故乡和居所他始终是“不在而在,在又不属于”的境况中。祝立根是一个孤独者,他在现今大时代历史进程中,发现了个体生存的秘密——“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无乡可归的双重孤儿”。所以现实中的诗人和诗中的自我在孤独命运这点上默契携手,他们都是飞跃在低吼的怒江之上无所着落的水鸟,是乡宴上的陌生人,是怀着孤岛的心与大雾对峙的人。祝立根的这种孤独似是一种被悬浮的“中间物”的存在,那么诗人如何让肉身和精神有所附着呢?他将诗歌当做了自己的宗祠,将语言当做游子回乡的车马,让漂泊的灵魂有了救赎与归宿的可能,但又不至于走向虚无。沿着祝立根的宗祠诗学漫溯亦可感受到其诗就像一溪涓涓流水,从自己的心胸中涌溢出来,穿过人世间片片的江河湖海,又收束到了自己心胸中。如此,祝立根又不是孤独的,他对人世汪洋中卑微个体生存有着敏锐深切的感同身受。
现代文学大家沈从文出走湘西,以湘西为虚构背景创作《边城》说道:“我想建一座希腊的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这对祝立根来说亦然,14岁就离乡念书,在外漂泊十余年,油画职业的失败与生活的艰辛,使得诗歌成为灰暗浑浊生活的微弱灯火。祝立根自述一位好诗人就是一位好巫师,通过喊魂而让词语复活。村中宗祠就成为他诗歌的隐喻,“它作为未知世界和现实人生的桥梁,一头连接着未知的世界,一头又始终看顾着人间的烟火熄灭又升起”。在现实人生海洋中,“保身保家已显力不从心”,于是就只能在诗歌中“喂鹰、饲虎”(《在多肉植物馆》)。
诗歌是一场与语言的搏斗,而首先是与自我的搏斗。祝立根将诗歌当做村中宗祠,这是一种救赎情愫的隐喻。但并不意味着这宗祠就是诗人的归宿,是现实生活“退败者”温暖的避风港。相反,宗祠与诗人之间是一种相互缠绕、相互消耗的关系,用祝立根的话来说就是石头与匠人在互相消耗、互相打磨。或者再进一步,如祝立根在四月份诗歌交流会上所谈到的那样,并非我们在打磨石头,而是石头在打磨我们,是诗歌及语言又重塑了我们的生活。“在满是涂鸦的墙壁前/喃喃自语,妄图为自己招一次魂。/可一切终将徒劳。/孩子们无法理解这些从顶光画室退败下来的人/脸上蔓延的暮色”(《呼啸》),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画家或诗人的祝立根是一个“退败者”,是一个喃喃自语的旁观者。一旦深入到语言世界中,他就恢复了活泼的天性,用戏谑、游弋、反讽的诗语嘲讽自我,也嘲讽着周围的阴暗世界。“好吧/就让自己痛痛快快逃一次,像怒江水/从乱石中抽身而出/有些苍白,有些呜咽/有些跌跌撞撞”(《剖析书》),各种考证、审查、登记与评比,大时代裹挟着渺小的万物众生奔腾直泻,在这样的时代里诗人选择了“逃避”,选择了“抽身而出”,但这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而是在对时代的逃逸中找寻自我的存在。还有在《喜白发》中“噢,我终于长出了一根白发”,还有《回乡偶书,悲黑发》“秋风白了小伙伴们的坟头草/一头黑发,令我心惊/令我羞耻”,或许是生活中承受了太多的焦灼、彷徨与苦闷,祝立根拥有反常的诗学眼睛、反常的感受力。他与生活之间保持了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的疏泄则非反讽的怪异式语言不可。对语言问题的处理其实也即对自我与世界、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处理,在此语言成为祝立根看待世界过滤现实的一副“眼镜”。经过这些反讽性怪异式的修辞,个人在现实世界中的悲苦、焦灼、漂泊成为一种痛苦的自省与普遍的底层关 怀。
祝立根是谙熟这种“反骨”性修辞的,他对诗语口气的拿捏恰到好处。在他的诗歌中随处可见信手拈来的揶揄嘲讽、机智微妙的现代性批判以及感伤弥漫的乡愁抒情。在大名鼎鼎的《胸片记》中,“那年在怒江边上,长发飘飘/惹来边防战士,命令我:举手/趴在车上。搜索他们想象的毒品/和可能的反骨,我不敢回头/看不见枪口,真的把一个枪口/埋在了胸口,从此我开始怀疑/我的身上,真的藏有不可告人的东西/我的体内,真的长着一块多余的骨头”,因“长发飘飘”而引来边防战士的检查,进而胆战心惊地对自己生发了种种怀疑和自省,在此后的世俗生活中“填简历,我写得一笔一画/说明情况,我说得絮絮叨叨”,但最终发现不过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卑微如蝼蚁的生存者,是不值得强大的世俗机器去反复检查的。但在医院里,“我”面对着检查身体的机器仍然是不由自主地举起了双手。这真有卡夫卡小说中的荒诞感,世俗力量的强大导致卑微自我的痛苦自省。这种痛苦自省不仅来源于青少年时代的悲苦生活,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儿子”,更是多年读书所坚守的心中理想主义之光,以及诗人本身的善良、本分的性情。世俗规则,以利为主,尤其是在现代性社会浪潮中,势必与心中理想之光发生抵牾。可贵的是,诗人并非一味地在诗中批判这种为人处世的规则,而坚守自己的信念。对于两者,他采取了一种游弋不定的态度,时而努力地投靠世俗规则以在人情社会生存下去,时而又否定了这种生存态度,“很惭愧,我还是不甘心/想怀抱烈火,在精神上直立行走/前几年,向猪问道/贪恋烂泥和残羹,到最后/还不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狼嚎、猿吼,会伤及爱人/我知道,现在我在学习把心坎上的石头/扔进流水,或某首小诗”(《与兄书》),以及在《与友书》中感叹“一个小职员的穷途末路”,在《寄远》中嘲讽流浪狗式的生活及对主人的讨好态度,《洁癖患者》中小知识分子的辛酸命运等。在此,我们不妨将这种在双重反讽中游弋不定的修辞称为“祝立根式诗语模式”。祝立根认识到了这种悬浮的中间物的命运,是一种孤独者的命运,最终是有所着落的,就像鲁迅《过客》中的“过客”最终勇敢的面对那些无物之阵一样,诗人也会怀着一个孤岛的心,与大雾对峙(《访山中小寺遇大雾》)。
司马迁因受极刑而“发愤著书”,韩愈也提出“不平则鸣”,苏轼对于诗文创作也有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出”,祝立根诗思诗情似继承了这些传统文论,因为有太多的悲苦、焦灼与不平,他“一直为心胸中的波涛所裹挟”,他的诗就像泉水是从胸臆中涌溢出来的一样。“榕树从胸口抽出根须”(《草木间》)、“胸腔里,早已沧海桑田/那些愤怒的灰烬”(《纪念碑》)、“穿过怒江,迷恋着脚下的波涛/和胸中慢慢长出的迎风羽毛”(《夙愿》)、“每天,我都会在那儿/捧水洗脸,往那儿归还身体里的涛声”(《悲恸海》),这些诗句就像榕树一样从诗人心胸中生长出来、蔓延开来。祝立根似乎对“头发”这种意象情有独钟,直接以“头发”命名的诗就有《回乡偶书,悲黑发》《喜白发》等,甚至诗集也以其中一句诗“一头黑发令我羞耻”来命名。在《喜白发》中,“噢,我终于长出了一根白发/天呐!那么多胸中的尖叫/积压的霜雪,终于有了喷射而出的地方”,诗人一反常规,因为生长出了一根白发而欣喜若狂,而这其实是内心压抑的突然释放,在敌人间亮出了自己的立场。这些胸中涌溢的诗句都是诗人痛苦的自省,是在茫茫人世中自我寻找的确认。可贵的是,诗人并未沉溺在自己的悲喜之中,对于人生海海中的平凡众生,始终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就像鲁迅所说:“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是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也是仁者之心。比如在《广袤》中,借人贩子之口对底层缅甸女子、年老色衰的妓女的关怀,为了生存,她们对卖掉自己的人贩子甚是感激。还有《体内的声音》,此诗平铺直叙地描写了一位背砖的老妇女,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时刻为这位劳动妇女的一系列动作而揪心不已,“终于,又捡起的一块再也没有地方安插下去/嗬!我暗暗吐了一口气,渴望着/她能够把它/放回去。/可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她背起背篓转身而去,/想拽着自己的孩子,手里/紧紧拽着那块哀号的砖头”,这位妇女的背已经不堪负重,但是为了生存,仍然选择手抱最后一块砖。果然,“我只是听到了哗的一声”,似乎这声音是我久已盼望的,并未出我意料之外,让揪着的心落了地。再有《悲恸海》《汪洋》这样的诗歌,诗中虽并未有明确的抒情对象,但是人世汪洋中的所有“溺水者”,却是我“——具体的、放大的一生”。祝立根的诗有着丰富痛苦的自省,就像从胸臆中自然涌溢出来的泉水,漫延到人世间的汪洋湖海,但这悲悯同情并非是泛滥而肆无忌惮的,总是能够收束到自己内心中。如祝立根所认为的那样,诗人祝立根就成了宗祠里的巫师,通过“请神上身”和“推己及人”,诗人能够和亲人、路人甚至死人感同身受地站在一起。
最后,祝立根所承继的诗歌传统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祝立根的诗多是短诗、抒情诗,并多沉郁雄浑的气象。霍俊明在《多余的骨头,或尘世拖着刀斧》提到祝立根诗有三种意象群:“一是以乡村为核心展开的前现代意象;二是围绕着山川、草木、河流这些自然空间生成的外化意象;三是以城镇为中心的公共现实空间的意象。”的确如此,或许是生活在云南边地的缘故,祝立根对自然景物、公共意象有着超越性的敏感,他总能将这些意象和自己的心绪贴切形象地联系起来,比如《在夜郎谷兼寄贵州兄弟》中“瀑布是青山的白发,青山老了/白花茅是一堆堆乱石的白发,石头/也老了。我一直在等一个这样的下午呀/身体里的黑,被一根根白发照亮”,祝立根爱写头发,于是瀑布也成了青山的白发,茅草也成为乱石的白发。这其实是古典诗歌中的比兴手法的运用,这使得诗人与边地风景人情保持了一种混沌一体又疏离旁观的关系,既能深入其中感同身受的抒情,又保持了现代性眼光的批判。另外,祝立根的很多诗都是赠别诗、饮酒诗、怀乡诗、游记诗、羁旅诗,这与古代诗歌功能如出一辙,但他又有自己的才情和理解。比如他的一些怀乡诗、游记诗中对于故乡和云南的理解是很独有的。对于故乡祝立根是深深眷恋着的,但他的怀乡与古代游子怀乡有很大的不同。古代游子的思乡是比较单纯的,就是思念亲人,现代作家的怀乡如沈从文等则出于对城市、对现代性的批判,故乡、乡村承载着他们乌托邦的想象。祝立根的怀乡,或者对云南的地域写作,更接近于鲁迅对故乡绍兴的关系。故乡的确是让诗人泪流满面的地方,他曾很多次想象自己像一只飞鸟穿越怒江之上回到家乡,但他对故乡并未有过分的赞美,只是将其当做“独守光阴墓园的老看守”,一针就能“将我扎得泪流满面”(《乡村医生》),他很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于故乡而言只是“乡宴上的陌生人”,而对于长期寓居之地,却始终融不进去,是异域的陌生人,是一种悬浮的中间物的存在。这或许也是祝立根将诗歌当做自己宗祠的一个重要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