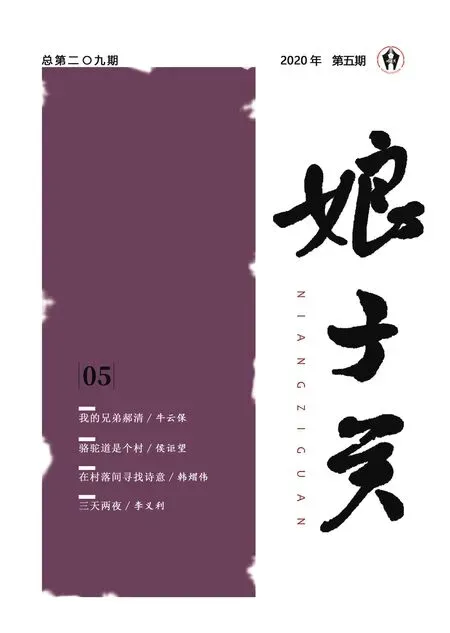我的兄弟郝清
牛云保
一
青春年少的郝清和丰满圆润的师姐的绯闻闹得人尽皆知、满矿风雨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有天上夜班,是我接郝清的班,天热我不想在宿舍待着,一个人慢慢悠悠地往单位走,反正时间也早,赶十点接班就行了。快到车房时,我看到四五个刚上坑的工人,趴着腰围着绞车房的窗户偷看,偷看什么呢。我也趴着腰从窗户里偷看,我看到郝清和师姐活色生香不堪入目的一幕,他们太忘我了,我从窗户边走开,踢了一足门,工人们骂着跑了。郝清开了门,我劈头盖脸地说,大热的天关什么门。郝清意识到什么,一句话没说,换了衣服就走,以前他总是等师姐洗漱完相跟上下班。
绞车房老规矩,上夜班时副司机前半班睡,后半班开车,这谁都知道,前半夜人不困,可谁让咱是副司机呢,又是上班不到两年的新工人。
躺长椅上又睡不着,老想着接班时看到的那些内容,想他们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又想师姐真不要脸,她比郝清大十二三岁,是结了婚的人。想半天又想起我和郝清同一天来队报到,我是刚招工来矿的,郝清是下坑一两年调上来的。郝清一到队部又是散烟,又是队长书记的叫,一副老江湖的样子。我和郝清同一天安排给一个师傅,师傅不让叫师傅,说她不过大我们十几岁,早工作几年,叫师姐好了。
一个班混熟了,郝清让我看他肚上的一道刀口,郝清说,坑下的铁梁撞断他的肠,做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
思来想去,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嫉妒郝清了,我自己吓了自己一跳。后半班的车我老出故障,闹得正司机也睡不好,坐起来骂了我好几回。
丰满而又风骚的师姐,不知何时又和大她十几岁的矿长认识并走得熟络,矿长每次下坑都要来车房坐坐,矿长一来,师姐忙得风车转一样:“郝清,给领导倒杯水,”座椅上开着车的师姐,扭过来扭过去地使唤着郝清忙这忙那,“郝清把我箱里的烟拿出来。郝清你去锅炉房打壶水。”提着壶的郝清嘴里自言自语地骂着,磨磨蹭蹭东瞧西看地走着,一壶水半小时打不回来。师姐黑着脸问:“让你打壶水这么费事。”郝清很重地把壶坐电炉上,一句话不说,坐门口抽烟。十八岁来矿上班的郝精烟瘾已大得厉害,烟雾中透出郝清一张因焦虑愤怒而变得怒气冲冲的脸。
师姐对郝清的心事一目了然,“郝清,我和刘矿长说了,到时调你矿小车房开车,”师姐看着转怒为喜的郝清,心里偷着笑了笑,说,“到时咱姐弟俩一起调上走。离开这脏不拉叽的地方。”
郝清在宿舍里把这好消息告诉我时,还不无炫耀充满友情地说:“苟富贵,勿相忘。到时哥哥走了,肯定帮你一把,给你也调个好工作。”师姐和矿长有一腿这是公开的事,郝清和师姐的关系我又知道得清清楚楚,矿长调郝清去矿上开车就是一句话的事,我和郝清走得更近了,三天两头地请郝清吃饭,老家的土特产也时不时地给郝清拿过来。
自从师姐调矿上后,矿长再没来我们车房一回。我几次三番地暗示郝清该去找找师姐了,起先郝清支支吾吾地避着,后来实在没法了咬牙切齿地对我说,那婊子耍我了,理都不理我了。
失去了师姐好梦落空的郝清和我,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我重拾旧好,拼命地看着名著,以解忧愁,郝清也跟着我如痴如醉地看着,我们俩总是一前一后进出矿图书馆,形影不离地上下班。
书看多了,我试着给《矿工报》投稿,挣了几十块稿费,请郝清小酌了几回。酒酣耳热之际,郝清说他想在坑口卖羊肉汤,并邀请我加盟。郝清显然成竹在胸,羊肉汤摊的地点,进货渠道,多少钱一碗,给我讲得头头是道,最主要是本不大利不小,我们弟兄俩说得热血澎湃,都感觉到血往头上轰隆隆得冲着。对发财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激荡着我们这对只有一份工作一穷二白的难兄难弟。
还是那句老话,钱难挣。一个月下来,郝清首先扛不住了。
在矿坑口摆摊,首先得过了矿武保部这一关,一没送钱二没打招呼的我俩,出摊没几天就让武保部的内保人员撵得推着车东躲西藏。有一回跑得快了,一锅开水浇郝清腿上,更怕的是混混的白吃白喝,郝清不服,有回一混混又来白吃,郝清摆出一副要钱不要命的架势:“先给了钱再吃。”混混一愣,问郝清:“你说啥。”郝清脖子一梗,说:“给了钱再吃。”喝羊肉汤的都不吃了,都盯着混混看。
我给顾客正舀汤,也没顾上理郝清。郝清和混混打起来时,我忙过去拉架,拉开人好说赖说给混混二百块才劝走。
一场架打下来,我还没说散,郝清就败下来了。
我又重操旧业,在各种报刊发表豆腐块。郝清迫不及待地又喜欢上文学,没日没夜的手里捧着名著,连走路都看着,逛商店,买菜也胳膊上夹着本书,嘴里整日念念有词,夜里睡觉后半夜醒来,总能看见郝清伏案写作,苦思冥想,稿纸满地。
几个月下来,郝清变得深沉,凡人不理,连走路都变了,不再是大步流星,而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人们都说郝清变了,变得有文化了,郝清听了微微一笑,颔首点头。
郝清突然间又变得焦躁起来,给《矿工报》投了几月稿只字未发的他脾气大得怕人,谁见了都躲着走,对我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不得不每天小心地和他说话。队里的人说,郝清提前进入更年期了,过了这股劲就正常了。
二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年同一批招工进矿的男女,一个个搬出了宿舍都成家了,最后就剩下郝清一个形单影只地坚守宿舍。我被日子逼得焦头烂额每日奔跑在养家糊口路上时,郝清通知了我大婚的日期。我为他欣慰之余听一个单位的人说,新娘是师姐的邻居,师姐做的大媒,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婚礼简单热闹,郝清老家没有来多少人,我专门上前问了郝清母亲的好,郝清和我倾心交谈过他的家世,他父亲在他出生四天时在坑下一次事故中丧生了,母亲带着他又嫁给了本家的一个叔叔。
新娘模样端庄周正,配郝清绰绰有余。婚宴结束时,我和郝清喝了杯,诚心诚意地祝他以后一天比一天好。婚后的郝清不再落拓不羁,每日西装革履地穿行在大街小巷,一副居家过日子的好男人。郝清老婆怀胎显怀后,便不上班了。郝清说,选煤厂活累,一不小心伤了胎吃大亏了,女人怀一次不容易,郝清家里家外两不误。郝清精力旺盛,还一如既往地醉心于文学,参加了矿上举办的各种文学讲座,一不小心又认识了矿降压站的刘红艳。刘红艳是我们矿的才女,诗歌散文通讯报道样样精通,是《矿工报》的知名作者。人都说刘红艳是怀才不遇,可惜了她一副好身材好笔杆。
郝清有天上班唉声叹气,我问郝清:“咋了兄弟,有什么事和哥说。”郝清躲开我。过了几天,郝清脸上一道一道血印,我问郝清:“你和人打架了。”郝清给我点了支烟,自己又点了支:“兄弟,老婆抓的,老婆逮住我和刘红艳了。”鬼使神差地,刘红艳也迷上郝清了,两人吟诗作赋,互换情书,还河边散步,花前月下窃窃私语。有天两人竟然趁老婆回娘家时相约去郝清家拿书,书没拿上,让郝清老婆杀回马枪破门而入,两人还没形成事实,但郝清正对刘红艳搂搂抱抱上下其手,老婆一回来,郝清手忙脚乱忙拿把尺假装给刘红艳量身高腰围,嘴里说给刘红艳做衣服。郝清老婆也不是好骗的,挺着肚扑上去就打刘红艳。郝清一怕老婆伤了胎,二怕刘红艳挨了打,抱着老婆让刘红艳快跑。郝清跪地求饶,痛哭流涕,指天赌咒地说痛改前非,放跑了刘红艳,老婆左右开弓又咬又抓。
听了郝清的讲述,我上下打量着郝清:“兄弟,真的假的?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刘红艳可不是一般女人啊。”“兄弟骗你干啥。”郝清脱了上衣让我看他一身的黑青印,我看了看,问:“老婆不是吊起来打的吧?”“那倒没有,全是掐的。”郝清诗人一般忧郁地看着窗外。窗外春光明媚,阳光灿烂,一对麻雀叽叽喳喳地在树上跳着。我问他:“你咋想的。是休了老婆娶刘红艳?还是继续挨打受气过下去?”“不知刘红艳咋想的,她嘴上说离婚了和我过。”郝清对刘红艳是难以割舍,又觉得在老婆身上良心过不去,又怕师姐骂他。
有天我出门打水,见门口站一壮汉,问我:“郝清是不是这里上班?”我忙摆手摇头,壮汉说:“你们车房的郝清勾引人家老婆,破坏别人婚姻家庭,今天我非卸他一件。”我吓得就走,绕了一圈从窗户上跳回车房,叫郝清赶紧躲起来,不想郝清比我还灵,早藏地下室了。
壮汉等了半个时辰,嘴里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改天过来收拾你。
经此一吓,郝清变得神出鬼没,上下班不定时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来了单位要么一言不发,要么说起来滔滔不绝,有时一个人在阴暗角落里双腿盘坐,两眼微闭,苦思冥想着什么。
事情并没有经师姐和单位的人苦口婆心的劝说而停止,刘红艳和丈夫离了,郝清在孩子出生百天后也毅然决然地离了,郝清净身出户,又搬回了单位宿舍大楼。
命运又一次捉弄了郝清,我们矿的才女刘红艳拒绝了他的求婚,用我们电影里常见的文艺语言对他说:“我们不适合在一起,相爱并不能决定在一起相守一辈子。”郝清当头挨了一棒一样傻了,双眼圆睁恨不能掐死刘红艳:“我为了你都离婚了,你不跟我离什么婚啊?”刘红艳躲开曾经爱她爱得死去活来今天还一如既往为她抛妻弃子的郝清的眼睛,刘红艳爱情片看多了,自然而然地模仿着电影女明星的一招一式,两眼平视着远方,一字一句地说:“我离婚是我的自由,我没有逼你离婚吧。”郝清想了想,是啊,人家并没有逼我离婚啊,可郝清还是想不明白,问刘红艳:“那你为什么离婚啊?”“我受不了婚姻的束缚,我渴望自由,我不愿把自己埋在凡人俗世中,我想走出矿山到我想去的地方去。”才女刘红艳朗诵完为郝清最后作的一首诗歌,转过身就走,撂下郝清一个人叫天不应叫地不管浑身冰凉地坐在地下。
三
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郝清突然间疯狂地陷入一心想发财的梦想中,对文学和女人视若洪水猛兽,说这都是害人的东西,只有金钱是永恒的,世上唯有钱才会忠心耿耿地追随着你。钱生不带来却死能带去,是你的就是你,钱给你带来安全感、满足感。我知道郝清嘴上不说,心里在怨恨刘红艳嫌他穷。
郝清瞅准了股市,他认为股市是个挣钱的好地方,把钱放进去就行了,不像别的买卖累人,最关键是不用跟人打交道,省心,借了五万块钱的郝清勇猛地跳进股海,每日风雨无阻股市看大盘,关心时事,一上班给我唾沫飞溅地讲股市,先知先觉地分析国事政事。郝清为股票的大涨彻夜难眠,为股票的大跌捶胸跺足,半年下来郝清没疯,我快要让郝清逼疯了,为了躲避郝清对股市的分析研究,我在单位躲着郝清让着郝清。
快过年时,郝清突然失踪了,班也不上了,假也不请,我们队长让我去宿舍找找看,是不是郝清病了。去了郝清宿舍,一股怪味席卷着烟味扑面而来,郝清目光呆滞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我吓了一跳,十几天不见,郝清变成如此模样,胡子拉碴不说,整个人面黄肌瘦。我问郝清:“咋了?兄弟,你遇上什么难事了?”郝清和我要烟抽,郝清摸了把脸,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兄弟是穷命啊,股市里的钱跌完了。”我把窗户打开,新鲜的风吹进来,我和郝清倾心相谈,我劝他每天不要胡思乱想了,赔了就赔了,勒紧裤腰带,每天好好上班,人生还来得及。郝清抱着我哭了,说他什么也没有了。我说,你人好好的还有份工作这就行了,借下的咱慢慢还。
人生的十字路上,事业如日中天的师姐又一次帮了郝清一把。已升为副主任的师姐不费吹灰之力帮郝清摆平了被别人逼债一事,上了班的郝清又恢复了往日的洒脱不羁,上班迟到早走,下了班灯红酒绿。我奇怪的是他和师姐的若即若离,说远吧,每回郝清山穷水尽时,师姐总及时雨一样来到郝清身边。说近吧,我从未听郝清说过他和师姐如何如何,我想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藕断丝连吧。
为了还清股债,为了过上好日子,郝清绞尽胆汁地想着生财之道。我知道郝清从来就不是安分守己的人,我说,你先缓缓再说,先积攒点钱咱再做个小买卖,郝清鼻子里哼了一声,说,燕雀安知鸿鹄大志。
郝清盯上了坑口大院里堆积如山的废铁,我们车房和大院只有一墙之隔,郝清昼伏夜出,蚂蚁搬家一样蚕食着大院的废铁。有了点家底,郝清马上买了辆摩托,骑着摩托,载着废铁,每日风驰电掣地穿关过卡。有了生活奔头的郝清,没日没夜受死受活地拼命偷铁卖铜,你分不清他什么时下了班,什么时是上着班。郝清一天到晚穿着一身黑脏污烂的工作衣吃住在单位,小恩小惠着我们队长和我。队长睁一眼闭一眼,我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地放纵着郝清。为了一包烟,我心甘情愿地一个人开着车,任郝清越墙倒腾废铁。
一月下来,郝清竟和矿武保部的大小官员打得一片火热,和看门的师傅称兄道弟,每日吃吃喝喝。郝清不是偷铁了,而是变成拿铁。拿废铁成了他的全部工作,在夜色的掩盖下,郝清能大摇大摆地进院,东挑西拣地扛上铁就走。
郝清还清了债,又变得神采飞扬,好烟好酒地呼朋唤友。
身心膨胀的郝清嫌摩托带铁来钱慢,开上了面包车在矿岗楼进进出出。郝清成了矿上的名人,所有人为他竖起大拇指,称他为能人,有本事的人。大家都说,这年头能弄下钱就是大爷。
师姐为他这样打了几次电话,郝清对我说,她管得太宽了,她算我什么呢。我劝他,毕竟是偷,你再有人是不是也听听师姐的话,人家毕竟是帮了你大忙的人,不要看武保部的人吃你喝你,真出了事,他们躲得远远的,倒霉的还是你。郝清说,这比吸毒还上瘾,我想收手呢,每天弄不下几百块心痒痒的觉都睡不好。
为了把事业做得更大,为了能迅速致富,郝清又盯上了坑口的电缆。郝清不愧是郝清,几个回合下来,坑口材料员就被郝清好烟好酒完全收服了,坑口材料员和郝清里应外合地每天大肆偷盗着电缆。郝清每日在我们面前故意大把大把数着卖铜挣来的钱,看得我眼热心跳,又羡慕又嫉妒,与此同时,有了钱的郝清对刚接班来矿的女工王青莲展开了炽烈的追求。王青莲刚满十八岁,长相俊美,浑身充满着一股农村少女的气息。王青莲对这个花花世界还没有完全看透,处处显得不谙世事,这正中郝清下怀。郝清除了偷铜就是围绕着王青莲转,别人给王青莲介绍个对象,郝清想方设法地阻挠,连哄带吓哄骗着王青莲。我亲眼见过一个刚分配来矿的大学生对王青莲有点意思,来车房接过几回王青莲,这让郝清醋意大发,气急败坏地撵上大学生又打又骂,吓得大学生再没敢在车房门口露面。
郝清迎来事业爱情双丰收,抱得美人归还大发横财,搬出了宿舍外面租下家和王青莲公开同居,女上班男偷铜,开着面包车双双把家回。
可惜好景不长,郝清拉着一车电缆出矿时,让西城公安盯上了。郝清进去半年费尽周折出来后,又恢复了他穷困潦倒的生活,已习惯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的王清莲,不再脉脉含情地对他百依百顺了,时时显得不耐烦。
为了过上以往的生活,郝清还想重操旧业,可郝清偷铁卖铜的名声太大了,武保部的几个干部都跟上受了罚,所有的人都避之不及。人都知道,要不是师姐上蹿下跳地活动,他早让矿开除了。
郝清给看门的师傅夹窗户扔了两盒烟,看门师傅赶紧又从窗户扔出来:“不会抽烟。”郝清拉了车废铁还没走出百米,武保部的人就从天而降,以前称兄道弟一块吃吃喝喝的兄弟变得铁面无私。郝清递过二百块,武保部的人一巴掌打掉:“你什么意思?打发要饭的呢?我没见过二百块钱。”郝清忙掏烟,武保部的说:“先回部里再说。”郝清说:“兄弟这铁我不要,卖了都归你。”“我稀罕你这点钱,走,先回部里。”武保部的人连推带搡地把郝清弄回部里。
罚了一万的郝清欲哭无泪,上班不到两年的王青莲沾染了一身恶习,变得庸俗不堪,竟两天三头地不回家了。郝清为了这个家,为了哄王青莲开心,举债度日,四处借钱,借了又不还,借的不多,但人都讨厌。
“哥,借你十块。”郝清为了能借上钱,见谁都是哥。
“没有。”
“五块。”郝清低三下四。
“一分也没有。”
这时的王青莲又和一个有妇之夫的工人传出绯闻,郝清不信也不行了,王青莲半月不回来了,回来了又冷眉冷眼,扔东甩西,已到了山穷水尽的郝清再也不想失去这个家了。郝清让一寸,王青莲进一尺。郝清想,这样下去可不行了,我正面进攻不行,来他个迂回侧击。
郝清找有妇之夫的妇人去:“嫂,你知道你家的人勾搭俺老婆不。”妇人看都不看郝清一眼。
“你也不管管?”郝清原先计划好的话一句也用不上了。
“你不嫌丢人。”郝清快要哭了。
“你们不要脸,我还想活人呢。”郝清怒了,实在忍不住了。
妇人站起来:“滚,先回家管好你老婆。”
妇人身材高大,一脸横肉,不怒自威地吓得郝清退了半步:“我管不了这些闲事,回家管好你的臭娘们,一个巴掌拍不响。”
郝清落荒而逃。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郝清虚弱得饭都不想吃。想东山再起的郝清又发现了新的生财之道——买彩票,别人是一张两张地买,他是一盒两盒地买,可连袋洗衣粉也没中。郝清又放眼全矿,不信没条生财之道。
一个捡炭的开启了郝清的智慧。看着捡炭的在垃圾堆里在废弃的煤场里捡一袋炭能卖十块,郝清顿然一悟,对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我卖炭啊,炭虽然来钱慢,但也是条路啊。郝清在这条财路上说干就干,郝清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郝清每天比下坑的还黑,郝清连捡带偷,靠着以往的一点关系,武保部的也不太管他,毕竟是捡点炭,和铁性质不一样。郝清的小面包呼啸着又从岗楼口进进出出。
郝清脸上又有了笑容,王青莲也不跑了,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两口子计划着要个孩子,折腾了半年,王青莲肚子一点动静也没有,郝清有前妻生下的儿子为理由,理直气壮地指责王青莲不行。王青莲嘴上硬,心里却打鼓。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生孩子,两口子拼命地又折腾了半年,结果颗粒无收。王青莲看着郝清白天黑夜地劳累,自己先怕了,说:“咱先抱个,我听老人说,抱一个引一窝。”郝清生气:“我种子质量一百个放心,是你的地不行。”“我的地咋不好了,要墒有墒,要水有水。”王青莲做贼心虚地又说,“再好的地碰上年成不行,受死也不行。”又说,“咱抱个不是和亲生的一样,就是没生了下。”郝清有自己的打算,前妻给他生下儿子了,抱一个就抱一个吧,抱个闺女省心。
两口子意见统一,王青莲真抱回一个闺女来,孩子已过百天,长得又白又胖。
四
我曾经坚定地认为,郝清会乐观勇敢地活下去,他虽然活得那么艰难。但他还是死了,他死得又扑朔迷离。
今年夏天特别的热,下了班回家,就不想出去,我们队长是下午四点多给我打的电话,手机里我都能感到队长上下牙齿嗒嗒的叩击声:“老刘快来回副井车房,出事了!”我问队长有什么事,队长是个年轻人,用快哭的声音说:“一时半会儿说不清,你赶快来就行了。”我下楼开上车就走,脑子里想了各种出事的可能性——车房里突然有人病了?还是电机烧了?到了车房,门口围着好多人,进去一看,我吓得叫了一声跑开。下班时还和我有说有笑的郝清,现在夹在钢丝绳和滚筒之间。
郝清的徒弟来平嘴里自言自语着在车房转圈圈走着。
队长说:“死了。”
我又走在滚筒边,看了看挂在半空中的好友郝清:“老郝,老郝。”我大着胆推了推老郝的上身又喊“老郝,老郝。”郝清面朝着滚筒,胳膊粗的钢丝绳缠绕在胸脯上,我仔细看了看,钢丝绳缠了他两圈。绞车房里站满了人,人们只是看着,车房里静悄悄的,似乎都在想着:一个开绞车的是如何把自己缠在了滚筒和钢丝绳之间的。
队长让来平把绞车倒回来,来平只是嘴里念叨着,傻了一样的看着一群人。我把他推开,坐在了司机座上,把绞车启动了,一点一点地把郝清放下来。一伙人扶着拉着他,我走过去看着放地上的郝清,郝清的眼眶里充满着血,从眼角里慢慢地渗出来,郝清双眼暴突,愤怒地瞪视着这个世界,钢丝绳缠烂的上身渗透出一片血红。急救大夫看了看也走了,我找了件工作衣把郝清的头脸盖住。
人们把郝清往车上抬时,一只新穿的绝缘鞋从他脚上掉下,我捡起来放门口。我看见从他身上滴落下来几滴血,下午的阳光照上去,竟变成了金色的,救护车没有上来时的鸣叫,悄无声息地把郝清拉向了公墓的太平间。
队长给我点了支烟,说:“你不要回了,就替老郝顶个班,明天我再安排人。”我把烟吸了一口,我把烟头烧得红红的烟放在了郝清的工作箱上,细长袅袅升起的烟雾飘向了半空,我在心里说,老郝,一路走好。我给郝清点第二支烟时,太阳已下去了,车房里隐隐约约的一片黑暗,我把郝清的工具箱翻了翻,几件工作衣里夹着一本日记。
我给我的志同道合的文学挚友郝清点第四支烟时,我看完了郝清近期所有的日记。
月亮升起来了,灰蒙蒙的天空中,月亮看上去也疲惫不堪。
车房里一个组的同事都来了,不知谁在郝清的工具箱上放上了供品,还点了一支香,谁也没说话,只是站了会儿。临走时,一个工人开玩笑说,今晚小心老郝给你们打手机啊,可没有一个人应和,也没有人笑,开玩笑的这个工人就讪讪地一个人前面走了。
五
翻开郝清的日记,日记中的郝清和现实中的郝清判若两人。日记中的郝清哭着叫着挣扎着,日记中一个最真实的郝清赤裸裸地站在你面前,日记中的这个男人哭比笑多,这个男人才华横溢,文字飞扬,这个男人怀才不遇却又孤身奋斗着,为了生活有苦不言,为了家庭忍辱负重。
一整本日记是一个完整丰满可怜楚楚的男人。前妻为了儿子的抚养费堵在郝清单位门口。大妻哥赌博欠下高利贷,郝清在王青莲的威逼利诱下四处借钱。老家的亲戚打电话借钱,郝清瞒着王青莲偷偷摸摸打钱。郝清在家逮住王青莲和男人幽会,为了孩子,为了家丑不外扬,郝清打掉门牙往肚里咽。一整本日记简直成了郝清的斑斑血泪。
我本以为,郝清一死一切烟消云散,不想一种郝清是自杀的阴谋论在我们单位悄悄蔓延,可郝清死后发生的一些事不得不让人怀疑。
我们单位里的好多人在郝清死后显得异常担忧焦虑,整天四处打问矿上对郝清的死亡处理结果,这些人起先是遮遮掩掩地打问着,互相试探着交流着郝清一些消息,不料都大吃一惊,大家手里握着郝清打下的欠条,多则几万,少则几千,都觉得上郝清当了,原来郝清都骗他们了,原来郝清做的一套说的一套。一伙人说,郝清当时借钱说是买家,或是给老人看病,那他到底拿上这几十万干了啥啊。
我找出郝清送我的一本诗集,我怀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从诗集中搜索着郝清的一点点蛛丝马迹,我甚至暗自庆幸郝清从没开口向我借钱,可我又心痛如绞,我恨郝清为什么不向我借钱,我又隐隐察觉到郝清是另有所谋,从一开始郝清是不是就是做好有借不还的准备。
有天郝清上班时为无钱买手机唉声叹气,他说手机烂得实在不能用了,他去市里买来,可最便宜的也得五六百,我本不想理他,看着他一上午愁眉苦脸坐在车房里一个人自言自语,我又害怕又可怜他,我把我箱里的一部旧手机给了他,郝清马上眉开眼笑,甚至有点手舞足蹈地在车房里擦地整理工具,看着他,我想起那个心高气傲才华横溢留着一头长发的郝清,临下班时,郝清郑重其事双手颤动着把一本薄薄的诗集放我桌上,说:“哥,这是我几十年的心血,兄弟送你本做个念想。”“你死呀还做个念想。”我心里想郝清什么时候还出书了,我翻看着书,我问他,“这谁给你出的书?”“一个文友给我联系的,要了我一两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郝清给了我,我压工具箱里从没有翻看过,这是我第一次拿出来细细地一字一句地研读着。
队长说,矿上意思是私了,往上报时说是郝清得急病死了,私了与谁都好,郝清家属能多算一百来万,公了只有几十万,矿上的干部又不用受处分,工人的奖金不少发一分,算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
郝清死了能算二百来万,一下刺激了全矿的人,手里握着郝清欠条的人也松了口气,有的竟说,郝清这回没白死,二三百万呢,老婆孩后半辈子享福了。
死者为大,我们单位平时和郝清关系不错的几个工人去公墓太平间给郝清上了香磕了头。我看见郝清静静地躺在冰棺里,我们围着郝清转了一圈,一种强烈地想抱他想打他的感觉冲击着我,说不清楚这种强烈的愿望来自哪里。是一种遗憾?还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怨恨?也许是多少年的情同手足的难舍难分。郝清静静地躺在玻璃罩里,我们近在咫尺,却永远不能再相见。多年的兄弟依恋之情,使我痛得不得不扶着墙走,又驱车几十里去宾馆看望郝清的老婆孩子。郝清女儿上大学了,她小时我常见,上了学都忙了,再没见过。看着郝清女儿,我感觉时光过得真快。快不说,郝清竟和我阴阳两隔了,人世间的一切真的变得太快了。
我们走出来,有几个工人说悄悄话,说看不出王青莲有一点悲伤,头发染的还是黄的,手指甲还是红的。队长说,除了女儿伤心地哭,我就没见过郝清老婆哭过,低着头装呢。队长又说,十几天了就没去看看郝清,上炷香。
郝清自杀的消息在我们矿传得此起彼伏,我们队里的工人一上班就讨论郝清是不是自杀的事。郝清徒弟来平说,他是那勤快的人,一上班就拿起墩布去擦地,问题是滚筒后面就不是他的卫生区啊。来平给我们看车房里调出来的监控,监控里的郝清在滚筒后面来来回回地走了几回,显得磨磨蹭蹭,监控里的郝清在钢丝绳的缠绕下在滚筒上转动时,我于心不忍地坐一边,人们说郝清没叫一声。
来平一来车房就是郝清的徒弟,郝清的死吓得来平十几天不敢上班。上了班的来平对师傅恨得咬牙切齿,他首先一口咬定师傅就是自杀的,他说他对师傅了如指掌,他说师傅玩网贷呢。人们不懂,来平解释说,网贷就是电脑上玩高利息呢,把钱给了平台,挣人家的利息呢,师傅玩的平台都找不见了。人们说着议论着,我听着,有一个说,郝清平时上班哪天也忘不了手机,就是手机丢家里了也要不上班回家取,那天他清清楚楚记得郝清没带手机。他还说,让郝清回去取手机,他先替他上会。来平说,师傅的手机能忘了带,那是专门丢家里的,一上班有半个班在手机看挣了多少。
我想起郝清前半年的样子,穷困潦倒的郝清穿戴打扮干净利索,变化最大的是郝清整日背个小包,上班放箱里,下班背身上,我还开玩笑说,郝清,包里背废铁呢,郝清那时不置可否地神秘地笑了笑。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去看郝清老婆孩子时,他女儿说,爸爸平时上班从来不和她说上班走呀,说走就走了,可那天爸爸专门和她说,爸爸走呀。
郝清的死变得疑点重重,矿安监处会同我们队的人还去滚筒后面专门研究了半天,众人看着也都无法说清郝清怎样进去的。滚筒四周戒备森严,就是为了防止卷进人专门围着铁栏,一个可怕的却又清晰的论证在人们心中形成,除非是郝清专门跳进去的,这是郝清的一场阴谋。整个车房除了滚筒后边这个死角没有监控,整个车房都布满了天罗地网。
郝清的死亡事故还没处理完,又传来了师姐办公室上吊自杀的消息。
我知道师姐这几年也过得异常艰难,人老珠黄、无儿无女的师姐先是下了岗,后来做生意又赔得一塌糊涂,返回来上班,又遭遇离婚。我经常见师姐一个人上下班走在路上,形容枯槁憔悴。无能为力的我只能远远地看看她。
工人们把师姐和郝清的棺材放一块,说,这两人是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
这个世上只有我知道师姐对郝清的好,师姐对郝清的良苦用心是我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对这个世界这个人世深有体会并挣扎拼搏求饶之后才悟出来的,师姐调到矿机关后对郝清的若即若离是为了郝清能有个家,所有熟悉郝清的人说,不是郝清有个好师姐,矿上不知把郝清开除多少回了,可这种好,郝清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一点感恩感激之情。
我也是后来得知,师姐是孤儿出身,上班没几年后养父母都相继去世,无牵无挂的师姐婚姻上又磕磕绊绊,也许这个世界上郝清是唯一给过她最温暖最刻骨铭心的人。师姐为了郝清有个好前程,费尽周折想方设法地把他调进调度室,可郝清又盯上科办公室主任之位,师姐劝他一步一步来,先把调度员干好,当我们还羡慕郝清坐办公室里喝茶聊天就挣了钱的时候,欲壑难填得陇望蜀的郝清为没有得到办公室主任一职,而情绪低落自暴自弃起来,工作上丢三落四,吊儿郎当,此时正逢下岗高潮,失去了靠山的师姐第一批被割了下来,郝清也顺理成章又被赶回了原单位,继续回队开绞车。
我始终不得师姐和郝清其解,她俩到底是谁害了谁?
郝清死后一个月,矿上和郝清的老婆达成了协议,这时郝清前妻携子来到矿上,提出要分一半,这一下王青莲也傻眼了,没想到郝清前妻会来,却又是合情合理的事。王青莲不给,说,你和郝清离了,你儿子是不是郝清的还两回事,前妻说,你女儿是郝清的?
死人已经在太平房一个月了,不能再放了,老家的人要求入土为安,先埋了再说。送郝清回老家时,我们几个单位的工人陪着郝清回了老家。下午四点多,郝清下葬时天空飘起了雨丝,郝清的棺材上马上湿淋淋的,队长拿着手机拍着,埋葬郝清时,人们很匆忙,就像郝清的一生一样。
回了矿,我听人说,因前妻和王青莲在赔偿钱上争得你死我活,矿上没法分钱,就让她们走法律分。前妻去法院告了王青莲,她们后来咋回事,钱分开了没,我也无从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