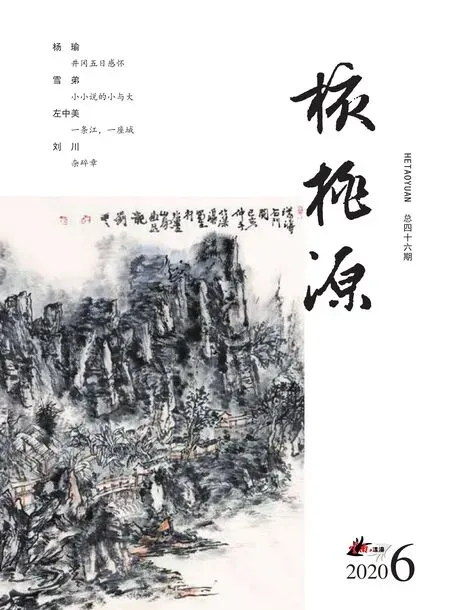戏 痴(二题)
蝶衣水袖轻舞,眉眼流转不离哑叔。哑叔微笑颔首,蝶衣一招一式更加轻盈灵动。人们便说:这一对戏痴!
哑叔和蝶衣同为小城汉剧界名角。程家班北上西安南下武汉,所到之处场场爆满,创下了经久不衰的辉煌。哑叔擅长武生,蝶衣善演花旦,戏里戏外,一如天上仙侣误落凡间。
彼时正逢庙会。舞台上哑叔蝶衣眉目传情,看得台下观众如痴如醉。却见前排中央一人,眯着小眼睛盯着蝶衣,目光黏在蝶衣粉嫩的俏脸上。此人络腮胡子一抖,嘴里骂道:奶奶的,老子在战场上没被要命,到这里却被这妞把魂勾去了!然后起身去了后台。络腮胡子何许人也?从武汉战场上撤回来的孔团长。当晚,蝶衣和哑叔就被孔团长带回了驻地。
孔团长借口为母亲祝寿,要唱三天大戏。晚上便迫不及待地来找蝶衣,把一枚金戒指递给蝶衣说:今后你就给老子一个人唱戏吧。蝶衣看看那一脸的络腮胡子,厌恶地扭过头去。孔团长碰了一鼻子灰,掏出手枪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说:看不上老子?信不信老子做了你!说罢,朝身后一呶嘴,两个卫兵噌地一下上前就要扭住蝶衣往外拖。
这时,哑叔忙陪着笑,躬身对孔团长说:长官息怒,蝶衣乃民间戏子,未免有些紧张,能否等戏唱完容我再劝劝她?孔团长斜睨哑叔一眼,鼻子轻哼一声,抓起手枪走了。当晚,蝶衣和哑叔想逃,见门口有士兵把守,只好作罢。
三天大戏只剩最后一场了,孔家祠堂前人山人海,十里八乡的人都赶来一睹小城名角。孔团长的娘高兴得张着一嘴壑牙连声叫好。最后一场《辕门斩子》唱着唱着,只见哑叔双目圆睁,指着坐在老太太身边的孔团长唱道:可恨那倭寇马踏汉口,你却藏家中独自贪欢,抢民女占祠堂大显淫威,有何颜面见列祖列宗,难不成是那禽兽投胎?台下依然如痴如醉。接着,哑叔一挥马鞭指向孔团长的娘,继续唱:老娘亲你细思量,想当初何不将他马桶溺亡?留这厮白吃军粮,今骂他你休责怪,只因他辱了你孔家门楣……
热闹非凡的台下突然静了下来,孔团长看看身边气得浑身颤抖的老娘,再看看台上的哑叔,细细回味那几句唱词,终于明白原来是对着孔家列祖列宗骂他,气得脸色由黑转红,继而铁青,掏枪朝天叭的一枪,台下的人们哗啦啦散去。
晚上,孔团长端着一碗镪水,捏着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哑叔下巴说:让你唱,老子把你变成哑巴!哑叔说:实不该冲撞长官,但求放过蝶衣,若能积极抗日,我一戏子死而无憾。说罢,猛地夺过碗一饮而尽,抽搐着身子晕死过去。孔团长先是一惊,继而缓缓松开了手,冲士兵摆摆手说:放了他们吧。翌日,孔团长率兵南下,在武汉战役中与日军激战,一人杀掉数十名日军,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
蝶衣和哑叔回到程家班,蝶衣依旧唱戏,哑叔改行拉胡琴。本来俩人早该成为夫妻,只是哑叔不愿拖累蝶衣。哑叔宁愿一辈子坐在台侧,看蝶衣唱戏。蝶衣也一直单身,在哑叔的目光中把生死情仇、悲欢离合演绎成极致。
后来小城解放,哑叔和蝶衣进了县剧团。蝶衣还唱旦角,哑叔依然拉着胡琴。再后来,孔家祠堂被红卫兵捣毁,蝶衣和哑叔四处奔走,到有关部门解释说孔团长是抗日英雄,那个年代自然无人相信。找的次数多了,就认识了革委会刘副主任,刘副主任看上了蝶衣。刘副主任把哑叔扣上了包庇国民党军官的帽子打成了特务。哑叔说不出话来,却一封接一封地给上级写信为孔团长辩解,后来被拉到县城的河滩上枪毙了。
那一晚,竟无人敢帮哑叔收尸。殷红的血把鹅卵石都染成了红色,人们看见蝶衣一身洁白衣裙在河滩上浅吟低唱,轻舞水袖。第二天在河湾深潭里找到了蝶衣,蝶衣已经僵硬的身体依旧是舞台上的造型,满面含笑,眼波流转。
小城再无蝶衣。成为刑场的河滩从此少有人迹,偶尔有老人经过,会听着流水的呜咽声说:听,那对戏痴又在对戏文了呢。
白先生
白先生!胡老三把一袋大洋扔在白先生面前。白先生头也不抬地说,大当家的,医心堂素来只医好人,作恶者恕不医治。
胡老三说,我出一百大洋!白先生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请回吧!胡老三恶狠狠地说,姓白的,你等着!白先生轻轻摇了摇头。胡老三来找白先生,是要给二当家的麻五治枪伤。本来,胡老三占据清风寨险要之地,日子过得逍遥自在。但麻五见日本人在城里耀武扬威,就极力撺掇胡老三投靠日本人。胡老三说,日本人亡我国土,岂可卖国求荣!麻五便擅自见日本大佐宫本一郎。宫本送给清风寨五十条枪,让麻五劝降胡老三。进了青龙山,早有匪徒报告,说是麻五搞到了几十条枪,让前去接应。胡老三带人刚接上头,却遇上青龙山游击队,一颗流弹迎面飞来,只见麻五纵身挡在胡老三面前,子弹噗嗤一声钻进了麻五的左眼。胡老三只得招呼众匪背起麻五,跑回清风寨。
胡老三对着昏迷不醒的麻五拜了又拜,然后下山去找白先生。谁知,白先生不肯救治,胡老三恨得牙痒却又无可奈何。
三更时分,胡老三潜入医心堂。凑近窗前,只见白先生用一把小刀在麻油灯上炙烤,然后向一个昏迷不醒的人腿上的枪伤扎进去,割去腐肉,再一挑,一颗子弹头掉在下面的盘子里。又取出银针扎上止血,将药粉调成糊状,填进那人腿上的血洞里,再用白布扎了起来。片刻,来人就醒了。旁边一人掏出几块大洋,白先生连连摆手说,医心堂素来只医善者,队长为打小鬼子受伤,白某岂能收钱?
胡老三躲在一只水瓮背后,看着来人出了门,心里猜想定是游击队的人了。正迟疑间,撞在了花盆边沿,发出哗啦一声。白先生轻声说,出来吧,大当家的。
白先生取出一包药粉说,大当家的是一条汉子,白某敬重你,只是你那兄弟,只怕是医得了人却医不了心啊。
胡老三按白先生的嘱咐,给麻五调药、取弹、敷药,麻五醒了。见劝不动胡老三,独自带了部分人马投靠了宫本。谁知不久,宫本一郎便带着日本兵,由麻五带路攻上山来。
麻五上山骗开寨门,让鬼子从暗道上山。麻五说,大哥,听我的吧,往后你是皇协军大队长,我是副队长,咱还是亲兄弟。胡老三说,二弟,我的命是你救的,但我胡老三不能忘了祖宗,你当你的皇协军,我当我的土匪,咱俩井水不犯河水。麻五说,好!交出清风寨这么多年积攒的金银财宝,我就让宫本放了你!
胡老三仰天大笑道,好你个麻五!麻五拔出枪来说,胡老三,别怪我不仗义了!说完,对着天空连开三枪。从暗道爬上来的日本兵将胡老三团团围住。胡老三撂倒十几个日本兵,被麻五一枪射中大腿,被日本兵吊在了大树上。麻五对宫本嘀咕了几句,宫本一边拷打胡老三,一边逼问清风寨的钱藏在哪儿。最后把一根烧红的铁条从胡老三腿上的弹孔插进去,胡老三惨叫一声晕死了过去。
睁开眼睛,胡老三问,鬼子呢?麻五呢?白先生一边给他涂药一边说,死了。胡老三说,白先生,谢谢你。白先生笑了笑,指了指身后说,该谢的人在这呢。胡老三看过去,正是那晚白先生救治过的游击队长。
那人看着胡老三说,大当家的,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吧!胡老三扭过头去说,我不干,我差点被你们打死了呢。白先生拈起几枚银针扎进胡老三的脑袋,胡老三只觉眼前的火光亮起,仿佛看见宫本正呜哩哇啦地喊着,弟兄们一排排的倒下,胸口汩汩冒着血泡。最后他的妻子抱着孩子从地窖里跑出来,扑向晕死过去的他,却被宫本一刀劈倒在了火堆里烧成了焦炭。胡老三又晕了去了。
再次醒来,胡老三拉着白先生的手哇哇地哭着说,白先生,你救了我的命也救了我的心,我听你的!随后,胡老三带人挖出了藏在寨子里的金银,捐给白先生在镇上建了一家医院,自己随着游击队南下抗日去了,后来牺牲在战场上。
解放后,医院成为了镇卫生院。白先生一直坐诊,直到九十多岁,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