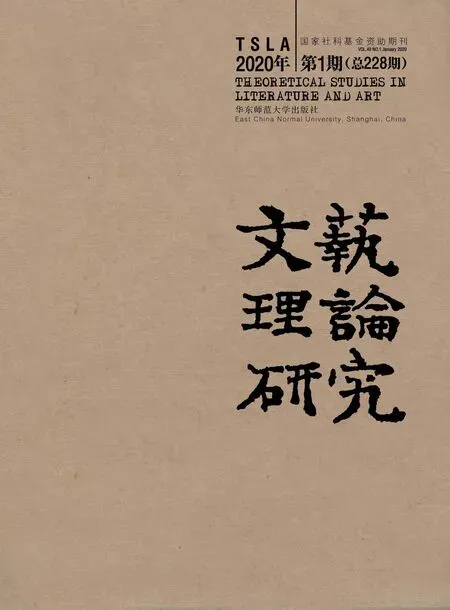“美术革命”的现代性及其困境
曾小凤
一般认为,中国社会自晚清以降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上,都历经空前未有的急剧变革。伴随着一系列现实政治的刺激,“革命”几乎成了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共享的一种话语形态。1902年,梁启超在《释革》中阐明所提“诗界革命”中的“革命”一词是从日人所译英语“revolution”借来,它的确切含义并不是中国古代“以暴易暴之革命”,具有与“天演”相关联的“变革”或“改革”之意(123—26)。到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和“美术革命”相继提出之时,一般人对这些激进口号的想象,大都不会将之与暴力性质的政治革命混为一谈,其直抵“文学”和“美术”本体的革新之义是相对清楚的。无论是倡议者,还是公众,他们使用和接受“革命”一词的心理预期早已脱略了那种暧昧不明的政治革命想象。
就“美术革命”而言,1919年吕澂和陈独秀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所开展的“美术革命”通信,恰逢其时地在议题上应接了“文学革命”的时潮趋向,使日益显出沉滞的“美术”一途真正融汇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之中。“美术革命”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对象性: 对作为特定知识范型的“美术”的批评。从批评史而不是美术史的角度审视“美术革命”,需要关注的问题,主要不是这个议题的社会化过程,而是要揭示批评主体的文化心理与社会思潮、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因为从根本上说,“美术革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美术的批判和否定中获得其议题的价值和有效性的,而它的中止恰也凸显出这一共同的价值取向中所包含的严重分歧,即对“美术”的不同想象。
晚清民初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及其社会化运行,无疑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批评史的一件大事。尽管“美术”作为单一词汇的运行(如译介、传播和接受)是其概念内涵中的重要方面,且学界已有不少研究,①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个词在晚清至“五四”的历史语境中却是和一系列概念相竞争与互动的,包括“艺术”“文学”“美文”“美育”“审美”“美感”“美学”“美术史”“美术批评”等,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具有强烈现代人文精神取向的话语形态。基于此,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美术”看作一种能动的知识话语,放在晚清至“五四”的历史语境中同与它竞争或互动的概念联系起来考察,以此深化我们对“美术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关系的认识。
一、 “文学”之“美”的确立
从晚清“诗界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文学革命”,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文学”完成了其作为一门现代意义的独立学科的创建。大体来说,作为现代学科之一的“文学”,在学术谱系上历经了从“词章”到“美术”再到“文学”的演化过程(贺昌盛33—38)。但转换到从“美术”的立场,来看“文学”逐步演递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复杂历史,就会产生一些有意思的新问题: 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演进过程中,“美术”和“文学”是如何建立起学理关联的?为何“文学”会从“美术”中独立而出?当“文学”走向一种现代意义的学科形态后,“美术”又如何?
相比“美术”这一日源新学语,“文学”是一个中国古语词,意指关于“文”的学问和技能。这个词与“literature”的互译关系,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来华传教士艾儒略的翻译;其后,这一译法被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采用,并经由日语“bungaku”(文学)的双程流传而播扬甚广(刘禾380)。在晚清西学潮流的双向译介与传播过程中,“文学”的传统义和现代新义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鉴于此,晚清学人基于“文学”的不同学术取向与理论阐发,正是在新旧语义混杂的层面展开,贺昌盛将之总结为四种路向: 一是章太炎的广义“文学”论,其要义在于强调“文”之“学”的功用性;二是刘师培的“骈文正宗”论,注重“文”在“纹”的意义上的“美饰”特质;三是王国维的超功利“审美”说,强调“美”之于文学乃至人生的超越性;四是梁启超的“文以致用”说,关注“新文体”所具有的文化启蒙意义(贺昌盛113—18)。这四种学术取向构成一种对话关系,代表了晚清学人为“文学”正名的努力,同时也开拓出现代意义的“文学”在致用与审美两条理路上的学术基础,而“美术”作为“文学”审美特质一面的理论支持,内在于晚清学人重新界定“文学”之本质的思考中。
其中,尤以王国维的“美术”用例最具代表性。“美术”,是王国维学术视野由“哲学”移于“文学”之后频繁使用的术语(叶嘉莹107—109)。作为王国维文学批评架构的核心观念,“美术”主要用于判定“文学”以“美”为旨归的学理内涵,如他在《〈红楼梦〉评论》开篇“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的宏观立场对“文学”之审美无功利性的自觉思考。在论述逻辑上,王国维先是在“物”与“我”的关系层面,判定“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进而对“美”作出分析,指出“美之为物”可分为“优美”“壮美”和“眩惑”三种;最后通过概述“人生”与“美术”之关系,得出“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王国维,《红楼梦评论》2—5)的结论。显然,王国维是在美感经验的普遍意义上观照“美术”,其内涵不止于今天约定俗成的绘画、雕塑、建筑等视觉艺术,还包括诗歌、戏曲、小说等“文学”的子目在内,是一个整体性的知识概念。这种基于“美术”的学理范畴定义“文学”之本质的学术取向,在把“文学”归为“美术”之一种的同时,也确立起“文学”以“美”为价值内核的新观念。
最能彰显“文学”之“美”价值观念的,便是“美文”和“美术文”等术语的时兴。与“美术”的译介情况类似,“美文”这一概念在中文语境中的时兴,也是经由近代日本学者的译介及运用。明治十二年(1879年),日本纯文学理论家菊池大麓所著《修辞及华文》,借用汉语词“华文”翻译“belles-lettres”,成为“美文”观念进入日本学界的起点(裴春芳120)。随着“美文学”热潮在近代日本的兴起,“美文”也发展成为晚清学人汲取新知以改革传统文学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在晚清民初之际,继王国维评论“倍根之文”不免有几分“美文之病”(“倍根小传”212),刘师培从保存国粹的立场就“美文”观念展开了进一步探讨。②1907年,在《国粹学报》新开设的“美术篇”栏目中,刘师培发表了一系列以“美术”为名目的文论,③成为他在“文篇”栏之外耕耘“文学”之本质的第二个学术阵地。以《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一篇为例,刘师培从“书法”“词章”“画绘”“小说”等四个方面具体阐明“美术之学”与“征实之学”的区别。在他看来,“美术者,以饰观为主者也”,而“实学则以考覆为凭”,二者落实到“词章”中则有“文言”和“质言”的分轨,“文言之用,在于表象,表象之词愈众,则文病亦愈多。然尽删表象之词,则去文存质,而其文必不工。故有以寓言为文者,如《庄》《列》《楚辞》是也,而其文最美”(刘师培,“论美术与征实”101—103)。在此,刘师培是借由以“饰观”为主的“美术”,为“文言”之“美”辩护,从而确立起他以焕发中国古学精粹为旨归的“美文”观。
不应忽视的是,刘师培所论“美术”与王国维一样,都是围绕“文学”展开论说,这距五四时期狭义之“美术”内涵还有很远。“美术”在刘师培的文章中主要是为“文学”之“美”的特质立说,而“美术学”(或曰“美术之学”)是与“征实之学”(也即“实用之学”)相对的概念,二者以辩证统一的关系“寓于美术之中”。这一点,用刘师培的话来说,即是“舍实用而外固无所谓美术之学也”(刘师培,“中国美术学”128)。离开“实用之学”来谈“美术学”,或者相反,都会远离刘师培从“美术”出发探源“文学”之“美”的初衷。
另一位从“美术”的知识范畴来谈论“文学”的是鲁迅。1908年,鲁迅在《河南》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论,④同样是借“美术”阐述一种有别于传统文章之学的“纯文学”观念。这在《摩罗诗力说》中表述得很清楚,大意是“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摩罗诗力说”87)。正如刘师培的“美术学”主要是为“文学”之“美”立说一样,鲁迅所讲“纯文学”并非指向一种分类学意义上的文体类型,而主要是为了和“美术”建立起同质关系,并用后者“兴感怡悦”的本质属性来界定前者(“纯文学”)的内涵。在确立了“文学”以“美”为旨归的学术特性后,鲁迅进一步指出“文章为美术之一”(“摩罗诗力说”87)。联系晚清章太炎有意将“文”区分为“形质华美”之“彣”与“起止素绚”之“彰”两种,⑤便知其学生鲁迅将“文章”(文学)从中国传统学术及其知识系统中拆解出来,纳入“美术”这一新的知识范畴中予以定义的革命性意义。要言之,作为西学新知之一种的“美术”,成了“文学”在其内涵、外延及功能等基本学术质素上的新规定,这亦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
由此,再来看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开头提出的“何为美术”的问题,就显得意味深长。鉴于个人知识视野和独特经验的不同,在以王国维、刘师培和鲁迅为代表的晚清学人将“文学”归属于“美术”的过程中,势必出现概念的义界及实际运用上的差异。⑥而要统一这种因人而异的个性化认知状况,最有效的自然是给“美术”下定义。关于何为“美术”,鲁迅首先在词源上指出“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art or fine art)”;然后从“以美术著于世”的希腊之民的艺术出发,进一步阐明决定“美术”之产生的“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最后概括得出“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的结论。像“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这些门类,在鲁迅看来,只要符合“三要素”原则,“无问外状若何,咸得谓之美术”(“拟播布美术意见书”1—2)。在这里,鲁迅将“文章”看作“美术”的不同形态表现,显然是延续了他在《摩罗诗力说》中“文章为美术之一”的观点。
总结来看,在清末民初学人的心目中,谈论“文学”基本离不开“美术”这一新视野,这种强调“文学”之“美”的学术特性及至视其为“美术”之一种的观点已经是共识。由此,我们今天清理“美术”一词进入中国的历史时,就不能忽略它作为思想的概念工具实际参与并引发晚清学人对传统“文学”的反思性认识,以及围绕“文学”之“美”的特性展开的深刻思考。当晚清学人用“美术”这一新的知识话语思考“文学”的本质特性时,中国古代的辞章之学也就开始被想象和理解为以“美”为内核的“文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认为“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或研究范畴来讲,其实是20世纪的发明”(王德威108)。当然,这离不开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洗礼。
二、 从广义“美术”中出走的“文学”
作为独立学术门类的“文学”学科的确立,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逐步改善有密切关系。陈平原、贺昌盛和罗岗等学者都论述过肇始于晚清、成熟于“五四”的学制改革对于“文学”学科的建立起到的根本性推动作用。⑦其中,陈平原强调作为一种知识生产途径的“文学教育”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走向”。在他看来,谈论“文学革命”,无论如何绕不开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学”学科的建制问题,这是“从一代人‘文学常识’的改变,到一次‘文学革命’的诞生”的重要环节。鉴于此,他将研究的着眼点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人的“个人才华”转为“制度建设”,目的是“突出知识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以便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1—2)。陈平原从文学教育和知识生产的关系角度透视“文学革命”,意味着他用更具体的作为一种知识话语的“文学革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取代了抽象且空泛的“文学革命”是什么的追问。这样的讨论实际上是以一种更开阔,也更复杂的眼光看待“文学”及其“革命”。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单是要关注“文学”发展成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制度因素,更重要的是追问“文学”作为一种能动的知识话语是如何参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借用福柯式的语言来表述,“文学”已由一个知识概念转化为一种能动的“话语实践”(福柯236)。
要考察“文学”在晚清及至五四时期的话语实践,最便利的就是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转型视野入手。所谓“中国现代学术”是相对于传统学术而言,其最重要的表征在于学术理念、知识系统以及学科门类之间的断裂和区别。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及其知识系统主要集中在经、史、子、集“四部”框架内,也即通常所说的“四部之学”;而中国现代学术则是依照西方近代学科门类及知识体系,建构起以文、理、法、商、医、农、工为骨架的“七科之学”(左玉河2—7)。这一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轨,是在晚清西学东渐之时代潮流的影响下发端,至五四时期确立完成。用陈平原的话来说,“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6)。正是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作为知识之一种的“文学”被纳入现代教育的学术分科体系中,发展成为一门具有完整知识系统的独立学科,其标志就是“文学”从广义的“美术”中脱离出来。其中,以北京大学“文科”为主导的“文学教育”及与之相表里的“文学革命”运动,在推动现代“文学”观念的生成及其学科化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7年5月,刘半农以《我之文学改良观》积极声援胡适和陈独秀高呼的“文学革命”论,并抛出改良文学的第一个问题——“文学之界说如何乎”。文中,刘半农首先批判了当时文坛界说“文学”的两种理论: 一是“文以载道”说,认为持此论者“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二是指出“文章有饰美之意,当作彣彰”的理论仅仅抓住了“文学”的“皮相”,却丢失了其内在的“骨底”——“性灵”与“意识”(刘半农1—2)。这里,刘半农对“文以载道”说的批判,实际上接续了陈独秀的观点。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是将“文学之末运”归咎于韩愈“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革命论”137)。事实上,对于“文以载道”理论的态度,几乎成了判别“文学革命”的支持者及其反对者的显著标志。就反对者而言,最典型的便是后来在“双簧信”事件中被刘半农点名批评的林纾,其文学理论就是从古文家的“因文见道”出发,⑧而他与所代表的桐城派在“文学革命”潮流中首当其冲的深层原因也在于此。
在陈独秀这里,他揭举“文以载道”是导致“文学之末运”的根源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替从“道”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文”正名。有关“何谓文学之本义耶”,陈独秀主张“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分途,认为二者存有“美感”和“伎俩”的高下之分,只有提倡无功用、与“载道”和“有物”无关的“文学之文”,⑨才是“文学”获取独立性的关键。引人注目的是,就在陈独秀竭力提倡“文学之文”的过程中,与“美术”观念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类文体——骈散文——被划归到了“应用之文”旗下。⑩这样一来,在陈独秀以“应用”与否为“文学”划界的新标准下,刘师培等晚清学人用“美术”这一新的知识话语为六朝骈文争得的合法地位就遭到质疑,乃至被彻底排除在了“文学”之外。在此意义上,陈独秀界定的“文学之文”,虽然也是讲究“美感”,却与晚清学人借助舶来的“美术”话语为“文学”之“美”立说的价值观念截然不同。
有意味的是,刘半农的“文学之界说”是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定义出发,“分一切作物为文字(language)与文学(literature)二类”,在他看来,“文学”与“文字”的本质区别在于“精神”之有无(刘半农2)。这虽然比陈独秀以“应用”与否界定“文学”的方法更抽象,但在实际划分文类的过程中却不至于全盘否定六朝骈文的文学性,后者在白话文尚未推广之际其实最为符合纯粹美感意义上的“文学之文”。由此,我们也能理解刘半农对“彣彰”说有所保留的批评态度,他只是以“精神”之有无为标准指出了这一理论对文学内在的“性灵”与“意识”的忽视,并未一笔抹杀“文章有饰美之意”的主张。相比陈独秀以“应用”之名切断传统文学的分类体系而重构文学的知识系统,刘半农则是从“精神”这一更为抽象的说法出发探寻“文学”之本义。这或许是刘半农的主张只能称之为“文学改良”,而陈独秀的意见才是真正的“文学革命”的深意所在。
不过,“改良”也好,“革命”也罢,无法逆转的一个事实是“文学”经由五四知识分子的叩问,一方面与建基于“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彻底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又与晚清学人藉“美术”这一舶来的知识话语确立的“文学”之“美”观念保持了相当距离。通过这两方面的批判和否定,五四知识分子构建出一个以“美感”“情”“精神”等特性为主的“文学”新范畴。然而,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是,随着“文学”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美术”自身却面临着相当程度的语用困境,最显明的便是美术界有关“美术”“艺术”和“图画美术”等概念的混用,吕澂的《美术革命》指出了这一点。由此,需要进一步追问:“美术”伴随着晚清及至五四时期文学改良和革命等公共事件到底发生了怎样的知识形态的转变?
三、 “图画”如何“美术”?
如前所述,作为日源新学语的“美术”自晚清传入中国学界后,便承载着一套与“中学”截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知识系统,它被以王国维、刘师培为代表的晚清学人用来重新观照和阐释中国传统文类,“文学”的现代性发生即为一例。而日后“文学”从广义“美术”中出走乃至狭义“美术”概念范畴的生成及其学科化,尽管与晚清民初学制改革不无关系,但终究还是受制于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在中国旧学与西方新学这一对立而非统一的知识框架中的价值取向。如陈独秀对儒家“文以载道”理论的批判,以及以“美感”之有无来判定“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价值高下,这内在于其个人的西学取向与强烈的文化自我批判意识中。因此,与其说五四时期“文学”与“美术”的分离建基于自上而下的学制改革,不如说它发源于晚清至五四时期愈演愈烈的文学改良和革命等公共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它在整体上体现为一种自觉与传统文化决裂的现代性价值诉求。
就“美术”而言,它之所以在五四思想文化界再度成为中心议题,很可能是因为很长时间内它只是被视作一个纯粹外来语加以接受,自身并不成其为“问题”。只是在以胡适、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发起的文学改良和革命的公共事件中,在促使“文学”从广义“美术”范畴中迅速出走,发展成为一门具有完整知识系统的现代学科的时刻,凸显出“美术”在学理内涵和学科建制两方面的语用困境。
第一,在学理内涵上,民初鲁迅从现代美感经验的普遍意义上界定的“何为美术”在五四的文化语境中已经不再适用——也即那种“文章为美术之一”的观点需要修正,一种新的、狭义的“美术”观正在形成。用吕澂的话来说,“凡物象为美之所寄者,皆为艺术(art),其中绘画、雕塑、建筑三者,必具一定形体于空间,可别称为美术(fine art)”(“美术革命”84)。这就把纯粹外来语性质的“美术”(fine art)看作了“艺术”(art)的子目,后者作为中国古代“连接雅与俗、正与变、源与流、道与器的中间概念”(文韬36),尽管在晚清康有为、刘师培等人的著述中初步实现了与西方“艺术”概念的现代对接,但它融中西、新旧观念于一体的概念范畴其实比“美术”更为复杂。因此,当吕澂取天虹一友辩正的“艺术”概念,指出美术界“混称空间时间艺术为美术”及“至有连图画美术为言者”等“亟宜革命”(“美术革命”84—85)的事例时,不但没能继鲁迅之后进一步回答“何为美术”,反而令问题变得更复杂了。
就“美术”与“艺术”的运用关系而言,也许正因为“美术”在其内涵、外延及形式特征等方面很难归于统一,因此在那些并不需要表明价值取向和审美内涵而只需标示知识分类的学术体系内部,“艺术”一词倒显示出了某种潜在的优越性。作为中国古代的学术专有类称,“艺术”在晚清文化语境中相当于与“西政”对举的“西艺”范畴,如张元济仿照西式学科体制设置“文学”“艺术”两大学术门类,并将与西学实业相关的课程全部列入“艺术”名下。需注意的是,晚清学人在把“艺术”往“美”的方向引导时,也相当程度地保留了它与传统技艺相勾连的一面,或许这是中国近代艺术教育主要从注重实用性的“图画”开始起步的重要原因。
这就涉及第二个方面,即晚清民初艺术教育的学科建制问题。就“艺术教育”而言,虽然清政府1902年和1904年相继颁布的两个新学制——《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明令规定在中小学堂、师范以及工科和农科等实业学堂开设“图画”科目,但由于其“随意科”的性质再加上师资力量的严重欠缺,在清末学堂教育中可说是形同虚设。其情形,如姜丹书后来忆述李瑞清向晚清学部奏请开设“图画手工科”一般,“学制初创,部颁专门分科制度只有理化、史地及文科等等,而遗忘了艺术性质的学科。其实不是遗忘,乃是遗弃。推其所以遗弃的原因,实由于传统的轻视。在草订学制的衮衮诸公,以为艺术无甚用处,不屑培植专门师资,所以摈诸门外”(姜丹书109)。事实上,在晚清学部“遗弃”“艺术性质的学科”背后,有过一场是否建立“美术科”“美术专门学校”的争议,结果是采纳日本教育专家的意见,缓设具有专门性质的“美术”一科。这是中国早期艺术教育在发轫期的特异之处,它主要是作为中小学堂、师范及实业学堂的选修课程,而未能像近代日本学制那样从一开始便设立专门性质的美术学校。因此,作为中国早期艺术教育基础课程的“图画手工科”,无法与被编入晚清新学制系统的正式科目(如文学科)相提并论是可想而知的。
这一局面的根本改观,要等到民初蔡元培在全国推行“美感教育”时才正式开始。1912年2月,蔡元培拟定《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把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和“尚实”等五项,改成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的军国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和美育主义等“五主义”(蔡元培134—36)新教育宗旨。这五大主义是以辩证统一的关系寓于各门学科中,只是依着“各教科性质之不同,而各主义所占之分数,亦随之而异”(135)罢了。如“图画”一科,在蔡元培看来,尽管是以“美育”这一“主义”为主,但“其内容得包含各种主义: 如实物画之于实利主义,历史画之于德育是也”,而“其至美丽至尊严之对象,则可以得世界观”(136)。这样一来,以往在晚清学堂教育系统中无足轻重的“图画”课程就变得不可或缺,它除了以陶冶情感为目的的“美育”外,还兼有发展“实利主义”“德育”和“世界观”等其他几项教育宗旨的价值。从中,我们不难领会蔡元培实际上是用一套新的教育观念重构了“图画”的学科地位,这对于民初发展以“图画”一科为主的专门化艺术教育产生了重要的推力作用。
四、 “略逊”还是“进步”?——中国画的价值危机
既然狭义“美术”观念是在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批判过程中生成的;那么,它与中国传统绘画围绕“文人画”所建构起来的一整套批评话语体系发生抵牾甚至是冲突,就变得在所难免。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围绕中国画衰败与否展开的那场旷日持久的“中西-新旧”论争,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根源于“中西”两种不同价值体系的批评话语的抵牾与冲突。其中,以“文人画”为内核的中国画所遭遇的价值危机,与其说是抑“写意”扬“写实”的绘画本体危机,倒不如说是作为“他者”的西方美术观念已经内在于论战双方对待中国画的态度或信念中,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和批评话语的“失语”困境。
对此,不妨以徐悲鸿和陈师曾这两位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对待中国画的“态度”为例来说明。1918年5月14日,徐悲鸿在著名的“中国画改良之方法”的演讲中,提问“中国画在美术上有价值乎”(“画法研究会”)。这个在今天看来显然不成问题的“问题”,真实地折射出身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语)的五四时代的中国美术家所面临的某种话语尴尬。徐悲鸿的回答是“有”。他具体指出,“有,故足存在”(“画法研究会”),意思是中国画的“存在”可证明它“有”价值,反之亦然。但是,徐悲鸿并未循着中国画固“有”的“价值”展开论说,而是话锋一转,接着设问道:“与西方画同其价值乎?”他的回答是:“以物质之故,略逊。”(“画法研究会”)这两问两答,特别生动地显现出“中国画”在五四时期所遭遇的价值危机,以及它与“西方画”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力/知识关系。当徐悲鸿借用“西方画”的价值评判标准(如“物质”)来衡定中国画在价值上的“略逊”时,却无异于否定了中国画自身的价值。
问题在于,如果不以“西方画”为范型对“中国画”作所谓的价值诠释,那么,它自身的价值又如何体现出来呢?陈师曾的《文人画之价值》表明了一种站在“传统”与“反传统”两种文化取向之间为文人画作出价值辩护的特殊方式,相当于拾起徐悲鸿第一问的话头,在“文人画”这一更具体的题旨上接着说。在陈师曾看来,文人画的价值并不在“画”本身——即“画里的工夫”,而在于它是文人“迥出于庸众之上”的“修养品格”的集中显现(“文人画之价值”)。他把这种“修养品格”具体阐释为“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四要素(“文人画之价值”),并以此来界定文人画的价值。尽管陈师曾确实避免了用“西方画”的价值标准来简单地框定文人画,但他这一以文人的“人格”为切入点进行价值界说的立场,却是基于对西方现代主义绘画的肯定,以此重建文人画的价值体系。这在陈师曾以西方“现在新派的画”为例,来论证“文人的不求形似,正是画的进步”(“文人画的价值”5)的观点中鲜明可见。正是由于接受了近代西方宣扬艺术家主体创造精神的美学观念,陈师曾才可能跳出中国传统画学围绕形神、笔墨、雅俗等概念范畴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并重新对文人画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价值辩说。然而,这种辩说又只能在以西方现代新派美术为参照、为工具的前提下方可实现,终究还是脱离不了五四时期“中国画”与“西方画”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力/知识关系的怪圈。
无论是徐悲鸿以“物质”之说评定中国画的“略逊”,还是陈师曾用西方现代“新派的画”来佐证文人画的“进步”,二者归结起来只是一种途径,即借用西方的文艺理论方法来重新厘定中国画的价值。只不过,相比徐悲鸿意在切断文人画价值体系的中国画“改良”论,陈师曾从“人格”这一中西批评的契合点为文人画之价值张目的论说显得更为保守罢了。在这个意义上,“略逊”也好,“进步”也罢,实际折射出五四时期“中国画”在与“西方画”的不平等权力/知识关系中的“失语”困境。因为,从根本上说,中国画的“价值”只有在它自身的历史传统中才能真正寻得,但这种历史与价值的内在统一性却被“转型时代”(张灏114—20)的文化取向危机无情地撕裂了。
按照勒文森(Levenson)的观点,“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感情上的义务,对价值有一种理智上的义务,并且每个人都力求使这两种义务相一致”(勒文森3—4)。对于徐悲鸿、陈师曾及其同时代的美术家来说,他们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很难重归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想,从中获得精神上的自我再认与自我定位。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儒家的基本道德价值——以“礼”为基础的规范伦理和以“仁”为基础的德性伦理(张灏114—15)——建构起来的中国传统画学理论体系的解体,也就势所必然。一种以“西学”为范型、为工具的中国现代美术理论体系的新途,也就应运而生。
注释[Notes]
① 在思路上,这些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是纯粹语源学意义上的“美术”概念考察,即阐明这个词在近代日本的翻译及运用过程,如陈振濂:“近代中日美术观念的迁移: 关于‘美术’一词的语源考察及其他”,《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年),50—93;彭修银:“近代日本‘美术’概念形成之考证”,《日本研究论集》(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370—81;林早:“‘美术’在东方文化历史语境中的生成”,《新中国文论60年: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2009年卷》(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462—67。二是注重这个词在中国的引进史研究,如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美术研究》4(2003): 60—71;林晓照:“晚清‘美术’概念的早期输入”,《学术研究》12(2009): 93—100。三是比较学意义上的“美术”与“艺术”的综合考察,如王琢:“从‘美术’到‘艺术’——中日艺术概念的形成”,《文艺研究》7(2008): 44—49;刘悦笛:“近代中国艺术观源流考辨——兼论‘日本桥’的历史中介功能”,《文艺研究》11(2011): 25—32;林晓照:“清末新学语‘美术’与‘艺术’之差异——以王国维、严复为中心的讨论”,《美术学报》5(2012): 66—72。
② 关于刘师培与章太炎的文学论争,参见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 从晚清到“五四”》,夏晓虹,王风主编(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238—59。
③ 作为1905年创刊的《国粹学报》之主要撰稿人,刘师培的文章主要刊发在“文篇”“学篇”等栏目中。暨《国粹学报》于1907年新开设“美术篇”栏目后,刘师培在该栏相继刊发有《古今画学变迁论》《中国美术学变迁论》《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论美术援地而区》等文章。
④ 有关鲁迅与《河南》杂志的关系,参见韩爱平:“《河南》杂志与鲁迅——兼论《河南》杂志的时代意义及其影响”,《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2013): 150—56。
⑤ 关于“文章”,章太炎认为,“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推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章太炎: 《国故论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0。
⑥ 尽管王国维自身实际上对“美术”与“文学”“艺术”有着相当明晰的界别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他是以西方“无功利审美”为最高标准进行“美术”的论说。在王国维看来,“美术”系“天才之制作”,其中又以“文学”为“顶点”,这是因为“文学”在描写人生精神苦痛方面有着更大的效用,更能达成“美育”的使命。对比来看,王国维所界说的“艺术”则无此要求。参见彭修银:“王国维的‘美术’义界及其‘日本因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2017): 50—55。但是,与王国维同时代的其他学人,如刘师培、黄宾虹、鲁迅等人,并不像前者一样对“美术”“文学”“艺术”三者作出清晰的义界,反而是广狭义并用的情况更属常见,这从晚清《国粹学报》所刊发文章的用例中,即可见出。
⑦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下。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5;贺昌盛:“近代大学体制的变革与‘文学’学科的初步建构”,《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23—39;罗岗:“‘校园内外’和‘课堂上下’——论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内在关联”,《当代作家评论》4(2002): 133—40。
⑧ 林纾在《与姚叔节书》中高度肯定古文家的“因文见道”,即“古人因文以见道;匪能文即谓之知道。盖古文之境地高,言论约;不本于经述,为言弗腴;不出于阅历,其事无险”。另,林纾还在1915年作过《桐城派古文说》,在1916年出版《春觉斋论文》等文章。有关林纾与桐城派的学理关联,可参见王济民:“林纾与桐城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2007): 105—10。
⑨ 关于为何提倡以及何为“文学之学”,陈独秀在答曾毅的信中说得很清楚,称“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及正当的条件也”。曾毅、陈独秀:“通信”,《新青年》2(1917): 4—10。
⑩ 参见文韬:“散文的转换与文章的裂变——关于‘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论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09),36—43。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画法研究会纪事第十九”,《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3日第144号,第二版。
[“The 19th Chronicle of the Research Society of Painting Techniques.”DailyMagazineofPekingUniversity23 May 1918.]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年2月11日),《蔡元培全集 第2卷》,高平叔编。北京: 中华书局,1984年。134—36。
[Cai, Yuanpei. “Opinions on New Education.”CompleteWorksofCaiYuanpei. Vol.2. Ed. Gao Ping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134-36.]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独秀文存》。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3年。137。
[Chen, Duxiu. “On a Literary Revolution.”CollectedWorksofChenDuxiu.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13.137.]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
[Chen, Pingyuan. “New Education and New Literature: From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to Peking University.”LiteraryHistoryasaDisciplin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1-2.]
——: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 -.TheEstablishmentofModernChineseAcademics:CenteringonZhangTaiyanandHuSh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北京: 中华书局,1922年,刊刻本。
[Chen, Shizeng. “The Value of Literati Painting.”StudiesonChineseLiteratiPaint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22.]
——:“文人画的价值”,《绘学杂志》2(1921): 5。
[- - -. “The Value of Literati Painting.”StudiesonPainting2(1921): 5.]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Foucault, Michel.TheArchaeologyofKnowledge. Trans. Xie Qiang and Ma Yu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贺昌盛:“从‘文之学’到‘纯文学’——晚清学人的‘文学’著述及其学术取向”,《南京社会科学》1(2013): 113—18。
[He, Changsheng. “From ‘Literature’ to ‘Pure Literature’: The Literary Writings and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Schola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NanjingSocialSciences1(2013): 113-18.]
——:“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从‘词章’到‘美术’再到‘文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12(2007): 33—38。
[- - -. “The Academic Lineage of the ‘Literature’ Disciplin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Rhetoric’ to ‘Art’ to ‘Literature’.”ChinaSocialSciencesExcellence(LiteraryandArtTheory) 12(2007): 33-38.]
姜丹书:“现代中国艺术教育概观”(1940),《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109。
[Jiang, Danshu. “Overview of Modern Chinese Art Education (1940).”JiangDanshuonArtEducation.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1991.109.]
约瑟夫·阿·勒文森: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Levenson, Joseph R.LiangCh’iCh’aoandtheMindofModernChina. Trans. Liu Wei.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6.]
梁启超:“释革”,《饮冰室文集》。上海: 广益书局,1948年。123—26。
[Liang, Qichao.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volution’.”CollectedWorksfromtheIce-drinker’sStudio. Shanghai: Guangyi Book Company, 1948.123-26.]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刘半农文选》。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
[Liu, Bannong. “My Views on Literary Reform.”CollectedEssaysofLiuBanno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6.1-2.]
刘禾: 《跨语际实践: 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Liu, Lydia H.Translingual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Culture,andTranslatedModernity—China,1900-1937.Trans. Song Weijie,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刘师培:“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开明国文读本 第6册》,王伯祥编。上海: 开明书店,1933年。101—103。
[Liu, Shipei.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ne Art and Positivistic Scholarship.”TheKaimingReaderon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 Ed. Wang Boxiang. Shanghai: Kaiming Bookstore, 1933.101-03.]
——:“中国美术学变迁论”,《刘师培论学论政》,李妙根编。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128。
[- - -.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ne Art.”LiuShipeionAcademicsandPolitics. Ed. Li Miaoge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1990.128.]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 编年版 第1卷 1898—1919》。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7。
[Luxun. “On the Power of Mara Poetry.”CompleteWorksofLuxun. Vol.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4.87.]
——:“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美术论集》,张光福编注。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2。
[- - -. “Proposal for Spreading Art.”LuxunonArt. Ed. Zhang Guangfu.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1-2.]
吕澂 陈独秀:“美术革命”,《新青年》1(1919): 84—86。
[Lü, Cheng, and Chen Duxiu. “Art Revolution.”NewYouth1(1919): 84-86.]
裴春芳:“美文·美术文概念的兴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15): 119—30。
[Pei, Chunfang. “The Rise of the Concepts of Belles-lettres and Artistic Literature.”JournalofTsinghua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 4(2015): 119-30.]
王德威:“现代中国文学理念的多重缘起”,《南京社会科学》11(2011): 107—16。
[Wang, David Der-Wei. “The Multipl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oncepts.”NanjingSocialSciences11(2011): 107-16.]
王国维:“倍根小传”,《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佛雏校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212。
[Wang, Guowei. “Biographical Sketch of Francis Bacon.”WangGuowei’sUnpublishedEssaysonPhilosophyandAesthetics. Ed. Fo Chu.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1993.212.]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评论》。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2—5。
[- - -. “Overviews of Life and Fine Art.”CritiquesofA Dream of Red Mansions.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2-5.]
文韬:“雅俗与正变之间的‘艺术’范畴——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中的术语考察”,《文艺研究》1(2014): 25—38。
[Wen, Tao. “The Concept of Art amid the Dualisms of Highbrow/Lowbrow and Orthodox/Unorthodox: A Termin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ystem of Classical Chinese Academics.”Literature&ArtStudies1(2014): 25-38.]
叶嘉莹: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Ye, Jiaying.WangGuoweiandHisLiteraryCriticism.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7.]
张灏:“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张灏自选集》。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14—20。
[Zhang, Hao. “The Transitional Era’s Significance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Self-selectedWorksofZhangHao.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2.114-20.]
左玉河: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 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Zuo, Yuhe.FromtheScholarshipofFourLibrariestoThatofSevenSubjects:AcademicDivisionandtheEstablishmentofModernChineseKnowledgeSystem.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