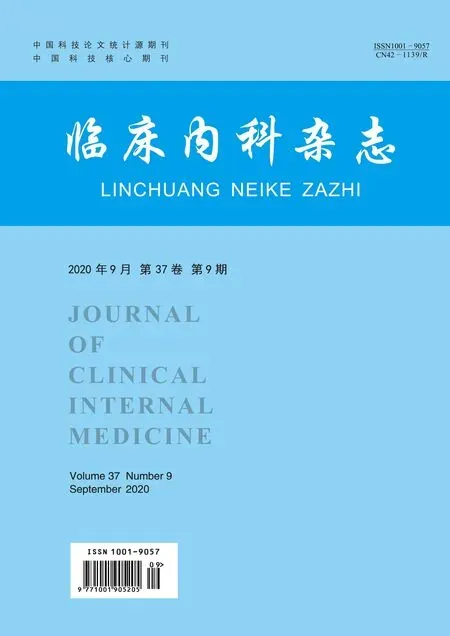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诊断腹膜后混合型淋巴结核一例
曹满菊 龙丹 高山
患者,女,28岁。因“腹痛半个月,加重1周”于2019年5月17日入院。患者半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位于上腹部,表现为阵发性隐痛,与进食、活动无明显相关,无腰背部放射痛,不伴腹胀,无恶心、呕吐、反酸、烧心、胸痛、胸闷、心悸、发热、盗汗。自服“达喜、三九胃泰”后,腹痛症状缓解不明显。1周前腹痛再次发作并加重,转为持续性胀痛,程度较前加重,偶伴头晕。为求进一步治疗,外院以“腹痛待查”转入我科。既往史:2010年有不明原因重度贫血并输血史;2013年因右踝关节骨折行内固定术;2017年行剖宫产手术;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病史,否认乙肝、结核病及结核患者接触史。入院体格检查:T 36.5 ℃,P 85次/分,R 25次/分,Bp 83/55 mmHg。神志清楚,体型消瘦。皮肤黏膜及巩膜无黄染,浅表淋巴结未触及明显肿大,心肺听诊未及明显异常,腹部平软,无压痛、反跳痛,腹部未扪及明显包块,肝脾肋下未触及,双下肢无水肿。辅助检查结果:2019年5月16日外院行肝胆脾超声提示肝左叶与胰头之间低回声病灶;上腹部MRI平扫+增强结果提示肝门区、胰头区、十二指肠间隙肿瘤性病变(4.3 cm×4.1 cm×4.7 cm),伴胃、幽门管、十二指肠球部及降部受累,腹膜后多发淋巴结肿大,多考虑为恶性肿瘤(间质瘤/孤立性纤维瘤等),双肾旋转不良。入院后初步诊断:腹腔包块待查:恶性间质瘤?患者入院后当天急查血常规结果: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1.3%,淋巴细胞百分比13.9%,中性粒细胞计数7.07×109/L;肝功能:总胆红素25.3 μmol/L,直接胆红素6.9 μmol/L,白球比值1.15;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糖链抗原199(CA199)正常。胸部X线片检查结果:左下肺感染。给予抗感染治疗(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奥硝唑)。2019年5月21日行超声内镜引导下腹膜后占位穿刺检查:超声见腹膜后巨大低回声病变,超声切面直径约54 mm,边界尚清楚,与胰腺及肝门部相邻。行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术(EUS-FNA),穿刺出少量絮条状组织和脓性物,送检细胞学和组织病理学检查。细胞学检查结果:除稀少腺上皮细胞外,见大量脓细胞和坏死物。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凝血、炎性渗出及坏死物。上述检查结果无肿瘤证据,倾向于感染或肿瘤合并感染。继续给予抗感染治疗,但患者症状无改善。2019年5月28日复查上腹部MRI平扫+增强+弥散成像(DWI)结果示:肝门部、胆囊、胃窦幽门部后上方、门静脉下方见不规则肿块影,边界尚清晰,呈稍长T1、稍长T2信号,DWI弥散成像高信号,ADC信号减低,增强扫描呈不均匀强化,内见斑点状,纤维分隔状低信号未强化影,大小约4.5 cm×4.6 cm×5.6 cm。胰腺头部与肿块部分粘连;肝门部及腹膜后多发大小不一、结节状类似信号影,DWI高信号,增强后结节状强化;肝脏体积不大,表面光整,肝裂不宽,肝内外胆管无扩张,肝实质内未见明显异常信号;胆囊不大,壁不厚,其内未见异常;胰、脾形态信号未见明显异常;腹腔未见积液。诊断:肝门部占位,间质瘤或淋巴瘤可能,肝门、腹膜后淋巴结肿大。对比外院及我院MRI检查结果提示腹膜后占位性病变较前增大。结合病史及现有检查,患者腹腔肿块性质不明,无法明确诊断。遂停用抗生素,继续给予营养支持治疗,但患者症状无缓解。经多学科会诊后,于2019年5月29日再次行EUS-FNA,穿刺出中等量条状组织和豆渣样物,送检细胞学和病理学检查。细胞学检查结果:淋巴结核(混合型),见图1。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镜下见凝血、坏死物质、上皮样细胞及多核巨细胞,见图2。2019年5月31日复查胸部CT结果:双肺纹理增强,纵隔内未见明显结构异常。追查患者无胸部结核,追问无结核病史及其家族史。患者最终诊断:腹膜后孤立性、混合型淋巴结核。遂转入襄阳市结核病防治院,开始给予规范口服抗结核治疗,观察半个月后无特殊不适办理出院。之后进行电话随访,2个月后患者腹痛症状逐渐消失,体重开始回升,现继续随访中。
讨 论
结核病是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感染性疾病,人群感染率高,肺是最常见的感染部位,感染肺外其他部位的结核统称为肺外结核。肺外结核可单发,也可与肺结核并存。在肺外结核中,淋巴系统是最常见的感染部位。Lerner等[1]的研究结果提示,人类原始淋巴管内皮细胞(hLECs)是结核分枝杆菌的潜在生态部位,结核分枝杆菌可在淋巴结中建立持续性感染。腹部淋巴结由于其丰富的淋巴群及分支,是腹部脏器结核中最常见的受累器官,主要累及腹膜后间隙第2腰椎以上区域淋巴结。一般认为腹部淋巴结核感染途径包括以下3项:(1)患者通过吞咽含有结核杆菌的痰液,细菌自破损的胃肠黏膜进入胃肠淋巴系统;(2)结核杆菌直接通过血液系统感染腹部淋巴结;(3)由腹部邻近脏器的结核感染灶直接扩散至腹部淋巴系统。本例患者表现为孤立性的腹膜后淋巴结核。
在临床表现上,腹腔内淋巴结核可出现腹痛、腹胀,多由增大的淋巴结病灶炎症刺激或挤压其他脏器所致,不一定出现典型的结核毒素症状。既往有文献报道肺结核合并腹腔内淋巴结核引起小肠扭转[2],或原发性胃结核导致幽门梗阻引起腹痛[3]。本例患者主要表现为持续性上腹部胀痛,且病程仅有半个月,无其他不适。有研究报道,腹腔、腹膜后间隙淋巴结核可并发大量乳糜腹而表现为腹胀、腹水,可能与乳糜池处炎性瘢痕阻塞淋巴管和腹腔淋巴管通透性增加使淋巴液外渗有关[4]。
在病理学上,结核杆菌感染淋巴结首先引起淋巴结增生、肿大,继而出现干酪样坏死。在本例患者中,穿刺物病理检查可见坏死物、多核巨细胞及肉芽组织增生,符合结核杆菌感染征象。腹部淋巴结核通常累及脾脏、肝脏、回盲部及腹膜,较少累及胰腺,如累及胰腺,多伴有淋巴结肿大,这时常误诊为胰腺癌并多发淋巴结侵犯。肝癌、胆囊癌及胆管癌也优先转移至肝门和门腔间隙的淋巴结,因此累及肝门部的淋巴结核更应与转移癌鉴别[5]。本例患者影像学检查虽提示病灶位于肝门部、胆囊、胃窦幽门部后上方、门静脉下方,且与胰头粘连,但并未累及毗邻脏器,而表现为孤立性。
由于腹部淋巴结核的症状、体征呈非特异性,又缺乏明确的影像学特征,易被误诊为淋巴瘤、恶性肿瘤多发并累及其他脏器、结节病等。尤其是恶性淋巴瘤,二者临床表现相似,缺乏区分二者的特异性症状和体征,对于位置较深的病变如腹膜后病变,难以获取细菌学及组织病理学资料,较易误诊。既往有病例报告报道原发性膀胱结外边缘区淋巴瘤误诊为结核性膀胱炎[6],肺上黏液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因缺乏结核感染证据,最后对肺上病灶行组织病理检查确诊为淋巴瘤[7],腹腔内肿块拟诊为肠系膜淋巴结核,最后术中病检确诊为肠系膜恶性淋巴瘤[8]。
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X线计算机体层成像(PET/CT)是目前诊断肿瘤最先进的设备,在良、恶性病灶的诊断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也可对良性淋巴结核与恶性淋巴瘤进行初步鉴别诊断。但即便是PET-CT也会出现误诊。韩骏锋等[9]收集了8例患者,行PET-CT检查均诊断为腹腔肿瘤或腹腔转移瘤,后行手术或腹腔镜经病理学检查诊断为腹腔结核。因此,术前确切的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是确诊与鉴别诊断的关键。表浅的皮下淋巴结还可通过超声、CT引导下穿刺活检,而位于腹膜后的淋巴结由于位置深,周围血管多,超声受腹壁和肠腔气体影响,CT无法探及血管而避开,因此对于腹膜后占位的穿刺病检较困难。而EUS-FNA不同于CT、体表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其可有效避免腹壁脂肪、肠腔积气等因素对图像的影响,对纵隔、腹腔、腹膜后占位及肿大淋巴结均可行穿刺活检,且受病变部位的影响较小,尤其对病变位于腹腔深处者的诊断阳性率较高。但若病变邻近重要脏器,尤其是大血管时,此时经皮体表穿刺活检的风险较高。而EUS携带有血管多普勒超声,可探及血管,从而避开血管对病灶穿刺行病理学检查,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10]。Puri等[11]对142例疑似腹腔淋巴结核的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患者均不宜行经皮穿刺或经皮穿刺失败,最终91.1%的患者成功进行了EUS-FNA并明确诊断,且所有患者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EUS-FNA常见的不良反应仅为暂时性的咽部疼痛,经对症治疗后很快缓解,表明EUS-FNA的有效诊断率较高,且创伤较小,且可多次穿刺、重复穿刺病检,进一步提高阳性率。穿刺所取组织不仅可送细胞学、组织病理学、肿瘤标记物检测,还可以涂片找抗酸杆菌及行微生物检查。病理学检查结果提示坏死组织、肉芽肿组织、干酪性肉芽肿及多核巨细胞时应考虑结核杆菌感染可能。本例患者第1次行EUS-FNA穿刺取出较多坏死组织,细胞学和病理学检查未明确诊断,考虑与结核病灶范围较大、病变中央坏死物较多相关。第2次EUS-FNA通过在病变周边穿刺取得较多组织条,最后通过细胞学和病理学检查诊断为淋巴结核。由此提示,对于较大病变,应对其中央和周边进行多点穿刺,提高阳性率。
综上所述,通过本病例,我们认识到腹膜后巨大占位虽累及多个脏器,但并不全是肿瘤性病变,还包括淋巴结核。由此进一步提高对肺外淋巴结核的认识,淋巴结核可累及多个脏器,及时行EUS-FNA可得到细胞及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进行诊断,值得临床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