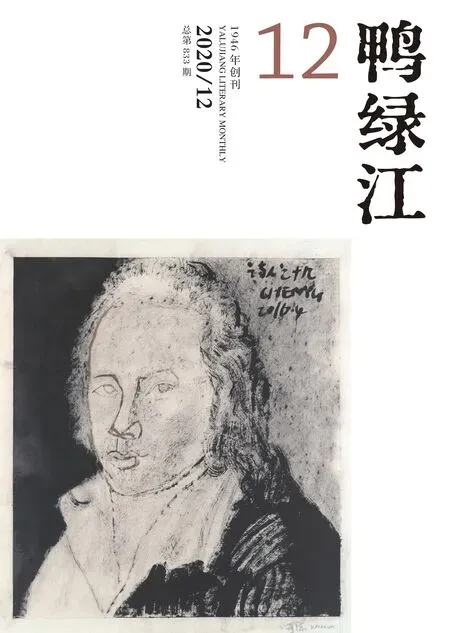屈《天问》原:关于黎幺新作的必要不充分絮语(评论)
朱 琺
我大学时代的文字学老师很有可能是位积极的网络爱好者。世纪之初,各种论坛(BBS)方兴未艾,他驰骋在校园网上,潜水,也偶尔露峥嵘,混在一群年轻人中间激扬文字,他注册的ID 叫“屈天问原”。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但一眼就把老师认了出来:且不说他发言内容悉用繁体汉字(这也深深影响了我),密度自不侔于他人,也不论其内容与语气与见识超拔于其他灌水者;就单看这用户名的四个字,仿佛是来自上古《诗经》年代的句子,即刻就有一股古雅气息扑面而来:往昔的纸背可以力透,而今荧屏一样会被人格与风格穿过去。
这种感觉,虽不中,亦不远矣:揉揉眼睛,“屈天问原”四个字虽然不见诸成语辞典,无法马上与某个固定的意思勾连起来,但很容易地就能在笔画的矩阵中看出连在一起的“天问”两个字——这不是两千多年前屈原的名作么?说屈原,屈原也就“灵皇皇兮既降”——降临了。我发觉,顿时有双重的意味结伴而来:一则,文学史上《天问》这一文本奇崛的边界是屈原所确立的,使“天问”拥有其特异形状的乃是作者屈原,而“屈天问原”四个字也完全可以作如是解;再则,与先前的辨识次序相反,却与先鸡后蛋这种普泛的创作事实相同,我在“屈原的文字”中看到了“天问”,天问乃是屈原从内部生发,而并不借以外力:谁说《天问》一定是屈原在观看了楚国宗庙壁画之后产生的一系列疑窦呢?即使涉及宗庙壁画上的题材,那必也是屈原自幼耳熟能详、牢记在心的景象,何须再次与画面面对面?各种纠结在理性与崇拜之间的诘问,萦绕在心头远非一两天的事情,久久盘旋脑海中,仰天而啸,终于俯首成咏,唾珠咳玉,成就不朽的篇章。以上两种阐发,均以古典事实扣合当下的表达,我文字学老师的化名由此可以被视为一次用典与解经,引经据典成为还原其语义奥妙的必要方式。
不过,这可能依然没有穷尽“屈天问原”的用心与效果:须知,“天问”进入四个字的符号序列之后,节奏被割裂开来了,无论句法还是篇幅,皆遭解构而重组,“天”与“问”之间形成缝隙,此中有新意,搬弄成两个并峙或接踵的动宾短语,貌似反拨了既有的终极之问,以及文字倒影中与天相对立的人的怀疑精神,却以一倍的规模承继了原有衣钵:使天屈服、弯曲垂下,或者说敬请上天(屈有“使折节”“弯曲”“敬请”等义项,参见《汉语大词典》),在(我的)追问之下供出原委,拱然呈明原理,使万物现出本相原形。正是在这个语义层面上,“屈天问原”四个字方可见出与屈原《天问》相通的心意,这个古今未见有先例陈说的崭新表述,在修辞上绵密连绵,而在气势上又超越古人。
拿到黎幺兄的新小说《天问》的时候,这件往事不由从记忆中弹跳起来,像阳光下浪里跃出的白鱼。而等到读完小说,那二十年间从未写下的三层读后感已经很不矜持,呼之即出了。说起来,当初我从文字学老师的文字奥义中感受到过的知觉,并非迟到此刻才重现,先前读黎幺的《山魈考残编》,以及收录在《纸上行舟》一册中的《柒拾贰》《机械动物志》等各篇作品时,同一种灵光早就一再被启廸,暗流反复涌动。到如今,因为《天问》这个题名,一下子把往事和我的阅读经验串联迭合成了同一个清晰却有待申说的场景,仿佛是古时候饾版拱花的套色印刷。
我觉得黎幺的《天问》无疑也可以进行类似上文的训诂,他的小说经得起探赜索隐,在句行乃至文字的层面上,逐一讨论语义及其组合关系。正如多年以前,在面对詹姆斯·乔伊斯时很多人都会油然而生的笺注冲动,作者自有理由拒绝把底牌都摊开让人一览无余,可总会有读者自甘承当起相关责任。比如,从开头“喝过早晨的第一碗羊奶,祭司顺着楼梯登上塔顶的瞭望台”一句,就很令我有打开话匣子漫说的愿望。其中若有若无的若泽·萨拉马戈与可能存在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阴影,使这个故事与比利牛斯山以南的修道院、地中海上并大西洋中都柏林里尤利西斯的航线具有相似的呼吸节奏——这因此是一个反向的巴别塔形入口,一个伪装成开头的楔子,深深探入文字世界的内部……
但问题是,依首段的比例,本文的篇幅恐怕未必能满足于揭示这一句。况且,这种烦琐解析与过度阐发或许也要先冷却二十年。倒不担心它有无效之嫌,而是因为我有一个未曾充分发挥过的看法,打算先在一个叫《博尔赫斯文献学导论》的写作计划中操练一番。我认为:小说可以依作者的食谱爱好一分为二,不存在价值评判上的高低,但应该用不同的方法论对待(此处宜有安乐椅上吃饲料的母鸡与散养啄虫食草的母鸡之比);广谱翻阅的作者与取径于生活的小说家不同,前者阅读或藏书量远超出奥尔罕·帕慕克所谓“一个作家有1500 册图书就绰绰有余”者,他们精心建筑的文本,往往会触发文献学原则伴随着文学原则双相启动,始终处在一种可称之为“比较级”的状态中,令单一学科背景的评论都顾此失彼、首鼠两端。具体来说,即需要以基于“世界文学”甚至大于文学的目录学视野来像弹格一样揭示作者的漫游轨迹,有待系谱分析与原型批评及异文比勘等方法的版本学像来魔镜一般来映现文本的变形记录,还有则是先前已经提及的细密到字词层面的训诂学精神来摸骨似的盘点修辞、分析意义。就此,我总觉得,至少是我,还没有充分准备好成为黎幺的读者;而另一方面,黎幺也一定要发表更多的作品:要是作者对相似意象与题材反复从不同面向上处理,就类似他的《猴的越狱》与《柒拾贰》那样,将为细心的读者构成类似版本校雠的特别兴味;要是有书籍规模的、篇帙更接近老普林尼《博物志》或至少是亚里士多德《动物志》的《机械动物志》暴露于世,“琳琅满目”这样的古老经验方能得以在汉语文学文本中重现——或许会是蒸汽时代的琳琅(琳琅者,美玉也),朋克风格的目录也未可知;要是这样,我想,那个倒置的通天塔形楔子会不止于一厢情愿地为论者临时安置在《天问》的开头,而能更清晰地浮现在同一系列文本的密集注脚和互参本校法中,共通的文本地宫于焉轰然打开。
当然,以“未来黎幺论”之类的名义编订一个多年以后才有可能兑现的评论计划,并不能推诿当下全部的书写责任。《天问》中自有不必延宕的若干事实,譬如,黎幺的小说略大于当下日常。他历来作品的叙事视野横跨欧亚、纵观古今,出入自然界,将不同场域对接如烹小鲜,关注“最后与最初的人”;所以,《天问》中的祭司与星相师的遭遇自然是他以往文学主题的下一块基石,将屈原《天问》在内的经典文本搬运作为本文底文也算故技重施。经验之外的书写,不必单称之为魔幻现实,也未必只是对时间与空间的深耕,古典学与超现实两相凑泊不唯是个题材问题,而首先是一种写作态度,基于面对现实有所拒绝:“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超现实因此同时是“三折画”:超越、超脱并超验于现实,也是超级的现实。现实”。而就素材及其处理方式来说,它因此或许也因为专注而小于漫漶紊乱的实况;通常意义上的情节遂不再是字句通往主题的必经之路。
阅读黎幺的文本,我觉得可以随时进入一个个微观的意义世界,他的词语始终处在博喻而博物的生态中。如果单以经典文学的阅读与评论经历来实证,那个“七宝楼台”的历史比况或许将以有为也,可我并不认为,在包括《天问》在内的作品中,黎幺笔下的句子会因其建构与独特回路而无法拈出引用。无法开拆的状况实是一种排他性效应,常见于漫过一定篇幅边界的抒情诗。黎幺十多年前就开始发表短诗,近年却基本上将小说当成了主业。他的创作轨迹并非一个诗人的跨界或改行之举,或者左圆右方的两栖作战,而是两个次元的一次会通,语言中活跃的诗性因子催化情节成为小说的框架与外骨骼,而不再如惯常那样充当作品动力的苦役,也不沦落为种种文本实验常有的能指链。隐喻的逻辑赋予了小说一个世界应有的、应有尽有的、理所当然的更斑斓的样态,也是对狭义上的世界实相不间断地怀疑与提问。它们甚至也就是真实的接口与开关,小说家制造开关并在段落中暗示了如何打开这个开关。由此,小说同时摆脱陈词意义上的抒情性与宏大性,文本主题的根本指向可以回溯到文学创世之初的“史诗”那里,但与长诗的落脚点与节奏又判然有别,我不知道该换用什么概念来命名:“诗史”显然也不妥当,需要新的词语和范式来对靶。一篇理想的小说本身,其叙事所延展的,也就是一个新的对靶范式,关于现实、关于理念,也关于既有的原型与底文。
《天问》与《天问》以及其他文献结成的,是一种新型同盟关系。文本之间的友谊也是我一向关心的领域,并谋求我笔下的文本与黎幺小说长期交好。不将人视为友谊的主体,这不是强求委婉的修辞,也不仅仅是要避免衣装的人情,或者要躲闪“抱团取暖”之讥——我所理解的称职的小说家,置身于以赛亚·柏林式的隐喻环境里,大约只会进化成狐狸与刺狸两种,我看不出其中哪一类会在凛冬将至时更容易相互靠近而忘记观察、幻想与书写。写作面向上的一致性和四维向度上的多交点是结盟最常见的前提,而作者们于是有类似通家世交的默契感,无须像街心花园里两个遛熊孩子的陌生人偶遇,要么心不在焉,要么充满警惕,圆睁各自的虎目,视线时刻牵牢自家娃儿在与球玩耍时的一颦一笑,看他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让小说的归于小说吧,这因此是特在小说的阅读与分析时有效的行动,具体到会把惺惺相惜还原成一次次折返跑:以己度人与以人度己,前者是凭借着自己的经验来开路——看他的思路,拆解文字中可能的种种埋伏,绕开一个个迷障,在小说的华容道上放眼看疑烟四起,自以为甩脱追兵扬鞭仰面大笑,再直奔题旨而去;后者则反复提示,把他的文本搬作标准与尺度来衡量我的作品又将如何是好……基于这代持的小说友谊,黎幺这篇《天问》之“原”究竟曾是什么(作者原意)与还是什么(文本效应),我突然觉得无须继续还原、屈打成招,无须还在为屈指数不过来而感到惶惑了,这就掩旗而走,带着《天问》的余声,且改且写我自己的小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