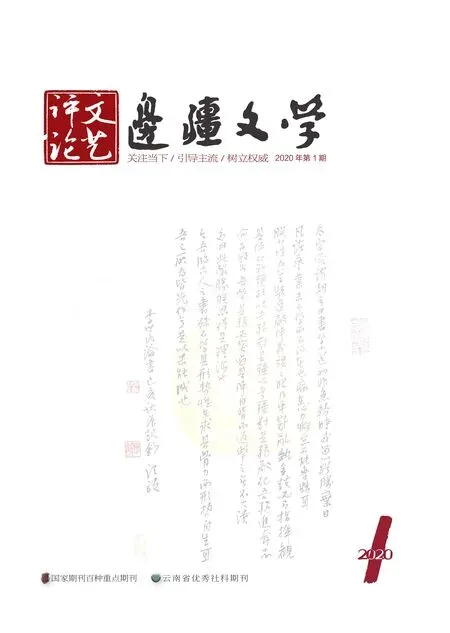董秀英:佤族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
袁智中
(作者系:佤族作家,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授)
村村寨寨打起鼓敲起锣,
阿佤人民唱新歌,
党的政策照亮阿佤山,
阿佤人民生活越来越快活。
跳呀!尽情地跳!
唱吧!放开阿佤人高亢的嗓门尽情地唱,用阿佤人的歌声,预祝阿佤山的大丰收。
啊!木鼓,让你那古老、深沉、悠远的声音响彻阿佤群山吧!
——董秀英:《木鼓声声》
1981年春,佤族作家董秀英在《滇池》文学期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木鼓声声》,敲响了佤族书面文学的第一声木鼓,终结了佤族没有书面文学的历史。从这一年春天开始,董秀英带着她“让佤族木鼓那古老、深沉、悠远的声音响彻阿佤群山”的文学理想和时代宣言,以佤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拉开了佤族“自我书写”和“自我言说”的文学序幕,佤族书面文学也由于董秀英的出现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董秀英,1949年出生于云南省澜沧县竹塘乡大塘子村一个普通的佤族家庭,在家排行第三,是五兄妹中唯一的女孩。在董秀英幼年时代,刀耕火种与狩猎采集仍是盛行于阿佤山区的一种生计模式,为了获得无处不在的精灵和鬼神的庇护,确保粮食丰产,村落祭祀与家庭祭祀总是不断循环交错。此起彼伏的人牲和家禽献祭不仅消耗着佤族社会仅有的物质财富,也让佤族社会陷入了更深的贫困与愚昧,常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成为了佤族人日常生活的写照。父母的早逝,更是将董秀英一家生活推向了绝境。虽然有着舅舅、舅妈的抚养,但董秀英童年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董秀英说,“到了七八岁,自己还没有衣服穿,赤裸着身子和男孩子们一起玩,她总幻想着,要是能从小溪里漂来一条筒裙多好,她可以立即穿在身上。”(艾克拜尔·米吉提:《佤族文学:从董秀英到聂勒》)直到解放军进驻阿佤山,在她的家乡创办了学堂,董秀英的人生才迎来了第一次转机。学堂的汉族老师不仅让她拥有了一个汉族名字“董秀英”,还教她读书、写字、懂道理。在恩师的鼓励和资助下,董秀英冲破套在佤族女性命运上的枷锁,赤着脚从偏远的佤山部落走到县城完成了初中学业,再一路向着省城昆明进发,凭着自己的坚韧倔强,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成为了佤族为数不多的第一代女性知识分子。197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的她,被分配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拉祜语播音主持和新闻编辑。这一段成长经历,民族解放与新生的喜悦,成为后来董秀英文学作品中反复被言说和展现的主题。
1980年7月,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西苑饭店隆重举行。“大力发展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积极培养、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和发展、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重要任务之一。会议决定创办全国性的文学期刊《民族文学》杂志、设立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采取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参观团访问团、举办少数民族创作班和创作读书会等措施,积极培养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文学队伍。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迎来了第一声春雷。而当时,在云南22名参会代表当中,却没有一名女作家,包括佤族在内的许多民族还没有自己的作家。正如玛拉沁夫先生指出的那样:“在这个历史重要的转折点上,被拉下一步,就会步步被拉下。如果不很快扭转少数民族文学的滞后状况,少数民族文学将很难步入主流文学的大潮中。”(吴哈斯塔娜:《玛拉沁夫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1980年9月,乘着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东风,云南作家协会召集在昆明的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座谈,著名作家彭荆风、诗人晓雪传达了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精神。虽然当时的董秀英作为佤族代表身份应邀参加了会议,但当时的她还没有发表过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已经三十年,佤族还没有自己的作家和书面文学的严酷事实,强烈激荡着她的心。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佤族知识女性,董秀英感觉到身上肩负的责任,但却不知如何去成就佤族文学的梦想。
而此时,早在1952年就作为进军阿佤山先头连成员、亲自参与阿佤山的解放和政权建立、对佤族和阿佤山有着深厚感情的彭荆风先生,也迫切希望看到佤族能够拥有自己的作家。当他看到皮肤黝黑的董秀英时,便主动向她走去,问她是佤族还是景颇族?当得知董秀英是佤族的时候,就亲切地问她:为什么不写点东西?当听到董秀英回答“想写,不敢写”时,彭荆风先生就热情鼓励她大胆拿起笔来写自己民族的生活,并承诺帮她修改。于是,时年31岁的董秀英,在彭荆风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悉心指导下,很快写出了第一篇散文作品《木鼓声声》拿来请彭荆风先生指导。正如彭荆风先生所说的那样:“虽然第一次写作,文词、结构都较稚嫩,却写得朴实、清新、有感情。我很高兴,佤族这人数不少的民族,终于出现了第一篇文学作品,这可是‘创世纪’的文学。”(彭荆风:《忆董秀英》)彭荆风先生帮助修改后,推荐在《滇池》1981年第一期发表。彭荆风先生在随文配发的《第一声木鼓》中,将之称为“阿佤文艺写作上敲响的第一声木鼓”。
1982年4月,刚刚创刊不久的《民族文学》到昆明举办滇池笔会,云南省作家协会将初出茅庐的董秀英作为佤族作家重点培养对象推荐参加了笔会。在为期一个月的创作笔会上,在时任《民族文学》责任编辑艾克拜尔·米吉提的悉心指导下,董秀英根据自己的童年经历,创作了平生第一个短篇小说《河里漂来的筒裙》,经艾克拜尔·米吉提先生修改后,发表在了《民族文学》1982年第九期上。“我坐在河埂上,河水清得见底,小白鱼摇动着尾巴自由自在地嬉戏着。以前,阿爸阿妈带着我到河边来,我拾柴,阿妈烧火煮饭,阿爸下河捞鱼摸螃蟹。我喜欢吃螃蟹的脚,阿妈螃蟹烤得黄生生的递给我,我嚼着,脆脆的,香香的。”“‘文化大革命’来了,阿爸被那些带红袖套的人斗死了,阿妈吓跑了,家里只留下我和六十岁的阿奶。阿奶做不成活,我们穷得成了叫花子。我已满七岁,还光着屁股。一些调皮的男娃娃拿泥团儿打我,用麻刷我的光屁股。”(董秀英:《河里漂来的筒裙》)就这样,董秀英携带着来自于母族自然天成、稚嫩清新的文化气息和鲜明的自传体叙事风格,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
董秀英的出现,引发了文坛的高度关注。为帮助佤族这个历史上没有文字的民族尽快培养出自己的作家,实现佤族作家“以我手写我族”“以我手写我心”的千年梦想,董秀英被送进了鲁迅文学院进修,参加了很多文学创作培训活动,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顺利当选为云南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董秀英也不负重望,在中国作协、云南省作协和众多文学前辈的扶持和提携下,以自己的坚韧、勤奋、才情和文学担当,在短短的两年间(1981-1982年),相继在《滇池》《民族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了《木鼓声声》《河里漂来的筒裙》《海拉回到阿佤山》《敬上一筒泡酒》《洁白的花》《佤山风雨夜》等6篇作品。虽然说,与生俱来的佤族文化身份和佤族部落的成长背景,使得董秀英得以以“在场者”的身份、以部落族人的审美立场,去展示佤族真实生动的历史过程和鲜为人知的民俗生活画卷。但却像大多初涉文坛的少数民族作家一样,在政治解放、“民族的新生和进步”为主题的“仿写”过程中,无声继承了新旧对比、对“落后”部族文化的批判和对解放赞颂的审美立场,使作品打上了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二元对立的时代烙印。但正如艾克拜尔·米吉提先生所感叹的那样:“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字,没有人接受过教育,何从谈起书面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由于没有本民族的书面文学传统,对于她而言,作为开创者的压力、责任与使命是何等的重大。”(艾克拜尔·米吉提:《佤族文学:从董秀英到聂勒》)作为当代佤族文学的先行者,董秀英的出现对佤族作家文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是在这短短的两年间,董秀英的短篇小说《海拉回到阿佤山》和《佤山风雨夜》,相继荣获“云南省‘民族团结’征文一等奖”和“云南省1981-1982年文学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为佤族书面文学赢得了第一份至高荣誉。
正如彝族作家黄玲指出的那样:“很多作家都是在民族文化的熏染下形成自己对世界的态度。一旦进入写作这一精神活动的空间,对母族文化的依恋和回望,会不自觉地贯穿于作品中。那是作家精神家园的根之所在,灵魂的归宿地。”(黄玲:《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董秀英经历了短暂的学习、模仿,在不断“返回民族”和“走出民族”的文化归途中,沉睡于体内的民族文化主体意识日渐觉醒。董秀英再度高扬着“让佤族木鼓那古老、深沉、悠远的声音响彻阿佤群山”的雄心和文学理想,依然决然放弃了“乡土批判”的审美立场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干扰,开始调转写作视角,立足于母族文化的审美立场,带着自第一篇作品诞生之日起就暗含着的强大母族文化烙印,以其独特的民间文学叙事风格和母族文化深刻的体验,相继在创作发表了《石磨上的缅桂花》《背阴地》《最后的微笑》《九颗牛头》等六个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自觉踏上了母语部落文化的回归之路,以一己之力支撑和推动着佤族书面文学一路向前。1991年,董秀英以《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为名结集出版了自己、也是佤族的第一本作家文学集,其中收录了她1981-1990年创作发表的12个短篇小说和1个中篇小说。1992年,董秀英创作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佤族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摄魂之地》,使佤族文学在短短的时间内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董秀英也因为自己的坚韧、勤奋、才情和文学担当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继1981-1982年荣获的两项省级文学大奖外,她的短篇小说《最后的微笑》荣获了“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优秀短篇小说奖”(1981-1984年);短篇小说《九颗牛头》荣获“首届云南文学艺术创作奖一等奖”(1991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文学集,荣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1988-1991年);长篇报告文学《姆朵秘海·天崩地烈》(后更名为《大蛇摇动的土地》)荣获“昆明新时期10年文学艺术评奖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摄魂之地》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2018年,中篇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入选“改革开放40年云南40部小说排行榜”,成为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群中一颗闪亮的明星。如同著名作家张蔓菱评价的那样:“佤族,由于有了董秀英,虽然在生产生活、交通、经济等方面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况,却突然一下子在文学上比许多兄弟民族领先,多了一位自己的丰产作家,多了若干真实细致系统地描述‘佤族’的文学文字。”(张蔓菱:《阳光照耀董秀英之路》)
文学在为董秀英和佤族文学赢得诸多荣誉的同时,也让她在不断的民族文化回望中,不断升华着自己对母族刻骨铭心的爱和责任。她在长篇小说《摄魂之地》日文译本的《自白》中这样深情地说道:“我们的佤族是一个勇敢的民族,我是用一种爱心来写这部长篇的,我爱我的民族,我写作是倾注了对本民族的全部爱。”“我是阿佤人,我爱我的故乡,当我又回到佤山的怀抱时,我感到是这样的幸福。”(董秀英:《木鼓声声》)爱有多深,责任就有多大。
1988年11月6日21时03分,董秀英的家乡澜沧县发生7.6级强烈地震,震源就在她的老家竹塘乡战马坡村地底下13公里深处。一夜之间,仅马坡村就有近300人丧生,董秀英也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三个亲人。她连夜奔赴家乡,遍访灾区,与她所爱的乡亲感同身受地震带来的创伤,饱含深情写下了那篇著名的长篇报告文学《大蛇摇动的土地》,她在文中写道:“看到他们悲凄的面孔,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泪水像雨水似的流了个不停。”为了救助那些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孤儿,养活自己收养的十来名佤族孤儿,董秀英不顾已疾病缠身的现实,决定暂时放下手中的笔,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昆明开起了“佤山饭庄”,以一己之力支撑着这个被她戏称为“吃饭合作社”的“民族大家庭”,最终积劳成疾。
1996年12月16日至20日,在中国首都北京,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这是董秀英向往已久的时刻,然而,就在赴京出席大会前夕——1996年12月7日,作为云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董秀英却因患肝癌不幸与世长辞,年仅47岁。噩耗传来,大家十分悲痛。为董秀英,也为刚刚绽放的佤族文学。为表达对为位佤族作家的敬意和深切的哀悼,会议自始至终都保留着董秀英的席位和摆放着写有她名字的水牌。
之后的数年,彭荆风、艾克拜尔·米吉提、黄尧、张蔓菱、何真等许多著名作家均为董秀英的离逝写下了饱含深情悼念文章,以不同方式表达着对这位佤族作家的深切怀念。彭荆风先生在《忆董秀英》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如果她能如常人般健康地活到古稀之年,也还有25年的长时间可写作,如能心情平静,始终不渝地严肃对待文学,当可写出许多好作品;即使天不假年,她不在开饭馆上浪费那五六年时间,也可多留下一两部作品。”在董秀英去世后的二十多年里,对于董秀英作品的研究一直在继续着。董秀英以文学的方式和民族的大爱,为自己和佤族赢得了尊严,以自己的才情和民族担当铸就了佤族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