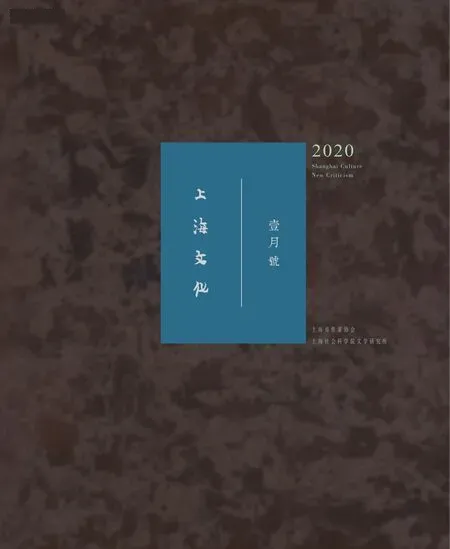现代寓言及“好人”与“牛”及“狗”之关系陈集益中短篇小说集《制造好人》读札
赵振杰
一
陈集益所言及的“批评精神”就在于此,很大程度上讲,他的小说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践行这种现代性美学
作为花城出版社策划推出的“现代性五面孔”第三辑中的一部分,《制造好人》不可避免会将读者的目光再次聚焦到“现代性”命题上来。“我的小说与现代性是否存在暗合?”这也是作者本人疑虑和关心的问题。在该书自序《土地里能长出现代性吗?》中,陈集益坦言:“现代性于我是一个经常听说但又不太清楚具体含义的词汇。因此谈论这个词我会感到心虚。……关于现代性概念的解说,我只断章取义地记住了福柯的几句阐述,即现代性是‘一种态度’,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一种‘哲学的质询’——或者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这一种批评的精神,可能这正是能被我记住的原因。”集益的创作谈向来如同他的性格那样,谦逊低调、朴实无华,却又总能一针见血,切中要害。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五副面孔》中强调,现代性应立足于三重辩证法来进行“反思性监测”——一种实践意义上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它具体表现为:首先对立于传统,即批判现代化过程中所要革除的传统弊端;其次对立于现代化,即对理性、科技、进步、未来等词语和命题的质疑与反思;最后对立于现代性自身,即对“批判的武器”进行“武器的批判”,时刻警惕现代性中任何一副面孔形成新的话语霸气。由此,文学的现代性通常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诉求,为时代变革开道呐喊,积极促成历史“断裂”和美学范式转变;另一方面,它又代表着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不断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审察和反省,始终探寻着接续和抚平历史罅隙与审美裂痕的途径与方法。
陈集益所言及的“批评精神”就在于此,很大程度上讲,他的小说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践行这种现代性美学。例如,那些以“吴村”为背景的所谓乡土小说,往往呈现出一派粗鄙、蒙昧、凋敝、荒凉的气息与景象,而代表着传统伦理秩序的“父亲”形象,也总是一副懦弱、渺小、忧郁、沮丧的模样,显而易见,“父亲”及其生活的“吴村”是没有现代性意义上的“未来”可言的,历史似乎就此“终结”了,那里只有欲望和权力催生出的混乱、疯狂、暴力与死亡(如《制造好人》以及未收录作品集的《正在消失的父亲》等);然而,对于工具理性主导下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城市文明、科技神话、经济社会、商业伦理……陈集益又时刻保持着警惕与质询,于是作者笔下的“城镇”几乎等同于失格的人间炼狱抑或是情感冷漠的人性屠宰场,人的价值与属性荡然无存,完全异化为大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机器零部件,沦为一具具受欲望驱遣、被利益支配的行尸走肉(如《特殊遭遇》、《狗》、《侍候》以及未收录作品集的《吴村野史》、《人皮鼓》等);现代性景观所带来的“眩晕”与“震惊”,迫使作者原地转向,背身前行,在“前不见古时,后不见来者”的荒蛮时代,眺望远去的故乡,追忆逝去的传统,寻觅着属于自己的心灵驿所和精神憩园,于是吴村的田亩与耕牛,金塘河畔的竹林与果园,母亲手上的老茧,父亲脸上的皱纹,老爷嘴上的旱烟……都被涂上一抹古典主义“光晕”与浪漫主义温情(如《驯牛记》、《金塘河》等),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他的小说中始终隐藏着一个微弱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而这一形象又被分散在各色人物身上,他们面对着传统秩序全面瓦解,现代价值伦理尚未形成的现实境况,进退维谷,举步维艰,“往往怀着美好的愿望出发,但走向覆亡的悲剧”。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笔下的人物时常面临着两难的绝境,难以抉择,深陷“怎么做都不行”的泥淖而又无法自拔。
二
我始终片面而执拗地认为,集益的小说普遍带有鲜明的“寓言”色彩
有评论指出,陈集益的小说创作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先锋文学痕迹的偏虚构性写作;另一类是以实写实的批判现实主义写作,简单从叙事类型上来看,这种解读具有“实事求是”的准确性,然而,就个人的主观阅读感受而言,我始终片面而执拗地认为,集益的小说普遍带有鲜明的“寓言”色彩。据本雅明的观点,“寓言”对立于古典主义的“象征”。“象征”是一种世界繁荣期的艺术形式,它对应的是一部理想的历史,表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明白晓畅”的世界,以和谐、对称、明晰、完整为标志;而“寓言”则是一种世界衰落期的艺术形式,它对应着一部理想崩溃、社会倾颓的历史,表现的是一个混乱不堪、残缺不全的社会,以忧郁、破碎、含混、多义为特征。“寓言”是艺术在衰微的、充满灾难与痛苦的现代社会“唯一的形式”。
阅读陈集益的小说,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对这种“寓言”化写作有着十分明确的艺术自觉和执着的文学追求——“我为什么就不能在乡村看到癫狂、荒诞、异化、梦魇,看到这个时代投射的阴影产生一些稍微‘现代’的思考呢?我以为乡土也好,城市也罢,写实也好,虚构也罢,仅仅是小说的主题思想和人文精神的载体,我们需要在惯常的认知上写出新的思想、新的意义”。作品集自序中的这段自信十足、霸气外露的自白,几乎等同于陈集益“寓言”写作的叙事宪章或文学宣言。
落实到具体写作实践上,小说《制造好人》可以说是一篇从内到外都散发着卡夫卡气质的“寓言”小说。“制造好人的机器真的要运到吴村了,这事让我很是紧张。”这开篇的第一句话所带来的陌生化效果,一点不亚于《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其中所携带的荒诞感、象征性以及讽刺意味被和盘托出。“好人”、“制造”、“机器”、“实验”……这些关键词不可避免地将小说的“寓言性”引向历史、政治、社会、制度、文化乃至人性的纵深处——
何为“好人”?当以阶级为纲的成分划分失效之后,“好人”的判定标准何在?道德层面上的好坏,能否通过技术层面上的不断创新来加以量化、区分?革命乌托邦废墟上悄然构建起来的科技乌托邦,是否正在以工具理性之名给人们提供新的“虚假幻象”?身份属性取代血统、成分之后,为何阶层内部的暴力与冲突反而变得愈演愈烈?……这一系列沉睡的问题都在“好人机器”被运到吴村的那一刻起,被重新激活。当经过改造的第一个试验品——傻子连桥——决心做一个“好人”时,整个吴村瞬间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与其说村民惊讶于“好人”的制造效果,毋宁说他们更加担心自己会沦为下一个“傻子”。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美国作家辛格的著名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显然,陈集益是在以“傻子寓言”的方式针对社会现实和人性本身开展共时性审视与反思:一方面是对那些本末倒置的文化政策的辛辣嘲讽,小说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在一个好人丧失生存土壤与水分的空间里,企图凭借抽象的顶层设计来重建伦理价值完全是一种虚妄,顶层设计有多完美,社会实践就有多荒唐;另一方面是对道德重建和人性救赎的坚守与期许。“好人”之“好”,在于其不计成本和代价的纯粹性,商品社会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显然不适用于此。好人的唯一衡量标准就是,当别人都视你为傻瓜时,你依旧选择做一个好人。可见,成为“好人”的路径是艰巨而孤独的,但这并非放弃的借口。一如《傻瓜吉姆佩尔》中所言:“圣书上写着,当一辈子傻瓜也比做一小时恶人强。……信仰本身是有益的,好人靠信仰活着。”
如何“制造”?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是“谁”在制造,以及要制造“谁”?据小说中交代,“制造好人其实是省里几个艺术家搞的什么行为艺术,他们要找一个地方进行这项实验。托人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我们这偏僻地儿”。抛开动机和目的不谈,制造者与被制造者之间的等级秩序已经昭然若揭。行为艺术家以一种“他者”的身份强行进入吴村,这其中既隐喻着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强悍入侵,同时也暗示了高等生命以“布道者”的姿态对低阶人群的“文明改造”。在此后的文本叙述中,这几个行为艺术家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到乡村事务中来,即便是村民械斗的高潮期,作者对这些外来者也只字未提,直到小说结尾处草草记录一笔:“那几个‘省城来的朋友’,那帮子猢狲!他们是不是真的艺术家,他们搞的是不是真的行为艺术。在我被抓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也无从打听。”显而易见,作者并非在塑造典型人物,而更多的是在建构一个类似于《1984》当中“老大哥”的意象,即一种外在的强制性干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村更像是一个动物园或是实验室,村民们只不过是供这些行为艺术家“观赏”的宠物或“解剖”的小白鼠。与其说他们是在制造“好人”,毋宁说他们是在制造混乱,并以采集科学数据为由堂而皇之地旁观灾难,消费痛苦。最后扔下几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之类的廉价嗟叹,全身而退。而这恰恰正是《制造好人》对人性之恶的另一重审视与批判。
“机器”原理与“实验”目的。陈集益在小说文本中对“好人机器”的组成部件及其运行原理进行了十分翔实的描述,这不免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另一篇小说《在流放地》,同样是“机器”,前者是用来制造“好人”的,后者是用来惩罚“坏人”的,然而给人带来的阅读体验却是出奇地相似。冰冷的铁椅、坚硬的焊钉、黑色的罩子、密密麻麻的电线、棺材一般的制造舱,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制造体验,都给读者营造出一种充满了暴力、残酷、血腥的行刑场景。血淋淋的身体暴力似乎隐喻着权力意志、等级秩序、工具理性作为一种规训与惩罚机制对人性、人心的扭曲与异化;如果说机器来到吴村,仅仅是为了一场先锋艺术实验的话,那么,抛开伦理道德等制约性因素不谈,“实验”本身所取得的效果显然是超预期的,它确乎从哲学和心理学层面上深度解剖了人性中普遍残留的“集权主义”基因以及挥之不去“平庸之恶”。作者故意将省城来的艺术家安排住在村里的大会堂里,并强调:“在大集体时期,社员们在这里吃大锅饭,开过会,观看过样板戏,那时候常有村干部在这里居留,生活做饭。现在它破败了,不过用条石垒成的大门顶上,那颗红五角星依然清晰,墙壁上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标语也没有褪去。”其用意显然是在隐晦地告诫我们,历史虽然翻过了黑暗的一页,但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并非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一去不复返。吴村后来发生的一切,无疑印证了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断言: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人性并未终结,无底线的合群,人类势必走向癫狂。
三
有理由相信,“牛”是陈集益“动物世界”中的叙事“母型”
陈集益的这部小说集中共收入六个中短篇小说,除《制造好人》外,分别还有《驯牛记》、《金塘河》、《侍候》、《狗》、《特殊遭遇》。如果一定要在它们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话,我宁愿将小说集视作一幅抽象主义绘画——《制造好人》无疑构成了整幅画的底色与背景,为其奠定了忧郁、深邃、粗犷、尖锐的总基调;而其余五篇小说则在画面上共同拼贴组合成了一头(或多头)形似于“牛”的意象。王威廉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到,动物形象是进入陈集益小说世界的其中一条路径。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我更有理由相信,“牛”是陈集益“动物世界”中的叙事“母型”。换句话讲,《制造好人》之外的五个中短篇都与“牛”存在着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联系。
《驯牛记》中就有两头牛,一头是任劳任怨、本分敬业的母牛老老麽,另一头是狂野任性、放浪不羁的小牛犊包公。前者是暴力机器制造出的趁手劳动工具,在它身上负载着“做牛耕田”的传统伦理道德与儒家纲常秩序;而后者则是拒绝规训与惩罚的鲜活生命个体,在它身上散发着“不自由,毋宁死”的本能冲动与强力意志。从寓言的角度来看,《驯牛记》中的“好牛”之于“耕作”,与《制造好人》中的“好人”之于“制造”,乃至卡夫卡《在流放地》中“坏人”之于“刑罚”,其实并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
毫无疑问,《金塘河》中的父亲俨然就是传统意义上恪尽职守的“好牛”典范。陈集益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详细讲述了一心想要脱贫致富的父亲如何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万物和个人命运作斗争的朴素而感人的故事。围栏建坝、抗洪抢险、开荒垦地、挑水抗旱、深耕细作、驱兽灭害,直至误伤人命,不得已而出让土地以作赔偿……父亲的奋斗史也是从一场失败走向另一场失败的挫折史。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海明威的名作《老人与海》——父亲的形象就如同是“老硬汉”桑提亚哥,金塘河畔贫瘠的农田就像那浩瀚无垠的大海,短暂的丰收就是那条被意志征服的大马哈鱼,而洪涝、旱灾、虫害、野兽则犹如那凶残危险的鲨鱼区别之处在于,面对失败,桑提亚哥依旧可以从容高喊:“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但无法打败他。”而陈集益笔下的父亲却“从不反驳,他总是低头盯住地,似乎他的目光能穿透脚下的地,一直看到深藏在地底的地狱”。正是这一点差别构成了两部作品根源上的不同:桑提亚哥生命意志源于作者对人性尊严的自信,并且他拥有强大的宗教信仰作为寄托和慰藉;而父亲赖以存活的信念与动力则完全出自于一个男人的家庭责任,其背后是绵延数千年的儒家伦常道德作为依托。由此,我们不妨打个比方,如果说桑提亚哥一直富有激情又充满温柔,义无反顾地奔赴彼岸精神世界的大雄狮,那么父亲则是一头勤勉执着、内敛深沉,默默无闻地负重耕耘于此在现实生活中的老黄牛。
而《侍候》当中的母亲形象则几乎就是《驯牛记》中老老麽的人格版。在《驯牛记》中,已过生育年龄的老老麽依旧冒着生命危险艰难诞下小牛犊,为农耕提供了新的劳动力,然而当它再也生不出小牛,也没有了耕田的力气时,主人还是决定将它卖给村里的屠夫,并且用它的皮做了一件坎肩和一家人的靴子。一定意义上讲,“侍候”之于母亲,就如同老老麽之于耕作一般,几乎成为她毕生的使命和义务。乡下丈夫的丧事刚过“头七”,年迈的母亲尚未抚平内心的伤痛与愧疚,儿子的电话就已经在催促她尽快返城照看孙子了。然而,儿子的窘迫,以及儿媳的刻薄,又让她感到无尽的感伤与迷茫——在这个家,她的义务就是带孩子、干活,其他的待遇连保姆都不如,这不免让她想起哥哥的话,农村人养育子女就是指望他们养老送终的,可如今像她丈夫这样死在家里无人无津的,又何其之多啊。于是,母亲陷入到情感与道德的双重困境之中难以抉择:一方面是继续寄居在儿子的家里,忍辱负重,艰难履行母亲和长辈的职责,并伴随着能力的衰退与使命的完结而独自承受起老无所依的悲剧性命运;另一方面是为了赚取养老钱,或是忍受着“苟且偷生”的道德谴责,去照料瘫痪在床的曾经仇人,或是承受着“逃避责任”的内心煎熬,在城里找个老来伴,安享晚年。小说结尾写道,母亲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决定回家,至于回家之后作何打算,作者并未给出明确交代,只有“一团充满了想吐的咸腥味水汽四处弥散,并迅速裹挟、吞没了她”。这显然既是在预示着母亲前途未卜、黯淡无光的未来命运。
《特殊遭遇》中那个制鞋学徒“我”与《驯牛记》中小牛犊包公亦存在惊人的“经验相似性”。同样鲜活的生命,被毫无预兆地抛掷到这样一个硬邦邦的世界,没有笑容,没有温存,迎接他们的是无穷无尽的鞭策、驱遣、规训与惩罚。小牛包公为了保卫自己与生俱来的桀骜天性,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遍体的伤疤、一只眼睛、一条后腿,直至整个生命;而涉世未深的“我”也在金钱与权力合谋的资本工业牢笼中吃尽了苦头——来自老板的剥削与压榨,同事的讥讽与欺凌,以及身体欲望的诱惑与折磨,使“我”从未感受到一丝一毫人的尊严和生命存在的意义。小说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讲述了“我”因观看黄色录像而欲火难耐,又通过欲火焚身而拯救自我的荒诞故事。作者结尾处写道:“可怜我终于等来工作人员的‘赦免’,……蹲在地上,我久久地干呕着。我觉得这一回为了活命,就像卖了一次淫。”精神上的耻辱感转化成生理上强烈的呕吐反应,恰恰暗示了“我”对尊严和自由的无限憧憬与渴望,而这又与小牛包公桀骜不驯、宁死不屈的动物本能遥相呼应。
在《驯牛记》的结尾处这样写道:“家里从此没有了合养的牛,……最后我们家养了一头猪。”对于农民而言,牛显然要比猪的实用价值更大,牛可以用于耕作,而猪除了逢年过节打打牙祭外,似乎别无他用。然而,与驯化耕牛所需耗费的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相比,家猪的优势在于性温顺、易饲养、适应力强。这些都是闲话。值得一问的是,作者为何要在小说最后写下这样一笔呢?这我看来,另一篇小说《狗》恰恰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前文提到,《特殊遭遇》中那个制鞋学徒像极了《驯牛记》中小牛犊包公。如果这个类比成立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狗》中的主人公“我”就是《特殊遭遇》中那个已经长大成人后的制鞋学徒,即一头被阉割、被驯服的成年包公。作者在《狗》中这样写道:“关于失意之人患上抑郁之症,我并不奇怪,可身体为何要不断地胖起来,我感觉连身体都在捉弄我——我竟莫名其妙地长成了我曾经痛恨的某些官员的模样!以至于被脂肪控制的我,脑子真的被肥油占据一般,不知不觉变得混沌、疏懒和随遇而安了。我不但迁就于新领导的丑陋、昏庸、猥琐与不可捉摸,而且放弃了平调工作的念头。不光如此,我也逐步接受了妻子的背叛,习惯下班回家只有儿子默默地陪伴我。朝这个方向说,我已经像一堵被雨淋湿的泥墙那样垮下,无声无息,匍匐在地,垮得踏实了,或者说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由此可见,面对着官僚体制、社会压力以及情感危机的多重围剿,“我”已经在四面楚歌的庸常生活中放弃抵抗,缴械投降。而莫名其妙“胖”起来的身体,无疑意味着“我”正在逐步退化为一头饱食终日、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家猪”。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狗》就像是《驯牛记》的另类续编——《狗》中的“我”与《驯牛记》结尾里出现的“猪”存在着某种相同的遗传基因,抑或说,他(它)们都是“牛”的家族变种,在寓言层面上隐喻着现代人在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同时出现了大面积的“种的退化”。
他(它)们都是“牛”的家族变种,在寓言层面上隐喻着现代人在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同时出现了大面积的“种的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