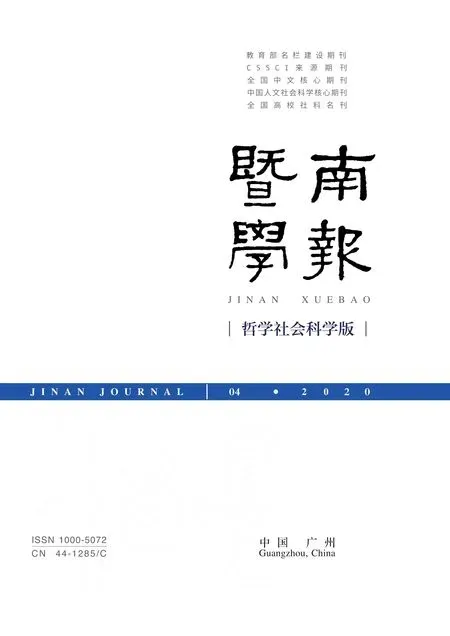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
——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
李建中
自黄侃先生1914年至1919年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作《札记》三十一篇算起,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从表面上看,近百年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似乎是被西学牵着推着甚至裹胁着:先是欧美范式,然后是苏俄范式,然后又是欧美范式……中国文论遭遇着异域范式的强制阐释,中国文论若离开异域范式就会失语,这几乎成为文学理论界的共识。但是,如果我们对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作深度考察,或许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至少不是完全如此)。
受西学的影响,清末我们有了“文学史”,“五四”之后又有了“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创时期的代表作,是郭绍虞、罗根泽和朱东润三位先生冠名为“批评史”的专著。朱自清先生写《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和《诗文评的发展》,大力推介三位先生的开山之作,说他们三人是用“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字”,“从新估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集部“诗文评”的价值,是从《总目》集部中发现了“系统的文学批评”,从而将“诗文评”这一“集部的尾巴”提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3—544页。
四库馆臣撰写总目提要时,喜欢用“平心而论”这个词。平心而论,20世纪以来批评史研究在中国本土的范式演进,并没有离开18世纪《总目》的知识谱系、理论范式和文化传统。或者这样说,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诸多范式之中,最具有原本原根、原生原创、原汁原味之辨识度的,还是源于《总目》的批评史范式。有学者指出,《总目》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一部学术批评史和学术文化史”(2)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总目》既是目录书也是批评史,是18世纪之前的学术批评史,“学术批评”包括了“文学批评”,故《总目》这部“学术批评史”理应包括事实上也包括了“文学批评史”。
说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源起于《总目》之集部诗文评,从静态(基本文献和评点方式)的层面讲是能够成立的;而从动态(范式演进和知识构型)层面论,“经史子集”作为传统的理论范式及知识形态,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何种关联?或者说,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是如何从“学出集部”走向“识通四库”的?这正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一、四库与范式
“范式”(paradigm,又可译为范型、范例或典范)这一概念,由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1922—1996)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大体上指称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所认同的符号、信念、价值和范例。之所以说“大体上”,是因为库恩对“范式”一语并没有严格的定义,乃至于有研究者从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总结出21种“范式”定义。这21种定义大致上可分为三类:形而上学范式或者元范式(metaparadigm),社会学范式(sociological paradigm),构造范式(construct paradigm)或者人工范式(artifact paradigm)。(3)参见[美]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范式的本质》,[美]伊雷姆·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编,周寄中译:《批评与知识的增长》,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7—84页。而在库恩关于“范式”的诸多定义之中,有两条值得注意:一是“范式”这个词,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最先出现时,是指某一学科的经典著作,比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和牛顿的《原理》和《光学》等;(4)[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二是库恩认为当科学家“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透试问题的多个部分”时,新的范式就诞生了,(5)[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03—104页。因而“范式”也是一种看问题的方式,“一种新的观察方法”,一种“看的方式”。(6)[美]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范式的本质》,[美]伊雷姆·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编,周寄中译:《批评与知识的增长》,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3、97页。众所周知,《总目》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经典,或者说是文献学的经典范式;当我们用《总目》这一“看的方式”重新审视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时,便在“元范式”的语境下,同时获得了“社会学范式”和“构造范式”:前者可标举为“中国范式”,后者可构建为“经学范式”“史学范式”“子学范式”和“集部诗文评范式”。
中国图书分类,从西汉刘歆《七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之六分,到西晋荀勖《中经新簿》“甲、乙、丙、丁”之四分,再到初唐官修《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之四部,直到18世纪乾隆年间《四库全书》之集大成,形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知识谱系系和学术传统。采用经史子集分部编纂的《四库全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总目》,堪称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大,体制最为完善,编制最为出色的知识分类与汇纂成果。《总目》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诞生,是《四库全书》的解题目录。《总目》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分法分为4大部,“部”下分“类”,“类”下分“目”,4部共44类、65目。部前有“总叙”,类前有“类叙”,目后附“案语”,依次评骘四库所著录或存目的一万多种古籍。四库与范式的内在关联,除了前面谈到的《总目》为百年批评史研究提供了“经典范例”和“观察方式”,而在文学理论范式之中西比较的层面论,《总目》的知识形态、话语行为和评点形式,于文化根柢处铸成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内在结构和民族特色。
文学理论是对文学阅读经验的反思,在反思过程中将其概念化、逻辑化、系统化,从而形成一种知识体系。在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构成中,依据什么原则、设置什么标准、按照什么路径来阐释阅读经验,是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在构造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西方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是作为单一主体并依据形而上学的各种原则来阐释阅读经验,从而形成具有西方思想特征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这种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优势在于,它往往是纯粹个人化的话语,指向形式化的、普遍化的理论模型,具有较大的阐释有效性和较高的创新意识,但其弊端是容易陷入独断论,并常常走向虚无主义,这也是西方文学理论知识构型的困境。
四库对中国文学理论范式的深度影响,同时在四个维度立体展开。集部诗文评是个体阅读经验的展示,但它们被置于经学知识形态、史学知识形态以及子学知识形态三维坐标的交叉之中,分别对应于思想、历史、文化。也就是说,个体阅读经验在思想的交织中、在历史发展的序列中、在多元文化的并置中展开。由于三种知识形态蕴含着三种话语主体或者说阐释主体,这样就形成了三种阐释主体或话语主体的交互阐释,对个体阅读经验的理论总结也就内在于思想、历史、文化的混合性之中,也被限定于这种交互阐释的有效性之中。在这种交互阐释中所形成的知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虽然没有达到形而上学的普遍化,也难以形成单一阐释主体的阐释的创新性,但使得中国文学理论处于对话性状态,避免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也避免了可能的独断论。这也就是由经、史、子、集所建构的多重主体交互阐释所形成的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特性和功能,能够有效避开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所遭遇的现代性困境,为中国文学理论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新的思路。
用《总目》这一经典“范例”来重“看”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范式演进,不难发现文学理论中国范式是植根于中华文明,运用汉字与汉语表述,内生于中国文学批评实践,总结中国经验而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整套文学理论观念、研究方法和知识话语。相较于欧美、苏俄等“西方范式”,“文学理论中国范式”之“中国”,既是中西比较下亟须彰显主体的相对之“中国”,又是古今传承中有待发扬传统的故有之“中国”,更是当前文学理论范式转换中有效应对危机的必要之“中国”。《总目》所包含的经学之思想语境、史学之历史观照、子学之文化视野、诗文评之个人阅读经验,共同构成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范式演进的四种理论维度、四种典型“范例”和四种“看”的方式。探讨四库与范式的关系,探讨《总目》与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之范式演进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要揭示文学理论中国范式“以经学为根本,以史学为源流,以子学为视野,以诗文评为方法”的总体特征。
二、学出集部
《总目》的文献学和思想文化史价值自不待言(有学者拿它与同为18世纪的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相比较);其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价值亦愈来愈引起学界关注。就“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名”是舶来的(即朱自清所言“‘文学批评’是一个译名”(7)《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3页。),其“实”却是原生原创、自本自根的:是从《总目》集部的“诗文评”之中生长出来的。《总目》集部的“诗文评类叙”,或可读为最早的也是最简的“批评史”: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颁《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世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章。《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8)(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9页。
《总目》集部“诗文评类叙”的这段文字,不仅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简中国文学批评史”,而且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范式”的最早概括和总结。
作为“最早最简之批评史”,诗文评类叙精练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的演变脉络:从两汉“文成法立”到魏晋“文论初出”,从刘勰、钟嵘“勒为一书”到中山、六一“体兼说部”,从宋人“务求深解”到明人“喜作高论”……历朝历代的文学批评,其路径是“考证旧闻,触发新章”,其方法是“讨论瑕瑜,别载真伪”,其目的是“博参广考,有裨文章”。不足300字的“诗文评类叙”,书写出两千多年的“批评史”,何其难哉,又何其妙哉。
作为对“批评史范式”的最早概括和总结,《总目》集部的“诗文评类叙”列举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具代表性的五种范例或范式:一是究源流、评工拙的刘勰式,二是第甲乙、溯师承的钟嵘式,三是备陈法律的皎然式,四是旁采故实的孟棨式,五是体兼说部的诗话式。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范式(或曰典范、模型或范例)之分类与命名,因其语境或层级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表述;而从言说方式及批评文体的层面而论,“诗文评类叙”的范式界说是颇为精当颇有价值的。
正是从《总目》集部诗文评这篇不足300字的“类叙”出发,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走上自己“范式演变”的历程: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这里“学出集部”中的“学”,是指20世纪创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门新的学科,是“学科”之“学”。而“识通四库”中的“识”,是指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学术知识和理论见识,是“知识”和“见识”之“识”。如果说“学出集部”是追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根源,而“识通四库”则是标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知识构型和理论内涵:两者共同铸成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
上引《总目》集部“诗文评类叙”所言“五例”及“简史”,分别为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提供了“批评”和“史”两大层面的范式或范例。而我们说“学出集部”,不仅仅是指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批评范式”和“述史范式”出自《总目》集部之“诗文评类叙”;在一个更为弘阔的层面或领域而言,“文学批评”所研究的对象(文学文本)和“批评史”所研究的对象(文论文本)也是出自集部:既包括集部五大类所收录或存目的海量文献,也包括《总目》集部的诸多提要和案语。
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曰:“《汉志》之《诗赋略》,即后世之集部也。……《诗赋略》所录五种百六家之文,大半皆别集矣。……当时无‘集’之名,而有‘集’之实。”(9)张舜徽:《张舜徽集·旧学辑存》(下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2008年版,第1085页。四库集部之五大类,一首(楚辞类)一尾(词曲类)自然是狭义的文学,诗文评类又是狭义的文论,而中间的别集类和总集类则既有文学文本也有文论文本。其实,早期的文献分类,并无“文学”与“文论”之别,如《隋书·经籍志》,集部仅分三类:楚辞、别集和总集,尚无诗文评,作为“文论文本”的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附列在集部的总集之中。到宋代王尧臣等编纂《崇文书目》,在集部列了“文史类”来安放文论一类的书籍。南宋郑樵《通志》分为“文史”与“诗评”两类,明代焦闳《国史经籍志》又合为“诗文评类”,四库从之。《总目》的集部诗文评,著录各体文论著作64部,731卷;存目85部,524卷。
《总目》“集部总叙”对集部五大类有一个提纲絜领式的总括:一是“楚辞最古”,二是“别集最杂”,三是“总集之作,多由论定”,四是“诗文评之作,著于齐梁”,五是词曲类“闰余”,“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在评鸷总集优劣时,《总目》“集部总叙”指出:
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岿然而独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10)(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67页。
《总目》“别集类叙”在依次评点了江淹、梁武帝、梁元帝、谢眺、沈约等人的别集之后,也有一个总括式议论:
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其余可传可不传者,则系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异也。(11)(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71页。
《总目》集部提要反复强调的“公论”,实乃文学批评史发展演变之规律,亦为文学作品和文论著作经典化之规律。就后者而论,即如“集部总叙”所言,须“翦刈卮言,别裁伪体”, 则“典册高文,清辞丽句”方能“高标独秀,挺出邓林”。四库馆臣对集部乃至四部典籍所做的汰选,在精心研读的基础上所精心撰写的提要,其价值和意义就是文化批评史层面的经典化。四库的这一文化传统及书写方式,为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所继承。而正是这一点,突显出文学批评史“学出集部”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文学批评史研究,既要通变乎时序、体要乎公论,亦要知人论世、得其用心。“学出集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从《总目》集部的提要之中,既能得其“公论”,亦可察其“公案”。南朝文学批评,刘勰、钟嵘二人与沈约的关系,既是文人恩怨,亦为文坛公案。《总目》“集部总叙”曰:
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钟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12)(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67页。
从文学批评史的层面论,透过刘勰、钟嵘与沈约的“词场恩怨”,不仅可以梳理南朝“声律说”的创生、阐释、传播和接受,还可以体察寒门学人的心态之微妙以及这种心态对文学批评的制约甚至扭曲。关于“亘古如斯”之“词场恩怨”对于文学接受和传播的复杂影响,还可以举出《总目》“集部总叙”所提及的宋僧惠洪《冷斋夜话》之攀附黄庭坚,宋叶梦德《石林诗话》之阴抑元祐诸家等。由此又可见,《总目》所做的工作,其实也是文学批评史所做的工作。
毋庸讳言,在20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草创期,学界虽然看到了“学出集部”的事实,但对此并未重视,而是更重视“西方观念”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影响,其“重视”之中又包含着几许“忧患”。朱自清先生说:
“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13)《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1页。
朱自清先生的这篇文章写于1934年,文中所预言的“将来”就是我们的“当下”。抚今追昔,不得不感慨朱自清先生直面现实趋势时的远见、忧患和预警。80多年过去了,“以西方观念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这一当年“学术界的趋势”,早已演变成当今学术界“不可避免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为20世纪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从18世纪一部目录学经典中找到自己的本根和本源,这对于扭转“以西方观念选择中国问题”的趋势,从而走出“以西释中”并“以中证西”的百年困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识通四库
朱自清在评介郭绍虞先生的批评史著作时,强调“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无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系统来”(14)《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39—540页。,而在评介罗根泽先生的批评史著作时又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各条,从一个方面,也不失为系统的文学批评,这里纪昀的意见为多”(15)《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页。,并称纪昀为“第一个有文学批评史自觉的”(16)《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53页。。朱自清还指出罗根泽批评史著作中不仅有大量的四库集部的文献,还注意到了“古经中的辞令”并“叙述史学家的文论”。朱自清在谈到四库集部文献与批评史的关系时还指出:“这一类书里也不尽是文学批评的材料;有些是文学史史料,有些是文学方法论。反过来说,别类书里倒蕴藏着不少的文学批评的材料,如诗文集、笔记、史书等。”(17)《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39页。朱自清这里所说的“别类书”,既包括集部,也包括集部之外的文籍如史部、子部等。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草创期,朱自清既看到这一学科“学出集部”的文献学渊源,亦看到这一学科“识通四库”的批评史事实。
正如文献的四部分类并非始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及《总目》,而批评史的“识通四库”也并非始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如果我们用“四库”泛指汉语文献的“四分法”(即“经史子集”之四部),则可以说,自从有了“文学批评”,也就有了文学批评的“识通四库(部)”。《诗经》既是儒家五经之一,又是狭义的或纯粹的文学作品。同样的道理,《毛诗序》既是经学,又是诗学,是故先秦两汉文学批评与经学相通。《史记》是史学,而其中标举“发愤著书”的《太史公自序》以及诸多的文学家列传则是文学批评。同样的道理,《汉书》里面也有大量的文学批评,是故两汉文学批评与史学相通。诸子之学,从先秦的儒墨道法,到两汉的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到魏晋南北朝的葛洪、刘昼、颜之推等,更是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实践。集部既是文学批评的对象,又是文学批评本身,就后者而论,集部中有选本批评、评点批评、文体批评和以注为论等等。当然,中国文学论“识通四库”的历史事实,是在百年批评史的演进过程中逐渐为人们所认知的。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将“识通四库”这一文献和学术的事实理论化、系统化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从总体上看,刘勰文论系统中的“经史子集”并非并列或同等。“经”是刘勰文论的“枢纽”和“纲领”,所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经,既是文之“魂”:“性灵熔匠,文章奥府”、“入神致用”;又是文之“原”:“渊哉铄乎,群言之祖”、“根柢槃深”。落实到五经,则依次为“《易》统其首”、“《书》发其源”、“《诗》言其本”、“《礼》总其端”和“《春秋》为根”,“所以百家腾越,终入环内者也”(《宗经》)。刘勰从《尚书》中找到“体要”这个关键词,其《征圣》篇四次提到“体要”,而刘勰文论所“体”之“要”无疑就是“经”。“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征圣》篇讲“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宗经》篇讲“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可见在刘勰看来,能否征圣宗经,实乃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成败之关键。
“长怀序志,以驭群篇”的《文心雕龙·序志》篇,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四项基本原则”:
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
“原始以表末”显然是“史”的路径和方法,也就是刘勰反复强调的“观澜而溯源,振叶以寻根”,“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这里的“根”和“源”还有“先哲之诰”无疑是“经”,可见刘勰文论的“史”也是以“经”为本源,以“经”为纲纪的。“选文以定篇”又显然是“集”的路径和方法,无论是楚辞、词曲还是别集、总集,都是“选文定篇”的结果。而“释名以章义”和“敷理以举统”则既有“子”的元素又有“经”的内核,或者说是在经学统驭之下的子学。训释物名是小学的功夫,而撮举大统则是经学的宗旨;由释名而彰义,由敷理而举统,则是《总目》“子部总叙”所言“博明万事,适辨一理”。在刘勰的四项原则之中,我们看到中国文论最早的“识通四库(部)”,从而为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识通四库”找到了历史缘由和经典依据。
让我们重新回到《总目》集部的“诗文评类叙”。平心而论,“诗文评类叙”的“五例”之中,先在地包含了“四部”。刘勰式的“究源流”,“源”在何处?“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文心雕龙·征圣》篇),刘勰的理论范式,最为根本最为核心的是“经学范式”。如果说,钟嵘的“溯师承”、“第甲乙”和孟棨的“旁采故实”、皎然的“备陈法律”,大体上属于“史学范式”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那么,刘颁《中山诗话》和欧阳修《六一诗话》的“体兼说部”,则显然是“子学范式”的“博明万事,适辨一理”。《总目》自身对集部诸多“诗文”的“评”,乃至于对四部所著录、存目的万余种典籍的“评”,无疑是“诗文评范式”的“讨论瑕瑜,别裁真伪”。
20世纪初,当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山大师们将《总目》集部的“诗文评”升格为“批评史”时,其“学出集部”之中,已经先在地准备或预设了“识通四库”的可能,因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百年演变中,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是《总目》“诗文评叙类”所标举的古典言说方式即传统批评文体的“五例”,逐渐演变为既原汁原味又与西学互鉴互证的兼有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之双重性质的“四式”:经学范式、史学范式、子学范式和集部诗文评范式。百年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演进,既是“西学范式”的影响史,也是“中国范式”的演进史——后者即可表述为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识通四库”,其经、史、子和集部诗文评这四种范式并不在同一个层面,借用《文心雕龙·宗经》篇的话说:经是“根柢槃深”,史、子和集部诗文评则是“枝叶峻茂”。经学范式是根本,是纲纪;史、子和集部诗文评范式是衍生,是羽翼。经学范式作为根柢是双重意义上的:思想与方法。前者是刘勰所说的“太山遍雨,河润千里”;后者则是戴震所说的“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即从“小学”(文字学)经由“经学阐释学”再到对文论关键词的释义与诠解。经学范式的方法论意义,是关注“字”“词”“道”之关系,由“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条路径,衍生出诸如文以载道、通经致用、以意逆志、立象尽意、深究诂训、精研义理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方法。
如前所述,从“经学范式”这一根本或枢纽出发,若“原始以表末”则有“史学范式”, 若“释名以章义”、“敷理以举统”则有“子学范式”,若“选文以定篇”则有“集部诗文评范式”。这三种范式分别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历史主义范式”、“文化研究范式”和“审美范式”及“形式主义范式”构成互释互证、互参互渗。就“史学范式”而言,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从20世纪初的开创到21世纪初的繁荣,其标志性成果均为“批评史”论著:开创期是郭绍虞、罗根泽和朱东润三位学者的批评史。繁荣期则是以“复旦七卷本”为代表的各种版本的批评史。不同体量、体例、路径和风格的批评史,自觉引入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和精神史的史识、史观和史法,力图在民族文化、民族心灵和民族精神的层面揭示中国文论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粹。
《总目》“子部总叙”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18)(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9页。子学“博明万事,适辨一理”,既融通百家之义,又自立一家之言。笔者曾尝试以子学的眼光和方法开拓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揭示儒道释文化的诗性精神如何孳乳出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儒家文化“比德”的人格诉求和“比兴”的话语方式铸成中国文论理论形态的人格化和理论范畴的经验归纳性质,道家文化的“道法自然”和“得意忘言”酿成中国文论言说方式的诗意性和审美性,印度佛教对世界的想象和中国禅宗对语言的超越又为中国文论提供了理路与诗径相统一的可能。视野弘阔与思想争鸣,兼收并蓄与新见独标,是批评史研究子学范式之优长。
比照现代学术分类,四部中羽翼经学的史、子、集三部,史学和子学分别与历史学和哲学相通,而集部之学则与文学相通。《总目》集部五大类皆为广义的文学文本和批评文本已如前述,而《总目》集部之目录提要就是具体的文学批评:集部不仅有“诗文评类”,集部提要大多为“诗文”之“评”。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对古代文论及文化的通变,不仅继承了“文以载道、通经致用”的经学传统,而且赓续了子、史、集之“史论评相结合”的具体批评的传统。后者使得中国文论在借鉴“西方范式”的同时,对失焦于“文学”、 以“理论”自身为目的的倾向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从而远离“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之窠臼,远离“理论生成理论”之陷阱。
探寻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范式演进,在借鉴西学范式的同时,要发掘中国资源,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归纳中国范式。正是在这一点上,《总目》为“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研究,不仅筑构了扎实的目录学和文献学基础,而且提供了精湛厚重的理念、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堪称经典的范例。现有研究对“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概括,或是深受西方中心主义与“冲击—回应”说的影响,以“中国范式”为“西方范式”的异域案例;或是陷入民族主义思维,过于强调中西范式之间的对立,从而缺少对话意识,均未能充分彰显“中国范式”的主体性、本土化或曰中国特色之所在。拙文以“范式”为视角,以“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为论域,以“经史子集”为焦点,以“中国范式”为主体,以“文学理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为目标,将内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学、史学、子学和集部诗文评知识形态与当下主导学术话语的社会政治、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和审美及形式主义等西方范式互鉴互证,从而在“文学理论”这一特定领域彰显“中国范式”的文化底蕴、学术智慧、思想魅力、理论资源与话语形态,通过与“西方范式”的互补互动,实现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重构,既重塑三千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灵魂和体貌,亦重建21世纪中国文论的知识图谱与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