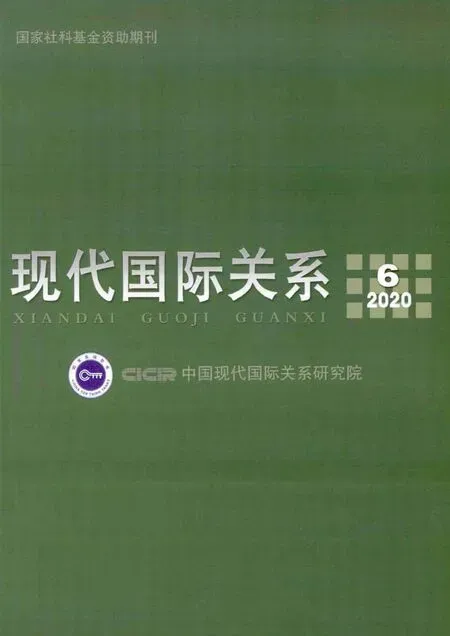全球公共卫生难题及其治理路径
杨 娜
[内容提要] 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促使公共卫生问题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当前全球公共卫生面临多元治理主体权责不明、卫生公共品供需失衡、医疗技术与疾病信息的获取存在能力鸿沟和共享壁垒等难题。导致全球公共卫生难题产生的原因有,全球卫生治理与国家卫生治理的优先议程不同、“安全型”与“发展型”卫生治理模式有差异、单边和多边的治理途径有别以及逐利与公益之间难找契合点。可从多层级卫生治理主体的协调与整合、多个治理环节紧密衔接、加强卫生领域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总结地区治理经验等方面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作为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为此不断提高本国的卫生治理能力,注重综合运用资源和技术等多种支持途径、提供体现地方差异和高融合度的卫生公共品,并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新规则和新标准的制定。
截至2020年6月中旬,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约800万,死亡病例超43万。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继意大利、英国、美国新冠疫情大暴发后,近期全球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最多的十个国家约一半在中南美洲,美洲确诊病例占全球确诊人数近半。(1)WHO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Dashboar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June 15, 2020.WHO的调查报告指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受到极大影响,接受调查的155个国家中,53%的国家部分或完全中断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治疗,94%的国家中从事非传染性疾病治疗的卫生人员部分或全部抽调支持新冠肺炎病人救治工作。(2)COVID-19 Significantly Impacts Health Services for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June 1, 2020.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与全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息息相关,公共卫生问题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疾病本身的危害性、卫生公共品的供需失衡以及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调困难,使得个别和少数国家的突发疫情迅速扩散为全球性问题。非典、禽流感、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的扩散,不仅威胁全人类的生命安全,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国际社会亟待加强公共卫生治理特别是对传染性疾病的共同防治。
一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现代交通愈加便利、人员跨境流动频繁,与城市化、工业化、环境污染等问题并存,促使传染性疾病越来越多地突破国家边界而大范围传播。(3)Kelley Lee, “An Overview of Global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in Parsons and Lister (eds.), Global Health: A Local Issue, The Nuffield Trust, 2000, pp.34-46.传染病的全球流行,严重危害人的健康,影响正常生产秩序,造成地区乃至全球的不稳定局面。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陷入困境,面临诸多难题。
首先,多种全球性问题复杂交织,致使传染性疾病的防控难度加大。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将包括传染病和慢性病在内的公共卫生问题列为影响最大的全球风险之一。(4)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18, Geneva, 2018.自20世纪70年代起,传染病以每年新增一种或多种的空前速度出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暴发流行性传染病,仅几小时后就蔓延至其他国家和地区。(5)程春华、杨久华:“未来中长期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发展趋势及其国际政治影响”,《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21页。截至2019年底,全球检测到的传染病有61种,涉及70个国家和地区。(6)韩辉等:“2019年1月全球传染病疫情概要”,《病毒监测》,2019年第12期,第1045页。新冠肺炎始发于2019年底,目前200多个国家已有确诊病例。至2020年6月中旬,中国确诊人数8余万,美国超200万,巴西逾86万。全球化极大地缩小了时间和空间距离,人员快速自由流动致使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速度惊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各国均采取封锁边境的暂时性措施,国家间经贸往来随之受到较大影响。全球化疫情致使全球经济遭受重挫,一些国家陷入经济困境,使其本就捉襟见肘的抗疫资源难以为继,疫情风险持续攀升。此外,全球化引发的其他问题恐加剧公共卫生危机。例如,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难题,它“导致许多病毒对温度和湿度高度敏感,微生物世界因其生存环境改变而演变着它们的毒性、传播方式和耐药力”(7)程春华、杨久华:“未来中长期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发展趋势及其国际政治影响”,《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29页。,人类对传染病防控的难度更大了。全球经济衰退、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人类活动范围的全球扩展,使得传染性疾病防控的紧迫性凸显,时刻考验着国家乃至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应对能力。
其次,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主体愈加多元,因权责不明、协调不力导致治理效率低下。主权国家仍是公共卫生的治理主体,政府可通过迅速调动全国医疗资源防止疾病蔓延,但各国国内卫生治理水平参差不齐难以确保应对重大疫情时步调一致。近年来,专业性国际及地区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团体逐渐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新主体。WHO是全球卫生治理的核心机构,是独立的卫生领域专业权威。(8)Richard Dodgson, Kelley Lee and Nick Drager,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A Conceptual Review, Department of Health & Development, WHO, 2002, p.21.各国疫情信息通报制度的形成、重大疫情全球警报系统(GOARN)的建立与全球旅游警告的发布树立了WHO在全球卫生危机中的权威地位。(9)张彩霞:“传染病问题的全球治理机制及其完善”,《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2年第1期,第63页。然而,当紧急卫生事件发生时,WHO的执行力常遭受诟病。如,非洲埃博拉疫情暴发后,WHO就因内部管理松散造成应对行动迟缓而遭遇信任危机。无国界医生、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非政府组织建立起来,在特定疾病治疗、药物研发、资金资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全球卫生领域的治理主体多元且各有所长,却因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造成职能重复或重叠,致使原本紧缺的资金和人才分散而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再次,卫生公共产品的供需失衡状况日渐突出。一些贫困的主权国家无法向本国国民提供卫生公共产品,导致传染病肆虐,此类公共劣品的负外部性具有了全球维度。(10)晋继勇:《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机制分析》,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4页。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治理颇具紧迫性。公共卫生属全球公益治理领域,其治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能否以及如何在公共卫生领域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核心”。(11)Richard Smith and Robert Beaglehole, Global Public Goods for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5-27.公共产品供给国结合自身的国家实力和“投入—收益”比例等现实决定公共产品的规模、去向和提供方式。全球卫生治理公共产品主要包括维系各种疾病防控和监测系统的资金、病毒研究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医护人力资源等。当前,卫生公共产品呈现出供需失衡的状况。虽说“一国对公共卫生安全的享有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享有,各国间是互惠互利而非竞争关系”(12)敖双红、孙婵:“‘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研究”,《法学论坛》,2019年第3期,第152页。,但有能力且有意愿持续不断地提供卫生公共产品的国家较少,还要考虑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难以避免某些国家的搭便车行为。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供应过于分散和供需常有不符导致卫生领域的合作难以达成或执行不力,卫生公共产品的全球供给恐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
最后,医疗技术与疾病信息的获取存在能力鸿沟和共享壁垒。鉴于疾病本身的特性及其传播途径的不确定,全球卫生治理既包括通报、警示、信息共享等初级治理形式,也包含病原体和药品价格共享、实验室研发等高级合作方式。(13)张彩霞:“传染病问题的全球治理机制及其完善”,《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2年第1期,第63页。然而,当前疾病及卫生信息数据体系并不完备,不利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如高结核病发生率国家中只有不到1/5有完善的生命登记系统,疟疾流行国家仅有过半国家提交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数据。(14)RifatAtun, “Time for a Revolution in Reporting of Global Health Data,”Lancet,Volume 384, 2014,pp.937-938.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拒绝将本国的疫情信息与他国或国际组织共享。如2008年,印尼顾虑到禽流感疫情可能造成国家形象受损的不利影响,且担心制药公司利用印尼病毒样本研发高价疫苗,拒绝同WHO分享禽流感病毒样本,要求制订疫苗售价顶限。(15)“印尼卫生部长:为改善国家形象 印尼不再发布禽流感死讯”,《联合早报》,2008年6月6日。在医疗资源获取方面,“出于保护相关行业利益的考虑,西方国家着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无疑加大了疫苗和基本药物的获取难度。”(16)汤伟:“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国际展望》,2016年第2期,第99页。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掌握着全球疫苗和特效药的技术和产能,发展中国家高度依赖发达国家主导的药物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产能与技术领域的鸿沟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卫生治理方面的差距。知识产品保护与高昂的药价导致暴发疫情的发展中国家对药物的可获得性大打折扣,进而延误疫情的可控时机,卫生危机持续恶化。
二
全球卫生治理既是技术层面问题,还牵涉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17)David Fidler, “Asi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and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Vol.5, No.2, 2010, p.269.因为涉及世界各国和各有关国家内部的多方利益,原本就难以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由此而言,全球卫生治理难以顺利推进,存在多方面的障碍和阻力。
一是全球卫生治理与国家卫生治理的优先议程不同,使得治理必需的医疗资源难以实现有效集中。各国面对的突发事件及其紧迫程度有差别,国内卫生治理水平不一,导致国家之间卫生治理的议程设置呈现各自特点。全球卫生治理与国家卫生治理的最终目标都是全人类的健康与安全,但面对具体事件和问题时,出发点和实施路径迥异,故全球与国家层面的治理议程设置亦有显著差异。对国家而言,以人类健康为全球卫生目标,同时还要维护国家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利益并力图实现相关对外政策目标。两个目的不完全一致导致国家在内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就全球卫生议题的优先性产生矛盾,卫生治理主体需在国家责任和全球责任中寻求平衡。(18)周康:《冷战后美国全球卫生外交研究——以传染性疾病的应对为例》,外交学院2019届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27~28页。一旦两个层面的卫生治理优先议题不同,有关国家由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和国内压力,通常会将本国卫生议题置于优先地位,这便加大了全球卫生治理中国家资源协调的难度,削弱了协同应对卫生危机的集体执行力。美国卫生治理的优先事项是,对暴发于海外的传染病进行早期监测,在这些传染病扩散到美国本土前有足够时间采取必要应对之策;发展中国家更为关心的是,改善国内医疗卫生条件,提高针对慢性病的基础医疗水平,国内出现传染疾病时能够有效防控,争取疫苗与特效药的平价获得;而完善集疾病预防、监测、治疗、医药技术研发等多位一体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对WHO至关重要。议程优先次序不同,资源分配和布局的重点领域就有别,治理的碎片化和分散化便难以避免。
二是安全型与发展型卫生治理模式的差异,阻碍了两类模式的行为主体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深入合作。美国是卫生治理安全化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已将公共卫生问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中。21世纪初,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全球传染病威胁及其对美国的意义》报告明确指出,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带来的全球卫生威胁,将给美国公民以及部署海外的美国军队带来威胁,造成美国和全球安全的复杂化。(19)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The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Threa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Change & Security Project Report, NIE 99-17D,January 2000, p.34;张业量:“美国的全球卫生安全政策——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的国际政治分析”,《美国研究》,2014年第3期,第13页。安全型卫生治理模式将公共卫生问题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有助于集中资源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但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度安全化的倾向。发展中国家质疑安全化是以“遏制而非预防”为目的,主要为了保护西方,如针对埃博拉疫情,西方援助着眼于隔离而不是常规治理,监测系统在交通要道设置屏障而非关注受感染地区。(20)汤伟:“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国际展望》,2016年第2期,第95、98页。发展中国家认同发展型卫生治理模式,即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全球卫生问题,认为贫穷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根源,只有缩小国家间医疗卫生水平差异,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全球卫生治理目标。欧盟亦倾向于从发展角度考察全球卫生治理,在战略文件中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产生全球卫生问题的主要根源,重申减贫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中心位置。(21)刘长君、高英彤:“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论析——兼论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国际展望》,2017年第2期,第103页。安全型与发展型卫生治理模式的行为逻辑有较大差异,前者出发点是防止传染病波及本国,对全球卫生治理的参与是维护本国利益的附带效应;后者则主张以协同发展促进卫生问题的根本解决。从短期看,将传染病看作安全问题,有助于控制疾病的蔓延趋势,尽快应对突发问题;从长期看,发现传染病的根源并从根本上消除之,必须将其视为发展问题,以解决贫困和医疗保健体系落后的问题为重点。两种卫生治理模式的巨大差异,注定了它们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协作的难度。
三是单边或多边的治理途径有别,加大了公共卫生领域南北合作乃至全球多边合作的难度。大国拥有较为丰富的医疗资源,良好的国内医疗卫生条件使其有能力应对慢性疾病的医治;一旦暴发传染性疾病,较为健全的疫情监测系统短时间内尚可担负防治工作。从长期看,疫情的无国界性使国家必须与邻国乃至往来较为密切的国家通力合作。美国倾向于通过单边或狭隘的双边方式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将公共卫生外交视为政治资源和软实力工具。美国曾制定为期5年、总额150亿美元的单独艾滋病行动计划,用以资助深受艾滋病困扰的部分国家,却拒绝了继续向全球艾滋病基金每年注资10亿美元。特朗普甚至于2020年5月底宣布终止对WHO的资助。金砖成员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积极推动全球传染病防治领域的多边合作,是全球卫生治理多边主义的践行者。五国致力于推进“全民健康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探讨有别于西方的全球卫生新议程,重点包括向WHO等国际卫生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和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22)Andrew Harmer, “The BRICS Countries: A New Force in Global Health?” Bull World Health Organ, 2014, Vol.92, No.6, pp.394-395.公共卫生问题的跨国性要求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开展紧密的国际合作。新冠疫情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说明,即使一国控制住国内疫情,如若他国防治不力,除非关闭国门,否则源源不断的“输入型病历”为本国疫情防治构成极大挑战。只有所有疫情发生国参与进多边卫生治理合作中,才能最大限度的遏制传染病的大规模传播。此外,卫生治理的单边行动常将政治目的和卫生目标混在一起,增加了卫生治理的复杂性,不利于资金资源的整合。
四是私利与公益之间难以找到契合点,药品两难加深了公共卫生治理困境。疫苗和药物研发主要由大型跨国药企主导进行。前期需投入大量资金,临床试验还面临失败风险和经济损失。2018年,全球药物研发投入比过去五年增加35%,但综合成功率却下降至11.4%(2015年为22.5%)。(23)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Drivers of Change and Evolution of Clinical Trial Productivity, IQVIA Institute for Human Data Science, 2019.追逐并获取巨额利润是医药公司持续研发的最大动力。为了保护国内药企的创新研发热情,发达国家纷纷完善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然而,这极易陷入两难的境地,即无专利保护,便没有药企愿意斥巨资且长期投入药物研发工作;但投资大则药品贵,疾病高发的贫困国家无力负担昂贵的疫苗及治疗药物。吉利德公司的丙肝药物索非布韦在欧美发达国家采取超高定价,美国售价为一粒药1000美元,在91个中等收入以下发展中国家则低价销售,如在埃及的售价仅为美国的1%。(24)“TPP框架下的药品专利保护争议”,《光明日报》,2015年7月31日。吉利德这种对特效药采取全球范围内分别定价的策略,试图兼顾利润和公益,却遭到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强烈反对,英国甚至暂停购药。大型药企以追逐盈利为出发点积极推进药物研发,在不影响巨额利润的前提下,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药品援助或低价售药。然而,当私利与公益产生矛盾甚至冲突时,企业无疑选择前者。如若国家或国际组织采取强制措施,则药企的研发创新积极性受挫,长期看亦无益于全球卫生治理的深入开展。
三
以传染病蔓延为代表的公共卫生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形势看,综合施策、多管齐下且将制度建设与具体举措结合起来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其中,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是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突破当前卫生治理困局的必要选择。
第一,明晰权责、提高效能,推动多层级卫生治理主体的协调与整合。全球卫生治理涉及国内卫生治理与全球卫生治理之间的互动、WHO的再定位与改革等方面。在国际层面,WHO在应对多起全球性卫生危机时发挥重要作用,但它常因资金短缺、下设机构行政效率低下、应急能力差而受诟病。为了弥补其不足,除了WHO从“发现、遏制”疾病暴发向疾病疫苗、药物研发和可获得性方面转变职能外,政府和非政府卫生治理新机制得以建立,或针对某种疾病或专司具体职能,如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GAVI。首个《全球健康与对外政策联合国大会决议》建议联合国秘书长与WHO总干事协同分析对外政策与全球健康相关的挑战和行动;(25)Sara E. Davies, “What Contribution 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ke to The Evolving Global Health Agenda?”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6, No.5, 2010, pp.1167~1190.联合国千禧高峰会特别指出全民健康应在应对流行性传染病、提供安全用水预防疾病等具体方面得以实现;(26)United Nations,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07, United Nations, 2007.“共享世界、共享健康”战略框架提出协调全球资源控制流感病毒、加强疾病监测投资等内容。(27)Mogedal and Alveberg, “Can Foreign Policy Make a Difference to Health,”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Medicine,Vol.7, No.5, 2010, p.2.在国家层面,政府虽是国内卫生治理的主体,但不能垄断与疫情相关的重要信息,防疫政策制定部门应与WHO、联合国卫生机构保持密切沟通。国家卫生政策制定者应综合专家、经济社会等部门多方意见。在地方层面,疫情发生地的地方政府除及时应对危机外,还要无隐瞒上报上级政府,为国家部门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卫生治理重点是分层级的,需要区别施策:一是合理分工,国际、国家、地方行为体履行各自职能,避免互相推诿,防止职能重叠;二是信息共享,与疫情相关的所有重要信息均要实现向各层级治理主体公开,充足信息的获取才能确保制定正确的政策;三是互动协商,国家卫生部门发挥宏观指导作用,地方卫生部门执行国家卫生政策,而国际卫生组织与国家卫生部门间无隶属关系,国际组织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整合各种资源、协调国家间行动。
第二,促进卫生治理的多个环节紧密衔接,特别关注每个环节的治理重点。以全球大规模传染病的防控为例,预防、监测、治疗和恢复,各个环节都不可或缺、环环相扣。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主体和治理侧重点。预防环节的核心是疫苗,疫苗既有技术壁垒又有售价障碍。贫困国家易暴发公共卫生危机,但无力自主研发疫苗,缺乏购买疫苗的资金。例如,禽流感疫苗需求量为5亿单位计量,全球生产能力仅3亿,且主要分布于发达国家,疫苗供需严重失衡,发展中国家近50%人口无法获得疫苗。(28)汤伟:“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国际展望》,2016年第2期,第105页。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于2009年6月推出“预先市场承诺”机制,201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盖茨基金会共同创建了旨在控制疫苗成本的“健康市场框架”(HMF),2017~2019年面向80个国家投入4.5亿美元。(29)UNICEF, Supply Annual Report,Copenhagen, 2016.2020年6月4日,世界各国领导人承诺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捐款88亿美元,以确保最贫困国家的3亿儿童在2025年前接种麻疹、脊灰等疫苗。(30)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World Leaders Make Historic Commitments to Provide Equal Access to Vaccines for All,” Global Vaccine Summit, June 4, 2020.主要大国均已建立起全球卫生监测系统。如美国早在21世纪初,就建立起“全球新发疾病监测和应对系统”;欧盟创建了“欧洲传染病网络”,包含流感监测、耐药性监测在内的17个分支网络;中国建立起能够监测39种传染病的全球最大网络直报系统。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的卫生监测系统信息能否以及如何共享,是全球传染病防治取得进展的关键。无论是慢性病还是突发传染病,治疗环节都是关键。在这一阶段,医护资源和药物可及性是重点。大国既有充足的医护资源,还有拥有药物研发优势的大型药企。由WHO或联合国牵头,推动发达国家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人员和药物援助项目,保证贫困国家的民众及时获得有效治疗。恢复阶段,除了包括病患的身心恢复,还包含疫病结束后经济社会正常活动的恢复。在这一阶段的主要治理主体为国家,但解除边境封闭、经济恢复所需资金等事项需相关国际组织加以协调。
第三,深化卫生治理的南南合作,力促南北卫生领域合作项目的开展。金砖五国在卫生领域的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金砖成员间协力将卫生议题置于国际发展核心议程中,强化卫生议题联盟,推动WHO朝着更多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方向进行改革,加强医药和疫苗研发合作,提倡以人为本、共同消除贫困、对非卫生援助“双赢”等新理念,(31)晋继勇、贺楷:“金砖国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动因、路径与挑战”,《国际观察》,2019年第4期,第127~128页。发挥金砖新开发银行的融资功能,加大生物科技合作与创新,强化全球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建设。(32)晋继勇:“携手抗击疫情,进一步提升金砖国家公共卫生合作”,《光明日报》,2020年2月17日。这些都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思想和制度基础。南方国家中的新兴经济体力量崛起,在公共卫生领域不仅是接受援助方,还日益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这有助于增加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促进供需有效对接。南方国家的共同需求有助于强化卫生领域的南南合作,南方国家亦可以通过寻求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带动提高自身卫生治理能力,尤其在特定地区特定卫生援助项目中开展三方合作,如英国-中国-坦桑尼亚疟疾防控项目。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无论是南南合作还是南北合作,应以缩小差距而非强化优势为合作目的、淡化意识形态而非扩大理念规范差异、落实具体项目为导向建立多方合作伙伴关系。
第四,依托日益接近的卫生治理理念与目标和高度依存的经济利益,总结可在全球推广的地区卫生治理经验。虽然各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程度、方式有差异,但它们的卫生治理理念与目标日渐趋同。《欧盟卫生战略(2008-2013)》明确指出其卫生治理核心理念为“公平”和“团结”。(33)Together for Health: A Strategic Approach for the EU 2008-2013,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其公平理念与《世卫组织宪章》中人人享有健康权的内涵不谋而合。新兴国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侧重将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更广泛意义的团结理念中,共享科技、医疗技术,共同应对卫生危机。
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间经贸往来增加,对外投资活动日益频繁。按2013年美元价格计,近期流感大流行导致的经济损失每年约5000亿美元,占每年全球收入的0.6%。(34)Victoria Fan, Dean T Jamison & Lawrence H Summers, “Pandemic Risk: How Large Are the Expected Losses?”Bull World Health Organ, Vol.96, No.2, 2018, p.132.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各国切断交通往来,中断经贸投资,全球产业链也遭受重大打击。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预估,此次疫情可能摧毁全球GDP的1%;牛津研究院进一步指出,当前疫情造成的全球大流行将使全球GDP损失1.1万亿美元。(35)Craig Stirling, Enda Curran and Catherine Bosley, “Economists War-Game Pandemic Threat to Global Growth,” Bloomberg, February 25, 2020.全球卫生风险加强了全球利益共同体,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合作基础。
卫生治理实践经验从地区推广至全球。区域内部经济联系密切、人口构成类似、生理结构相似,往往面临共同的公共卫生问题。例如,东亚地区人口密度大、经贸往来频繁,从非典、禽流感再到如今的新冠肺炎,东亚国家面临共同的卫生治理危机。东亚为应对危机,先后召开“东盟-中日韩卫生部长非典特别会议”、“中国-东盟关于控制高致病性禽流感特别会议”,签署《中国与东盟防止“非典”联合声明》,建立“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基金”、“东亚‘10+3’传染病信息通报网”,还创建了“10+3”出入境人员检疫统一标准和共同检疫原则。2020年2月20日,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议发表《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联合声明》,提出建立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和中国-东盟防疫物资储备中心,(36)“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疫情后可能出现‘爆炸性恢复’”,《中国青年报》,2020年5月6日。实现与东盟国家在检疫、交通、出入境各部门协调合作。以上卫生治理新机制的创建是地区卫生治理深入发展的制度基础,地区卫生治理的深化是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重要步骤。国际组织和大国可将协助地区共同抗疫的经验有选择地推广至全球层面,找寻国家利益、地区利益乃至全球利益的契合点。
四
中国是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一直以来都在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为此不断努力提升自身治理能力,提供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卫生公共品,并与发展中国家合力推进全球卫生领域新规则的构建。有鉴于当前全球卫生领域的严峻形势和国际合作困难,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任务更加艰巨,尤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大力气。
其一,提升国家卫生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国内卫生治理经验的国际分享。自2004年起,我国建立了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疾病防控信息体系已运行28个业务应用系统,分区域设置4类58支国家级和2万余支地方卫生应急处理队伍。(37)“为全球卫生应急树立中国标杆”,《健康报》,2018年5月14日。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客观上助推中国提高卫生治理的能力。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救治机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防控救治和资源调配方面的作用。(38)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求是》,2020年第5期。在中外卫生合作方面,加强国内经验的国际分享。中国建立起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在疟疾、血吸虫等方面与非洲国家进行中国经验适应性合作研究,参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机制工作组和全球慢性病防控工作。(39)“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中国中医药报》,2018年5月23日。中国同WHO的合作扩展为多方合作机制,如“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中东欧卫生部长论坛、中阿卫生合作论坛等;率先提出“大健康”理念,包含全民健康覆盖、中国质优价廉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等新方面。(40)王潇雨:“构筑人类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健康报》,2018年5月22日。中国在新冠疫情中的努力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疫情发生伊始,中国迅速分享部分毒株全基因组序列、研发核酸检测试剂盒、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肺炎疫情全球大暴发,数万中国公民和侨民身处海外疫区,中国在治疫经验、医疗物资等方面对外施以援手,既保护了海外同胞的切身利益,还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声誉。
其二,将医疗资源投入和高新技术应用等多种支持方式相结合。中国通过对外派遣医疗人员、开办医疗培训班等方式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进程。20世纪60年代至今,中国已向71个国家和地区派遣2.6万医护人员,为2.8亿人次患者治疗疾病,参与了埃博拉、鼠疫等重大疫情应急处置。(41)“中国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了力量和经验”,《经济日报》,2019年5月20日。中国以低于西方90%~95%的极低价格将疫苗出售给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乙脑援助项目向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贫困国家提供近3000万剂(0.45美元/剂)乙脑疫苗;2014年提供1.2亿美元物资协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42)“疫苗、抗埃和青蒿素:细数全球卫生治理的‘中国亮点’”,新华社,2017年1月19日。新冠肺炎的医治过程中,中国应用了新技术进行诊断与医疗服务。例如,利用5G技术进行远程医疗,在传统医疗基础上融合无线及高速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远程外科手术操作、无线远程会诊、患者监护等工作。(43)“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政府治理体系将迎来哪些考验?”《新民晚报》,2020年2月9日。相对于非典时期,此次新冠疫情期间,民众通过互联网可随时获得疾病的最新资讯、政府迅速掌握感染人群的密切接触者、知悉全国范围人员流动的行动轨迹,有助于疾病的防控。互联网医院集接诊、开处方、邮寄药物于一体,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慢性病人群的治病困扰。以上新技术的运用经验向外推广,可有效协助他国应对疫情。
其三,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应地方差异和具有高融合度的卫生公共产品。中国深知广大发展中国家最为急迫的卫生公共品需求,有针对性的供应、实现供需匹配才能确保卫生公共产品发挥最大效应。发展中国家除了需要资金、技术、人员方面的卫生援助外,还因地方特色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表现为卫生治理的地方差异。中国作为多民族、多人口的国家,在国内治理中重视地方差异性。“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援助行动中,更为注意结合被援助地区的本土性文化特征和区域卫生发展状况,致力于研究和实施中国经验的‘异地性融合’”;“重新审视卫生发展援助的资金规模和投向,对低收入和基础卫生设施薄弱的国家实施更多联合援助计划”,(44)高明、唐丽霞、于乐荣:“全球卫生治理的变化和挑战及对中国的启示”,《国际展望》,2017年第5期,第144~145页。从协助应对突发疫情、以资金和人员为主的“有形公共产品”向以提高当地自主卫生治理能力、技术经验支持为主的“无形公共产品”转变。
最后,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努力推进公共卫生新规则和新标准的制定,以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诉求。中国作为WHO理事机构成员,积极参与全球重大卫生政策的规则制定工作,包括发起多项重要决议、为WHO制定规范标准提供技术咨询、参与多项国际法典标准的起草等。(45)“构筑人类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健康报》,2018年5月22日。作为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致力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促进卫生相关的新规则制定。具体主张为,在新规则和新规范的制定过程中,更多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和现实国情;对疾病进行分类治理,如传染病与非传染疾病、突发与慢性病等区分管理;充分考虑地区特性、优先在地区层面促成一致规则的形成;公共品提供方面,防止从“公共产品缺失”到“公共产品过剩”、力促公共品供应由“应急性”向“长效性”转变。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协力扭转西方主导全球卫生规则制定权的现状,呼吁全球卫生规则与标准的制定切实从全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尤其关照弱势群体最基本的健康权利;支持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医学专家为WHO制定规则规范提供专业意见,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