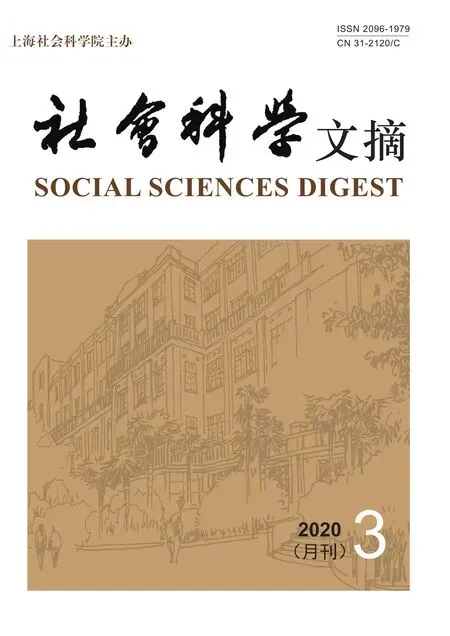互联网时代网民职业身份如何影响其政治舆论倾向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29亿。网民群体的观点态度与舆论倾向越发引起社会关注,互联网的政治-社会功能也已经成为学界热议的重要议题。
互联网的发展是否促进了不同政治舆论之间的有效交流?网络社会中网民的舆论倾向是趋于缓和还是极化?有学者乐观地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降低了知识的门槛,给人们带来异质性信息与意见,增进了有效沟通与观点融合;但另一些持怀疑论者则指出,互联网中“沉默的螺旋”更为明显,人们容易选择接受与自身倾向相似的意见,最终反而使舆论观点趋于极化。
针对上述争议,本文认为应当引入社会结构的视角展开分析。具体而言,为什么部分网民对待特定的政治议题有明显的态度差异,而另一些网民则显得中庸?怎样理解网络社会同时出现信息多元与政治舆论极化的悖论?对于此类问题的探索能够将真实社会结构带回网络社会的分析中心,并能更好地理解互联网的政治-社会功能,同时也为转型时期中国的网络治理提供参考。
理论与假设
网络社会中存在着诸多由政治、社会等不同领域的议题组成的公共舆论,其展现着网民群体对特定议题的潜在态度和倾向。已有研究表明,即使针对同一类议题,不同网民的舆论倾向也可能存在差异,媒介信息论与个体选择论是解释其差异形成的两大经典理论。前者提供了舆论倾向形成的信息供给侧原因,互联网被当作一种新的信息媒介渠道,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信息获取门槛,提高传播效率,拓展个体潜在的信息资源集合。但由于互联网内部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议题信息与媒介渠道,因此这一视角下的互联网功能及网民政治态度仍然是复杂的。后者回应了行动者如何分配注意力及筛选使用信息的问题,从微观的角度阐释了互联网时代网民舆论倾向的形成过程,并更倾向于认为互联网在赋予人们选择自由度的同时,助长了个体选择观点同质群体的交流偏好,可能加剧政治极化。然而,个体为何具有特定的偏好?诉诸微观的心理人格假设往往因测量困难而导致循环论证,故从网民个体偏好到宏观网络舆论的因果链条仍需引入群体层面的结构性视角加以分析。
社会结构与政治现象的关系是政治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议题。尽管社会结构存在不同的理论面向,但基于社会劳动分工位置的职业身份群体始终是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维度,其不仅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基础,而且具有相似的社会地位与声望报酬。早期的西方研究关注了从社会阶层结构到政治舆论倾向的理性选择机制,并指出劳工群体通常更倾向于支持国家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积极干预,资产者则出于维持现行市场秩序等考虑,倾向于支持自由放任等较为保守的观点,而中产白领阶层恰好处于二者中间的缓冲带位置。伴随现代社会利益群体的演化,仅依靠阶层利益对政治舆论倾向做出解释的难度逐渐加大,故对阶层意识、身份认同等社会心理与政治社会化机制的讨论逐渐兴起。此类观点把职业与阶层位置视作结构性的场域,政治倾向的形成寓于特定场域内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及新闻媒介等都是社会化的中介。综上,本文认为,社会结构论在逻辑顺序上要比媒介信息论与个体选择论更为根本,信息媒介往往是从特定职业身份到政治舆论倾向的中介机制,而个体选择的偏好其实也潜在地受到其职业身份的影响。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群体的结构性分化不容忽视,不同职业群体在某些意义上存在不同的利益基础,社会阶层的分析框架在当下的中国仍有较强的经验适用性。在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尽管网民群体的总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社会真正具备了去结构化和去中心化的特征。恰恰相反,本文认为,社会结构对政治倾向的影响延伸至了网络社会内部,甚至可以说,网民的政治舆论倾向其实是现实职业身份的投射,经典的理性选择机制与政治社会化机制在网络社会仍然存在。
在经验研究层面,已有学者发现中国网民在诸多政治议题上的舆论倾向皆趋同化,已有研究指出,对内政治支持越高的网民也更可能具有进取的外交态度。为便于研究操作与理论对话,本文同样选取对内政治支持和进取外交态度两个方面来刻画中国网民的政治舆论倾向,并以直接从事政治相关职业的党政工作者、作为文化精英的知识阶层以及作为普通大众的体力劳动者三类网民为例进行分析。一些报告显示,相比于知识分子网民,党政工作者的政治舆论倾向明显更为积极;而相对于上述二者,大众网民的态度倾向更为中庸。综上,类比理性选择机制,笔者提出假设1:特定职业身份意味着某种利益立场,其直接影响网民的政治舆论倾向。党政工作者网民更倾向于表达较高的对内政治支持和积极进取的外交态度(H1a);知识阶层网民则可能表达与之相反的政治舆论倾向(H1b);普通体力劳动者网民则对这些政治议题呈现相对中庸的舆论倾向(H1c)。
除了理性选择机制以外,社会结构性位置还意味着特定的社会地位与场域环境,它形塑着参与者的不同生活实践经历,导致不同网民群体接触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最终形成差异化的态度倾向。显然,主流媒体、微博、微信以及个体社会网络等是较直接的媒介渠道。已有研究发现,当下中国的主流媒体很好地构建了连结党政工作者与社会公众的纽带,对人们的国家政治认同有促进作用;微博等公共领域交流媒介的兴起则为知识分子等群体提供了信息多元化的替代性政治交流平台;而微信与朋友关系网络的特性相似,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社会资本,为个体提供潜在的信息资源集合。类比政治社会化机制,笔者提出假设 2:不同职业的网民所接触的信息媒介渠道不同,这间接地对其政治舆论倾向产生影响。党政工作者网民的工作生活场域使其更多接触官方主流媒体,且更可能通过微信朋友圈或朋友渠道了解政治新闻,这些原因加强了其对内政治支持和进取外交态度的舆论倾向(H2a);知识阶层网民的生活工作场域导致其与主流媒体的接触较少,但对微博等公共领域交流平台参与较多,这些原因削减了其对内政治支持和进取外交态度的舆论倾向(H2b);距离主流政治较远的普通体力劳动者网民在各种媒介渠道使用方面无明显的积极倾向,甚至有可能出于对公共事务的疏离而更少在微博公共平台中关注政治信息(H2c)。
研究设计
本文的数据源于“2015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具体数据介绍可参见“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本文剔除了检验题得分低于8分、被调查者年龄低于10岁,以及暂没有确定职业的学生群体和无业人员样本,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928份。
研究的因变量是网民的政治舆论倾向。其中,对内政治支持因子的测量问题包括类似“中国绝不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等五个与国内政治制度有关的舆论表述(KMO=0.897);进取外交态度因子的测量问题则包括类似“很多国际争端等对外问题都是其他国家首先引起的”等四个与对外态度相关的舆论表述(KMO=0.843)。相关分析显示两个因子具有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54)。
研究的自变量包括网民的职业类型以及接触政治信息的媒介渠道两部分。本文首先根据受访者的职业筛选出四类人群。一是党政工作者,职业涉及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中高层工作者(N=246)。二是知识阶层,职业涉及高校教研人员、新闻媒体工作者及律师等相关行业(N=272)。三是体力劳动者,职业涉及农业劳动者、工厂务工者等(N=341)。四是作为参照组的其他职业群体,主要包括如机关或公司普通职员、私企老板或自雇佣者、非政府组织等(N=2069)。其次,研究的中介变量为网民获取政治信息的媒介渠道,根据“您经常从下面这些渠道获得政治新闻,时事评论等消息吗”这一问题总结出主流媒体渠道、微博渠道、微信渠道、个体社会网络四个虚拟变量。
此外,研究将网民的家庭收入、教育程度、性别、年龄、政治身份(是否为共产党员)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研究首先运用嵌套回归模型来考察不同网民群体的舆论倾向差异;其次,由于所涉及的中介变量较多,笔者选择通过路径分析来估计不同群体对不同信息渠道的接触情况,因为特定中介渠道被处理为二分变量,故运用逻辑回归进行拟合;最后运用KHB方法,通过对嵌套模型的系数进行比较来检验中介路径的效应是否显著。
实证结果
(一)网民职业身份对政治舆论倾向的直接影响
总体来看,对内政治支持和进取外交态度的数据结果具有相似的特征。在纳入控制变量,但未包含媒介渠道变量的情况下,不同职业网民的政治舆论倾向有所不同。参照其他职业群体,党政工作者网民有明显较高的政治支持舆论倾向和进取对外态度舆论倾向,这与其现实利益立场和现行政治体制较接近有关;而知识阶层网民的政治舆论倾向在对内与对外两方面皆与党政工作者相反,这说明,知识阶层群体的工作场域相对独立于现行政治体制,其职业群体的利益基础与党政工作者在某些意义上稍有不同(H1a,H1b得证)。普通体力劳动者网民的倾向则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甚至在对内政治支持方面与参照组差别不大,这可能是因为该类群体网民日常工作与生活距离主流政治议题较远(H1c得证)。在此基础上纳入媒介渠道变量后,三类职业群体的作用趋势保持不变,但效应有所减弱。
此外,主流媒体、微博、微信及个体社会网络等媒介渠道变量也对网民政治舆论倾向产生一定影响。全模型将前述的所有控制变量以及媒介渠道变量都纳入分析,结果显示,主流媒体的使用显著增进了对内政治支持和进取外交倾向;微博作为网络公共平台,具有信息多元等新媒体特性,其影响效果与主流媒体相反;兼有个人社交媒介和新媒体特点的微信平台,有助于进取外交态度的形成,但于对内政治支持态度的影响不明显;在个体社会网络方面,通过朋友消息获取政治信息的网民更可能倾向于表达较高程度的对内政治支持与进取外交态度。
(二)网民职业身份对网民媒介渠道选择及政治舆论倾向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职业的网民具有不同的政治信息媒介接触程度。参照其他群体,党政工作者网民不仅更显著倾向于接触主流媒体渠道,而且更可能通过微信渠道和朋友等个体社会网络渠道获取政治信息;知识阶层网民显著倾向于使用微博平台接触政治热点信息,而明显较少通过主流媒体渠道了解政治;体力劳动者网民则显著地更少通过微博渠道了解时事热点,在这一意义上其可能是“政治冷漠”的——由于社会地位及生活方式等约束,在日常生活中远离主流政治。
对上述媒介渠道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对内政治支持方面,纳入媒介渠道变量后,党政工作者网民和知识阶层网民的效应系数都有显著的下降,系数差异分别为0.153与-0.134,混杂百分比则说明二者舆论倾向的形成分别有47.51%和57.72%是来自媒介信息渠道的中介效应;相比之下,体力劳动者网民的全模型直接效应系数的下降在统计上不显著,即媒介渠道的中介效果较不明显。在进取外交态度方面,纳入媒介渠道变量后,党政工作者网民和知识阶层网民的效应系数分别显著地变化了0.159和-0.134,混杂百分比显示媒介渠道的中介效应能够分别分解57.79%和40.90%的总效应;而体力劳动者网民的效应系数变化则不显著,即媒介渠道对体力劳动者网民的中介效应不明显。
以上结果说明,以其他职业群体为参照,党政工作者网民的工作场域与社会政治议题直接有关,其政治信息媒介渠道除了主流媒体之外,还包括朋友消息以及微信社交渠道,这些都是其具有高度的对内政治支持和进取的外交态度等舆论倾向的重要原因(H2a得证);知识阶层网民的日常工作场域和生活实践方式更为独立,且政治信息媒介来源多为微博等公共平台,致使其形成与党政工作者不同的政治舆论倾向(H2b得证);而体力劳动者网民由于日常工作繁重和距离主流政治议题更远等原因,相对较少关注和直接参与讨论政治话题,尤其显著较少在微博等公共平台上参与政治话题的交流,媒介渠道对其政治态度的中介效应不显著(H2c得证)。
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网络社会中网民的政治舆论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现实职业身份的投射,基于特定利益的理性选择机制意味着职业身份对网民政治态度存在直接影响,而处于不同日常工作生活场域的网民还具有不同的信息媒介接触情况,职业身份以此政治社会化机制又间接塑造着网民群体的政治舆论倾向。
研究基于网民的职业身份,刻画了三种不同的网民群体形象:党政工作者网民的现实利益立场与现行政治体制直接关联,而且更多通过主流媒体、微信及朋友消息等渠道了解政治,进而形成高度的对内政治支持和较明显的进取外交态度等舆论倾向;而知识阶层网民则由于利益立场与工作场域相对独立,其更多选择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微博渠道而非主流媒体了解政治信息,故更可能强调多元舆论观点和相对不同的声音;最后,普通体力劳动者网民由于其在日常工作生活及媒介接触方面结构性地距离主流政治较远,总体表现出较为中庸的倾向。
上述发现能够增进对互联网政治-社会功能的理解,看似纷繁复杂的网络政治舆论背后皆有其现实的社会结构基础。互联网对于党政工作者网民而言可能是舆论观点同质化的平台,对于知识分子网民而言则可能是提供多元化舆论观点的平台,对于普通体力劳动者网民而言则可能不是政治舆论极化的平台,而是某种亚文化的场所。就现阶段的网络舆论冲突模式来看,与传统框架理论的精英-大众两分法不同的是,网络社会的舆论分歧更可能存在于不同的精英群体之间,政治舆论极化的问题恰恰发于这一间隙,而普通大众与精英群体之间的舆论竞争则相对位居其次。
在实践中,转型期的国家网络治理不应忽视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基础,而应当把网络治理置于良好社会治理的基础上。在具体的媒介渠道方面,如何统筹协调主流媒体和微博之间的张力,如何更好地运用作为个人社交平台的微信进行治理,都是未来值得关注的议题。当然,本文仍然存在局限,所选取的数据在代表性方面有待提高,精英-大众等职业群体内部可能存在更多的变异或交叉,网民在其他公共议题的舆论倾向表现如何,也值得更多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