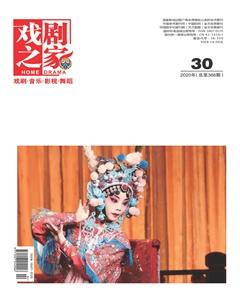电影《误杀》的叙事突破与视听语言分析
麻旭馨
【摘 要】电影《误杀》是马来西亚导演柯汶利的首部剧情长片,改编自2015年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成为我国2019年口碑票房双丰收的一部犯罪类型片。本文从叙事突破、视听语言以及主题表现三方面解读电影《误杀》,分析《误杀》视听语言以及如何在原版基础上实现本土化,实现叙事突破,增加新的价值内涵。
【关键词】误杀;蒙太奇;共情;乌合之众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30-0161-02
一、异境重构,语境本土化
《误杀》用后现代艺术的碎片化混杂方式,大跨度截取、化用十余部影片,融合于影片之中[1]。例如影片开头在棺材中点燃火柴便再现了西班牙影片《活埋》;李维杰讲电影时直接引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一家人在罗统时观看的电影是《天才枪手》;李维杰瞒天过海的核心在于韩国电影《蒙太奇》;最后棺材盖上的血痕致敬《妖猫传》,等等,这些影像碎片都或显现或隐匿于其中。
《误杀》的主线故事借用了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讲述了资深影迷李维杰为了保护妻女,利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制造不在场证据,与警察局长拉韫斗智斗勇的故事。不同的是,影片把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赛国”小镇,男主人公李维杰是一心顾家、为生活奔波的小人物,妻子阿玉则是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他们既要担负高昂的教育费用,也面临着女儿的逆反与隔阂,期待生活平安。家是中国人的情感核心,当女儿遭到官二代素察的欺凌时,站在妻女前面保护家庭的李维杰,自然引发观众的共情与认同。而改编中对于中国式情感的强化同样应用在拉韫身上,她为了找到儿子不惜代价,滥用警察局长职权,最后一无所有,让人可怜同情。语境改编使《误杀》从故事层面具有了中国意味。
二、犯罪类型电影叙事的突破
《误杀》叙事一波三折,节奏紧凑,高潮迭起。相较于《误杀瞒天记》163分钟的时长,电影《误杀》将时长缩减为112分钟,全片节奏更快,情节环环相扣。两部影片都讲述了资深影迷李维杰为保护妻女,利用电影反侦察手段瞒天过海的故事,但在《误杀》的最后,李维杰主动去警局自首,这是《误杀》在剧情走向上的最大差异。这一结局是对犯罪类型片公式化情节的挑战,与常见的犯罪类型片相比多了对于人性、社会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思考,多了思辨色彩。此外,在《误杀》中李維杰和拉韫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设计,跳出了邪不压正的叙事窠臼,带有了人性写实的意味。
《误杀》利用影片开头结尾相呼应的情节设计,对类型电影叙事的封闭结构进行消解,给讲故事留下了遐想空间[2]。影片开头是李维杰及黄毛在监狱里的越狱情节,镜头一转李维杰在颂叔的店里讲电影,这可以解释为越狱是李维杰口中的故事。然而在影片的彩蛋中,同样的监狱场景、人物、动作,甚至是相同的景别与运镜——李维杰扫着落叶抬起头直视镜头,让观众进行不同的深层解读。
三、《误杀》视听语言分析
(一)蒙太奇
1.平行蒙太奇与交叉蒙太奇。《误杀》中多次使用平行蒙太奇与交叉蒙太奇,在“赛场拳击”和“仓库误杀”两个场景中交叉剪辑最为突出。两个场景平行,事件同时发生,一边是泰拳拳手踢到肚子,一边是素察踢到阿玉肚子,一边拳手倒地,一边素察倒地,并且“泰拳”和“误杀”两边的镜头时长越来越短,镜头切换越来越快,节奏也越来越紧张。通过这一手段,导演将李维杰毫不知情的状态,与妻女遭官二代素察欺凌及误杀过程剪辑在一起,观众在这段观影过程中是全知视角,神经逐渐紧绷。
2.象征蒙太奇与隐喻蒙太奇。羊在基督教中意味着替罪、救赎以及牺牲[3]。在《误杀》中羊一共出现了七次,作为麦高芬串起整部影片的剧情发展的同时,羊的出现也是导演使用象征蒙太奇和隐喻蒙太奇的方法。
影片开头“误杀”片名出现的时候,背景音是羊叫声,随后画面转到寺庙中的布施,一只羊跟在僧人身后,此时羊代表怜悯与善意,隐喻男主天性善良无罪;男主沉车灭迹时第二次出现了羊,这时男主回避羊的注视,象征男主本性的抽离,已经有罪;男主因打抱不平和警察起争执,警察为泄愤射杀了一只羊,羊替男主死,代表替罪、牺牲;警察去学校找平平时,老师在讲“羊视力不好,很容易离群,所以经常被大型动物吃掉”这里隐喻男主利用了集体无意识思维编造了不在场证明;开棺验尸时,素察的尸体换成了死去的羊,羊代表替罪;在最后男主自首前,在寺庙出现一只活羊,代表了救赎;影片最后民众接受采访,“羊只要能好好吃草,才不会管是谁在薅它们身上的毛呢”,羊象征着民众。
(二)慢镜头
使用慢镜头的目的大概分为“制造滑稽效果”“强调心理对时间的感受”或“凸显某一重要时刻”,在《误杀》中使用慢镜头的目的是后两个。全篇慢镜头出现大概10次以上,特别是在影片最后,在大雨中开馆起尸一场戏几乎全部使用了慢镜头,慢镜头加上暴雨的场面调度,雨滴的速度被放慢,不仅制造出震撼的视觉效果,也通过刻意放慢速度,主观上加上寻找尸体的时间,提升李维杰最后绝地反击的震撼感。
(三)音乐呼应影片主题
影片结尾安安考试只考了70分,是涂改后才有的100分,男主李维杰表情凝重转身去买口琴,背景音乐《We All Lie》响起,暗示他们全都撒了谎,并且小女儿撒谎已经很熟练了。另外《We All Lie》是韩剧《天空之城》的片尾曲,《天空之城》主要讲的就是子女的教育问题,和《误杀》主题完全相符,与后面男主李维杰跑去自首为教育孩子相呼应。
四、《误杀》主题表现
《误杀瞒天记》将叙事重点放在主人公如何利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制造证据瞒天过海,免于责罚,而《误杀》则更加精炼地表现了这个重要情节,突出亲情与家庭教育这一主题。此外,《误杀》也对集体无意识进行了一定的表现,触及社会现实与人性议题。
(一)亲情共情与人性救赎
“共情”的概念最早由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从治疗心理疾病的角度提出,指的是个体准确理解他人的情感,并在特定情景下作出准确情感反应的一种能力[4]。《误杀》与《误杀瞒天记》相比,最大的差异莫过于结尾男主人公李维杰的自首,这也是很多中国观众认为画蛇添足的一笔,但导演为这个结局设计了令人信服的动机,那就是“身为人父”。男主人公李维杰实际上是一个学历不高、窝囊又爱面子的底层人物,唯一的爱好就是看电影实现英雄梦,他和大女儿之间有很大隔阂,被女儿称为葛朗台又受警察欺凌,夫妻关系摇摇欲坠。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妻女失手“误杀”素察之后却冷静地站在妻女前面勇敢保护家庭,使全家免于罪责,这样的形象自然而然地获得观众的共情与认同。
电影《误杀》给男主人公设置了信佛的特点,他在电影中一共布施了两次,第二次僧人拒绝布施即暗示他已经有罪,影片中多次表现他作案后良心不安,但促使他最终自首的一个原因是在寺庙与拉韫夫妇的见面,拉韫夫妇哭着求他,希望知道儿子是死是活。李维杰知道是自己杀了素察,拉韫的溺爱,都彭的冷漠,都使素察骄纵成性、肆无忌惮,是家庭教育的失败让素察受到了惩罚。此时拉韫夫妇的遭遇引发观众共情,拉韫夫妇并非无恶不作的恶人,他们也是出于亲情和对儿子的爱,不止失去了儿子,还失去了工作和地位,一无所有,令人怜悯。李维杰虽然利用自己的聪明逃脱了法律的惩处,但为小女儿树立了坏的榜样,小女儿学会了欺骗,为了得到口琴涂改成绩单,这也是李维杰选择自首的第二个原因。此外,瞒天过海引发了全国暴乱,而李维杰的父母正是在他幼时死于暴乱,这一点也是促使他自首的重要原因。
从前一直在逃避的李维杰,这一次选择了承担责任,他的自首既是对自己人性的救赎,也为家庭教育敲响警钟,小人物在此刻散发出光辉。
(二)乌合之众——集体无意识
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英文片名《Visual》,即视觉,指的是案子的核心诡计视觉错误。《误杀》英文片名是《Sheep Without Shepherd》,直译为“没有牧羊人的羊”,意译为“乌合之众”。在古斯塔夫·勒庞的社会心理学书籍《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他阐述了群体以及群体心理的特征,指出了当个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时,他有着自己的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当这个人融入了群体后,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淹没,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而当一个群体存在时,他就有着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5]。
在影片《误杀》中,羊作为符号多次出现,羊在《圣经》中指迷途者。电影中羊代表集体愚昧从众的社会人民,即“迷途羔羊”。影片中警察来学校找大女儿平平询问素察的相关信息,课上老师在讲“羊视力不好,很容易离群,所以经常被大型动物吃掉”。“视力不好”“被动型”即暗示百姓大众容易相信眼前所见的片面事实,往往忽略真正存在的客观事实,全盘被动接受眼前充斥的碎片化信息,男主恰好利用了群众的集体无意识思维编造了毫无破绽的不在场证明,让群众替他作伪证,正如牧羊人引领视力不好的群羊般轻而易举。
在《误杀》的影片背景中,“Sheep Without Shepherd”也指没有警察保護的群众,意在指代警民关系。警察作为牧羊人本应该是保护群众的安全,群众想要的是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就像在影片末尾,有人提及“羊只要能好好吃草,才不会管谁在薅它们身上的毛。”只要生活安定,牧羊人薅点羊毛他们是不会在意的。但是当牧羊人变成屠夫,不再保护羔羊时,羔羊就要奋起反抗了。在没有牧羊人的情况下,男主利用思维偏差编造毫无破绽的不在场证明,使群众坚信男主是无辜的。男主一家被警察带走时引起民愤,因为群众认为此时警察已经不再保护他们,开棺验尸时,棺材里不是素察的尸体而是一只死羊,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他们面对警察冰冷的棍棒公然反抗,在这场反抗中有群众被警察击中,此时警察已经变成伤害羔羊的屠夫,于是羔羊开始反抗,全国性的暴动开始,民众自我意识觉醒。
五、结语
电影《误杀》与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相比,叙事更加紧凑,导演在原版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创作,使语境更加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中国观众更容易产生共情,再加上导演独特的镜头语言所塑造的情感和主题表达,使《误杀》口碑和票房双丰收,成为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匹黑马。《误杀》不仅是一部叙事有所突破的犯罪类型片,更加入了对现实社会和人性、亲情、家庭教育的思索。
参考文献:
[1]杨俊蕾.<误杀>:异境悬疑与跨域影像[J].电影艺术,2020,(82).
[2]晓筠.从<误杀》>看犯罪类型片的破与立[J].中国电影报,2019,(02).
[3]吴小雯,胡少婷.解析“羊”符号在影视作品中的传达和运用——以<误杀>为例[J].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2019,(100).
[4]秦鹤梦.电影<误杀>中国式情感的表达与传播[J].西部广播电视,2020,(125).
[5][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