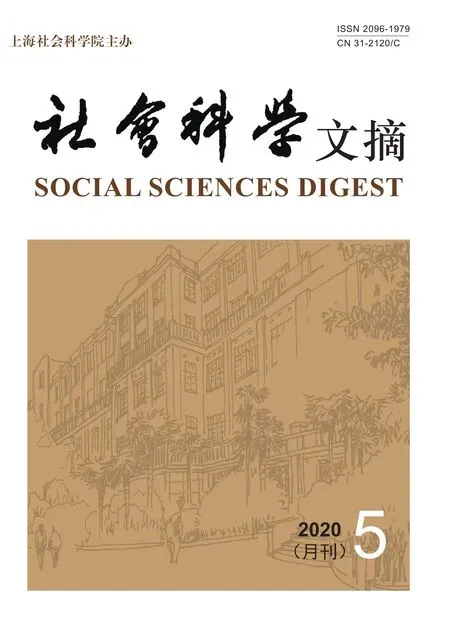欺诈的民法规制
文/许德风
欺诈、真意保留与错误是三个涉及行为人内心意思与其外在表示的制度。若从法律效果的相互关系上观察,真意保留和欺诈各据两端,而错误居中:在真意保留的情况下,表意人的真意被忽略,相对人的信赖受到保护;在欺诈的情况下,表意人可以请求撤销其意思表示以回复未受欺诈状态,相对人不仅不能取得权利,还应赔偿受欺诈人的其他损害;在真意保留和欺诈之间是错误制度,相对人的信赖是否应获得保护或表意人可否撤销其意思表示,要考察有关错误是否满足特定内容的要求(有些国家还会要求表意人无重大过失)。既有研究对真意保留和错误关注较多,对欺诈的研究较少。总体而言,我国民法欺诈制度已初具框架,但其细节仍需结合限制欺诈的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下先讨论作为社会现象的欺诈,再分析欺诈的含义及民法上可用于规制欺诈的具体制度。
规制欺诈的价值基础
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看,欺诈、欺骗或说谎是自然界最基本的现象之一。在伦理或道德层面上,人类对说谎的关注也早已有之。如康德认为任何谎言皆应禁止,无需区分谎言的善意与恶意,或者考虑受众是否有权了解真相。这是将谎言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一并考虑的判断,即或许有些谎言可以带来眼前的收益,但长远而言,谎言不仅会伤及说谎者自身(甚至在谎言不被发现的情况下),也会破坏人与人的沟通和信任,进而破坏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对说谎的干涉也有较深的宗教渊源。如在佛教中,“不妄语”位列“五戒”的第四戒。在圣经中,一个重要的教诲是谎言将毁灭精神,而毁灭精神比毁灭肉体更为可怕。在但丁的《神曲》中,说谎是一种罪恶,说谎者将在第8层地狱受罚,仅比最严重的叛徒高一层。总之,从人类社会的演进来看,一方面,说谎是基本生存之道——人通过说谎/掩饰来获取食物谋生或战胜敌人(所谓“兵不厌诈”);另一方面,作为复杂群体,人类相互之间也需要合作和信任,此种合作和信任甚至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石。这是法律要规制乃至惩罚欺诈的价值伦理与社会经济基础。
欺诈的法律含义
欺诈的法律内涵不容易界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欺诈是“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但何为“故意”“虚假”以及“隐瞒”,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1. 欺诈与信赖共生
欺诈可以按行为表现分为三种类型:沉默、隐瞒真实信息和告知虚假信息。其中沉默及不作为的欺诈最难认定。原则上,沉默并不构成欺诈。仅在行为人有披露义务的情况下,其不披露的行为方构成欺诈或通常所说的“故意隐瞒”。总结来看,披露义务的来源主要有:法律规定、交易惯例和特殊信赖。
为了鼓励交易,法律在某些时候会明文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市场的负面影响。例如,美国法针对二手车交易制定有“机动车信息和成本节约法”(Motor Vehicle Information and Cost Savings Act)。根据该法,若二手车经销商在销售过程中未告知购买者里程表读数不准,将违反关于披露义务的规定。
交易的性质及相关交易习惯也是判断披露义务有无的重要依据。例如,在很大程度上,旧书乃至古玩的买卖是一场当事人之间的“博戏”(game),无论是买受人还是出卖人都了解并受益于“走眼后果自负”的规则。
优势信息、信任或信赖等特殊关系的组合,也促成披露的义务。例如,一家煤矿公司雇佣地质学家探矿,在某农场地下发现了矿藏,于是在未公布该信息的情况下低价向农民购买该土地,同时向股东回购股份。一般认为,前一项交易中,公司的行为尚不构成欺诈或不实陈述,而后一项交易则可能被认定为欺诈。合理的解释是,不将前一项交易认定为欺诈,能更好地鼓励探矿,鼓励在信息上的投资;而在后一项交易中,公司与股东之间有信义关系,因此公司应当如实披露相应信息。对信义义务关系中的披露义务,波斯纳(Posner)法官在United States v. Dial判决中的说理值得借鉴:在当事人之间有信赖关系或信义义务时,应当认为一方已在交往之中“购买”了“诚实”(candor),而这是另一方承担披露义务的内在原因。换言之,在具有特殊的信赖关系(besonderes Vertrauensverhältis)的情况下,沉默本身也可以构成欺诈。
信赖导致披露义务的提升,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渗透于私法的各个分支。信义义务与欺诈常常相伴而生的原因在于,在信义义务关系中,一方(委托人)将自身的利益完全托付给另一方(受托人),若不提供有力的事后救济,委托人的利益将极易受损害,甚至使此种交易安排无法真正达成。这意味着信义义务本质上是一种“利他”义务,与一般交易中的“利己”(如买卖)或“善管”(如保管)都不同,强调受托人要告知委托人全部信息,交出全部获益,不谋求任何私益。若认识到这一点,便可以更好地理解资管交易、证券交易中信息披露的严肃性,理解实践中非常多“知情权”争议所涉及的并不是无关痛痒的信息的获取与传递问题。
2. 欺诈故意的多重含义
民法欺诈中的“故意”,强调行为人具有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主观状态。法律视角下的欺诈还可以作更为细致的分类,如可以分为关于事实的欺诈和允诺欺诈(promissory fraud),前者如出卖人故意隐瞒标的物的瑕疵而订立买卖合同并收取高价;后者指无履约的意思却声称将履行合同并作出承诺。刑法上的诈骗更多是指向后者。
对欺诈故意的判断,可分解为两个层次,一是表达内容的真实性考察(veracity inquiry);二是主观状态考察(scienter inquiry)。例如,行为人明知自己行将破产不能兑现有关支票还签发支票时,其是否有清偿能力为真实性考察所探问的事项;其签发支票时是否知悉该不能清偿状态为主观状态考察的事项。在多数情况下,裁判者关心的主要是行为人是否进行了虚假陈述,同时推定只要进行了虚假陈述,当事人便具有欺诈故意。另外,如前所述存在信义义务关系时,构成欺诈所要求的故意要件甚至会被违反信义义务的行为本身所替代。
欺诈恶意导致其他构成要件的放宽
欺诈与错误密切相关,那么,既然欺诈的结果是受欺诈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为意思表示,可否用错误制度替代欺诈?一般认为,在欺诈中,相对人的错误可以是民法错误制度下的“内容错误”,但主要是民法错误制度原本不提供救济的“动机错误”。后者如公司(管理层)发布虚假信息,导致投资者因此买卖股票(证券欺诈)。对于动机错误,民法上并非完全不提供救济,只是相比内容错误而言要求更为严格的要件。因此,可认为欺诈是错误制度的例外:法律提供此种例外性救济的正当性在于恶意欺诈对意志自由的严重侵害。除此以外,欺诈恶意的存在,还使法律在其他构成要件上往往采取相比诸如错误制度等更为宽松的标准,以下详述之。
1. 因受欺诈而撤销意思表示不要求内容上的实质性
在法律行为的视角下,因为欺诈将导致合同的撤销,似乎要达到类似解除合同制度中“根本违约”的程度,或者达到错误制度中足以影响交易基础的程度,但欺诈恶意的存在,降低了法律在实质性(materiality)要件上的要求。具体而言,只要行为人不实陈述了任何能引起或影响交易的情事,就足以构成欺诈,受欺诈人进而可寻求撤销合同等救济。这是欺诈与其他类似法律制度的重要区别。其考量在于,影响表意人作出决定的因素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主观的、个人化的因素,如果采取一般化的“实质性”标准,很可能会忽略这些个人的因素,这在错误的情况下尚有合理性,但在有欺诈恶意的情况下,很可能过于宽纵欺诈人而损害受欺诈人。
2. 欺诈恶意导致因果关系认定上的放宽
欺诈是典型的故意行为,在其构成之因果关系的判断上,这一观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欺诈制度的规范重心在于行为人欺骗他人的故意行为,对于受欺诈方的意思状态,应持宽容的态度。换言之,行为人的欺诈可以将相对人的“重大过失”正当化。某些时候,欺诈人的谎言可能相当拙劣,一般理性人并不会相信,但这一合理理性人的标准并不能适用于对欺诈的判断。这也是各国普遍确立的法律原则:在行为人欺诈时,相对人存在重大过失而不知,受欺诈人的撤销权不受影响,即就撤销权的取得而言,相对人的过失不在欺诈认定的考虑之内。除可以正当化受欺诈人的重大过失外,欺诈恶意还会导致因果关系判断标准在其他方面的放宽,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欺诈导致必要因果关系的放宽。很多国家在规范撤销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时,都放宽了对因果关系要件的要求。例如,在普通法上,要确立责任,欺诈只要构成受欺诈人行为的原因之一(furnish a reason)即可,而不要求其构成“主要的”(main)或“实质的”(substantial)“引致”(inducement)。又如,在英国法上,撤销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时,必要条件即“要不是”检验(but for test)并不适用。具体来说,即便被告欺诈人的抗辩“如果没有我的欺诈,原告也会订立合同”成立,也不影响原告撤销合同的主张,只要原告证明自己受到了被告欺诈的影响即可。其二,特定领域内的欺诈可豁免对因果关系的考察。如证券欺诈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其根源仍在欺诈制度的一般原理中。
总之,欺诈制度各构成要件相互影响,此消彼长。在发生欺诈时,因行为人主观恶意明显,不仅导致前文所述不要求欺诈内容上的实质性,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考察因果关系这一要件的必要性。即不要求行为人做出意思表示时的误解全部由欺诈引起,只要欺诈是引发该错误认识的共同原因即可。在判断因果关系时,只要欺诈引起的错误在效果上“加速”了缔约决定的过程即可,例如行为人的欺诈导致受害人不再进一步协商有关合同的价格条件。
恶意欺诈的加重责任
1. 从撤销后的相互返还到没收
意思表示的撤销属于财产规则(property rule)类的救济。与通常的认识不同,撤销之后的相互返还并不是中性的,目的并不是真正使当事人回到“未缔约之前的状态”。其原因在于,尽管适用不当得利的返还规则,但欺诈人因其恶意须返还全部获益,而受欺诈人仅须返还现存利益。如标的物非因受欺诈人的过错而毁损灭失,则受欺诈人不再负担返还义务,但受欺诈人对欺诈人的返还请求权不受影响。比较法上甚至还存在这样的规则:即使在因受欺诈人过错而致标的物毁损灭失的情况下,法院也应根据诚信原则,权衡欺诈行为的严重程度和受欺诈人的过错程度加以判断,必要时仍可免除受欺诈人的返还义务。
我国民法上对欺诈撤销权的限制主要体现在除斥期间规则上。在除斥期间经过的情况下,受欺诈人固然不能行使撤销权,但受欺诈人可取得“恶意抗辩权”(exceptio doli),拒绝欺诈人的履行请求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且这一抗辩不受时效期间的限制。换言之,即便撤销权的时效经过或者欺诈侵权损害赔偿的时效期间经过而使受欺诈人无法摆脱合同关系,受欺诈人仍可以拒绝欺诈人的履行请求。此外,基于不当得利的欺诈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也为受欺诈人提供了更充分的保护。
商法上关于欺诈撤销权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别规定。在法律效果上,通常所说的“欺诈—撤销—相互返还”的规则(如《民法总则》第149条、第157条)并不总是成立。例如,在《保险法》上,若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而违反告知义务,保险人不仅有权排除保险合同对其的约束力(解除合同),免除支付保险金的责任,而且也不需退还保险费(第16条第4款),相当于受欺诈人可以“没收”欺诈行为人的履行(保费)。“没收规则”是对欺诈行为的有力惩罚。为什么这样的规则仅停留在商法规范之中,而未成为民法的一般性规则?或许只是通常的欺诈中欺诈一方往往并未作出过履行,即受害人一方手中并不握有欺诈一方的财产,因此即便规定“没收”也于事无补。但这不是这一安排不能成为原则性安排的理由。
2. 基于侵权而废止合同或债权
欺诈是典型的侵权行为。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受欺诈人针对欺诈行为寻求侵权救济并无障碍。在英美法中,欺诈侵权制度历史悠久,包括与我国欺诈制度相对等的欺诈侵权制度(deceit)及相对独立的虚假陈述/不实陈述制度。这些规则有的相当于我国的侵权法规范,有的则类似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德国法上,值得借鉴的是,受欺诈人可获得合同废止权与债权废止权,即在因侵权行为而订立合同的情况下,请求废止合同或废止债权(Anspruch auf Zustimmung zur Aufhebung der Forderung)。
3. 加重的损害赔偿责任
刑法与民法的界分,并不能等同于惩罚与赔偿的界分。尽管惩罚有多重含义,但相对于赔偿而言,所指的主要是当事人承担超出实际损害的额外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刑罚之所以是惩罚,是法律并不探问加害人是否弥补了受害人的损失,或者说即便加害人弥补了受害人的损失,也要承担额外的刑责。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惩罚性赔偿金中超过实际损害的部分具有惩罚性。法律对欺诈的民法规制,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欺诈的民事惩罚上:让受欺诈人取得超过其实际损害部分的“罚金”,让欺诈人在交出欺诈收益之外,还承担更进一步的不利益。
让受害人而不是国家取得因欺诈而惩处的“罚金”的正当性,在于鼓励人们揭露欺诈,减少欺诈人给社会信用制度造成的损失。我国消费者保护制度中的加倍赔偿制度便具有类似的功能。某些时候,在制度上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让第三人取得对欺诈人的惩罚,以便更好地揭露欺诈行为。美国法上历史悠久的检举人(whistleblower)制度便是一例。到目前为止,检举人制度已经被联邦政府广泛应用于军工、金融、环保、医疗、税收等多个领域,是美国反欺诈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余论
欺诈的规制是一项综合工程,既需要宽严相宜的行政法规范(如对行政主体,包括警察、税务部门等说谎须受处罚)和刑法规范(如诈骗罪及相关的刑罚),也需要细致完善的民法规范。在这几个方面,我国法均有改进空间。现行民法上关于欺诈的法律规则过于强调恢复原状,未认识到欺诈撤销或欺诈赔偿制度本身的特殊性,忽略了对欺诈的惩罚。不仅如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甚至还普遍存在回避认定行为人欺诈而认定表意人的重大误解的做法。这些操作的背后,既有民事诉讼程序法中的证据发现、证据认定的原因,也有当前理论与实务对民法规制惩罚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原因,最终使受欺诈人只能据此撤销合同,而不能获得损害赔偿或其他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