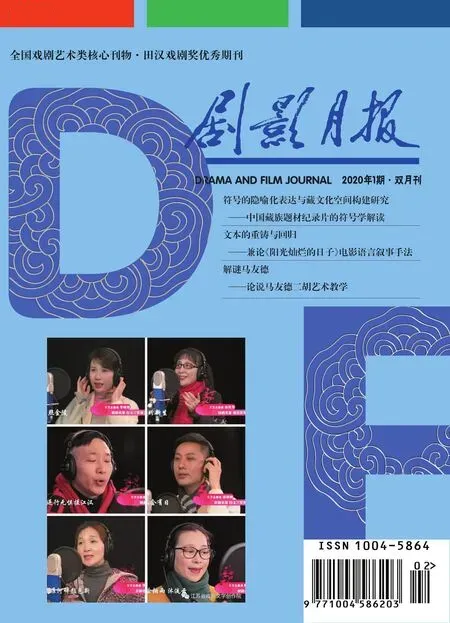新版昆曲《白罗衫》和音乐剧《悲惨世界》的人物对比研究
2019 年6 月21 日在江苏大剧院上演了新版昆曲《白罗衫》,看戏之时,突然萌动出将此剧与近期我观看的音乐剧《悲惨世界》进行对比的想法。这个念头萦绕于心数月有余,思路逐渐明朗清晰起来。
新版《白罗衫》改编自明末清初的昆曲《罗衫记》,由白先勇制作、张淑香编剧,于2016年3月首次亮相。剧中,贼人徐能谋害了知县苏云夫妇,拾得其子徐继祖抚养成人,弃恶从善。十八年后徐继祖上任为官,并接手了亲生父母的冤案,发现凶手正是自己养父。真相大白之后,徐继祖面对亲生父母与自己的养父,面临着内心的抉择。这一版《白罗衫》主要对徐能与徐继祖做了大幅改动,强调情与法的斗争与升华,谱写出近似于古希腊悲剧的乐章。
音乐剧《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由法国音乐剧作曲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Alain Boublil)共同创作的一部音乐剧,改编自维克多·雨果的同名小说。于1980 年在法国巴黎的Palais des Sports 首次公演。1982年,英国的音乐剧监制喀麦隆·麦金塔斯(Cameron Mackintosh)开始制作英文版本,并由赫柏特·克雷兹莫(Herbert Kretzmer)填词。英文的版本由崔佛·南(Trevor Nunn)导演,于1985 年10 月8 日在伦敦Barbican Theatre 开幕。《悲惨世界》被认为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故事以1832 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冉阿让在多年前遭判重刑,假释后计划重新做人、改变社会,但却遇上种种困难的艰辛历程。通过对冉阿让、女工、妓女芳汀和她的私生女珂赛特、警察沙威、青年学生安灼拉等不同阶级的人物塑造,展现出一个动荡的社会。
本文将对这两剧中的主要人物的罪、赎、罚之路以及律法信仰展开探讨。
一、徐能和冉阿让的罪——无法回头的旅途
徐能和冉阿让最初的犯罪动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白罗衫》的徐能“为活幼弟,不幸沦为贼盗”,《悲惨世界》的冉阿让因为“My sister's child was close to death.(我姐姐的孩子命在旦夕)”而偷取面包。这两个满含血泪的理由是戏剧为两人留下的余地。虽然客观上罪过已然,但在观众眼里,这两个人物值得同情,那个身处的时代才应该是谴责的对象。
这样心酸的故事里有一丝“性本善”的痕迹,奠定了人物黑白并存、善恶皆有的复杂形象。但这原初的“善”(我称之为“白”),终究经受不住生活的极度困顿和诱惑。在初次犯下罪行后,他们都在这条“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称之为“黑”)。如冉阿让在十九年的苦役潜移默化地奉行起罪犯的思想,他唱道:
“Turn your heart into stone!(心如铁石,无动于衷!)
This is all I have lived for!(这就是我毕生的信条!)”
他数次越狱,刚获保释便抢过一个孩子的四十苏(当时的法国货币)。再加上人们对罪犯的自然歧视和防备,不出意外的话,冉阿让或是成为穷凶极恶的强盗,或是被抓回监狱度过余生。徐能则是成为江心匪帮的首领,其多年来所作所为早已越过养家糊口的范畴,他杀人越货,杀夫娶妻,无恶不作。他们的恶劣行径已经把自己描摹成了黑色。
这些罪行终将成为他们最为后悔的旅途。虽然很大程度上出自时代的不得已,但个人的行为毕竟来自个人意志的选择。于是,他们都将为此终身背负起十字架,但冉阿让是幸运的那一个。
二、冉阿让和徐能的赎——在“银烛台”的感召下
在冉阿让完全走上徐能的道路、犯下无可饶恕的罪过之前,他得到了神父的一对银烛台。夜晚冉阿让对收留自己的主教行窃,但主教不仅没有揭发,还将偷窃之物尽数赠予冉阿让,又加上了一对银制烛台。“银烛台”在此可以有双重含义:1.主教近乎神性的仁爱对冉阿让的感化。2.基督教中“赎罪”的概念。
根据音乐剧中冉阿让独唱:
“Yet why did I allow that man(可我怎么又让那个人)
To touch my soul and teach me love?(触动我的灵魂,教我仁爱?)”
和主教的部分歌词:
“I have bought your soul for God(我已替主赎了你的灵魂)”
可以看出,音乐剧完全体现了双重含义。银烛台的光芒,将冉阿让从堕落的悬崖边拉回,走上行善与自我救赎的道路。之后的情节才会有冉阿让当上市长,使城市繁荣兴旺,后又帮助沦落的芳汀。这固然有些夸大了冉阿让的才智,但最大限度地表现出冉阿让逐渐回归的仁爱。
然而,《白罗衫》中徐能的“银烛台”却来得太晚。徐继祖便是他的“银烛台”,也是他的罪与赎的诡异的存在方式。这是多么矛盾和奇巧的事:一个初生婴儿瞬间打破了他对生命的漠视,而他刚刚谋害了孩子的父母。徐能从徐继祖处得到的其实并不止“银烛台”所代表的对众生的大爱(“逢庙进香,见贫布施”),还有浓缩至一人身上的小爱,也就是对养子徐继祖的舐犊情深。简言之,徐能的救赎历程是从人性到神性的悄然过渡。
相对而言,冉阿让从主教处学到了神性的宽恕和仁爱,在收养珂赛特之后才有了人性的父爱,这是一个从神性到人性的历程。此处或可以类比《春江花月夜》中由顺江而去的代代人生转入离人伤怀,由宏大叙事转入幽微洞见。徐能和冉阿让都在他们生命中的“银烛台”的感召下,回归到本初的“善”,摒弃了以往的迷茫,完成了罪犯到赎罪者、无情至有情的转变。
三、徐能和冉阿让的罚——逃避?担当?
同是尽力行善,然而在这数年状似安逸的生活里,徐能和冉阿让两人面对过去的纷扰时的反应却大相径庭。
徐能“颈上开花”的梦兆既是戏剧中惯用的“巧”,体现出善恶终有报的传统思想;又借助了现代心理学理论,暗指出徐能的心境也并非只有儿子登科封官的喜悦,还夹杂着对过往的恐惧、焦虑和梦魇。冉阿让虽然相较徐能处境更为凶险,数次面对被抓捕的困境,但并没有太多心灵上的困扰。究其原因,冉阿让是承认罪过并愿意接受惩罚的。剧中,冉阿让在放弃滨海蒙特勒伊市长的同时就已决定自首,他承认了“冉阿让”这个人曾经的罪行,自愿并坦然接受惩罚。正如英国的西·史密斯所言,正义是令人愉快的,即便在它给人以惩罚的时候也这样。于是冉阿让一夜苦思后,天明时分驱车前往法庭自首。虽然后来因为守护珂赛特,他不得不再度逃狱蛰伏多年,但他每次面对警察沙威时,每次都选择了自首。当代表尘世正义的沙威放弃抓捕冉阿让之时,这也意味着冉阿让在世俗领域的罪过已经被宽恕了。剧场里回荡着“Am I be forgiven now?(我是否已被原谅?)”的歌声,这是主角冉阿让的终曲,想必音乐剧《悲惨世界》已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徐能却不像冉阿让一般自黑暗走向光明。他在主观上抱着怀疑的态度:行善是否已足够抵消罪恶?如他在《诘父》一折中为自己辩驳时列出了自己向善多年这一事实,试图脱罪,逃避惩罚。客观上他早年间犯下的罪过不似冉阿让一般易于弥补,徐继祖就是行走的证据。在他眼中,没有完整赎罪的道路,只有无尽的隐瞒。徐能始终站在灰色地带彷徨:何处才是我归宿?于是他与冉阿让的罪、赎、罚之路在此分离。
四、徐继祖和沙威的律法信念——绝对?相对?
十八年后的徐继祖成为一个传统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登科举子,维护着社会的传统价值观。真相爆发前,他是律法这一抽象概念的具象化身。而沙威也是如此,原著中有这样的描写:“道理、正义、法治精神,满天的星斗环绕在他的后面和它的四周。他使法律发出雷霆……他捍卫绝对真理。”音乐剧《悲惨世界》用了一整首类似于歌剧咏叹调的“Stars”(星星)来表现沙威的绝对信念,歌中唱到:
“I will never rest(我将永不停歇)
This I swear by the stars!(我向星星盟誓)”
徐继祖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信念在养父徐能面前瓦解坍塌,沙威则因冉阿让失去了他毕生捍卫的信仰。在《白罗衫》中,徐继祖在说起徐能养恩时只是心痛,但并未完全动摇信念,他仍试图坚守朱红大堂上“公正严明”四个大字;之后徐继祖重复了徐能所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当于认可了徐能作为负罪之人的真心悔过。于是他陷入了与徐能此前完全相同的疑问:犯罪之人在弥补后可被原谅吗?代表绝对正义的公堂可能容纳下灰色的身影?他在父子深情和律法质疑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终于决定放走徐能,也击破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信仰——即律法可以判决任何事物。他拔剑欲自裁如他自己所言,是出于“逃避”,他难以面对真相和自我的精神审判。
随后徐能放弃出逃又打破了这个局面。事实上徐能渴望活下去,第一次的离开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逃离,他在找寻一条代替死亡的洗罪之路,终究无果。在此前有“何以教我为善不到头!”这样的问天之语就是证明。“天”在此亦可有两重含义:1.现实世界的律法容不下他2.精神世界也没有放下过去。既然不可能有圆满的结局,一场取舍势在必行。
徐继祖超越了沙威的纯粹视角。他说“如此忠孝非人道”,他承认了灰色地带的位置,选择相信以人的良心为赎罪入口,从而抵达了律法所不能及之处。他意图舍弃乌纱帽得到精神的圆满。剧中,徐继祖所说“牢笼”是自身觉醒以后为公堂所困,犹如“牢笼”一般,沙威的“牢笼”则来自他自己。沙威的信仰无法坚守,因为他就是他的信仰本身,两者同时崩塌。《白罗衫》中公堂上供起的那把长剑,和沙威跳江的纵身一跃,最适合的意象解读就是绝对正义。当结尾处徐能高高捧起长剑,映衬着匾额“公正严明”时,似乎有一丝献祭的隐喻。这是徐能的生命,也是徐继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