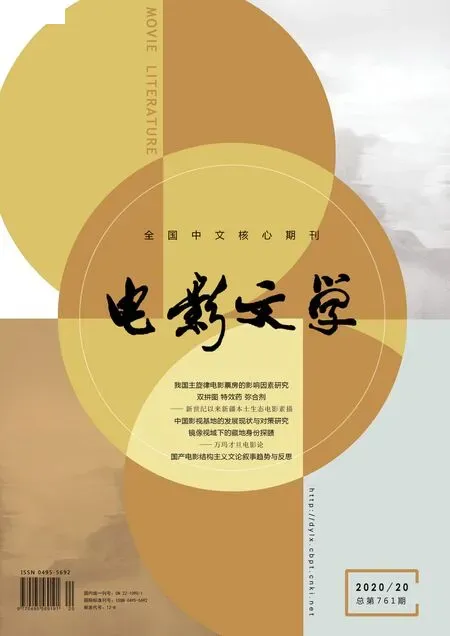现代美国科幻题材电影中生态伦理观的嬗变与超越
李 臻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22)
自20世纪晚期以来,生态恶化和资源危机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在科学界对生态和环境开展深入研究的同时,文艺创作者们也在作品中表达对相关问题的观察和思考。生态批评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发源,随后在欧美各国盛行起来,针对人与宇宙以及人类社会与大自然之间关系的讨论十分热烈。电影作为美国社会思潮的重要表达媒介,也一直参与相关的思想探讨,不论是严肃深沉的传统文艺片,还是流行的好莱坞商业片,都蕴含着诸多生态性元素,影片的故事常常或明或暗地试图对如下问题做出回应:人类究竟怎样看待自然才是合理的?个人、社会以及非人类的万物之间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秩序和伦理规范,才能达到和谐的理想?
新世纪以来,富含科幻元素的探险片和动作片大行其道,除了具有诸多商业特征之外,很多影片中也不缺乏对人类和地球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生态伦理观念是其中最常涉及的主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学研究不断带来新发现和新概念,科幻题材影片在审视这一主题时,展现出了某些突破传统的新视角。
一、以前沿的科学思维来审视自然生态,减少对移情、直觉和诗意的依赖
传统的生态文艺学一贯推崇以审美直觉来建立人与自然以及与异族之间的诗性关系,以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为理想的生态图景的代表。曾有许多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亲身接触其他物种时,感受到神奇的情感流动,进而与自然物产生灵性的融合,让内心的直觉战胜狭隘的工具理性。例如1989年的经典影片《与狼共舞》中,主人公邓巴中尉一边与被白人视为野兽的印第安人建立互信,一边与一头真正的野狼建立友谊,两者之间的隐喻作用不言自明。这头狼摆脱了传统寓言中的负面形象,成了大自然的使者,而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代表着一种融入自然的理想生态。
与诸多讲述人类与大象、狮子、猿猴等野兽亲如家人的故事相似,《与狼共舞》整体使用现实主义叙事方式,但却用具有超自然色彩的浪漫方式来塑造人与狼相遇相知、心意相通的情感关系。这种诗意的共生关系有利于构建人与其他物种友善相处、平等相待的生态伦理,但它不可避免地将动物人格化,将人与动物的沟通方式神秘化或简单化,而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生态观念,在当代影视作品中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如美国纪录片《黑鲸》,直接戳破海洋公园中人与鲸鱼亲密相处的谎言,指出野生动物都是被迫配合人类的娱乐而工作,其实身心遭受了巨大痛苦。证明了单凭人的同情心和想象力来与动物建立关系是不可靠的,甚至可能造成反生态的社会实践。此类知识的不断普及,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绝与野性生物零距离接触的活动。传统故事中缺乏科学支持的自然情怀逐渐受到怀疑,而将更现实的生态科学注入文艺作品的责任,则首先由科幻题材影片来承担。
2009年的科幻巨制《阿凡达》,被很多评论家称为外星版的《与狼共舞》,二者在后殖民主义精神内核和主人公背叛本族加入异族的情节设置方面,确实高度相似。两个故事的生态意蕴也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在《阿凡达》中,主人公与其他物种进行跨界交流的方式,已经被赋予了更具质感的科学解释。人类与土著种族纳美人(也称纳威人)之间难以直接沟通,但是通过基因改造技术,人类可以培育出兼具两个物种特点的阿凡达,并通过相应设备使之与人类的神经系统进行信息联通,而纳美人与潘多拉星球上其他物种的交流,则通过有线连接的方式实现,故事中的奥古斯丁博士清楚地将其表述为通过类似生物电流的介质来传导信息的巨大神经细胞网络,这其实是对当代生态主义自然观的形象化描述。这种细节设定虽然尚未完全成为科学现实,但与目前前沿的基因技术和脑科学研究成果已经非常接近,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与《与狼共舞》描绘的浪漫图景相比,《阿凡达》的主人公不是仅仅依靠开放思想或付出热情,就可以与环境融合,而是必须通过理性的指引和必要的技术手段,并且要忍受放弃人类某些天然特征的切肤之痛,才能实现与其他物种和异族的真正沟通,而且这种沟通虽然是可测量和操控的,但未必总是成功和稳定的。影片中设置的这些以科学认知为基础的生态关系模式,比依靠渲染情感和灵性的传统故事更具现实性,对于人们构建新的生态伦理的尝试,更具启发意义。
近几年来,如《星际探索》等更多科幻影片像《阿凡达》一样将地球生态恶化和资源枯竭作为无奈的背景,而故事中的人类由于受物质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也很难与地外环境顺利地融合。在《安德的游戏》中,即使人与其他物种成员间有和平相处的愿望,也因为沟通方法的匮乏而无法避免冲突和毁灭。在即将面世的《阿凡达2》的剧本中,人类与纳美族仍未能和谐共处,主角阿凡达不得不违反潘多拉星球的生态主义传统,秘密发展源自地球的武器科技,才能制衡人类,保住家园。这些相对悲观的生态图景,首先源于对当代生态科学和其他科学技术研究结论的现实考量,更加彻底地脱去了灵性和神秘主义的外衣。
二、呈现冷峻的生态现实,同时挑战主流生态批评话语和人文主义道德观
按照主流的深生态学思想,人类必须承认自然万物天然的内在价值,人类自身则应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与其他自然物平等相处,共同依照自然规律来生存。这种理想的生态图景在《阿凡达》中得到了塑造。或许出于商业片对观众情感的迁就,《阿凡达》的情节设定仍然具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所有纳美人和阿凡达都可以与巨大的“家园树”实现无限的信息交流。家园树是整个星球生物圈的神经中枢,既可以统一调动所有的生命抵御入侵,也可以统辖所有的物种,使之处于高度和谐的生存状态,甚至在食物链中被杀的各种生物,其灵魂的信息都可以被家园树所储存。但是,这样全知全能的设定,赋予了家园树一定的神性特质,也使生活在其怀抱中的智慧生物们免除了相当一部分对自我和环境的管理责任,他们只要遵从家园树神谕般的引导就可以保持和谐的生活。
然而,现实的生态环境从不具有这种高度自主和精确的调节能力,现代生态学研究已经发现生态系统并不是符合线性逻辑的稳定的系统,其平衡是动态的和相对的。激烈的对抗、损耗、突变和各种不确定因素是生态系统的常态。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技术水平,也不足以实现对自身和其他物种间关系的精确控制。像人类这样的物种所组成的社会能否有效地控制自身的空间扩张,使本物种的规模与环境承载力相协调?目前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乐观的回答,因为当前可预见的科技革新都无法改变人口与资源之间供求矛盾愈演愈烈的总趋势,除了有意识地限制人口增长之外,没有任何一种符合科学论证的手段,能够使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实现能量和信息交流的长期稳定或良性循环状态。但是限制人口增长以及牺牲人类福利的具体做法,在世界范围内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它不仅涉及技术上的困难,也与人文主义道德观的某些基础原则相抵触。
于是,在触及生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矛盾时,多数影片在生态叙事方面采取各种方式回避核心问题。不仅《阿凡达》采用了将反生态的人和保护生态的人一分为二的方法,如《拯救猫头鹰》等很多类似的故事中,破坏自然的也是一小撮利欲熏心者或冥顽不灵者,似乎只要击退了他们或教育过他们,善良的人们就可以和大自然共享宁静。《黑客帝国》和《终结者》等科幻灾难剧貌似戳破了上述的浪漫氛围,但仍设法绕过人类如何自我控制的话题,这类故事中计算机或外星人分析过人类的生存方式后,将人类视为感染了地球的病毒,但是主人公们已经不必再检讨过去的错误,因为计算机或外星人对人类的奴役和屠杀,使人类变成了挣扎求生的弱势物种。让全人类一起造成生态灾难,再一起面对浩劫后的余生,继而重新歌颂人类在逆境中的种种美德,甚至让计算机和外星人对人类的美德肃然起敬,最后回到让观众舒适的人道主义立场,是编剧们常用的一个捷径。而真正试图用技术手段阻止人类无限扩张的角色们,如《但丁密码》《猎杀星期一》等影片中的反派,最终都被描绘成带有极端宗教狂热或法西斯主义色彩,并且同时具有偏执、妄想、控制狂等心理变态症候。这样的思路不难理解,毕竟当年纳粹德国一边保护生态环境、一边灭绝少数种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践,给了后人口诛笔伐的依据。
但是,2018年的《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中,灭霸的形象突破了以往的窠臼。影片中的灭霸与漫画原型不同,在电影中灭霸并无特殊的出身背景,他试图杀死宇宙中一半的智慧生命,只是因为这是缓解生态危机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因为他看到宇宙中没有任何智慧文明能够通过温和的自我调控来实现与自然环境的高度和谐。尽管外形凶悍、战斗凶狠,但灭霸内心是知性和冷静的,没有任何歧视性立场和迫害欲望,也不漠视生命或嗜血好杀。他的目标是完全随机选取的,且只取必要的数量。他对来自异族的养女怀有真实的爱,同时丝毫不留恋技术文明或权势地位,在恢复了宇宙的生态平衡后,他选择在一个木棚里做隐居的农夫,欣赏夕阳下的秀美山川,一如在瓦尔登湖边隐居的梭罗。在影片中,无人能有效地反驳灭霸的生态伦理观。他希望解决的生态危机难题,其实也是全人类面临的难题,直至续集《复仇者联盟4》结束,灭霸虽死,但他寻求生态平衡的逻辑性和公心仍然难以被否定。养女卡梅拉对他喊道:“You don’t know it!” 意思是你是人不是神,不能断定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但这一呼声缺乏逻辑力量,反倒是灭霸体现出的超越个人情绪和私利的高道德感在很大程度上使故事中的英雄们都相形见绌。如灭霸这样以完全理性的方式捍卫生态主义理想、同时在精神上又无明显瑕疵的反派形象,在文艺作品中并不多见。尽管这一角色并不完美,却在观众中获得了不少同情与认可。科幻题材的故事引导观众面对冷峻的生态现实,既揭示了主流生态思想在科学上的局限性,也戳破了某些貌似天经地义的人文主义道德壁垒,而影片中的相关角色能够得到公众相当程度的认可,标志着全社会对生态伦理的思考走入了新的阶段。
三、打破人与人性的旧定义,重新描绘人在物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
在美国,物质生态批评的思潮方兴未艾,批评家号召人们认识和尊重一切物质的主体性,努力理解物质自身的叙事能力及其与人类的互动,否认只有人的意识有生成故事的独特能力,并由此消解人类高于自然物的地位。其实在人类与非人物质世界的互动关系这个议题上,科幻故事的探索和思考更加超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科幻电影中有关人工智能和人体改造技术的科研伦理辩论,早已不断抹平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界限。在本世纪初的《人工智能》《我,机器人》等影片中,模仿人类而生产出的机器人,因为与人类大脑拥有高度一致的物质基础和运行原理,所以不仅可以完整地继承人类的思维,而且能够产生与人类相似的情感,由此将人性并不为人类所独有——或者并非只有人类生养的后代才能作为人类——的问题呈现在观众面前。此种观点意味着,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众多形态演变的普通产物之一,不具有天然的特殊地位,继而引发人类个体是否可以被随意复制和改造等一系列伦理讨论。
在近年的《升级》《阿丽塔:战斗天使》等影片中,主人公为了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需要让身体接受技术改造,与各种机器材料和人工智能合为一体。这种边界大幅扩展的人体也被称为“后人类”身体。人类的意识可以在各种物质媒介中保存和流传,而与人结合的物质材料也自然而然地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其中的人工智能力量可以与人类意识平等合作,甚至能够启发或囚禁人类意识,最终让人类意识在没有清晰自觉的情况下彻底改变原有的面貌。在影片中,这种改变有时呈现为一种必要的生态进化,如果不接受它,人类就难以在剧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有效地生存。而《超级玩家》则延续《入侵脑细胞》和《黑客帝国》的设定,并将其推进到极端,直接描写人类个体的思想意识可以脱离血肉之躯而长期存活于数码技术造就的虚拟世界中,并构建整个虚拟社会。这将意味着生物体只是人的物质存在的可能形态之一,而对人来说最有意义的精神存在,亦即人性之所在,是可测量和可编制的。
人类对人性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在神权时代,宗教认为人具有源于神明的灵性,因而在各种故事中,人性里总有神性的影子。人文主义复兴并长期发展后,白板理论逐渐占据强势地位,即认为人类具有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意识能力,但出生时头脑是空白,具备着被教育塑造成多种面貌的可能性。近代一度兴盛的自然主义文学,曾质疑道德秩序的力量,认为人类个体大都不能摆脱动物性本能的影响,必然走向堕落。而现代生态主义思潮中,各个不同流派对人性的认识则受到诸多历史观念的影响。其中,被学界视为非主流的“科学生态批评”理论家最推崇用自然科学知识来指导生态价值观。他们认为人类神经系统中首先包含着长久的自然进化史所塑造的生物本能,这种与生俱来的属性也是人与动物相似的地方,同时人的生存模式也受到人类社会特有文化的长期锻造,因而现今人类的一切思维和情感方式,是生物本能和社会文化在互相碰撞中不断进化的结果。由此可见,科学生态批评对人性的看法是高度物质化的,它对人类生存历程的解释,很容易与前文所述的科幻故事中的观念相接轨:即人类是从简单物质形态逐步进化而来,未来也可能会继续演变为其他的物质形态。人类的意识是人体物质形态复杂演变的阶段性结果,个人未必能够充分地了解和掌控人性中的一切,人性也不会始终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定义,而是随着物质世界的运行而发展。这样的人性观将人类与周围的物质世界——包括自然环境与人类改造的环境——天然地联结为一体,纳入进化史的视野中,为后工业时代背景下人与其他自然物之间的生态性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而科幻题材电影无疑最生动具体地展示了这种空间。
结 语
现代美国科幻题材影片受到西方社会流行的科技文化和当地发源的生态主义思潮的共同影响,表现出依托前沿科学知识的视角来审视和探索新生态观念的突出特点。这些影片突破传统作品的故事框架和价值判定,在人类如何认识自然生态、如何具体地处理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以及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而深刻的新探索,对生态主义思潮中的多种生态伦理观做出了呼应、碰撞或超越,一边用艺术的想象力拓展出独特的实验空间,一边用更加贴近科学真相的思维,为当代生态思想的发展和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