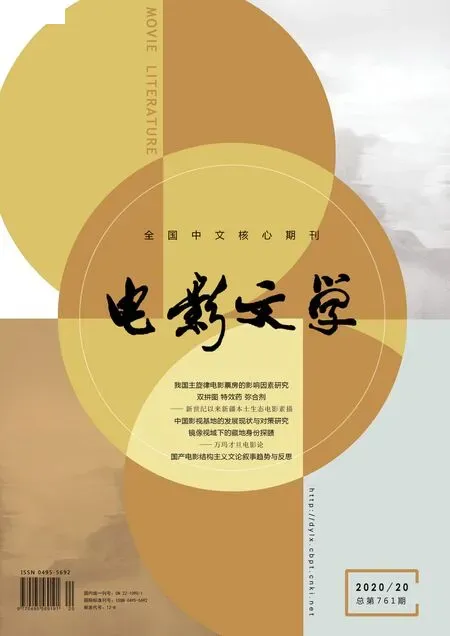禁忌之物:安哲罗普洛斯的“边界”符号
程鹏飞
(宜宾学院 文学与音乐艺术学部,四川 宜宾 644000)
边界是安哲罗普洛斯(以下简称“安哲”)电影的重要母题。在安哲电影中,边界往往表现为一种时间或空间的界限,比如国境之界、跨年跨世纪之界、生命边界等。借助具体的时空边界,安哲电影讲述了关于国家、民族、人生的阻隔与跨越的主题,这是有关安哲电影的边界研究中所达成的基本共识。在社会学中,边界是人类对事物获得基本认知的基础。按照事物表现出的不同特征,边界将事物人为地区隔开。换言之,边界一定是有两端的。跨越边界就是打破阻隔,由此端进入彼端。对安哲电影中边界的讨论往往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安哲罗普洛斯把对历史、生命、时间的整合性思考融入影片当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思维领域,即探讨一种人为的地理疆界对生命的束缚与阻隔。
但在精神分析学者眼中边界并非区隔两端,而是变成了更为主观的东西。齐泽克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不是被某条界限所分割开的两个层面,我们仅仅拥有现实与其界限——深渊与现实结构周围的虚空。在齐泽克看来,边界标志着某种根本的不可能性,从现实层面上它不可能被跨越,唯有将边界之外转化成一种符号性的被禁止的客体才能被获得。从主观层面来看,安哲电影中的边界是人物追寻不可能之物的符号化。与那些相信人定胜天的英雄人物相比,安哲电影中的人物是在事先感知到边界不可跨越的前提下,依然将其转化成一个符号性的被禁止的客体,最终踏上各种不可抵达的旅程。通过展现无法跨越边界的人物的旅程,安哲电影呈现出独特的悲情史诗的风格。
一、无法跨越的非客观边界
国境之界是安哲电影关于空间边界的集中讨论。在《鹳鸟踟蹰》《尤利西斯的凝视》《雾中风景》《永恒一日》《哭泣的草原》《时光之尘》等电影中都涉及了“边境”的主题。在这些电影中,“边境”往往以非常具象化的方式呈现。《鹳鸟踟蹰》中,希腊与阿尔巴尼亚的边境线是以三条颜色不同的线来呈现的。蓝线是希腊的国境线,红色是阿尔巴尼亚的国境线,白色代表了中间地带。《永恒一日》中,希腊与阿尔巴尼亚的边境被铁丝网隔开。而在《时光之尘》中,一条路障横在俄罗斯和奥地利之间。
从物理空间上,实体的线、铁丝网、路障作为“边境”的界限将本来相连的空间一分为二,成为此空间和彼空间;从政治形态上,“边境”的一边是共产主义,另一边是资本主义;从生存空间上,“边境”的一边是战争,另一边是和平。这些“边境”设立的前提是存在两种不同的空间形态,“边境”是一种形态的结束和另一种形态的开始的地方,它维持着两种形态各自的独特性,“跨越边境”就意味着由一种形态进入另一种形态。如果从阿尔巴尼亚跨越边境进入希腊,就是从战争的空间进入和平的空间,饱受战乱的阿尔巴尼亚难民就应该获得和平的生活,“边境”就是一条“和平之界”;如果从俄罗斯进入奥地利,或者更具体来说,《时光之尘》中的艾蕾妮是从俄罗斯到美国,雅各布是从俄罗斯到以色列,这条边界的跨越应该意味着流放生活的结束和美好家园生活的开始。然而在安哲的电影中,这种跨越实体边界的变化并没有发生。
《永恒一日》中,穿黄衣服的小男孩来自阿尔巴尼亚,他跨越边境从战争之地阿尔巴尼亚来到和平之地希腊,但迎接他的并非和平安宁的生活。在希腊,他被警察追赶,被人贩卖,一起来的伙伴在街头丧生,他的命运并没有因为跨越边境而改变,边境线并非真正的“和平之界”。齐泽克这样描述这条边界,它是恐怖的,能致人于死地,然而同时又魅力无穷。我们在接近它的过程中,祉福随时可能从天而降。然而,界限相对于地域具有优先性,我们仅仅拥有现实与其界限。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边境的铁丝网尽管客观上划开了两个不同的空间,一边有战争,另一边没有战争,但对于饱受战乱的小男孩来说,对和平之地的向往使“和平之界”符号化为边境上的铁丝网,只要跨越了铁丝网,和平生活就会来临。他并不知道和平之地是不可能之物,“和平之界”也仅仅是现实周围的虚空。所以,当小男孩跨越了铁丝网来到希腊,和平之地并没有到达,“和平之界”依然存在于现实的周围。现实与边界的关系就像影片中在铁丝网上攀爬、跨越的人一样,他们永远在试图跨越一条边界,却也永远无法真正地跨越,因为这条边界并非客观存在。
除了空间上的边界,时间的边界也同样如此。在《亚历山大大帝》《流浪艺人》《永恒一日》《时光之尘》等影片中,时间的边界具象为年岁之交、世纪之交、人生终点等各种形式。在《时光之尘》的结尾,历经半个世纪沧桑巨变的三位老人——斯皮罗、艾蕾妮、雅各布来到20世纪的终点。收音机里传来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斯皮罗和雅各布倒上酒,庆祝新世纪的到来,艾蕾妮突然走下病床,埋怨自己竟还没有给家人们做饭。这些景象似乎表明,家人们在新的世纪将不再经历分别,将迎来希望的生活。然而事实上,这条边界也并不存在,三人最终都无法跨越这个现实的边界。雅各布跳河自杀,艾蕾妮在床上安静地死去,只有斯皮罗在大雪中与小艾蕾妮一起迈向新的世纪,这当然并非现实,后面我们会提及,这只是安哲电影解决边境困境的一种象征性手法。新世纪的起点并非现实的终点,现实的边界也就不可能被跨越。所以,安哲的电影经常会呈现大量的跨越仪式——舞会、演出、婚礼等。与边境线上阿尔巴尼亚人攀爬、跨越的场景一样,人们仅仅停留在跨越时间边界的仪式中。
边界是人为的产物,是非客观的。在安哲的电影中,非客观的边界具象化为国之边境、年岁之交、世纪之交、人生终点等物质化的界限,将不可能之物转化成被禁止之物,用真实向符号的转变赋予“跨越”动作以意义,以此来彰显生命在时空旅程中的价值内涵。
二、人物在边界上
在《永恒一日》的开端,影片展现了斯皮罗的一个梦境:小伙伴给小亚历山大讲述了岛上古城的传说,并邀请他一起去古城探险。当亚历山大偷偷跑出家,准备跟小伙伴一起游向海岛的时候,被母亲的呼唤声叫回。影片用一个童年的梦境开端,昭示着时间的不可回溯。当斯皮罗从梦中惊醒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意识到了时间的不可跨越。在其他安哲作品中,类似的人物也在影片的开始就意识到了那个不可能追寻到的结局。《雾中风景》中的姐弟俩在一开始就错过了一趟火车,两人站在空空的站台上,陷入久久的沉思。《流浪艺人》中的第一个场景就是一个艺人报幕,而即将演出的是一个悲情故事《牧羊女伍尔夫》,接着就是两天没有休息的艺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艾吉翁车站。人物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对虚幻结局的预知是安哲赋予其影片的重要特质。即是说,人物已经知晓了边界的不可跨越,却依然要踏上追寻的旅程,这与那些坚定地相信边界之外拥有理想之地的人物相比,更具一种悲情的意味。
事先预知到追寻的无果让跨越边界之后的结局变得不再有吸引力。追寻的过程成为表现的重点,“跨越”动作的仪式化内涵成为边界主题的真正价值。齐泽克在分析弗里茨朗的《恶人牧场》时认为,影片中所有关键性的激烈对抗场面都发生在那条狭长的山道上。这绝非偶然。那条山道就是一道边界,它分隔开日常现实与“她”(指统治着边界之外国度的神秘女王)所统治的山谷——换句话说,所有重要的情节都发生在从现实到幻想的“他处”之间的通道上。安哲电影中的人物在将不可能之物符号化为被禁止的边界之后,所有的追寻过程也就发生在这条边界之上。于是,旅途、历史的碎片成为边界的具象化呈现,通过人物游走、舞蹈、凝视等仪式化的“跨越”动作使观众获得对时空边界的若即若离的感知,呈现出一种基于现实边界的生命喟叹。
(一)旅程作为边界
在安哲的电影中,街道、公共场所承担了大量的叙事内容,是人物旅程的重要空间。在旅程中,安哲电影中的人物是用行走的动作再现了时空的边界。
《流浪艺人》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艺人们巡回表演的旅程中,从艾吉翁车站到艾吉翁车站,艺人们在希腊大街小巷的游走串联起希腊十三年的历史。影片的开端,1952年11月,艺人们走出艾吉翁车站,他们已经两天没有休息,非常疲倦,1952年是帕帕戈斯元帅开始执政的一年,希腊从此进入到白色恐怖时期,而在影片的结尾,当艺人们走出1939年的艾吉翁车站时,希腊又进入到德国法西斯占领时期。在这个伟大的历史回环中,艺人们一直行走在独裁统治的边缘。从流浪艺人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艾吉翁车站开始,那个跨越“军政”统治的游走动作就反复出现在希腊的街道上,艺人们走过的路途成为从专政统治(现实)到自由民主(他处)的边界。进一步说,在艺人们经历的十三个春夏秋冬中,影片仅仅呈现了冬季的旅程,冬季的阴冷潮湿是对白色恐怖社会气氛的最佳诠释。电影现象学学者劳拉·马科斯说,很多我们所获取的知识“不是经由视觉模式,而是经由身体接触而来”的,“某些经验更可能以非视听性的触感、闻感和味感‘记录’下来”。艺人们在一路旅程中所感受到的希腊街道上的“潮湿”记录了跨越“军政”统治边界的过程。
《雾中风景》是另外一个讲述旅途的故事。在前文中已经提及,影片开始错过的火车已经预告了姐弟俩寻找父亲的无果,但二人依然要踏上一条虚幻的去往德国的旅程。在旅程中,姐弟俩在大雪里逃出警察局,在路边目睹了一匹马的死亡,遇到了好心的年轻人奥瑞斯特斯,姐姐乌拉被卡车司机强暴……姐弟俩寻找父亲的旅途被符号化为一条成长的边界,在这条边界之外,是姐弟俩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但一次又一次在这条边界上经历的身体创伤让他们感知到边界之外的不可获得。
(二)历史碎片作为边界
齐泽克在《如何令身体陷入僵局》一文中描述了一种西方故事常见的神话般的叙事。“这些作品都叙述了一场深入黑暗大陆心脏的探险,在探险开始之前,没有哪一个白人曾经涉足此地。旅行者们受到某些晦涩难解、歧义丛生的符号片段——瓶子里的字条、没被烧完的纸片,或者是某个疯人的呓语,暗示着在某个边界之外,美妙与/或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的引诱而开始了这段险象环生的旅程。”在安哲电影中,残破的建筑、古希腊雕塑、旧的电影胶片正是这些晦涩难懂、歧义丛生的符号片段,这些历史的碎片是通向伟大希腊的通道。
在《流浪艺人》里,剧团团长在一个残破的墙根之下被德军士兵枪杀,其他的剧团成员被德军抓住后,准备枪杀的地方是在古希腊神庙的残垣断壁之中。残破是时间的产物,那些残破的建筑一定都经历过初建时的辉煌,就像曾经无比璀璨的古希腊文明,它们并非本来就是残破的,历史曾经见证过它们的价值。但经过多次的战争、政治变革、社会运动,那些炸弹的碎片、普通人的鲜血在每一块砖瓦中落下痕迹,这种残破正是人物试图跨越时间边界的身体创痕的映照。
历史碎片的边界呈现是在被凝视的动作中完成的。《永恒一日》中,亚历山大向小男孩讲述了一位19世纪诗人索罗慕斯的故事,这位伟大的希腊诗人作为历史的碎片出现在亚历山大的视野中,亚历山大凝视着索罗慕斯,也凝视着伟大历史的边缘。对于凝视的动作内涵,拉康认为,当人们在注视某物的时候,主体也在被看之中,这种被看并不是真正地处于某物的“视线”之中,而是主体对于他者的欲望,也就是想象,使主体自身“摇摆不定”。在亚历山大的凝视中,他看到的是历史上那个伟大的诗人索罗慕斯,同时他还看到的是一个身患绝症的失败的写作者,也就是他自己,通过凝视索罗慕斯,他将自我投射进希腊的伟大历史中。
除了《永恒一日》中的索罗慕斯外,还有《雾中风景》中被注视的雕塑、《尤利西斯的凝视》中导演要寻找的默片胶片等。安哲电影中人物对历史碎片的凝视源于残酷的现实——或是政治的,或是人生的。观众也通过人物的凝视来凝视影片中的人物,将自身的现实投射进影片的时空中,以获得对现实边界的感知。
齐泽克说,人一旦主观地在现实边缘给划定了一条界限,那么,界限之外的不可能之地便突变为具有可能性的禁忌之地。安哲电影中的人物正是对禁忌之地若有若无地感知完成了跨越边界的旅程,观众借助人物的身体共同感知时空的边界,获得带有创痕的人生体验,这是安哲电影的主要价值。
三、身体对边界的跨越
如果我们在现实这一端走得足够远,那么我们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到了另一端,进入了纯粹幻想的领域。在心理体制中,“现实”是“多余的”的东西,是主体“弃绝了”它自在的自我障碍物。幻想所呈现的现实是作者无法填补的自身要求的障碍物的“外部化”。虽然禁忌之地是永远无法到达的,安哲却将身体作为媒介创造出一个幻想的现实以弥合不可能到达的边界,这个通过仪式化的动作和时空并置的方式创造出来的超现实时空最终完成了对边界的象征性跨越。
在《时光之尘》的小酒馆段落中,导演A带着中年斯皮罗来到小酒馆寻找艾蕾妮,但进入小酒馆之后,中年斯皮罗变成了老年斯皮罗、新年夜,他跟艾蕾妮、雅各布一起来到小酒馆,画面慢慢跟随老年斯皮罗,艾蕾妮和雅各布渐渐成为背景。接着,中年斯皮罗的画外音响起——“我们到达多伦多时,正值午夜”,但画面中依然是老年斯皮罗。此时,时空开始发生混淆,老年斯皮罗开始与中年斯皮罗、中年艾蕾妮对话,他看着艾蕾妮歇斯底里地摔砸着东西,他准备离开,艾蕾妮追到门口。此时,一个颇具奇观性的画面出现——老年斯皮罗与中年艾蕾妮拥吻在一起,不同时间的两个人物同时出现在一个空间中。时空的并置在中年斯皮罗一进一出小酒馆的过程中发生,时间与空间的边界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得以跨越,而这个象征性的符号就是老年斯皮罗的身体。安哲借由人物的身体作为媒介进入幻想的领域。在安哲的电影中,诸如此类的时空并置经常出现,成为安哲电影解决边界困境的主要方式。
如第二部分所述,人物通过身体完成了对时空边界的感知,逐渐确认了从一开始就已经意识到的跨越边界的不可能性,为了实现边界的跨越,身体作为媒介以各种姿态将不同的时空并置,创造出一个个奇观化的场景。安哲以想象的身体的在场试图弥合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在《时光之尘》的小酒馆段落中,老年斯皮罗走进小酒馆的时间是新年夜,是新旧交替的边界。老年斯皮罗跨越了这条边界,安哲用老年斯皮罗身体的在场弥补了中年斯皮罗的不在场,当中年斯皮罗跟艾蕾妮走出小酒馆时,斯皮罗与艾蕾妮的这段时间被重新缝合。
在安哲电影中,主要通过仪式化的动作和时空并置完成对边界的想象性跨越。
(一)仪式化动作
仪式化是人类学中的一个术语。当代人类学将人类文化分为观念、行为、物质三种范畴。仪式既不是物质范畴的事物,也不是存在于人脑中的观念,而是付诸实践的一种行为,是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安哲电影中的仪式化行为主要表现为跨越边境、跳舞、婚礼等。
1.跨越边境。人类学英国曼城学派代表人物维克多·特纳把人类的社会关系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日常状态,另一种是不同于日常社会生活及社会关系的仪式化状态。仪式是一种处于稳定结构交界处的“反结构”现象,仪式过程就是对仪式前和仪式后两个稳定状态的转换过程。在《永恒一日》中,斯皮罗将小男孩送到边境,小男孩给亚历山大讲述了越过边境雷区的经历。他蹲下身,做一个扔石头的动作,站起来,然后再蹲下。通过小男孩模拟跨越边境的动作将他离开阿尔巴尼亚和将要回到阿尔巴尼亚两个时间并置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边境。第一部分已经论述过,边境线并非客观的边界,所以小男孩再现的是跨越心中的“和平之界”的场景。从现实层面看,小男孩跟表哥跨越边境线时是在场的,但从跨越非客观的边界来看,小男孩是不在场的。因此,小男孩通过模拟跨越的动作让自己在跨越“和平之界”时在场,以实现对非客观边界的跨越。跨越在《雾中风景》中又表现为被亚历山大叫作“海鸥”的人所做出的飞翔的动作。
从单纯的意义上,“仪式是一种无法摆脱的重复性活动———通常这是社会基本‘需求’的象征性戏剧化形式,无论这种‘需求’是经济的、生物的、社会的还是性欲的”。穿过形式的层面,跨越边境的行为成为打破阻隔、渴望沟通的象征。
2.跳舞。随着社会的发展,当神圣的救赎沉沦为人的世俗欲望追求时,日常生活仪式成为人类自我救赎的新方式和象征性的交际行为,也成为一种传播方式。跳舞便属于这种日常的生活仪式。
跳舞在形式上呈现为一种欢快的节奏,成为变换影片节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亚历山大大帝》中,第一场戏就是贵族们迎接新千年的舞会,在后面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共产村”之后,多次出现载歌载舞的场面,从节奏的角度上说,是舞蹈结构了整部影片。
在意义的层面上,跳舞依然强调沟通,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就跳舞本身而言,在舞蹈中人与人之间暂时摒弃了分歧和隔阂,在动作上达到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在安哲的电影中,跳舞常常与跨年同时呈现,比如《亚历山大大帝》中新千年的舞会,《流浪艺人》中1946年的新年舞会,《尤利西斯的生命之旅》更是通过跳舞连接了几个时代。跳舞成为一种打破时间界限的象征。
3.婚礼。《亚历山大大帝》《养蜂人》《雾中风景》《永恒一日》《悲伤草原》等影片中都出现了婚礼的场面,其中,《养蜂人》又是以婚礼开场。婚礼在形式和意义上的功能与跳舞是相同的,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根纳普在《通过仪式》(又译作《人生礼仪》)一书中开宗明义:“任何社会里的个人生活,都是随着其年龄的增长,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序列。”婚礼便是生命礼仪中连接两个人生阶段的“阈限期”。其意义呈现为打破人生的界限。
(二)时空并置
《永恒一日》的开始,通过梦境斯皮罗就已经意识到跨越时间的不可能,但当斯皮罗来到医院看望母亲时,他还是借由自己老年的身体实现了时空的并置,弥合了时空的边界。母亲拨开窗帘,呼喊着“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吃饭了……”,这正是影片开始时,正在海边玩耍的小亚历山大听到的母亲呼喊他的声音。母亲的声音作为媒介,使得儿时的时光在人生即将走向终点时再现,老年的斯皮罗轻声回应着母亲,仿佛听到儿时大海的声音。此外,声音有时还会以戏中戏的方式实现时空的并置。在《流浪艺人》中,俄瑞斯特斯来到旅馆,第一次见到妹妹,说出的第一句话是“啊,美丽的眸子”。这是艺人们经常排演的剧目《牧羊女伍尔芙》中的对白,戏剧中的人物以声音的形式穿越到现实,将现实时空和戏剧时空并置在一起。
在多数情况下,人物作为时空并置的媒介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混合了外表、动作、声音等各个方面。比如前面提到的《时光之尘》中的小酒馆段落,再比如《永恒一日》中经典的公共汽车段落,生活在几个不同时代的人物都汇聚在这一辆公共汽车中,而且彼此之间在表情、动作、话语上都发生交流,时间在这里完全失去了界限。就像是在一个容器中倒入不同颜色的水,颜色慢慢融合,最后混合成一种颜色。其他还有《尤利西斯的生命之旅》中新年舞会的场景,《流浪艺人》中共产主义阵营和资产阶级阵营在广场上游行的场景,等等。
从形式的角度来看,延续的时间和完整的空间发生突然的断裂,然后相互拼接在一起,往往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种是创造奇观,一种是创造意义。安哲在电影中创造了一个个奇观化的时空,在这些时空中,时间与空间的边界被抹去。人物跨越了不存在于现实中的彼岸,进入了符号性的幸福世界。
作为信仰东正教的民族,安哲罗普洛斯用超现实的方式谱写着本民族的命运悲歌。这种对悲剧命运的探讨并非仅仅对边境线以及分割时间的历史节点的批评,而主要源自于人物对非客观边界的不可跨越。尽管如此,安哲电影中的人物依然要踏上跨越的旅程,追寻那个可能的“禁忌之物”。人物在感知不确定性边界的过程中收获的身体的创痕成为安哲电影诗意的来源。最后,安哲电影通过创造一个时空并置的奇观化时空象征性地完成了对边界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