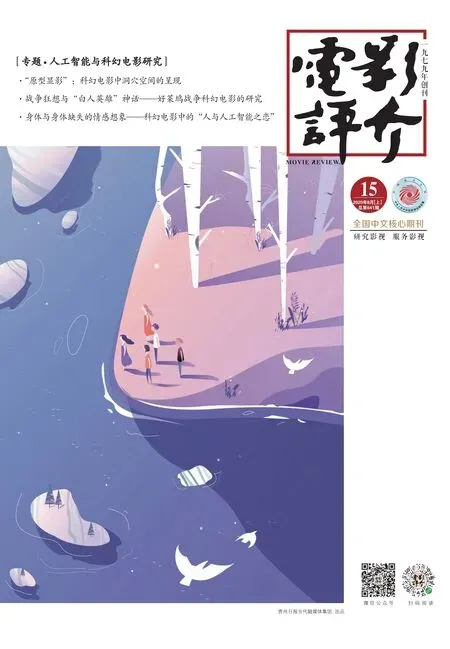《第三度嫌疑人》:对话异化与“悬疑”
莫韦姝
是枝裕和的《第三度嫌疑人》(2017)上映以来,其另类“悬疑”颇受关注。影片第一幕便是嫌犯三隅河边杀人焚尸且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悬疑犯罪片惯用的“悬疑-侦探-揭露”在银屏启幕之时便被打破。若说有“悬疑”,那么,是贪财生歹念,还是因仇起杀意,或是为财宁当刽子手,抑或是出于莫名“正义感”而行凶?如此的安排,让三隅的犯案动机“真相”,成为该片的唯一“悬疑”。案件受理人(律师、检察官、法官)、出庭证人(美津江、咲江)围绕“悬疑”展开对话,但又各有考量,且嫌疑人三隅数易供词,致使本该平等、多元且具有未完成性的对话异化。因此,愈临近片末死刑定谳,行凶动机真相却愈加模糊,“悬疑”非但未被“揭露”,反而再添“悬念”,客观上形成了貌似可抽丝剥茧却仍有“悬疑未解”的艺术效果。巴赫金(M.M.Bakhtin)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文论家之一,其对话理论有助于揭露对话异化内在机理,进而有助于“悬疑”解读。
一、三隅:平等对话之异化
是枝裕和较为关注小人物,处女作《幻之光》(1995)中的由美子命运多舛,成熟之作《无人知晓》(2004)中的单身母亲福岛惠子及四个子女孤苦无依,《第三度嫌疑人》中鳏夫三隅的境遇则尤甚。他出身社会底层,父母妻子无故相继离世,后因杀人入狱三十年,本来仅靠血缘维系的父女亲情又化为难以承受的仇怨,无异于孤家寡人,刑满获释后在食品厂忍受压榨谋生,后怒杀社长,再次接受审判,是被边缘化的小人物的典型。影片通过案件受理人重盛、摄津、实习生、证人等的视角来展现三隅的生存状态,对话是主要方式。巴赫金认为,地位平等、互相尊重是对话展开的前提,惟其如此,对话双方的独立意识及个性方能保全,否则将陷入独白境地。此观点对研究三隅话语与“悬疑”的关系极具启示意义。
从片中可知,三隅寄身食品厂,艰难维持生计,但作为廉价劳动力,又不得不忍受社长压榨,地位不平等是很显然的。不平等甚至一度成为重盛“法庭战术”中“仇杀”推断的“力证”,其与三隅的对话也自然被异化。细究二者对话可知,这种平等对话异化背后的主因则是三隅身份定位飘忽不定,游离于杀人嫌犯、父亲和底层小人物之间。他配合律师取证,先是支持“仇杀论”,后又顺着媒体的雇凶杀人报道,配合辩护团队“嫁祸”受害者夫人美津江,随即被当庭驳回。未经训练的观影者都能看出此举与杀人嫌犯身份的关联。“嫁祸”不成,但又揭开了三隅作为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真实,即他不得已为封口费而昧着良知生活并深感痛苦和无奈。此时,如他所言,“比起在工厂里靠封口费活着,不如呆在监狱不用骗人来得轻松”,不管其证词真实性如何,他埋怨“生命被挑选着!毫不讲理地”,自己总是那个“被制裁的人”,这能部分反映处于底层的三隅们被边缘化,无法与社会对话的窘境。若沿着这一思路审读剧情,那么,三隅最后翻供所说的,摄津、检察官曾明示承认杀人可免死,这从杀人者急于脱罪求生的角度看,也具有逻辑和事实合理性,何况片中律师、检察官与法官之间也确实存在着“和稀泥”的“默契”,这也不免为诱惑认罪留下想象空间。
不论是哪种犯案动机,都反映着再次面临制裁的底层小人物的真实状态:生活既是独白。对三隅而言,面对命运的挑选是如此,面对本该执着于真相去维护正义的律师、检察官、法官更是如此。毕竟,一方面操控命运的人无法找到,便无从对话;另一方面,上述案件受理人们大多都镶嵌在上了功利“发条”的机器上,连有一丝对话欲望的重盛也不例外,走心的对话更无从谈起。这种两不相顾的对话,无异于自说自话的独白,重要原因在于,作为律师的重盛根本无法跟上三隅身份变更的节奏,更何况重盛接手案件之初便认为“为了辩护,理解共鸣什么的是不需要的……又不是要交朋友”,也即是说,一开始他眼中只有杀人嫌犯三隅,而感受不到底层小人物三隅的痛苦,对三隅所说的“付房租是件很开心的事……因为监狱不需要房租”,他无法理解,更无法感同身受。父亲身份或许是二人能达成共识的唯一契机,但重盛为找求情证人,贸然寻访三隅女儿,这本已让三隅错愕,后又将早前唯一有可能与之平等对话的社长女儿咲江的交往作为“仇杀”推断的证据,甚至让其在庭审上如实陈述不堪的受辱往事,这又让三隅内心块垒再起。二人最后一次会面时,重盛说:“你否定杀人,咲江就不用说那些痛苦的证词了。”尽管三隅对此矢口否认,我们无从了解其翻供的真正动机,但在这两次渐次深入的对话中,三隅显然是以父亲身份参与。遗憾的是,这种对白仅有对话之形,却充斥着独白内核,是异化了的对话。巴赫金指出,“独白是完篇之作,对他人的回答置若罔闻,它不期待他人的回答,也不承认有决定性的应答力量”。重盛跟不上三隅身份变动的节奏,自然无法对其问题做出合理“应答”,他所有围绕“法庭战术”取证的对话,都具有独白的特质。用巴赫金的话说:“独白……某种程度上把整个现实都给物化了。独白觊觎成为最终的话语。它要把被描绘的世界和被描绘的人物盖棺定论。”对深谙“法庭战术”的重盛而言,其眼中的三隅无疑被物化了,就如同渡边老警长所说,三隅“就像空的容器一样”。如果说此片有存在主义倾向,那么“他人是地狱”的内在本质则是对话不平等,对话者身份被忽视,“应答力量”无法被触及。这也是未解“悬疑”的内在机理之一。
二、案件受理人:多元对话之异化
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巴赫金曾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艺术家……具有一种天赋的才能,可以听到自己时代的对话,或者说得确切些,是听到作为一种伟大对话的自己的时代,并在这个时代里不仅把握住个别的声音,而首先要把握住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关系、它们之间通过对话的相互作用。”富有对话性的文本亦应当如此。是枝裕和曾公开承认创作《第三度嫌疑人》旨在反思社会问题,因此,如果将此作视为新历史主义文本,那么应能听到当代日本的多元社会声音之间的对话,就如同后现代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社会语境本身就是文本,或者说只有通过文本才能理解社会语境”。惟其如此,方能理解《第三度嫌疑人》的“悬疑”机理。细究银幕作品可发现,多元对话被案件受理人阻隔或扼杀是“悬疑”构成的深层原因。
首先,重盛阻隔多元对话。重盛在首次会面后便认定“他看起来不像是希望减刑的样子”,即便如此,他介入对话伊始也未能给三隅更多的对话可能性。要知道,作为律师,他和摄津一样,都有先在的“法庭战术”目标预设,如他所说“先不管证据如何,作为辩护方向,目标在那里”,于是便作出了“因开除生仇怨”的“仇杀”推断,为此而“有的放矢”地收集证据。这一推断直接阻隔了其与三隅展开多元对话的进程,也延缓了犯案动机的探索进程,而有趣的是,虽然重盛对三隅的多元动机“后知后觉”,但三隅犯案的社会背景却经由重盛的视角得以展开,如与其同道的实习生了解到社长抓住了三隅们的弱点,让其忍受压榨而无法反抗;渡边老警长与重盛会面时则交代了三隅头次犯案的社会背景:失业者大量增加,人们向黑道借高利贷;在与接手过三隅旧案的父亲争辩“人性是否可改变”的对谈中,重盛则认为“人性可改”,触及日本法学界关于死刑废存的讨论。此后,他与三隅对话一步步深入,直至升华为“真相”与人性的探讨。因此,从本质上看,从认定三隅杀人到配合三隅翻供否定杀人,这已使得对话的单一性发生了变化。从这一角度上看,重盛则是银幕作品文本与社会多元声音相衔接的一个纽带,但他又集律师、父亲及人性探究者三重身份于一身,在审判过程中,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无法从律师身份中完全剥离,其对多元对话的阻隔程度便与其从审判“功利”机器中的剥离程度形成负相关,越是接近后二者,则越能彰显多元性。
其次,摄津、检察官、法官扼杀多元对话。作为三隅案的首个受理律师,摄津自始至终都认定三隅有减刑意愿,于是一开始便让其配合“谋杀”推断且认罪求免死。这种“法庭战术”扼杀了探讨三隅复杂犯案动机的可能性,为其反复修改供词埋下了伏笔,最后不得已才请精于此道的重盛担纲。细心观众应能发现,即便摄津退居二线,他作为审判“功利”机器,其单一对话立场一直都影响着案件审理,如考虑美津江合谋方案时,其虑及法官“颜面”而不甚支持,之后三隅彻底翻供时,更是极度厌烦,认为三隅和其他死刑犯一样,“审判一开始,死刑近在眼前,突然就害怕了”,他甚至指责重盛:“像你这样的律师是有碍于罪犯承认罪行的,给法官很差的印象”。此番言论与女检察官早前批判重盛的言辞如出一辙。可见,摄津实际上已与力主简化办案程序的检察官、法官达成了“默契”,如女检察官对前来查验物证的重盛所说,“都招供了,不要多管闲事比较好……”;再如法官在庭审时指出,“本次审判应该对被告的犯人性没有疑问才对”,而在休庭闭门会议期间,法官暗示为“体谅审判员们”“也能节省诉讼经费”,主张继续按原计划庭审。法官的眼神则成为大家达成共识的暗号,实习生能觉察到这种“不谋而合”的“默契”,却不明就里,摄津则解释说,“法官给的眼神的意思是,事到如今,从头开始,也不会改变结论。不按照日程审完一定数量案件,会对他的评价产生影响的。虽然立场不同,大家都坐在同一艘叫做司法的船上。”如果说是“船”,那么这或许不是日本法律的诺亚方舟,而是沉沦于该案“真相”及社会现实乃至人性之海的一叶扁舟。这或许正是是枝裕和关注社会、思考法律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
若说重盛在类似于“盲人摸象”的游戏中探讨真相,那么摄津、检察官和法官则在扼杀多元声音,埋没真相,而三隅的反复,与其说是内心纠结,还不如说是对单调“法庭战术”辞令的反叛。世界是多元的,声音亦然,对多元声音的探寻、躲闪、绞杀,正是《第三度嫌疑人》“悬疑”产生的重要机理。
三、出庭证人:未完成对话的异化
“未完成性”是人存在的特性,也是对话的特性,如巴赫金所言,“对话是不可完成的,只要生存着有思想的和探索的人们,它就会持续下去。对话的终了,与人类和人性的毁灭是同义语”。但需指出,这是最理想化的有益于真理探讨的对话,以柏拉图所记载的苏格拉底的对话为典型。但在现实生活中,到处存在着未完成性对话的异化。这种异化要么表现为采用模糊话术,使得对话无法深入,要么是对未完成性的直接扼杀,导致对话终止。这在《第三度嫌疑人》出庭证人美津江及其女儿咲江的对话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透过这些话语,可管窥该片“悬疑”产生的机理。
美津江作为受害者的妻子,其出场甚少,但每次出场都给观众留足了想象空间,重要原因在于,她采用了模糊话术,语言充满模糊性,导致对话无法深入,却“悬疑”颇多。如其第一个对白:“不要说出我的事,我不会做对你不利的事的。”这是案发后美津江给三隅发的短信,显然,“我的事”“对你不利的事”在片中便存在很多解读版本,因此,被重盛团队当作美津江“合谋”证据加以利用,而检方则认为此证据不足以采信,法官极力调和,最后“同意但表示与案件没有关联性”。庭审时,美津江则否定短信为自己所发,咬定自己死去的丈夫为发送者,又确切所言之“事”是指“工厂的事”,而工厂又由死去的丈夫操持,自己无从了解。因此,所言何“事”,自然也就死无对证。重盛团队的“合谋”推断就此“流产”,首次庭审如期结束。关于所谓何“事”及其与三隅、美津江“合谋”关联性的对话,也就戛然而止。如前所言,此情形正中法官、检察官下怀。也即是说,“事”未明确,但在剧本内却不了了之,这种完成性,源于美津江的模糊话术,而止于法官的判决,在事实上已无再探讨的可能。因此,重盛团队不得不再折回到“仇杀”推断上。
对于对话未完成性而言,美津江这一角色的杀伤力还在于其对咲江言论自由权力的限制甚至狙杀,如在庭审之前,她曾明确警告咲江“不要说什么多余的话”,而当咲江问及“多余的话指的是什么”,她仍旧采用模糊话术,只简单地说:“工厂的事,爸爸的事”。显然,咲江对于工厂造假的事是心知肚明的,对于“爸爸的事”更是不堪回溯的,其内心充满着倾诉的欲望,认为母亲与其担心,不如把“真相”说出来,而且直言自己“到今天为止没有和别人说过,才更痛苦,并不想像母亲那样,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如巴赫金所言“只要人活着,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他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说出自己最终的见解”,咲江的“痛苦”在于不能说,其未完成性表达的可能性被母亲美津江所限制甚至狙杀。重盛团队的出现为她纾解难言之隐提供了可能性,但却因为三隅翻供而使得其不得不配合重盛的“法庭战术”,再次将呼之欲出的“真相”压抑于内心,随着三隅被判定死刑,这一隐情成了在法律程序上“终结了的东西”。虽说“世上还没有过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着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头,而且永远只在前头”,但对话未完成性的前提是自由,对于如咲江一样连言论自由都受限制的人而言,其对话的未完成性只存在于理论之中,因此,在片中她不得不忍受对话未完成性异化所带来的痛苦。
反过来说,美津江模糊话术及咲江言论自由被限制,虽然导致了对话未完成性的异化,但这对于好奇的观众而言,则是值得玩味的。这也是《第三度嫌疑人》“悬疑”建构的重要内在机理之一。
结语
《第三度嫌疑人》或许没有道出三隅案的“真相”,但却真真切切地道出了三隅们的生活真实,更描摹出了日本社会现实及当代人性样态之一隅,模糊而又清晰。若将之视为一个独特的“悬疑”文本,那么,其结构便类似于一个“块茎”,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进入,但所得结论又迥然,这便是这一银幕作品特有效果,而被异化的对话便是这一效果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也是是枝裕和引导观众思考社会问题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