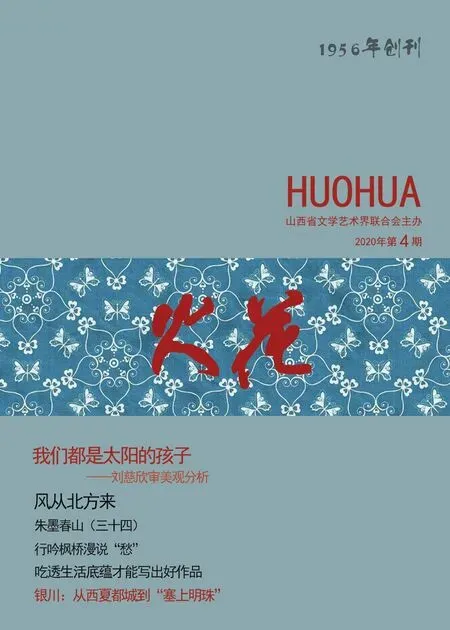吃透生活底蕴才能写出好作品
杨占平
前些年,在市场经济大潮和享乐主义思想的强烈冲击下,文学写作的时尚化、商业化成为一种趋势,一些作家把文学创作当成了五光十色的浮华世界,人文精神在文学作品中失落了。在这种环境下,一度时期现实主义作品比较难写也难出版;纵使写出来、出版了,经济效益也不理想,不大能销售得好。特别是一些出版单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根本不重视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版与发行,每年勉强出版几部,仅仅是为了参加评奖;而那些感官刺激强烈的作品,容易出版且卖高价,有赚头,便争着出。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是因为当今文艺界存在一种轻视生活体验的倾向。一些作家在创作观念上过于看重自我,表现出来就是:一是只关注缺乏普遍意义的个人意识,强调个人内心世界高于一切,作品倾诉自我体验,展示身边生活琐事,才是艺术,于是,出现了“用身体写作”之说。二是拒绝活生生的现实感受,追求玄妙的所谓“哲学境界”,在他们眼中,什么国家利益,什么民生疾苦,什么民族大业,都是无关紧要的,只有超越现实,在理想的层面上探讨人性、人情,才是高尚的。三是过分依恋历史,热衷于考证或戏说某些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甚至按照个人喜好,随意更改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以此获得所谓“卖点”。四是把写作技巧和表现形式置于生活内容之上,内容只是为写作技巧服务,社会意义、文学价值都是技巧的附属,根本不去审视当代人的基本命运。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写出来的作品浅薄,不接地气,广大读者不喜欢。
有位作家在一家工厂体验生活时,工人朋友对他说:“现在是钱的天下,头上顶着钱不怕雨不怕风,手里摆着钱不怕冷不怕热,好多作家都写赚钱的东西去了,你还跑工厂干嘛呀!”一些作家受名利思想的驱使,急于成名和得到经济回报,一旦抓住一个题材就洋洋洒洒,下笔千言,草草从事。其结果,自然没有挖掘到现实生活中真实和美好的东西,更谈不上感染力。
这类作品的严重不足之处,是对现实生活中丑陋现象采取某种认同的态度,缺少向善向美之心,人文关怀在他们的心中没有地位。他们虽然熟悉现实生活的某些现象,但他们对现实缺少清醒的认识。同时,这些作品既没有触及改革攻关中症结所在,也没有揭示现实中造成人文关怀缺失的深层社会原因,尤其是价值观上的原因。
虽然注重深入生活,坚持现实主义作品创作的作家越来越受到读者的认可,但是,有时还要承受一些压力,有人会嘲讽说:这种作家就只能写出这类“歌功颂德”的作品来。面对如此议论,意志薄弱一点的作家,就只好跟着赶时尚化、个人化潮流,采取远离普通大众,走向纯粹个体本位的创作态度。于是,在当代文学创作越来越宽容和体现个性化以后,描写社会现实矛盾和问题,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写作选择,在少数作家那里似乎成为“不真实”、“虚妄”等的对应物。对他们来说,好像只有个人所想象到的一切,才具备可靠的真实性。也有些作家愿意涉及底层生活,但却缺乏心入的感情,缺乏真切体验,叙述把握上力不从心,只能是以表面现象写作,无法展示底层人民的内心世界,很难将底层人民的命运与社会矛盾结合起来;或者是只能在虚构和想象中刻画人物,不能不落入俗套,显得特别虚假。
我希望文学界能够确实改变不正确的观念和作法,真正深入到生活的核心里,让各自的作品能有突破,这是文学发展和广大读者的期盼,也是广大作家应当有的担当。不过,我们也明白,任何一种突破的面前都会有艰难的过程,都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因此,有志于深入生活,保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首先应当正确认识时代,把握生活的本质。追踪着现实社会的前进步伐,描写了当代生活的人物与事件,也不等于就体现出了时代的本质,还需要有追求本质的自觉意识和深度写作的方式。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发展的时代,一个务实的时代,虽然现实社会中还存在某些落后和腐朽的东西,那些物欲和情欲横流的生活场景,那些颓废、悲观、无奈的情绪,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局部和表层存在;但是,它们并不是时代生活的主流和方向,对其一味地涂抹、赏玩,将会堆积生活表象而泯灭现实的本质内涵,是会曲解或者误解我们的生活的。我们的时代还是一个负重行进的时代,变革中的多种矛盾交织,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还有待我们去克服和解决。
其次,要独辟蹊径,突出自身特点。只有以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科学的批判精神,以独特的风格和艺术特色,才能在当代文学之林中独树一帜。突出作家个性和作品特色,是文学作品取胜的根本。要着力表现执着的追求和渴求变革的火热情怀,表现古朴的人情世态和追求文明的不懈努力,表现底层人民心理的蜕变、矛盾和冲突。要善于捕捉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始终坚持严肃的创作态度,关注弱势群体,探寻人的内心世界和深层心理,以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感,做人民心声的代言人,做时代进步的记录者。
我们山西文学界一直有一个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百姓命运,敢为人民代言的优良传统。赵树理曾经说过:“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他“宁可不上文坛”,甘心当一个“地摊”作家。全国解放后,赵树理随工作单位进了北京,有了固定的收入,工资待遇都不低,买了房子,接来了家属。按说,他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况且,他从二十年代起已经颠簸了几十年,也应当享受城市相对安逸的生活了。可他骨子里流着的农民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合。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的状态和农民的生活。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15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如鱼得水般愉快。他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操心庄稼收成好坏,研究农业政策的实施,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农村政策有误,农民利益受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记着的仍然是农民过着艰苦日子。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没有几位像赵树理这样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这样期盼农民过上好日子的。
马烽也说过:“我写作,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中国农民和农村干部。”如果没有去他熟悉的农村与农民生活上一段时期,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同农民的心灵融会贯通,就会感到不踏实,写出的作品总是不满意,或者是失败之作。他一有机会就去农村走走。他不用记者采访式方法,总是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同干部们研究工作,同大娘大嫂们拉家常,同小伙子们说笑话,甚至还调解家庭纠纷。五、六十年代,他骑上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饲养房、土窑洞、工棚、破庙都住过;农民也从不把他当作家、当外人看待,亲切地称他“老马”。为了更好地体验生活,他曾到汾阳县挂职当过两年县委副书记,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1958年前后,我在一个县里担任了二年县委副书记,虽然是个客串书记,但有一些问题也不能不管,担子压在肩上,你也就不能不去过问。实际上也就是工作逼着你去熟悉人,去了解生活。而且那时候我年纪还轻,身体也好,下乡经常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带着行李卷,走到那里就住到那里。到水利工地上,和民工们一块住破庙,滚草铺,也是常有的事。”
正是有了这段经历,二、三年功夫,马烽写出了十几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如《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青春的光彩》《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难忘的人》《太阳刚刚出山》《老社员》《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其中的几个作品当时就轰动一时,在读者中的反响非常大,几十年以后也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应当说,马烽的这些创作实绩,在当时的文坛上是非常突出的,在他个人创作生涯中也是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他与赵树理、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文学界的一个热点,也是后来人们称他们为“山药蛋派”的重要依据。
“文革”以后,马烽年岁大了,他不再骑自行车,坐上了汽车,但他发挥汽车的优势,尽量多跑一些地方,多接触一些人,真正了解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的思想。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约他和孙谦写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于是,两个人又像过去一样,结伴下乡,感受生活。他们跑了山西省内的交城、文水、汾阳、临县、榆次、平定等县,广泛接触农村基层干部,走访社员群众,实地考察了好几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同时,结合他们几十年来对农村生活的了解,经过深思熟虑,写出了反映县委书记朱克实拨乱反正、解决冤假错案、大抓农田水利建设故事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剧本改名为《泪痕》拍成电影后,举国上下轰动一时,差不多家喻户晓,获得了当时各项电影大奖。80年代后期,马烽写作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葫芦沟今昔》,就是在下乡时发现,当时大多数人对于责任制之前的农田基本建设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学大寨”的产物,不愿承认责任制以后一些农民的富裕正是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结果使本应属于经济领域的农业生产又落入了政治窠臼。马烽对此问题认真思考一番,就有了《葫芦沟今昔》的构思。他在这个小说中,用当代意识和历史态度观察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发生的变革,从现实与历史、局部与全貌、表层与深层的有机统一中,揭示农村改革的某些本质问题,希望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一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事件,比如“学大寨”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些工程属于政治运动的产物,确实是劳民伤财;有些工程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像葫芦沟那时候搞的治理乱石河滩工程,就是八十年代走上富裕路的基础。
赵树理和马烽他们关心的是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大作家。现在的山西作家中,关注现实的传统仍然延续着,因为他们都明白一个真理:千万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脱离时代,脱离人民。只有深入现实,扎根人民,吃透生活,才能了解广大群众需要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知道如何创作他们喜爱的作品。同时,大家都深刻感受到,可以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许多来自生活、来自生命的表现方式,从而使各自的作品更鲜活,更生动,更有吸引力和震撼力。